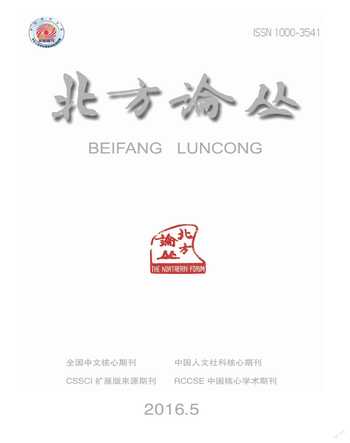论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
2016-06-09李永刚
李永刚
[摘 要]兰克的历史主义以“求真”为基本旨趣。兰克从主客两个角度来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但在这一经验性诉求背后隐藏着一先验性诉求,即“理解”上帝。对兰克而言,历史主义本质上是经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经验性是先验性指导下的经验性,先验性是通过经验性而达到的。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使其处在思辨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中间位置,构成了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
[关键词]兰克;历史主义;经验性;先验性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104-05
Abstract: The historicism of Ranke regarded the Truth as the basic purpose, and ensured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tow angles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ere was a transcendental appeal at the back of this empirical claim, namely to understand God. To Ranke, the empirical and transcendental were unified in historicism in essence, namely, the former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later, and the later is achieved by the former. The duality of historicism in Ranke made itself at the middle of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ositivism, which constituted the focus of debates on historical thoughts.
Key words:Ranke;Historicism ;the empirical;the transcendental
兰克以其“客观性”原则为历史学争得了自主地位,被尊为“历史科学之父”。在19世纪的历史主义潮流之中,兰克独树一帜,既拒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历史哲学,又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思辨历史哲学;他既奠基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基础之上,又与浪漫主义的历史观有着明显的差别。兰克的历史主义以“客观性”为基本旨趣,但在其背后隐藏着“理解”上帝这一先验性诉求,因而其历史主义本质上是经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并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语文解释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从而成为了融解释学入历史主义的先驱。本文试图从经验性与先验性两个角度解读兰克的历史主义思想,并挖掘其历史主义中蕴含的解释学思想。
一、兰克历史主义的“客观性”诉求
兰克在其成名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中明确宣称:“历史向来被赋予评判过去、教导人们以利于未来的职能。本书不敢期望如此崇高的任务。它仅只想显示过去本质如何(how it essentially was)①。”[1](p86)这就是后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如实直书”原则。作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兰克从主客两个角度竭力实现他所追求的客观性原则。从客观方面说,首先必须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为此,兰克将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作为历史著述的主要史料来源:“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正在到来:那就是,我们编写近代史时,不用再依靠甚至是一些当时历史学家的记载。除非,那些历史学家确实对事实具有亲身的体验和直接的感受,那么他们的记載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完全不必理会那些依据与原始资料相距甚远的材料而写成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依据的材料不是当事人的记述,不是真正原始、未经篡改的第一手档案材料。”[2](p.97)兰克的皇皇巨著都是建立在档案文献、事件当事人的回忆等第一手材料基础上之上的,这使其著作具有了很大的可信性。其次,兰克将语文—批判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之中。这一方法并非兰克首创,在此之前,尼布尔已在其罗马史研究中运用了这一方法,兰克的贡献在于将其发展为一套可教可学的方法——“外校法”,主要是通过对关于同一事件的大量记述和档案记载的比对,并联系其作者的品质、与事件的关系、获得知识的机会等来证明资料的权威性。此方法的运用集中体现在作为《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附录的《对近代历史学家的批判》一文,正是这一部分为兰克赢得了同行们的尊重,也由此而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兰克对档案文献的重视和善加利用开时代风气之先,并为后世历史著述树立了楷模,正如古奇所说:“他不是第一个使用档案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在他开始写作时,著名的历史家都相信回忆录和编年史是首要的权威资料。而在他停笔时,每个历史家,无论后来成名的或没有成名的,都已学会了只满意于当事者本人,以及同他所述事件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的文件和通讯。”[3](p.215)
从主观方面来说,历史学家在历史著述中须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兰克一再强调历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之一就是“不偏不倚”:“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它们存在的根基,并完全客观地描述它们。”[1](p.14)这也就是“客观性”的本质体现。但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其“前见”或“历史性”进入史料的,兰克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明确主张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历史学家“自我消失”:“假如可能的话,我希望自我消失,仅只让事情本身说话,仅只让强力本身显现。” [4](p.48)如此,最“客观的”历史著作,或者说历史的真相就在于史料的自动排列,连贯而成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兰克本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这却是历史学家应该追求的终极目的,历史著述应以此终极理想状态为依归。兰克是很乐观的,认为我们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最终结果终究是可期待的。同时,在历史写作中,兰克一贯秉持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作为一名新教徒所撰写的《教皇史》就是最好的体现:“这本著作既不是有所偏袒,也不是因为出于某种考虑而对罗马教皇予以揭露,它完全只是全面而公正、不偏不倚研究的结果而已。” [2](p.62)
兰克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于它收集、发现和渗透于(史料);它之所以是一门艺术,在于它再创造和描述已经发现和经过检验了的(史料)。其它科学仅仅满足于记录已发现的东西;历史学需要一种再创造的能力”[1](p.8)。这段话表明了以下三点:第一,艺术性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这种艺术性使历史学区别于其他科学。历史写作并不是学者们的自娱自乐,历史著作的根本价值在于供大众阅读,以发挥某种宗教或政治功能,这是自中世纪以来,历史学一直肩负的使命。中世纪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服务于宗教理论的证明和宣传;近代史学则是宗教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相互斗争的战场;启蒙运动以来的“新史学”则是为了总结有用的教训,“是用前例来教导人们的一种哲学”[5](p.76)。兰克史学同样负有某种使命,即把欧洲描述为列强之间对抗与均势的统一体,因此,历史著作必须具有可读性,这就必然不同于仅供同行学者阅读、检验的实验报告。第二,历史著作要具有文学艺术性,但它绝对不等同于历史小说,因为后者掺加了大量的虚构和幻想,而前者则严格根据历史事实来撰写,“我们想要原原本本的真相,不需要任何装饰。这种真相可以通过对具体个体的研究而获得,余下的由上帝去考虑!但是在历史当中,即使是在最细小的事件当中,也没有诗情画意,没有富有创意的想象”[2](p.124)。这表明,历史著作的文学艺术性是第二位的,是服务于客观性、科学性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兰克的历史著作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就像吉本一样,我们可以将兰克的著作当做文学作品来赏析,只不过这一文学作品也提供了历史信息而已,兰克这位艺术家是用历史事实来从事艺术创作的”[2](导言,p.38)。第三,兰克认为,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于历史学之中,“历史学必须同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两者之一不存在,历史学就不会成为两者之另一”[1](p.9)。这表明了历史学的独特地位:一方面它不同于其他科学,因为历史学有一种再创造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这就是兰克一再强调的对史料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艺术,因为后者关注于理想领域,而历史学关注于“实在”,但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说,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体。正是这种历史观决定了兰克历史写作的旨趣:既汲汲以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又力图保障历史著作的可读性,但毫无疑问,前者是首要的。
兰克之所以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这是由其历史主义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历史主义强调个体性的价值,强调重返历史处境而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那么,如何真正落实历史主义的基本诉求,这就需要在历史研究中,严格遵循兰克的客观性原则或“如实直书”原则,因为任何历史理解和评价都奠基于历史真相之上,而兰克的客观性原则就是为了重现历史真相。所以,在历史学实践中,客观性原则构成了历史主义的根基。当然,这一原则受到了广泛的推崇,同样也受到了大量的攻击。德罗伊森就称这种客观性为“太监式的”,不合乎人性的,因为人性必然是有所偏党的,“以最客观的方式,以最实事求是的方式表達事件,最主观的色彩会呈现出来”[6](p.96)。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称之为“冷血的客观性”(bloodless objectivity),它是与“真正的历史感相矛盾的” [4](p.102)。但这并没有否认“客观性”原则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他们并不反对“客观性”原则本身,他们所强调的是由于人本身的历史性,历史学不可能真正实现兰克所热切期望的绝对客观性,它不过只是“那高尚的梦想”(彼得·诺维克语)而已,也就是说,他们最终所反对的仅只是兰克的乐观主义态度而已。
二、兰克历史主义的“先验性”诉求
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并不是兰克史学思想的全部,相反在其背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目的,即对上帝的认识和理解。兰克与黑格尔一样,都坚持表现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外在现象是内在本质的体现,由此,兰克所宣称的历史学“仅只想显示过去本质如何”未必是自谦之词,因为它体现了兰克历史研究的伟大抱负,即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客观研究而探究历史本质,也就是体现在人类历史之中的上帝,此即兰克历史主义的先验性。
兰克坚持泛神主义的观点,认为:“所有的历史中都有上帝在居住、生活。每一项行动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也在宣扬着上帝的名字,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我认为是,历史的伟大连续性。”[2](p.324)正是从“证明上帝存在”这一先验目的出发,兰克的历史观才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世界历史的内在目的论。历史学家总是根据某一“目的”来选择和排列史料的,关键在于确定这一“目的”来自何处,如果它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头脑,是历史学家赋予历史本身的,这就是外在目的论。兰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烈拒斥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认为它外在地为历史设置了一个先验目的,是用非历史的态度看待历史,相反,真正的历史目的是内在于世界历史本身的。兰克之所以主张历史学家的“自我消失”,其意义就在于消除历史学家自身目的的强加,以便使历史本身的目的起作用。历史“目的”是通过历史行为或历史事件的“意义”来体现的,符合目的的便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历史“意义”是通过历史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后果”来体现的,因为成功或失败决定了意义的实现与否。所以,可以说,历史的“目的”是由“后果”体现的。如此,也就可以理解兰克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埋首于无人问津的原始档案之中,因为历史研究就是为了揭示历史事件或行为的后果和意义,以便真正把握历史的目的。
第二,世界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统一体。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历史是骚乱、冲突、朝代更迭等无数偶然事件的集合体,但在兰克看来,在偶然的历史现象之后隐藏着必然的联系,即世界历史通过各种冲突而走向均衡与统一的进步历程:“它们(文明的进步,真正精神的、创造性的力量,生命本身,道德精神等)展现、获得这个世界,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自身,并且相互之间进行斗争、妨碍和压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演替中、在它们的生命中、在它们的衰败与复兴中包含着不断增强的充实性、不断提高的重要性和不断拓展的范围,隐藏着世界历史的秘密。”[1](p.52)但兰克并不完全认同启蒙时代的进步历史观,他承认历史上存在着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以及把不同民族和个体引向人类理念和文化理念方面,但在人类的文化、道德和精神等方面是没有整体的进步可言的,因为文化是随着社会、政治进步而发展的,但我们很难说某一时代的文化一定高于此前的文化。以历史学为例,虽然我们现在获得了更多关于过去的知识,但任何人都不敢宣称自己是比修昔底德还要伟大的历史学家。这种进步观反对两种倾向,即经验主义的单纯罗列史料的观点和黑格尔的普遍进步观念,兰克认为两者都是错误的:前者仅是“为史料而史料”,后者则预先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兰克的进步观是具体的历史研究的结果。
第三,思辨—神学观念指导下的历史主义。兰克把历史主义观念落实到历史研究之中,或者说,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来证实历史主义的基本观念,但应该承认的是其历史主义观念背后隐含着思辨—神学前提。他认为:“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其价值并不在于它创造了什么,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在于它自身。”[1](p.21)这就奠定了历史主义的先验基础,即每一时代都与上帝“直接”相关联,正因为如此,所有时代在价值上才都是等值的,没有那一时代低于或高于另一时代,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必须深入每一时代,从其自身历史处境中理解其意义和价值。每一时代的“主导理念”,或者说“时代精神”,就是上帝与此时代“直接相关联”的体现,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这一“主导理念”或“时代精神”,但不是在精神自身的发展历程中,而是在其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展现它,也就是说,兰克历史主义的先验性,即主导理念或时代精神,是从历史的经验性研究中赢得的,这是兰克历史主义区别于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根本之处。同时,正是由于主导理念或时代精神是绝对上帝的体现,兰克历史主义才不会陷入相对主义困境,相反,这本质上是一种以绝对主义为基础的多元主义。
第四,世界历史的“个体”与“一般”。自赫尔德以来,生命观点被广泛地应用于历史理解之中,兰克继承了这一观念,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生命整体,而每个个人、民族、国家作为“个体”都是这一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兰克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历史、理解上帝,但我们不能采取从一般到一般的哲学研究方式,而只能采取从个体到一般的历史学研究方式,因为“我们确实可以从容不迫、放心大胆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然而却不存在任何一条道路可以从一般性理论通向特殊的观点”[2](p.138)。由此,历史学可以,也必定会通过对个别事实的探究,而提升到一种对事件的普遍观点,从而把握事件之间的客观联系,这是兰克所主张的正确认识世界、理解上帝的道路,但它并不是纯粹经验主义的道路,因为兰克的客观主义研究是以先验的、普遍的观点为前提的,“将特殊联系于普遍不会损害研究。没有普遍的观念,研究将是贫乏的;没有具体的研究,普遍的观念将蜕变成幻想”[1](p.25)。这就充分证明了兰克历史主义经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经验性是先验性指导下的经验性,先验性是通过经验性而达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兰克的历史主义同样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且是一种泛神主义的历史哲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黑格尔,而兰克之所以一再明确地拒斥黑格尔,就在于两人走了不同的道路,黑格尔走了哲学的道路,而兰克走的是历史学的道路。但这两条道路在理想状态是合一的:“如果哲学是其所应是,如果历史学绝对的清晰和完整,那么,二者将彼此完全重合。”[1](p.15)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历史学与哲学、历史主义与思辨历史哲学是统一的。
三、兰克历史主义的“理解”观
在方法论上,兰克除主要运用了来自尼布尔等人的语文—批判方法之外,解释学作为一种隐性的方法也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兰克本人对解释学并没有自觉的意识,也没有使用“解释学(Hermeneutik)”一词,但必须承认的是,兰克的历史主义思想处处闪耀着解释学的光辉。
蘭克的解释学来自于其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和与施莱尔马赫交往。在大学期间,兰克主修的课程就是古典语文学和神学,接受了严格的古典语文学的训练,而且其博士论文以研究修昔底德为选题。毕业后的最初7年,在奥德河法兰克福高级文科中学任教,教授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学和历史。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同施莱尔马赫交往甚密,这既得益于两人共同的宗教信仰,也得益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相同态度。虽无明确的证据,但这些经历足以表明,兰克对解释学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同时,兰克对历史学的独特定位也使其走向了解释学,“如果历史学希望作为一门自主学科而抵制哲学,并且不会降低为实证经验主义的无意义性,历史学就必须理解自己为解释的科学(a hermeneutic science)”[4](p.46)。
解释学方法服务于兰克的历史主义思想,根据历史主义的二重性,我们也可以将解释学区分为经验性与先验性两个层面。从经验性的层面来看,解释学是应用于具体历史研究的方法。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不在于收集史料,而在于理解,“历史学的目的与其说是收集事实和排列事实,不如说是理解事实。历史学不只是单纯地依靠记忆,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首先依靠批判的理解”[1](p.77)。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解”?因为兰克认为,历史学不满足于仅仅记录历史现象,它具有一种“再创造”的能力,即“重构”的能力。对于“重构”,施莱尔马赫是从文本理解的层面来论述的,认为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个性和精神,解释者就必须通过语法的和心理的解释而返回到作者当时的处境,与作者“处于同一层次”,以便重构作者的个性和精神。兰克所要理解的不仅仅是文本作者,而是历史人物和事件,这同样需要历史学家抛弃自身前见,返回到人物或事件的历史处境,从而做到“真正地”理解他们。这也解释了兰克客观性原则的两个方面,即直面第一手史料和“自我消失”,两者都是为了能够“重构”真实的历史事实。
就具体的解释学方法而论,兰克将来自于语文解释学的整体与部分解释学循环的方法,扩展到历史理解之中。历史研究发端于对具体人物或事件的客观认识,但要真正理解某一人物或事件,须将其置于民族、国家或时代等相对的整体之中,也就是从“主导理念”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具体人物或事件;同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历史细节被挖掘出来,这又加深甚或修正了对“主导理念”或“时代精神”的理解。历史学正是在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中得到发展的。兰克之所以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即一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与其它国家的交流、对抗中而存在的,因此,一国的某一政策也就不能仅仅从内政方面来理解,而要置于国际关系整体中加以理解。
从先验性的层面来看,兰克的历史主义弥漫着上帝的身影,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就在于“理解上帝”:“当我们揭示真相,剥去它的外壳,展示它的本质之时,这一过程恰巧也展示了那蕴藏在我们自身的存在、内在生活、来源、呼吸之中的上帝,至少是证明了上帝他的存在。”[2](pp.8-9)在这样一种泛神主义的理解理论中,世界历史被理解为大全生命,即上帝的显现,“理解”就是在世界历史现象之中“体认上帝”,或者说“分有上帝”的过程。那么,如何实现对上帝的理解呢?兰克认为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也就是揭示历史真相,这是前提和基础,但不是关键性的,关键性的在于第二步,即“直觉”。正是借助于直觉式理解,历史学家能够探知历史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精神联系,而上帝就“存在于”这种精神联系之中。那么,为什么能够“直觉”精神联系呢?这里的理论假设在于,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与上帝具有同质性,这是维柯的人与历史具有同质性理论的神学化的表现形式。正由于历史学家的根本职责在于理解上帝,兰克认为,历史学家也就是牧师,他们像牧师一样,承担着神圣的职责,负有神圣的使命。反过来说,正是这一神圣的职责保证了兰克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历史学家的“历史性”、前见,并不必然就是客观性的妨碍,反而可能会是助力,兰克就是典型体现。
在兰克这里,“理解一词就具有了其近乎宗教性的色彩。理解就是直接地分有生命,而无需任何通过概念的思考中介过程”[7](p303)。这种没有任何客观方法而言的天才式的直觉理解,是浪漫主义精神在兰克身上的集中体现,其后来者,如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对此展开了激烈批判,他们的目的就是祛除“理解”概念上的泛神主义色彩,将其作为方法论概念来使用。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但更主要地在于他们将解释学更多的是看作一种可应用的方法,而非一种形而上学。
四、结语
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使其处在思辨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中间位置:仅从其经验性而言,兰克毫无疑问是一位经验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历史科学之父”的称号也更多地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仅从其先验性而言,兰克毫无疑问是德国观念论哲学的继承人,与他一再拒斥的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并没有太大差距。正是这种二重性奠定了兰克在历史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也成为了史学争论的焦点,正如伊格尔斯所说:“的确,差不多每一种有关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的德国历史思想或美国历史思想的重大讨论都集中在或至少牵涉到是接受还是拒绝兰克的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问题。”[8](p.154)但应该承认的是,兰克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潜心于档案文献的历史研究者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他并没有系统论述其历史观和哲学观,而是散见在其历史著作的各处,可以说他对于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其后学者,像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才对历史方法论有自觉的意识。
[参 考 文 献]
[1]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M]. edited by Georg G. Igg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德]列奥波德·冯·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M].易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The Discovery of Historicity in German Idealism and Historicism[M]. edited by Peter Koslowski. New York, Springer, 2005.
[5][美]卡爾·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M].何兆武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M].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系长江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