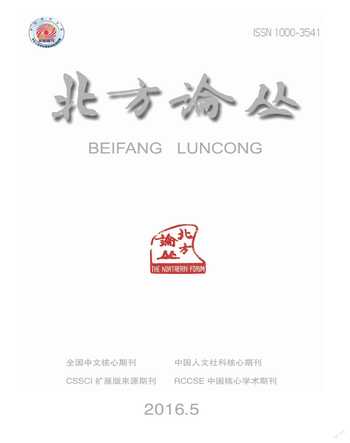利玛窦佛教观的转变及影响
2016-06-09周黄琴
周黄琴
[摘 要]基于入住中国之考虑,利玛窦曾通过“以僧自居”之方式获得中国官方与百姓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却越来越感到早期所使用的佛教权设不仅毫无意义,反而成为传教途中的一大障碍,致而他果断采取了“弃僧附儒”之策略,并公开对佛教发起攻击。然令其始料不及的是,此举虽然看似合理,但却给基督教在中国日后的传播自设了更大的障碍,乃至一度陷于被驱逐中国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利玛窦;辟佛;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81-07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ide China, Matteo Ricci had ever acted himself as a Buddhism so as to be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But as the time fly, Matteo Ricci had even more recognized the idea he used in the past had no significance, but acted as a hinder to his missionary work, so he had resolutely used the strategy of abandoning the Buddhism and following the Confucianism. The strategy had been seemed reasonable, in fact, it had acted as the more great hinder to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Key words:Matteo Ricci; criticize the Buddhism; influence
眾所周知,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自1583年9月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到1595年更换儒服之前,均以“僧人”自称。虽然此举一度获得了中国官员与百姓的认可与接受,以至可以入住在中国,但令人诧异的是,在随后的传教中,利玛窦不仅没有认识到佛教这个媒介在传教中的重要意义,相反看到更多的是佛教在传教过程中的阻碍作用,致而放大差异,并公然发起攻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来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为了更好地使天主教立足于中国,理应借助中国各方力量来推行其说,那为何素以理性著称的利玛窦既敢对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一千多年之久的佛教发起攻击呢?对于此举,一些天主教徒都难以理解,并提出质疑,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引起传教士们的反思,亦没阻止天主教与佛教之争。对此,本文力图作一定的探究,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利玛窦当时之心境与意图,以及其后所产生的影响。
一、“以僧自居”
尽管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来看,文中不仅没有彰显“以僧自居”之行为,反而是充满了大量批佛与贬僧之举。对于如此反常之举,我们只要熟知此作乃利玛窦晚年的一部追溯性作品,即可一目了然。
首先,从书信的记载来看,晚明早期神父曾以“僧”之方式获得进入中国居住之权利。如1583年利玛窦在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书信中指出:“知府对他们非常怀疑,而且不可获得在那里居留;但知府的上司,即两广总督曾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他们答应说‘是之后,便准许他们在那里居住,并提供食宿;尤其神父们声明愿作中国皇帝的顺民时为然,他们应该更换衣服,神父们以为这样很好,于是他把北京和尚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是他所能恩赐最体面的服饰了……对钟表谈得不多,因为它是西欧式与中国的更漏大不一样,而且分点也和我们的不一。他们所惊奇的是我们钟表是自动的,会报时间,有长短针把时间指出;但这不是让我们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他所赐给罗神父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庙宇中,非常讲究,不曾受中国官吏的往访与打扰……两广总督于今年初,伴同其他官吏进庙烧香礼神。”[1](p.40)而随后作为助手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完全因循罗明坚所开启的“以僧自居”之范式。
其次,从《天主实录》的记载来看,作者不仅多次自称为僧,而且还使用了佛教用语,体现出了很强的“以佛传耶”的内在意图。《天主实录》为罗明坚与利玛窦于1584年撰写的第一部中文作品,但就文中内容而言,不仅在引文的结尾与正文的开头处分别使用了“天竺国僧书”“天竺国僧辑”等字眼,而且在正文中还有“解释僧道诚心修行升天之正道”之篇章,以及引文中还多次“以僧自称”。如其云:“僧虽生外国,均人类也,可以不如禽兽而不思所以报本哉?今蒙给地柔远,是即罔极之恩也。然欲报之以金玉、报之以犬马,僧居困乏,而中华亦不少金玉宝马矣。然将何以报之哉?惟以天主行实,原于天竺,流布四方,得以捄拔魂灵升天、免坠地狱……僧思报答无由,姑述实录而变成唐字,略酬其柔远之恩于万一云尔。”[2](p.4)甚至到1595年,利玛窦曾因《天主实录》中的“僧人”称谓与大量佛教用语之存在,竟“下令毁版”,不再使用此书。直至1627年,传教士重编《天主实录》之时,则对其中的佛教用语做了一些删改。
再次,从现有的其他作品内容看,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皆曾“以僧自居”。据《中国札记》的记载,利玛窦虽没有直接陈述“以僧自居”,但文中内容仍不乏折射出他曾以僧自居过。如其云:“建筑在附近的庙宇,它那名声吸引着大群的人,包括城市的高官在内。当官员们想拜访我们时,他们便以庙宇为借口;因为访问普通市民,特别是访问外国人,被认为有失他们职位的体面。”[3](p.215)而且在1588年,当利玛窦遭受广州一批耆老们的控告时,他还是以来自“天竺国”的僧人,而非澳门之地进行辩诉。
同时,据平川祐弘的《利玛窦传》、罗光的《利玛窦传》、裴化行的《利玛窦神父传》之记载,无论是面见广东海道,还是肇庆知府时,罗明坚等早期神父皆自称为来自“天竺”之僧人,而且还以“僧”之身份,进行各种法事活动。正如裴化行在《利玛窦神父传》中指出:“弘扬佛法者来自西土,新来的这些人也是来自西土——或称‘泰西国,不过,中国人分不太清楚。因此,他们的传道活动统统得按佛教的模式进行。”[4](pp.119-120)正因如此,罗明坚的浙江之行与日后利玛窦的英德、南雄之行,皆被安排在寺庙里居住,并以佛教仪式进行相应的法事活动。更为甚者,据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的而为利玛窦于1588年所起草的罗马教皇致万历皇帝的“国书”所载,教皇不仅在开头与结尾处皆以“都僧皇”自称,而且在文中还把传教士称为“僧”或“儒僧”。如其云:“先年曾委数僧,游至盛国,闻君明臣良,相与翊景运,文风丕振,苍赤宁生,经书家喻户晓,猗欤称綦隆矣。惟天主上帝,其事未解明否,今再令上僧四人……并旧住三僧,二德、玛窦、安东,代生趋拜足下,外具敝国土物为贽,薄将鄙诚。”[5](p.2)
最后,从天主教内部的批判与辩护声来看,亦可佐证利玛窦曾“以僧自居”过。如裴化行在《利玛窦神父传》中,甚至引用诺比利神父的十一项论证,为利玛窦穿僧服之举进行辩护。如其所云:“我们坚持引述诺比利神父的辩诉,是为了表明,传教士们在服装上同化于和尚引起了许多微妙的问题;况且,必须指出,后来,在写下来之前,利玛窦早已至少在实践上——即使不是在原则上,放弃和尚服装。也是在以后,宣教圣部会议决议禁止传教士服装等同于佛教僧侣。”[4](p.86)
综上所述,尽管利玛窦曾“以僧自居”过,但我们更应明白的是,此举并不是他真正被佛教思想所折服,而仅是把佛教当作一种进入中国与秘密传教的权设而已,其最终目的反而是要最终战胜与取代佛教之地位,所以,虽披着佛教之形,但在他的骨子里实际上是蕴含着强烈的排佛冲动。如此矛盾的心态亦在《天主实录》中得到了体现,即既自称僧人,但又存在着批佛之舉。其实,这种矛盾的状态不仅为利玛窦日后的传教活动带来了很多麻烦,但亦为其“由僧到儒”的身份转换奠定了基础。
二、公然辟佛
虽然对于佛教,其实罗明坚早在《天主实录》中就发起了批判。在他看来,不仅“释迦经文虚谬,皆非正理”,而且世人求弥陀释迦而甚灵验之举亦是“邪魔恶鬼潜附佛像之中诳诱世人”而已。如既曰:“杀牲者魂灵不得升天,或魂归天堂者复能回生世界,及地狱充满之际者复得再生于人间”,又曰:“禽兽来听讲法亦得以成其道果”。而且虽允诺后人诵读《大乘妙法莲花经》则可获得天堂受福,但若“以理论之”,则将陷入自相矛盾与荒诞之境地,即“使有罪大恶极之徒,家有钱财,买经诵读则得以升天受福;若夫修德行道之人,贫穷困苦,买经不得,亦将坠于地狱”[2](pp.8-9)。然而,对于当时中国居士或僧人而言,并没有引起足够之重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天主实录》中存有大量自称为“僧”之举,因而易导致一种误解,即为佛教内部的自我批判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心学、庄学的兴盛,以及僧界的堕落,以至晚明俗界与僧界都存有批佛之举,特别是狂禅者更肆无忌惮地批佛。同时,还有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罗明坚时期的天主教在中国还处于极其微弱的状态,社会影响很小,致而没能引起僧人与居士的重视。
但是,自利玛窦被遣送到韶关之后,其反佛的意向与行为却越来越明显。首先,在日常行为上,利玛窦越来越想凸显自身与僧人的差异性,并力图撇清与佛教的关系。其具体表现为:第一,利玛窦既拒绝中国官方为他已定的居住于南华寺之安排,而且在参观南华寺时,亦拒绝礼敬寺庙里的偶像,甚至对六祖真身也缺乏敬畏之心;第二,利玛窦不仅具有强烈的“弃僧为儒”的转换身份之愿望,而且于1595年则公然弃僧服,换儒服;第三,为了消解中国人的疑心,起初利玛窦在传教方面还是极其谨慎小心,但到韶关后却要求受洗之教徒公开毁弃佛像、烧毁佛书;第四,对印度的称呼上,亦由原有的“天竺国”之雅称转向了“身毒”之贬称。
其次,在书信方面,利玛窦逐步走向了贬损僧人形象之面向。如在1584年9月13日致罗曼的书信中,利玛窦虽提到了中国的三大宗教,但并没有明显贬损僧人之意。如其云:“中国共有三个教派,一为‘释教、一是‘道教和‘儒教,而以后者最出名。”[6](p.56)可到了1595年,利玛窦在致阿桂委瓦的书信中则称:“僧和我们的托钵会兄弟差不多,在中国并不太受重视。在这里计有三大宗教:儒、道、释,而释可说地位最低的一个,他们不结婚,每日在寺中念经礼佛,多不读书,可谓是低级百姓之一。他们固然也讲修行立功,但一般而言,他们的毛病却不少,派别又多,因此官吏多不理睬他们。和尚削发去胡,住在寺庙中,不成家,每日仅照顾神坛而已。”[6](p.202)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不仅认为佛教在中国三大宗教中属于地位最低的教派,而且僧人虽讲“修行立功”,但一般多不读书,整体素养偏低,故在中国亦不太受重视,可谓“低级百姓之一”。
最后,利玛窦在撰写的中文作品中竟公然批佛,即不仅共八篇的《天主实义》中既有七篇存有批佛的内容,而且在《畸人十篇》与《中国札记》等作品中亦都存有批佛之举。从批判的内容来看,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质疑中国汉朝使者去天竺取佛之事实。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甚至指出,天主以至仁之心而于“汉朝哀帝元寿二年冬至后三日”托胎降生,以拯救世人之堕落[7](p.217)。而哀帝元寿元年却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大有争议的时间点。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亦认为,中国人本来去取基督教思想,却误求了佛教,而且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亦正好与巴多罗买、多默等使徒在印度传播基督教义为同一个时期。
其二,否认佛教的正统性与独立性。无论就《天主实义》,还是《中国札记》的记载来看,利玛窦都认定佛教剽窃了西方思想家的思想与基督教的内容。如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不仅在第五篇《辩排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说,而揭斋素正志》中认为,佛教的“轮回”说是对古希腊“闭他卧刺(Pythagoras)”思想的剽窃,而且在第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中认为,佛教的“天堂地狱说”是对基督教思想的窃取,即“天主教,古教也;释氏西民,必窃闻其说矣……释氏借天主、天堂、地狱之义,以传己私意邪道”[7](p.108)。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不仅仍坚持上述之论,而且还认为,佛教的“四大说”是对“德谟克利特”多重性思想的剽窃,同时佛教的“三位一体”与独身思想,以及出家朝圣、乞求布施、唱经、献祭时所穿的袍服等仪式都受到了“基督教福音书”的启示。更为甚者,利玛窦甚至认为,僧人们在祷告时所常念的“达摩”之名,或许就是“要崇敬使徒巴多罗买的权威”[3](p.106)。
其三,利玛窦对佛教“空”“杀生”“轮回”等思想进行大肆攻击。利玛窦不仅在《天主实义》第二篇的开篇中就发起对佛教之“空”的批判,即“于天主理大相刺谬”,并从“空无”不能生“有”、贵贱、“无始之物”等多个面向驳斥“空”论,而且在篇四与篇五中还从六大面向对佛教的“轮回”“杀生”论进行大肆抨击,即“夫轮回之说,其逆理者不胜数,茲惟举四五大端”[7](p.146)。
其四,利玛窦对佛教的诵经、念佛名即可免罪受福的修行方式与偶像崇拜行为都极为鄙视。在利玛窦看来,佛教所倡导的通过诵经或呼佛名即可免罪、受福,以及成佛的修行方式都极其荒诞不经。因为不仅诵读经典即可“得到天堂受福”之论会导致陷入“使有罪大恶极之徒,力能置经诵读,则得升天受福;若夫修德行道之人,贫穷困苦,买经不便,亦将坠于地狱舆”的荒诞境地,而且呼诵“南无阿弥陀佛”之举亦“无益于德,而反导世俗以为恶”,即“小人闻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污本身,侮上帝,乱五伦,以为临终念佛者若干次,可变为仙佛也”[7](pp.201-202)。而且,在众多作品中,利玛窦都表现出了对佛教偶像崇拜行为的鄙视之情。
从上可知,利玛窦虽素以“理性”著称,但对于佛教的批判,其中不免展示了“欧洲中心主义”与基督教至上性之观念,致而导致一些对佛教的歪曲判定或误读现象。如在剽窃的界定上,既没有详细的时间考证,亦没有史料佐证,仅是凭一己之猜测而已,甚至即使在面对两大宗教的相似性内容,亦没有从宗教共性之因的面向去思考,而只是武断地判定为对基督教的剽窃。
对于利玛窦的批佛之举,其实最早之不满并不是来自于僧人,而是虞淳熙居士。从资料的记载来看,他不仅曾致信于利玛窦,批评利氏不全窥佛教秘义就独施攻具之鲁莽行为,而且还指出了此举给利氏自身所导致的风险性,即“幸无以西人攻西人,一遭败蹶,教门顿圮。天主有灵,宁忍授甲推毂于先生,自隳圣城,失定吉界耶?”[8](p.658)因为在虞淳熙看来,佛教与天主教并非全然对立,而是存有“互融”之情况,故希望利氏重新阅读佛经,能理性地对待佛教。可是,利玛窦在回信中不仅指出其批佛之举完全是“据理立论”,而非谄佞儒者,亦不接受虞淳熙的“互融”之意,并反复彰显天主教与佛教的差异性与不可融合性,甚至仍不忘批佛。虽然利玛窦认为,批佛之举全在于理性,而非他因。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背后还存在着三大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基于护教之考虑,他力图通过批佛达到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性与至上性之目的。无疑,这种观念不仅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罗明坚、范礼安等传教士对佛教之态度的影响。就罗明坚的《天主实录》与范礼安的《要理本》而言,其不仅在内容方面存有对佛教“轮回”、“杀生”、念佛名等修行方式的批判,而且在文章的框架结构方面亦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7](pp.8-12) 。
同时,从批佛的行为来看,利玛窦完全是以基督教思想作为审视与批判佛教的基准,致而一旦发现佛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构成冲突时,则会发起攻击。如基于基督教之观念,上帝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还是决定世人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审判者,所以,利玛窦既无法接受佛教的“空”,亦无法认可佛教的“轮回说”、杀生,以及其他偶像崇拜行为。实际上,《摩西十诫》开篇就要求教徒们除了天主之外,不可崇拜“别的神”,因为“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9](p.107)。所以,利玛窦不仅不礼拜寺庙里的偶像与六祖真身,而且在《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中国札记》等篇中,都充满了对偶像崇拜行為的批判,甚至要求受洗之教徒做出毁弃佛教偶像之行为。
但我们又不可否认的是,利玛窦尽管力图通过对佛教的批判来凸显基督教的纯正性,但在异国他乡,为了使基督教能得以生根发芽,他又不得不需要借助一些本土的媒介与文化载体传播和维护基督教,致而导致无意间又对基督教纯正性构成伤害。所以,在利玛窦身上有时会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即当他大肆批判佛教的偶像崇拜行为,并判定为迷信活动时,他却又能容忍民间祭祀中的各种祭拜行为与鬼神崇拜的存在。
其次,基于传教需要之考虑,利玛窦希图通过辟佛之举以获得一些儒者的支持。尽管利玛窦在《利先生复虞铨部书》中否认了“非佛是儒”为“谄士大夫”之举,而取决于“离合”,但事实并非如其所指。其实在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深刻感触到要在异乡之地获得传教之成功的话,单凭个人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借助一些外力。可这些外力的来源定位利氏认为不可能是僧人,而应是儒者、官员,以及皇帝。因为他在中国的生活实践中,既深刻体悟到了儒者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且还发现了虽然佛教作为中国最大的教派,在中国具有很多信众,但在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实际处于极为低下之地位。更为甚者,在当时,由于心学后人不断地禅学化,从而导致一些儒者,特别是东林党人对佛教的不满,而此现象却又易强化利氏斥佛之观念。如据《中国札记》的记载,不仅礼部尚书冯琦曾上奏过反佛之奏章,而且皇帝还下过“倘若官员们愿意做偶像的奴隶”的话,那“就让他们都到沙漠里去,那里有和尚居住的寺院”之圣旨,以致礼部尚书作出了一个“凡是参加文字竞赛或者科举考试的人——而他本人有权主持所有这一切,——如果提高偶像崇拜,除非是加以贬斥而外,就不能获得任何学衔”之规定 [3](pp.436-437) 。而利玛窦为了获得儒者的支持,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亦想通过批佛之举来获得儒者之支持。
据谢和耐的研究,不仅达尼埃洛·巴笃利早在1663年就指明了“传教士们于明末在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人中交了大批朋友一事”,而且在谢和耐看来,“这种沟通并非是由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掌握有许多说明东林书院或东林党成员仇视佛教的证据”[10](p.15)。同时,利玛窦在1609年致视察员巴范济的信中,亦有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述,即“在我所著的书中,我就以称赞他们(儒者)而开始并利用他们来攻击别人,而不直接去加以批驳,虽则解释了他们和我们信仰不一致的观点。我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以至于不仅文人们不再是我的敌人,而且还成了我的朋友”[3](pp.685-686)。
无疑,对利玛窦而言,他非常清楚要使基督教立足于中国,则必须要获得中国儒者们的支持。正如侯外庐所言,倘若传教士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其必然不会与中国正统学说发生正面冲突,而应是更多的迎合,而且“儒家传统中并没有一套严格的宗教教条与宗教信仰,用天主教的上帝来附会古代的‘天或‘帝,是比较容易的一种办法”[11](p.1208)。
其三,鉴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需要考虑,利玛窦认为,只有通过对佛教的批判,才能使基督教摆脱原有佛教身份的束缚。因为在进入中国早期,利玛窦等传教士曾经“以僧自居”,从而导致中国民众与官员一度把他们等同于僧人。无疑,对利玛窦而言,他非常清楚早期的“以僧自居”不过是他们消解中国人的猜忌,并能顺利进入中国的一个最好权设。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此时的他所面对的境况已与十多年前的境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他看来,佛教已没有作为权设存在的意义了,不仅如此,反而演化为妨碍传教士凸显自我思想的一大障碍。或者说,佛教已成为他传播基督教思想的一大拦路虎,即不仅会使基督教之独立性与价值被佛教的相似性因素所湮没,而且僧人的身份亦妨碍他与中国官员和文人的交流。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就“由僧到儒”身份更换问题,与范礼安有着深入交流之记载。在利玛窦看来,第一,倘若教团需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名称;第二,现有僧人身份不仅不能推动教团的发展,反而还妨碍着传教士们的工作;第三,中国百姓把神父与寺庙里的和尚混为一谈;第四,根据在中国传教的经验,“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否则,“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 [3](pp.275-276) 。
由上可知,尽管利玛窦在批佛的内容上存有很多武断性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辟佛之举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非武断之行。同时,若从宗教的影响力来看,在中国史上唯独佛教具有强大之影响,因而若能从理论上去驳倒它,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转变后的影响
对利玛窦而言,由“以僧自居”,到公然辟佛的转变,其中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也是他在中国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一大转变,即由“他者”向“自我”的一大回归。但令利玛窦没想到的是,本以为通过对佛教态度的转变不仅可以摆脱原有身份之束缚,从而真正回归到基督教的本色上,而且还希望通过对佛教的打击,达到取代佛教之目的,可事实并非如此,反倒来了一连串的负面效应,甚至把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推至极度危险之地。
首先,通过辟佛之举,无疑使基督教可以从原有佛教的阴影中逐步摆脱出来。由于利玛窦早期曾以僧自居过,所以,在国人的心中一度把传教士等同于僧人,把基督教等同于佛教,致使基督教思想曾被湮没在佛教之中。可利玛窦日后毁弃僧服,换上儒服,并对佛教思想进行大肆批判的一系列举措,无疑为摆脱此困境,使基督教思想的独特性得到彰显在做努力。正如裴化行(HBernard)所指,对利玛窦而言,尽管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得到了很大提高,但还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把他阻挡在‘中国社会之外,那就是他与和尚之间哪怕纯粹是表面上的亲缘关系” [4](p.166)。正因如此,利玛窦不仅没能看到基督教与佛教的相似性成分的价值,反而看到的是这些相似因素对基督教传播的阻碍性。
其次,人为性地为基督教的传播设置了障碍与对手。不可置疑,利玛窦通过对佛教的批判而使基督教思想与教派的宗旨得到了体现,但我们更应思量的是,在当时闭关锁国的环境下,而又没有得到皇帝应允的前提下,利玛窦过早暴露自身目的,并不是一个稳妥之举。因为从《中國札记》记载看,尽管利玛窦与官员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无论从韶州,还是南昌的传教,两地的反教运动从未停息过。利玛窦只是把其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即民众的愚昧、对外国人的敌视、僧人的低贱地位,以及僧人的怂恿,而没有从深层次的面向去思考是由于中西文化在观念与思考方式的一种冲突。利玛窦虽然在中国传教的过程采取了一些适应性的策略与方式,但他实际上没能真正把中国文化的内容融入到基督教思想中,仅是把僧或儒视为外在的一种权设而已,若一旦达其目的,则会被视为敝屣,并大肆践踏,诚如佛教之命运。利玛窦之举无疑会激发中国很多文人对他意图的无端猜忌,从而为传教活动自设了一些障碍。
或许对利玛窦而言,佛教不仅是外来的“邪教”,而且其僧人亦“卑鄙无耻”,毫无社会地位,所以,从理性层面考量,对它的批判理应不会存在着什么风险。但利玛窦忽略的是,佛教虽为外来的宗教,但到晚明时,已在中国经历了近1 600年的时间刷洗,早已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更需认识到的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很少主动去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反而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人之性情,更多的是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身。所以,晚明佛教虽然不如唐宋时辉煌,但却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正如孙尚扬所指:“至明末,佛教已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沃土中。任何想撼动其根基或彻底消除其影响的尝试者,都不能不先考虑自身的理论力量,尤其不能不考虑由此种尝试可能带来的后果。”[12](P.86)事实上,利玛窦根本没有从这个面向去考虑,否则的话,不可能会出现以刚入中国几年的基督教去对抗已入中国一千多年的佛教之现象。因为在他的心中,佛教只是一外来邪教,唯独基督教才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所以相信世人一定会乐意放弃佛教而去接受基督教。
再次,对日后其他传教士与教徒们的佛教观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从资料的记载来看,无论是日后的传教士,还是教徒们,在接任利玛窦辟佛之大旗后,不断对佛教发起攻击,甚至还开出了以辟佛之举来传播基督教的向度。如英国艾约瑟迪谨氏于1857年撰写了《释教正谬》,并对佛教的“教乘”“轮回”“三宝”“偶像”“净土”“观音”“地狱”“持咒”“止观”“涅槃”“无常”等思想进行了驳斥。
而作为基督徒的杨廷筠,不仅在《天释明辨》中承继了利玛窦的佛教窃取基督教与西方哲人思想之论,并从天堂、地狱、杀生、奉斋、轮回、念诵、三世佛、三十三天、阎罗断狱、出家、律教宗等三十方面的内容对佛教发起全面攻击,而且在《代疑篇》《代疑续篇》等作品中,还通过对佛教的批判,以达传播基督教之目的。张星曜的《天教明辨》虽为一部论道之书,但其中亦贯穿了对佛教思想的批判,甚至还认为佛教是对基督教思想的剽窃,即“阿罗氏所携景教经典二十七部俱为释氏窃取”。即使对于具有强烈实学精神的徐光启而言,他不仅在教难发生之前曾向皇帝上疏过《辨学章疏》捍卫基督教与批判佛教,同时在教难期间,亦积极保护传教士,并不忘批判佛教。如他在致贝拉米诺的回信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护教之心与对佛教的厌恶之情。而且在《辟释氏诸妄》中,还对佛教的“地狱”“施食”“持咒”“烧纸”“念佛”“禅”“宗”之论进行了批判。
最后,南京教案的出现与福建反教运动的白热化,以及《圣朝破邪集》的问世,都对基督教的传教构成巨大打击。对于明末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两者冲突的挑起者不是僧人,而是传教士。即使当利玛窦大肆批佛之时,僧人们亦没有马上做出回应,而只是虞淳熙居士通过书信之方式,规劝利玛窦放弃批佛之举,并指出了佛教与天主教存有“互融”之处,但均被利玛窦拒绝。更为甚者,天主教方面不仅没有收敛自己的辟佛行为,反而在随后不断发起对佛教的攻击,激起一批具有佛教情怀的文人与僧人在“不得已”之下,齐力予以还击。
据《明史》记载,礼部郎中徐如珂很不满王丰肃居南京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与其徒“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之举,“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四十四年与侍郎沈氵隺,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随后,给事中余懋孳亦上疏皇上,要求力驱传教士,即“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令,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13](pp.3561-3562)受方从哲之命,1616年8月31日,沈氵隺带兵包围了南京教堂,并逮捕了王丰肃等传教士,从此正式拉开了南京教案的序幕。此次教难虽然历时很短,但无疑对基督教的打击较大,即不仅对钟鸣仁、曹秀、姚如望、钟鸣礼、张寀等主要教徒予以定罪,并把王丰肃、谢务禄等传教士遣送澳门,而且还对违制楼房、圣像、经书进行没收处置。
自崇祯七年(1631年)以来,福建反教运动亦越来越激烈。据《破邪集》的记载,作为福建巡海道的施邦曜于1637年不仅“以夷乱华”“以邪说惑人”之罪到宁德县、福安县缉拿传教士,还以告示之形式告知百姓,即“凡有天主教夷人在于地方倡教煽惑者,即速举首驱逐出境,不许潜留。如保甲内有士民私习其教者,令其悔改自新,如再不悛,定处以左道惑众之律,十家连坐并究,决不轻贷”[14](pp.77-80)。1637年十一月初五日,福建按察使徐世荫与福州知府的吴起龙等纷纷撰写告示,告知百姓,天主教为“左道邪教”,日后需“严加防察”,如误入邪教应改过自新,若执迷不悟,则将“尽法重治”,“其地方若有教堂妖书,尽行拆毁焚除,不得隐藏,违者该保约并处不贷。”另若见艾儒略等天主教传教士,则“即禀官严拿究治”,如果“容隐不举,事发一体连坐” [14] (pp.81-83) 。
为了有效打击天主教,徐昌治把群臣、诸儒、众僧批判天主教之作品汇集在一起,并于1639年初刻于浙江,即名《圣朝破邪集》。此作品的一二卷,分别记录了南京教案的相关资料与福建反教运动的三个告示,三至六卷则主要载录了黄贞、王朝式、许大受、黄廷师、魏濬、陈候光、戴起凤、虞淳熙、王忠等二十多位官员与民间儒生的反教作品,七八卷则主要汇集了云栖祩宏、释圆悟、释普润、释通容、释如纯等七位高僧与黄贞、张广湉等多位居士的反教文章。无疑,无论从涉及面,还是儒、释的结盟而言,此作品都对天主教构成了巨大之冲击。
综上所述,对利玛窦而言,由于受到基督教排他性观念的驱动,以及鉴于护教与传教策略上的思考,致使他胆敢对已经扎根中国一千多年的佛教公开发起攻击,全然忽视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实上,从佛教观的转变上来看,利玛窦不仅没能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佛教与基督教的异同,亦没能以平等心进行双方思想的内在交流,而是以基督教至上之心态去排斥异己之佛教,致而既会导致很多言论的武断性,亦容易伤害本土文化士人的尊严与内在情感,容易激起一些士人的反击与抵抗。而且利玛窦亦没能从同为外来宗教的佛教身上吸取融入中国的优秀方式,即既能不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入适合中国人性情之成分更好地实施佛教中国化,亦没对异己思想发起攻击,而是采取和平共处之方式来对待。可利玛窦虽然在传教中采取了一些适应性策略,但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早期的“以僧自居”,还是日后的附儒之举,都不过是外在形式上的一种借鉴或仅为权设,未能真正从深层的面向上去接受。同时,在没能扎根与彻底掌握对手的情况下,竟敢贸然发起攻击,这无疑亦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导致整个教派陷于危险之境地。
[参 考 文 献]
[1][意]利玛窦.利玛窦全集:第3册[M].罗渔译.台北: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
[2]黄兴涛.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M].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上册[M].罗渔译.台北: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
[7][意]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M].梅谦立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意]利玛窦.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朱维铮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9]圣经[M]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2006.
[10][法]謝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1998(4).
[13]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二百十五[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4]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57册[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
(作者系肇庆学院副教授,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