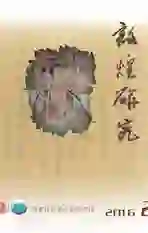一种不曾存在过的历史纪年法
2016-06-03邓文宽



内容摘要:路易·巴赞教授是欧洲突厥学的泰斗,其代表作是法国国家级博士论文《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然而,本文作者发现,巴赞教授使用了一种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六十纪年周期”:由十二生肖配六甲纳音(用五行代替)而成。本文追根溯源,找出这项学术错误发生的根源是:误读了黄伯禄神父1885年出版的《中西历日合璧》中六十甲子表所附的六甲纳音内容(黄神父也未正确理解六甲纳音)。根据出土回鹘资料中的历法要素,作者对回鹘所用纪年方式进行了复原:1.“行肖法”(代替天干的五行配生肖),2.“干肖法”(天干配生肖),3.“干肖纳音法”(天干配生肖再配纳音)。这三种源自汉族又经改编的六十甲子,在回鹘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段曾经被分别使用过。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认识汉族六十甲子在周边民族文化中的嬗变,文章又对吐蕃六十甲子和回鹘六十甲子做了比较,分析其异同。文中所附汉族、回鹘、吐蕃六十甲子表,均可作为研究相关出土文献年代的参考。
关键词:回鹘;六十甲子;路易·巴赞;黄伯禄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2-0125-12
Abstract: Professor Louis Bazin is a leading European scholar of Turkolog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being his Ph.D. dissertation,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Turkish Socie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finds that Professor Bazin used a chronology that never existed in history-a sixty-year cycle created by combining the Zodiac and a sixty year cycle represented by the Five Elements. After intensive research, the source of the mistake has been discovered: Professor Bazin misunderstood the cycle of sixty years in the“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alendars”published by Priest Huang Bolu in 1885(Priest Huang did not properly understand this chronology either). Based on the calendar elements of unearthed Uighur document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ries to restore the calendar used by the Uighurs, finding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a combina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as a substitute for the Heavenly Stems)and the Zodiac; a combination of the Heavenly Stems and the Zodiac; and a combination of the Heavenly Stems, the Zodiac, and a cycle of sixty years. Calendars of these three types have been used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Uighur histo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ycle of sixty years in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Tibetan and Uighur cycle of sixty year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tables of Chinese, Uighur, and Tibetan sixty-year cycles attached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study of unearthed documents. development of new prescriptions.
Keywords: Uighur; cycle of sixty years; Louis Bazin; Huang Bolu
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0—2011)教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国学者,以研究突厥历史而享誉学林,被誉为法国乃至欧洲突厥学的一代宗师。巴赞教授的代表作是其法国国家级博士论文《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出版社和匈牙利科学院合作,于1991年正式出版。其汉文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教授完成,最早由中华书局出版[1];最近,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了这个译本[2]。
由于个人术业所在,《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汉译本刚出版时,就有学界朋友希望我写一篇书评。但因该书所涉语言类知识颇多,而这一方面又是我的短项,故而未敢领命。2014年,该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我到书店淘书,因封面换了颜色,书名也有改动,就糊里糊涂地又买了一本。回家一看,确实是买重了(此类事在我是经常发生的)。一本书买了两次,说明在我的潜意识中认为它很重要,所以,必须认真去读,否则,对不起这部名气巨大的学术著作。拜读之后,觉得确实有些话想说出来,以就教于中外学林的博学通人。
一 解读巴赞教授的六十纪年周期表
读过该书,冷静沉思之后,我发现巴赞教授在为相关突厥文、回鹘文等多种出土碑铭定年时,使用了一种历史上根本不曾存在过的“六十纪年周期”。下面,我将引证巴赞教授的有关认识,以及他对自己这种方法在定年时的运用,加以分析和讨论,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回归到正确的定年方法上来。如果我的认识有错,或者误解了巴赞教授的本意,欢迎中外学林的同仁予以批评和指教,我将洗耳恭听,时刻准备检讨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巴赞教授在第五章“晚期回鹘人的历法科学”之第12自然节中[2]286-287,说明了他的定年方法。他说:
在甲子或干支纪年中,将“生肖加五行(12×5=60种不同的结合)之结合借鉴自汉族星相学”。我发现它作为历法的复杂分类因素而出现在回鹘文献中了。从开始研究起,对它的解释就被西方学者们严重地误解了,他们曾认为可以把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中的10“干”(天干分类)和“五行”(木、火、土、金和水)两两相对地结合机械地运用于其对应关系中。然而,在与我本书有关的时代,这种对应关系(BC6)仅对于哲学——巫术思辨才有效,而绝非是对历法有效。在历法中却运用了另一种更要复杂得多和更要“博学”得多的方法,而且直到19世纪时依然行之有效。黄伯禄神父对此作了全面描述(BC8—9)。
我自己在着手研究的最初几年,也曾陷入到对该词的一种误解之中(这在原则上是很符合逻辑的),仅是在发现了自己导致了某些无法解决的矛盾时,才从这种错误中幡然醒悟。
我于下文将简单地阐述一番两种对应体系之间的差异,对于其中的汉文方块字,则要参阅前引黄神父书中的几段文字。
第1种对应方法:五气(五行)+10干(天干)分类法。天干(10)自行连续地分配在“五气”。其具体情况如下:1+2,木;3+4,火;5+6,土,7+8,金;9+10,水。以前引数字(以0代10)而结束的60甲子编号,就相当于上文列举的继它们之后的五行之一,如,第34为火,28为金。
为了避免一段引文过长,先引到这里。对于古代历日内容和结构不很熟悉的读者,读上述引文会存在一些困难。其实,这段文字内容并不复杂。这“第1种对应方法”就是巴赞教授在前面批评过的“从开始研究起,对它的解释就被西方学者们严重地误解了”的天干与五行相配的方法。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行是木、火、土、金(铁)、水。依照传统的五行理论,每一个五行可配两个天干,如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铁),壬、癸配水[3]。巴赞教授将天干排为由1到10 的序号,故他的“1+2,木”,也就是“甲和乙,木”;“3+4,火”,也就是“丙和丁,火”,如此等等。这样,十个天干就可以由对应的五行替代了。他说的“第34为火”,指第34号干支丁酉,其天干“丁”配“火”;“28为金”指第28号干支辛卯,其天干“辛”配“金”,看本文附表1 会立即明白。
下面接着引述巴赞教授的原文:
第2种对应方法:五气(五行)+60甲子纪年对于五气(五行)不再是在天干的周期中,而是在60甲子的周期中划分(天干中的每一种都要相继与五气中的三种相联系)(表1)。
这第2种复杂而又“科学”的分类体系,才是中世纪回鹘人“官方”习惯中用于历法的唯一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更为简单和通俗一些,稍后随着历史传到了吐蕃、印度支那等地。这两种方法仅在60年的16年中偶然地相会,永远不会融合在一起。
可以说,这“第2种对应方法”便是巴赞教授的六十纪年周期,而且他认为是“中世纪回鹘人‘官方习惯中用于历法的唯一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读懂它。
第一, 他认为在这种方法中,“不再是在天干的周期中,而是在60甲子的周期中划分”。
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在这种方法中,不再考虑天干与五行的配合;括弧内是说,在一个完整的六十干支表中,每个天干与“五气”(五行)中 的三个相遇。比如天干“甲”,仅与金、水、火这三个五行相遇。请参考下文附表1“汉族六十干支表(附天干、地支与五行对照及各干支纳音)”的左侧上下六格,干支序号是1、11、21、31、41、51,虽然天干“甲”用了六次,但相配的“五气”(实是纳音,详下文)仅有火、金与水三个。
第二, 巴赞教授所绘的这个表格,左侧由上至下为代替地支的十二生肖;上面由左至右的木、火、土、金、水不是代替天干的,因为他的表已将天干排除在外,而是代表汉地六十干支所配纳音的(各干支的纳音见附表1),这个纳音又是用五行(他称为“五气”)代替的;表中间由上述二者详加所得的数字序号,相当于汉地六十干支序号。所以,把这个表的三部分内容合起来便是:鼠加木等于汉地干支第49号,猪加水等于汉地干支第60号,等等。读者若有兴趣,可以与本文附表1《汉族六十干支表》所列各干支及其序号逐一进行对照,只是对照时,需把十二地支换成对应的生肖罢了。
第三, 为了准确理解巴赞教授这个六十周期表,按照他生肖加纳音(用五行代替)的思路,我将他的六十周期表绘成本文的附表2。为了进行比较,我又将巴赞教授认为从一开始就“误读”了的天干(用五行代替)加地支(用生肖代替)的方法绘成本文的附表3。对附表2和附表3我全部加上从1到60的序号,以便对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汉地六十甲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这样,对于不熟悉历日内容的读者会方便很多,因为只看号码就能立即找到。
将附表2、附表3进行比较后,发现在一个六十周期中,仅有16个是相同的,序号是:3、4、15、16、17、18、29、30、33、34、45、46、47、48、59、60。正由于此,巴赞教授在前述引文的末尾才说:“这两种方法,仅仅在60年的16年中才会偶然地相吻合,永远不会融合在一起。”
第四, 巴赞教授六十周期的根本特征是“生肖加纳音(用五行代替)”,不再考虑天干的作用。
下面我将依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提供的资料展开讨论,看看这个纪年方法能否成立。
二 以五行代替天干在八世纪初年已用于历日
巴赞教授在前引文字中批评第一种纪年方法,也就是他认为一开始就被一些学者误读了的“五行(代替天干)加生肖”的纪年方法(即本文附表3)时说:“在与我本书有关的时代,这种对应关系(BC6)仅对于哲学——巫术思辨才有效,而绝非是对历法有效。”事实恐非如此。他所说的“与我本书有关的时代”,应该指8世纪中叶,因为由他定年的鄂尔浑1、2两号碑分别在公元732和735年,以及其他文献,时间多在8世纪中叶。然而,用五行代替天干这种方法在8世纪初就已经用在历日中,且“对历法有效”了。
1982年,藏族学者催成群觉和索朗班觉发表了《藏族天文历法史略》一文,内云:
公元七〇四年,赤德祖赞时期黄历历书《暮人金算》、《达那穷瓦多》、《市算八十卷》、《珠古地方的冬、夏至图表》、《李地方的属年》、《穷算六十》等典籍传至吐蕃地区。[4]
可知,8世纪初叶传入吐蕃的“黄历历书”有多种多样,其中的《穷算六十》值得注意。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宗祥(汉族)和却旺(藏族)二位先生为《穷算六十》做了如下的解释:
《穷算六十》的“穷部”Byung Rtsi是个姓氏。“穷算六十”与“李地方”的算法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十二生肖与五行配合算的。每两年配一行。例如去年(按,指1978年)土马,1979年是土羊,1980年是铁猴,1981年是铁鸡……12×5=60[4]32。
查历表,1978年是农历戊午年,1979年是己未年,1980年是庚申年,1981年是辛酉年。除去地支被生肖代替外,天干戊、己、庚、辛分别被土、土、铁(金)、铁(金)所代替,完全符合天干与五行的搭配关系(详见附表1和附表3的55、56、57、58各号)。
就目前材料而言,我们虽然不能指证这一套知识和纪年方法的最初出处,但它们属于汉族传统的术数文化当无疑问。由上引可知,以五行代替天干并配生肖,形成一种改编版的六十干支如附表3,在8世纪初不仅已经产生而且业已传入吐蕃。虽然说吐蕃未能立即使用这套改编版的干支进行纪年,但这套知识既已产生并传播开来,那么它在数十年后的8世纪中叶传入回鹘并用于纪年则是完全可能的。回鹘文献中的那些与《穷算六十》相同的纪年资料便是证明。再者,这段时间,生活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民族与中原唐王朝之间交往甚为密切;而且,从大的视野去看,回鹘属于广义突厥民族的一部分,但汉地早在公元586年就已向突厥颁历[5],百余年后,改编版的汉地六十干支传入回鹘并被使用,亦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见,巴赞教授为自己设立的认识前提是难于成立的。
三 六甲纳音的出现、入历和读法
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在讨论回鹘历史纪年法时,巴赞教授始终未用“纳音”这个概念,而是在指称事实上的“纳音”时使用了“五气”、“五行”这些容易导致混乱的说法。但事实上,这全是汉民族术数文化中的“纳音”与六十干支(又称六十甲子)相结合,便是“六甲纳音”或“纳甲”。只是在历注中,五音(宫、商、角、徵、羽)分别用五行(各自对应的五行依次是土、金、木、火、水)进行了代替。中外不少学者于此不明就里,反而同代替天干的五行(木、火、土、金、水)相混淆,从而生发出一些原本不该发生的错误。
迄今为止,我们仍不知六甲纳音最初是如何产生的。但至晚在出土的公元前3世纪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已有了按“五音”对六十干支的分组,现引录如下(为便于比较,我在每个干支后的括弧中均加了干支序号,下同):
禹须臾:辛亥(48)、辛巳(18)、甲子(1)、乙丑(2)、乙未(32)、壬申(9)、壬寅(39)、癸卯(40)、庚戌(47)、庚辰(17),莫(暮)市以行有九喜(九七背壹);
癸亥(60)、癸巳(30)、丙子(13)、丙午(43)、丁丑(14)、丁未(44)、乙酉(22)、乙卯(52),甲寅(51)、甲申(21)、壬戌(59)、壬辰(29),日中以行有五喜(九八背壹);[6]
(以下略)
我们将上面两组干支与本文前面引述的巴赞教授那个用干支序号编成的表加以比较,发现第一组干支全在该表属“金”(商音)的那一栏(简文不全,缺癸酉和甲午);第二组则全在属“水”(羽音)的那一栏。其余略去的三组,分别在该表的“木”(角音)、“火”(徵音)和“土”(宫音)各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比较,这里从略。
可知六甲纳音这种术数文化知识先秦时代即已存在。但是,它又是在何时作为历注之一引入历日的呢?就目前出土资料而言,最晚在《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中就已存在。
该历日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10号古墓,其第16行云:“廿一日辛丑土执 岁后,母仓、归忌、起土吉。”第17行云:“廿二日壬寅金破 岁后,疗病、葬吉。”[7]其中各干支后的“土”和“金”便是该干支的纳音。同样从吐鲁番古墓出土的《唐开元八年(720)具注历日》也有相同的内容,如:“十二日癸巳水闭没 岁位。”[8]这说明,六甲纳音这一术数文化,至晚在7世纪中叶已作为历注内容之一纳入历日,到巴赞教授研究的那些文献所在的8世纪中叶,应该已成为一项常见知识。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种六甲纳音的内部关系和它的读法。就我掌握的知识,六甲纳音中的“音”(用五行代替)是配给每一个干支的,比如:甲子、乙丑这两个干支分别配“金”,丙寅、丁卯配“火”,如此等等。我们在敦煌出土的唐宋写本历日中也见到了它的读法。比如,藏于英国图书馆的S.1473+S.11427bV《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并序》,其卷首云:“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干水支火纳音木。”[9]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珍本部的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开首即云:“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干火支土纳音土。”引文中的小字就是该年的纪年干支及其对应纳音的读法。再看本文附表1第19号干支,可知壬、午对应的五行分别是水和火,故称“干水支火”;“壬午”这个干支的纳音为“木”(代替角),故云“纳音木”。第23号干支丙戌,丙、戌对应的五行分别是火和土,故称“干火支土”;“丙戌”的纳音为“土”,故称“纳音土”。这种读法,无论是出土的唐宋元实用历本,还是传世的明清历日,以及今日仍在港、澳、台广泛使用的民用历书暨日本历书中,依然未变。
我们认为,一个纳音是对一个完整的干支而言的。而巴赞教授却认为,那个代替五音的五行只是对一个干支中的地支而言的。按他的理解,在“甲子金”这一组纳音中,“金”只与地支“子”相配,而不是与“甲子”这个意义完整的干支相配。当然,这里的“子”可以用生肖“鼠”代替。于是,他将“鼠”加“金”,也就是将地支和纳音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新的组合,认为在回鹘历法中就是用这个组合来纪年的。本文前面复原出的附表2就是这么产生的。
我们再看巴赞教授是如何用他的纪年周期去为相关文献定年的。在吐鲁番地区出土过三条庙柱文,一条为汉文,两条为回鹘文。回鹘文之一云:“己火羊年,二月,新月三日,当此人获得了(后略)”[2]303。按照我的读法,此处当读作“己羊火年”,“己”这个天干尚未用五行代替(详下节),“羊”代替“未,”,还原出来便是“己未火”,附表1第56号与此正同。而按照巴赞教授的方法,则读作“羊火年”(或“火羊年”),在他的表(本文附表2)上正巧也是56号。不过,我想问,如果这里的纪年是“羊火”(或“火羊”)这个组合,那么天干“己”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这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吗?在下节我们将会看到,用汉族原来的天干与十二生肖进行组合,形成改编版的回鹘六十干支,既用于纪年,也用于纪日,正是回鹘历法的重要特色。
另一条回鹘文《金光明经》有:“牛年,五气之火,十干分类的‘己。”[2]304按我的读法,应该读作“己牛火年”(干支第26号)。但若按照巴赞教授的读法,便成为了“牛火年”(或“火牛年”)。好在这里天干未用五行取代。若用五行代之,因“己”为“土”,就会变成“土牛火年”,不涉及纳音的话,便应读作“土牛年”(见附表3第26号);而在巴赞教授那里,却是“火牛年”(见附表2第26号),“土牛”变成了“火牛”,再以此为据进行定年,就未免相去甚远了。
综上可知,这里根本的差别是:六甲纳音中的五音(用五行代替)是与一个完整的干支相配呢,还是仅与其中的地支相配?怎样才算是正确的认识?
关于六十干支(甲子)纳音,清儒钱大昕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一目中指出:
纳音者,又以六十甲子配五音……五音始于宫,宫者,土音也,庚子(37号)、庚午(7)、辛丑(38)、辛未(8)、戊寅(15)、戊申(45)、己卯(16)、己酉(46)、丙辰(53)、丙戌(23)、丁巳(54)、丁亥(24),乃六子所纳之干支,古为五声之元,于行属“土”,于音属“宫”,所谓一言得之者也(后略)。[10]
这一组干支在六甲纳音中全属于配“土”,亦即“宫”音那一组。
此外,在中国民间算命先生那里,这种配合关系也有30句口诀,如“甲子、乙丑海中金”,“丙申、丁酉山下火”,“戊辰、己巳大林木”,等等。显然,也都是将完整的干支与“五音”(用五行代替)相配的,而不曾将天干与地支分开过。
总之,无论是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还是中古时代的实用历本、清代学者的著述,以及当代东亚地区仍在行用的通书,或在民间术士那里,我们得到的认识,全是一个完整的干支配一个音,而不是只将地支(或生肖)与五音相配。更不存在用生肖配五音这样一种组合去用于纪年,这在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中都从未有过。
四 回鹘六十干支表复原
出土文献和碑铭资料表明,突厥和回鹘曾经广泛使用过十二生肖纪年,其名称和次序与汉地十二生肖完全相同[11],所以,关于这一纪年形式,此处从略,不再讨论。
既然我们认为巴赞教授那个六十纪年周期难于成立,那么就应该找出回鹘人曾经使用过的纪年形式。因此,必须先从出土资料中找出那些构成纪年规律的历法要素,然后再根据它们加以复原。下面我们将每类资料引出一条,并进行分析。
1. 敦煌藏经洞出土、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珍本部的P.Ouīgour2号回鹘文文献,其4—5行有“土猴年tonor月有(姓)朱者只身来此(后略)”[12]。此件既出土于敦煌藏经洞,则其年代不能晚于11世纪初,因为现知有纪年的敦煌汉文文献最晚为公元1002年。这里的“土猴”,“土”代替天干,“猴”代替地支,二者的结合就构成了下表(附表4)第45号。因为“猴”与五行“土”(代天干)相配仅此一位,换成汉历,便是“戊申”,请与附表1、附表3、附表5的第45号进行对照。回鹘此种六十干支纪年形式,若果单独抽出来,事实上就是本文附表3 所具有的内容。
2. 前引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庙柱文之一:“己火羊年,二月,新月三日,当此人获得了(后略)”。依照我的理解,当读作“己羊火年”。其中“己羊”是纪年干支,处在附表4的第56号。因为“羊”代替地支“未”,所以换成汉历,就是己未年。己未在附表1、附表3和附表5上都在第56号。至于“火”,它就是己未这个干支的纳音“徵”,用“火”代替了,也见于附表1第56号。这条资料与第1条的不同之处在于,第1条“土猴”中的五行“土”代替天干“戊”,但此条仍旧保留了汉族的天干原名,不用五行代替;再者,还保留了汉地原有的六甲纳音内容。顺便指出,我们在本文第三节曾引过吐鲁番阿斯塔纳210号古墓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那里面的纪日方式也是干支加纳音。若与同是吐鲁番出土的这条回鹘文庙柱文做比较,就会发现,其差别仅仅是将地支换作了生肖,天干和纳音则完全相同,这是富有思考意义的。既然在公元840年回鹘占领吐鲁番之前将近200年,汉地的这种历法知识就已传播到了那里,回鹘占领后能不受其影响吗?
3.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编号TM14[U4759])题记有:“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虎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回鹘文《玄奘传》内有“腊月戊龙日”云云。可见,汉族天干配十二生肖(代替地支)这种组合在回鹘人那里不仅曾经用于纪年,也用于纪日。与第2条资料相比,仅是少了用于代替纳音的五行,此外完全相同。这条有“壬虎年七月”的资料,有关专家推断为1302年[13],相当于14世纪初。
通过上引三种形态的回鹘文纪年资料可以看到,第一,汉地原来的地支已经完全由生肖取代了,不再有任何表现;第二,汉地的天干则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用对应的五行来代替,如第1条资料,一种是继续保留汉地原名不变,如第2、3条资料;第三,汉地的六甲纳音被照搬进回鹘历法中去了,见于上引第2条资料。简言之,汉地的天干(或用五行代替)、地支(全用生肖代替)、六甲纳音(一如汉地,仍用五行代替)全都引进了回鹘历法。用巴赞教授的话说就是:“8世纪时于突厥人官方文献中沿用的历法,是对于唐朝官历的一种准确改编。”[2]
根据上述回鹘历法资料,我现在将其绘成附表4《回鹘六十干支表(附天干与五行对照及各干支纳音)》。
这个回鹘六十干支表将已知回鹘用干支纪年、纪日的内容几乎全部包含了进去。不过,在不同时代,所用纪年形式有别。极为粗略地划分,大致是:漠北回鹘汗国时期(744—840),由汉地传入的干支中的天干已用五行代替,如1号干支读作“木鼠”(内容同附表3);840年西迁后,使用了天干加生肖再加纳音这种组合,如1号干支是“干甲支鼠纳音金”;到了元代,又将纳音舍弃不用了,如1号干支只是简单地读作“甲鼠”。但任何时候,1号干支都没有变成由生肖“鼠”与纳音“金”去组合,读作“鼠金”或者“金鼠”。如果将天干用对应的五行去代替,1号干支也只能读作“木鼠”,不能也不曾读作“金鼠”。其余各个干支与此均同。
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认识汉族六十干支对周边民族的影响,我现在把吐蕃(藏族前身)的六十干支绘成附表5,以便与回鹘六十干支表进行比较。将附表4、附表5加以对照,可得如下认识:
1. 回鹘和吐蕃都曾将汉地的天干用五行代替。其不同处在于:回鹘也曾直接用汉地原来的天干,但在吐蕃未曾发生;吐蕃曾运用汉地的五行知识将代替天干的五行分作“阳”和“阴”,但在回鹘未曾发生。
2. 回鹘只用汉地的十二生肖,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地支;吐蕃虽主要使用生肖,但也曾单用地支纪年,如敦煌文献有“辰年牌子历”,这或许是那一时段在其治下有汉人的缘故。
3. 回鹘历中曾经保留了汉地的六甲纳音,但吐蕃历不曾保留。
显然,回鹘和吐蕃这两个民族在接受了汉地的六十干支后,并未生硬地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汉文化的理解,进行了适当损益和改造。但其六十干支的文化内涵,仍旧完全处于汉地六十干支及其纳音,还有五行和生肖知识的范围之内。只要将附表4、附表5与附表1比较一下就能明白,这里不再辞费。
五 《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与《中西历日合璧》
在本文第一节引述巴赞教授的论述时,我们注意到他说:“在历法中却运用了另一种更要复杂得多和更要‘博学得多的方法,而且直到19世纪时依然行之有效,黄伯禄神父对此作了全面描述。”在该书的其他地方,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见解是受到了黄神父的启发,而且再三表达感激之情。故此,我们必须对黄伯禄及其相关著作加以了解。
黄伯禄(1830—1909)为江苏海门人,字志山,号斐默,洗名伯多录。他1843年入张朴桥修道院,为首批修生之一,习中文、拉丁文、哲学和神学等课程。1860 年晋升为铎品,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1875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小修院。1878年任主教秘书和神学顾问,并专务写作。他一生出版作品极多,有些收入了光启社出版的法文版《汉学丛书》,《中西历日合璧》是其于1885年用法文出版的著作,此即巴赞教授依托和参考的主要书籍。
既然黄神父该书对巴赞教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就必须弄清黄氏的观点。该书涉及中国古历的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1.十天干与五行及方位的对应关系;2.十二地支与生肖、五行及方位的对应关系;3.六十干支表;4.清代历史纪年表(以及一些预推的年表)。其中对巴赞教授影响最大的是六十干支表那部分。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将黄伯禄书中的表格原封不动地移录过来,成为本文的附表6(黄伯禄《中西历日合璧》中的六十干支表)。
这个表的核心内容仍是用汉字表示的,各个项目说明则用法文。其实,它仍是一个汉地的六十干支表,只是在每个干支右侧附加了两项内容:一是该干支中的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对应关系,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等;二是该干支的纳音(用五行代替),如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等等。这些内容在汉地传统历日中均为习见项目,毫无奇特之处(请参阅本文附表1)。黄伯禄在将这些中文名词译成法文时,将“纳音”直译成了“五行”(elementa),因为这里的纳音就是用五行代替的。这也说明他对“纳音”这项术数文化尚无真切清楚的了解,只是从表面去认识,未免皮相。可是,经过巴赞教授的组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怎么回事呢?他将该表每一号干支中的附加内容即地支对应的生肖,与纳音加以合并,便产生了本文附表2那个“六十纪年周期表”。而且,本文第一节引述的他那个用干支序数形成的表,即生肖加“气”(实是纳音:木、火、土、铁、水)等于干支序号,起初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将生肖放在前面,而把五行(他称之为“气”)放在后面。现在终于看清,这是在没有弄明白黄伯禄六十干支表与其附加内容关系的情况下,简单照抄的结果,只要将本文附表2与附表6加以对照,便会一目了然。但在中国历法史上,从未存在过用生肖和纳音进行组合并用于纪年的事情。至于用“五行加生肖”以代替干支,本质上仍是对古已有之的汉族六十干支的改编(如附表3)。我只能遗憾地说,巴赞教授没有弄明白黄伯禄表上的“五行”是代替“纳音”的,与代替天干的五行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这个纳音只能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干支而言,不能把它配在代替地支的生肖上进行组合。单就这一点而言,黄伯禄原表没有太大的错误,因为毕竟他没有进行这样的组合,只是巴赞教授对该表进行了过度解读而已。反过来说,如果黄伯禄神父真正懂得历日中的纳音知识,他就不应该在他的表中称纳音为“五行”,而应该直接称作“纳音”。如果他能这样做,也许就不至于对不谙中文的巴赞教授产生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学术错误的发生,黄伯禄神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无论是黄神父,还是巴赞教授,都不具有对中国古代术数文化“纳音”及其在历日中安排的认识,这是很可惜的。
仔细想来,巴赞教授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错误,一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历日的丰富内容、结构及其内部关系不很熟悉,二是他过分自信地认为公元8世纪中叶还没有产生以五行代替天干、以生肖代替地支,如“甲子”变成“木鼠”、“乙丑”变成“木牛”这种改编版的六十干支(即附表3),而且已用于纪年。但藏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早在公元704年,即8世纪之初,这种改变版的六十干支(《穷算六十》)就已传入吐蕃。我推测,它的实际产生年代可能还要再早一些,估计当在7世纪的中叶或下半叶。当巴赞教授看到黄伯禄的六十干支表上有附加的“生肖”和“五行”(实际是纳音)时,对照回鹘文献上出现的“五行加生肖”如“火羊”、“土猴”等纪年,便认为它就是黄伯禄干支表上附加的那些东西。这不能不是绝大的误会,让人为之深觉遗憾。
参考文献:
[1]路易·巴赞,著.突厥历法研究[M].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
[2]路易·巴赞,著.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3]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652.
[4]催成群觉,索朗班觉.西藏天文历法史略[J].藏学研究,1982(2):22-35.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6[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5485.
[6]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22.
[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74.
[8]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30.
[9]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560.
[1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7-49.
[11]周银霞,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回鹘古代历法[J].敦煌研究,2004(6):62-66.
[12]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88-89.
[13]G.Kara und P.Zieme.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 bersetzung(≡Berliner Turfan Texte Vii)[M].Berlin 1976:S.66,z.1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