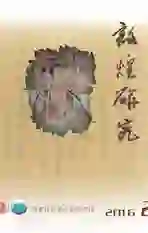敦煌捺印佛像研究
2016-06-03戴璐绮
戴璐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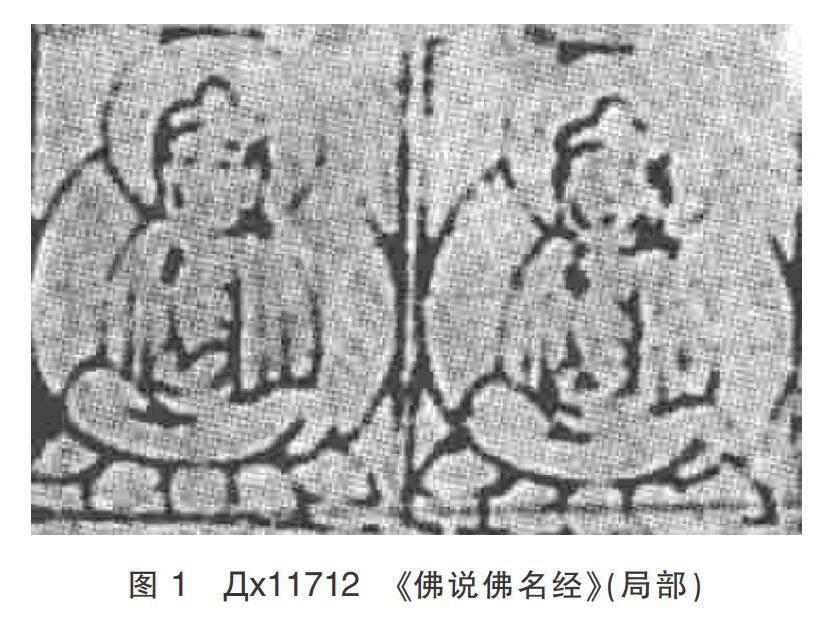


内容摘要:敦煌捺印佛像是敦煌版画艺术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敦煌文献中捺印佛像的分析研究,就如何正确辨别捺印佛像,捺印佛像的用途以及捺印佛像演变为雕版印刷术的原因做了探讨。
关键词:敦煌;捺印;佛像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2-0086-09
Abstract: Dunhuang Buddhist seals are a kind of woodcuts from Dunhuang.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Dunhuang Buddhist sea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ous Buddhist seals correctly, the use of these seals, and the reasons they were eventually turned into block printing.
Keywords: Dunhuang; Buddhist seals; Buddhist images
敦煌版画以佛教题材为主体,是敦煌图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怡、邹晓萍《敦煌版画艺术的风格特点》一文将敦煌版画分为佛经扉画、单叶佛像、陀罗尼经咒、捺印佛像四类。其中“捺印佛像为敦煌版画中单幅形象最简单的作品”,“捺印佛像的刻印是为了组成千佛像,单个形象无论多么简单,将之以四方连续方式重复捺印,亦能构成壮观景象”[1]。王、邹二人虽然将敦煌捺印佛像单辟为一类,但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所谓“单幅形象最简单的作品”只是对于捺印佛像特征的粗略描述。而“捺印佛像的刻印是为了组成千佛像”的论断,虽然符合大部分捺印佛像成组出现的特征,但也不能涵盖全部情况。例如P.3024V上的一幅图像,《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定名为“捺印弥勒变”,其内容是经变图而非单个佛像,绘画场面宏大,线条细腻,恐怕不能以“简单”二字形容。这种经变画出现得很少,通常一方独存或两方并存,并非大量成组出现。虽然不符合上文归纳的捺印佛像的两条特征,但毋庸置疑该图像的制作手法属于捺印。笔者认为,捺印图像与一般版刻图像的区别在于其印制方法,即捺印与刷印的差异。捺印,即将刻好图像的刻板按印在纸上,印在上,纸在下,因为可以多次按印,所以同一卷面中常大量成组出现;刷印,即将刻好图像的刻板刷上墨汁,再以纸张覆盖按压,印在下,纸在上,所以一般一纸一幅。
谢生保、谢静《敦煌版画对雕版印刷业的影响》一文中提到,捺印的千佛、菩萨像可能是佛经扉页画的源头,也是中国木刻版画的开始。郑如斯、肖东发先生在《中国书史》中也说:“这种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2]的确,捺印佛像是敦煌版画中最特殊的类别,它与其他三类版画在印制方式上的差异,见证了敦煌版画制作方式的发展过程。而敦煌版画的发展过程,又是中国印刷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敦煌捺印佛像做进一步的整理研究。接下来笔者将根据之前的定义重新整理敦煌捺印佛像资料,简述敦煌捺印佛像的辨别及其用途,并据此对捺印佛像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关系加以补充。
一 敦煌捺印佛像资料的重新整理
从捺印佛像的制作方式入手,笔者参考邰惠莉《敦煌版画叙录》收录的版画资料 ,以及王怡、邹晓萍的分类标准,重新整理敦煌捺印佛像资料如下:
P.4086 禅定千佛
说明:每列三幅。
P.4087、 P.4013、 P.4514/17(A)、 P.4514/22
游戏坐菩萨
说明:每列三幅,每幅7.5×6.1cm。
P.3880 禅定千佛与游戏坐菩萨组合
说明:左半为禅定千佛,同P.4086;右半为游戏坐菩萨,同P.4087。每列均三幅。《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与邰惠莉著录有P.3880V,按其图案与
P.3880方向相反,当为同幅印墨透于纸背所致。
P.3943、P.4728、S.P.255(1)、S.P.255(2)、
P.4024bis西方三圣
说明:每幅6.4×6.1cm,每列四幅。
P.3528、P.5526、P.4514/21、P.3970、S.P.17、S.11390A、S.11390B、上博022 禅定千佛
说明:S.11390A、S.11390B仅存两幅千佛残像,S.P.17残,每列至少三幅,捺印模糊,其余禅定千佛像均每列四幅。其中P.3528捺印不均匀,从其错列情况来看,第一排当为横排捺印,此后依次纵向捺印。
P.4514/19 西方三圣与捺印佛像组合
说明:左半为西方三圣,同P.3943等;右半为禅定千佛,同P.3528等。
S.9488、台北141 亭阁式塔
说明:每幅5.9×2.9cm。S.9488残,可见两行三列亭阁式佛塔痕迹。台北141每列五幅。
P.3954、S.7001 禅定千佛及亭阁式塔组合
说明:亭阁式塔同S.9488等。P.3954禅定千佛每列三幅,五列一组;亭阁式塔每列四幅,两列一组。S.7001除第二组列千佛十二列外,同上卷。
P.3938、 P.3961、 S.P.7、S.P.258、 S.P.259、
Дx19088、Дx19089、Дx19090 供养菩萨
说明:P.3961现存每列19幅,7幅为一组,共三组(首组前两行残),每组皆先横向捺印第一行,再依次纵向捺印列。P.3938每列七幅。以上二卷图像排列较整齐。S.P.7仅余四幅。S.P.258、 S.P.259皆残卷,排列不规整,与法藏卷捺印方式不同。Дx19088、Дx19089、Дx19090可缀合,仅存3行,排列最为杂乱。
P.4076、S.P.252、S.P.253、S.P.19、S.9487B、Дx5108 水月观音
说明:每列三幅,每幅7.8×4.8cm。图像在雕刻上有细微差别,线条相同,胖瘦不一,每列图像相同,似为纵向捺印。
P.4078、P.4514/17(B)、P.4514/20、S.P.18、傅图39(188109) 善跏倚坐千佛
说明:每列五幅,每幅5×3.2cm。
P.3957、P.3983、P.4714、S.9483、S.9484、
S.11391 说法千佛
说明:每列四幅,每幅6.4×4.3cm。
P.4514/18、P.6008、浙敦200 亭阁式塔
说明:每幅7.3×5cm。P.4514/18、P.6008每列三幅,浙敦200中有一片残片,仅存一尊完整佛塔像。
P.4514/23、S.9481 半善跏倚坐千佛
说明:每列四幅,每幅7×5.9cm。
BD09520 散坐佛与结跏趺坐佛组合
说明: 1纸至17纸前半为每列五幅的散坐佛,17纸后半以后为每列四幅的结跏趺坐佛。
BD15279 木捺佛像(朱印)
说明:每列八幅。
P.4514/24 禅定千佛
说明:每列五幅,朱印模糊,竖排捺印。
傅图38(188108) 佛像卷子
说明:每列四幅,每幅6×5cm。共17纸,先粘贴,后捺印,故两纸骑缝处亦有捺印。
S.11389B、S.11389C 禅定千佛
说明:残片,存留部分一列至少三幅。
Дx11579、日本龙谷大学藏(西域古语写经·古文书类) 印沙佛
说明:俄藏相对完整,每列三幅。佛结跏趺坐,背光、头光上均有回型花纹。
S.13242 印本千佛像
说明:残,已无完整单幅图像。
S.P.254 千佛
说明:每列两幅,每幅10.7×9.3cm。捺印绘彩,图像差异较大。
S.P.260(1) 半跏坐地藏菩萨
说明:每列四幅,尺寸不明。
S.P.260(2) 说法千佛
说明:每列三幅,尺寸不明。
EO.1231 禅定佛像
说明:仅余一幅,6×5.1cm。
Дx1340 说法千佛
说明:残,每列约三四幅,捺印杂乱。
Дx2877 西方三圣
说明:残,每列至少两幅。
Дx5951 观音
说明:每列两幅,画面模糊,仅观音面目依稀可辨。
Дx6274、 Дx6275、 Дx6276、 Дx6277、 Дx11506
说法千佛
说明:Дx11506仅余两幅,墨色较深。其余每列四幅,色极淡。
Дx6282 善跏坐佛像
说明:残,仅余两幅。
Дx7690、Дx7697 禅定千佛
说明:残,仅余三幅。
Дx11056 禅定千佛
说明:残,每列至少九幅。
Дx11579、 Дx19091、 Дx19092、 Ф312 说法
千佛
说明:每列三幅,四卷捺印方式相同。
Дx16400 禅定千佛
说明:残,仅余半幅。
Дx16401 菩萨像
说明:当为禅定千佛,残,每列至少三幅。
Дx16405 善跏坐千佛像
说明:残,仅余四幅。
Дx16406 禅定千佛
说明:残,仅余半幅。
上博008 说法千佛
说明:每列三幅。
P.3024V、P.4514/10(1)、P4514/10(2)、P4514
/10(3)、S.4644V 捺印净土变
说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称之为“捺印弥勒变”,高13厘米,宽10.5厘米。其绘画场面宏大,线条细腻,多为一方独存或两方并存,或可佐证捺印佛像与一般版画、敦煌壁画的关系,具有一定资料价值。
BD14711 西方三圣
说明:一佛二菩萨,高14.5厘米,宽11.8厘米,周围环绕梵文经咒。
S.P.256 药师千佛
说明:每列五幅,无框架,画面中可见“七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廿三日”、“廿九日”、“卅日”等标记。
S.P.257 游戏坐菩萨
说明:每列四幅,朱印。
Дx2881、Дx2882 说法佛像
说明:存三方,印于《开元廿九年(741)二月九日授得菩萨戒牒》中的戒牒题名、师名、弟子名及菩萨名上端。
Дx2889 禅定佛像
说明:捺印于《乾德二年(964)五月八日南赡部洲娑诃世界沙州三界寺授千佛戒牒》中。存五方,三方印于授戒弟子,另两方分别印于授戒时间和授戒师道真。
P.2994、 P.3392、 P.3482、P.3238、 P.3414、
P.3143、 P.3455、S.532、S.4915、P.3482、P.3320、
S.347、P.3140、S.4844、S.4482、S.5313 禅定千佛
说明:此种捺印佛像每方5.8×5.4cm。P.2994《甲子年正月十五日三界寺授李憨儿八关戒牒》、P.3414《甲子年正月廿八日沙州三界寺授李憨儿八关斋戒牒》、P.3455《乾德三年正月十五日三界寺授李憨儿五戒牒》、P.3140《三界寺授弟子李憨儿戒牒》、P.3392《沙州三界寺授八关斋戒牒》、
P.3482《三界寺授八关斋戒牒》、P.3238《乾德二年沙洲三界寺授戒弟子张氏牒》、P.3143《三界寺授女弟子提菩最最戒牒》、P.3482《三界寺授八关斋戒牒》、P.3320《乾德二年九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女弟子张氏五戒牒》、S.347《乾德三年正月廿八日沙州三界寺授八关斋戒牒》、S.5313《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每卷五方,分别印于授戒弟子、授戒时间及授戒师处,其中P.3140最末授戒师一方已残。S.532一卷共有三份戒牒,其中《乾德二年五月廿三日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与《乾德三年正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捺印方式同上;《乾德二年五月十四日沙州三界寺授八关斋戒牒》共七方,四方印于授戒弟子,一方印于授戒文头,一方印于授戒时间,一方印于授戒师。S.4915《雍熙四年五月沙州三界寺授菩萨戒牒》捺印共六方,三方印于授戒弟子,三方印于授戒时间。S.4844《乾德四年(966)正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捺印共五方,其中三方印于授戒弟子,两方印于奉请诸佛菩萨处。S.4482《雍熙四年沙州灵图寺授菩萨戒牒》捺印共五方,其中三方印于授戒弟子,两方印于授戒时间。卷中无授戒师。以上各卷除S.5313疑为墨印外,其余皆朱印。
P.3439、S.2448、P.3206、P.3207、S.1183、
P.4959 禅定千佛
说明:此捺印为3×6的小格佛像组成的千佛印,大小为13×5cm。P.3439《三界寺授李信住李盛住八戒牒》共七方,朱印,有残。依次印于授戒弟子、授戒时间、授戒师三项。授戒师为道真,时间为太平兴国八年(983)。S.2448《太平兴国九年(984)正月八日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存两方,印于授戒师、授戒弟子。P.3207《太平兴国八年三界寺授李憨儿八戒牒》共捺印两方,印于授戒弟子和授戒时间。其余P.3206《太平兴国九年三界寺授邓住奴八戒牒》、S.1183《太平兴国九年某月廿八日[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P.4959《三界寺授李憨儿戒牒》各捺印三方,依次印于授戒弟子、授戒时间、授戒师。
P.3203 禅定佛像
说明:印于《太平兴国七年(982)三界寺邓惠集授戒牒》中,共三方,朱印,每方8.5×5.7cm,各印于授戒弟子、授戒时间、授戒师。
P.3483、S.4115 阿弥陀立像
说明:此种捺印每幅13.8×8.9cm。P.3483《三界寺授张氏八戒牒》、S.4115《雍熙二年(985)五月十五日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捺印各两方,印于授戒弟子与授戒时间。
S.330 《太平兴国七年至雍熙二年(982—985)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六通
说明:此卷出现捺印三种,一种同P.3493等卷中的千佛印,出现于太平兴国七年和九年的戒牒中;一种同P.3203《太平兴国七年三界寺邓惠集授戒牒》中的禅定佛像,出现于《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女弟子程氏戒牒》中;一种同P.3483等卷中的阿弥陀立像,出现于雍熙二年戒牒中。授戒弟子、时间、授戒师处各一方。授戒师均为道真。各戒牒在时间上没有沿承关系,应当为后期缀合而成。
Дx3397、Дx4980 禅定千佛
说明:两片可缀合,为《佛说佛名经卷第十二》。卷首与卷中各一行,与佛名无对应关系,似为装饰栏线。
Дx11712、津艺106 禅定千佛
说明:捺印于《佛说佛名经》中,卷首卷中各一行,与佛名无对应关系。只有轮廓,无五官等细节。二卷或可缀合。
津艺017 千佛、千菩萨
说明:捺印于《佛说佛名经》中,上、中排为千佛,下排为千菩萨。佛、菩萨将经文隔为二栏。上下图案不对应,当为横排捺印。平均二行经文捺印一组。
津艺041 千佛
说明:捺印于《贤劫佛名经》一卷,每一佛名上一尊,捺印绘彩,两种色彩交错。
Дx6285 加彩禅定千佛
说明:印于《佛说佛名经》中,捺印加彩,每一佛名对应一尊。
Дx11574 禅定千佛
说明:印于《佛名经》中,每佛名上方捺印三方。
北大D079 千佛
说明:《贤劫佛名经》中,每佛名上方一尊,捺印补绘。
以上共收录捺印佛像53种,134件。另有8件因数目有限,难以判断,特列为存目如下,以备参考:
S.P.247 阿弥陀佛
说明:仅一幅佛像,环绕梵文经咒,有汉文说明。或为手绘,难以判定。
P.6001 彩绘佛名经
说明:仅余三幅佛像,其中两幅不完全,故难以判定。
Дx3717V 千佛
说明:残片,捺印于“佛本行”三字后,极淡。
Дx9036 佛说佛名经残片
说明:仅一幅佛像,面目不清,或待补绘。
Дx10474 佛说佛名经残片
说明:完整的佛像仅一幅,且有手绘加彩痕迹。
上图031 佛说佛名经卷第六
说明:共十幅,用于“从此以上”总结句头,单幅差异较大,但有挡字现象,不排除为捺印图像。
上图086 佛说佛名经
说明:仅二幅,有手绘加彩痕迹。
上博023 佛说佛名经
说明:每一佛名上一尊,有手绘加彩痕迹。
二 敦煌捺印佛像的辨别
整理敦煌捺印佛像资料的过程中,时常会面对辨别材料的问题。
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观察卷中的图像是否完全相同。这种方法在面对大量成组出现的捺印图案时十分有效。但在图像数量有限时,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这是因为敦煌捺印佛像在制作时存在多模并印和印绘结合的情况。
多模并印是敦煌捺印图像制作时的常见现象。为了保证效率,捺印时往往多块刻版轮流印制。这些捺印往往有着统一的图案,但在雕刻时难免有些出入,再加上捺印时墨色不均,使用年限和频率不一,印版损耗情况不同等原因,印制的图像就会产生一些差异。
印绘结合,就是捺印之后,再补绘线条或色彩。敦煌捺印图像中,部分图像只有大体线条,缺少细节,甚至没有面目五官,如Дx11712的捺印佛像(图1),不但线条断续,且缺乏面目五官。这类捺印图案,除了可能是粗劣制作之外,也有尚未完成、须补绘填色的可能。S.P.254中的几幅捺印图案(图2-1、2-2、2-3),向我们揭示了印绘结合工艺中补绘填色的过程。先用统一的模印印出浅浅的线条,定下图像的大致位置和大小,再手工补绘细节,填充色彩。因此,通过印绘结合制成的捺印图案,往往大体结构、大小相同,但在细节上会有很多差异,线条也不如印制时那么流畅平滑,图2中佛像的莲台基本纯属绘制,各不相同。
多模并印或印绘结合制作出的图像,各有各的特点,一般在单一出现时比较容易辨认。但若在一卷中同时使用,制作出的图案就会出现较大的差别,其图案的相似度甚至不如一些精美的绘制图像。因此,虽然捺印图案在线条、墨色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常常大量出现,通常可以很快辨认,但由于多模并印和印绘结合情况的影响,再加上学者常见的影印图版部分失真,图片质量与原卷无法相提并论,使捺印佛像的辨别障碍重重。例如邰惠莉在整理敦煌版画资料时,将P.4639《佛名经》(图3)中的佛像当作捺印彩绘。卷中的捺印佛像排列整齐,图案比较统一,在细节上比S.P.254中呈现的捺印图案更加一致。但仔细观察该卷,可以发现许多莲座上的颜料遮住了佛名开头的“南”字上部,可以确定该卷系先抄录佛名,后补上图像。肉眼观察可见图中各佛像大小不一。经测量,该卷中的佛像高度在4.2cm到5.1cm不等,宽度在3cm到3.5cm不等。此外,佛像中头光与背光的位置也多有出入,其中“南无大灯佛”的头光与背光等高,而其他佛像的头光都明显高于背光。这在捺印佛像中是十分少见的,即便是采用了多模并印与印绘结合手法制作的捺印图像,其单尊佛像的大小和结构也会基本一致。再加上上排左部的“南无提沙佛”和“南无宝藏佛”,中间的“南无乐说聚佛”和“南无法自在佛”都出现了因为绘制得太近,其中一尊的背光将另一尊的背光遮挡了一小部分的现象,这与捺印图像会发生重合的现象完全不同。在该卷中,佛像重合或遮挡的现象都有出现,似乎是绘制时的无心之举。综上所述,笔者认为P.4639应当不是捺印图像,而是绘制图像。
三 敦煌捺印佛像的用途
敦煌捺印佛像可以按其出现的位置和数量分为三类:一是单独成组捺印,组成大幅的千佛图案;二是捺印于《佛名经》或《佛说佛名经》中;三是捺印于佛教戒牒中。
成组出现的千佛图案种类很多,有禅定千佛、说法千佛、善跏倚坐千佛、供养菩萨、水月观音、地藏菩萨、游戏坐菩萨、亭阁式塔、西方三圣等,通常一幅卷子中连续捺印同组图像。但也有例外,如P.4514/19左半为西方三圣,右半为禅定千佛;
P.3954、S.7001为禅定千佛和亭阁式塔的捺印组合。组合捺印的卷子所存不多,组合起来的每种图案也有单独捺印的卷子,因此组合捺印尚不占主流。另外从画面的线条与墨色来看,大部分佛像在制作上比较粗糙。有些捺印图像虽然画面相对精细,线条也比较丰富,但捺印时墨色并不均匀,排列上也多是紧凑而不整齐。由此可见,大部分成组捺印的千佛图案的主旨并不在于审美,而是出于实用的目的。
谭蝉雪先生的《印沙·脱佛·脱塔》一文提及千佛版画与印佛作法的关系:“印佛作法是释教修行建福的方式之一,以木刻或铜铸之佛和塔形象印于纸上、净沙上或虚空中……纸本绢画属于印佛作法。”[4]由此可见,部分捺印佛像应该是当时的佛教信徒为禳罪消灾、修行功德而印制的。不过谭先生此文重在说明与敦煌印沙佛会有关的印沙、脱佛、脱塔活动,对纸本捺印佛像只是一笔带过。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著《佛徒印像考》一文,其中引及唐代义净《南海寄归传》卷431“灌沐尊仪”条云:“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5]用以说明印佛之俗来源于印度,此说甚是。唐金刚智译本《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云:“或以七俱胝佛像塔印,用印香泥、沙上、纸上随意印之多少,如念诵有功德。”[6]可见印佛作法与念诵佛号的性质相同,都是为修行功德之用。
邰惠莉在论述S.P.256一卷时,曾提及该卷画面中可见“七月八日”、“十四日”、 “十五日”、“廿三日”、“廿九日”、“卅日”等标记,邰猜测其当为八关斋所用之道场画。“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廿三日、廿九日、卅日”又称为“六斋日”,是在家信徒每月受持八关斋的时间。八关斋,又称八关斋戒,是佛陀为在家人所制出家法门。一般修持八关斋戒是不需要道场的,且道场画也没有标注斋戒日期的必要,再加上该卷的日期出现得十分均匀,基本每19幅出现一次,因此笔者猜测,这些千佛可能是在家信徒在六斋日修持八关斋戒的同时印佛作法、修行功德所作。
大幅千佛图案往往呈现有规律的空隙,将图案分隔开来,但是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例如P.3961(图4)现存每列19幅,7幅为一组,共三组,每组皆先横向捺印第一行,再依次纵向捺印列。而P.3938(图5)每列七幅,捺印方式类似。笔者原本以为这些空隙的出现当是捺印者出于裁断的需要故意为之。不过通过更加清晰的彩图来看,恰恰相反,大幅的千佛图案是由数张单页黏合而成的。从P.3961的印制方式来看,虽然粘贴处有明显空隙,但黏合的骑缝处又有捺印图像覆盖,可以推断其捺印方式基本是一张纸印完之后即粘上下一张继续捺印。由此可见,捺印者并不清楚自己一共会捺印多少尊佛像,而是在修行的过程中随印随添。大幅捺印佛像的制作并非出于审美或传播的需求,而是修行者自己印佛作法、修行功德的记录。
《佛名经》或《佛说佛名经》是敦煌卷子中常见的佛教文献,有的只列佛名,有的图文并茂。捺印于《佛名经》或《佛说佛名经》中的佛像,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佛像与佛名无明确对应关系,这样的图像一般简单粗糙,作为装饰边栏捺印,例如Дx3397、Дx4980、Дx11712、津艺106、津艺017中的捺印图像,尤其是津艺017《佛说佛名经》一卷(图6),共捺印三排图像,上、中排为千佛,下排为千菩萨。佛、菩萨将经文隔为两栏。上下图案不对应,平均两行经文捺印一组。虽然单个图像十分简单,但以捺印佛像作为边栏,佛、菩萨组合捺印的制作方式还是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的。二是佛像与佛名一一对应的卷子,卷中的捺印图像一般比较精美,印制之后还会手绘加彩,例如Дx6285、Дx11574。其中Дx11574(图7)一卷字迹工整,书法美观,每个佛名上对应捺印三尊佛像,排列整齐,占到了整个页面的一半。这些佛像似乎已经不止是装饰作用,而是整个《佛名经》的一部分,或许象征着佛的法、应、报三身。谢生保、谢静认为:“在手抄佛经卷首和中间,手绘或捺印的千佛、菩萨像可能是最早的扉页插图。”[7]这些《佛名经》或《佛说佛名经》中出现的捺印佛像可能与佛经扉页画一样,在装饰的同时也与经文本身有直接的联系。
捺印于佛教戒牒中的佛像出现得很早,通常出现在戒牒题名,授戒师名,授戒弟子,以及佛、菩萨名上端。其作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印章。
王书庆的《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对五代宋初戒牒中出现的印章种类、位置做了详细说明,在此不做赘述。但文中将捺印佛像与“沙州都僧统印”并提,默认捺印佛像的作用等同于印章:“印章是给牒机构认可的标识……戒牒中的印章均做工精细、不易假冒,做工精细的印章钤上几方,一则证明受戒的真实性,二则给造假者一个难造的障碍。所以印章在度牒中显得尤为重要。”[8]既是防伪的印章,那么在图案规格、数量、位置上应有一定的规范,因此王书庆提出了“同是道真所传授的戒牒,为什么印章的形状内容及戒中加盖印章的数量不尽相同”的问题。
笔者认为,戒牒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必须有严格的捺印规范以防止假冒。《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一文中也提到,有的戒牒上有涂改的痕迹,并以此佐证施萍婷先生的“废弃说”。同时,佛印应当也不等同于印章,不是用于认证防伪的标识。前面已经提到,敦煌印佛作法的活动颇为兴盛,因此产生了很多捺印佛像卷子和数篇印沙佛文,佛印应是当时的佛教信众普遍拥有的法器,而并非宗教权威独有的信物。同一位授戒师,在不同的授戒时间,选择不同的捺印图案,在授戒弟子、授戒时间、授戒师这几项重要内容上捺印几方佛像,可能是一种宗教习惯,而不是官方认证行为。
四 敦煌捺印佛像与雕版印刷术
辛德勇先生在《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一文中,综合了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秃氏祐详和中国学者向达的研究成果,详细描述了从捺印佛像到梵、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再到真正的雕版印刷术面世的过程[9]。不过,四位学者都只谈及大幅印刷的千佛图案,将其作为“广布所印之佛像或记号而用者”[6]579,因而相较于中国传统的印章而言,捺印佛像具有传播的目的,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印刷术。
上文关于大幅千佛图像的用途的分析中已经指出,这些图像是当时的佛教信徒为了禳罪消灾、修行功德而印制的。在修行的过程中,信徒们不断往已经印满的卷子末尾补充新的纸张,最后形成大幅的千佛图案,作为自己修行的记录。因此,这类卷子中的捺印佛像虽然数量很大,但并不具备传播的目的。而佛教戒牒中的捺印佛像,不论是作为防伪认证还是宗教习惯,同样不具备传播的目的。真正具有传播目的的是印于《佛名经》与《佛说佛名经》中的捺印佛像。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捺印佛像被认为是佛经扉页画的源头,在装饰的同时与经文本身也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图文并茂、互相补充的传播方式与陀罗尼经咒类似。S.P.247(图8)所示《无量寿陀罗尼》,编号者将其作为印本处理。该卷中为一尊佛像,因只有一尊,故无法判断是否为捺印佛像。佛像四边环绕着梵文经咒。卷末以汉字注明:“此无量寿大誓弘广,随求心所愿必从佛眼母。殊胜吉祥……佩之者,身同诸佛,普劝四众,持带结缘,并愿同登真常妙果。”从形式上看,该卷除去卷末汉字说明外,其内容结构与辛德勇先生提及的四川等地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十分类似。对于一般信徒来说,该经咒中的佛像是整幅经咒力量的源泉,而环绕于周围的梵文经咒,作为一种不可理解的符号,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二者相互补充。至于卷末的汉字,是对这组图文的实际功效的具体解释说明。三者都是为了传播而巧妙设置的。
此外,国家图书馆藏BD14711南齐写经卷背印有一组捺印佛像(图9)。佛像高14.5cm,宽11.8cm,
四周环绕梵文经咒。石云里考证卷背同时出现的“永兴郡印”当属南齐,因而推定这些捺印佛像的制作时间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并乐观地认为这些佛像有图有文,版面尺寸相当大,距离成熟的雕版印刷仅一步之遥[10]。笔者认为,这些有图有文的捺印佛像制作年代尚且无法确定。卷背的“永兴郡印”与捺印佛像位置相差甚远,未必是同时印制。且从唐代僧人义净对印度印佛风俗的描述来看,显然是对异国奇俗的记录,可见当时中国并未流行印佛之俗。不过,BD14711一卷中的捺印佛像已经开始从图像到文字的尝试,文字环绕佛像的形式与陀罗尼经咒印本十分相似。虽然其中的文字部分过小,印制不清,显然并非为阅读之用,但其具备传播的用途,可以作为辛德勇先生所述捺印佛像发展为陀罗尼经咒印本的中间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捺印佛像之所以在中国演变为雕版印刷术,是由于传播的需要。捺印佛像传至中国后,除了传统的印佛作法的用途外,还被用于陀罗尼经咒、《佛名经》与《佛说佛名经》等,具备了传播的用途。这是从捺印佛像发展为雕版印刷术的内在因素。
参考文献:
[1]王怡,邹晓萍.敦煌版画艺术的风格特点[J].敦煌研究,2005(2):32-35.
[2]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20.
[3]方广锠.“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63.
[4]谭蝉雪.印沙·脱佛·脱塔[J].敦煌研究,1989(1):19-29.
[5]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M].何健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581.
[6]大正藏:第20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78.
[7]谢生保,谢静.敦煌版画对雕版印刷业的影响[J].敦煌研究,2005(2):46-51.
[8]王书庆.敦煌文献中五代宋初戒牒研究[J].敦煌研究,1997(3):33-43.
[9]辛德勇.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4,16:4-176.
[10]石云里.新公开的敦煌南齐写本上的捺印佛像[J].中国印刷,2000(10):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