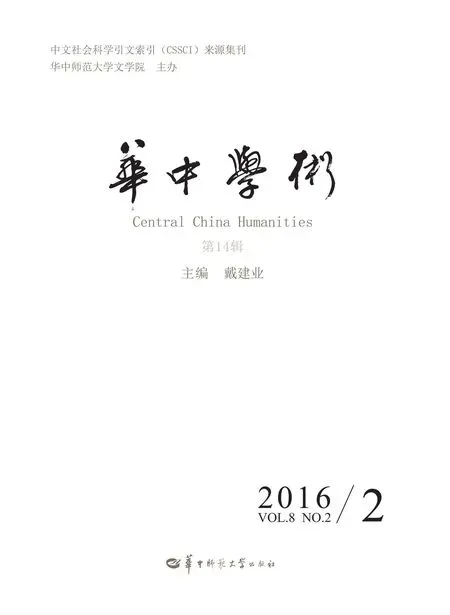诗歌、艺术与真理
——论巴迪欧诗学思想的逻辑展开
2016-05-15张璐
张 璐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诗歌、艺术与真理
——论巴迪欧诗学思想的逻辑展开
张 璐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本文通过对法国当代哲学家巴迪欧的诗学思想进行分析,试图说明他在对不同的象征主义诗人的赞许与舍弃背后所蕴含的反柏拉图的观点,进而指出他对马拉美诗歌的青睐源自其所体现的数理本质。同时,本文还指出了巴迪欧的诗学思想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最后揭示了他把诗歌作为一种真理程序的理由,从而证明了诗歌在巴迪欧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巴迪欧;诗歌;真理;非美学
对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的研究层出不穷,大部分是从本体论或政治学的角度入手,而本文则从艺术批评和认识论的角度入手,对巴迪欧的诗学批评和真理观念进行分析,从而解剖其非美学理论的核心,即艺术的使命这一问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我们将关注巴迪欧在诗歌方面的研究:对于他来说,哪些诗人是关键性的?他看重诗歌的哪一种功能?我们会重点探讨他对象征主义的研究,谈论诗人时代和马拉美、贝克特等,并且,在艺术模仿论上巴迪欧是如何反柏拉图的:就诗歌而言,客观描写和仿真是次要的,甚至不合法的,诗歌是真理探索者和发现者,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者,因为诗歌负责承载关于永恒主题的思想,并在这些主题上进行真理探索。其次,我们会转向巴迪欧因此而产生的哲学理念:在巴迪欧眼中,感觉的地位如何?主观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巴迪欧对诗人和哲学家所做的地位转换意味着什么?我们会谈论巴迪欧与海德格尔在关于诗与数、诗与哲学两个问题上的契合和分歧,并发现:感觉具有临场性,因而带来主观艺术的先锋性与合法性。最后,我们将分析巴迪欧的真理四程序所隐含的价值理论:什么是巴迪欧的非美学的斗争目标?它如何在真理四程序理论的框架内构造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巴迪欧认为,数理、诗、政治创造和爱都是先于哲学的,这些预审者组成了真理预审程序的四种类型,而哲学是姗姗来迟的。
一、 诗歌应当探索真理而非模仿现实
我们知道,欧洲诗歌有着古希腊史诗和中世纪骑士叙事诗的久远的叙事传统,这种“艺术模仿现实”的创作思维是对柏拉图所创立的理念论和模仿说的现实映射。相对而言,19世纪后半叶短短四十年间昙花一现的象征主义诗歌浪潮,是一种对柏拉图美学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叛:象征主义者把诗歌变成一种文学游戏,在玩弄文字中表达诗人的感觉。20世纪对柏拉图的反叛是全方位的,在伦理学、美学、绘画、雕塑、音乐、建筑、戏剧等诸多领域,都发展出各自的直觉主义、先锋派、象征主义、抽象艺术、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等,而象征主义诗歌就是这一浪潮在文学上的典型之一。
欧洲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思路与当时柏拉图主义引导的帕尔纳斯派的客观主义为敌,大张旗鼓地提出主观诗歌。象征主义诗人对现实有着明显的厌恶情绪——波德莱尔在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就是典型——他们把诗歌当成一种逃避和反抗模仿现实的武器,试图回归浪漫主义潮流,并更进一步寻求灵性、想像力和梦幻的感觉,并且希望散文、小说、幻想、故事都进化成类似的诗歌意义,旨在通过强有力的象征符号来暗示诗人设置的客体,把诗歌变成谜语嬉戏。这种隐喻化与暗示性的操作手法,通过声音、颜色等直觉赋予一些画面或物体象征意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并与当时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潮流交相呼应。
象征主义抒情诗饱受诟病的是它晦涩的文学技法,也正是这种晦涩使象征主义抒情诗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在欧洲潮起潮落如过眼云烟。瓦尔特·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中探究了抒情诗在欧洲的窘境:难懂且从未流行[1]。本雅明站在艺术的大众化的视角来看,认为抒情诗相比叙事诗或其他叙事文本难以获得读者的青睐是一种遗憾。而巴迪欧则反之,继承了乔伊斯和贝克特等文学家的思想,认为技法上的挑战,不仅仅是对作者的挑战,也是对日益慵懒的读者的重要挑战。这显示出巴迪欧在接受美学上倾向于精英主义,因为象征主义的晦涩技法正是对柏拉图的反叛之一。只有当技法不是“模仿”而是“表现”之时,艺术才真正远离柏拉图模仿说中所谓的“虚假的模仿”,成为有资格表现真理之物。
与巴迪欧相同的是,本雅明引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称,“只有诗人才是胜任这种经验的唯一主体”[2],并称波德莱尔的诗肩负着国家大计般的使命。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与时代经验、与民族—国家的关联密切,这点也是大多数批评家都认可的。让-保罗·萨特,即便他对超现实主义的诗歌颇不以为然,并自称与诗歌无缘,但也写了《波德莱尔》一书,力图重演这位诗人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人的心声。可见,象征主义之所以受大部分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尊敬,在很多现代思想家眼中都是欧洲文坛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的文学标志,主要是因为象征主义抒情诗所表达的主题正是当时,乃至现在的城市人的存在状态,因为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与工业化初期城市生活的混乱息息相关。在主题的选择上,象征主义乃至之后的荒诞派诗人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每个诗人各自都有别于他人的重要主题或持续一生的主题,这奠定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学价值。比如,波德莱尔的主题有“震惊经验”“大众”“赌徒”,马拉美的最典型的主题则是“数”和“骰子”,兰波的主题有“无序”“语言”“爱”和“地狱”,而贝克特的核心主题是“生存”“词语”“思想”。
巴迪欧最熟悉和青睐的作品正是马拉美、兰波、贝克特三人的,而这主要是出于对他们作品主题的喜爱。比如巴迪欧非常重视贝克特的诗歌《最糟的,嗯》,诗中用“双眼”“词语渗出的”“来源是头脑的软软的物质”等隐喻和符号来指代“思想”和“精神的物质形象”。巴迪欧借贝克特之口想说的表达的是这个观点,即诗歌以最简单直接的形式承载思想。因此有人提出了“兰波 —贝克特—马拉美”序列,来归纳巴迪欧的美学批评的核心视野。[3]其次,巴迪欧在诗歌批评中归纳了一个“诗人时代”(ge des poètes),列举了七位诗人。他认为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存在着与哲学的缝合,正是这种缝合,使得诗歌成了巴迪欧后来所谓的“哲学的程序”。他说道:“就我所关注的诗人而言(不过我认为诗人时代已经终结,从这种终结的立场上看,我自己的名单也弄完了,最后这个名单也终结了),我认为有七个关键性的诗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诗人’——他们不可能获奖——但他们是诗人时代的代表和亮点。这些诗人中荷尔德林是他们的先知,是预示着诗人时代来临的浮标,其他几位诗人都是巴黎公社之后的诗人,他们代表着展现为有导向的意义的无导向型的开启。他们是马拉美、兰波、特拉克尔、佩索阿、曼德尔施塔姆和保罗·策兰。”[4]最后,巴迪欧也认可一些非欧作家,比如阿拉伯语诗人拉比德·本·拉比·阿,但因为译介较晚的原因,对他们的谈论只停留在只言片语。但我们可以说,巴迪欧的诗学荣誉大厅是开放给全世界的,只要那些作品能说出真理。
然后,反过来,也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除了巴迪欧青睐的那些诗人,还有谁被刻意忽略掉了?巴迪欧说,在欧洲诗歌里,他的名单已经终结了。而在整个象征主义浪潮中,他很少提及另一些在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例如波德莱尔、魏尔伦、里尔克、叶芝、艾略特等。我们无法想象一位法国哲学家没有读过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主题和技巧在现代诗歌上的贡献是公认的,因此唯一的理由是,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不足以支持巴迪欧的关于诗歌包含观念这一主张。包含观念这一要求贯穿了巴迪欧的所有艺术批评:他对贝克特、马拉美诗歌的褒奖正是因为两人的诗歌包含了思想和观念,他要求戏剧应当成为“观念戏剧”,他对电影的惋惜则是电影相对于戏剧则更远离“观念”。
如此,巴迪欧对诗歌美学价值的评估已经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与大多数批评家一样,巴迪欧认为现代性的诗歌(乃至现代性的艺术)是反模仿的,象征主义诗歌的晦涩技法就是一例,但他对此并不特别褒奖或贬低。在他看来,除这些技法之外,对诗歌价值起更决定性作用的是诗歌的主题、所包含的观念、所承载的思想、所探索的真理。诗歌是真理探索者和发现者,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者。描写和仿真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诗歌负责承载关于永恒主题的思想,并在这些主题上进行真理探索。而这些永恒主题,比如“爱”、“数”、“生存”等一些主题是首要的,“城市”这个主题则是次级的。这正是巴迪欧所建立的“真理四程序”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 感觉的临场及其把握真理的先锋性
20世纪的学院哲学家们并不认可柏拉图—康德所坚持的理念的客观性和哲学王的理性,我们看到了康德“基本存在论”关于客体的局限性。因而胡塞尔迫不得已重拾主观主义,然后海德格尔继续解构主体和客体拜物教,判断真理与知识是对立的,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哲学交付给诗歌而非科学,开始将诗歌与哲学进行一种“交织”(un entrelancement),但这种交织带来了无导向的迷茫。在海德格尔眼中,诗歌是最美的、最不含技术成分的语言,语言是探知存在的途径,存在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因此,哲学必然在且仅在诗歌中形成和发生。而在巴迪欧眼中,诗歌是哲学接触真理的程序、预审与奠基,哲学是对诗歌的分析、逻辑、整理,并且,并非仅仅是诗歌是有此预审程序的能力,数理、政治创造、爱,也是如此地介于真理和哲学之间的。由此可见,对巴迪欧而言,诗性也不是哲学的全部特性。特别是巴迪欧认为,诗歌以一种制衡而非对抗的方式,与数一起,共同作为真理的发现者、真理的程序而存在(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种可能)。
虽然海德格尔和巴迪欧同对诗歌青睐,但是他们对诗歌赋予的地位不同,这是两位思想家的主要区别。由此就诞生了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与巴迪欧的真理四程序理论。这也是巴迪欧经常被现代哲学界反而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的原因。尽管巴迪欧对理性、逻辑存在进行批评,但没有像其他20世纪的哲学家一样,完全驱逐它;他对诗歌的先锋性地位青睐有加,但也反对海德格尔把诗歌与哲学缝合在一起。巴迪欧于是在《艺术与哲学》一文中提出把诗与哲学进行去结(dénouage)或一种去关联(un dérapport),对诗概念化。这就引出了两人的分歧:海德格尔把对客观性的解构引向了对科学的解构,并把数和诗对立起来,把知识和真理对立起来,不自主地回归了一种古老的二律背反;而巴迪欧马上就质疑了海德格尔建立的这种二律背反的合法性,并认为,诗歌与数学虽然分属完全不同的本质,但数和诗是平行的,而非对立的,是远房亲戚,而非敌人。这时,巴迪欧经常给出的战斗性例证就是他一再重申的马拉美的名诗《骰子一掷》。
巴迪欧批评海德格尔的出发点是令人欣喜的,把我们从二律背反的两个公理的不可调和的悖论中解救出来,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但遗憾的是,他对数和诗之间关系的阐述只停留在诗包含数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剖析数包含诗这个角度。巴迪欧似乎没有揭露出数学和艺术本质上的相关性的另一面:艺术不仅包含数学,艺术也是建立在数学内的,诗(乃至各种艺术)都是数学的复杂形式。比如音乐和建筑,都奠基于代数学和几何学。毕达哥拉斯、莱布尼茨等人都对此有过研究。
让我们暂时先回到巴迪欧的诗学视野,来看马拉美和他的诗。斯蒂凡·马拉美是象征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第一个将象征主义理论系统化的诗人。他认为诗是从无到有、超越经验的独立存在;诗是一种魔术,运用咒语来创造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绝对理念世界。在创作方法上,马拉美十分强调暗示性的重要,其理论具有神秘主义和唯美主义的色彩。巴迪欧称其“借由技巧的清晰可见,这可见性也是诗意思维的思想,诗在能力上超越了感性所能胜任之事”,认为马拉美和象征主义诗人,“他们在命名之熔炉中奠基了所指,后者胶合起字词来让感性的临时消亡能超越时间地存在。”[5]在谈论20世纪的时候,巴迪欧也把马拉美置于与爱因斯坦等人齐高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都被认为是20世纪初叶的标志性人物。巴迪欧在其巨著《存在与事件》中,特地为这位诗人之王留了一席,并且模仿海德格尔留下了对马拉美最大的褒奖:“我自己也曾渴望,哲学能够最终与马拉美的诗歌活动处在同一时代。”[6]也如海德格尔常借荷尔德林的《在柔媚的湛蓝中》一诗里的“诗意地,人栖居在大地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一样——巴迪欧认为海德格尔思想的力量,正是来源于以诗性来结构哲学对客观性的批判(之后则产生分歧)——他也经常借马拉美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比如,巴迪欧为2004年出版的英语版文集InfiniteThought(该书收录了1992年的法语版Conditions和1998年的D’undésastreobscur的几篇文章)一书而专门撰写的《哲学与欲望》一文开篇就说:“马拉美陈述道:‘所有的思想都引起骰子一掷。’在我看来,这个谜语般的公式也意味着哲学,因为哲学提出要思考一般性(theuniversal)——这对所有思考倒都是真的——并且它还基于承诺偶然(chance)总扮演一个角色,一种承诺也是一种风险或一种赌注。”[7]又如,在《哲学宣言》的《诗人时代》一章中,巴迪欧说:“当兰波对‘主观诗歌’施加嘲讽,当马拉美建立起一种观念,即诗歌不发生除非它的作为主体的作者离开,这时他们明白,诗歌的真理才发生了,因为它所陈述的既不拔高客观性也不拔高主观性。”[8]
在巴迪欧眼中,对柏拉图模仿说的最佳的双重反叛就是马拉美的长诗《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首诗在形式上与主题上都备受瞩目。文学批评家首先被这首诗的韵律、图形化形式和散文笔调所惊奇,穷尽于讨论其结构[9];而哲学家则完全越过了马拉美在结构上的创新,直接讨论另一个核心——诗歌的主题和符号。这首诗中有不少的符号,如数字、恒星、星座、骰子、船长、海妖,带有毕达哥拉斯式的古代哲人风味,颇为难懂。其中最核心的主题是“数”这个概念。
一些批评者,如切斯拉夫·米沃什,就批评马拉美和象征主义的诗歌陷入了一种赫尔墨斯主义(l′hermétisme)——一种玄奥的晦涩难懂的神秘主义,借用那些没人能说清究竟确切地是什么的象征符号故弄玄虚。但巴迪欧对此予以反驳,指出:“诗既非描述亦非表达。它也不再是对世界的疆域所作的动人绘画。诗是一种活动。诗教导我们,世界并非像物体的收藏般呈现。世界并非与思想对立的。它是这样的——对于诗歌活动而言——临场要比客观性更必要。”[10]正如他一贯的“诗歌反模仿”的态度。
这里,巴迪欧还借此提出了诗的“临场”(la présence)这个概念。这样对诗歌进行定义,便把象征主义的合法性和纯粹的描述性或叙事性诗歌的不合法性的对立展示了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语言文学阵营内的职能与分工重新配置。在这个重新配置下,诗歌的责任变化了:不要客观描述,要主观临场。当马拉美要求我们着手使用“暗示的,永不直接的”词语时,那是一种去客观化的命令,为了迎接突然的临场。因而象征主义诗歌的晦涩难懂,正是因为诗人的私人化的感觉,一种主观心理活动的结果。就像一个人去别人家里总觉得布局乱糟糟的,而主人则没有这种感觉,主人觉得一切东西都安置在自己合适且方便的位置,主客双方只有在一个完美的偶然下才可能契合,不然客人就需要谦逊和耐心来解读主人的布置。因而,对《骰子一掷》中诗人通过符号的神秘来故弄玄虚的批评,只是因为缺乏耐心的肤浅。在这首图形化的诗里,数(Le Nombre)与偶然(Le Hasard)这两个词语,明显地居于显要地位:这两个词语被放大了字号,并且大写。也就是说,马拉美通过骰子这一隐喻,希望揭示和分析的是数学上的偶然性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清晰无误的。
三、 真理四程序背后的价值理论
除了艺术的主观感觉,还有什么是临场的、最接近真理的?我国学者蓝江归纳道:“巴迪欧本身就将马拉美看作自己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后康托尔的集合论数学,以及马拉美的诗学是巴迪欧思想的三大主要源泉),尤其是当巴迪欧将马拉美的诗《骰子一掷》中的偶然性的哲学意蕴充分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几乎成了一个全新的将诗学话语同哲学阐释结合在一起的方式。”[11]这三者恰好是巴迪欧归纳的政治创造、数理、诗三个方面,加上巴迪欧又提出的爱——其实关于爱的伦理学、关于社会契约的政治学、关于感觉的美学都属于价值理论的哲学——这四者,构成了真理四程序,更严格的表述是哲学接触到“真理的预审程序的四种类型”(Quatre Types de Procédures de Vérité)。

巴迪欧在《艺术与哲学》一文中揭示出,数理与诗意之间,在心智上,有一种根本性的对抗。以柏拉图为典型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要求以数理式的权力来取代诗意式的权力,成为哲学、政治、理性能够开始的程序和保障。同时,各种不同的美学学说都对诗歌(艺术)的认识论上的功能表示怀疑,在认识论层面,他们鼓励数理而驱逐诗篇。这使得西方世俗社会的伦理学——关于幸福的算计(边沁)、平等与契约(卢梭)、理性的狡计(黑格尔)、价值与交换(马克思)——都基于数理式思维的。
但是,巴迪欧在《何谓诗歌,哲学怎么看它?》一文中,巴迪欧是反对这种数理和理智(la dianoia)的全能性的。巴迪欧认为,诗歌捍卫心智。诗歌之所以是一种重要的心智捍卫者,巴迪欧直言是因为“在思想中,诗篇与之相对抗的,确切地说就是数学断裂的思维本身的裁判权,数理型心智力量的裁判权”[13]。基于对数理和理智的全能性的反对,巴迪欧试图寻找出其他能够与数理和理智对抗的人类思想领域,而诗歌正是其中的一个范畴。
关于对诗歌这一范畴的正名,《艺术与哲学》一文提出把艺术与哲学的关联分成四种,即训导模式(le schème didactique)(艺术没资格表现真理)、浪漫模式(le schème romantique)(只有艺术才能表现真理)、古典模式(le schème classique)(艺术不能也无须表现真理),认为这些模式在这个世纪已经饱和(saturation),并提出一种批评家广泛称为“非美学式的”(inésthétique)方案(艺术能生产一部分真理)。巴迪欧本人通过对艺术把握真理的内在性和独特性的能力,支持非美学式的艺术与哲学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使得哲学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我们之前已经推演过,巴迪欧如何论证“诗歌探索真理而非模仿现实”,“感觉的临场及其把握真理的先锋性”。所以,诗歌是临场的,艺术是临场的,感觉是临场的。感觉是先锋的,艺术能接触到真实,诗歌有责任承载真理(可以类比同样推演其他三个范畴)。那么,什么是不临场的、缺席的?哲学是不临场的、缺席的、间接的。这就是巴迪欧把艺术和真理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并把哲学排斥出“真理的第一接触者”的方式。
继而,巴迪欧强调了诗人的地位。他认为诗人和他们的诗歌的思想深度并不落后而是先于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理论,而迟到的哲学家们的努力则是逻辑化、系统化诗人们已经发现的真理。并且,哲学家们不但借诗人(艺术家)之思,还借数学家科学家之思、政治家之思、伦理学家之思,来运用在其各自的形而上学中——前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往往也都有数学家、政治家、伦理学家、艺术家的身份。但自从柏拉图的模仿说拔高了哲学的先锋性,建立起哲学与真理之间的唯一的直接性地位(且抬高哲学王的合法性并贬低了其他职业在其理想国中的地位),而继承和发扬柏拉图主义的中世纪神学和后神学时代的欧陆哲学,都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混淆了这种先后顺序。直到20世纪,反柏拉图的三股浪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形成了思想界的大规模布局,才使得哲学家反哲学家(柏拉图主义)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并奠基了巴迪欧的这种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解读巴迪欧的理论为回归前柏拉图时代的认识论的考古学。
这便是巴迪欧以对认识论层面的解构和重构为开端,建立起一套价值理论:如果我们以艺术为切入点来看,诗论、非美学理论、真理程序理论是层层递进的。其诗论包含于其非美学理论之内,而其非美学理论也是更宏大的真理程序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注释:
[1] [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39~140页。
[2] [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1页,第147页。
[3] Alvarado,N.,“Poésie et philosophie chez Alan Badiou”,Philosophieetcritiquescontemporainesdelaculture,Paris,Université Paris 8,2007,p. 64.
[4] [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5] Badiou,A.,PetitManueld’Inesthétique,Paris,Seuil,1998,pp.38-39.
[6] Badiou,A.,PetitManueld’Inesthétique,Paris,Seuil,1998,p.61.
[7] Badiou,A.,InfiniteThought:TurthandtheReturntoPhilosoph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Oliver Feltham and Justin Clemens,London,Continuum,2003,p. 39.
[8] Badiou,A.,Manifestepourlaphilosophie,Paris,Seuil,1989,pp.52-53.
[9] 图形诗之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回文诗、璇玑图诗,或苏轼的神智体、形意诗、谜象诗,或后来的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首创的画诗Calligrammes,由书法la Calligraphie和表意文字l’Ideogramme自造的一个新品种。不过《骰子一掷》的字形变化较少,只有大写、字体放大、错位排列这三种技巧。
[10] Badiou,A.,PetitManueld’Inesthétique,Paris,Seuil,1998,p. 50.
[11]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12] [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67页;[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54页。
[13] Badiou,A.,PetitManueld’Inesthétique,Paris,Seuil,1998,p. 33.
【推荐人语】这篇论文首先通过分析巴迪欧对象征主义诗人的批判,指出了他的诗学思想的反柏拉图本质。然后,又将其与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了巴迪欧对马拉美的诗歌中所蕴含的数理的迷恋,具体阐述了其对柏拉图思想的反叛。在此基础上,该文最终确证了巴迪欧对诗人的推崇与其真理四程序的关联。全文观点清晰,论证得体,尤其在对巴迪欧诗学思想的逻辑展开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把握,对厘清巴迪欧诗学思想的来源、背景及其与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