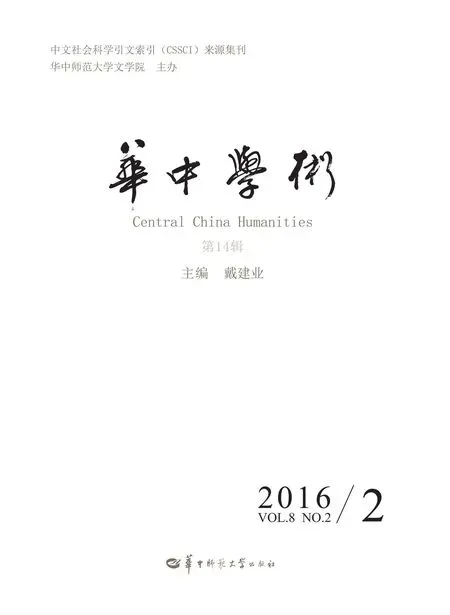汉语起源感叹说的历层证明
2016-05-15夏凤梅
夏凤梅 郭 攀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56;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汉语起源感叹说的历层证明
夏凤梅 郭 攀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56;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历层研究模式较历史研究模式更适合汉语起源感叹说的证明。汉语词、句二级单位语表的历层表现是:原始叹词→派生出的原始动词、原始指代词→派生、衍生出的他类诸词。原始叹词句→派生出的原始动词句、原始指代词句→(原始叹词)·[理性说明语+(语气词)]。汉语的历层事实是对汉语起源感叹说有说服力的证明。
汉语;感叹说;起源;证明
一、 汉语起源的感叹说
语言起源感叹说认为语言起源于原始人因各种感受而引起的感叹,人类语言就是由这种感叹声演化而来。根据是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些感叹词。卢梭指出:“语言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我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起源于人类的激情。……是基于激情的人类社会生活和需要产生了语言。”[1]刘师培亦说:“盖有情然后有声,有声然后有言,……有知而后有情,有情而后有意,情动于中,则形于言。所以吐露其情感,发舒其意志,以表示他人者也。此即语言之源。”[2]
基于属种关系,汉语的起源也因此而有了承袭上述说法的感叹说。不过,作为一种假说,明确度终归不高。在此结合涉及感叹说的相关研究对其核心内容做一些相对具体的概括[3]。
(1) 汉语起源状态与后起状态间是一种源流关系。这种关系可进一步落实到表里二层面。
语里意义:发源于情绪义,以情绪义为基础发展出理性义,进而形成现今情绪、理性共存的语义系统。
语表形式:发源于原始词句兼属性叹词,以叹词为基础发展出其他诸词类和句子结构模式,进而形成现今不同时间层次表义形式共存的语表系统。
(2) 源流所对应内容的存在状态是:单纯混沌状态——部分混沌之“源”与清晰化之“流”并存状态。其中,混沌状态是以混沌理论为基础概括出来的。主要特征是:单位上,集大小不同层级单位于一身;意义上,属宏观情绪类型,对客体的具体感知处于一种蕴含的隐性状态。清晰化状态是将视点主要投射到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上,将混沌的感知逐步析分且相对清晰地呈现出来的状态。
(3) 实现由源至流纵向演化的方式主要有积淀、分解、派生和衍生。其中,积淀是部分混沌之“源”一定程度弱化或变性之后沉积于“流”状态中的方式。分解主要是混沌性意义在总量不变情况下直接对应性清晰化的方式,类型上包括情绪义的细化,但主要表现为混沌性情绪义中处于隐性状态的建立在具体感知和认知基础上的理性义的显化。派生,是以叹词为基础,通过语音形式上的部分改变而发展出新的语言形式来的方式。衍生,是以情绪义为导向,通过辗转关联而获得“源”状态总量之外诸意义或经模声、模态等手段获得新的语音形式的方式。
二、 汉语历史、历层二研究模式适合度比较
汉语起源感叹说证明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具体的语言事实。
汉语语言事实的研究,常用的是历史研究模式,一种以时间过程为纵轴的坐标系作为依托的逆向主域研究模式,如通常沿着上古期(公元前18—公元3世纪)→中古期(公元4—12世纪)→近代期(公元13—20世纪)→现代期(五四至今)展开的研究[4]。此模式之外,我们还曾构建了一种历层研究模式,一种以文明进程为纵轴的坐标系作为依托的顺向全域研究。其核心特征有三[5]:
(1) 以文明进程为纵轴。文明进程是以文明程度为依据,沿着由无至有、由原始至进步、由低至高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内部层次关系是将广义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经系统评价而概括出的三个递相推进的历层性一级文明层次。即动物语言层次、准人类语言层次、人类语言层次。其中,重点关注的人类语言层次内部又继续析分出二级文明层次:准具象性文明层次、准抽象性文明层次、抽象性文明层次。
(2) 顺向研究。以动物语言层次为起点,沿着文明进程范畴内部动物语言层次→准人类语言层次→人类语言层次(准具象性文明层次→准抽象性文明层次→抽象性文明层次)的顺序对各层次语言系统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过程和规律展开研究的一种路向,一种不套用某一已有语言体系,而将各文明层次语言理论体系的概括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路向。
(3) 全域性研究。人类语言层次的共层范围设定为全域汉语系统,即通常的汉语系统核心部分之外再加上副语言、副文字等边缘部分。
分析发现,尽管汉语起源感叹说的承袭所依托的研究模式主要可归为汉语历史研究,而且采用其模式亦可以对汉语起源感叹说进行证明,但是,历层研究模式对语言事实进行研究的做法更适合汉语起源感叹说的证明,能够更好地提供汉语起源感叹说所需要的语言事实。
起源状态的证明:历史研究模式的做法通常是以现有上古书面语料为据展开断代研究,以上古时期的语言事实对起源状态进行证明。这种做法的不足有二:一是上古时期所属文明层次之于汉语起源状态针对性不强。据考察,汉语起源状态所处的文明层次大致是动物语言层次。因距离5万余年前的原始语言时代相差较远,所切入的时代相对晚近,故上古一开始呈现出来的就是三大文明层次共现且以人类语言层次为主的综合性质。甲骨卜辞中反映人类语言层次的多层联合复句、偏正复句例[6]:
(1) 戊申卜:己其雨?不雨,启,少。(《甲骨文合集》20990)
(2) 戊辰卜:在画犬中告麋,王其射,亡灾,擒?(《甲骨文合集》27902)
以这种综合层次的语言事实证明单一的与动物语言层次相应的起源状态显然针对性不强。二是上古时期动物语言层次的语料极少。如整个甲骨卜辞中,叹词只有“俞”一个。而使用上,原始性独用的亦十分有限。相比较而言,历层研究模式的做法是:以动物语言材料和各个历史时期动物语言层次汉语材料为据对与起源状态相应的动物语言层次展开共层研究,以动物语言层次的语言事实对起源状态进行证明。不难看出,这种做法避免了历史研究模式的不足,更适合起源状态的证明。
演化过程的证明:历史研究模式对过程的研究是沿着时间纵轴展开的,得出的是有序的历史时期。历层研究模式则是沿着文明进程纵轴展开研究的,得出的是有序的文明层次。比较可知,在历史时期序列上,相同文明层次内容往往具有反复出现的特征。如强程度副词中上古诸词位强程度磨损后,中古、近古强程度副词的二次反复更替。其中,上古为“甚”、“孔”、“极”、“绝”、“最”、“至”、“尤”,中古新生的有“奇”、“煞”、“生”、“非常”、“分外”、“极其”,近古新生的有“到大来”、“怪”、“好”、“好生”、“很”、“老”、“十分”、“忒”。而文明层次序列因打破了时空界限就不存在这种反复。无论上古的“甚”、“孔”、“极”、“绝”、“最”、“至”、“尤”,还是中古、近古的“奇”、“煞”、“生”、“怪”、“好”、“很”、“老”、“忒”,皆归为准抽象性文明层次,无论中古的“非常”、“分外”、“极其”,还是近古的“到大来”、“好生”、“十分”,皆归为抽象性文明层次。由此看来,历层研究模式是直线型研究,历史研究模式则是曲线型研究,存在着诸多曲折,乃至于反复的迂回,历层研究模式的做法相对经济一些。
源流所对应内容存在状态和演化方式的证明:存在状态是演化方式的直接结果,彼此有机地关联在一起,无须专门证明。而分解、派生、衍生三方式的证明,尽管二模式都能够实现,但历层研究模式因不涉及演化过程的反复,故证明起来更加快捷。
三、 汉语起源感叹说的历层证明
这里采用历层研究模式对汉语二核心单位发生发展的基本事实进行历层揭示,并通过与汉语起源感叹说核心内容主体部分的一致性比较,对其成立与否进行较为可靠的证明。其中,所据历层研究模式的内容除历层的思想方法之外主要有二:一是系统评价出的三大一级文明层次。二是汉语发生模式上的整体渐细规律。二核心单位,指的是词和句。其中,词级包括了词素。句级指具体的句,还包括同具体的句密切关联的段。
(一) 词级单位语言事实
动物语言层次。表里内容分别概括为:混沌性词级情绪义;原始叹词。这里的原始叹词,类型上指的是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惊讶或赞叹、伤感或痛惜、欢笑或讥嘲、愤怒或鄙斥、呼问或应诺五分类中排除掉“呼问或应诺”的前四类[7],使用上,指的是独用形式。例:
(1) 曾子闻之,瞿然曰:“呼!”(《礼记·檀弓》)
(2) 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吕氏春秋·行论》)
(3) 当然了。这件事儿我们可以向领导说清楚。 哼。(王朔等《编辑部的故事·侵权之争》)
例中的“呼”、“嘻”、“哼”分别表示较为纯粹的惊叹、讥嘲、鄙斥类情绪义。这是动物的人和动物共有的原始表义形式。王力将其叫做“情绪的呼声”,并说:“情绪的呼声是表示各种情绪的……它只是表示一种大概的情绪。”[8]赫尔德否认原始叹词是人类真正的语言,但亦承认原始叹词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基于感觉的纯粹表示情绪的“自然的自发语言”。“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
准人类语言层次。表里内容分别概括为:有所分解的词级情绪义;派生出的原始动词、原始指代词。在此,有所分解主要指的是在混沌性情绪义中蕴含的行为、指示等方面隐性理性义的显化。其中的行为义,王力曾细化为招呼、答应、赞同、否认、追问、叮咛六类。而派生出的原始动词主要是黎锦熙所分叹词类中的呼问或应诺,原始指代词主要是今指示叹词。原始动词和原始指代词仍是独用形式。表允诺、呵斥、追问、答应义例:
(1)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尚书·皋陶谟》)
(2) 朔笑之曰:“咄!”(《汉书·东方朔传》)
(3) “先喝点水,不用忙。”掌柜的说,松开了手。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 “哎!哎!”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老舍《骆驼祥子》)
原始动词和原始指代词今口语中仍大量存在。前者如吴江吴语呼鸡声“喌”,后者则有河北保定话“喏”、江苏淮阴话“呶”、陕西扶风话“嗲”、江苏宿迁话“捏”等[9]。
人类语言层次。表里内容分别概括为:分解、衍生出的词级理性义;派生、衍生出的他类诸词。其中,派生、衍生出的他类词,有的还可一定程度地探寻到其历层演化轨迹。例:
歌。名词“歌”源于原始叹词“呵”。李壮鹰指出:“歌”字的初义就是嗟叹,《黄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声为歌。”注:“歌,叹声也。” 《集韵》:“歌,古作‘可’。”王筠《说文句读》:“可,口气舒也。”这种抒情的叹词“可”又常通“呵”。这样即可建立联系:叹词“歌”源于叹词“呵”,名词“歌”在叹词“歌”基础上转化而至[10]。
许。动词“许”源于原始叹词“许”。杨树达说:“许”从“午”声,“午”即“杵”之象形字。“许”字从“言”从“午”,谓舂者送杵之声也。《说文·臼部》:“舂,捣粟也。从廾持杵以临臼,从杵省。”《淮南子·道应篇》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此“许”为劝力歌声之证也。举大木者当劝力,举杵舂粟者亦当劝力矣。即实言之,举杵劝力有声,“许”字之本义也,口有言而身应之,故“许”之引申义为“听”[11]。
嗾。动词“嗾使”的实词素“嗾”源于原始动词“嗾”。《说文·口部》:“嗾,使犬声。”段注:“使犬者,作之嗾也。《方言》曰:‘秦、晋之西鄙,自冀、陇而西,使犬曰哨。’郭音骚。哨与嗾一声之转。” 原始动词“嗾”的演化过程大致为两步:一是口头使犬自然音至表“嗾使狗追咬人或动物”和“唆使”义的词化。例:
(1)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2) 尔如狗耳,为人所嗾。(《北史·宋弁传》)
二是动词“嗾”与“使”同义复合导致的词素化。例:
百姓冉兴,为人嗾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图画碑帖》)
(二) 句级单位语言事实
因原始叹词具有词句兼属特征,故动物语言层次和准人类语言层次句级单位语言事实同词级单位基本相同。在此,例不赘举,二层次表里内容则分别概括为:混沌性句级情绪义;原始叹词句。有所分解的句级情绪义;派生出的原始动词句、原始指代词句。
人类语言层次。吕叔湘指出:“感叹词就是独立的语气词。我们感情激动时,感叹之声先脱口而出,以后才继以说明的语句。后面所说的语句或为上文所说的感叹句,或为其他句式,但后者用在此处必然带有浓郁的情感。”“大多数句末语气词,虽然主要的作用不在表示感情,却往往可以带有感情色彩……‘啊’字的作用是表示说话的人有相当的情绪激动,凡是用‘啊’的句子都比不用的生动些,就是因为加入了感情成分。感情很强烈,就可以算是感叹语气。”[12]参照以上论述,本层次表里内容分别概括为特定的混清结构模式。
语里:“(混沌性情绪义)·不同程度清晰化的理性义”。
语表:“(原始叹词)·[理性说明语+(语气词)]”。
上二模式中,括号表示有无不定,间隔号表示前后两部分顺序可以逆序组合的选择关系,书面上对应的标点,可以是叹号、句号、逗号、破折号等。语气词,是分解了的混沌性情绪义中部分情绪义仍不同程度被保留的标记。这种模式的语言事实,我们组织学生做了系统的调查,发现其历层过程在人类语言层次内部继续表现出了三类文明层次关系,并历层地呈现出情绪义及其表达形式渐少、理性义及其表达形式渐多的趋势。
(1) 表里内容为混沌性情绪义·不同程度清晰化的理性义、原始叹词·[理性说明语+(语气词)]层次。其中,理性说明语的内容有渐多的趋向。例:
(1) 佥曰:“於!鲧哉!”(《尚书·尧典》)
(2)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3)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庄子·养生主》)
(4) 呜呼!为无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5) 噫吁嚱,危乎高哉!(李白《蜀道难》)
(6) 嗟呼!嗟呼!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汉书·司马迁传》)
(7) 哎唷,哎唷,哎唷,你们看,她还能眨眼睛哪!(王朔等《编辑部的故事·人工智能人》)
(8) 就是要用事实来教育读者啊,自觉地抵制这流言蜚语对社会跟生活的侵袭。哎唷,提高对谣言的,哎唷,抵抗力啊。(王朔等《编辑部的故事·飞来的星星》)
(9) 我要爱歇着,还不来催呢!哼!(老舍《春华秋实》)
(2) 表里内容为不同程度清晰化的情绪义、理性说明语+语气词层次。其中,理性说明语内容亦有渐多的趋向。例:
(1) 帝曰:“畴若予工?” 佥曰:“垂哉!”……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 佥曰:“益哉!”(《尚书·舜典》)
(2) 寡人信之矣。(《战国策·魏策二》)
(3) 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史记·管晏列传》)
(4)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
(5) 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天时欤?地势欤?人事欤?何丧乱之若是也?(《晋书·伏滔传》)
(3) 表里内容为不同程度清晰化的理性义、理性说明语层次。例常见,不赘。
基于上述词、句二类核心单位发生发展的基本事实,再对比汉语起源感叹说核心内容主体部分不难发现,二者间尽管详略程度有别,但整体格局具有较大一致性。
同历史、历层二研究模式适合度的阐述相类似,感叹说核心内容主体部分中源流所对应内容存在状态与实现演化的方式密切关联,无须专门说明。
汉语起源感叹说核心内容、主体部分实现演化的方式有分解、派生、衍生三类,汉语词、句演化方式与其一致性关系从历层演化的表里概括上直接体现了出来。
汉语起源感叹说的源流关系与词、句发生发展基本事实的一致性,下面以表的形式呈现。因语表与语里间存在对应关系,为求经济,一致性的呈现只选用语表形式。

源流感叹说原始词句兼属性叹词以叹词为基础发展出的其他诸词类和句子结构模式词原始叹词派生出的原始动词、原始指代词派生、衍生出的他类诸词句原始叹词句派生出的原始动词句、原始指代词句(原始叹词)·『理性说明语+(语气词)』
据此,不难得出结论:汉语起源“感叹说”基本成立。
注释:
[1] [法]卢梭: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胡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3~22页。
[2] 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北京:国学保存会,1905年,第1页。
[3] 高名凯:《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7~372页。
[4] 向熹:《简明汉语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1~44页。
[5] 郭攀:《汉语历层研究纲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4页。
[6] 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309~313页。
[7]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0页。
[8]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26页。
[9] 陆镜光:《汉语方言中的指示叹词》,《语言科学》2005年第6 期。
[10] 李壮鹰:《嗟叹与咏歌》,《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11]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1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