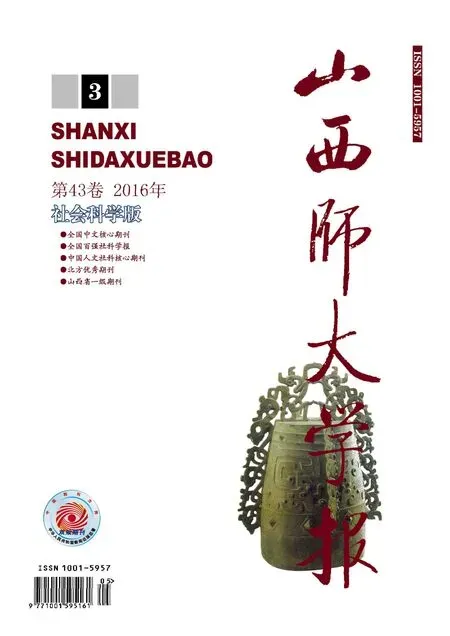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分体归类与评点考述
2016-04-13禹明莲
禹 明 莲
(贵州师范大学 国学院,贵阳 550001)
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江苏武进人。乾隆五十一年考中举人,嘉庆四年考中进士,嘉庆七年卒,年四十二。其年不永,其仕偃蹇。曾前后七试礼部,而后遇散馆。奉旨以部属用,朱文正公珪特奏,改授翰林院编修。《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生事略》《武进阳湖县志》等均有著录。张惠言才识甚绝,事事争当“第一流”。其治经精通虞氏《易》、郑氏《礼》,为清儒《易》学三大家之一;其古文取法韩、欧,与同乡友人恽敬齐名,为阳湖派奠基人之一;其词作品最少而影响最大,辑有《词选》两卷,被风靡百余年的常州词派尊为开山鼻祖。
在赋学领域,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叙录》称皋文“特善辞赋”[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惠言于赋,专家能事,殆无美不臻”[2],今人曹虹则称其弟子董士锡为“赋史奇才”[3],董氏“年十六从舅氏张惠言游,承其指授,为古文、赋、诗、词皆精妙”[4]17—18,渊源所自,足以明其师之赋学造诣。又张惠言的同年好友云:“同年张编修皋文,少好《文选》辞赋,尝屏他务,穷日夜为之,卒乃归于治经,然辞赋亦不废。”[5]可知张惠言少时学赋,高揖马扬,深得古赋之味。其另一友人王灼一日见其所作《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何必托齐、梁以下自域乎!”[6]1377张惠言对古赋的精深识见还体现于《七十家赋钞》的编选评点中,曾国藩云:“评量殿最,不失铢黍。”[7]263刘声木评为“千古绝作”。因此,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亦可称独出冠时,深蕴其对赋学批评的独特贡献。
鲁迅指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选本[8]。编选者对作品的取舍、编次和评论,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编者的批评标准和宗旨,因此总集是一种占有重要地位的批评形式。学界关于《七十家赋钞》的研究,着重探讨张惠言赋学思想的变化、影响及地域关联上。如王思豪由手稿本至康绍镛刻本的差异洞察张惠言赋学观的变迁。[9]潘务正则从常州学风与《七十家赋钞》的地域特征探讨其内在关联。[10]陈曙文认为清常州词派的形成得益于张惠言赋学思想的延伸及影响。[11]这些观点均充分肯定了张惠言的赋学地位及成就。本文由张惠言是编的选录编纂、刊刻评点切入探讨其赋学批评的渊源和价值。
一、《七十家赋钞》的选录观
清初辞赋总集的编选,上承明代复古思潮及科举考试导向的双重因子,呈现出会通古律的批评主题。如清初陆葇《历朝赋格》、王修玉《历朝赋楷》、赵维烈《历代赋钞》、陈元龙《历代赋汇》等均为通代辞赋总集,选录标准上古律兼收。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则涌出大批仅以科举为鹄的律体总集的编选评点,如沈德潜《国朝赋楷》、朱一飞《律赋捡金录》、法式善《同馆赋钞》、朱九山《同馆赋钞》等。而此期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编选评点,独以古赋为宗,止于六朝,显与文坛主流“风尚”悖异。
值得提出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姚鼐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时所编《古文辞类纂》特列辞赋一门,并云“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12]3。可知姚鼐选赋至晋宋而止。十三年后,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张惠言在北京景山官学教习任上所编订的《七十家赋钞》断自六朝,同样以古赋为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使得是编宗旨更为扑朔迷离。张惠言在《文稿自叙》中云“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13]124,王灼将业师刘大櫆所授古文法则转劝张惠言,赋则未必。《清史稿》本传载“惠言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6]13242,可知张惠言赋学是由马扬下及韩欧,而桐城家法的核心是由唐宋八家而统摄三代两汉,这样来看作为辞赋总集的《七十家赋钞》与古文总集的《古文辞类纂》的选录旨趣并不一致。那么,张惠言的编选及归类深味何在呢?先观其目次:
卷一:《楚辞》十二家八十二篇:屈平二十五篇、宋玉十一篇、景差一篇、贾谊一篇、淮南小山一篇、东方朔八篇、庄忌一篇、刘向九篇、扬雄一篇、枚乘八篇、曹植八篇、张协八篇
卷二:周二家十五篇:荀况六篇、宋玉九篇;汉六家十二篇:贾谊二篇、枚乘一篇、邹阳一篇、公孙乘一篇、武帝一篇、司马相如六篇
卷三:汉十七家二十六篇:淮南王安一篇、 孔臧一篇、 董仲舒二篇、 司马迁一篇、中山王一篇、王褒一篇、班婕妤一篇、扬雄七篇、刘歆一篇、班彪一篇、梁鸿一篇、崔篆一篇、冯衍一篇、杜笃一篇、梁竦一篇、班固三篇、傅毅一篇
卷四:汉七家十三篇:张衡五篇、王延寿一篇、马融两篇、蔡邕两篇、边韶一篇、边让一篇、祢衡一篇;魏八家十一篇:王粲一篇、文帝一篇、陈思王植三篇、邯郸淳一篇、何晏一篇、卞兰一篇、嵇康一篇、阮籍二篇
卷五: 晋十一家十二篇:向秀一篇、张华二篇、木华一篇、陆机二篇、陆云一篇、左思三篇、潘岳八篇、挚虞一篇、成公绥一篇、郭璞一篇、孙绰一篇
卷六:宋五家八篇:傅亮二篇、谢恵连一篇、谢庄一篇、颜延之一篇、鲍照三篇;齐一家一篇:张融一篇;梁四家十一篇:简文帝二篇、江淹七篇、沈约一篇、陆倕一篇;陈一家一篇:江总一篇;北周一家四篇:庾信四篇
张惠言选录自屈原至庾信的赋作七十家二百六篇(定稿196篇),自言“通人硕士,先代所传,奇辞奥旨,备于此矣。其离章断句,阙佚不属者,与其文不称辞者,皆不与是”[5],可见张惠言的择选标准甚严。在选源上,张惠言参照众本,择善而从,一字一句均精心校勘,王葆心评论云:“近世张皋文钞七十家赋,于题下自注明某书,并互校其字句于本文下,是又选家于不同各本中又有拣择从善之例,亦以免人持他本以疑此本也。”[14]885如宋玉《笛赋》题下注“《古文苑》”,又如贾谊《吊屈原赋》题下注“《汉书》,序依《文选》”。张惠言认为《汉书》所录《吊屈原赋》较为可信,而序文则从昭明之说。
总集编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文体的辨析与归纳,从中也可看出编选者的主张。如储歆《唐宋十大家类选》分文章为六门三十类,姚鼐《古文辞类纂》依文体划分为十三类等。“一般作法即将文体首先分门,然后系类,以克服列类繁琐,而取得纲举目张的效果”[15]33。徐复观认为,文体之“体”是指形体,中国古代的“文体”即“艺术的形相性”,包含三个方面意义:一是“体裁”之体,或称为“体制”;二是“体要”之体;三是“体貌”之体。“若以体貌之体是感情为主,则体要之体是以事义为主。若以体貌之体是来自文学的艺术性,则体要之体是出自文学的实用性。若以体貌之体是通过声采以形成其形相,则体要之体是通过法则以形成其形相。”[16]133—134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编选评点,则是兼顾选文的体与貌,即艺术性和实用性兼具。
作为授课读本,是编有着明确的源流本末意识,示人以门径。《七十家赋钞》在张惠言生前并未刊刻,其手稿本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直至道光元年康绍镛最早刊刻。从稿本到刻本,我们得以窥见张惠言在赋篇的编选上,曾有如下改动:
卷一:东方朔《七谏》七篇,改为八篇;删除曹植《九咏》,增枚乘《七发》八篇,张协《七命》八篇
卷二:增宋玉《讽赋》,删贾谊《旱云赋》
卷三:增董仲舒《山川颂》二篇,删扬雄《酒赋》,增《太玄赋》、《逐贫赋》
卷四:删王粲《寡妇赋》、应玚《愁霖赋》
卷五:删杨泉《织机赋》、陶潜《闲情赋》
卷六:删顾野王《舞影赋》、庾信《竹杖赋》
张惠言的这些批注,在道光刻本中均遵照并一一改动,是观照其赋学观的最佳依据。张惠言对每一卷都有细致的增删改定,如对卷一赋篇及篇目的增删,东方朔《七谏》上可溯至枚乘《七发》,下可沿及曹植《七启》,体现出循源类聚的分类标准。“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曹植作《七启》,张协作《七命》,皆《七谏》之类”。又关于“七体”类“七”的含义,分歧甚多,如李善云:“《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五臣云:“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前汉东方朔,字曼倩,为太中大夫,免为庶人。后常为郎上书,自讼不得大官,欲求试用。”枚乘说七事以启发太子这一事实本身,“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后继者如东方朔《七谏》,机括大抵相似却再无新意,可见其构思之宏阔,篇制之宏伟。故在篇目上明确指明为七,有助于听者(太子)的接受。因此何焯评《七发》云:“数千言之赋,读者厌倦。裁而为七,移形换步,处处足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独为文章宗。”[17]941而缘于古书体例习惯,七体变为篇目时,则须加上前面序言,即为八篇。宋人鲍慎思云:“篇目当在乱曰之后。按古本《释文》,《七谏》之后,乱曰别为一篇,《九怀》、《九思》皆同。” 此张惠言将七体类赋作定为八篇,应属此意。
从张惠言的选录旨趣看,以温柔敦厚,中正典雅为归,故在手稿本中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赋篇全部予以删除。从张惠言的改动看,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六朝赋所删甚多。不仅在卷一中将属于魏晋之后的曹植《九咏》和张协《七命》改为枚乘《七发》,在卷四、卷五、卷六中所删除的亦均为六朝时期赋篇。张惠言自序载“论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5]又说“其在六《经》则为《诗》”[5],明确将赋体提升到诗的高度,以诗体言志表意的功用量裁赋体。以此为标尺,贾谊《旱云赋》以自然灾害暗喻执政者“政治失中而违节”,显然不合礼教;王粲《寡妇赋》极言悽怆悲凉之伤痛,甚至“欲引刃而自裁,顾弱子而复停”。此外,应玚《愁霖赋》、杨泉《织机赋》、陶潜《闲情赋》、顾野王《舞影赋》、庾信《竹杖赋》均因与儒家诗教的中正之旨相悖,而遭删除。可见,张惠言从赋体出发,删订赋篇时,有着明确的辨体尊体意识。如扬雄《酒赋》,《汉书》题为《酒箴》,张惠言便认为“非赋”而删除。此外,张惠言将七体、颂体则均归为赋体,这一赋学观对后世赋集深有影响,如戴伦哲《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凡例》云:“谱中所列之赋,如《反离骚》《九辩》《七激》《哀时命》《山川颂》等篇,一照《七十家赋钞》例收入。”[18]因此,张惠言选赋时体与貌、形式与内容的综合考量,在乾嘉律赋大兴的文坛仍有一席之地。
二、《七十家赋钞》体例分类考辨
从体例归类看,张惠言既按时代远近分类,又按家数异同辨析,在清代众多的赋集选本中苦心孤诣。其门人董士锡为其撰作祭文最先肯定这一贡献:“今之辞赋,孰就榘规,曹庾而来,其体以衰。先生遐思,探赜钩妙。醰醰愔愔,遗韵入奥”[19],张之洞评价曰:“古体究源流者,宜《七十家赋钞》最高雅。”[20]250张惠言以古赋为选录范围,内涵赋体的源流、风格、本末等批评内涵,第一次以选本形式对古赋及其源流作了归类与评点。
(一)以家分类与渊源本末
张相《古今文综·评文》曰:“赋之分类,约有两涂,一曰分家,一曰分体。皋文《七十家赋钞》,源流本末,条举件系,法刘向之《诗赋略》,此分家之为也。昭明太子撰録《文选》,京都、效祀诸目,部居不杂,此分体之为也。”事实上,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采用以时代为次和以家分类相绾合的体例。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以家数分类看,章学诚谓:“钟嵘《诗品》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于刘向父子。”[21]95然《汉书·艺文志》将各家赋作只列篇数,具体篇目及分类标准均未可知,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用留下不尽的解释。由于时代绵渺,章太炎、刘师培、顾实、程千帆等从风格、地域、体裁等维度进行推测,合理但不确凿。《七十家赋钞》根据时代先后将七十家赋作按内容重新归类并评点,是对《汉书·艺文志》模糊分类观念的辨明与完善。
在“推源溯流”层面上,赋体起源这一历史公案亦是总集编纂绕不开的环节。如萧统认为赋自诗出,荀宋为首,“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22]1,然《文选》的编纂首先是以类而聚,类分之中,又以时代为次,回避赋体起源的纷扰。
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叙》中论赋体起源时,以荀卿在前,屈原在后,“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辞表旨,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畅;不谋同称,并名为赋”[5],又言《诗经》之后,则有“能之者”和“淫宕佚放者”两类人继之,前者“变而不失其宗”,后者“坏乱而不可纪”,似扬子“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划分。此两类赋风的开拓者,即屈原和荀子,“其志洁,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为也”[5],“刚志决理,輐断以为纪,内而不污,表而不着,此荀卿之为也”[5],屈辞与赋体因缘相近,却又不失为“《诗》之苗裔”,于赋体则为权舆。而赋体之独立,始于荀、宋以赋为名的创作实践。如刘勰云:“荀况《礼》《智》、宋玉《风》《钓》, 爱锡名号, 与诗画境。”[23]134比较荀、宋, 荀略为先。因此张惠言在目录编排时,将屈原置首,荀子置后,下及宋玉。张惠言于荀子《六篇》手批云:
六篇连读,前五篇陈《佹诗》,末篇正断之。荀子治学,以礼为要,故首篇赋《礼》,礼必以知行云,故次赋《知》,知者,汤武以贤,桀纣以乱,故曰夫是之谓君子之知与请归之礼不同也,《云》以喻五帝之治也,《蚕》以喻汤武之放弑也,战国时訾汤武者已多,故曰名号不美,与暴为邻,《箴》以喻纵横是也,蚕名恶而理美,箴名美而理恶,故皆曰理,与请归之云不同也。微嫌宋玉《风赋》等九篇次于荀子赋六篇之后,未免时代乖错,白璧微瑕,无伤具体。
这段评语见于手稿本。荀卿赋,《汉志·诗赋略》著录为十篇,今《荀子5赋篇》中有《礼》《智》《云》《蚕》《箴》五赋,张惠言将末章《诡诗》算为赋体,故称六篇。荀赋名为咏物, 实则采用春秋战国间流行的“隐语” 形式, 宣传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和政治主张。思想大于形象, 义理掩压文词。而宋玉则是继屈原之后,好辞而以赋见称的第一人,宋玉《高唐》《神女》等作,对汉代贾谊、相如、扬雄等大赋的成熟和定型有着师范作用。《七十家赋钞》的编纂,宋赋反在荀赋之后,因此张惠言称“微嫌宋玉《风赋》等九篇次于荀子赋六篇之后”,而托之时代乖错,实质上宋稍晚于荀,二者之别属于本末问题。林颐山光绪二十三年重刻《七十家赋钞》指出:“自来儒者立言必则古昔,故虽词人之赋,辗转拟式,如枚乘《七发》、相如《子虚》等篇,其式不无少变,然综覈大要,侈丽闳衍兼寓温雅,固由学诗多识而得,即降而嫚戏诙笑,仍不失为诗人善戏谑兮之微旨,设援词必己出为例,抑末矣。”[24]将七十家赋由受诗学影响多寡,而分为本末之别。枚乘、相如赋作由屈、宋而来,嫚戏恢笑则源荀赋。张惠言《读荀子》亦自言:“一言而本末具者,圣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遗,然而不虚言,言以救世者,贤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习相远。上知与下愚不移,所谓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谓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恶,所谓操其末也。”[13]32圣人之言为本,荀子之言则为末。求观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若求孟子之言,亦从荀子为始。以此来看,张惠言对赋源的认识以本末观而非纯粹时代论,显是别具匠心。
(二)赋篇分合与聚类区分
分家体例外,张惠言又兼顾以体分类。总集以体分类的渊源,可上溯至《文选》聚类区分的方式。所谓聚类区分,是按照题材将赋篇归类。骆鸿凯曰:“由斯选者,清世得三书焉:一曰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二曰李兆洛《骈体文钞》,三曰王闿运《八代诗选》,三书各名一体,虽非承选而作,而编次体例,准的昭明。”[25]290意谓三书选篇虽非承自昭明,在编次体例上则以昭明为准的,上自周秦,下至隋季,限断选材,精宏可考,可谓萧选复现,闓导后学。萧统聚类区分的题材划分形式,是历代类书、总集编纂的典范和参照,《七十家赋钞》亦不例外。《文选》以题分类,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类;张惠言在体例上对《文选》的继承,主要是在分类上根据题材的类聚,如卷一可归为楚辞一系,卷二周二家十四篇,荀况六篇,宋玉八篇,张惠言评曰:“皆讽赋。”在体例设置细节安排上,张惠言又采用与《文选》完全相反的方式。如萧统自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文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22]3即先以类分,再以时分。张惠言卷一以楚辞类为首,卷二至卷六先以时代相次,时代之后,兼考虑赋家与类例的划分,甚至将同一赋家的多篇赋作按不同类别分散置于各卷,有利于从类别上加以区分赋作主题。如卷一楚辞类入贾谊《惜誓》,扬雄《反离骚》,卷三汉十七家二十六篇入扬雄七篇;又卷二汉六家入贾谊二篇:《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六篇:《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同一赋家赋作类型是多样的,赋体自身亦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按赋体分篇的方式内蕴张惠言对赋体的认知和批评。林颐山曰:“武进张编修《七十家赋钞》熟精各种家法,仿刘略旧例,条其家数篇数,又益之以所重家数。”[24]可知,张惠言对七十家赋各家法的谙熟。
此外,由于文体本身的多重内涵,《文选》分类亦颇受后人诟病。萧统共收38种文体,其中骚、七、颂各占一体,吴讷曰:“《文选》编次无序”,姚鼐亦批评其分类不如《汉书·艺文志》,“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张惠言则将三体统归为赋体,避免此弊。又略早于张惠言的姚氏,在编选《古文辞类纂》时,亦“一以汉略为法……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也”,认为齐梁以下赋体气卑语徘,古韵无存,故无可取之处。《七十家赋钞》于北周虽仅选录庾信一家,却入选4篇之多。事实上,张惠言自作赋,亦师法选体良多,“综观一代,惟张皋文《黄山》诸赋,规摹选体,毋惭殆庶”[25]268。此即上文所谓《古文辞类纂》与《七十家赋钞》均选录六朝以前古赋却各有用心:姚鼐反对的骈俪文,却是张惠言年少时的心力所在,是其古文辞赋创作的良好坚石。可见,张惠言与姚鼐虽均以《艺文志》为法,旨趣各异。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编纂,以古为归,仿《汉书·艺文志》和萧统《文选》;又如其为文一样,不同流俗,“皋文学古人之学,为古人之文,荣于古者虐于今。即令假以年寿,而贤如文正,亦第以文章之士目之。皋文之所以立其言者,恐亦未能见之于用,而其文之仅存,固已矫然不屑苟同于流俗”[26]。《七略》《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赋体分类方法,张惠言绾合二氏,寓以己意,还体现在其对所选赋作的评点中。
三、 从评点看张惠言的赋体观念
张惠言评点上承何义门,在评点中对赋篇篇目、作者、真伪等均有考证辨析,是晚明杨慎等复古家所倡导的实学之风之延续。然张惠言评点《赋钞》,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引录清初何义门赋论甚多,但并不是照搬原评。如扬雄《甘泉赋》 题下引《汉书》解题,又引何义门云:“赋家之心,当以子云此言求之,无非六义之风,非苟为夸饰也,其或本颂功德而反事侈靡淫而非,则是司马扬班之罪人矣。”扬雄《长杨赋》尾批引何义门云“长杨之事,尤为荒逸,故其辞切”。张惠言在引用前人评点的同时,还对何氏评点进行再评论,显示出乾嘉学者审慎的态度。
班固《两都赋》尾批:“何义门云:‘前篇极其眩耀,主于讽刺,所谓抒下情而通讽喻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分说两篇,非是此赋大意,在劝节俭、戒淫侈,后篇懼侈心之将萌是其主句,宣上德即所以通讽喻也。”
曹植《洛神赋》尾批:“何云:‘恨人神以下皆陈思自叙其情,君王指宓妃,喻文帝不必以序中君王为疑。’案: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为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处,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兰,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见意处。湘夫人可称公子,宓妃亦可称君王也。”
评点本身是针对作品的篇章字句,张惠言不仅对赋篇大旨对前人有所纠正、辨析,甚至具体到篇章字句的内涵。对于所选赋篇,张惠言态度是有区别的。首先对赋作真伪进行考证,断其是非。如评枚乘《梁王菟园赋》:“此篇奇丽横出,非后人所能伪造,盖传久失真,错脱不可理耳,以意属读,亦可想见风格。”司马相如《长门赋》题下注:“此文非相如不能作,或以为平子之流,未知马、张之分也。” 评扬雄 《蜀都赋》:“此篇错误脱阙,然非伪作。”对于伪篇,因时代近古,张惠言并非完全否定其价值,而是有意择其佳作,或备作考校。如宋玉《讽赋》题下注:“《讽赋》《笛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五篇,皆出《古文苑》与《文选》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所引往往参错,皆五代宋人,聚敛假托为之。以宋玉之文存者绝少,故录之以备好古者参校焉。”邹阳《酒赋》题下批:“《西京杂记》梁吴均伪撰此等赋,皆赝,然亦六朝作也。择其少佳者钞之。”相如《美人赋》:“此恐六朝人所拟,然却是佳作。”还有不能确定是否伪作者则存疑,显示出审慎的态度,如宋玉《笛赋》“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句下夹批:“《文选·文赋》注及鲍明远《玩月诗》注:‘师旷将为白雪之曲’,《初学记》引亦自师旷,起句云‘师旷将为阳春北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艺文类聚》引与《初学记》同,惟‘北鄙’作‘北郑’,‘取’作‘得’,章樵云:‘楚襄王立三十六年卒,后二十余年方有荆轲刺秦之事’,此赋果玉所作也?”显然此句或为后人孱入,或《笛赋》为伪作无疑。
事实上,何焯所代表的是清初官方学派的见解,其评点带有理障的弊病。自清初帝王倚重宋学以控制士人,维护统治,不仅帝王自己热心性道,还利用科举、职官、祠庙等加强舆论导向。《清史稿·选举三》:“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6]3147顺治二年,顺治帝规定“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6]3148。顺治十二年,授先儒朱子熹徽派十五世孙煌,奉婺源庙祀。康熙二十九年,授闽派十八世孙溁,主建安庙祀。关氏三人。[6]3321—3322康熙五十一年“诏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此外,康熙自己亦对朱子性理之书多有研磨。四十四年,拜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6]9898。康熙还树立这种性道观楷模,如甘文焜是康熙削藩时死于吴三桂叛乱的功臣,圣祖南巡,幸杭州,御书朱子诗及“永贞”额赐其子国璧。并谕曰:“汝父尽节,朕未尝忘,此为汝母书也。”[6]9723无疑对士人的臣服有巨大的威逼利诱作用。
而何义门曾任康熙帝八子胤禩侍读,认为不仅朱子有益增志气、长识见,还对朱学以外的学问都甚有帮助。何焯《与徐亮直》:“《朱子语类》全者最宜看,可以增志气,长识见。《四纂》是示学者以朱子学问门户,并杂学亦有助,馆课之暇,切望时加寻味。”[27]《与少章季方书》:“向日止读朱子书,不知程子之深粹。其地位殆孔孟之相越,谨以语贤。昆玉倘能同味乎?”[27]而科举作为帝王统治的工具,在清代初年为了更好地钳制士人,还玩起文字狱的游戏,高压之下,一变而为考证风气。《清史稿5儒林传》载:“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6]13099四库馆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之后,文坛评点之声已渐渐堙没在历史碎片的钩稽整理中了。
对延续宋学思潮,在乾嘉时期反因过度推尊而走向反面。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张皋文《七十家赋钞》持论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如《高唐赋》云:‘传祝已具,言辞已毕,亦不过言祀山灵之礼而已。’皋文云:‘下及调讴。’《羽猎》明用屈子,则礼乐武功皆得其理已,附会无谓矣。《神女赋》云:‘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皋文去褰帱请御、睠顾系心之诚也,若以为赋神女成何语耶?按题为赋神女,若以为屈大夫褰帱请御,更成何语耶?且班婕妤《自悼赋》云:‘君不御兮谁为荣’,古人原不以此等为忌讳也。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也。固矣,夫皋文之论赋也。”[28]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张皋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尚不尽化。然淳雅无有能及之者,早年虽讲汉学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29]可以说,张惠言对何焯评点的继承,甚至走向相反面。如《七十家赋钞》的编纂评点,其根源可上溯至朱子:“选家于前代文家,有所改易增删,已开于昭明太子,而昭明又上依太史公录赋入列传有删取之例也……近世张皋文钞《七十家赋》,于题下自注明某书,并互校其字句于本文下,是又选家于不同各本中又有拣择从善之例,亦以免人持他本以疑此本也。其法亦开自朱子之《韩文考异》矣。”[14]885
与康熙、何焯所倡导的比兴诗教相关,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评点还显示出比兴寄托观念,认为诗赋一体,诗词同源。如张惠言认为,《高唐》《神女》两赋“盖为屈子作也,屈子曾见用于怀王,故以高唐神女为比,冀襄王复用也,不然。先王所幸而劝其遊,述其梦,宋玉岂为此谬妄乎?”《高唐赋》题下注:“此篇先叙山势之险,登陟之难,上至观侧则底平而可乐,所谓为治者始于劳终于逸也。结言既会神女,则思万方开贤圣,此岂男女淫乐之辞邪。”《神女赋》“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夹批:“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冀王之特识不惑于谗也,交稀恩疏,其在迁江南之前乎。”又如傅毅《舞赋》“简惰跳踃,般纷拏兮。渊塞沈荡,改恒常兮”句下夹批:“序既分别郑雅,赋复先拟醉状,明此为淫乐,所以示戒,诗人宾筵之意也。”马融《广成颂》“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此颂以风讲武而极之木产,尽寓属车,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亦异乎班张之旨。”祢衡《鹦鹉赋》“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句加圈,评曰:“何义门云西京之衰,可以再兴,伤时不复,故以寓其意也。”王粲《登楼赋》“白日忽其將匿”句加圈,何义门云:“白日将匿,以比汉祚将尽也。”
《七十家赋钞》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张惠言在北京景山官学教习任上编订。此时期评点之风渐趋于消歇,嘉庆十七年郏抡才《古小赋钞》和嘉庆二十二年王芑孙的《古小赋钞》均以小赋为主,于断句处有圈点但无评论。前者如施源《古小赋钞序》:“马卿《上林》之作,札给尚书;子渊《洞箫》之篇,颂胪宫女。而温丽既成于百日,研炼亦至于十年。渊乎大文,非朝夕已。若夫怀铅殿角,槖笔风檐,听宫漏之声,视花磚之影,虽复思若涌泉,文成翻水,而奏折几扣,行卷数番。揆其体制,小赋而已。”后者王芑孙《古小赋钞自序》云:“识小即小以见其大也,赋者鸿通之业,不穷其变,将无以大之,大之必自初学始,初学天禀有不齐,人力有未暇,研都錬京,作之非俄顷所成,读之非旦夕可既。”二人均取小赋为士子教习读本,这是因为科举律赋有严格限制,往往二三百字为宜,本身并不是鸿裁巨制。此外,此时期尚有谢璈的《丽则堂历代赋钞》于所选有简单的音释,沈德潜的《历朝赋选笺释》,录有孙鑛及何焯的评点,价值不高。因此,继何焯之后,《七十家赋钞》代表了乾嘉文坛赋学批评的高峰。
[1] 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M].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2] 中科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茗柯文补编[M].齐鲁书社,1996.
[3] 曹虹.赋史奇才董士锡的文学成就[J].南通大学学报,2010,(3).
[4] 张惟骧.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M].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
[5]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M].道光元年合河康氏刻本.
[6] 赵尔巽,等.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7] 张惠言.茗柯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 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9] 王思豪.手稿本《七十家赋钞》的学术价值[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4).
[10] 潘务正.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与常州学风[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1).
[11] 陈曙文.《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6).
[12] 姚鼐.古文辞类纂[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13] 严明.董俊钰选注评点《张惠言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14] 王葆心.古文辞通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5]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6]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2004.
[17]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 戴伦哲.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M].光绪九年刻本.
[19] 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M].清道光二十年江阴暨阳书院刻本.
[20] 张之洞撰.司马朝军详注《輶轩语详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文物出版社,1985.
[22]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4]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M].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5] 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6] 秦瀛.张皋文文集序,小岘山人集:续文集卷一[M].清嘉庆刻增修本.
[27] 何焯.义门先生集[M].清道光三十年姑苏刻本.
[28]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M].1943年刻本.
[29]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M].清宣统武进盛氏刻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