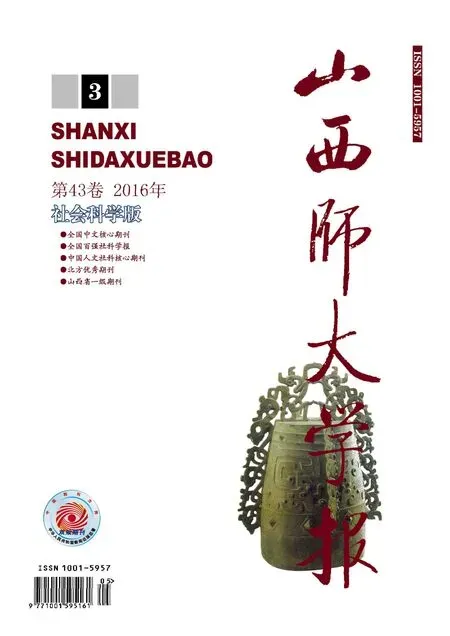跨国代孕法律规制探究从国际法律冲突角度分析
2016-04-13游文亭
游 文 亭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目前各国对代孕的立法态度主要有如下三种:(1)完全支持,如以色列;(2)完全反对,如英国;(3)有条件支持,如美国。中国对代孕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截至2015年12月31日,我国国内尚无一起因代孕引起的法律诉讼或立法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因代孕产生的法律问题。2015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联合国家计生委办公厅等9个国务院厅级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代孕突出问题。除上述《通知》外,我国暂无对代孕明确的法律规范,但此通知足以明确表达我国政府对代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社会对代孕的看法因人而异,政府对代孕的法律规制有所缺失。反对代孕的人不在少数,主要基于道德的考量。代孕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探究的是代孕面临的各种法律冲突如何得到有效解决,各国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对代孕进行明确规制,也可直接认可国外立法而不通过国内法加以规制。各国不同的法律规定使得国内外法律冲突愈发明显,同时也使代孕母亲、委托夫妻、代孕出生的儿童备受非议,这些主体正处在国际规范的模糊地带。通过制定统一的国际规则,订立国际公约或双边协定,不仅可以填补立法空白,还可将备受非议的代孕主体利益合理化。
一、跨国代孕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从医学角度划分,代孕包括两类:一种为传统代孕(不完全代孕),另一种为妊娠代孕(完全代孕)。传统代孕,是指卵子来自于代孕母亲本身,而精子来自于意愿父母中的父亲或是一个不明身份的精子捐赠者,二者通过试管授精[1]怀孕。其受孕过程相对简单且价钱较便宜,风险是精子捐赠者的素质高低及品德是否优良无法保证。[2]妊娠代孕,是当精子和卵子经试管授精形成受精卵后通过培育成为胚胎,再注入代孕母亲体内进行怀孕。[3]这种类型的代孕能够根据基因关系进一步再细分:一种是胚胎基因均不是来自于意愿父母,胎儿和他们没有任何基因关系;另一种是精子或卵子可能来自于意愿夫妻的其中一方,另一方是捐赠者。而妊娠代孕可能涉及五个法律关系主体:代孕母亲、匿名捐精者、匿名捐卵者、意愿父亲、意愿母亲。[4]因为与胎儿有基因关系,意愿父母基因会被胎儿遗传,妊娠代孕带来的法律问题可能较为简单;但在双方基因与胎儿均毫无关系时,这一问题会变得相对复杂,可能涉及从国籍取得到监护争议的各种法律问题。
从经济利益角度划分,代孕分为无偿代孕和有偿代孕。无偿代孕,是指代孕不需要经济补偿或是接受不超过代孕基本费用*代孕基本费用包括孕期产检费用和治疗费用、房屋租金、最低生活保障和人寿保险。的补偿。有偿代孕,也叫商业代孕,指意愿父母除支付代孕基本费用外,还需支付一次性金钱补偿,即报酬。
(一)用国际收养法律制度规制代孕的弊端。目前没有国际统一的法律规范规制代孕问题。《1993海牙国际公约》是目前与代孕相关的最接近的,其中规定了对儿童的保护和在跨国收养方面的国际合作,可以说该公约为代孕行为作出了指导性规范。目前全世界有超过80个国家批准、同意或承认海牙国际公约,包括美国、英国、印度等。2010年6月海牙特别委员大会对代孕问题提出了讨论,最终决定不为国际代孕问题进行立法规范,没有受到明令禁止意味着公约间接承认代孕的合法性。[5]
200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对夫妻向法院起诉,他们请求获得一对双胞胎孩子的监护权,这对双胞胎是通过妊娠代孕在英国出生的孩子,代孕协议签订时代孕母亲同意放弃日后对新生儿的所有母亲权利。但她后来不愿意遵守承诺,拒绝将孩子给意愿父母。英国法律承认代孕母亲为新生儿的合法母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承认意愿父母的合法父母地位,法律冲突由此而生,于是这对夫妻不得不向所在地的英国法院起诉以获得监护权。英国最高法院认定这个案件无法直接适用《国际收养公约》,因为这与该公约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只能根据《国际收养公约》国际冲突规则,选择使用新生儿惯常居住地法律。但该案法官Mark Hedley在审理中发现,这对三个月大的双胞胎无惯常居住地,他们出生在英国,与来自美国的意愿父母也没有基因关系,所以美国并非惯常居住地;但他们的生母与他们也没有基因关系,即使出生在英国也无英国国籍,所以英国也非惯常居住地。Hedley法官最终无法适用《国际收养公约》,只能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庭判例,判定这对夫妻享有双胞胎孩子的监护权。
这个案例同时还证明了《国际收养公约》无法解决的另外两个代孕问题:有偿代孕和无国籍宝宝的国籍认定。首先,关于有偿代孕合理性问题。如果经济补偿能使一个母亲同意放弃对孩子的各种权利,那么收养公约完全认可对收养进行合理经济补偿。同理,代孕也可以有偿,为孕育一个胎儿支付费用,禁止经济补偿可能对代孕不利,这同时也可能使意愿父母离获得对孩子的监护权更加遥远。其次,代孕宝宝国籍取得问题。根据收养公约,父母权利因宝宝出生而获得,因公约规定而解除,这意味着新生儿可以因其生母的公民资格而成为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然而,代孕问题超出了这个范围,因为代孕宝宝没有合法登记的父母亲而无法获得公民资格。《国际收养公约》未规定这种情况,于是意愿父母在获得孩子后只能带着一个无国籍宝宝回到自己的国家,有些甚至因此而无法回国。
可见,代孕已经超出了《国际收养公约》的规定,然而并没有相关法律对代孕的国际冲突进行合理规范。[6]这种法律冲突召唤着新法律规定的出台,以更好地解决意愿父母、代孕宝宝和代孕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不得不承认,《国际收养公约》中规定了合理的国际冲突解决规则,而仍有大量的代孕问题无法通过收养公约得到解决。
(二)孩子利益最大化。当遇到代孕案件,司法机关在无法律规范作依据时,根据法理,应遵从法律原则作出判断。“孩子利益最大化”[7]原则,曾作为美国法庭判定父母是否拥有监护权的标准,判决得到一部分人的通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应当通过更严谨的、相类似的具体规则来判断,但哪个规范最为类似至今尚无定论。
对于“孩子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最大程度挖掘孩子的潜力为原则,包括孩子父母的意愿、孩子本人的意愿、以及为孩子利益最大化实现的相关人等的意见,此外还包括父母技巧、护理耐心、责任感、精神及身体健康程度及家庭稳定等因素;[8]另一种观点认为,海牙会议常务委员会报告显示《国际收养公约》才是最好的执法依据,对于代孕,协议应当补充规定如下内容:(1)尽量使孩子留在他出生的家庭中;(2)如果收养,则以民族内部优先解决为辅助性原则;(3)有必要尊重孩子的收养意愿;(4)保留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5)全方位评估收养父母的抚养能力;(6)为孩子找一个适合的家庭;(7)创造安全的成长环境;(8)提供专业化收养服务。[9]
世界各国统一实施孩子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对各国公序良俗的冲击,比如市民管理政策、公民健康保障、亲属法律规制等社会各方面容忍度都要加大,这一收养标准存在争议是必然的,只是需要通过法律加以完善。英国禁止商业代孕,认为这违反了公序良俗,却在2010年受到挑战:一对英国夫妻雇佣一个美国伊利诺伊州妇女为他们有偿代孕,尽管英国的公序良俗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然而法官认为,否定这对夫妻的请求并不符合孩子利益最大化原则,于是判定夫妻二人对孩子拥有抚养权。
孩子利益最大化不仅仅是法庭对此案作出判断的因素,更应当是法庭裁断任何相关案件的最高准则。平衡公序良俗与当事人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当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孩子利益最大化。事实上,实施孩子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使主权国家在公民资格获得的问题上更加灵活,比如特别政策,或是父母基于“孩子利益最大化”而非“国家利益最大化”得到的监护权,使孩子获得公民资格,也使案件结果更具合理性。
二、国际法律冲突的表现
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将代孕通过立法规制,[10],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承认代孕的合法地位。它们可能只承认无偿代孕的合法性,不承认商业代孕的合法性,如巴西、希腊、荷兰、以色列、南非等国家[11]。以色列1996年率先通过了《以色列胎儿孕育协定》,承认无偿代孕的合法性及相关利益保护,比如承认生母在宝宝刚出生后一周内享有所有母亲权利;英国承认意愿父母为孩子利益而享有的各项父母权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严格处罚商业代孕的同时保护无偿代孕。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立法态度:
(一)开放型。印度被称作“国际代孕中心”,印度政府承认有偿代孕和无偿代孕的合法性,却没有代孕的法律规制。代孕占了印度旅游业的很大一部分,2012年代孕收入为印度的工业产业贡献了高达200万的GDP。印度成为国际代孕母亲的主要供给市场,使得代孕不至于陷入无供给的困境。另外,在印度代孕是非常廉价的,只需花费 25000美元,而在美国至少要翻三倍。印度至今尚无法律规制代孕,只是在2005年,由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公布了一项立法建议,此后无人问津。代孕现象与日俱增,同时成为印度的民族问题和法律问题,面对越来越多的代孕诉讼,印度政府于2008年提出关于代孕的立法提案,但至今这项提案仍未被印度议会通过。
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承认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俄罗斯法规定了代孕需符合一定条件,比如意愿夫妻签署代孕协议前要获得配偶的书面同意。乌克兰虽然也同时承认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但代孕协议中的两对父母同时享有父母权利:传统代孕母亲和她的配偶是孩子事实上的父母,意愿父母是法律推定的父母。
其他一些国家对代孕采取沉默的态度,既不禁止也不承认,如新西兰、泰国。这些国家不明令禁止代孕,可视为对代孕的间接承认,但代孕在这里也并不受到法律保护。
(二)禁止型。意大利、挪威、西班牙采取完全禁止代孕的态度。法国也完全禁止代孕,最高法院曾提出一系列建议反对代孕的合理性;德国也对代孕采取完全禁止的态度,不承认任何代孕协议。
中国没有对代孕进行立法规制,2006年代孕变得较为普遍时政府曾对此行为进行逐步打击,此后香港承认妊娠代孕。[12]直至今天,我国的代孕数量很多,除前文提到的《通知》外未见相关法规出台,中央政府同时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打击代孕的立法态度,但仍未正式立法。
国际对代孕无统一的立法规制直接导致了各国对代孕问题的国内立法缺失。[13]试图去跨国执行代孕协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没有国际统一立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护意愿父母、代孕母亲、代孕宝宝以及这个协议涉及到的每一个当事人的利益。
三、跨国代孕法律规制及解决法律冲突的立法建议
跨国代孕数量的与日俱增说明意愿父母不会因为立法的严格限制而放弃代孕这项选择,因此代孕亟需一个全新的统一立法规制。
(一)父母权利的获得。多数代孕法律争议都在于对父母权利的认定上,对此认定许多学者提出了立法建议。传统科学认为基因遗传是代孕不可磨灭的父母关系,对于意愿父母来说,这也许是很好地获得父母权利的方法,但是否最合理、最科学的方法,有待商榷。目前可认定父母权利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妊娠。许多法院认为父母权利可以通过妊娠关系来解决,却违反了本国对于收养的法律规定。在试管婴儿技术成熟前,妊娠具有不容置疑的亲属关系,如今,因为妊娠而取得理所当然的母亲权利,理论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目前明确规定采用此标准,尽管普遍认为妊娠作为父母权利取得的基础仍相对牢固,但代孕问题的出现往往使问题变得复杂。[14]通过妊娠认定父母权利会带来三个问题:
其一,代孕母亲无法自愿放弃生母权利。无论出于对协议的诚信履行还是对金钱的渴望,代孕母亲如果愿意放弃生母权利,那么基于妊娠所产生的母亲权利便无法改变。如果法庭只通过妊娠关系认定妊娠妇女为孩子的母亲,那么意愿父母与代孕母亲之间的监护权之争将会是个持久战,结果是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无国籍孩子。这种法律规范导致的高额社会成本将会使跨国代孕问题更加恶化,旷日持久的法律战也会导致代孕母亲与意愿父母两败俱伤,这对孩子的幼年成长也极为不利。
其二,代孕母亲放弃她的母亲权利后,意愿父母无法依据现存的收养制度合法地收养代孕宝宝。无偿代孕母亲因妊娠关系被认定为合法母亲,而她放弃母亲权利后,意愿父母只能通过收养成为合法父母。而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生母在世的孩子无法被收养,使得意愿父母取得合法监护权受阻。有偿代孕则更为复杂,代孕费用的存在可能消灭代孕母亲对她所生宝宝进行抚养的欲望,于是无法判定放弃抚养权是否代孕母亲真实、自愿的想法。在德国Balaz有偿代孕案中,当代孕母亲收取了报酬,放弃母亲权利便要面临各种质疑,甚至诉讼。而意愿父母一方也要面临持久的法律战争,以证明她们的收养是合法的。
其三,妊娠认定使意愿父母获得父母权利的途径被阻断,而他们获得监护权的直接依据应当是代孕协议,而非妊娠过程。多数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协议时,就做好了放弃所生宝宝的各种权利的准备,同时被法律赋予父母权利意味着意愿父母要对孩子尽抚养义务。例如,一对土耳其夫妻与一个英格兰代孕妇女签订了无偿代孕协议,后来他们却无法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因为他们没有英格兰的永久居住权。法庭认定代孕母亲尽快地放弃她的母亲权利,同时这对土耳其夫妻也是很不错的养父母人选,但意愿父母没有妊娠过程无法合法获得父母权利,最终这对夫妻只能通过极为例外的“特许方式”取得了英格兰居住令,之后带着孩子回到了土耳其。这就是以妊娠作为父母权利取得标准所带来的困扰。分析这些案例可以发现,父母权利的最后获得者基本都是意愿父母,而他们谁都不希望通过诉诸法律来获得这项权利。
2.基因遗传。科技的发展使试管婴儿变得普遍,于是妊娠不再是认定母亲权利的唯一标准,特别是精子和卵子都来自于匿名的捐赠者时,更加无法判定。如果将基因认定为母亲权利的获得标准,那在如今捐赠者信息保密的时代,当一个宝宝与代孕母亲或意愿父母都没有基因关系的时候,这个宝宝就成为了没有母亲的孩子,没有父母意味着这个孩子无法获得公民资格和法定监护人。本文提及的各案例中法庭最终也都使用了其他标准作为认定父母权利的必要条件。
虽然基因关系可以作为认定父母权利的标准,但这标准并不绝对,它可能会成为许多试图通过基因关系获得孩子的谋利工具。比如张三为获得孩子,于是捐赠精子,一对意愿父母签订代孕协议后,选取了张三精子与某女的卵子结合,生出代孕宝宝,张三根据基因关系自然成了孩子的父亲,而意愿父母却为别人作了嫁衣裳,这显然不合理*美国一个代孕中介曾在国外通过捐精代孕生宝宝,然后将这些孩子以每个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意愿父母,这种获得报酬方式的代孕可以认定为贩卖儿童,被海牙国际公约严格禁止,这个代孕机构已被美国警方一网打尽。。
3.意愿。从上述各案例可以看出,意愿作为认定父母权利的标准颇具合理性。这一标准已被南非政府采用。在以色列,尽管犹太人的法律仍将传统妊娠作为母亲权利获得的标准,但国家法律将代孕协议作为认定父母的依据成为这项规定的例外适用。意愿父母优先于妊娠母亲和基因父母的认定最符合客观事实,在代孕协议各方当事人中,意愿父母获得孩子的愿望最强烈,并为此付出费用,因此倾向于对意愿父母利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如同前文各案中认定父母权利的情况一样,只有意愿父母才是最符合“孩子利益最大化”的父母。从孩子的意愿角度看,他们应当受到出生国和父母所属国的保护,尽快找到合适的父母亲抚养他们成长,这也是符合宝宝意愿的。
当然意愿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代孕协议阻止了本应由生母所尽的责任义务,同时使基因母亲和妊娠母亲放弃了母亲权利,只能由意愿母亲来充当这个角色,换句话说,孩子无法在亲生母亲身边长大,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足。
认定意愿父母监护权的合法性,多数国家主张基于基因遗传,这种规定引发许多争议,且这一标准需要意愿父母一方与代孕宝宝有基因关系才可适用,而通过履行代孕协议反而使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为了避免无基因关系去争夺孩子监护权的法律战争,当孩子的基因不是来自于妊娠妇女时,第三种认定方法打破了传统代孕模式的母亲认定。当然,父母认定这一问题也可以变得非常简单,如南非,法律规定意愿父母就是孩子的自然父母,他们对孩子有合法的责任义务,其他人不会再有任何争议。实质上,这种法律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父母角色获得的途径不同而已。
(二)商业代孕的认可。对于商业性有偿代孕合法性的认定,学界意见不一。多伦多大学法学院Margaret Radin教授认为,商业代孕是对妇女的蔑视和贬低,是男人或上层社会妇女对穷苦妇女的一种压榨。报酬,尤其是宝宝出生后才支付,会成为生母放弃对所生孩子尽抚养义务的主要诱因。也有一些人认为商业代孕等同于婴儿买卖,这种行为应当受到整个社会的道德谴责,并且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他都会觉得自己曾被当作商品进行过交易,因此受到影响。反之,代孕支持者同样也考虑到了女性地位问题,他们认为代孕能够充分保障一个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因为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创造经济价值。
实践中看,多数代孕是有偿的,报酬是对代孕母亲的一种补偿,使代孕协议更加公平。尽管商业代孕被很多人批判,但怀胎十月所受之苦、所作的个人牺牲得到合理补偿应当能为更多人所理解。虽然代孕母亲通过代孕获得了一定的报酬,但这种报酬并非针对婴儿本身,也不能因此否定有偿代孕,否则任何高回报的工作都会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15]事实上,印度一项关于代孕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代孕妇女之所以愿意为代孕作出牺牲,即使无偿,也可因此感到自己的价值。当然,代孕妇女的情感因素或宗教信仰也会成为无偿代孕的主要动机,她无偿代孕可能只是因为乐于助人,享受帮助一对夫妻建立一个完整小家庭的幸福。
对于商业代孕获得报酬的争议并不能导致商业代孕被完全禁止,反而将它推向了一个安全地位。国际社会对商业代孕的态度应当更加倾向于接受,毕竟多数的跨国代孕都是有偿的,代孕应当获得报酬,这也是对女性付出劳动的劳务补偿。在商业代孕被国际认可的同时,应当更加强调对孩子利益的保护,防止借此贩卖儿童。
对于有偿代孕的规制,大胆提出几点设想:首先,报酬的范围应当以代孕付出的成本为基础,这些成本包括医疗、保健、法律费用等,除基本成本外,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作为怀胎十月的辛苦费;其次,报酬应当透明化,所有的费用在代孕协议中列明,在受孕前就将所有费用全部写在协议中,不能随意增加;再次,代孕协议及费用应当格式化,在签订后由第三方盖印保存,防止借着补偿代孕母亲的名义进行代孕宝宝的买卖;复次,代孕机构在代孕前应当充分告知双方当事人商业代孕的各项内容,并提供怀孕期间及宝宝出生后的各类咨询服务。以上四点规制能够尽量保障商业代孕合法化,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商业代孕,但承认代孕的各国可以考虑上述建议。
(三)无国籍宝宝的认定。跨国代孕宝宝公民资格的认定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父母资格的获得对于孩子国籍问题的解决十分重要。
使各国统一公民资格的取得及认定标准是不切实际的,意愿父母所属国及代孕母亲所属国的国际冲突解决是签订代孕协议前要确认的一项重要事件。因此,各成员国应当尊重意愿父母并授权他们的宝宝能够通过国际收养公约获得本国公民资格。
国际冲突规范要求意愿父母在签订代孕协议前,应确保代孕母亲所属国能够确认他们的代孕收养合法,通过这样合法的收养就可以获得公民资格。当签订代孕协议前,如果意愿父母无法确认这些信息,那么意愿父母所属国的代孕机构就应当与代孕母亲所属国的代孕机构沟通解决方案,以确保将来代孕宝宝能够获得公民资格。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代孕中介机构的经纪人都应当在宝宝出生时就确定他所属国的公民资格,这也是设立代孕中介的一项职责所在。
(四)国内代孕管理机构的建立。在各国设立代孕管理机构能够保证代孕的程序化和透明化,减少国际法律冲突及对人权的侵犯。鉴于文化背景不同,各国应依照各自标准分别设立。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有条件地承认代孕的合法性,但对代孕的条件规定不一致。以色列作为国内代孕立法的表率,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际收养公约》为标准设立了代孕中介的国家,在以色列国内任何代孕都要通过代孕中介签订代孕协议;在南非,儿童法规定签订代孕协议的意愿父母必须适格,代孕母亲必须了解她这种行为的所有法律后果,生一个活体婴儿,并获得报酬当作自己的一项收入;在英国,签订代孕协议的男女必须已婚,且法庭应当预先审查所有代孕报酬是否合理;在印度,健康法规定代孕母亲应当在45岁以下,并通过HIV测试,同时确保她没有服用任何刺激性药物,且在代孕前6个月内没有纵欲。
并非建立统一、严格的代孕法规就能阻止各种代孕问题的出现,在国际收养公约影响下创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标准才是最为可取的。各国应当先建立代孕管理机构,再开始进行法律规制,这样意愿父母所属国与代孕母亲所属国能得到更加有效地协商。
此外,代孕管理机构应当对商业代孕进行严格监督,各国间的代孕管理机构也可互相监督。并且管理机构应当是公权力机关,只有在没有利益驱使的情况下,金钱才不会成为扭曲代孕管理机构基本职责的罪魁祸首。解决代孕问题的国际法律冲突,能够更好地保护代孕宝宝、代孕母亲、意愿父母以及代孕管理机构本身,同时也能找到更为良好可靠的解决冲突的方案,形成良性循环。
四、结论
跨国代孕屡见不鲜,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只有通过科学的立法规制才能更好地解决国际法律冲突,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国家之间可以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使国际法律冲突的解决落到实处。[16]
第一,意愿父母应当自孩子出生开始被赋予父母的权利,减少因确认父母权利而进行的长期法律诉讼。这种法律拉锯战对每一个代孕协议当事人的伤害都极大。
第二,各国应当对商业代孕问题持有不同程度的认可,因为有偿代孕协议在某种程度上使代孕显得更为公平。承认商业代孕的合法性能够更好地补偿代孕母亲,使其身心得到更大的愉悦并确保怀孕期间充足的营养供给,这对代孕宝宝及意愿父母也是有利的。
第三,国家间应当加强合作,通过代孕母亲所属国的先前承认,使意愿父母能够顺利为宝宝取得所属国公民资格,减少无国籍宝宝的数量及由此引发的法律冲突。
第四,各国达成代孕协定建立统一的代孕管理机构,安排各项代孕事宜。代孕管理机构应当专业化,对每一项代孕协议及当事人进行严格审查,以确保意愿父母、代孕母亲、代孕宝宝的各项权利不与国内法相冲突。
显然,代孕管理机构能够听取意愿夫妻的意见,特别当本国没有代孕立法时,为他们选择合适的国家进行代孕提出合理的建议。如今方便的网络搜索为许多意愿父母提供了多种选择,尽管这些代孕机构的合法性值得商榷,但他们的有效建议或许能使不少意愿父母避免误入歧途。
[1] 汪志刚.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利用为背景[J].法学研究,2014,(2).
[2] 于晶.代孕技术合理使用之探究[J].河北法学,2013,(1).
[3] 刘强民,王磊,闫晓辉.代孕的夹缝求生——妊娠代孕合法化的法律进路,山东审判,2012,(5).
[4] 康茜.代孕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研究——以代孕契约为中心[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1.
[5] 王轶子,徐艳文.国外代孕现状及其管理[J].生殖与避孕,2014,(2).
[6] 曹丽萍.代孕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研究——以代孕契约为中心[D].长沙:湖南大学,2012.
[7] 王丽萍.论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父母照顾权为中心[J].法商研究,2005,(6).
[8] 张鸿巍.儿童福利视野下的少年司法路径选择[J].河北法学,2011,(12).
[9] Kimberly D Krawiec. Altruism and Intermediation in the Market for Babies [J].66 WASH & LEE L.REV.203.231 (2009).
[10] 周平.有限开放代孕之法理分析与制度构建[J].甘肃社会科学,2011,(3).
[11]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ct. 1990. c. 37 (U.K.) (amended 2008) [EB/OL].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0/37/contents/enacted.2015-10-29.
[12] 任巍,王倩.我国代孕的合法化及其边界研究[J].河北法学,2014,(2).
[13] 刘余香.论代孕的合理使用与法律调控[J].时代法学,2011,(3).
[14] 徐国栋.体外受精胎胚的法律地位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5).
[15] 刘萃,张卓娅.商业性代孕合同性质探究[J].学理论,2010,(10).
[16] Sarah Mortazavi. It Takes a Village to Make a Child: Creating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J].2012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0 Geo.L.J. 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