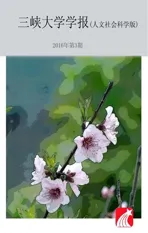论1978年至1985年我国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
2016-04-04侯强
侯 强
(江苏理工学院 思政部, 江苏 常州 213001)
论1978年至1985年我国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
侯强
(江苏理工学院 思政部, 江苏 常州213001)
摘要: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前,我国科技文化进入恢复重建阶段。是时,党和政府基于对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和认识,以及对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刻分析和把握,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强大作用,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从而真正迎来了科技现代化的春天。
关键词:科技文化建设;科技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始实现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党确立了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翻开了科技思想发展的新篇章。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前,为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的局面,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党中央在科技和教育战线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推动了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
一、科技文化恢复重建的理论创新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中波澜壮阔地展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解放思想入手撬动历史转折,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特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时,随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向前推进,党不断探索和回答“发展什么样的科技、怎样发展科技”这个基本问题,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科技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一整套科技文化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形成,并使之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及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其不仅确立了新时期党的科技工作指导思想,使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而且将科技文化建设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变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上来。在扑面而来的新科技革命浪潮面前,如何推进我国的科技文化事业,成为党和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时,科技、文化和教育战线的正本清源,为科技文化的现代化迎来了春天,加快了新时期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
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经济战线来说,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来推进技术革命,认为离开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没有办法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要把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来,社论认为不仅需要对技术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安排好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而且还需要正确处理好科研成果与应用推广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和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扬技术民主[1]。即科技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相互关系、科技工作的方针及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同年6月1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186这不仅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促进了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风气的形成,而且为新时期恢复正确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文化。是时,在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战略转变的大背景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把科学技术真正放在关键的地位上”[3],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80年12月25日,国家科委在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着重研究了新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起草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向全社会发出了科技政策调整的信号,并于翌年转发。其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这个发展方针指导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放弃构建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目标;二是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科技的重要途径;三是科技要将促进消费品的生产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过去的以生产资料和工农业生产装备为主。”[4]这些理论创新对于抑制是时科技领域内的好高骛远、盲目赶超的倾向,摆脱科技工作中“左”的影响,切实地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时代的进步是以理论的创新为先导的。1982年9月,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确立了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发展战略。同年10月,国务院领导人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发表的《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讲话中,代表中央确定了“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5]的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现代化发展理念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其一方面为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科技工作更好地转向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属于我们党的理论创新。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出发,党又及时提出并实施了人才强国的战略。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就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6]41。此后,这一讲话内容不断被表达和强化。1978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为适应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组织部就专门召开了两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胡耀邦在座谈会上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7]会后,保育钧根据胡耀邦的谈话,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将其整理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明确阐明放弃“团结、教育、改造”这一陈旧的知识分子政策,代之以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由此解开了转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结”[8]。1981年3月27日,胡耀邦又在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关于一九八〇年知识分子工作情况的汇报》上所作的批语中指出:“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这就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的重要责任。
1982年1月30日,针对当时要求出国出境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且不少人去而不归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强调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要求对知识分子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把是否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并取得成果,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和单位领导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同年8月22日,聂荣臻在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是与共产主义事业不相容的。”[9]紧接着11月25日,聂荣臻在会见《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同志时,又就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并且要在这方面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呼吁“努力在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的团结友爱关系”[10]。同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其序言部分又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并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这些不断的申说和强调,不仅使得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定论,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观念和社会风气在全社会得以逐步形成。
二、科技文化恢复重建的实践推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肯定了建国以来至文革爆发前17年的科技、教育工作,开始在科技、教育战线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拐点”。是时,在正确的科技政策指导下,科技文化恢复重建的步伐明显加快,大大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为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科技界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1979年8月20日,国家科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紧接着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学十四条”、“广州会议”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进一步澄清了科技战线上的路线是非。在随后的12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转发了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5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同美国政府进行争取回国斗争问题的调查结论》,肯定了5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为争取回国同美国政府进行的斗争是爱国的革命行动,中组部要求各部委为被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妥善解决各种遗留问题。有报道显示,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科技战线的平反人数就有近八万人之多[11]。
与之同时,知识分子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实。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对科学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6]225。1980年2月25日,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在批转的《民政部、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关于闲散在社会上的科学技术人员安排使用意见的报告》中,对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执行。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重视和运用科学家的力量,在整个社会造成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风气”[12]。及至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2]26
为确保基础性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根据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和生物学部89名学部委员的建议,批准从1982年起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全国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该基金采用国家财政拨款,按照自由申请、同行评议和择优资助的原则进行管理,促进了我国科技运行新机制的形成。1982年12月20日,为使全国军、民各方面的科技工作统一筹划、协调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成立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和管理全国科技队伍,领导科学技术长期规划的制定,研究重大技术政策的决策,决定重大技术的引进以及消化和协调各部门的科技工作。
为大力推动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科技管理的科学性,党和政府又十分重视科技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的培训。1980年4月22日,国家科委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举办了科技管理干部学习班,学员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科委和科技干部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同年8月17日,中国科协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积极开展在职科技人员专业培训工作的意见》,指出科技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必须坚持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同时进行的方针,并要求以国际科技界公认的“终身教育制”原则来制定培训方针。
是时,伴随着科技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学术期刊的创办也逐步步入正规并走向成熟。以《自然辩证法通讯》为例,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创刊,于1979年1月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其一方面把国外新颖的学术思想评介到国内,另一方面把国内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坛,担负起了中外双向交流的任务,培育和促进了科学技术哲学等相关学科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同年2月,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外交部关于颁发科学技术人员对外通讯联系和交换书刊两个规定的请示》,废止了1972年颁发的《中国科学院关于对外交换书刊等工作的暂行规定》和《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研究人员对外通讯联系的几点规定》,进一步放宽科学技术人员对外通讯联系和与外国科学技术人员的接触,以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1984年12月17日,为引进从事应用技术的专家来华定居工作,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科委《关于来华定居专家工作待遇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通过提高工作和生活待遇,吸引外籍华人及其他外籍科技专家、学者来华定居工作。
随着科技春天的到来,一些学术活动也开始恢复。1979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茶话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震、方毅、邓颖超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由此,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的学部正式恢复活动。同年2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在政协礼堂又举办了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以肃清“文革”对爱因斯坦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大会总结和赞扬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恢复了爱因斯坦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这次大会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重视,不仅新华社为这次会议专门发了新闻稿,而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分别以一整版篇幅摘要刊登了周培源和于光远的大会讲话稿。1980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商定的中美天然产物化学双边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美方正式代表12名、中方正式代表30名,会议共提出56篇报告、论文和专题讲话。是时,我国科学界与国外科学界的联系正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恢复和重建科研秩序、凝聚科研队伍,一些学术组织也相继恢复重建并展开活动。1979年12月9日至15日,中国光学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出席成立大会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强调不要把光学学会办成官僚机构,而要让科学家自己来管理,把光学学会办成光学科学之家。1980年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北京召开,确认中国科协担负着动员和组织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参加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建设、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同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群众团体进行科学技术交流的任务。这次大会是新中国科技团体发展史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中国科技界继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有资料显示,至1980年止,已恢复和重建的各种专业学会已达106个[13]。
与此同时,新时期中国的科技计划体系也逐渐形成并付诸实施。1982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在各行业、各部门提出项目建议的基础上,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调整为38个重点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组织全国科技力量和有关企业单位共同实施。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技计划,也是我国第一个科技计划,意在解决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的问题。1984年6月,国家科委又将《关于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机遇的对策》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建议研究制定新技术园区的政策,以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对世界高科技发展作出了初步的反应和部署。
此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催动下,一系列科技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如1979年11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规定由国家科委统一领导自然科学奖励工作。该条例将自然科学奖分为四等,规定凡集体或个人的阐明自然现象、特性或规律的科研成果,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重大意义的,可授予自然科学奖。同年12月10日,国务院又批转了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拟订的《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以做好工程技术干部的考核和晋升工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三、科技文化恢复重建的时代意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正本清源,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对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前,党和政府基于对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和认识,以及对我国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刻分析和把握,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强大作用,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是时,我国科技文化建设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开始大踏步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从而真正迎来了科技文化现代化的春天。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赋予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政治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在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中,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最先出现的文化新气象之一。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不仅“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而且进一步指出“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翌年9月1日,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又代表党中央郑重指出,要“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党和全社会认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并且决心尽可能创造条件,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14]。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党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不仅再也没有动摇过,而且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日益趋于充分、全面和深刻[15]。
随着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为例,从1982年开始受理申请项目起至1984年底,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已完成学术论著(文)7628篇,共有152项成果通过专家评议或技术鉴定。其中,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计有2797篇,有些成果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6]。又以轻工业战线为例,在1983年10月11日召开的全国轻工科技工作者先进表彰大会上,1052个项目荣获轻工业部1980年7月至1983年3月科技成果奖,137个集体被授予“全国轻工业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称号,487名科技人员被授予“全国轻工业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17]。是时,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科技战线出现了一片崭新的气象。
其二,促进了人们对知识力量的信仰,提高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科学技术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步步清算和纠正,党和政府进一步认识到过去吃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亏太多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科学家也由此重新成为人们景仰的楷模。以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为例,为满足年轻人积压了多年的学习愿望,我国的高等教育在8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科学素养。据《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显示,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新增普通高等学校211所,几乎平均每3天增加1所,1985年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179.04万人[18]。是时,科学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至成为时人的座右铭。
在全社会对知识力量普遍信仰的同时,科学技术事业也得到了党和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对此,《人民日报》在1979年1月21日发表的社论中明确指出:“事情十分清楚,搞四个现代化,就是以现代的先进技术普遍地装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各个部门,从而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1]翌年,方毅又在《红旗》杂志发文指出,我们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和改造,进而取得更多的发明创造,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6]87。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认识的深化,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显然,这些科学技术的论述已不仅仅是一种科技主张,而且是一种深刻的科技文化态度。
其三,丰富和深化了对科技发展规律的认识,促进了一个理性化科学技术发展时代的到来。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阐明“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6],敏锐地把握住了科技革命的历史发展脉搏,对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认识。及至1983年10月9日,面对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对此,《红旗》杂志也发文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应选择创新战略[19]。显然,面对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为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党和政府开始思考如何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从而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编制15年科技发展规划,强调不片面追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是立足中国的国情,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1983年初,针对国民经济的需要,以解决各行业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而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这个“科技攻关计划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科技计划,是国家指令性计划,标志着中国的科技管理逐步从以科技规划为核心,转变为以一系列中期和年度科技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方式”[20]。1984年6月,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持续不断的猛烈撞击声中,国家科委又将《关于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机遇的对策》的报告呈送国务院,提出了制定新技术园区和孵化器的政策,开启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新探索,对世界高科技发展作出了初步的反应和部署。
其四,推动了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的密切结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整体健康发展。1981年2月23日,国家科委党组在《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针对我国长期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脱节,要求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应当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且要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其首要的任务。在同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指出,我国“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服务。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强大的生产力,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21]。这些科技发展方针的提出,无疑大大推动了新时期科学技术迈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在把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的科技发展方针的正确指导下,我国科技工作的各领域形成了一个共同发展和良性互动的格局。以1981年为例,我国在世界上最先掌握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技术,标志着在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研究方面继续保持着原先国际领先的地位。同年,我国又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3颗卫星,成为继苏、美、法等国之后世界上第4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这些标志着我国在生物科学、原子能技术、运载火箭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卫星通讯技术等方面,已接近或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时,由于在科技工作中开始引入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相当数量的科技研究成果形成了生产力,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以“六五”期间为例,我国“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12个国家级技术开发与科技成果商品化及推广计划,其中大部分是指导性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22]。与之相适应,我国技术市场也开始萌芽。1980年,全国首家“技术服务公司”在沈阳市建立,技术成果开始进入贸易领域。有资料显示,1984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已达7亿元[23]。及至1985年1月10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决定广泛开放技术市场,繁荣技术贸易以促进生产发展,规定只要是能够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一切技术都可以依法转让。这一法规的出台,将我国此前自发形成的技术交易及时纳入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有力地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文化的恢复重建,为我国新时期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并日渐成为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软实力。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科技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带来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发展局面,显著增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社论.把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来[N].人民日报,1979-01-2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方毅.当前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J].红旗,1980(2).
[4]胡维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的科技政策及两点思考[J].民主与科学,2008(1).
[5]赵紫阳.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M]//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765.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胡耀邦.为什么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M]//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8-49.
[8]本刊特约评论员.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N].人民日报,1979-01-04.
[9]聂荣臻同志谈知识分子问题[N].光明日报,1982-09-01.
[10] 聂荣臻.努力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N].人民日报,1982-12-19.
[11] 胡菊芹.在拨乱反正中开拓科技复兴之路——追忆营造“科学的春天”时期的方毅[N].科技日报,2009-08-21.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M]//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733.
[13] 陈建新.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300.
[14]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5.
[15]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255.
[16] 中国科学院发展史(预印本)[M].北京:中国科学院,1989:94.
[17] 张应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1949-1988)[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507.
[18] 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M].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244-245.
[19] 马洪.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术革命[J].红旗,1984(6).
[20] 方新.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49.
[21] 赵紫阳.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32.
[22] 《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科技全球化及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
[23] 《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中国法律年鉴(1989)[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858.
[责任编辑:刘自兵]
中图分类号:G 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3-0091-06
收稿日期:2016-03-16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3BDJ014)”。
作者简介:侯强,男,江苏理工学院思政部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