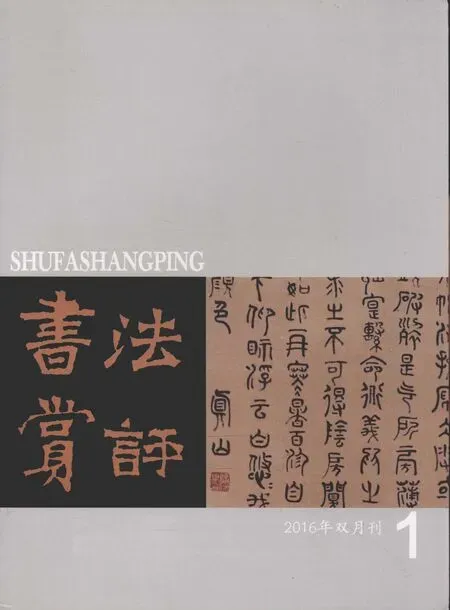蒋维崧行书的艺术格调及其形成探析
2016-04-03吕文明
■吕文明
蒋维崧行书的艺术格调及其形成探析
■吕文明
明代王铎云:“书未宗晋,终入野道。”[1]王铎一生誓守此言,一直在向晋宋大家王羲之、米芾取法,不敢有丝毫懈怠。清人吴德旋评价:“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2]至清代,书家对于书法境界的追求能近乎北宋已属不易,魏晋只是一种艺术理想,于今犹然。今人评价书法也常以魏晋为旨归,书家常标榜自己书出于 “二王”,有魏晋风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代书家极少有得魏晋书法之精髓者。书法到了高层次绝不仅仅是形似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气度的无限接近,现当代书家中能有此气度者寥寥无几,蒋维崧先生是我们所理解的现当代书坛离 “二王”或者说晋人风度最近者。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解读蒋维崧先生的行书。
一、与晋人一步之遥:蒋维崧行书的基本格调
蒋维崧行书远取 “二王”法,近学沈尹默,对此学界已形成共识。而这恰恰是我们剖析蒋维崧行书格调的一条基本路径。“二王”是东晋以来历代书家临摹和学习的典范,学习者虽多,但有成就者却凤毛麟角,原因就是取法不当。蒋先生学习书法的入门功夫是褚遂良和虞世南的楷书,而褚、虞两位大家均是从 “二王”法中来,因此唐代以后他们离 “二王”最近,从褚、虞过渡到 “二王”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从古法的渊源来看,蒋维崧先生与 “二王”之间仅隔着褚、虞两位 “二王”嫡传大家,且褚、虞为后世学王书家中所得最多但又能自成面目者,因此,他们是今人学 “二王”最好的桥梁。蒋维崧的行书不仅得益于古人书法精神的熏陶,他同时还在现实生活中向沈尹默学习,得沈师亲传,这在20世纪诸位书法大家中可谓幸运至极。沈尹默所处的时代正是碑学狂飙突进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他的书法融合着碑学和帖学两种风格。他学习书法从欧阳询 《醴泉铭》《皇甫诞碑》入手,二十多岁开始学习汉碑,后习魏碑,从 《龙门二十品》入手,最喜 《张猛龙碑》,而后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 《元显隽》《元彦》诸志,遂用心临摹。学习北碑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30年,沈尹默先生才出碑入帖,从米南宫而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 “二王”。帖学是其终极追求,但碑学的 “先入为主”早已深深影响了他。所以,沈尹默的行书就是对碑、帖的融合,是以帖学为主线而掺入碑意以壮其气的大胆尝试,沈尹默因此而能在20世纪上半叶诸位大师中标新立异卓尔不群。蒋维崧向他取法自与学习古帖不同,因为沈尹默的书法中掺入了鲜活的碑学生命因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帖学日渐衰退之际,这样的掺杂实际是为当时和今天的书家学习 “二王”寻找一条最好的路径:用碑学的清新和雄壮激活帖学的羸弱和衰相。二十世纪的书法大家大多在践行这样的艺术路径。所以,蒋维崧向沈尹默取法就把自己对 “二王”古法的理解进一步推向前了。从这个视角来看,二十世纪的书法大家中,沈尹默、蒋维崧离晋人最近,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书作品中表现着一种活泼的艺术生机,这就是魏晋格调。这种格调与一般意义上的魏晋法度和魏晋韵味不同,它是一种融冶碑帖于一炉、在继承中追求创新且最大限度地接近魏晋书法精神的新型艺术品格。
二、练得身形似鹤形:蒋维崧行书魏晋格调的形成
明末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论及诗文曰:“夫诗文之道,萌析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3]他指出了诗文创作的三要素:灵性、时代和学问。沈尹默在论及现代书法时也说:“现代书学要开朗、飞跃、生动。我们要比前人写得好。书法要有前人的法度、时代的精神、个人的特性。”[4]沈尹默此言与钱谦益之说略近,都强调时代精神和个人特性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唯有对前人法度的追求与钱说之 “学问”不同,但这也符合书法与诗文两种不同文艺类型存在差异的事实。而沈尹默毕生强调学问对于书法的重要性,这已成为他的主要艺术主张。蒋维崧的行书深受沈尹默影响,我们因此而把个人特性、时代精神、古人法度和学问学术作为蒋维崧行书魏晋格调形成的基本元素。
第一,清峻之气与萧散之风。蒋维崧先生字峻斋,徐超教授曾撰文 《借来 “清”字说峻翁》,得到蒋先生首肯。清字 《说文》解释为 “澄水之貌”,峻字意为山高而陡。蒋先生个人形象、气质以及学问和书法中都透着这样的清峻气息,清峻成为蒋先生人格特质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先生一生无欲无求,淡泊名利,可谓清之极也;其为人低调、静穆,性情高古,此可谓峻也。有此清峻之气,先生的书法自然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气质,是 “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样的书法气息与其为人联系在一起,如果从古人那里寻找渊源,我们很自然地将其归入魏晋的书法序列中。苏轼云:“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 《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5]唐代书法家张旭最精彩的是草书,但后世书家尝评其草书无晋人格调,苏东坡推重其楷书 《郎官石柱记》正是此意。其所用 “简远”二字正可作为魏晋书法的基本格调,若再与魏晋士人放浪形骸、逍遥山水的名士风度联系起来,“萧散”二字最合晋人之格。蒋维崧先生行书字字独立,用笔轻松自如,纯以意行,天真烂漫,字行的间距又进一步拉开,遂造成作品的空灵秀润、静穆典雅。宗白华云:“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6]蒋先生所追求的这种近于晋人的萧散简远之风被其逐渐推向高峰,更深刻影响了后学。
第二,碑帖融合的时代与重振 “二王”的探索。蒋维崧先生青年时代正赶上书风鼎革之后书坛一片混乱之时,可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书法在经历了帖学繁荣和碑学狂飙之后陡然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和安静中。蒋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我上小学时,学清道人的多,学张裕钊的人多。上大学时不行了。”[7]再加上当时战乱频仍,国土沦丧,天下大乱,生计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事情,极少有人去思考书法问题。在这种时候,沈尹默先生横空出世,打破了这种茫然和寂静。蒋先生在谈到沈尹默的书法时说:“他也经过了写北碑这条路,不是完全写二王,跟过去写二王的不一样。”[8]跟随沈尹默学习书法,蒋维崧自然受到他的这种书学思想影响。但是,在现有资料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蒋先生临习北碑的记录,这或可看作蒋先生直接从沈尹默处取法的一种表征。他的行书从时人处得法远胜于古人处,这是那个纷乱不堪的年代书法学习境况的一种体现。在当时,书法还是为实用,从时人处取法正是实用至上的表现。但是,后来蒋先生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演习篆籀,又是对沈尹默的一种超越,他在 “二王”行书的面目中加入篆书笔意,这样的写法按照阮元的观点正是对魏晋古法的复活与重构。所以,蒋先生笔下的行书面目又与沈尹默大不相同,“近年峻斋先生的书法风格一变:方笔渐多,秾华渐尽,在丰润中略趋瘦硬,在整饬中力求自然率真。人之一生,时势、境遇、历练、修养,都会随着时光流逝,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风貌”。[9]方笔和趋于瘦硬都是篆籀之气对行书创作产生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蒋先生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他不仅走出了业师沈尹默的学术视野,更进一步拓展了行书气韵的取法领域和作品的艺术张力。这样的探索对今天学 “二王”的书家具有重要启示。
第三,“二王”古法与时代新风。蒋维崧篆书中有行书笔意,“二王”古法对其影响可谓深远,并在他的书法艺术中形成大通的境界,即篆书和行书气韵的贯通与接近。当然,行书对篆书影响的过程同时也在改变着行书的笔意,因为非常传统的“二王”古法很难直接融进篆书的创作中;同时,篆法也在深刻地影响蒋先生的行书创作。所以,蒋先生在取法 “二王”的过程中,旧的法统也得到了适当调整,“二王”古法因此而呈现出新气象。这也是蒋维崧先生行书中魏晋风度的一种体现,即在继承中进行融合时代风尚的艺术创新。“二王”古法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上,每每与时代潮流相结合,便形成时代新风,“二王”书法在二十世纪的表现面目就是以沈尹默、蒋维崧为主导的静穆雍容、端庄典雅的艺术新风尚。这种风尚的根基是“二王”古法,但在发展过程中掺入了许多新的审美因素,其表现面目因此与 “二王”及其传承大不相同。蒋维崧先生于此走得更高更远,他的笔下已经与 “二王”书法的面目相去甚远,但是,仔细审视,又全然是 “二王”的气息和精神,这是把“二王”书法精神彻底融化到笔下的高明之举。看蒋维崧先生临王羲之尺牍让人大跌眼镜,那已经不是王羲之的书法面目,而纯然是蒋先生自己的行书。这正如明代王铎在临摹张芝、王羲之和王献之书法作品时,全然不管原帖风貌,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写,书写过程中把古法和自己的心意融合表现,王铎称之为 “臆临”。临帖不易,臆临更难,既要学习古人精神,又要摆脱原帖的束缚,进入到自由自在的创作境界,这个尺度很难拿捏。蒋维崧先生正是用这样的办法完成了对 “二王”法度的继承和超越,并逐渐探索和研究出适应我们这个时代审美风尚的蒋氏行书体。
第四,学问文章与书卷气象。书法界像蒋维崧先生这样看重学问和学术的人并不多,有人也搞学术研究书法,但却并没有把自己的学术关注与书法创作联系起来,学问学术不能为创作服务,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清人龚自珍云:“文章学问之光,书卷之味,郁于胸中,发于纸上,一生不作书则已,某日始作书,某日即当贤于古今书家者也。”[10]蒋先生虽接受了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并长期在政府机关和高校工作,但是,他像极了旧式书斋里的文人。先生喜好读书,手不释卷,但懒于著书立说,他的学问都在脑海里,在思想中,更在其笔下化作笔墨氤氲。他的学问在篆书中表现最为明显,其金文书法显现着十足的文气,而对其行书,这种文气表现虽不如篆书那么足,但是,与 “二王”书法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蒋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的小行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书卷气。这种气息不是魏晋尺牍那样的潇洒和飘逸,也没有太多的技法表现,只是一种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书写中的自然、灵动和文雅的气质。这样的气质已经远远抛开法度的局限而进入到自由自在的书写空间。这样的自由自在与魏晋士人的气度和书法气象非常接近,只不过他们达到自由气象的途径有所不同:魏晋书家主要靠灵性和情怀,而蒋维崧先生在今天却是充分调动了学问文章之气的参与,二者殊途同归。蒋维崧先生于此可谓开一新气象。
三、千秋名氏要烦君:蒋维崧行书的学术价值及其未来
乔大壮当年曾赠诗蒋维崧:“刓金泐石事纷纷,小学销沉剩二分。何处更求秦相笔,异时真叹郢人斤。研朱纸上调花露,倒薤窗前拓篆文。料检行縢余旧冻,千秋名氏要烦君。”[11]乔大壮对蒋维崧艺术的未来寄予厚望。所谓 “千秋名氏要烦君”主要是指篆刻艺术,乔先生希望蒋维崧篆刻将来能有大成。可在现实中蒋维崧远远超过了恩师的期望,于书法之成就毫不逊色于篆刻,尤其是其行书,对当代书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的行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典范。他的行书集古人法度、时代精神、个人灵性及学问学术于一体,因此,在他笔下出现的书法艺术形象已经成为时代书法的象征。这种书法艺术形象的形成又暗含着继承中的创新、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对于个人性情和学问的长期坚守,所以,他的象征意义和典范作用是永恒的。
参照蒋维崧先生的书法艺术之路,当代中国书坛在国展大旗指挥下所进行的书法创作应该作一个深刻反思,并适当叫停书法展赛活动,让书法回到书斋中,回到性灵和学问的天然载体中。这一改变对书法界将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在嘈杂的展赛活动中成为所谓的书法家,而对于学问、对于书法的未来则思之甚少。蒋维崧先生对此曾有过一段经典语录:“书法人才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修养非常重要。一开始写字还看不出来,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读书,没有传统国学修养,就上不去了。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现实中的例子、身边的例子很多很多。”[12]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当代书法家对书法的发展缺乏一种思想性,还处于简单的描形和技法训练中,对个人综合素养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蒋维崧先生身上找到参照。他在行书创作中既继承 “二王”又有所创新,并融入时代风尚、个人性情和学问学术,最终自成面目,形成格调高古直逼魏晋的精神气度,这对当代书法实在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启示。基于此,蒋维崧先生的行书将作为 “二王”书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艺术表征而永载史册。
注释:
[1]胡传海:《王铎墨迹大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95页。
[3]钱谦益:《题杜苍略自评诗文》,《钱牧斋全集·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4]常诚:《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蒋维崧先生行书艺术浅析》,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47页。
[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6页。
[6]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7]徐超:《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泰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页。
[8]徐超:《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泰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9]黄苗子:《蒋维崧书迹》“序言”,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1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6、437页。
[11]刘晓东:《我所了解的蒋峻斋先生》,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编:《独上高楼——蒋维崧教授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44、45页。
[12]徐超:《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泰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