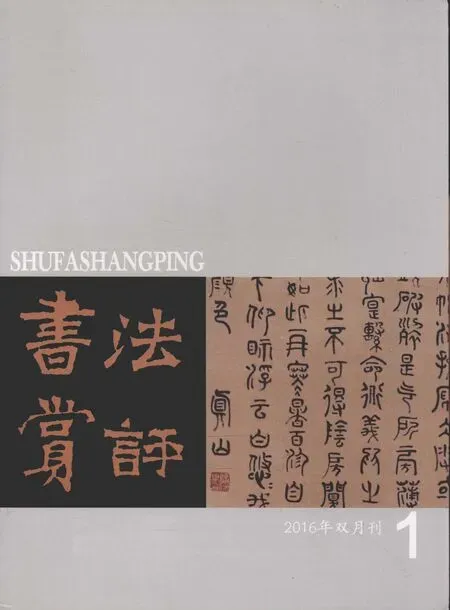论金文笔画线条之美
2016-09-07■查律
■查 律
理论研究
论金文笔画线条之美
■查律
汉字字形是书写的语言符号,书写是汉字形态呈现的手段与方式。
清徐灏注笺 《说文解字》 “书”:“书从聿,当以作字为本意。”而 “聿”字本身就是以手拿笔之形。我们从这两个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上可以知道,古汉字的书写工具是 “毛笔”。金文是经过刻铸工艺之后的文字留痕,尽管不是毛笔书写的鲜活形态,但是我们认为前人精心的工艺制作后为我们留存的先秦文字形态是可信的,现实的字形信息为我们理解书写所凝聚的文化内涵带来切实的依据。

图一 聿 甲骨文

图二 聿 金文

图三 书 金文
在汉字演变与书写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笔画形态在甲骨文初始时期是较为细长的线条的形态,而商周金文所呈现的是粗壮的线条。商代金文中有不少是笔画极为粗壮的,可知甲骨文的笔画是由于工具材料的原因而呈现为挺健细劲的形态。在汉隶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汉字书写是有着明显块面化形态特征的。如果以笔画粗细与整字大小的比例论,商周金文中有不少是可以与汉隶以及南北朝时期的粗笔书迹相当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将前者称之为线条而不是块面。两者的不同在于,汉隶以及南北朝时期的粗笔书迹中笔画起收笔出现圭角,笔画整体呈现出多边形的形态特征,此时笔画的块面感就很明显了。相比较而言商周金文的笔画起收处以圆弧为特征,因此它们在总体上属于线条。
在书体形态中行书笔画总体上与楷书笔画的块面感有共同之处,而比楷书更为多变,同时也有部分明显的线条化形态存在。草书在以章草为形态时块面化笔画特征明显,在早期今草的小草形态中也有很多块面化笔画形态,而当草书的书写走向大草时笔画连绵,则完全是线条形态的了。
对于各种字体笔画形态线条与块面的区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对它们予以定位与理解。总体来说笔画的块面特征是属于静态的,而弧形线条形态则更趋向于运动。综合笔画与字形整体,一般将篆、隶、楷三体定为静态的书体形态,而行草书则属于动态化的书体形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金文笔画中的运动性特征。古代金文是静中寓动的书体形态,并且其运动性是主要的,只不过其运动形态更为内在而不同于行草书。
宋苏轼言:“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成为书也。”书写是对书写对象的创造,是一种精神的赋予。商周金文无论以原铸或拓片的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生命的动象与精神情态,而其笔画就是举手投足的瞬间定格。金文的笔画除了明显的横、竖形态外都是自由多变的,但是这种自由多变完全不同于草书。金文与草书都以线条的形态来展开自身,但是金文是以空间性为原则的,而草书则是在交互、缠绕的线条运动中展现被时间引领、交织、重叠、回环的多层面、多维度的时空一体性。草书中的冲突与平衡不断交互、延展并以相应的节奏展现了以情感体验为主导的视觉世界。
金文线条是属于文字构形的手段与基础,它对于部件形态的呈现是有着严格约定的,因此金文线条在呈现自身的过程中必须是非常经意的,也就是说书写者非常清楚线条形态、运动幅度及其在字中位置的内在规定。但是在这种规定之下仍然具有可变性的变化余地,对于这个余地的合理掌控是书写者对书写视觉展现的个人化表现之依据。但是在金文中这种由于书写者取向所呈现的 “风格”特征绝非是一种刻意的主动追求,这是在 “适意”的内在需求主导下的必然。对于我们来说,对金文的审美以及书写继承首要的不是对差异性的把握,而是对于共性的理解与尊重。
金文所展现的线条共性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由静而动,动而复静,静中寓动;第二,拙而生妍,妍而复拙,拙中寓妍;第三,敛放分明,放而复敛,敛中有放。这三点分别是动静、妍拙与敛放。动静的表现最为直接的是曲直变化,直为静,曲为动。“妍拙”是很少用的词,一般都说 “巧拙”。在书法中 “巧拙”是视觉性很强的判断,金文中的 “巧”不同于其他书体,在形态上谨守着一定的度,这种 “妍巧”是 “慧巧”,“妍”是有度的、具有智性的美感。一般论书说 “收放”而不说 “敛放”,我认为金文在总体上是呈现一种含蓄的收放,这种含蓄是一种态度、态势上的收敛,是精神的持守而不是行为上的收束。“敛”与 “静”“拙”相应,但 “敛”不是作为 “静”的 “直”,金文在曲直中均有其敛,“敛”是蓄而待发,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关于动静。在金文中笔画的弧曲运动比较明显的往往是在中间部分,也就是说总体呈弧曲运动的笔画在起笔、收笔时相对比较安静,由较为静态的起笔作势过渡到弧曲运动,然后又在收笔处归于平和与安静。多节奏动态的弧曲线条是由单位弧曲形态组合而成的,往往也呈现这一明显的动静特征。弧曲是一种旋转的运动,具有不稳定性,但是当弧曲笔画的起收趋于安定时,不稳定的弧曲运动就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了。这种限制是以起收笔处作横势或者纵势的形态来达成的。当起收笔归于横向或者纵向的时候笔画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感,并形成整字的内在秩序。小篆带有弧曲的笔画中起收笔处较长的纵横直线部分是主要的,弧曲运动幅度受到较大限制,形成小而规则化的形态。商周金文的笔画形态中运动往往是主体,起收笔的静态只是一种倾向,因此所呈现的是自然书写状态下的适意秩序,而不是如秦小篆那样过于人工化的笔画与字形取向。当然,这种弧曲运动的轨迹是以从容平和为特征的,金文的弧曲并不呈现为运动中的激越与冲突,而更多是圆融自在。由于线条弧曲的圆融与平和,弧线的弧深往往较浅 (弧线曲率较小),这种较浅弧深的弧形笔画形态不会形成局部视觉点。也就是说当观赏者注视金文的弧曲笔画时,笔画所呈现的形态是整体的,我们不会将视线停留在过于笔画的局部上。此时我们更会注意笔画整体在整字中的位置与功能,这时笔画会引导观者扩大视域至整字乃至于整篇。
关于妍拙。在金文中笔画的妍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弧曲运动所显现的婉转流美;其二是笔画中的尖细精巧与厚拙迟涩的对比。就金文笔画形态而言,最为妍丽的笔画是弧曲与尖细笔形的结合。商与西周早期的金文多直笔,如殷商晚期的 《戍嗣子鼎》。(图四)
《宰甫卣》(图五)与西周成王时期的 《保卣》、(图六)西周昭王时期的 《折觥》(图七)等。在这些笔画以直笔为主要形态的金文篇章中,曲直的形态对比就显得更为强烈,因此粗壮迟拙的横竖笔画 (在纵向取势的字形中竖笔较长,比横笔更为明显)与运动流美的弧曲笔画相应相合,对比而互显其致。运动的笔画是活泼欢快的,使整篇文字形象呈现出生机与活力。西周中后期,弧形笔画渐渐成为常态,直笔数量的比例越来越小,并且除了少量的单独横竖笔画外,更多的只是在笔画的局部呈现相对较直的形态倾向。笔画局部中的直形一般是弧曲的两端或者是两个不同弧曲间的过渡转换部分。在这种字形情态中妍拙的变化更加微妙,如 《墙盘》。(图八)这是一种妍拙交融的状态,但是作为弧曲的运动笔画自身仍然被限定在一定的度中。在商与西周时期这种度是极为明确的,只有在春秋战国中出现不少笔画变得更为细巧、弧曲运动更为强烈的金文形态,如 《栾书缶》。(图九)此时审美的倾向开始改变,更加轻率与世俗化的表现渐渐增加,开始脱离商与西周的金文审美基调。在商与西周的金文中弧曲与尖细形态结合的笔画是整字中的眉目,顾盼传情,有效地活跃整篇气氛,丰富了整篇的色彩,但是这种精巧妍丽除了极少的点笔外多是附着于更为厚拙的长笔画上,或者只是长笔画上一个极小的端点,至巧之处被极为明确地限制着。在商周金文中拙是首要的,尽管妍巧是不可缺的,但只是调节与增色,它们的存在不可破坏雅正的审美基调与核心要求。
关于敛放。在商周金文中 “敛”应当理解成笔画展现运动的适度与节制。从表面上看,文字的书写只是完成符号的准确显现,金文虽然是毛笔书写的转换形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古人的书写完全与其心性相关。毛笔书写的特殊触感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主动把握与创造性、掌控形成了书法作为艺术的必然,书写与心性的关联与合一标志其并非是单纯的构形技术。在金文中为数较少的尖巧起收笔是以露锋方式完成的,其他笔画基本以含蓄的形态呈现起收两端,“含”是金文笔画的基本特征。金文的书写并非为含而含,而是书写者内心表达的必然选择。“含”的书写必然是 “敛”的。敛不在于笔画长短上的故意收缩,而是在表现字形构建充分前提下的适度含蓄。

图四 商 戍嗣子鼎

图五 商宰 甫卣

图六 西周 保卣

图七 西周 折觥

图八 西周 墙盘 (局部)

图九 春秋 栾书缶
就书体演变而言,隶书的点、撇与捺是最早出现露锋的笔画形态,此时情感的展现力被强化了。楷、行、草三体在草隶中孕育而生,露锋渐渐成为书写的常态。露锋是对 “含”的破坏,也可理解为情的完全畅达必然会导致对 “含”的破坏。含不等于没有情感,是一种情感的内化状态,而露则是情感外化的必然。在金文中尖笔起收也是一种露的形态,但是这种露仅仅只是 “露”,微小的露后主体仍然是含蓄的。我们可以通过尖笔起收的笔画中段形态来判断此时起收笔所 “露”的内涵与意义,但其以中锋为主的表达方式对于所露来说必然是有限的。楷、行、草的露锋是与其露时的侧锋相配合而形成丰富情感的有效展现,此时的起收笔形态是多变和微妙的。
在金文中有比较畅情的笔画,那就是字中较少的长笔,或曲或直,这是情感状态的适意展现。显然,抒情不是金文之主责,金文在于表达生命力量的蓄与发。从容而有余,笔到意留,这是金文书写的基本状态。书写者在笔画表现时处处有留即处处蓄之,这是对自身生命状态的珍惜与留意。金文中展现了无穷的意趣情态,是一种近于稚拙的展现,处处天真。天真在于以发现的眼光感悟未知,而不是将自身的完全力量投射出来。先人在金文中显现出来的持重而率真、朴素而细腻、自然而适度的线条表现,处处留情而不逞情、处处随机而不随意、处处得意而不着意的书写状态才是真正感人之处。这是金文的精神与灵魂。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