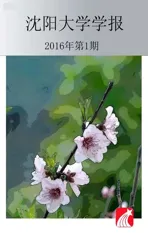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治动员——一种社会空间理论分析视角
2016-04-03闫义夫
闫 义 夫
(内蒙古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治动员
——一种社会空间理论分析视角
闫 义 夫
(内蒙古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包头014010)
摘要:以社会空间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来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分析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进行的政治动员之所以对社会转型升级产生了极为强劲的推动力,与“面对面”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相互独立的空间场域,以及聚合跨地域跨行业的变革联盟力量这三种要素密不可分,最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 政治动员; 社会空间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进行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转型升级。以社会空间理论来分析中国数亿人口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是一个重要而且较新的视角。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演进、策略调整以及政治动员手段方式等研究较多,而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进行论述的却相对薄弱。政治动员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对社会空间有着一定塑造和影响。与此同时,社会空间也同样制约着和影响着政治行为。社会空间理论主要分析个人、群体和公共机构在空间环境中的行为过程,它研究了不同社会空间尺度环境下不同层次行为主体的选择和行为,社会空间的变化与政治行为很可能是直接相关的。在这样的活动中,存在一种制约或者一种“隐藏”的结构,对政治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和研究。社会空间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事实上,马克思和齐美尔等经典作家就曾论述过,即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以及他们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到,工厂中工人的大量集中将大大地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能力。齐美尔指出,如果围绕某个静止的建筑物形成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前者将在人们的互动中充当至关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枢纽(群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社会空间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如《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阶级、集体、社区: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整合》《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社会空间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空间视角,社会空间是一切行动者的集体合体,杂糅着社会制度、政治运作机制等因素,是限制着行动者决策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与结构性条件的集合。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范围的社会空间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而是一个具有政治-社会性质的复合体,有点类似于吉登斯所说的“权力容器”。这种社会空间对行动者及其行动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影响。结合经典理论作家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本文以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来分析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治动员现象。
一、通过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动员主体与客体形成了“面对面”的动员格局
在疾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五反”运动过后,在农村和城市中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如农民协会、宗族组织以及行会等组织要么被取缔解构,要么被重组。这些类型的组织不再发挥利益表达功能,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来解释,其理由是“共产党已经最好地代表了全体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1]。
(1) 农民协会被取缔。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满足了农民土地、生产资料等物质利益要求的同时,也对原有的农村社会造成冲击和改造,导致农村权力结构大换位。农民协会成为了农村的权力中心,是土地改革时期作为合法执行机关,也是实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的重要组织形式和新的基层政权形式。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地区,都组建农民协会这一组织。1950年中南、华东两大行政区会员人数已达3 000多万人。1951年西南地区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 000多万人,到1952年10月,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农民协会会员已达8 800多万人[2]。可见,农民协会成为农村社会中一只重要的政治组织力量。然而,农民协会并未成为一股独立于国家行政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而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之时,开始逐渐被政权机构所取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95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的报告中说:“农民协会,土改后已无新任务,逐渐流于形式,……主要的是应帮助政府推动生产”[3]。显然,对于农民协会定位限于“帮助政府搞生产”,不久之后,中央便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主要职能是代表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取消农民协会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间未必有直接关联,但是无疑是消失一个潜在的阻力,“面对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其地位远比面对着自治村社的苏俄国家要有利”[4]。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理想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为实现农民土地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5]。
(2) 宗族组织被解构。在农村中真正的社会组织是家庭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宗族组织。它既是传统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组织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为一种社会集体。宗族组织类似于基层的自治性社会单元,它不属于国家科层制度。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讲,中华帝国一方面有一个独立的“帝国中心”,它是帝国政治文化的焦点;另一方面则是许多散落在“边陲”的社会单元。但是它所起的作用是科层制度所不能比拟的,主要表现是其内在结构的内聚力。从晚清王朝到民国政府都试图以基层建制(保甲制度)改革入手,竭力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但是,宗族组织有着较强的抵御能力,阻止了中央权力向农村社会的渗透和介入。主要原因有:①是保甲制度与宗族组织在人员构成上功能重叠,“事实上,不少下层组织只是改头换面的宗族组织而已”[6]。②是缺少宗族组织的支持,保甲制度很难发挥作用。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急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运动和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对宗族组织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中指出,征收祠堂、庙宇等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将没收所得归国家所有之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从经济角度上看,通过土地改革,宗族组织共有的族田被重新分配,瓦解了宗族组织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他们有着独立的经济地位,大大减少了对宗族组织的依附。从政治角度上看,国家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取代了宗族组织治理。1950年政务院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成为乡和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有科层制的行政人员和基层党组织代替了族长,实现了对农村的管理和控制。另外,“通过对原有居住点的重组……形成混合的、杂居的新的行政格局,是家族聚居、家族联系失去了原有的便利地理条件,家族间日常的交往更困难”[7]。从思想角度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以及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实践中,颠覆了传统的宗族组织伦理文化传统,向农民灌输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最后,从社会改革角度上看,新婚姻法象征着妇女解放以及家长制的土崩瓦解。
(3) 资本主义工商业行会被重组。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8]。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就必须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就不能不对其工商团体予以关注。在城市中的行会组织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而且这些行会大多数由大资本家或帮派把持。为此,中央政府责成各地人民政府负责成立工商业联合会,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行会组织进行整顿和改组,使之改造成为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有积极作用的人民团体。各地工商局整顿和改造的主要原则之一,即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大、中、小(商会、对外贸易同业公会、银钱业公会等)作为会员单位吸收进来,同时国营企业、合作社也作为会员单位加入。经过建国初期头两年的整顿和改组,各地方新的工商联——同业公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并未对这新组织的人事制度进行改造,“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同业公会仍保留着独立的组织,他们代表本行业的各工商户来参加工商业联合会,不仅其经费的收支和干部任免不受到工商联的监督,而且这些同业公会过去往往被大企业主所把持,中小企业主很难获得平等权利”[9]。而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为进一步深入改造同行业公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联合和同业公会中发生较大改组,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政务院颁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了工商联合会的基本任务:例如,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其中,为了解决同业公会在工商联中的阻隔作用,通则规定:市、县工商联以该地区内的公私企业为社员,不再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同业公会转变为工商联领导下专业性组织。而且,其职能限定在加工订货、执行产销计划等经济领域。由此可见,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国家政权对同业公会实行一种解构策略。在组织上,工商联合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建立直接联系,剥离了同行业公会的组织基础;在职能上,将同业公会社会功能限定在“利用、限制、改造”框架下的经济领域,不再具有维护同业共同利益的功能。实际上工商联组织的建立和1952年下半年的改组,取消和规范同业公会的独立性和社会职能,将悠久、分散、独立管理的带有封建社会性质的行会组织转变为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全国性统一组织。
在疾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五反”运动过后,在农村和城市中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如血缘宗族力量、农民协会以及行会等组织要么被解构取缔,要么被重组。这些类型的组织不再发挥利益表达功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社会中层组织销声匿迹,这一层次的权力真空被以党员、干部的组织网络以及工会、青年团、妇联组织等替代。这样的组织体系不仅将农民、手工业者、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纳入到组织调控体制中,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与农民、手工业者、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直接的“面对面”的二层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变得更为直接、更具有渗透性、更易于操控。结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能够在这种“裸露式的社会”中长驱直入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
二、社会流动性逐步减弱, 在城乡间、私营企业间形成了相对隔绝、封闭的空间场域
社会流动性逐步减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户籍制度的设置来控制和限制政治动员客体(主要指农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迁移。另一方面,外部劳动力市场受到国家政权管制,私营企业中雇佣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限制。
(1) 通过户籍制度的设置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水平流动和迁移。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二元身份制的一项社会管理体制[10]。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起始点是1950年公安系统内部颁发的《特种人口管理暂行颁发(草案)》,正式开始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1951年针对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较频繁,给社会秩序和治安治理的维持带来了困难,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对城市人口进行管理,主要目的是维持城市社会治安和构建稳定秩序。1952年政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并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提出吸收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防止盲目流入城市,避免增加城市的负担。1953年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阶段,城市就业机会增加,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和工矿区。针对上述情况,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1],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1954年发出了一份“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联合指示。1955年国务院通过《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进一步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将户籍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1956年和1957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通过以上历史资料表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户籍制度的功能与影响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强化的过程,其变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侧重点在城乡居民的人口登记管理职能;第二个阶段,侧重点在限定人口自由流动、迁移方面的功能和城乡居民相关利益分配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行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管理和约束。尽管新中国第一部《五四宪法》承认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但是落实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是对公民的自由迁徙进行了管制和控制。
(2) 国家政权通过对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管制,限制了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国家政权规定私营企业“不能任意雇佣和解雇工人,任意增加劳动强度,任意改变工资,也不能使用童工……”[12]。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是出于规范城市劳动力市场、保障私营企业中工人权利,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束缚和削弱私营企业主的管理权限。这项政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不但私营企业主雇佣劳动力不再按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自由雇佣工人,更为重要的是,私营企业中工人很难发生自由流动、工人不能任意解雇使得工人流动处于静止状态。
农民和私营企业中工人的自由流动,均受到国家意志或管制或保护的介入。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意志需要用制度和政策建构一种“人工维持的秩序”。一方面,户籍制度的设置,农民自由流动、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等行为受到了管理和约束。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地域分布比较集中,行政归属清晰、社会关系比较固定、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比较明确。这样,中国共产党能够较便利地运用经济和政治等手段,对农民进行动员。不论是对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对城市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改造私营企业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外部劳动力市场进行管制,限制了私营企业中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劳工队伍非常稳定,几乎不流动。而且,企业内部的党组织管理完善,结构合理,党员干部队伍人手充足。每一家企业被纳入国家的监督之下后,企业中便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党组织”[13]。政治动员的对象在一处地方停留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党组织去做政治宣传活动,致使党组织的教育和发动职工的努力得以实现。
三、动员聚合阶级阶层力量,促成跨地域跨行业的阶级阶层联盟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阶级阶层动员是阶级斗争最为重要的环节,它组织和动员广大劳动阶级,赋予其合法的斗争方式来改造和教育自身以及改造其他阶级阶层,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着必要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资源[14]。正是通过动员并且聚合阶级阶层力量,形成了跨地域跨行业促成社会变革的阶级阶层联盟。
(1) 在农村动员聚合贫农阶层力量推动农村社会生产资料变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关键形式。就其组织规模而言,它比“互助组”和“初级社”的规模要大得多,由三百到五百农户组成,扩大到由几个自然村所组成的行政村;就其财产制度而言,带有私有财产制度的股份制度取消了。而中国农业集体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最大的不同,即不是解决富农问题,而是解决中农问题。正如邓子恢指出:“主要是通过贫农解决中农的问题”[15]。具体来讲,就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向贫农倾斜,联合贫农阶层力量来实现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专门强调建立合作社必须保持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使之成为合作社中的领导骨干,对于那些没有树立起贫下中农优势的合作社必须予以解散或者进行改组。以此同时,毛泽东透过阶级分析的透镜,把因为生活困难或还不富裕的贫农、新中农中(包括中中农、老中农中的下中农)作为依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贫农阶层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热情高涨,主要原因:①满足生产的需要。贫农因在经济上缺少生产资料(土地、牲畜等),寄期通过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来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②合伙平产心理。到了初级社和高级社阶段,贫农阶层表现出较大热情,不少贫农甚至把农业合作化看成是继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次“翻身”运动。例如,在缴纳股份基金时,贫农不出现金,但要中农交现金;一些贫雇农组成的合作社在向中农和富农借用牲畜时,常常不顾牲畜的体力超载或超时蛮干;有的贫农看到中农购买牲畜时说,“将来走进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马?!”[16]不少贫农这种“建社后先吃中农投资、后吃国家贷款的风气”[17]属于合伙平产的积极性,并且不利于农村生产。尤其,在到“高级社”阶段,在分配方式上物质利益这时日益集中在贫下中农身上,这种情况与前一个阶段(初级合作社)明显不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土地分红,意味着经济利益由中农向贫农这两大阶层之间直接转移。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动员和倾斜下,由于贫下中农的人占绝大多数,一个跨地域要求变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形成了。
(2) 对工人阶级进行动员聚合工人阶级力量,推动城市生产关系变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数十年革命斗争中不懈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执政合法性支持以及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帮助,而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帮助,则必须给工人看得见的利益。党和新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介入,消除阻碍在工人阶级利益诉求面前的障碍。帮助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和控制是通过一些与资本家分享企业控制权力的机构实现的。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进行监督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劳资协商会议和增产节约委员会两种。早在1950年,劳资协商会议就被赋予了较大的权力,一开始就具有干涉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事务的权力。到了后来已不仅是调节劳资关系的机构,而且成为供人督促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的组织。作为劳资协商会议的发展,增产节约委员会实际是国家在私营企业中统一领导增产节约运动的常设机构。它对企业签订合同、制定计划、技术措施、原料供应、人事任免等一切重大问题在协商基础上进行决策。“增产节约委员会是厂子的最高领导机构。劳资协商委员会是解决劳资关系的政治——如根据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决议,签订劳资合同。厂务会议是资本家执行自己职务的组织,它不能违背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决定”[18]。很明显,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下,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关系发生了颠倒,他们资本家“没有明了,现在已经改变成新的关系了。过去整个政权都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今天的政权、军队、警察都不只保护你一个阶级利益,而是保护四个阶级利益了,所以一切应与工人共同商量了”[19]。另外,在当时,宁左勿右的政治大环境下,干部群体对工人斗争思想和行为给予很大的支持。随着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工人阶级要求公私合营的心情越来越急迫。“不断向政府送申请书,希望早日实现公私合营甚至改为国营”[17]418。正如毛泽东所说,农业合作化超前完成,断绝了城乡之间的市场联系,“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资本家)不得不这样”[20]。所以,在工人阶级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也敲锣打鼓地加入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去了。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动员理论分析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在团结谁、依靠谁和改造谁的问题上,通过动员聚合变革生产关系的中坚力量,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主义改造中不合作者的心理和行为,调动了大部分成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快速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变革。
四、 结语
以上的叙述和分析为社会空间理论框架下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某种新的视角,之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和考察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政治动员,是因为通过这样的视角或框架有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说明1953-1956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对传统社会组织的解构和重塑,推进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进程,迅速提升了政治动员的潜能;社会流动性的逐步减弱,使动员客体处于相对隔绝、相对独立的空间场域,有利于政治动员的有的放矢。也就是说,社会空间的塑造提高了政治动员的能力。而且,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为进一步重新改造社会空间,形成跨地域跨行业阶级阶层联盟提供了可能,是政治动员累加演进的产物。政治动员一步步推进,是社会空间一层层重构的过程,动员潜能与社会空间结构的重构处于一种相互彰显的过程中。从这样的视角,也许可以解释大部分社会成员为何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了。
参考文献:
[1] 王绍光. 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04.
[2] 郭圣福. 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会[J]. 天府新论, 2007(6):12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118.
[4] 秦晖.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268.
[5] 于建嵘.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变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232.
[6]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101.
[7] 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59-60.
[8]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0.
[9] 董志凯. 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126.
[10]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2):56-75.
[11] 董志凯. 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221.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142.
[13] 安德鲁·华尔德.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M]. 龚小夏,译.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128.
[14]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133.
[15] 邓子恢. 邓子恢自述[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261-262.
[16] 陈吉元,张家骥,杨勋.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3:91.
[17]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331.
[18] 中华全国总工会. 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M]. 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9:26.
[19] 中国工运学院. 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144.
[20] 高华民.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评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5/6):164.
【责任编辑曹一萍】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Reform of Socialism: Perspective of Social Space Theory Analysis
YanYif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space,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it is analyzed and expounded that, the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China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related to three factor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face to face”, the independent space fiel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formation of cross regional and cross industry alliance for change,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hange of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Key words: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social space theory
中图分类号:D 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464(2016)01-0050-06
作者简介:闫义夫(1983-),男,河北深县人,内蒙古科技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期资助) (2015F153)。
收稿日期:2015-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