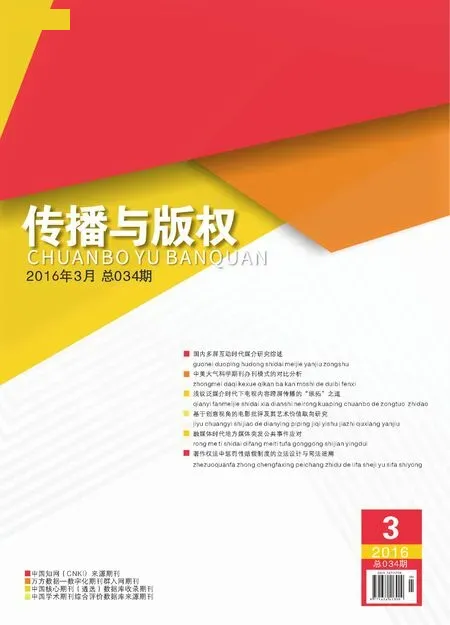媒介事件理论下的社会化媒体“微直播”
——基于2015年“9·3”大阅兵的分析
2016-03-28刘子靖
刘子靖
媒介事件理论下的社会化媒体“微直播”
——基于2015年“9·3”大阅兵的分析
刘子靖
[摘 要]结合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理论,对“9·3”大阅兵中,以新浪微博“秒拍”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微直播”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研究。大阅兵中,“秒拍”的大量运用不仅代表了一种新兴直播手段,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大阅兵这一传统媒介事件的格局、生产机制和效果都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媒介事件;社会化媒体;微直播;秒拍;大阅兵
[作 者] 刘子靖,武汉大学。
2015年9月3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以下简称“大阅兵”)成为全球瞩目的事件,也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大阅兵中,以新浪微博“秒拍”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微直播”成为一支庞大的现场直播力量。有学者对比“9·3”大阅兵和2009年的阅兵指出,六年间,社会化媒体信息传播已从“无图无真相”转向“无视频无真相”[1]。
长久以来,在诸如大阅兵这样的全球性重大事件中,现场直播一直是电视媒体的专利。基于对电视直播功能与影响的认识,传播学者戴扬与卡茨曾在1992年提出“媒介事件”的概念。本文主要结合媒介事件的相关理论,来探讨秒拍“微直播”在大阅兵中的实践和影响,从而分析社会化媒体“微直播”的价值和意义。
一、“9·3”大阅兵:一个典型的媒介事件
为了更简洁、准确地定义媒介事件,戴扬和卡茨借鉴语言学上的符号关系学、语义学、语用学分类方法,概括了三个必备要素:(1)从符号关系学上讲,媒介事件就像一个标点符号,给其他节目播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画上了句号。这表现为媒介事件的干扰性和垄断性:电视台暂停日常节目来专门直播媒介仪式,人们则暂停日常活动守在电视前观看直播。(2)从语义学上讲,媒介事件承载着“一整套核心意义”[2]。这主要是指组织者为媒介事件赋予的神圣的、仪式性的意义。(3)从语用学上讲,媒介事件“使巨大的观众心驰神往”[3]。这表现为观众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收视状态,大多数人们积极主动地收看电视直播,并对媒介事件的意义产生认同。按照这一理论的定义,2015年“9·3”大阅兵无疑属于“媒介事件”。
干扰性和垄断性。首先,9月3日当天,全国共有32家省级卫视频道、337家地市级主频道全程转播了中央电视台直播信号[4];此外,腾讯、爱奇艺、优酷等视频网站也参与了直播;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中大量相关话题成为热点。其次,为顺利完成大阅兵,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机动车限行”“暂停办进京证”“学校延迟开学”“全国放假三天”“股市休市”“北京市工业企业停产或限产”……可见,大阅兵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常的传媒节目播放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大阅兵仪式的意义。作为一个全球性事件,“9·3”大阅兵意义的建构是该事件仪式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从大阅兵仪式中的一些元素可以看出,比如“抗战老兵”体现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裁军30万”的承诺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路线;“军队各式装备”体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维护国家利益、世界和平的态度……正是通过大阅兵这样一个隆重的、盛大的仪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进一步得到突显和强调。
观众的共同观看。据央视网消息,9月3日阅兵当天电视收视数据[5]显示,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全程直播总收视率达18.18%,全国全程转播的电视频道,并机总收视率达25.62%,总收视份额达83.66%,全国共有4.89亿电视观众收看了央视直播,还有10亿[6]网民通过互联网浏览和收看大阅兵。十几亿观众的共同关注,说明大阅兵这一事件成为当天很大一部分人“共有的经验”,使“观众彼此合一、与社会融合”[7]。在网络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如此兴盛的今天,电视收视率能够达到如此规模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事件是有一定认同的。
二、“微直播”:大阅兵事件的新兴直播形式
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媒体形式中,视频是能够完整呈现事物原貌的最佳形式。同时,视频的不同呈现方式中,直播是唯一保持事件时空一体性的呈现方式。长久以来,现场直播一直是电视的专利。尤其在大阅兵这样的全球性重大事件中,电视是唯一能够将事件现场带到全国甚至全球观众面前的媒介手段,使人们如同在现场观看事件的整个进程。
虽然互联网的用户生成内容机制,早已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特权,开启了草根传播的时代,然而在诸如大阅兵的传统仪式性媒介事件中,电视直播仍占据着垄断地位。在我国特殊的媒介格局和体制下,甚至可以说是中央电视台的专利。我们看到,大阅兵当天的直播,不论是我国中央级、地方级电视台还是网络视频网站,甚至国外电视和视频网站,都采用了央视的视频流信号。
然而,“9·3”大阅兵中,以新浪微博“秒拍”和微信“小视频”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微直播”,成为与电视几乎同步的新兴直播方式。据秒拍官方统计,截至9月3日阅兵结束时,“我们的胜利日”话题下共有2.6万网友参与,上传了3.4万条视频,当天播放数量超4亿次。这些视频,不仅来自于大量现场观众,也有不少来自于媒体记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光明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贡献了超过700条视频,单条内容播放量均超过10万,最热的单条内容播放量更是超过100万。这些秒拍视频既直播了阅兵现场的大量精彩片段,也形成了一个个互动话题,吸聚了人们的注意力。
三、“微直播”的价值和意义
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的叙述有两个起点要素:电视和直播。这是因为:(1)“在极力张扬即将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方面,电视已经几乎达到难以自拔的程度”,相比之前所有媒介,电视“易接受性、高吸引力、图文并茂、声画合一等特性,使其拥有较大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8]。(2)电视的直播是“在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中进行”,实现了“对真实时间与远地点的连接”[9]。正是直播的方式,才使重大事件成为人类同时“观看”、共同见证和参与的历史事件。此次大阅兵中,大量由现场观众传播的秒拍视频,几乎实现了与事件发生同步,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秒拍视为一种直播方式。秒拍这一新兴直播技术的运用,打破了长期以来电视在媒介事件直播中的垄断地位。秒拍的大量运用,不仅意味着直播主体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秒拍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阅兵这一传统媒介事件的主体格局、生产机制和传播效果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一)“微直播”改变了媒介事件的主体格局
传统媒介事件的主体由组织者、电视台和观众三方组成。在阅兵事件中,组织者是指我国党和政府,主要职责是组织阅兵仪式并为其拟定历史意义;电视台作为生产者,主要是直播大阅兵事件;观众则是大阅兵仪式的观看主体。根据观看场所不同,观众可分为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以往阅兵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是唯一的生产者,在连接组织者与观众之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秒拍“微直播”的加入,则使大阅兵事件的主体成为“四方”:组织者、电视台、现场观众、非现场观众。其中,现场观众的身份发生了分裂,他们既是媒介事件的直接观看者,同时也成为现场事件的记录者和传播者。现场观众既包括现场的大量普通大众,也包括媒体专业人员,他们通过智能手机和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着几乎与现场同步的视频。非现场观众由两大部分组成:电视观众和网民。电视观众是守在电视机面前观看电视直播的人群,网民则是在社会化媒体中观看“微直播”的用户。
(二)“微直播”改变了媒介事件的生产机制
依照媒介事件理论,传统媒介事件是由组织者、电视台和观众三方共同“协商”[10]生产的。以大阅兵事件为例,这三方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和关系如下:组织者即国家党和政府,组织阅兵仪式、拟定事件意义并且赋予央视特权,使其成为唯一的事件直播主体。央视作为权威、官方的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一方面将组织者拟定的事件意义作为框架,去架构事件的拍摄与传播;另一方面通过传播渠道的垄断性和干扰性,“让人们待在家里”[11]收看直播,从而实现对观众和事件的规范与控制。最后,观众集体凝视式的观看也是媒介事件意义进行有效传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阅兵进行的时间段内,当人们与家人朋友守在电视机前,按电视的直播影像流来“观看”事件时,媒介事件的意义更容易内化为人们的感受和理解。
“9·3”大阅兵中,新浪微博秒拍“微直播”的加入,使部分现场观众成为事件生产者。不同的生产者,意味着不同的组织框架。因此,在“微直播”作用下,大阅兵事件的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微直播”打破了央视作为唯一生产者的垄断性地位。这意味着央视主导的事件传播框架和其建构媒介事件意义的控制性同时也被打破了。观众在不同直播主体对比中,甚至会对央视的架构产生置疑或否定的态度。大阅兵中,人们对八一制片厂与央视视频的对比和热议,便是最好的印证。另外,“微直播”使电视观众发生了分流,一些观众转移到社交媒体中,通过“秒拍”来观看事件和现场。在社交媒体分享和互动的鼓励机制下,人们由被动的接收者转向主动的观看者、传播者,他们通过即时的点赞、评论与转发,表达自己的判断与态度,并对其他人的观看产生影响。可以看出,在“微直播”作用下,组织者、生产者和观众之间的协商机制更加复杂和多元。这样一来,事件的传播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三)“微直播”改变了媒介事件的传播效果
戴扬和卡茨用“萨满教化”[12]来形容传统媒介事件的效果,他们认为媒介事件的仪式表演就好像萨满举行祛病仪式,在一种崇敬、热情、神圣的社会氛围中,矛盾、冲突、不和被治愈,社会达成一种暂时性的“共识”。
戴扬和卡茨借助仪式人类学理论,认为媒介事件仪式使社会进入了一种“阈限期”[13]。在此期间,“记者们暂时搁置起往常的批评立场”[14]、“街上的观众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收起怀疑,避免做否定判断”[15]、整个事件的播出是在“崇敬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的”。可以说,这样一个矛盾隐藏、价值共享的“阈限期”,正是媒介事件的“萨满教化”效果。在制造媒介事件这一效果的仪式过程中,电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电视通过垄断注意力,将不同范围、不同类型的人们吸聚到同一个时空的仪式中,“组织了一种全世界范围的催眠术……把我们大家全部调离那些世俗的关怀”[16];另一方面电视根据组织者拟定的意义,通过聚焦、镜头切换、解说等方式对事件意义进行建构和解释,引导人们按照拟定意义观看和理解媒介事件。
然而,此次大阅兵中,当大量“微直播”同时成为事件直播主体,并将观众从电视机面前分流到社交媒体中时,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削弱了媒介事件的效果。
“微直播”解构了电视对人们注意力的垄断。传统媒介事件中,现场外观众只有通过电视直播才能在事件进行同时观看到仪式,然而“微直播”作用下,人们有了新的观看渠道,且更符合其当下对社会化媒体依赖的媒介使用习惯。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碎片化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及多元、开放的信息环境,使各种各样的话题不断涌动并随时可能成为热点,分散了人们对大阅兵事件的注意。
社会化媒体“自由而多元的意见市场”中,人们看到了更多元的信息内容。浏览新浪微博秒拍视频,除了传统的阅兵列队、武器、领导人等内容外,现场观众排队进场时的花絮、出席的明星、帅气或美丽的军官等内容也成为记录的内容。而且,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娱乐特性,这些内容往往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并引发广泛互动。
社会化媒体的分享、互动机制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人们根据自身喜好选择观看内容,并在再次传播过程中发表观点,这样一来,传统媒介事件中电视线性传播的“催眠”效果被大大弱化。
媒介事件中,仪式是建构意义的重要方式。正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事件“既是技术上的成功,也是仪式的胜利”[17]。当电视建构的完整的、神圣的、共享的仪式被社会化媒体的碎片化、娱乐性、多元性削弱时,媒介事件的官方拟定意义及其传播效果也将发生弱化。
四、结语
在戴扬和卡茨《媒介事件》一书中,他们明确地将媒介事件区别于新闻事件。目前,已有诸多学者从新闻报道视角对社会化媒体短视频进行了研究,尚没有学者从媒介事件视角进行研究。当我们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以秒拍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微直播”时,我们看到,它的兴起不仅仅代表着信息传播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整个事件的生产格局、机制和传播意义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化媒体“微直播”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喻国明.从秒拍看社交媒体演进——以2009、2015两次大阅兵为例[EB/OL].http://weibo.com/p/100160388436607 6978799?sudaref=www.baidu.com&sudaref=login.sina.com.cn.
[2][3][7][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3.
[4][5]辛闻.央视阅兵直播总收视份额达59.36%[EB/ OL].http://news.china.com.cn/zhuanti/2015kr/2015-09/04/ content_36498365.htm
[6]隆洋.创纪录!2015中国阅兵共吸引14.89亿观众[EB/ OL].http://www.guancha.cn/local/2015_09_05_333059_s.shtml
[8]姚坦.媒介事件透视与电视角色解读——《媒介事件》述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4-129.
[9][17][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
[10][11][14][16][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4、69、8、120.
[12]姚坦.媒介事件透视与电视角色解读——《媒介事件》述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4-129.
[13][15][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