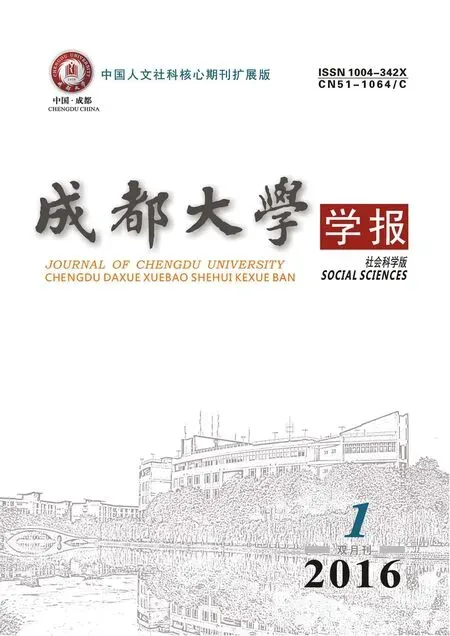浅议沃森与勒沆的“法律移植之争”
——兼评方孔先生的法律移植观
2016-03-23文艺
文 艺
(四川大学 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浅议沃森与勒沆的“法律移植之争”
——兼评方孔先生的法律移植观
文艺
(四川大学 法学院, 四川 成都610207)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但对于它的具体含义、可行性与否,全球的学者们似乎永远都在争议着,其中尤以美国比较法学家艾伦·沃森和法国法学家皮埃尔·勒沆的唇枪舌战最为激烈。本文简要梳理了二人的此番旷世争辩,并结合方孔先生的深刻点评,得出法律移植是在共性的自然法基础之上的实在法范畴内的行为。
法律移植;含义;实在法;自然法
一、何谓“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这一概念是法理学和比较法学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它并非属于法律术语中的原生词。据《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移植”一词最初由植物学、医学领域引入。常见表达便是“将野外的一株植物移植到户内的花盆里”,“某心脏病患者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等。由于法律移植本身是基于其他学科所“拿来”的一个合成概念,而各学科又必然存在内涵外延之不同,这便导致此概念的先天不足。在笔者眼中,此番先天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后续系列争议。首先,对于法律移植的含义,法学界看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法律移植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①。另有观点认为法律移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或内容或形式或理论)吸纳到自己的法律体系中,并予以贯彻实施的活动②。而通说的思路则是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其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③。此外,除去“法律移植”一词,法学作品中也会出现一些与其相当的词汇,诸如“借鉴”、“吸收”、“模仿”、“引进”、“接受”等等,也有学者直接换掉“移植”一词,替之“继受”,认为对近代而言,主要指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之后,被迫或主动地采行西方国家法律的现象。至今,对于纯粹法律移植的概念依旧说法各异,似乎也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精确的结论。
二、沃森与勒沆的“法律移植之争”
艾伦·沃森,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比较法学家,其盛誉并非仅限于此,他还涉猎罗马法、法制史等,在其著作《法律移植》中以翔实而丰富的史例配合,将其法律移植观向人们娓娓道来。在沃森看来,法律移植,即一条法规或者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族)向另一国(族)的迁移,并且此种现象一直是屡见不鲜的。为此,他列举了牛触事件(动物伤人)在《埃什南纳法令》、《汉穆拉比法典》、《出埃及记》三部不同时代法律中出乎意料的制定形式及实体内容之类似性,以此表明即便年代相隔遥远,必定存在着某些接触,也即是所谓法律移植的现象。另外,他还讲到,移植法律在新的环境中不应由于原有文化的抗拒而萎缩。一次成功的法律移植正如人体器官的移植,应该在新的机体内成长,并成为该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④。沃森否认外部环境对法律移植的影响,认为即使在对外国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实现法律借用。因为法律与社会环境的外在并没有什么实质联系,法律可以不问历史、不问文化地轻松移植。为此,沃森列出了大量史实:从西欧对罗马法的接受,到比利时对法国民法典的承继,再到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对各国的影响。作为一名擅长法史的比较法学家,沃森确实擅长“摆事实、讲道理”——用铁一般的浩瀚史例辅以观点示于大众,而这往往让人们一边感叹法律移植历史悠久、规模巨大,一边被灌输了“法律移植必然可行”的观点。
面临这样用无比翔实的例子支撑下的“法律可以移植”的观点,法国学者皮埃尔·勒沆在其《如何比较》一文中举起了与此势不两立的大旗——大谈法律移植的不可能。在勒沆看来,任何意义上的法律移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究其原因,是因法律乃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又各属于每个社会,然每个社会终究不同,因而唯有该社会的成员才能理解该社会的文化现象。诸如英国人不可能懂得法国法,抑或是当代的英国人也不能理解中世纪莎翁的戏剧。
基于勒沆彻底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能性,沃森开始了他的论战,誓要维护并坚守法律移植的可能,在《法律移植和欧盟法》一文中,他认为勒沆的观点早已过时,即过于看重外在环境对法律的影响,错误地以为文化现象就是法律,更批判勒沆的论述全是大话,没有实质,除了空洞苍白的法哲学,并没有着眼于现实的东西。沃森反驳勒沆曲解了法律移植的概念,重申自己所谓的法律移植仅限于规则、概念和语句的借用,并不包含精神。而之所以限于前者,是因为它们的切实可触及、可接触性。另外,他将法律移植等同于法律借用,强调其在法律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正如千年之前的汉谟拉比法典至今依旧生动一般。对于勒沆口中不同的社会文化差异所致法律移植的不能,沃森则一面肯定该差异的存在,一面更强调法律移植的功效——消除此类社会文化差异,带来一荣俱荣的共性。此外,沃森认为移植后的法律虽不同于从前,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植并未成功。为此,他还做了一个比喻:自己是一位种西红柿的商贩,用一定条件(土壤、阳光、水分)将西红柿苗培育至六英尺,而后买家买回其中一株幼苗,但却不再依照此前的条件栽培,然后沃森试问“难道这株在买家照顾下的西红柿苗就不是之前的那株西红柿苗了吗?”他想勒沆必定是持否定的态度,原因还是在于移植的不可能。最后,沃森又连举几例,对天长啸着发出了一声“法律移植是必然的”感叹。
勒沆似乎也不甘示弱,在《不可能的法律移植》一文中对沃森继续进行批驳。他继承了几百年前孟德斯鸠的要义,坚持把法律视为人民的精神之体现,并称由于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内在差异原本就可归因于不同的精神文化,因此法律移植从根本上便无从谈起。法律并非如沃森所说,能够完全脱离环境得到解释,而是必须把规则放到具体的环境中,联系上下文去理解。自然而言,法律不能离开环境就被移植。出于解释者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不同,解释并运用法律的方法便截然不同。规则从一种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环境,早已脱离了其必须保有的根基,加之语言等因素,规则的本来含义早已面目全非不复存在。所以移植之不可能性在于规则隐藏在“那里”背后的含义不能被“这里”所取代。
三、“法律移植之争”之分析
在笔者眼中,沃森与勒沆的“法律移植之争”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谁都有理,但却谁都不能说服谁。但如果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冷静下来,不要慌忙“站队”,便会发现诚如方孔先生所言,这场争论压根毫无意义。于是笔者也就给所谓的争论打上了引号,进而说明原因:
(一)“法律”概念后天不明
沃森最初给法律移植所下定义是:一条法规、或者一种法律制度在国与国之间或者族与族之间的迁移。后来他又对其进行进一步阐述指出,除去制定法规则,还可移植法律的机构、概念和结构等。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沃森的实在法立场,他将移植的客体“法律”列举了出来——从法规到制度再到机构、概念,这些无不属于实在法之范畴。何况他所给出的大量史实,更是为其烙下了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印记。于是乎,沃森眼中的法律仅是客观世界所存在或者曾经存在的具体的、实在的法,它看得到、摸得着,自然也就易于移植,就像那株西红柿苗照样的扎根生长。相反,勒沆则是站在一个自然法学派的角度,以其自然法的观念理解着被移植的“法律”:它是人民精神之凝聚,是一国文化之体现,是植根于某一社会便再不可能脱离的东西。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环境对于法律的影响,人类不可能如抽丝剥茧般将法律从环境中拿出放下,在勒沆看来,抽象着的自然法就是法律的一切,那株脱离原生环境的西红柿苗已今非昔比,因为耐以生存的环境已经不存在。如此看来,也正如方孔先生所言,两个人对法律的界定就没有交集,于是法律移植的争论注定就是笑话一场。就像两人约好在中点见面,一人向左走,一人向右走,两人方向截然不同,又怎可能会中点相见呢。
(二)“移植”概念先天不足
笔者在前文中提到过“法律移植”一词起源于植物学、医学,后来才进入法律的领域,被合成为一个崭新名词。基于此,该词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反应。欠缺了在法律界的土生土长,于是产生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诸多理解。沃森承认经过移植后的规则会出现排斥反应,造成被移植后的客体不能与曾经的客体一一对应,就像函数中p与p′一般,但他认为这并不能否认该移植没有成功。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沃森眼中的“移植”一词没有渗入褒贬的感情色彩,他的移植观不去评价结果的成功与否,只要有这个行为动作,就已经“即遂”。勒沆则与此不同,他说一个命题式陈述即使从技术上讲已经融入了另外一个法律秩序,但它依然会被当地文化作不同的理解。于是,这一规则最核心的元素并没有在移植以后幸存下来,因此这并非成功的法律移植。我们不难看出,勒沆口中的“移植”一词是渗入了一定感情色彩的,即对法律移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唯有成功的移植才能称作法律移植。鉴于两人的又一概念理解没有交集,笔者提出一些见解,“移植”一词应为中性词,仅表达了客观行为的作出,而不应包含对结果的判定。试举一例为支撑:有这样一句话“医生为某病人移植了肝脏”。我们从字面上能够获取的信息只可能是“该病人做了一个移植手术——移植了一个肝脏”。但我们是不能就这句话推测出“术后是否出现了排异反应,且排异反应是否影响性命”这些信息的。以此类推,法律移植也不应该对事后的成功予以肯定、而对失败就予以否定。因为评价本身就不是移植所能够掌控并包含的。
四、关于方孔先生的法律移植观
方孔先生在其著述《实在法原理》中对沃森与勒沆的“法律移植”争议进行了详细而精彩的论述,认为争论更多是因两人对“法律”这一基本概念理解不清造成的。而后方先生一面隔岸观火,一面提出了自己对于“法律移植”的看法:法律移植就是一个社会向另外一个社会借用具有相同自然法基础同时也具有物化偶然性差异的实在法⑤。在方先生看来,法律移植的本质特性有两个:第一,法律移植只能是实在法范畴的行为;第二,法律移植的行为必须有共同的自然法做基础。笔者在此同意方先生关于法律移植本质特性的第一点,法律移植原本就是客观世界中的客观行为,其移植对象必然也只能是存在于客观世界能被人类所感知的事物,诚如实在法。若要细化,便是诸如规则、原则、概念、机构、概念等方先生称之为物化偶然性的结果。我们可以将自然法视作应然法(即应该存在的法律),它虽然也如客观规律一样遍布社会,但我们并不能信手拈来,更不能随意移植。因为自然法是超越人的意志而存在,并非可量化可观摩,又何谈能够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孟德斯鸠说“物质世界有其法,动物有其法,人有其法”。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感知动物世界的法则然后将其移植于人类社会。至于方先生所认为的法律移植必须有共同的自然法做基础,笔者对此持不赞同的态度。在方先生看来,自然法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的自然法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且自然法并不能超越现实社会而存在。但事实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移植西方上层建筑(包括法律),两者虽在地理位置、文化风俗、历史传统方面差异巨大,日本还是从此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让人不得不感叹如此移植竟让萎靡不振的日本走向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道路。而纵观当时形态,日本属于封建主义社会,而西方国家则为资本主义社会,按照方先生的逻辑,这两个不同社会孕育出的自然法肯定是不同的,但日本确实成功借鉴移植了西方实在法。另外,方先生还在书中提到现代中国法律对欧洲法律的借鉴和移植无所不在,并评价说没有法律移植就没有现代的中国法律。笔者更疑惑了,既然每每强调自然法是孕于各自的社会中且不能超越社会现实,那么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又怎么能够移植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法律呢。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法律移植的充要条件并非是必须有共同的自然法做基础,而可以换种角度说只要两者不排斥便可。因为只要是人类社会,不论出于什么阶段和种类,它们或多或少是有一定共性的,一味地寻找别无二致的自然法,这确实不能,但若能够探求自然法中的相似部分,做到求同存异,相信能够办到。
五、结语
“法律移植”问题始终是比较法研究中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问题,无论是沃森与勒沆的所谓“法律移植之争”,还是看客方孔隔岸观火地深刻表态,都能够给予人们一种质疑的精神:努力用即便一点点的怀疑、批判,去看一个似乎早已通说的盖棺定论的问题。
注释:
①沈宗灵:《论法律移植与比较法学》,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1期,第1页。
②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2003年。
③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④阿兰·沃森著,贺卫方译:《法律移植论》,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第63页。
⑤方孔:《实在法原理——第一法哲学沉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1页。
(实习编辑:郑舒)
2015-11-18
文艺(1990-),女,四川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D909.1
A
1004-342(2016)01-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