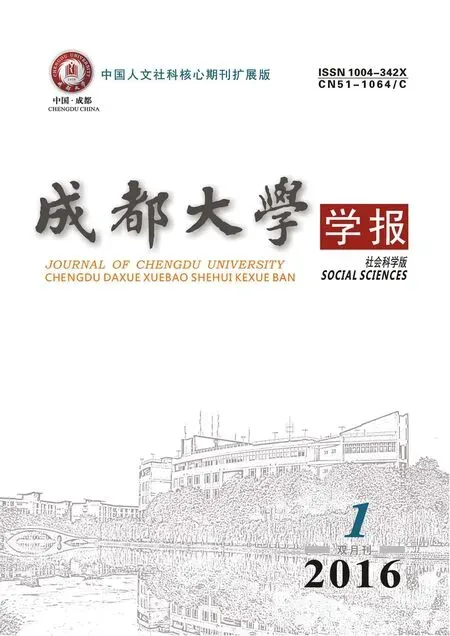“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
2016-09-02罗文军
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文艺论丛·
“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
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637009)
1885年出版的《西学略述》,由入华传教士艾约瑟编译而成。该书对西方诗人诗作有较多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首次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该书对西诗类别和韵律的介绍,又使之获得了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译介行为的赞助者以及晚清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在《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中产生了导向作用,并促成了其中文学性质的显现。在中国文人面前呈现出西方诗歌面貌,这既与艾约瑟遵从的“学术传教”策略保持了一致,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诗歌的认识,同时在近代中国的西诗译介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艾约瑟;《西学略述》;西诗译介
1880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受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聘请,担任了中国海关的翻译,并接受了将“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译为华文的任务。至1885年,“西学启蒙十六种”丛书由此告成。正如编译者艾约瑟于自序中所言,“抵今五载,得脱告成,十有六帙。而其中之博考简收者一,曰西学略述”①,作为丛书第一种的《西学略述》,其“博考简收”对西学知识作了较多介绍。而从中西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该本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诗歌知识,从而在近代的译介史中占据了一席较为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其中的西诗译介所关联的历史时段、所呈现的文学面貌以及所包含的文化因素,仍是讨论中西文学译介问题时需要仔细审视和思考的问题所在。
一、晚清社会需求下的知识导向
艾约瑟在序言中表明,除开《西学略述》,丛书包括“依诸原本者十五,曰格致总学启蒙,曰地志启蒙,曰地理质学启蒙,曰地学启蒙,曰植物学启蒙,曰身理启蒙,曰动物学启蒙,曰化学启蒙,曰格致质学启蒙,曰天文启蒙,曰富国养民策,曰辨学启蒙,曰希腊志略,曰罗马志略,曰欧洲史略。” 李鸿章为该丛书作序,也称“此书十六种,即麻密纶大书院原本也”。实际上,丛书的内容正是来自约翰·爱德华·葛林(John Edward Green)所编“历史与文学基本读物系列”(the Series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Primers),“麻密纶”即原出版者英国伦敦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 & Co.of London)。②由此十六种图书的书名以及原本的内容性质,可见出艾约瑟于此对各门西学知识作了介绍,这之中包含了一种对晚清中国作出“启蒙”的意图。
要认识艾约瑟的西学知识译介问题,显然离不开对整个社会语境和丛书出发点的审视。面对晚清洋务运动对西方科学长技的强烈需求,不管是出于一种传教策略,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有利地位,传教士在中文书刊里大量译介西学知识,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逻辑。1878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就明确谈及这一点:
曷言乎著书也,泰西士人,勤学好问,渊博非常,来寓中国,习土音,学华文,无日敢怠。不几载,精通言语文字,爰注各种书籍,如天文、地理、格致、性理、医学、算术等书,共五十一种。考究精详,译成行市,足以嘉惠后学,扩充新学。每书一出,购者纷纷。始焉茫然,继焉豁然,终焉恍然。所谓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矣。华士细加探索,寻彼书中之妙理,颇觉实获我心。且有日报,新闻纸馆,万国之事如在一室之间。阅报者,心窃喜之。此中华前所未有者三也。③
据1899年出版的徐惟则《东西学书录》所载,19世纪共出版介绍西学之书571种,其中西人译著(大部分是与华人合作的)462种,占比例为81%。④这里所谓的西人或泰西人士,实际上大多为来华传教士,如林乐知、丁韪良、艾约瑟、李提摩太等。清廷开办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等机构之后,以传教士为主的来华西人也参与创办了多所以西学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新式学校。在1875年前后,该类学校就达800所,学生人数约2万;至1899年增至2 000所,学生约有4万,为同时期洋务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有利条件。容闳、马建忠、伍廷芳等后来颇有成就的人物,早期都在这些学校接受过教育。⑤社会形势使然,新式学校和学生的增加,使得整个社会对西学产生了急切而又巨大的需求。提供适宜的教学内容,也成为了在华人士急欲进行的工作。如1877年“益智书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在第一次入华传教士大会召开期间成立,意图就在于为教会学校的学生编撰合适的教科书。在1890年第二次入华传教士大会上,该会改组为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仍沿用了“益智书会”这一中文名,其职责仍包含了教材的编写和出版。⑥
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委托艾约瑟翻译西学启蒙丛书,显然正有着适应晚清社会需求的意图。赫德自1863年开始主持中国海关,大量参与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务。洋务派开办新式教育,所需经费就多来自赫德所主持的海关,教师也多由其介绍。⑦引入教材性的西学知识图书,于赫德来说,正是应有之意。对此,艾约瑟在丛书的自序中已有表明,图书发起为“总税务司赫君,择授以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俾于公牍之暇译以华文”。李鸿章为丛书所作的序,也有如此认识:“余自治兵,讫于建节,迭任南北洋大臣。往在江表,就制造局,译刊西学书大小数十种。既来畿甸,创设各学堂,延西国教习,以诲良家子弟之聪颖者。涂径渐辟,风气渐开,近复有博文书院之设。而赫君之书适来,深喜其有契余意,而又当其时也。”⑧除此之外,傅兰雅此时期也组织了一套新式教科书“格致须知”,包括《天文须知》、《地理须知》、《地学须知》、《电学须知》、《化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等多种。该丛书盛行三十余年,至1904年清廷实行新学制,其中大部分还被采为了教科书。由此见来,整个社会语境以及具体的赞助者,都成为了传教士西学译介的促进原因。
在西方文学译介方面,艾约瑟1857开始于《六合丛谈》连载的“西学说”,已然包含较多的西诗内容,1879年、1880年在《万国公报》上对威廉·柯珀的译介,也显示出了较强的文学色彩⑨。由此可见,在译介西学丛书时再次引入西方文学知识,对于艾约瑟来说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丛书第一种《西学略述》共分十卷,依次为“训蒙”、“方言”、“教会”、“文学”、“理学”、“史学”、“天文”、“经济”、“工艺”、“航海”。其中明确设有“文学”一卷,且包含了较多的西方诗歌知识。在自序中艾约瑟指出《西学略述》的内容为“博考简收”,这其实表明译介者于其中融入了主观的择取和呈现。在刊于《西学略述》卷首的自序中,艾约瑟开篇即有如此言说:
名世者圣,称述者贤。所以启迪生民,嘉惠后学,事虽创,若仍旧言,历久而愈新。此大地有国,莫不皆然者也。至于代变时迁,一兴一革,来今往古,有异有同,倘勿溯其源,更孰悉其委?且欲得其才于后日,惟务求善教于兹时。迩者中西敦睦,不限舟车,商使互通,无分畛域,故得交相,择购利生。致治之书,咸译以本国文字,藉便披研,盖亦借助他山之一道也。⑩
序尾也表明其意图在于,“若夫即指见月,举隅反三,是则有望于学者矣”。这种意图既吻合了整个社会语境,同时也影响到了有关西诗内容的译介。
二、“博考简收”与文学性的西诗译介

1.西诗考原;2.希腊学传至罗马;3.欧洲诗文创始旧约;4.词曲;5.口辩学;6.古今诗分有韵无韵;7.伊底罗诗;8.哀诗原;9.希腊士人奉九女神;10.闺秀诗原;11.论说;12.野史;13.长诗盛行考;14.近世词曲考;15.印售新闻纸考;16.德国诗学;17.翻译;18.评论。





昔犹太、希腊、罗马诸国之诗,率不押韵,非若近日泰西诗之多作韵语也。然至希腊罗马之时,诗句长短,已有定式。如和美耳及威耳吉利诸人,其诗每句分六部,每部作二节三节不等。若第一、二、三、四诸部,其间或二长,或一长二短,尽可随意参错。至于第五部,则一长二短,第六部则二长。千篇一律,不容谬误。若夫词曲中之科白,则每句六部,每部皆一短二长。以一句言,其二节、六节、十节,皆为歌音重顿之处。今之泰西诗人无师古者,故各国新出之诗,其格式皆多至十数,每句或八节,或十节,或十二节,或十四节不等,而末复多协以韵,取悦人耳。
其中所论述的“部”、“节”,无疑正是现今所称的“音步”、“音节”。荷马、维吉尔之诗“每句分六部,每部作二节三节不等”,其意即是每句分为六个音步,每个音步包含两个或三个音节。据笔者所见的有限史料,这无疑是继“西学说”之后,有关西诗节奏、韵律等知识的最为详细的介绍。由此也许可以说,将西诗“步”(音步)、“节”(音节)概念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就是艾约瑟这一传教士。长短参错、节数不等的西诗韵律,以及“无师古者”的“新出之诗”,显然有可能为中国读者带来一种新异的印象,从而有助于他们了解异域文学的特征。
此外,艾约瑟专篇介绍了“伊底罗诗”,其中还包含关于十四行诗的知识:
伊底罗义近于诗之有赋,故凡咏人咏物,言景言情,以及题墓志哀诸诗,胥归此类。泰西盛行十四句之诗,而意大利与西班牙,以及英人尤喜为之。如今著名于英国之牧童歌、四季诗、女师诗,及礼拜六晚农夫归家之状,生民流落荒寂无人之村,诸篇什并久见重于世外。又有著名诗人米罗敦所作之忧喜二诗,尤为脍炙人口。近英国诗家名德尼逊者,遵伊底罗体成诗一部,名曰古帝王伊底罗。其书一出,时人即无不争先睹为快。
艾约瑟所述“伊底罗”,应为“Idyll”之音译,意指田园诗,或牧歌,或类似较短篇幅史诗的叙事诗。“咏人咏物,言景言情”,以及所列牧童歌、四季诗等,正与“Idyll”体的意指相吻合。而德尼逊(丁尼生)所作Idylls of the King(今译为《亚瑟王之死》,或《国王之歌》),无疑正是这里所说的“古帝王伊底罗”。可以肯定,艾约瑟在此以“伊底罗”之名,明确将这一诗体介绍到了中国。现在称为“十四行诗”的诗体,于此对应的正是“泰西盛行”的“十四句之诗”。《遐迩贯珍》译介弥尔顿时,曾在英文目录中标出“sonnet”,此处明确译之为“十四句之诗”,并言意大利、西班牙、英人尤喜为之,这也算是对该种诗体更为直接的介绍。

三、“即指见月”与“有望于学者”的意图


在整个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中,艾约瑟的《西学略述》的确具有了较为突出的意义。它的内容涵括较广,既包含了古希腊罗马诗家,又介绍了但丁、弥尔顿、歌德、席勒、丁尼生等诗人,对《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威廉·退尔》等作品也有简要评说。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前的中文著述里不见记录,显然为第一次输入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约瑟对西诗的类别和韵律知识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一点实在是难得,因为它在介绍诗人诗作的基础上,进入了更为抽象的诗学理论层面。总之,艾约瑟于此突显的文学属性、知识属性,极为有利于中国人士进一步认识西方诗歌。


艾约瑟进入中国,其实一开始就遵从了“学术传教”的策略,而且成为了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语言、典籍、佛教等,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教义宣扬和知识传播于他都十分重要,他在这两方面也作出了实际贡献。经传教士之手的西学知识传播,往往包含了传教意图,但它们也带给了中国社会积极的意义。对于中国人士来说,接受其中的西学知识,而过滤掉其中的传教意图,的确也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因此,《西学略述》里的西诗介绍,以及“西学启蒙十六种”的知识呈现,也可以理解为是中西文学交流,或者说整个西学东渐中的一个积极事件。注重其中的积极一面,显然也更符合艾约瑟所言的“有望于学者”,由此也能更好地理解翻译接受中所存在的过滤现象。其实,入华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本就不宜只作单一的理解。将之仅仅视为传教表现,或者全部归入“殖民侵略”,显然也会忽视知识传播之中所包含的客观价值。
注释:
①艾约瑟:《叙》,《西学略述》,上海盈记书庄藏版,“光绪戊戌八月仿泰西法石印”,1898年。
②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③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第515期,1878年11月23日。
④转引自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152页。
⑤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⑥“益智书会”,1902年改名“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名“中国教育会”,1916年改名“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⑦陈景磐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83页。
⑧李鸿章序:《西学略述》,上海盈记书庄藏版,1898年。
⑨参见罗文军:《故事、诗及教义:艾约瑟对威廉·柯珀的译介》,《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⑩艾约瑟:《叙》,《西学略述》,上海盈记书庄藏版,1898年。此文曾以《西学略述自识》为名,刊于《万国公报》1889年6月。只文中“一兴一革”写为“一兴一莘”,“倘勿”写为“倘弗”。
























(责任编辑:刘晓红)
2015-12-19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数据库建设(1896-1949)”和西华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412478)的阶段性成果。
罗文军(1978-),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I052;H315.9
A
1004-342(2016)01-5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