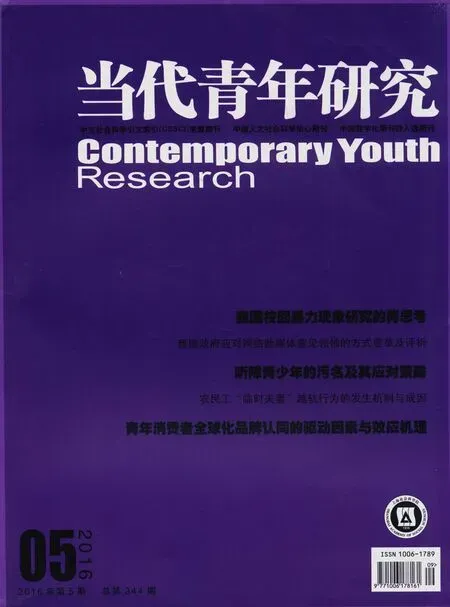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及其应对策略
2016-03-19杨运强
杨运强
(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
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及其应对策略
杨运强
(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
任何人类差异都可能成为污名的对象。在社会差别的分类审视下,听障青少年遭遇的污名类型多种多样。从综合视角来看,可分为三类:形象可怕怪异,令人恐惧;身体无用低能,形同朽木;境遇窘迫不堪,让人可怜。在面对这些污名威胁时,他们管理身体与预设的规则体系进行周旋,业已发展出三种污名应对技术:一是身体改造,常态身体的追求;二是身体装扮,秘密信息的管理;三是身体抗争,弱者的对话方式。研究此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走进听障群体的世界,帮助他们远离污名的困扰,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相互理解、信任与支持,推动社会的和谐融合。
污名;听障青少年;污名应对;管理技术
一、听障青少年的污名——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污名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在社会差异的分类标准下,任何个体都可能成为污名的对象。作为残疾群体中的一部分,听障青少年(也称聋人)自然难逃例外。事实上,听障青少年被污名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听力出现问题往往意味着灵魂不洁、魔鬼附体或前世作孽的报应,听障儿童不是被忽视、贬低就是被隔离、抛弃,甚至遭到残忍杀害。现在,在根深蒂固的“残废”观作祟下,社会对听障群体的污名印象依然客观存在。许多人在听到听障一词时,脑中浮现的还是哑巴、低能、残次品等刻板画面,故此,听障青少年基本都经历过污名的干扰和压力体验。“每个聋人的成长经历中,几乎都曾有过不愉快的经验。有的被故意放鞭炮,有的被误会是小偷,有的被认为是文盲,有的被嘲笑是‘哑巴’等”。[1]
污名是一种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背负污名不仅会使个体的生活、交往受到影响,甚至“波及与其相关的他人身上”。在污名的干扰与压力下,听障青少年及其家人背负着难以忍受的羞耻感和罪恶感,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控制,有可能产生对社会的疏远和敌视,甚至发生反社会行为。在此背景下,厘清听障青少年群体遭遇的污名标签,明确他们遭遇污名的反应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此外,从污名研究的现状看,虽然时下污名研究渐成热点,但听障者的污名研究却至今无人问津,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及其应对同样一片空白,这对污名研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鉴于此,本研究将围绕这一问题做些尝试,希望以此为契机增强社会各界对听障群体生存处境的关注,帮助其顺利地融入社会。
二、对听障青少年污名研究的质性设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听障群体属于脆弱而又易受伤害人群,对他们进行研究不仅要把复杂微妙的事情解释清楚,也要保证他们不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质性研究具有很强的弹性和灵活性,可以不受先验假设的影响,也可以摆脱研究工具、研究程序的约束,特别适合深入弱者的世界洞察心声,让研究看到“一个与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2]。此外,由于听障青少年的知识广度、理解能力、语言表达甚至思维发展等表现不佳,使用具有一定阅读和理解要求的问卷或文字调查也并不适宜。质性研究“解释性理解”的视角及使用观察、访谈、日记分析等多元方法获取资料,则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为我们“更深入了解被污名者真正使用的、具体的污名应对策略,从而为以后把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临床提供了可能性”[3]。
为了清晰呈现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及应对全景,本研究选择了19位大学中重度听障生①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了技术处理。情况如下:T=特教教师;S=听障学生;P=家长;如S-RF,代表听障学生任方。作为对象。他们年龄在17-25周岁之间(男11人、女8人;农村15人,城市4人),心智发展成熟,认知表达能力突出,对污名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因此,依托这些样本可以获得完整和丰富的资料。在获得资料时,笔者主要采用观察和访谈法进行。利用特教教师的身份便利,笔者通过与听障生“交朋友”的方式进行了系统调研。同时,考虑到部分听障生表达能力有限,个人叙述可能遗漏或失真的事实,研究还利用第三方资料进行了补正。比如访谈对象上,充分引入特教教师、家长及听人好友的观点和看法,资料来源上,充分利用已有文献,并辅助利用收集的听障生日记、作文、网贴等。
为保持了资料的“原汁原味”,笔者行文时多以“白描”方式进行。虽然某些地方对阅读是个挑战,但也有利于保证“第一手资料”的鲜活和真实,加深我们对这一主题的了解和认识。
三、污名面相——社会对听障青少年的刻板认知
听障青少年是残疾青少年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听障学生人数已占国内残疾学生总数的24.16%。[4]这一庞大的、外观与一般人无异的群体,却遭遇连绵不断的污名威胁。在日常生活中,听障青少年的形象通常是灰色的、负面的、消极的。有人称呼他们聋子、老闷、哑巴等,还有人认为他们“过于冲动、判断力弱、好赌、类似游民、小偷、文盲、比较笨、活在寂静与黑暗的边缘、缺乏合作精神、冷漠、孤僻,等等”[5]。从综合视角来看,这些零散的污名可以归为三类:
(一)形象可怕怪异,令人恐惧
作为一种残疾现象,听障在传统文化中的形象是可怕而令人厌恶的。听障群体被妖魔化为各种恐怖的形象,譬如畸形、怪物、非人类、孽障作怪等,这些异型、虚弱的缺陷应该被“扔到台切特附近的深渊中去”[6]。或者,“依照普遍的信念,跛子、瞎子,尤其是那些独眼龙、聋子、秃头、斗鸡眼(内斜视),所有这些人,都是应该避免接触的。人们常这么推断,一个人既然身体方面有缺陷,品行上也必定同样如此”[7]。在世人的眼里,他们是不祥的预兆,邪恶的象征,危险、肮脏而又令人恐惧,对这些“厄运的携带者”,应给把他们与文明世界断然分离。“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他另一种圣餐”。[8]
今天,在医学-心理模式统摄下,听障青少年在没有完全摆脱迷信或神学束缚的情况下,又被科学鉴定为需要治疗的和不健康的人。所谓教育就是实施特殊的隔离控制和医疗介入,“着眼于找出接受特殊教育者本身的缺陷、病理,进而由专业人员介入处理其个人的问题”[9]。借助所谓客观、公正的方式,听障青少年又被顺利地贴上病理、异常的标签。因此现在,他们依然是与常人不同、行为怪异、心理变态、情绪障碍的“特殊分子”。林伶旭指出,对听人而言,听障者的行为会让人觉得怪异。比如他们为了沟通用眼睛“盯”看对方,听人就会觉得他们没有礼貌;他们习惯拍打以引起对方注意,听人就会说他们“很像猴子”[10]。手语是听障群体的特殊语言,在部分人眼里也是怪异的表现。“听人是口语,聋人的语言是手语,但是聋人打手语的时候听人感觉有点特别奇怪,诧异的目光看着聋人打手语,感觉聋人手语像那个……张牙舞爪,精神病人”。“我们去外面玩,星期五坐公交车回家,别人大笑我们,全部看着我们,感觉像看精神病一样”(S-CMM)。此外,听障青少年还有其他一些怪异的标签,比如头脑简单、冲动多疑、好猜忌、自我中心、独来独往、性格倔强、破坏性强、动作大而粗鲁等。总之,这些怪异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可怕而又危险。T-BLS说,大多数认为听障群体像傻子一样,第一次见他们会有些害怕。“因为他们到外人面前很热情,手舞足蹈的,发出奇怪的声音,外人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可多人都是害怕。”
(二)身体无用低能,形同朽木
无用、低能是社会强加的第二个标签。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时期,身体是重要的生产资源。强健、完整的身体是劳动、抵御外辱的根本,缺损、羸弱的身体则容易成为家庭、社会的拖累。在此种文化影响下,“聋哑瞽目世之废疾也”的观念开始生成。由于身体“不便”导致听障青少年行动能力受限,无法顺利、高效地参与社会生活,重度患者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因此,他们在人们眼中形同一群只会“分利”而无贡献的包袱、累赘。
光绪年间,丁韪良指出:“昔时民之聋聩者,每以残废目之,不屑教诲,或任粗学工作而操业为生,或竟光阴而累人养赡,良可悯也!”[11]。古楳也曾忧虑地写道:“社会对于盲聋哑等残缺不全的人,仍存歧视的心理,当作残废看待,至多不过本着人道主义,不忍听盲者、聋者、哑者立于人群之外,终身苦恼,甚至乞食道旁,因而简单施以简单的训练,增加谋生的机能。从没有想到‘天下无废人’。”[12]。现在,听障无用、低能的观念在文明进程中有所减弱,但长期的文化惯性还是让人们对他们无法平等对待。T-JJR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听障“不会说话,也听不见”,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无法建立正常的家庭。还有人认为听障是“很重的残疾,甚至是比腿瘸的,或者其他的残疾程度还要重”。T-SC也有类似的体会。“社会上的人什么吧,觉着聋人像傻子一样,一说起来这哑巴还会写字哩,还会认字哩,还会学着算数哩”。听障生们同样认为,社会对他们存在偏见,认为他们笨、“一聋三分傻”。“现在社会上大多数都是认为聋人就是傻子一样”(T-BLS),他们“思维和正常人不一样,智商不如正常人”(T-JJR),“低能,愚昧无知”(S-CMM)。这种听障者无用的观点,甚至影响到家长的观念和行为。“家里人对他也不是抱有很大希望,反正就是你长大能够顾着自己、饿不着就行了”。“他觉得聋人就算再怎么样也不会特别优秀,就是下再大的功夫,他也成不了国家主席”(T-SC)。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特殊教育的出现加剧了听障生无用的观点。许多研究者认为,特殊教育的历史就是将差异分化和障碍医疗化的历史。特殊教育让一些人接受一种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的特征就是依赖和无能。[13]对孩子进行鉴别、分类并进行特殊安置,弱化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也降低了人们的教育期望。当前,弱化的特殊教育是此种观点鲜明的注脚。比如聋普教材被分割为两种系统,聋校教材编制的原则和标准大大降低。“相对普通学校同年级同学科教材,聋校单编教材总的说在教学内容上有所减少,教学的进度有所放慢,教学的难度有所降低,九年义务教育教学总体水平相当于普通学校初中一年级的程度。这是聋校单编教材最基本的特点”。[14]以此来看,特殊教育可能不是价值中立的机制,而是污名赋予和社会再制的工具。一旦被贴上特殊教育的标签,就等于被戴上无能、异常的帽子,会影响个人的资源获取和职业选择。
(三)境遇窘迫不堪,让人可怜
“疯痴残废的一群,皆是人世间的可怜虫”。身体残缺者的污名是社会分类的手段,也是他们社会身份的形成过程。当残缺的身体被标识为“残疾”时,人们就会根据标签划出各自的群体边界,依靠库存的“我群”“异类”知识行事,残疾者因而常被排斥、疏远在社会的角落或边缘里,成为世人眼中的需要可怜、需要同情关爱的人。
“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有相当的家庭把残疾人视为累赘、讨厌的废物,不当人对待,抛在一边,冷了无人问,饿了无人管,任其自生自灭”。[15]在此背景下,世人对待听障群体不是歧视就是怜悯,缺乏平等的态度和立场。戴梦龙先生曾指出,“现社会对聋哑之成见,牢不可破者为二种,一为蔑视,一为矜悯,前者以为聋哑业已丧失官能,其行为能力实在一点都无。为无用之废物,而予以遗弃。后者转其道以论,则为聋哑者官能损失其二,行为之可怜及其愚蠢之难教化……近如豢养一无知之动物而已”。[16]这种认为听障者需要同情和慈悲对待的现象,在代表国家意志、社会文化、大众情怀的教科书中同样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残疾群体在教科书虽有“一席之地”,但所占比例明显偏低,而其形象不是令人同情的,就是身残志坚的,而后者更能引发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张恒豪、苏峰山的研究同样有类似的结论。他们分析了台湾1952—2003年间教科书中的障碍者形象,发现教科书对障碍者的描述多是可怜的、励志的、需要帮助的、鼓舞人心的。障碍被认定为个人的问题,而没有多元文化的相关讨论。[17]一位听障者对这种文化偏见非常恼怒,他指出,聋人都说:“除了听,聋人能做任何事。”“这句话好听是好听,但对中国的聋人来说,纯属十足的自欺欺人!当你听不见的时候,十个人中肯定有九个人都会叫你哑巴子。”“几千年了,我们默然,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只能闷在肚里,正好印证了‘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18]。
同情是人性的光辉。考虑到听力缺损无法享受声音的馈赠,外表与常人无异却坎坷曲折的人生等,在同情心的影响下产生怜悯心理、慈悲情怀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并不一定符合听障青少年的实际。S-GJ诚恳地指出,对听障群体“绝不能投以可怜的目光,因为我知道这样不是对他最好的。因为最需要的是自尊哦。他们都是跟普通人一样啦,虽然我(他)们的身体结构要比他(我)们要完善,但是他(我)们的工作能力也不见得要比我(他)们差呀,甚至比我(他)们要强呢?所以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两样”。
四、污名应对——听障青少年的污名管理技术
对听障群体的污名反映出社会理解、包容、支持的缺失,指明了人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不过,听障青少年即使在污名面前处于劣势,但他们并不会束手待毙。相反,通过“管理与他的缺陷有关的信息”,他们将身体转化为社会交往的符号,想方设法在与污名的较量中占得先机,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一)身体治理:常态身体的追求
当下语境下,“异常”的身心特征通常是污名滋生的源泉。在污名压力下,听障青少年及其家长很快想出身体治理的技术。即通过医学塑造或改变身体的方式改善或祛除“异常”,消除污名。“就好像残疾人去做整形手术,盲人治疗眼睛,文盲参加补习班,同性恋接受心理疗法”[19]一样,借助身体治理的方式,就能抹平身体的差异,远离污名的威胁。
1.医疗矫治的努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身体的美学标准与可视化紧密关联,身体健康、优美、发育完整被认为是生活的“基本资源”。对于身体缺失的听障生而言,如果能让身体回归正常,拥有普通人一样的听力,他们就能顺利摆脱污名,过普通人平等安然的生活。
S-ZSS告诉笔者,她非常“羡慕听人有听力”。“当想个普通,我在心里不只说过了一次了,不受人的眼光,自己做自己就好,自己的梦想,当想个普通了”。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美好的梦想呢?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听障是一种疾病,对付疾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医疗干预,这是摆脱污名的捷径,甚至是唯一道路。因此,听障青少年基本都有求医问药的经历。比如S-LX 在作文中写道,“由于我四岁因药物中毒致聋,父亲为我南下北上,餐风宿露,节衣缩食,四处求医”。甘肃家长也回忆说,“西安、南京,哪有信息我们就往哪里看,我们两个挣的钱全部都花在她看病身上了”。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家长们愿意尝试任何新奇的治疗技术:药物、针灸、按摩、敷药……“社会上一疯传哪里治耳朵好,家长都去了”(T-BLS)。“妈妈发现我听不到,带我去郑州看病,花钱太多了,针灸扎头。”“喝那个药,嗯,很苦”,“还有去河北看病,第一次去河北看病上当了,第二次又去了郑州这个”(S-JF)。虽然有的家庭并不富裕,但为了孩子早日恢复常态,治疗时家长们往往不遗余力,有时甚至十分固执。“针灸,花钱太多了,妈妈坚持不放弃,希望我的耳朵可以听到,钱花完了,妈妈去找姥姥家借钱,姥姥节约两千多给妈妈。姥姥早上4点、5点爬山砍柴,卖,挣钱。就是做藤条编的东西去卖。老爷养羊”(S-JF)。
遗憾的是,“家长只忙着给孩子治耳朵,治耳聋”,“把钱花到治疗上”,却对至为重要的康复训练知之甚少,结果孩子的听力不仅未见改善,还错过了康复的关键节点。在闭塞落后的农村,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当时只知道去医院看,到处看,至于什么康复,我们不知道。到后面她长大之后,电视上说有康复训练才知道。但是她已经长大了!要是刚几岁开始就可以”(P-HN)。
2.科技辅具的寻求
医疗矫治虽然“听起来很美”,但巨大的热情却难以换来医学奇迹的出现。“跑了很多地方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花的医疗费也不少”(P-WXD)。P-HN也说,知道孩子听力有问题后,“到医院给她看,到处治。我们跑到山西,找专家也治不好,买药、买枕头也不行。从两三岁一直看到五六岁也没有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助听器或耳蜗——这些高科技辅具成为解决难题的新途径。在广告宣传中,这些辅具可以改善,甚至解决孩子的听力问题,让“失去的身体功能重新得到实现”。这一“承诺”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因此,在耳蜗出现之前,借助助听器“恢复听力”成为很多家庭和青少年的希望。
S-CMM告诉笔者,她小时候非常希望有一个助听器。“如果我戴上助听器的话,我可以听到声音”。虽然戴起来感觉不舒服,“杂音特别多,蜜蜂叫,青蛙叫,特别乱”,但她还是希望“有”,因为“我想做的事特别多,都是靠有听力的”。S-WXD在13岁时终于有了助听器,但因为家里困难,买的是“便宜货”,所以他想换一个质量好点的,那样“听起来比较清晰吧”。不过,助听器虽然有些效果,但需要具备一定的残余听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使用。而且助听器使用起来也十分麻烦。比如啸叫、漏气、不美观,还要不断更换,“耳朵一长大吧助听器就不配合了”。于是在耳蜗出现以后,对身体改造的努力又开始发生转移。问题是,耳蜗价格十分昂贵,做完手术后还要语训,这意味着又要花费一笔费用。因此在是否选择耳蜗上,听障生们充满了纠结。S-CT说,“医院的人工耳蜗太贵了,买不起,爸爸妈妈条件有限”。S-XH也充满了矛盾,“如果有机会,不知道”。在笔者加入的“耳蜗交流群”里,经常讨论的就是如何“挣钱”做耳蜗的话题。
客观而言,身体治理虽然可以做到效果的“立竿见影”,但却并不是最高效、最务实的选择。这是因为,身体治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还伴随一定的身体伤害和手术风险。更重要的是,即使排除上述问题,它还有一定的身体“门槛”。比如很多人推崇的耳蜗,也无法适合所有个体。那些蜗后性听力损失、耳蜗骨折、内听道直径不足2毫米等的人就被排除在外。在此背景之下,一种名为“身体装扮”的技术受到听障青少年的青睐。
(二)身体掩饰:秘密信息的管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赏心悦目、令人愉悦。如果不能天然地达到这些标准,利用错觉艺术隐藏或掩盖令人沮丧的部分,同样可以起到效果的异曲同工。身体掩饰,即指通过穿衣搭配、化妆技巧、形象设计等实现对污名发生源掩盖或弱化的修饰技术。与身体治理相比,身体掩饰稳妥可靠、简便易行,因此在听障青少年的污名应对谱系中十分常见。
1.巧妙的借用
随着年龄增长,听障青少年的自尊心开始增强,对自己的身体信息变得敏感起来。为此,采取手段确保身体秘密“不泄露”,成为其公共场合行为的第一准则。比如佩戴助听器的青少年,对助听器的使用会严格控制。根据场合、对象决定佩带的必要性,如果确实无法避免,也会利用自身优势及周围环境创造出眼花缭乱的控制技术。
众所周知,助听器分为口袋型、耳挂型、耳道型、耳内型。体型越大,目标越明显,被发现的机率越高。因此体形小巧、比较隐蔽的耳内型成为听障青少年的“最爱”。“咱的孩子越是大了,越不愿意戴助听器,他怕别人看见”(T-GQH)。“几百的都是盒式的,不好看。耳背式的,也不好看。隐形的好,但是比较贵”(S-WXD)。但是,所谓隐形只是相对的。为此,佩戴助听器的青少年会根据性别、环境创造出其他防御技巧。(1)性别。借用性别优势,以头发、饰品等巧妙地隐藏秘密。比如S-SLH是女孩,它的助听器被浓密的长发遮盖,不留任何痕迹。男生的情况有些复杂,不过在长发飘飘不是性别专利的时代,这样的难题自然不算问题。(2)气候。气候不同,利用的物品也有所不同。天气寒冷时,可资利用的物品十分丰富,帽子、围巾、套头衫、耳罩等都可拿来使用。天气炎热时有些麻烦,因为炎热让遮挡耳朵的物品减少,但这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帽子、蓝牙耳机、随身听等,这些装饰既显得时尚,也能发挥遮掩的功能。
戈夫曼对身体掩饰的“套路”做过阐释。他指出,物理器械可以减轻残疾的主要损伤,但它“容易成为污名符号,从而让人产生拒绝使用的念头”。于是,听障者会采用一些方法使这些矫正器械隐蔽不见。“玛丽姑妈(一个听觉困难者的亲戚)好像对各种早期声音接收器了如指掌,这些号角状助听器品种繁多。她有各种图片,显示这类助听器是怎样装在帽中,用作装饰性的梳子、水壶和手杖,藏在扶手椅、餐桌上的花瓶,甚至男人的胡须里”。[20]凭借上述灵巧机智的防护技术,听障青少年就可能有效阻止身体秘密的外露。
2.“装”
为了隐藏身体信息,听障青少年还发展出“装”的策略。所谓“装”,就是以佯装正常的方式掩饰秘密的身体策略。
公共场合不打手语是“装”的方式之一。手语是听障群体的交流工具,但手语使用伴随激烈的身体动作,很容易造成秘密显露。于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如同一个普通人,听障青少年对手语会进行限制。比如,平时“交流感情,凭眼神;买东西,先让别人买,然后他通过观察,弄清价钱,再掏钱,不动声色地买”[21]。T-GQH也告诉笔者,听障孩子年龄越大、越聪明,烦恼就越多,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是聋人”。所以,他们在公共场合都会控制手语的使用。很多听障生也赞同这种观点。S-CMM指出,“聋人打手语的时候听人感觉特别奇怪,诧异的目光看着聋人打手语,感觉聋人手语像那个……张牙舞爪,精神病人”。为了避免嘲笑与歧视,她们没办法只好尽量减少手语交流。
听障青少年还使用另一种“装”的策略,即“把自己蒙受污名的缺点的标记显现为具有另一种特征的标记,而这种特征的污名程度更低一些”。换言之,他们与人交往时会先发制人,通过主动暴露或营造一个小的污名情景转移视线,借以掩盖自己的听力状况。生活中笔者也发现,与健听人交流时,听障青少年往往会故意装作没听清楚,或者表现得“在做白日梦,是个心不在焉的人,是个无动于衷、容易无聊的人,甚至正在头晕,或者发出鼾声”,无论如何,都会让你觉得他的表现“不会被归咎为耳聋”。[22]这实际上即是“装”的策略的具体应用。另一种“打掩护”的策略与“装”类似。比如“弗朗西斯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想出各种复杂技巧来对付‘宴会中的平静时刻’和音乐会、橄榄球比赛、舞会等的中场休息”。它的策略是:在宴会上靠着声音洪亮的人坐;如果有人直接问她问题,她就哽噎、咳嗽、打嗝;由自己控制谈话,让别人说一个她已经听过的故事,问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23]。借助这些不同寻常的“装”,污名信息被他们妥当地进行了包装和隐藏。不过应当注意,“装”的技术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苦心积虑的“装”有时适得其反,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另外一种形式的污名来。
(三)身体抗争:弱者的对话方式
当身体治理或修饰不足以解决困扰时,听障青少年还会采取另一种方式“发声”。即以柔弱的身体与不公平的秩序进行对抗。身体抗争是“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群体维权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24],它指的是以身体作为载体,通过身体的反抗性行动表达意见、诉求,实现既定目的和利益的博弈策略。在正常渠道无法维护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利用身体抗议获取道德支持,也能变身体劣势为“无权无势者的政治资源”[25]。
1.冲突性抗争
身体抗争首先表现为激烈的冲突性对抗。即以自残、自杀、自戕、破坏、暴力等极端方式获取社会关注,表达利益诉求。冲突性抗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颠覆性,是听障青少年危机时刻使用的“底线型”策略。
如前所述,特殊教育是一种污名化的机制,一旦步入其中就等于背上依赖、无能的污名。而且,在污名的环境里,听障青少年还要面对“弱化”的教育设计,为预防污染和安全保护的人为隔离。种种事实让他们认为待在学校只会妨碍发展,于是纷纷以“自毁前途”的方式选择逃离,退学、辍学的情况十分严重。S-RF指出,他们在学校“对社会了解很少,别人一问都不知道”,他非常郁闷,一度有辍学的念头。因为辍学还能“跟外面一些信息接触到,都了解”,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他的一位同学退学了,就是源于这种想法。“有一个男同学对学习没兴趣,就想退学,不想上了,他的父母家长老师都不想让他退,强迫他去上学,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让他退了。”“学校太封闭了,他想去外边多交流。”此外,意图改变现状的“努力”也在此起彼伏地上演着。S-WXD告诉我,在学校里“聋人特烦特讨厌,不满意开始破坏,有摔门窗、砸玻璃,老师批评很多次……心里就是越积越压,最后发泄地都砸门窗!有些聋人看那墙壁恨得直挠!自己手疼但是会砸墙!”S-WSH也说,学校给他们“造成内心的一些理解能力有障碍,还会造成一些攻击性的问题,如打架,对心理有伤害”。
自杀作为最为极端的方式,也是听障青少年的对抗方式之一。笔者曾遇到一位跳楼自杀的听障生,他的故事即是暴力抗拒的证明。这位听障生小时候缺乏管教,长大后脾气暴躁,经常与家人、学校发生冲突,多次自残、出走。一次冲突后,学校派老师把他送回家里,希望家人对他批评教育,但家里人又担心他在家惹是生非,又坚持老师把他带回学校……这位学生陷入进退维谷、双重抛弃的局面。于是,这位“无家可归”的孩子,选择以跳楼向所有人“亮剑”。“前一段跳楼那个孩子,他就是为了引起关注,你不是不管我吗?我就一会儿跳楼了,一会儿自杀了,就是让你来关注,让你来管我。”(T-AY)。身体对抗是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方式,“如此激烈的身体抗争手段,意味着残障者在面对社会的蔑视、污名或压迫下,死亡对他们而言不再可惧,反而成为个人逃离或宣誓权力的重要途径”[26]。
2.仪式性抗争
在暴力抗争之外,听障青少年还有温和的抗争方式。这时,身体不再是血腥的斗争工具,而是灵巧的博弈道具。没有赤裸裸的身体对抗,只有仪式性的身体表演。通过富有渲染力的象征性行动,他们有时借助佯装的方式就能吸引目光,实现“以小搏大”的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人潮集中的街头看到残疾者自持“惹眼”的身体,通过暴露“隐私”博取同情,或者听障者拿着“残疾证”乞讨,推销廉价物品等,实际上都是仪式性抗争的灵活运用。此时,展示“弱小”并非就是弱势的表现,而是弱者以退为进的生存策略。当然,依靠牺牲自尊获得怜悯总是让人有些难为情,但相比“免费的午餐”,又何乐而不为呢?S-CMM就提到这种方式蕴含的“好处”。她听力不好,腿部也有些不便,因此总能得到别人的优待。“我在聋哑学校,我同学照顾我,说我身体太弱了,不让我干活,还帮我插队。后来我想找点事干。早上六点半值日时提前半个小时去,把水洒一地,然后拿着拖把拖,我前脚拖把刚落地,后脚同学就到,把拖把给我夺过去。‘谁让你来这么早,以后活儿不需要干’。”
以劣势的身体闯入“禁区”展示力量,也是听障青少年获得“重生”的手段。习惯上人们认为,生活中存在一些身体的“禁区”,在那里,残疾者无法像常人一样出色地工作。这意味着,身体应该“呆”在各自的空间不许僭越。如果有人违背了规则,就会冲击现有的分类框架,引发混乱。但是从“倒逼”的角度而言,打破规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造混乱。混乱中人的角色发生模糊,残疾者可以借机震撼普通人的心灵,促进他们反省并重构自己的残疾观念。比如,舞台过去是健全者的天下,因为听不清声音,这里没有听障者的容身之地。但《千手观音》成功颠覆了人们的刻板认知,听障者不能跳舞的“规矩”立时风吹云散。现在,很多地方积极推动聋人舞蹈发展,听障青少年堂而皇之地进入健听人的传统领地,并屡屡在国际、国内舞台上登台亮相,斩金夺银。这种对常规的挑战搅乱了既有的分类框架,有效地开拓了他们“可被接受的活动范围”。T-SC欣喜地谈到了这种变化。“在绿城广场表演节目,表演完大家都觉得,呀!聋哑人还可以跳舞呢?跟着节奏!包括盲生能弹一些乐器,而且弹得这么好,这让人们感觉很吃惊!”“他们都没想到。”
“关心残疾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近些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取得让人欣喜的成绩。但是应当看到,在社会“有色眼镜”的指认下,听障青少年及其他残疾群体还面临着或隐或显的污名困扰,虽然这种情况与过去相比已明显改观。现在,听障青少年还面临着怪异、无用、可怜等污名偏见的干扰,生活和成长都遭到巨大影响。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和注意。研究发现,在残酷的污名指认面前,听障青少年不是沉默、被动或任人摆布的对象,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预设的规则体系进行斡旋,千方百计在与污名的较量中占得先机。这一惊心动魄的博弈过程,既反映出他们为融入社会的不懈努力,也折射出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曲解与忽视。污名带来的消极后果十分普遍,对听障青少年本身及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帮助他们消除污名,既是特殊教育事业变革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污名不是单向赋予的结果,而是内外多种因素交织共构的产物。在帮助他们消除污名困扰时,不仅需要仰赖听障青少年个人的主观努力,国家、社会、家庭及其他机构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转变人们的“残废”观念,还要在政策、制度及行动策略上做出倾斜性的调整。总之,听障青少年不是不幸,只是不便;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元独特的象征。只要提供足够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完全可以和普通人一样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10]林伶旭.无声的呐喊——台湾聋人文化的形构与危机[D].台湾:世新大学,2004:6、38.
[2]普拉尼·利亚姆帕特唐、道格拉斯·艾子.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M].郑显兰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165.
[3]杨柳、刘力、吴海铮.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117-128.
[4]田宝、张扬、邱卓英.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比较与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7(08):54-56.
[5]黄婷婷.永不止息的自我征战:听障者/聋人求学经验之叙说研究[D].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2004:17.
[6]郭卫东.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8.
[7]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M].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175.
[8]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4.
[9]张嘉文.台湾校长对特殊教育需求定义的观点之社会学研究[J].特殊教育学刊,2010(02):1-27.
[11]丁韪良.西学考略.聋聩学[M].同文馆铅印本,清光绪九年(1883).
[12]古楳 .残不废教育[J].中华教育界,1948(05):24-26.
[13]黄志成.全纳教育:关注所有学生的学习和参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7.
[14]顾定倩.聋校课程与教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64.
[15]陆德阳、稻森信昭.中国残疾人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205.
[16]戴梦龙.聋哑在法律上之研究[J].残不废月刊,1948(14):1-8.
[17]张恒豪、苏峰山.战后台湾国小教科书中的障碍者意象分析[J].台湾社会学学刊,2009(42):143-188.
[18]从故乡到异乡.我是中国聋人[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d1498010003ih.html 2008-05-09.
[19][20][21][22]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59、126、129、141、142.
[23]吴德荣.此地无声胜有声[J].新疆教育,1992(04):22.
[24]刘怡然.城中村拆迁中的身体与底层抗争[J].社会科学战线,2014(05):29.
[25]波尔塔、迪亚尼.社会运动概论[M].苗廷威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2:196.
[26]林怡华.身心障碍者的鉴定、安置——一个身体政治的观点[J].政策研究学报,2010(05):164.
The Stigma of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Yang Yunqiang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ny human difference could become the object of stigma. The study found that under the social difference classification,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ce experience various kinds of stigma.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errible and weird image, which is frightening; useless and deficient body, which is like rotten wood; poor and embarrassing situation, which makes people think they are pathetic. In the fact of the threat of stigma, they manage their bodies to fight with preset rules system, which leads to develop three kinds of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stigma, namely, body modification as the pursuit of normal body, dressed-up body as the secre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hysical struggle as the way in dialogue of the weak. Doing research on this problem can not only be beneficia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deaf and help them stay away from stigma, but also increas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support in the society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s well.
Stigma;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ce, Coping Strategy on Stigma
C913.5
A
1006-1789(2016)05-0047-08
责任编辑 曾燕波
2016-03-09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部地区残疾儿童随班就读保障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YJA880042。
杨运强,郑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