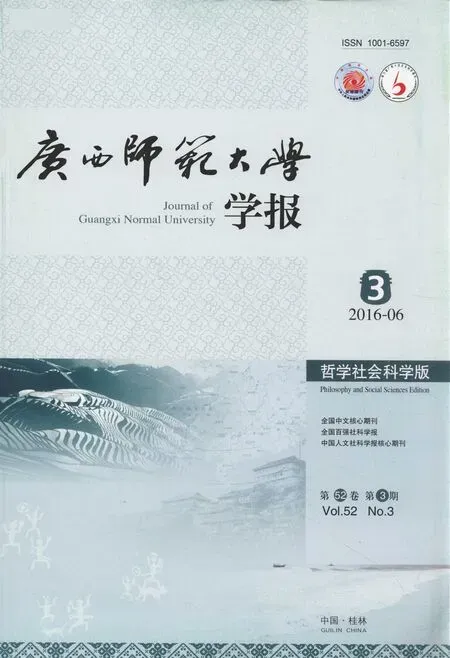规约与生计:乡规民约对经济活动的调适
——清代南疆民间自我管理系列研究之一
2016-03-19宾长初莫绍初
宾长初, 莫绍初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2.中共平乐县委党校,广西平乐542400)
规约与生计:乡规民约对经济活动的调适
——清代南疆民间自我管理系列研究之一
宾长初1, 莫绍初2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2.中共平乐县委党校,广西平乐542400)
[摘要]乡规民约由一定区域的民众集议制订,一般由族长、乡老(寨老、都老)、头人以及团练组织监督执行,对国家法起到补充作用。在清代广西社会中,乡规民约对经济活动作出了很多规范性约定,并得到实施,在保护农业生产活动、协调手工业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护圩市贸易秩序及保障商民利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相对而言,其对乡村社区经济活动的调适比对城镇社区经济活动的调适更为有效。
[关键词]乡规民约;经济活动;自我管理;调适;广西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谓之四民,除了四民之首的“士”属于知识分子、基本上不从事经济活动之外,其他三民分别从事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农、工、商业既关乎从业者的生计,也关乎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农、工、商业的发展。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是传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对经济活动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出许多管理经济活动的方法,保障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其中,民间社会的乡规民约在保护农业生产活动、协调手工业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护圩市贸易秩序及保障商民利益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为研究视域,探讨乡规民约对经济活动的调适,以就教于方家。
一、保护农业生产活动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广西在历史上是一个农业省份,以种植水稻为主,谷米生产自给有余,往往输出周边各省,尤其以输往广东为多。清代广西各地的碑刻对此有所记载,如乾隆年间的《重建粤东会馆碑记》(原碑藏于苍梧县龙圩镇粤东会馆旧址内)云:“西省田畴广美,人民勤动性成,中岁谷入辄有余,转输络绎于戎,为东省赖。”《奉督宪行藩宪永禁派抽阻挠接济碑记》记载:“粤东民食,全赖西省米谷源源接济,一有阻滞,客贩便稀,民食有碍。”[1]297清代前期广西谷米有余裕输往外省,除了上引碑文所言广西“田畴广美”、人民勤劳之外,我觉得还与广西民众有一套管理农业生产活动的办法有关。从目前搜集到的乡规民约可以看到,民间社会在保护水资源、耕牛以及确保农作物免遭践踏、破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约。
广西是水稻产区,在水稻生长期需要有充足的水资源保障灌溉。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村民往往以乡规民约的形式,组织修筑堤坝,严禁私自拥塞、开挖堤堰,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乾隆四十年(1776),荔浦县乡民立议修筑金雷坝,乡民拟订的《筑坝议约碑文》规定,凡此坝受益者,按其拥有田亩多寡派出劳力筑坝,“田亩以三十工该筑坝一人为约”,“以二十五工以上至三十工以下该人一名,三十五工以上,五十五工以下该人二名……余此类推”(按:“工”为桂东北各县田亩计量单位,1工约等于0.6亩)。当筑坝时,坝长于先一日鸣锣告知各村。第二天清晨,各人早早饮食,锣响头遍,随赴坝所;锣响二遍,齐集工地;锣响三遍,即行下水运石。“否则每人罚钱一百文,存作众人理坝修沟茶水之需。不遵众议者,任由众人定罪。”同时还规定:“所有来往木筏、竹筏,若遇天旱水紧之时,毋得任意私开,倘有不遵,一经拿获,罚钱三千六百文,交坝长筑坝公用。船只视多少加倍议罚。”[2]933光绪三十四年(1908),灵川县黄柏大堰河口及各堰车漕被篺商堵塞,“致使水车停转,无水灌田”,“对于各村农业殊多妨害”,沿河堰乡民呈请官府制止篺商的不法行为,并议定修堰简章(《孙钦晃为一六两都管理水堰暨篺商所放竹木过堰发布告示碑》),共六条,全文如下:
第一条:凡各堰被水冲有崩口,未经修筑时,无论船、篺均不得由该口放过,致加损害。犯者一经察觉,应将该船篺扣留,指名呈县讯办,并赔偿损失。
第二条:凡每年修筑各堰,应视崩口之大小、损坏之多寡,定修筑之日期,不得有所限制,致碍成功。
第三条:凡各堰河口车漕,每年自十二月初一日起,方准随堵随开,至次年二月初一日止。如有船户、篺商违规堵塞者,查觉呈县讯办。
第四条:凡各堰每年修筑时,所开消水口附口,如船户、篺商希图便利,情愿津贴修费,要求由消水口放行者,每一逗收银二仙,每船一只,收银一毫,不得任意私索。如有违规多收,致滋事端,各堰自理,堰帮概不负责。船户、篺商亦不得恃强逞放。违者处以应收修费十倍之罚金。
第五条:各堰筑成后,二比愿留水口放行收费者,仍照前条规定办理。
第六条:本规条,自呈请府宪核准日实行。
以上各条得到桂林府知府孙钦晃的认可,认为其“农商两便,尚属可行”,并将其与官府告示一同勒碑保存,“俾两造永远遵守,毋得故违干咎”。[3]470
类似的规约还有不少,如灵川县黄田村水源,水分两枝,分别灌溉村东南面、北边粮田,由于有人在天旱季节私自塞挖堰口,两枝水源水流不足,严重影响粮田灌溉,所以村老公议规约(《黄田村公议管理陋坡堰禁约碑》),将堤堰重修,两枝均匀分定,嗣后上游不得壅塞下游水口,下游也不得截挖上游水路,“如有塞截,一经查出,罚银一两”;又规定不许在此堰内车鱼,“如在此堰车鱼,罚银一两伍钱,决不容情”。[3]231这些保护堤堰沟渠的乡规民约,实际上是为保护农田水利、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乃至丰产丰收而采取的措施。
在农耕社会,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对耕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其爱护有加,广西各地甚至还有专门为耕牛举办的节日,名曰“牛魂节”。据地方志记载:“每年至五月二十内耕耘已毕,选取吉日共作牛魂节。假如一家有四人,即杀四鸡蒸糯米,糯米仍染五色,以五色蒸熟合鸡用大叶子包,各人自带到平时看牛处,至午刻各人相食,仍另以糯米饭包一大包灌牛食,以酬其耕作之劳,因名牛魂节。”[4]各地乡规民约均有保护耕牛的条款,有的规约强调耕牛的饲养,如灵川县的《桂局村公议禁约碑》要求“每日归放耕牛二次。上节人必放至社公脚下,下节人必放至湾塘岭,归时亦然。违者罚艮五分”[3]198。有的规约禁止私宰耕牛,如平乐县的《沙子杨梅村乡规碑文》提出“凡耕牛,原系耕种之本,街市、村庄毋许私宰”[5]800-801,灵川县的《河边村公议禁约碑》则规定“私宰耕牛,并借过节乱杀牛者重罚”[3]261。甚至在本地发卖牛肉也在禁止之列,如《梅知县为三都六十两图公议禁约出示晓谕碑》规定:“两里人等已奉示禁,不许宰杀牛只,即外乡生、熟牛肉亦不得来境圩村发卖。违者拿肉议罚。”[3]272总之,规约制定保护耕牛的条款,目的在于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
1.1.2 主要仪器。HP-6890/5973型GC-MS联用仪(Hewlett-Packard,USA);ELX 808型全自动酶标仪(BioTek Instruments,USA);BSA124S型电子天平(Sartorius,Germany);RE-52A型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DRT-TW型电热套(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农民辛勤劳作,盼望的是农作物顺利生长,有所收获。因此,对牲畜践踏农作物以及私自盗窃农作物的行为深恶痛绝。各地乡约对这种行为都作出了严格的处罚规定。对牲畜践踏农作物,处罚方式不一,有的规定处置猪、羊等牲畜,如灵川县的《黄栢村十甲众议立禁碑》规定:“禁田地豆、麦、菜茹、棉花、葱、蒜……牛犯一钱,猪犯枪死,猪入园亦枪死。”[3]135有的要求牲畜的主人赔偿损失,如灵川县的《塘源村众议立禁碑》规定:“禁浪放猪、牛食坏田禾、麦、豆,捉获者煎豆腐,罚肉三十斤。”[3]130对盗窃农作物的行为,几乎所有的乡规民约都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其中阳朔县的《清道光年间广和里白沙堡、立郎二村村规民约》规定得比较详细:凡偷盗田禾者,“勿论男女日获者罚钱一千六百文,夜获者罚钱二千四百文”;凡盗窃地货如豆、麦、糁、粟、高粱、包米、烟、桐、茶子等项者,“日获者罚钱乙千文,夜获者二千文”;凡偷窃田中地内茹菜、油菜、红薯、芋头、棉花、瓜果、笋子等项者,“日获者罚钱三百文,夜获者罚钱六百文”。[6]461这些措施对保障农民收成大有裨益。
二、协调手工业的各种社会关系
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除了造就了成熟的农业之外,还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在洋货输入前,广西各地的家庭手工业是家庭经济的补充。农民“各务本业”之外,“凡田间所需多以农隙自行修造”,其他如石工、缝工、木工、泥工、竹工、铁工,“亦皆力穑之家兼营”;妇女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则“纫麻出棉”,“农事既毕,机声札札,与小儿啼笑之音相杂”,一派“物不外求”的自给自足景象。[7]987这是广西全省的普遍情状,不独桂平一地状况。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一些手工业行业得到较快发展,形成了有特色的行业,主要有粮食加工业、榨糖业、榨油业、造纸业、瓷器业等。如榨油业,除了榨取花生油、茶油等食用油外,还榨取供工业使用的桐油、茴油和桂油。如平南大乌、六陈一带山区出产桂枝、桂心、桂子等,以此制成桂油,由商人贩往海外。[8]粮食加工业除了碾米等粗加工外,还有制作面条、米粉等精加工。容县“粉榨之设,由来已久……邑中业此者不下三百家,家家日耗谷百余斤”[9]1129。同时,一些村镇逐步发展成为手工业特色村镇。清末,都安、隆山、那马三县纱纸业发达,其中都安高岭圩是制造纱纸的中心,盛时(光绪末年)有槽口千余,“年造纸二万五千担以上”。[10]121临桂县东乡田心村也是一个以造纸为业的村落,至今仍有造纸用的石槽等散落在村旁。
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手工业者往往通过规约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及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临桂县东乡田心村与盐上村、王家崴都是以造纸为业的村落,三个村议定公约(《三村公约碑》,现存于桂林市临桂区田心自然村),规定禁止偷取纸料,“郡人漂洗纸料以供捞纸营生,如有偷取者,即同盗窃,罚银一两五钱”,并规定不许裁减纸料,造纸“务遵原式,方为公平,如有改小纸帘及短小纸片者,罚银五钱”。三街镇周边各村有种植甘蔗并制造黄片糖的传统,嘉庆年间,一些不法之徒扰乱正常的生产销售秩序,各村民众乃于嘉庆五年(1800)在城隍祠集议,作出如下规定:一是使用统一的公秤,不得短斤缺两。二是凡是牙人带客来买糖,每100斤,“卖主出用钱三拾贰文”;若客人独自来买糖,“卖主不得歁斤欠两,装头盖面”。卖主如果私自勾结牙人另用私秤,“假装糖面,缺少斤两,一经查出,依众公罚,决不宽贷”。三是凡客商买糖,“不得小楝内掺入大楝……如违公罚”*据《灵川历代碑文集》编者解释,“不得小楝内掺入大楝”为当地方言,其意是说,卖糖时,卖者不得暗中将小块的或碎的糖片当作整块的糖片混合在一起出售。;“各榨糖内不得掺合石羔,如违罚戏一台”。[3]221这两份规约都明确规定手工业者不许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看起来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也是维护手工业者的利益。通过规约的形式,禁止不法之徒的短视行为,以诚信维护品牌效应,保障了手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些以手工业为主的村镇,还会制订带有行规性质的规约。如灵川镇艌匠户村是以造船、艌(修)船为主业的村落,该村旧时有一个造船会的组织,凡学习造船手艺者必须先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会费加入该会。会首由全体会员公推德高望重、技艺高超者担任,每年正月十五日过后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咸丰元年(1851),该村制订规约(《艌匠户村众议修造船只收费条规碑》),对修造船只费用以及相关事务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凡入造船会者,本村人每名捐钱260文; 外村“随娘接养、招赘上门”者,每人各出钱1 200文,“如不遵者,不得学此手艺”。
第二,对制造、修理过江渡船、灵岩船、龙船等所需费用,根据吃自家饭还是吃主家饭不同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比如造过江渡船,“如四丈以上,吃自饭者,每丈价钱一千九百文,吃主家饭者,每丈价钱壹千正。如五丈以上,吃自饭者,每丈价钱贰千贰百文,吃主家饭者,每丈价钱壹千四百文,如不从众,公议罚钱壹千贰百文。如三丈以上,吃自饭者,每丈价钱壹千陆百文,老板待饭,每丈价钱九百文”。同时还规定了什么情况下论丈计价,什么情况下按点计价。如修艌旧船,“不得包断,只得点工,吃自饭者,每工价钱贰百陆拾文,船老板待饭者,每工价钱壹百陆拾文。如不遵者,公议每只罚钱壹千贰百文”。而制造新船则只能“论丈照价,不得点工,如不遵众者,罚钱乙千正”。制造灰渡船、货船等则必须论丈计价,不得“减少行价、包断、点工,查出公议罚钱壹千陆百文”。
第三,公祠不许私自使用,公物不得化公为私:“众姓公祠内不准掏牛、放物、屯草、垒石。如众上所置板凳,只许借用,不与长放家内私用,各人知会各家。如谋私用,如持强众者,公议罚钱捌百文。”
第五,对抽厘敬神规定:“新造大小船只,每捐抽钱十文;如新造龙船,每只捐抽厘金钱乙百文,归众敬神。”
第六,对欠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船老板有欠以前师傅账、需另请师傅者,“须要结清以前师帐目以后,方可开工所做”,倘有师傅明知船老板未结清以前师傅账而横行霸做者,“公议罚钱贰仟肆百文,决不宽恕徇情”。[3]321-322
据编者介绍,上碑提到的艌匠户村,以阳姓人家居多,阳姓祖上为造船军工,其中一支于明末定居艌匠户村,以造船、修船为主业。他们组织造船会,会首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会员也往往是本姓族人。可见,上述规约只适用于本村本族,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规。但该规约又规定,凡是从事造船、修船者,必须入会,必须按照会规收费,不得私自减价和改变计价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它又有行规的一些特征,我们姑且把它视为一种带有行规性质的乡规民约。这些规约对维护手工业者的利益和手工业的生产秩序乃至对本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维护圩市贸易秩序及保障商民利益
在传统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是重要的补充。在农村圩市中,商品贸易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作为商贾云集的圩市,“各乡土产之物于此售卖,各乡朝夕所需于此取给”[11]151,是商品集散地和商民交易场所。随着圩镇及其贸易的发展,在商品交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一些规约来解决,圩市交易行为也需要一些规约来约束和规范。
圩镇是介于城市和乡村的聚落,兼具城乡特性,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因此,公平贸易、诚实经营不仅是为了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圩市的正常秩序。一般而言,在圩市成立之初,官府为了招商贸易,制定圩规,勒石公告。如《温知县发布管理大河圩市场告示》中除了规定禁止各种不法行为外,还制订了各行买卖圩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牛行中买卖牛只,牛主、屠户、贩子及判牛人,一律秉承公平原则,“按牛偿价,远近一体,生熟无欺”;凡判成一头牛,只许取判钱48文,“不得通同作弊,暗索肥囊,将价高低,故为颠倒,违者公罚”。第二,买成一头牛,须交定钱100文;如果所买生牛有毛病,允许退还圩市,过期不准退还。第三,买牛人无故退还生牛,以此杀价,“造成争端,酿祸不浅,理合公罚”。第四,凡判成一口猪,每口出判钱8文。第五,盐、米、布匹、杂货等项,斗、秤、尺、寸等都要公正,不得有欺诈行为。[3]204
上述圩规要求参与买卖各方做到买卖公平、价格合理、远近一体、生熟无欺。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不法之徒采取以次充好、缺斤短两的方式,欺骗消费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商贾的声誉和整体利益。为了规范市场,约束商家的行为,各商民制订规约,严禁各种不法行为。如上文提到的《梅知县为三都六十两图公议禁约出示晓谕碑》就规定:“两里杀猪人,不得灌水,头、脚、下水不许搭肉同卖,即外乡人来卖干肉,亦不得搭,水肉更不得卖。如违拿肉议罚。”[3]272无独有偶,南宁扬美圩的《通乡士庶设立禁约永远碑记》也有类似规定:“圩市所有一切屠宰,无论皮肉下水,不得灌水、搭骨、喂盐。如有灌水、搭骨、喂盐,实有害人,任从本乡外人等获捉,众议罚银三两六钱正归庙。其秤务宜司马,如敢抗违,呈官究治。”[12]735这两份规约说明:圩市确有猪肉灌水等不法行为存在;商民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商家的长远利益,制订规约,约束不法行为。这无疑有助于圩市贸易的正常发展。
在圩镇商业活动中,除了买卖双方外,还有牙人、挑夫等参与其中。所以各地规约要求所有参与商业活动的人都要遵守圩规,不得破坏贸易秩序。最有典型性的当属大圩码头挑货力钱的有关规约。
临桂县大圩(今属灵川县)是漓江岸边的重要圩镇,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盛,百货辐辏,是漓江沿岸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不但吸引了众多客商来此经商,而且吸引了大量挑夫在此谋生。挑夫来往于船、店之间,挑运货物,遂成为大圩重要行业。为了加强管理,大圩商民历来定有章程,对挑夫脚力钱有明文规定,干隆、嘉庆年间,挑夫脚力钱是每担三四文不等;道光三十年内增至每担五六文;而到了咸丰年间,挑夫竟然向客商、铺户索要脚力钱达三五十文,致使“客商裹足不前,圩市寂寥,贫富皆为其困”。针对日益恶化的经商环境,咸丰六年(1856),念四团总局会同团总、客商、街长等开会商议,制定新章程,“勒石刊布,饬众遵守”。该章程(《念四团总局酌定码头挑货力钱告示》)共8条,涉及挑夫脚力钱及挑货秩序的有6条。第一,对挑抬店铺货物下船和在河下将货物过船的脚力钱作出明确规定:装货下船每百斤给力钱8文,并根据码头远近适当增加1至2文;河下将货物过船,每百斤给力钱3文,抬大包、大篓货物,每百斤给力钱8文。第二,挑夫挑抬货物时必须经铺户、商客验明筹码,看验箩皮后才允许挑货,不得喧哗。第三,挑夫不得私议不挑某家的货物,如有违反者,“革出团外,永远不准挑抬”货物。第四,铺户出货时,人人皆准挑抬,不得恃强霸住。第五,铺户出货时,“必由铺主先称箩皮,后到者不得掺箩强挑”。第六,挑抬者不得遗失客商、铺户货物,“倘有此情,革出,永不准挑抬”货物。[3]334-335圩镇商民通过规约对挑夫脚力钱及行为作出细致规定,无疑有助于遏制挑货过程中的不法行为,维护市场贸易秩序。
广西是一个多山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群众大多居住在大山深处,离圩市较远,加之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购买日用必需品颇为不易。一些商贩便深入山区,走村串寨,推销日用商品,并向村民收购土特产品。有些商贩还得到少数民族头领的认可和支持,定居在山区开铺经商。各少数民族制订规约,对入山商贩与乡民给予保护。我们以大瑶山石牌律为例,剖析乡规民约对保护商民利益的作用。
瑶族石牌材料颇多,但没有专门保护商民利益的石牌,对商贩进行保护和约束的条律散见于数十个瑶山主要的石牌中,目的在于保护善良商贩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村民自身利益。在保护善良商贩的安全方面,大瑶山石牌律(《坪免石牌》)规定:“不论河[何]人见客买卖生意,不得乱昨[作]横事,莫怪石牌。”[13]324石牌律(《六十村石牌》)还规定,如果客商在进瑶山的路上遭人抢劫,“众石牌人……闻知即起团追拿。如有闻知不起团追捕,究治”。[14]219可见,瑶民通过石牌律保护商贩在大瑶山的正常经商活动,这既保护了商贩的利益,也保障了大瑶山的商品流通。在保护乡民利益方面,石牌律也有明确规定,如《评王券榜牌文给照》规定客商进山买卖要公平交易,不允许坑蒙拐骗,行凶强取,“倘若不遵,任从王瑶刑罚赏令施行”[15]265;《金秀、白沙等五十一村石牌》则规定客商与瑶民做买卖,双方自行议定价钱,“算数不明,为论村团算清”[14]234。这些规定,既维护了瑶民和客商的正当权益,也保护了正常贸易的开展。
四、余论
以上是有关乡规民约对经济活动调适的评述。这仅仅是从制度层面的分析,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乡规民约的实际运作情况如何,是否有效?诸如此类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
乡规民约由一定区域的民众集议制订,一般由族长、乡老(寨老、都老)、头人以及团练组织监督执行。民国《贺县志》记载:“乡约者,本乡居民为保持一乡之公共安宁,明示禁约,使各家子弟勿相违犯者也。”乡约由本乡村耆老、各姓族老及素有乡望者发起,并定期在乡村公所、庙观等公共场所醵资设宴,召集全乡村民举行大会,提议本乡村应订立之禁约,交由会议表决。通过后将规约贴在要道通衢,以示实行,并互相告诫,切勿违犯。对违犯禁约者,视其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处理,通匪、为匪等危害地方的重罪,“由乡老或会集本姓族老捆送官厅惩办”。小偷小摸、家畜践踏人家作物及一切不道德行为,“违者由被害人或证人牵带牛畜,或连同证人到公所,投请乡老、族老详查事实,评定曲直,依照公议禁约酌罚之”。[16]194-195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由寨老(都老)、头人等监督执行。如上思地区的都老有两个主要职责:一是领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二是督促村民执行村规民约、维护村中社会秩序。村民中如果有谁违犯了村规民约或有伤风败俗之事,都由“都老”从中调解或裁决;若事情较为复杂、问题较大,“都老”解决不了的,则召开长老会议或村民大会研究讨论,作出裁决。[17]107由于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又有族长、乡老、头人等监督执行,乡规民约对乡民有较强的约束力,实际效果也比较明显。如贵县乡绅龚振家“力田习贾”,治家严整。“制六庐乡约六条,行之数十年无弊……家训十六则,子孙世守。”[11]1002-1003在少数民族地区,乡规民约的社会效果更为明显。如三江县侗族聚居区,清咸同以前,“民间设立条约甚严,遇有偷盗,不论大小,鸣众集款杀之,不报官司,故民不敢为盗。凡牛羊放草,任其他往,主不寻捕,听其自归,鲜有失者”。咸同之后,乡规民约不如前此之严酷,但其成效,“历有表现于社会,其自治自卫之精神,殊有足纪也”。[18]157-158
圩市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规约由绅商合议制订,由团绅监督执行。但是,有研究者认为,圩市禁约的实施效果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该研究者援引一位黄姓扬美人的话说,扬美商人在早先应该还是“比较老实”的,只是到了后来,“做”的人多了,法不责众,长老们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19]198大圩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上文提到,咸丰年间团绅、客商制订章程,对挑货力钱及行为作出细致规定,对维护圩市贸易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光绪六年(1880),又有上、下码头一些不安守本分的挑夫混乱强挑、勒索商人、滋事争斗。大圩盐运水利分府不得不传集两码头挑夫百余名集议,规定以后各挑夫都要按照章程,不许混挑货物,不得遗失客货,不得勒索脚力钱。如有混挑货物者,除公同议罚外,还要送官究治;如有遗失客货者,要照价赔偿;如有勒索脚力钱者,一经查出,照议等罚。盐运水利分府还出示晓谕,自本章程出示之后,各挑夫必须遵照章程,安分守己,“倘有不法之徒混乱领挑、滋事、并勒索挑力钱文,许该团绅、客商、□头指禀重究,决不姑宽”。[3]404官府介入圩市管理,说明民间禁约在圩市管理中的效果是暂时的、有限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荔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荔浦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6.
[3]曾桥旺.灵川历代碑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4]颜嗣徽.归顺直隶州志·风俗志[O].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5]平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乐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6]阳朔县志编纂委员会.阳朔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7]程大璋,等.桂平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8]张显相,黎士华.平南县志·舆地·物产[O].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9]易绍德,封祝唐.容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10]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1]欧仰羲,梁崇鼎,等.贵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12]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宁市志·文化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13]莫金山.瑶族石牌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14]黄钰.瑶族石刻录:第一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1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6]梁培煐,龙先玉,等.贺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17]《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8]魏任重,姜玉笙.三江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19]吕俊彪.财富与他者:一个古镇的商品交换与族群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文俊]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3.001
[收稿日期]2015-12-18
[作者简介]宾长初(1962—),男,广西平乐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莫绍初(1963— ),男,广西平乐人,中共平乐县委党校讲师。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3-0001-06
Norms and Livelihoods:the Adjustment of Village Rules for Economic Activities——Part One of a Serial Research on the Folk Self-management in Southern Frontier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IN Chang-chu1, MO Shao-chu2
(1.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2.CPC School of Pingle County Committee, Pingle 542400, China)
Abstract:Village rules are formulated through collective discussion by the folk people in a certain area. The kind of rules is commonly supervised and implemented by heads of clans, the elder with high status in a village (or heads of fastnesses, or dulao, which means a head of a clan in the ethnic Zhuang), tribal chiefs, and organizations of tuanlian (a kind of village military group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16-1912), and functions well as a complement to the national law. In Gu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village rules made a lot of normative agreements for and were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spects such as protec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coordinating var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intaining fair trade order, and ensuring the interests of merchants. In contrast, the kind of rules functions better in adjusting social economic activities in rural rather than urban communities.
Key words:village rules; Guangxi; economic activities; self-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