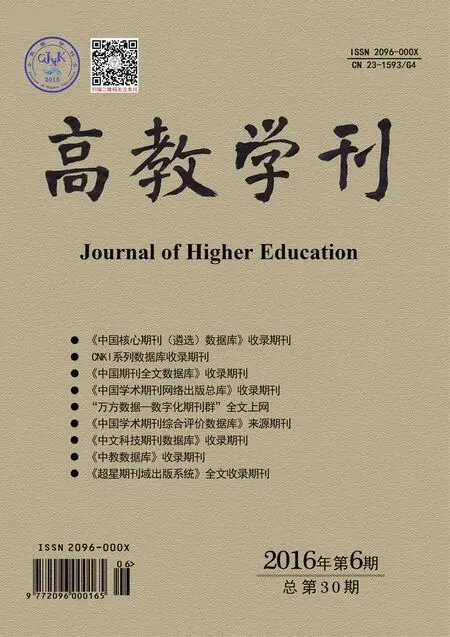隐喻认知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如何培养大学生隐喻能力*
2016-03-18段钨金王颖段亚妮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唐山063009华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河北唐山063000
段钨金 王颖 段亚妮(、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唐山063009 、华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河北唐山063000)
隐喻认知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如何培养大学生隐喻能力*
段钨金1王颖1段亚妮2
(1、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唐山063009 2、华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河北唐山063000)
摘要:隐喻能力是大学生必备的英语语言能力之一,本文围绕如何培养大学生隐喻能力,对隐喻能力内涵重新界定,以此提出从隐喻的体验认知理据、原型范畴意识、意象图式路径、概念整合模式四个方面来考量如何培养大学生的隐喻能力。
关键词:隐喻认知;隐喻能力;大学英语教学
王颖(1978,9-),女,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段亚妮(1990,6-),女,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
Abstract:Metaphoric competence is on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bilities that all college students must possess. Concerning how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metaphoric competence, this essay redefines metaphoric competence, 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taphoric compete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four important aspects of cognitive motivation, prototype category awareness, image schema approach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Keywords:metaphor cognitive; metaphoric competenc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引言
20世纪70年代,G.Lakoff和M. Johnson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提出了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远不只是语言中的修辞手段,更是人类认知和建构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人们通常使用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或理解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使用隐喻,正是由于隐喻的普遍性,隐喻认知理论认为,在目的语中学习,使用和理解隐喻的能力非常重要,这种能力就是“隐喻能力”。
近年来,隐喻能力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关于隐喻能力的研究一方面是综合性的,集中体现在隐喻能力测试(Asch & Nerlove 1960;Piaget 1961;Winner 1979等)以及隐喻能力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Glicksohn 1993;Boers 2000;Littlemore 2001;魏耀章2007等);另一方面是分项研究,分别从隐喻理解(Danesi 1994;王寅2004;袁凤识2012等)、隐喻解释(Johnson 1989;Littlemore 2001;石磊2010等)和隐喻产出(Danesi 1 994;Johnson,1996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以往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儿童或母语为英语的人群或英语专业学生,而对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隐喻能力的研究在国内很少。鉴于此,本研究从隐喻认知理论出发,探究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如何培养学生隐喻认知能力,重点思考对隐喻能力内涵的重新界定,以此提出培养大学生隐喻能力的具体内容。
一、大学英语教学与隐喻能力的培养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4日发布的有关“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数据”统计,2015年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为4018 .1万,大学英语教学面对着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对外交流和国际化进展程度,而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判定取决于大学生的英语能力。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这里所说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目前主要指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前者是乔姆斯基的核心概念,指理想的语言使用者关于其母语语言系统的知识,后者是海姆斯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说话人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Hymes,1972,转引自严世清,2001)。Danesi最早提出了隐喻能力(metaphorical competence)的概念,Danesi(1994)认为,“隐喻能力”是“概念流利”(conceptual fluency)的下意概念。用隐喻方式说话是本族语者语言能力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说,隐喻能力是人们熟练掌握一种语言的重要标志。王寅等(王寅,李虹,2004)通过考察“隐喻”一词在《辞海》中的定义发现人们习惯性把隐喻归入修辞学范畴,隐喻能力属于语言能力中的一种,而认知语言学将隐喻提高到人类思维和推理的高度来认识,看成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因此隐喻能力就不应再被看成语言能力的一部分,进而提出在语言教学中要同时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隐喻能力的“三合一”的语言教学观,并建议在新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应当明确提出“三种能力培养不可偏废”的观点。我国英语教学的现状是,学习者“仅仅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性而不顾多样性,学生的二语能力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没有明显的进步”(文秋芳,2001)。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使用失误以及石化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由于隐喻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特征,二语学习中隐喻能力的培养以及隐喻语言的使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因此,学习者隐喻能力的培养应该也有必要作为二语学习的目标。
那么,如何界定隐喻能力?隐喻能力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问题学界目前依然没有达成一致。Danesi(1995)将隐喻能力定义为识别和使用新颖隐喻的能力。Low(1988)概括隐喻能力为隐喻意识与理解以及隐喻的创造策略。Littlemore(2001)认为,隐喻能力分为四种能力:隐喻识别的准确性、隐喻理解的速度、隐喻解释的流利性和隐喻产出的原创性。以上对隐喻能力的定义基本上都属于对隐喻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国内学者(严世清,2001;王寅,2004)认为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隐喻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三个概念,其中隐喻能力是掌握一门语言的高层次标准,对于扩宽思路、创新思维起着重要作用,应与其他两种能力受到同等待遇。袁凤识等(2012)认为隐喻能力的定义应该充分体现出区别性特征和认知语言学体验观,并提出隐喻能力的新定义,认为隐喻能力是“认知主体基于自身体验在两个不同范畴的认知对象之间构建一定语义关联的能力”。这一定义有一定深度,其核心是基于体验构建认知对象间的语义关联,但深度不够,没有回答如何构建语义关联问题,因此,我们主张对隐喻能力重新定义,认为隐喻能力应指以体验哲学为指导,具有较强的原型范畴意识,善于应用意象图式、概念整合等思维模式建立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关联,实现语言意义深度扩展的能力。以上对隐喻能力的重新界定重点从隐喻的体验认知理据、原型范畴意识、意象图式路径、概念整合模式四个方面细化了隐喻能力的内容,下文围绕这四个方面探讨如何培养大学生的隐喻能力。
二、引导学生探寻隐喻的体验认知理据
体验哲学最早由Lakoff & Johnson(1999)提出,其主要观点认为:范畴、概念、心智和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的感知而逐步形成。体验性哲学认为人的身体的、认知的和社会的体验是形成概念系统以及语言系统的基础,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体验哲学理论主要包括三条基本原则,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Lakoff & Johnson认为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通过隐喻建构,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而不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心智能力。思维的隐喻性体现在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语言是人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人际世界的感知和体验,是基于感知和体验的高级认知活动,而隐喻则是人类进行高级思维和处理抽象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文秋芳,2013)。由此可见,隐喻是以体验认知为理据的。
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形成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也是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和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类对空间概念的理解是以人体结构为中心进行的,从而产生了前后、上下、左右等概念,通过隐喻应用到抽象概念,如用于时间,便有了the day before yesterday和the day after tomorrow及前天、后天的表达,用于社会域,把社会阶层分为upper class,lower class,用于政治域,有left wing,right wing(左翼、右翼),汉语还有左倾、右倾,左派、右派等。以人体部位为隐喻源就更普遍了,以英语face为例,人们通过对自身面部的体验,依此为隐喻源来喻说其他尤其是更抽象的概念,如物体的正面the face of a lock,或指外表、外貌the face value,on the face of it,或指名声、尊严lose or save one's face,或指胆量He had the face to ask for more。或用于动词表示面临、遭遇The world is facing a serious climate challenge。或表示直面、接受Let's face it。
可以说,所有隐喻表达都可以找出体验认知理据,大学英语教学中只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寻找语言背后的体验认知理据,就能逐渐培养他们的隐喻意识,从而不断提高他们的隐喻能力。
三、强化原型范畴意识,培养学生词汇深度知识的扩展能力
人们通常用词汇量的大小来指学生的词汇广度,而词汇深度知识指的是“学习者掌握一个词全部意义和用法的程度”(李晓,2007),包括词的多个义项、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搭配。所谓词汇深度知识的扩展能力指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能够在词汇的形态(包括音位和形位)和语义之间,词汇意义与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能力。例如学习英语词interview,首先能够发现该词在形态上是由两个形位(或称词素)组成,即inter和view,前者是“相互”之意,后者是“看”,所以形义结合得出它的原型意义是“相互看一看”“相互见面”,进而扩展为:会晤(领导之间见面)、面试(考官与考生见面)、问诊(医生和病人见面)、采访(记者与公众见面)、访谈(实验者和被试见面)等。由于扩展能力是深层次的信息处理能力,因而它能有效促进信息在记忆中的保留和从记忆中提取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学习。
认知语言学认为词义的扩展主要是通过隐喻(也包括转喻)来实现的,即用一事物来喻说另一事物,把具体概念映射到抽象概念,利用已知概念领域预测未知事物,从而实现了词义的扩展,如hand原型意义是人体上肢腕以下拿东西的部分,通过隐喻可以扩展为:
(1)形状、功能上类似人手的东西,如clock hands;
(2)手有左右之分,可用以指方向、方面,如turn right hand,turn left hand,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3)儿童最早的体验之一是用手抓东西,如玩具,所以隐喻为掌握、控制,例如,I shall put the matter into the hands of my solicitors.我将把这件事交给我的律师们去处理;
(4)以手做事,进一步扩展为参与、照顾、帮助,如,The hand of the military in shaping government policy was obvious.军队显然参与(插手)了政府政策的制定。The child is in good hands.这孩子有人照顾着;
(5)与序数词连用表示来源,如I heard the news at first han fr om her.我直接从她那里得知这一消息,materials at second hand指第二手材料。
强化原型范畴意识就是强调英语学习过程中词汇原型意义优先学习的学习策略,然后从原型意义出发,通过隐喻或转喻,以链接或辐射的方式扩展词义,最后形成词汇的语义网络。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词汇深度知识的扩展能力,又能减轻学生记忆负担。
四、通过意象图式思维路径提高学生隐喻理解能力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是一种概念结构,是体验性在认知上的体现。基本的意象图式植根于日常的生活体验中,如感觉、运动、发力、受阻等。这些图式与我们身体的构造和姿势、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对其他事物的操控等密切相关。在与世界的交互中,我们赋予世界秩序和模式。通俗地说,意象图式是我们脑子里存储的大量静态和动态的画面和场景。基本的意象图式用于抽象的认知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概念隐喻。
Mark Johnson在他的The Body in the Mind著作中列举了27个作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图式(M. Johnson,1987:126),Croft & Cruse(2004:45)概括了7大类意象图式,王寅认为基本意象图式主要有11种:容器、路径、连接、力量、运动、平衡、对称、上下、前后、部分——整体、中央——边缘等。意象图式通过隐喻机制扩展后可以形成更多的尤其是抽象的范畴和概念。王寅指出意象图式是理解隐喻和转喻的关键,当一个具体域的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抽象域的概念时,意象图式起了关键作用,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的重要依据。“人类的理解和推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意象图式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意象图式交织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丰富的经验网络和概念结构,这就是我们能理解意义的基础。”(王寅,2007:177)以容器图式为例,人类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一个容器,勾画出一个三维空间,具有内部和外部,如,In me thou seest the twilight of such day. In me thou seest the glowing of such fire.(Shakespeare,Sonnet 73)诗句中的in me就是一个容器图式,当把人体看成是容器时,容器里所装的是可以感知到的实体或物质,及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the twilight of such day,the glowing of such fire。再如I'm seeing love in her。可以用隐喻的语言解读为:在她的身体这个容器里装满了叫做爱的东西(段钨金,2012)。再如路径图式,通常包括始源——路径——终点,如She's writing a PhD thesis and she's nearly there。这里nearly there就是强调路径的终点,以路径图式隐喻写作过程,及WRITI NG IS TRAVELLING,视活动沿着路径发展,nearly there告诉我们她即将完成论文写作。
既然意象图式是理解隐喻的关键,在教学中向学生明示各种各样的意象图式,训练他们用意象图式路径进行思维,从而理解抽象、复杂的隐喻表达,就可以提高学生的隐喻理解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善于进行意象图式的思维就是具备了隐喻思维的能力。
五、建构概念整合思维模式,培养学生隐喻的动态整合能力
随着心理空间理论的发展,Gilles Fauconnier & Mark Turner(2002)发现了反映许多语言现象中的一条重要的心理空间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概念整合包括建立相互映现的心理空间网络,并以各种方式整合成新的空间。概念整合网络包含四个心理空间,其中两个称为输入空间(input spaces),并在其之间建立跨空间的映现。跨空间映现创造或反映了两个输入空间所共享的更抽象的空间,即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第四个空间是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是从输入空间中进行选择性的映现而来的,它可以各种方式形成两个输入空间所不具备的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并可把这一结构映现回网络的其它空间中去。
Fauconnier & Turner认为概念整合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叫做双域整合能力,“人类的特性就在于具有双域概念整合能力”(转引自,王寅,2007:217)。概念整合中的两个输入空间相当于隐喻中的两个域(始源域和目标域),整合空间所产生的新创结构便是隐喻的喻底,所以概念整合理论能很好地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及信息差异大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并置后是如何产生隐喻意义的。如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用始源域butcher来喻说目标域surgeon,二者信息差异较大,并置后产生了两个输入空间:外科医生、屠夫。前者使用工具为手术刀,行为过程是给病人做手术,行为目的是治病救人;后者使用工具是屠刀,行为过程是屠宰动物,行为目的是食用或出售动物的皮肉。类属空间是共有信息:人使用锋利的工具对另一生物体施某一行为。经过动态整合后,在整合空间产生新创意义:该外科医生像屠夫对待动物一样对待病人,这是个拙劣的医生。
既然说概念整合理论能很好地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那么,要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就势必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概念整合能力,虽说概念整合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带有一定先天性,但对于学习那些概念结构复杂、信息差异悬殊,需要进行动态整合的隐喻来说,教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结束语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正处于新一轮的深度改革阶段,有关专家正在研究制定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新指南应该考虑将目前日益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教学新理念纳入指导思想加以重视,尤其应该考虑将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同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等量齐观,深入思考如何改革大学英语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来提高大学生的隐喻思维能力。鉴于此,本研究以隐喻认知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为指导思想,围绕如何培养大学生隐喻能力展开研究,重点从隐喻的体验认知理据、原型范畴意识、意象图式思维路径、概念整合思维模式四个方面细化了隐喻能力的内容,提出通过引导学生探寻隐喻的体验认知理据,强化原型范畴意识,通过意象图式思维路径和概念整合思维模来提高学生隐喻能力。本研究可望对新指南的制定有所贡献,对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所作为,同时为认知语言学服务于大学英语教学事业有所推进。
参考文献
[1]Asch,S. E. & H. Nerlove.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Function Terms in Children [A]. In Kaplan,Bernard and Seymour Wapner(eds.).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Theory[C]. 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0.
[2]Boers,F. Enhancing metaphoric awareness in specialized reading[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0a,19:137-147.
[3]Croft,W. & D. A.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4]Danesi,M. Recent research on metaphor and the teaching of Italian[J]. Italica,1994,71:4.
[5]Fauconnier,G. & M.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ew York:Basic Books. 2002.
[6]Lakoff,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Littlemore,J. Metaphoric competence:a language learning strength of students with a holistic cognitive style [J]. TESOL Quarterly,2001,35(3):459-491.
[8]Low,G. On teaching metaphor[J]. Applied Linguistics,1988,9(2):125-147.
[9]Johnson,M. 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0]Winner,E. New names for old things:The emergence of metaphoric language[J].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1979(6):469-491.
[11]段钨金.莎士比亚第73首十四行诗的认知隐喻解读[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17-120.
[12]李晓.词汇量、词汇深度知识与语言综合能力关系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352-359.
[13]石磊,刘振前.隐喻能力研究:现状与问题[J].外国语,2010(3):10-16.
[14]魏耀章.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对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理解和生成的影响[D].上海交通大学,2007.
[1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6]文秋芳.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17]严世清.隐喻能力与外语教学[J].山东外语教学,2001(2):60-64.
[18]袁凤识.再论隐喻能力的定义[J].外语教学,2012(5):1-7.
作者简介:段钨金(1962,2-),男,汉族,内蒙古集宁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2015年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隐喻认知视角下的语言实体观研究”(项目编号:HB15YY011)和2014年河北省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立项项目“隐喻认知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如何培养大学生隐喻能力”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YYJG24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06-0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