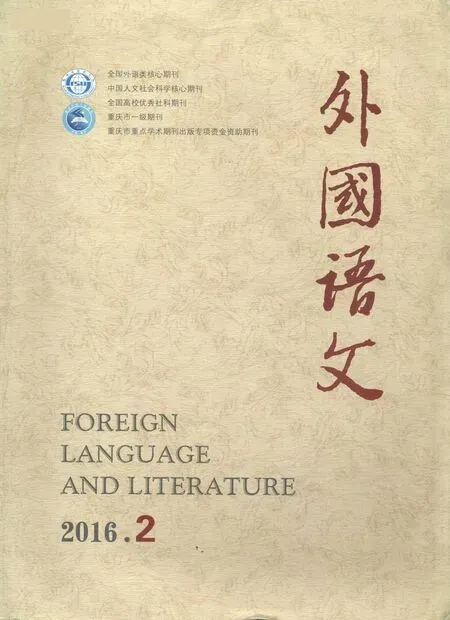救赎的力量
——论《大主教之死》的审美救赎
2016-03-17张健然
张健然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92)
救赎的力量
——论《大主教之死》的审美救赎
张健然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300192)
摘要:在地域小说《大主教之死》中,薇拉·凯瑟通过表现土著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观念以及凸显他们的“新感性”特质和印第安艺术的“光韵”,展现出印第安文化具有治愈现代文明痼疾和挽救现代性危机的救赎力量,诠释了文学艺术担纲的审美救赎之职。审美救赎是凯瑟打破资本主义社会“铁笼”的策略,旨在纠正启蒙现代性的过激发展带给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以期建立一种人与社会、自然与文明、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理想生存范式。这些艺术构想不仅与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观相互抵牾和抗衡,还是凯瑟在想象世界中探求救赎现代性之策的最佳脚注,进而表明她的地域书写以一种超越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国家、本土与全球相互对峙的创作姿态,介入社会现实和反思人类文明的出路。
关键词:薇拉·凯瑟;《大主教之死》;审美救赎
0引言
长期以来,评论家将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视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地域文学的代言人,将她的作品等同于“怀旧”“保守”和“反现代”,并认为它们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具有“逃避主义”之嫌(Reynolds, 1996:1)。诚然,在以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为背景的地域小说中,凯瑟颂扬拓荒者纯良、敦厚、实干的美德,描摹出富有乡土色彩的美国西部图景。但这并不说明作家刻意回避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招致的社会弊端,亦非盲目地怀旧,更遑论逃避问题层出不穷的现代社会。凯瑟生活和创作的黄金时段见证了美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从田园文明向机械文明转型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工业化和标准化的社会大生产,合力将美国带入快速的现代化进程。毋庸置疑,作为历史现代性的基本维度,社会和经济现代性奠定了现代美国文明的物质基础,但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的文明“综合征”。资本主义的追本逐利和精于计算将现代文明推向异化的渊薮,现代人沦为机器大生产流水线上的齿轮,人际关系疏离,炫耀性消费盛行,社会物化,这些文明“综合征”共筑成一道美国社会的病态景观。正如迈克·斯宾德勒指出,随着汽车、消费市场、超市、购物中心等现代性的标志遍及美国社会的角落,“美国中西部地区也正在步步逼近灾难,淳朴粗犷的小镇风貌日渐模糊,古道热肠的‘西部精神’消失殆尽,人格沦丧和人性扭曲是人们对乡村小镇的普遍感受”(Spindler, 1983:98)。现代性以一种强大的吸附力,将“进步”“祛魅”等启蒙的核心观念附着于美国中西部的乡村小镇,使得该地域普遍受到文明“综合征”的侵扰。面临现代性痼疾向乡村小镇蔓延的现象,以薇拉·凯瑟为代表的地域作家在创作中是否仅仅倾向于诗意化的乡村小镇叙事?是否她的地域作品缺少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答案是否定的。凯瑟不同于同时代的德莱塞、菲茨杰拉德、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后者无情地撕下启蒙现代性的光鲜面纱,揭示现代人的精神萎靡和幻灭,并在艺术殿堂开始奥德修斯式的求索,寻求拯救没落的西方文明的方案。她的大多数地域小说以乡村小镇为叙事空间,将诗意化的乡村小镇叙事作为管窥现代性之隐忧的视角,并试图从这些叙事空间表征的地域文化中觅得救赎现代性的精神支点。这些思想前瞻性地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宗教衰落之后,用“审美救赎”的光亮烛照人类文明出路的理念。
作为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审美救赎”以批判工具理性为理论出发点,矛头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异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主张凭借审美或艺术的力量,对宗教沦落之后陷入社会“铁笼”中的现代人和拙劣的现代文明提供一种世俗救赎。审美救赎的目标是抑制工具理性,克服异化力量,恢复人的完整性。面临一个传统崩塌、现代人精神式微的世界,马克斯·韦伯、赫伯特·马尔库塞、西奥多·W.阿多诺等西马批评家都肯定艺术具有的审美救赎功能,极大地丰富了审美现代性的内涵。韦伯明确指出,艺术具有将人从理性主义之重压下解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Weber, 1946:342)。马尔库塞认为,审美通过某一种基本冲动(消遣冲动)而发生作用,能够“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马尔库赛,2008:119)。阿多诺坚称,宗教衰落,传统消逝,现代艺术和文学在提供价值判断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艺术能重新展现人们在现实中所异化的人性、理想和内心的乌托邦,因为“艺术是对被挤掉的幸福的展示”(Adorno, 1997:136)。实际上,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判断”的概念和“审美无利害”论,肯定审美带来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康德,1964:46)。谢林秉承康德的审美立场,提出“艺术哲学”的概念,并希望通过审美带来的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实现拯救人类的宏大理想。可以说,审美的救赎功能是一个美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命题。席勒提出审美涉及的感性冲动能弥合人性的裂痕;尼采将酒神精神视为人走向自由的手段;海德格尔倡导人类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这些哲学家的出发点是肯定艺术作品的审美救赎之职,借此,他们开启了批判现代性的先河。
作为美国地域文学的典范,凯瑟的地域创作向读者展示一个充满“可能性救赎”的世界(Fisher-Worth, 1990:37)。本文以凯瑟的地域小说《大主教之死》(DeathComesfortheArchbishop, 1927)为例,将其放置在作品创作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大背景下作考察,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阐释作品的审美救赎思想,认为凯瑟通过表现土著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观念以及凸显他们的“新感性”特质和印第安艺术的“光韵”,展现印第安文化具有治愈现代文明痼疾和挽救现代性危机的救赎力量。审美救赎是凯瑟打破资本主义社会“铁笼”的策略,旨在纠正现代性的过激发展带给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以期建立一种人与社会、自然与文明、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理想生存范式。这些艺术构想不仅与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观相互抵牾和抗衡,还是凯瑟在想象世界中探求救赎现代性之策的最佳脚注,进而表明她的地域书写以一种超越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国家、本土与全球相互对峙的创作姿态,介入社会现实和反思人类文明的出路。
1解放自然的审美救赎观
罗伯特·多曼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地域主义和现代主义有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把握到启蒙现代性的病灶在美国社会的反映,皆把美国表征为一个“非人的、动荡不安的、颓废的、自私的、物化的、空虚的、堕落的国度”(Dorman, 1993:2)。这些负面表征是启蒙现代性将现代文明带入危机状况的有力举证。以防美国继续堕落,避免人的精神沙化愈发严重,以及规避传统彻底崩塌,现代主义作家积极寻求解决启蒙困境和救赎现代人的方案。埃斯特拉德·艾斯泰森精辟地指出,“现代主义可被视为美学英雄主义,面临现代世界的混乱(一个‘堕落’的世界),它将艺术视为……是对现代现实中的混乱秩序的一种拯救”(Eysteinsson, 1990:9)。如果说具有世界主义视野的美国“垮掉一代”的作家纷纷走向巴黎左岸,向古老的欧洲文明汲取救国的养料,而哈雷姆文艺复兴的黑人作家从黑人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对抗同质化社会的策略,那么,地域作家则从地域文化和社群意识中获得疗治现代性病症的精神力量,体现出知识分子在现代文明陷入一元化危机的大背景下试图缓解现代性危机的审美救赎思想。
同样地,凯瑟的地域小说《大主教之死》是一部浓缩了作家审美救赎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被批评家称为是凯瑟“最为精心构思的一部作品”(Woodress, 1987:406),小说以19世纪40年代拉都主教和助手维兰在新成立的新墨西哥州传教的经历为线索,探讨人与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多维关系。凯瑟从现代的视角重审历史,引领现代人走进印第安人居住的美国西南部和体验多元化的地域风情,凸显印第安人的淳朴以及他们解放自然的天性。借此,凯瑟一方面影射她写作时代的物化现实;另一方面,意在呼吁在异化社会倾轧下的现代人放弃矫揉造作的物化审美,走向自然审美,并在解放自然之中缓解现代生活带来的精神焦虑和心理恐惧,使得处于均数状态的人们在此岸获得精神依托。
在《大主教之死》中,凯瑟给精神空虚的现代人开了一剂审美救赎的良药:解放自然。依照马尔库赛的观点,解放自然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解放人的自然,即人的原出冲动和感觉;二是解放外部的自然界,即人的实存的环境 (马尔库赛,2008:121)。就该小说而言,解放自然的审美救赎观是指解放现代人的外部自然环境。凯瑟通过描绘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象,引导现代人效仿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崇尚自然,释放自然中促成生命的原始力量,创造民胞物与的生活意境。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欲动促使他们尊崇大地,关爱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每一种生命体。透过拉都主教的视角,现代人管窥到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之道。千百年来,这些纳瓦霍人、阿孔玛人、霍比人、普韦布洛人和佩科斯人是美洲大陆上最和善、最忠诚的居民。他们虽属于不同的部落,但解放自然的理念将他们紧紧相连,共同谱写出人在自然中“诗意栖居”的和谐乐章。凯瑟写道,印第安人“是真正地生活在他们的岩石上:生于斯,死于斯”(Cather, 1931:99)。他们死后把能量还回大地,供养其他生物,以轮回的方式回报自然的恩泽。这种行为既体现一种关爱自然的伦理思想,又再现了解放自然的审美观。印第安人僭越人与己、物与我的差异,遨游天地,以解放自然的精神腾飞在理性不能上升的精神高空,诠释了一种和谐的、无功利性的审美理念。
解放自然,不干预自然的运作,是印第安人抵制大自然被启蒙现代性的“祛魅”逻辑所统摄的方法。印第安人从不把自然当作实用对象,却将自然看作美的发源地,尊重自然的原初价值,以素朴的生活方式在自足自为的自然本体中,参与宇宙的和谐运动。他们认为自然是万物之母,因而,从不试图改变大地的容貌,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对大地的关爱。小说中,印第安人的住所完美地展示出他们与自然相融相契的生活状态。“霍比人建在平顶山上的村庄,与脚下的岩石合为一体,从远处看根本就察觉不到。”(Cather,1931:236)印第安人“无论到那里,从不惊扰任何东西,来去不留痕迹,像水中的游鱼,天上的飞鸟”(Cather,1931:236)。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科利考特对印第安文化的评价相吻合:“传统的印第安文化象征着一种遗失但未曾忘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Collicot, 1998: 203)在此,凯瑟借印第安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影射现代人生活的物化和非自然性。小说发表于1927年,此时的美国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虽迎来经济现代性的快速发展,却招致社会异化、实用主义泛滥和工业主义甚嚣尘上等现代性的拙劣后果。对此,凯瑟深感厌恶。在小说中,她虽未直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将自然空间彻底地转化为资本空间的做法,但她把前现代的自然空间视为尚未受商品经济运作影响的审美对象,使之充满不可言说的美感,并以此召唤现代人将解放自然看作现代主体通达精神乐园的一种救赎方式。
凯瑟倡导解放自然的审美救赎观,并不体现为一种无目的怀旧,而是一种包含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凯瑟的怀旧不是呼唤现代人回到前现代的自然空间,而是将前现代作为反衬现代的一面镜子,映照现代社会的弊病所在。她的怀旧是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否定之上,体现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即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国家文化与地域文化、技术文化与自然文化甚至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压制与反压制的关系。可以说,凯瑟在《大主教之死》中对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审美观的再现,意在突出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之中怀旧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地域与国家之间相互博弈而形成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助推无精神寄托的现代人从孕育印第安文化的地域文明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原动力。凯瑟期望通过解放自然产生的审美体验,修复工具化的文明常规加诸现代人之身的精神创伤,矫正理性主义钳制现代人的情感表达而造成的人格扭曲,因为审美这一种表意实践“在恢复被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表意实践所‘异化’了的人的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潜能”(周宪, 2005:158)。《大主教之死》中解放自然的审美救赎观是肇始于浪漫主义主张解放自然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升华,也是凯瑟对生活在千篇一律之中的现代人实施诗意救赎的艺术构想。
2恢复艺术“光韵”的审美救赎观
不同于其他20年代的知识分子公开地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展开“无情的”“全面的”批判(虞建华,2004:25),凯瑟以一种内省的姿态,撤回到一片安全的主观文化岛屿,远离瞬息万变的客观文化,辩证地考察现代社会的利弊,寻求对抗社会异化力量的策略。凯瑟和她同时代的作家面临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宗教衰落、信仰动摇、传统凋敝、精神干瘪的物化社会。宗教伦理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传统理念亦不能舒缓现代人焦虑、空虚和怀疑的情绪。那么,人如何在现世找到精神皈依?阿索希娜指出,凯瑟视“艺术为宗教”(Acocella, 2000:12)。在凯瑟看来,艺术能够代替宗教,通过心无旁骛的审美体验,辅助现代人重建心灵的乌托邦,兑现启蒙规划许诺人们的幸福生活。无独有偶,在《大主教之死》中,凯瑟渴望用印第安人的艺术“光韵”,照亮异化生活中的灰暗场景,重振死气沉沉的现代生活,以期解救困囿于社会“铁笼”中的现代人。
小说中,印第安人的艺术“光韵”拥有田园艺术的和美与宗教艺术的凝重,它焕发出令人膜拜的气息,不仅能抵制机械复制时代造成艺术的平庸化,还能整合碎片化的现代生活,以及免除现代人被机械化的体系肢解成碎片的危险。本雅明(1999:265)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光韵”定义为“一切距离外的独一无二显现——无论它有多近”。 作为“独一无二显现”,艺术“光韵”具有本真价值和膜拜价值,呈现为有一定距离的、安详的审美景观。如果说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消弭了艺术“光韵”,而电影的“震惊”则充满救赎的力量,那么,凯瑟则在印第安人的艺术中找回了缺失已久的“光韵”。在她的笔下,印第安人将澎湃的艺术激情融入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对被文化工业祛魅的艺术进行复魅,使艺术作品散发出独特的“光韵”。以印第安人的教堂为例,它虽外观简陋, 但内部装饰充满着色彩艳丽、质地特殊的宗教圣物。小小的祭坛供奉着印第安匠人手工制作的各种圣像,这些木雕圣像并不是机械大生产流水线上丧失个性的粗制滥造品,而是具有本雅明式的“此刻此在性”和“独特性”的手工艺术品。它们“着色鲜艳,虽因年代久远而褪色,但还穿着衣服,像玩偶似的。与俄亥俄州传教教堂里那些工厂生产的石膏圣像相比,这些木圣像更符合神父的脾胃,……都是那么朴实无华”(Cather,1931:26)。这些承载着文化价值和个人情感的艺术品一方面说明印第安人有着虔诚和素朴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表明思想尚未被现代文明整合的族群持有超越世俗的艺术观。
与印第安人的艺术观相比,凯瑟所处时代的艺术创作受到市场经济这只无形大手的操控,现代艺术缺少个性和灵魂,呈现出一片扁平、趋同和碎片化的迹象。凯瑟曾言:“在西部目前流行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必须和别人相同,好像我们都是同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我们穿同款衣服,开同样品牌的车子,住在同一个街区的同样风格的房子。这些都太让人窒息。”(Bohlke,1986:46)凯瑟的言辞,以点带面,以区域现象辐射国家状况,不仅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个美国社会的趋同现象,甚至还前瞻性地预见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这种趋同化的本土现象向全世界范围蔓延的态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众化倾向暗含着磨平个性、抹除差异的消极力量,助长现代人耽于平庸和狭隘的生活气焰。凯瑟对机械大生产裹挟下的趋同社会深感痛心,令她更为痛心的是现代艺术被强制地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体系而失去自律性。在她看来,《大主教之死》中印第安人的艺术才是人类艺术的本质,更是现代人对抗异化的生存体验、褪去机械枷锁的力量之源。因此,凯瑟从遥远的印第安艺术中重觅一种特有的“光韵”,以其庄重、圣洁、光亮和独特的气蕴,使得现代艺术相形见绌,进而弥补了现代艺术被粗糙廉价的机械复制品所过滤的诗意和情感。
印第安人的艺术“光韵”不仅在宗教器物上熠熠生辉,还汇聚在日常生活的物品之上。拉都主教在杰西教父家里看到一只在部落里代代相传的木鹦鹉。“那是用一块木料雕制而成的鹦鹉,大小和真鸟完全一样……这东西非常轻,表面上有着古木那种洁白的天鹅绒似的光泽。虽然几乎没有经过雕刻, 而仅仅是磨光成形,却活脱的像真鸟一样,可以说是鹦鹉的一只木标本了。”(Cather,1931:86)这只木鹦鹉在印第安部落中世代受人膜拜,体现出印第安人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这种观念与现代人物化的审美体验形成比对,两者之间的反差不仅悬置甚至否定了现代人行合趋同的艺术观,还激起现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对艺术“光韵”的再记忆,从而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中无功利地鉴赏艺术的显性形式。小说中,凯瑟没有直接揭露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彻底向异化臣服的现象,而是采取悬置的手法,使现代性之隐忧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诗意化的叙事以及它所表征的印第安艺术的“光韵”。对她而言,艺术“光韵”犹如耀眼夺目的阳光,穿透一切,照亮万物,能使现代人忘却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挣脱物质欲望的枷锁,创造出充满自由的审美情景,从而解决现实生活无法减缓人类精神疾苦的问题。
在《大主教之死》中,凯瑟通过虚拟的艺术世界,塑造了一个充盈着印第安艺术“光韵”的审美场,向现代人呈现了一个机械时代无法复制的艺术殿堂。她对印第安艺术“光韵”的描摹,把现代人带回素朴的生活场景,使人们反观物质富庶的现代生活之下隐匿的精神贫困与心理惰性,呼吁人们用艺术来舒展情感和获得心灵的自由,进而将艺术审美转化为协助人类摆脱刻板生活桎梏的力量。因此,恢复艺术“光韵”的审美救赎观告诉我们:知识、进步和理性等启蒙理念并不能完全祛除尘世的阴暗,而艺术“光韵”具有驱逐生活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避免机械复制时代里艺术沦为商业附属品的命运,还能助推着人类在幽暗的现代文明中觅得一块光明的精神净土。
3 张扬“新感性”的审美救赎观
现代文明是理性强制管束感性而催生的畸形文明,而现代人的历史是人存在于其文明中充满张力的历史。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以效率最大化和计算精密化为最高原则,忽略考虑人性中的感性因素。原本为人所用的理性日趋工具化,演变成令人窒息的异己力量,剥夺人们表达感性情愫的权利,使得人成为理性与感性相互割裂、角色自我与真实自我相互脱离的“单面人”,饱受个性扭曲的痛楚。要修复扭曲的个性,大多数西马批评家认为,唯有艺术,能胜此责。马尔库赛(2001:181)声称,“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这种文化;艺术,作为现存现实的异在,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艺术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这种对立的和谐化。”马氏赋予艺术调和感性与理性相互对立、协调异己现实与理想图式之间差距的功能,希冀通过艺术作品表达的“新感性”,刷新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认知意识,促使人们排遣被日益工具化的理性所钳制的感性。个体在这种释放真实情感的过程中,关照自身的本质自由,体味一种由于自我意识得以确证而产生的愉悦,使得爱欲备受压抑的现代人在此岸找到心灵的栖居地。类似地,在《大主教之死》中,通过前景化印第安人的狂欢化舞蹈和关爱他人的伦理,凯瑟赞扬印第安人的“新感性”特质,鼓励现代人效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爱欲的生存理念,恢复人的丰富性。
首先,印第安人狂欢化的宗教舞蹈既是他们表达爱欲的载体,也是管窥这些未沐浴启蒙之光的人们具有“新感性”特质的窗口。在印第安人眼中,每一个节日都是放松身心、表达情感的世俗节日,也是“宗教激情的伟大复苏”之时(Cather,1931:119)。每逢大小节气,印第安人身着盛装,载歌载舞,僵硬的身体顿时变得生龙活虎,展现出一幅狂欢化的图景。集体性的狂欢活动是对理性长期压抑感性的反拨。列斐伏尔提出,狂欢是“对被现代性压迫得越来越深重的日常生活的解脱,狂欢和节庆突破常规,实现感性、审美和自由的存在,使人们体味非理性的文明和反抗工具理性”(Lefebvre, 1991:47)。小说中,印第安人狂欢化的宗教舞蹈完美地结合人的理性和感性,使人成为符合美的规律的人,这一点与“新感性”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的诞生”遥相呼应(马尔库赛,2001:131)。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妇孺儿童,印第安人皆是“新型的人”的典范。拉都主教亲眼看见两个四五岁的印第安小男孩跳舞,“他们全神贯注地舞蹈,面容严肃,巧克力色的眼睛半闭着”(Cather,1931:233)。两人跳舞的动作,娴熟流畅,姿态柔美,使人陶醉其中,达到忘乎自我的境界。“他们那两双不比三角叶杨树更大的、穿着鹿皮鞋的小脚,不需要任何口令便能附和着不规则的、古怪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Cather,1931:233)。他们的舞蹈把被放逐在理性之外的感性情愫和个体活力融为一体,丰富的肢体语言突破了身体的疆界,优美的舞姿成为他们传递美感、播撒爱意的方式。他们将这种爱欲散播到对族人、部落、宗教和自然的爱护,以游戏狂欢的姿态向现代人表明:感性领地是一片让人身心愉悦的场域,是修复人性裂痕的黏合剂。
凯瑟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舞蹈的描写,表达的不是她对孕育印第安文明的地域文化的盲目崇拜,而是呼吁现代人以本土为根基,从地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对抗现代性招致的一元化危机。作为美洲大陆的最忠实、最古老的居民,印第安人用他们的智慧为多元化的美洲文明增色不少,他们懂得尊崇自然,顺势而为,善于表露感性。这些本能的天性少见于现代人之身,而他们所剩之物是挥之不尽的人性淡漠、归属感丧失和情感的机械化。凯瑟一针见血地指出机器的铁齿利爪抓破甚至蚕食现代人的生活土壤,对美国人沦为机械奴隶的现象痛下针砭,疾言厉色地讲道:“我们用机器听音乐,我们依靠机器旅行,美国人已经完全被机器淹没。有时候我甚至在思考,他们是不是借助机器才能哭和笑”(Randall III, 1973:156-157)。现代美国人和整个现代文明被机器合围,情感表达被机械化,人的感性之维遭受重创。对此,凯瑟既给予批判,又表示担忧,并发问:现代人应该如何修复感性之维的裂痕?作家通过精彩的地域创作,让世人看到工具理性霸权和独尊之外存在着感性和非理性的疆域,并以此敦促现代人像印第安人一样张扬“新感性”,回归淹没于理性之中的感性,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凯瑟的救赎理念与阿诺德·豪赛尔(1992:55)对现代主义美学的评价一脉相承:现代主义美学“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中解脱出来的种种要求”。在此,“种种要求”便是重建价值理性、追捧感性生命。因此,在小说中,凯瑟对印第安人的“新感性”特质的描摹是她探索对现代人进行精神救赎的另一种艺术想象。这种艺术想象已经超越某一具体地域的限制,上升为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性,使得小说文本具有地域文学的“普世价值”(Wyatt, 1990:xviii)。在现代性乃至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些“普世价值”正是照亮人们固守精神世界、走向感性与理性和谐共存之路的灯塔。
其次,印第安人的“新感性”不只是在狂欢化的舞蹈中有迹可循,还在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中得以展示,体现为关爱伦理向日常生活普及的现象。关爱是怜爱和感动的情愫使然,是一种人的爱欲的体现,它使人克服因自恋而陷入孤独的倾向,培育人们互爱的美德。小说中,出于怜悯和关爱,拉都主教毫不犹豫地救助玛格达莱娜,使她摆脱丈夫的蹂躏。玛格达莱娜从拉都主教和其助手的日常行为中,看到他们灵魂之中的善良和慈悲,因而,她不顾生命危险,在他们遇到困难之时,协助他们虎口脱困。同时,在拉都主教的协助下,玛格达莱娜在修女院当厨师和管家,重获新生,脸上露出安详而美丽的笑容。“似乎在跨过苦难的青春之后,她在天主的家庭里,再次迎来绽放。”(Cather,1931:79)拉都主教和玛格达莱娜互帮互助的行为是人处于本真状态下的爱欲使然。人只有回归本真状态,才会不计利益得失,人的感性世界才能迸发出久违的爱欲,心灵的激流才能冲破物质枷锁和逾越派别嫌隙,进而使人的存在符合美的规律。因此,在凯瑟笔下,印第安人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爱欲,他们的行为所诠释的“新感性”具有振奋萎靡精神的救赎功效。
印第安人的“新感性”特质承载着凯瑟向往诗意生活、唾弃物化情感和修复人性异化的救赎情结,也倾注了她对人的爱欲的肯定。印第安人的爱欲,对于被启蒙思想洗脑的大多数现代人而言,是原始的、未开化的,甚至是野蛮的。然而,凯瑟没有附和,却批驳现代人的感性被机械化、被物化的现象。她深知无法逃脱资本主义社会日趋物化的客观事实,因而,她选择回归和坚守自己的主观精神阵营,并与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艺术创作的方式缅怀印第安文明以及孕育它的地域文化。她通过新与旧、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比对,反观和确诊现代性的得失,并提供救赎现代人和解决文明病症的良方。正如阿多诺所指,艺术,抑或文学艺术,只有站在社会的对立面,通过获得自身的社会性偏离,方可表达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Adorno, 1997: 226)。显而易见,以《大主教之死》为代表的地域书写在背离、批判甚至否定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还以“新感性”破旧立新的潜能垂范,以期解救社会“铁笼”中的“单面人”和恢复他们的完整性,这一点无疑是凯瑟的审美救赎思想的人文意义所在。
4结语
凯瑟的地域创作常因采用写实的叙事手法而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品,也因弘扬乡土伦理和捍卫地域文化而被排斥在主张反叛、讲究革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之外。但《大主教之死》中的审美救赎思想让读者看到凯瑟的地域书写摆脱了“怀旧”“逃避”和“哀挽”等贬义之名,以关注现代性出路的姿态,在现代性危机的浪潮中探求缓解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挽救现代文明的方案。凯瑟以超人的姿态捍卫人的精神生活,并在《大主教之死》中勾勒出印第安人解放自然的审美意境,颂扬他们焕发“光韵”的艺术和“新感性”特质,重构了被现代文明压抑甚至剥夺的感性世界。这些思想承载的审美救赎观,正好与黑格尔倡导艺术的解放力量和韦伯坚持艺术的“世俗救赎”功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艺术带来的审美体验不仅能修葺被工业社会挤破的感性碎片,平衡理性与感性的天平,还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均衡发展,从而纠正启蒙现代性一味追求理性而招致的文明“综合征”。从这一意义上讲,凯瑟的地域写作从19世纪末期美国乡土小说专注于表达传统性、地方性和本土性的创作范式中脱颖而出,上升为兼具现代性、国家性和全球性的社会政治批判文本。正如评论家雷诺兹所言,凯瑟是一位“积极介入政治的作家,她的作品与自身所处时代的知识、政治和社会的各种辩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ynolds, 1996: v)。直至今日,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同一性思维逻辑向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之下,凯瑟在《大主教之死》中传达的审美救赎思想无疑是给精神物化和缺乏归宿感的人们指引了一条通往精神世界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Acocella, Joan.2000.WillaCatherandHerCritic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dorno, Theodore W. 1997.AestheticTheory[M].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Ltd.
Bloom, Harold. 1985.ModernCriticalViews:WillaCather[G].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Bohlke, L. Brent.1986.WillaCatherinPerson:Interviews,Speeches,andLetters[G].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Callicot, J. Baird.1998. InDefenseoftheLandEthic[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ather, Willa.1931.DeathComesfortheArchbishop, 2ndedition [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Dorman, Robert L. 1993.TheRevoltofProvinces:TheRegionalistMovementinAmerica, 1920-1945 [M].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Eysteinsson, Astradur.1990.TheConceptofModernism[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isher-Worth, Ann W.1990. Dispossession and Redemption in the Novels of Cather [G]. Susan J. Rosowski.CatherStudies,Vol. 1.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36-54.
Lefebvre, Henri.1991.CritiqueofEverydayLife,Volume.I[M] Trans. Michel Trebitsh. London: Verso.
Randall III, John H.1973.TheLandscapeandtheLookingClass:WillaCather’sSearchforValue[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Inc.
Reynolds, Guy.1996.WillaCatherinContext[M].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Spindler, Michael. 1983.AmericanLiteratureandSocialChange[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Weber, Max.1946.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M]. Ed. and Trans.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ress, James Leslies.1987.WillaCather:ALiteraryLife[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Wyatt, David. 1990.TheFallintoEden:LandscapeandImaginationinCaliforn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瓦尔特·本雅明.1999. 经验与贫乏[M].王炳军,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阿诺德·豪赛尔.1992.艺术史的哲学[M].陈超南,刘天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伊曼努尔·康德.1964.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赫伯特·马尔库赛.2001.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马尔库赛.2008.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虞建华.2004.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周宪.2005.审美现代性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校:肖谊
The Power of Redemption: Aesthetic Redemption inDeathComesfortheArchbishop
ZHANGJianran
Abstract:In her regional novel 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Willa Cather, by means of representing Native Indians’ concept of liberating nature and foregrounding their temperament of “new sensibility” and the “aura” of Indian art, showcases the redemptive power that can cure the malaises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save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thus thoroughly gives 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function of aesthetic redemption shouldered by literary art. Aesthetic redemption, as Cather’s strategy to dismantle the “iron cag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ims to redress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engendered by the radical development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to construct an ideal living mode in which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sensibility and sense can exist. These artistic conceptions not only offset and counteract the values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but also serve as the best notes to Cather’s pursuit for the plan to save modernity in the imaginary world. And they hereby attest that her regional writing, with a writing stance that transcends such binaries as the traditional/ the modern, the regional/the national, and the local/the global, engages with social realities and makes introspections on the outlet for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Willa Cather; Death Comes for Archbishop; aesthetic redemption
作者简介:张健然,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研究”( 10YJA75219)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12-25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2-0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