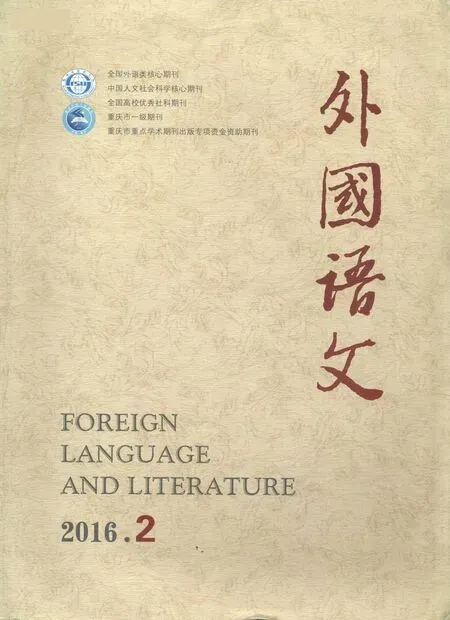中英比较诗学的新境界:论叶公超的中英诗学对话与创新
2016-03-17陶家俊
陶家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中英比较诗学的新境界:论叶公超的中英诗学对话与创新
陶家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本文运用症候式阅读方法实证研究20世纪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先行者叶公超探索的中英比较诗学对话与创新的新境界。叶公超青少年时期浸淫于英美大学人文教育,与罗伯特·弗罗斯特、T.S.艾略特、I.A.瑞查兹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批评深度结缘。1926年至1940年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为舞台,以《新月》《学文》等报刊为喉舌,致力于英国文学教学实践和现代批评实践。其现代批评思想比较阐发并打通艾略特和瑞查兹的诗学与中国古典诗论,建构了以文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为要素的中国新诗学。
关键词:叶公超;现代批评;中英诗学对话
0与英美现代主义和现代批评结缘
叶公超(1904—1981)1912年受叔父叶恭绰资助,先后到英国和美国读小学。在天津南开学校完成三年初中后,1920年他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尔班纳高级中学,之后进入缅因州的贝茨大学,1922年考入著名的艾姆赫斯特学院。在艾姆赫斯特学院求学的三年中,叶公超有幸成为驻校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入室弟子。弗罗斯特不仅用自由无拘束的人文主义教育方式熏陶培育叶公超,而且用心雕琢他的文才诗艺,教他创作诗歌的技法。在艾姆赫斯特学院的最后一年,叶公超结集出版了自己的英文作品集《诗歌》。他在英文诗创作上的天赋和发展潜力给弗罗斯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20世纪40年代末叶公超的学生林振述(笔名艾山)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老诗人弗罗斯特时,他还念念不忘自己20多年前亲手调教过的中国学生叶公超,“说他很有才气,如果继续把诗写下去,加上中国固有的丰富诗歌传统,则在太平洋的彼岸,不让泰戈尔……专美于前”(艾山,1985:26)。
1925年秋,叶公超进入英国剑桥大学麦格德伦学院攻读现代批评硕士学位。他成了I.A.瑞查兹奠定的现代批评的受惠者,与F.R.利维斯、威廉·燕卜荪这些现代批评剑桥学派的才子们成为同门师兄弟。20世纪20年代英国乃至英美的文化思想地图上艾略特和瑞查兹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眼中是最雄伟的地标(Wright,1979:37-65)。尤其艾略特是充满了革命精神的保守知识分子原型:他在创作现代主义不朽诗篇的同时,开创了现代主义诗学;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批判地拒斥现代性。在剑桥的一年中,叶公超与艾略特结下了师友之情,直接受到了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影响,对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歌巨作《荒原》及其他诗篇获得了比一般读者和寻常批评家更透彻、亲切、直观的感悟。叶公超给艾略特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中国诗人卢飞白在伦敦与艾略特见面时,他首先问到的是叶公超。
与同样受剑桥启迪的徐志摩相比,叶公超没有与众多英美现代主义人物建立并长时间地维系私人情谊。但是叶公超在更深厚的背景中、更亲密的人文主义传统中、更长的时间内承受英美现代人文教育的熏陶。他在英美人文教育浓厚的大学中,从深厚的人文思想传统出发来感知现代主义。其次,他机缘巧合,同时得到英美两位杰出的诗人之教诲。再者,他同时承受了剑桥学派的两个导师——瑞查兹和艾略特——的滋养,无论是在跨学科视域(文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的结合)、批评方法论还是思想观念上,都能将不同批评精髓融合并创新。
1912年至1926年的14年,从文质少年到弱冠青年,叶公超超越了常人的成长轨迹,结下了中英跨文化交流的奇缘,得到了诗坛高人的口传心授,深入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批评的腹心地带,打通了现代批评剑桥学派的正宗功法,对英美乃至西方文明深厚的人文传统精神心领神会。所有这些为他投身于中国现代批评话语的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旦进入中国现代大学场及与之调剂互补的现代文学场,一旦将西学新知与中国的诗学传统乃至时代精神嫁接融合,他将以超越的姿态建立现代批评的新论。
1叶公超的教学实践
1926年秋,叶公超开始在北京大学外文系任讲师。1927年春,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聘请他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9年夏,他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北大的半年他主要讲授“英文作文”“英国短篇小说”。他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授英文课。此外他为《北京英文日报》(PekingDailyNews)和《远东英文时报》(FarEasternTimes)撰写评论和社论。
在上海的两年半内他最大的收获是成为“新月派”成员,参与《新月》的创刊、编辑、撰稿等事务。在这段时间,北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相当部分人迁徙到上海。得力于叶公超在暨南大学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梁实秋、林语堂、饶孟侃、余上沅等相继在暨南大学外文系任教。叶公超主持的暨南大学外文系为这些学者提供了栖息地,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之忧,为他们推动“新月”事业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经济保障。
从1929年到1940年(除去1935年出国游学休假)叶公超相继受聘于清华外文系、北大外文系、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29年秋至1934年夏,他在清华外文系讲授的课程包括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英文”“英国散文”“现代英美诗”“文学批评”和“翻译”。他在北大外文系兼授的课程有“戏剧”“翻译”“英诗”“文学批评”和“18世纪文学”。大学一年级“英文”使用的教材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到了1933年,一年级“英文”使用的教材改用合选的英美名作家名篇,如爱默生的《自助》、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中的选段。“戏剧”使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英国戏剧杰作选》。而“文学批评”则是融合最新知识后的系统启发传授。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中回忆到:
我上的课是文艺理论。他在这方面信息灵通,总能买到最新的好书,买多了没处放就处理一批,新的源源不断而来。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叶崇德,1993:69-70)
他与吴宓合开“翻译”课。吴宓上英译汉,叶公超上汉译英。他选用的翻译材料主要是唐宋诗词和元曲。在教法上“除了承受牛津、剑桥的传统,对诗、对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着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是熏陶式、启发式的方法”(艾山,1985:26)。按照他在北大教过的学生林振述的解释,这是融合了英美人文主义传统与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和自由切磋法。更有意义的是,他在课余给予学生指导。例如他指导赵萝蕤翻译T.S.艾略特的《荒原》并为她的翻译写序。赵萝蕤比较外籍教师温德与叶公超的指导后,发现了叶公超令人叹为观止的理论功底和学问修养。
温德教授只是把文学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唐宋诗比较。他一针见血地评论艾略特的影响说:“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叶崇德,1993:70)
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启发熏陶融合了他对本土文化认同和价值阐发的反省。他谆谆告诫北大学生常风说:
咱们学外语的人总须另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只教外文、讲外国文学,不过是做介绍、传播外国文化的工作,这固然重要,可是应该利用从外国学来的知识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多钻研,认真做点一砖一瓦的工作,为建筑一座宏伟的殿堂做基础。(傅国涌,2004:71)
叶公超在这5年中亲手调教了一群才华出众、资质一流的未来学术和文学栋梁之材。这群叶门弟子在清华有钱钟书、王锡蓂、季羡林、杨联升、王辛笛、赵萝蕤、杨联升、张骏祥、王岷源、孙晋之、傅幼侠、赵萝蕤等,在北大有卞之琳、陈世骧、王学曾、常风、林振述等。
在长沙临时大学,他讲授过二年级“英文”“文学批评”两门课程。在西南联大,他讲授的课程包括“文学批评”“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及大一“英文”“英汉对译”“印欧语系语文学概要”“西方文学名著选读”和“英诗选读”。大一“英文”使用的教材是清华编的《英文读本》,所选文章多以中国为主题,内容包括毛姆的《苦力》、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在与吴宓等合上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中,他负责讲解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一时期他教过的得意门生包括穆旦、李赋宁、王佐良、许渊冲、金丽珠、杨静如、杜运燮、赵瑞蕻、吴其昱、李博高、吴景荣。尽管是在战乱流离的状况下,但是他在治学育人上仍用功勤勉。李赋宁回忆这一时期的叶师时这样感叹:“仍必须读书到凌晨两、三点钟。由于先生不断接触新思想、新概念,因此先生的讲课总有新的内容,使学生努力跟上时代,了解时代的脉搏和动向。但是先生更为重视基本理论和历史事实,使学生做到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叶崇德,1993:67)
纵观这十多年间叶公超所教授的课程,“文学批评”是贯穿始终的课程。加上他教授的“现代英美诗”课程和他发表的批评理论文章,承受他教益的学生眼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批评诗学世界。卞之琳在回忆叶公超的教学时认为“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三十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慈晚期诗”(叶崇德,1993:20),他撰写的诗学文章《论新诗》“不仅是叶先生最杰出的遗著,而且应视为中国新诗史论的经典之作”(叶崇德,1993:22)。
2叶公超的现代批评实践
叶公超的现代批评实践首先在于他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后期新月派和后新月派重要的组织者之一,在《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三份月刊的创办和发行中发挥了骨干甚至核心作用。这确立了他现代批评实践者的角色——占据公共空间中以文化象征革命为自觉使命的文学刊物的组织者、赞助者和评论家。这个角色既不同于普通的为赚稿费的职业撰稿人或作家,也还没有发展成熟到公共知识分子。在占据大学讲台这个现代知识和思想传播舞台的同时,他与同道们占领了文化媒介栖息的文学场的制高点。
1926年6月21日刚从巴黎回北京的叶公超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戏刊》上发表了评论爱尔兰戏剧家约翰·米林顿·辛吉的文章《辛额》。与他为《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写评论相比,这篇文章标志着他直接融入欧美同学圈子,成为徐志摩、胡适等主导的“新月社”“中国戏剧社”的新成员。
1928年3月,叶公超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了英国小说批评文章《写实小说的命运》。这年夏天他选编的《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一套四辑)由新月出版社出版。该选集前两辑收入杂感50余篇,后两辑选编散文40余篇。此外新月出版社还出版了他与闻一多合编的《近代英美诗选》(两册)。从《新月》1928年10月第1卷第8期开始,他开辟了“海外出版界”专栏,跟踪介绍英美文学创作、批评和出版界的现状。栏目撰稿人为叶公超本人和梁遇春。他为这个栏目一共撰写了约14篇评论梁遇春共写了18篇书评书话。为该栏目撰稿的还有他在清华的学生钱钟书。
1929年4月至7月,叶公超与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徐志摩共同主编第2卷第2期至第5期。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去世后,他单独主编了1932年9、10月份《新月》第4卷第2期、第3期,又与胡适、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邵洵美、罗隆基合作主编了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最后的三期。最后三期实由叶公超负责,他甚至用白宁、白苧、棠臣等笔名写各类文章来应付作者欠稿。
叶公超在后期《新月》中提携北大、清华的青年学子,使他们在文学批评上得到切实锻炼,迅速成长为20世纪30年代青年一代中崭露头角的新秀。他不仅延续了《新月》的生命,而且培养新一代的批评家、翻译者和作家。这些新秀包括北大的卞之琳、李广田,清华外文系的曹葆华、钱钟书、常风、石璞,中文系的余冠英,历史系的孙毓棠、哲学系的李克植,历史研究所的张德昌,外文研究所的杨绛。
徐志摩、叶公超等信奉的新月精神实为自由主义精神,是以自由-人文主义精神为底色的剑桥学派精神,借《新月》的喉舌,在高度文学化和思想化的刊物开辟的文学场中的嬗变和中国本土化。因此在舶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熔铸,它成为徐志摩所认定的维护“健康”和“尊严”、自由和人性的号角。这号角的变奏就是《学文》和《文学杂志》。
1934年5月1日,由叶公超任主编、余上沅任发行人的《学文》开始发行。刊名出自《论语》“学而篇第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2000:3)1934年8月出了第4期,叶公超在清华任教满五年后赴欧洲休假游学,《学文》停刊。《学文》的封面是由林徽因设计的汉砖图案,古朴典雅。四期刊物上刊登的代表性文章颇能证明其高远的文学和批评指向。第1期有林徽因的意识流小说《九十九度中》。第2期有杨联升经叶公超指导修改的随笔小品文《断思——躺在床上》、叶公超的批评文章《从印象到评价》。第3期有钱钟书最早剖露文艺圆通思想的《论不隔》。除了刊载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外,《学文》还译介英美文学批评名篇。第1期刊登了卞之琳在叶公超指导下翻译的T.S.艾略特的现代批评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第3期刊登了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诗的法典》。第4期刊登了赵萝蕤翻译的豪斯曼(A. E. Housman)的《诗的名与质》。叶公超在《学文》上仅发表了一篇文章,却不遗余力地培养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清华学生有季羡林、李健吾、钱钟书、杨联升,北大学生有包乾元、何其芳、徐芳、闻家驷、卞之琳、赵萝蕤等。
叶公超也参与了1937年1月由朱光潜任主编的《文学杂志》的编委工作。其他编委包括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废名、李健吾和凌叔华。不久北平沦入日寇之手,叶公超等纷纷南下,《文学杂志》出了四期后被迫停刊。叶公超在《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新诗诗论的经典之作《论新诗》,在第2期上发表了书评《牛津现代诗选》。
1926年至1940年的14年,叶公超发表了大量文章。从文章类别看,可分为英国现代主义批评、英语研究、英美文坛研究、散文随笔、中英文论比较研究、英美现代批评研究、翻译研究、中国本土批评理论建构、中国新文学批评乃至现代大学教育研究等主题。这些文章主要刊登在《晨报副镌·剧刊》《新月》北京英文刊物《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清华周刊》《清华学报》《学文》《自由评论》《独立评论》、天津《益世报》增刊、北平《世界日报》副刊、《文学杂志》《北平晨报·文艺》《今日评论》、重庆《中央日报·平明》等16家刊物和报纸上。除英文刊物《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和两份清华刊物外,剩下的13家报纸和刊物的主编分别是徐志摩(《晨报副镌·剧刊》)、沈从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叶公超(《学文》)、梁实秋(《自由评论》、天津《益世报》增刊、北平《世界日报》副刊、《北平晨报·文艺》、重庆《中央日报·平明》)、胡适(《独立评论》)、朱光潜(《文学杂志》)、潘光旦(《今日评论》)。这表明新月派人物掌控了宽广的传媒阵地。或者说这些刊物都是叶公超圈子中的同道和朋友任主编。从影响的角度看,叶公超借助徐志摩、沈从文、胡适、梁实秋、朱光潜、潘光旦以及自己掌握的传媒平台,使自己的现代批评思想从北大和清华,由《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向更广阔范围内的读者大众传播,由此产生广泛的影响。
3叶公超对艾略特和瑞查兹诗学的阐发
叶公超的《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1934年4月第9卷第2期)和《再论爱略特的诗》(《北平晨报·文艺》1937年4月5日第13期)*叶公超为赵萝蕤译《荒原》所作的序与《再论爱略特的诗》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序言是为上海新诗社1937年年初出版的《荒原》而作。同样内容的文章则刊登在同年4月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上。这两篇文章重在从宏观和比较视角提炼艾略特的诗学思想,同时交互阐发艾略特的诗论与中国传统诗论。艾略特的诗学代表作是他的《自选文集》(1932年)、《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但丁》《玄学派诗人》《〈庞德诗选〉序》《菲力普·马生格》《奇异神明的追求》是其中的精华。艾略特的诗学精髓包括:
(1)提出“客观关联物”理论,通过用典故、史事、旧句、动作和情节技巧等手法,将古今知觉、情绪、情感融在一起,使古往今来的欧洲文学同时并存,在异质性中营造共时效果,将抽象观念化成可感觉、观察的意象意境。
(2)提出异类异象对较论,其心理效果类似于瑞查兹论述的文艺通感。借鉴英国17世纪玄学派和法国19世纪象征派,将两种极端相反的事物或印象并置,打破读者的习惯感觉,产生惊奇反应,从而激发新的联想、感觉和认识。
(3)无论是古今并置、不同格式的综合、各种感觉的杂呈还是不同语言、文学、政治、宗教、神话等的杂糅,其目的是为了表现整个生活、整个时代乃至欧洲文明的精神境界。
(4)他的精神指向是欧洲文明的未来。不是社会变革乃至革命,而是心灵深处虔诚的信仰才能洗涤灵魂,根治人的贪欲、利欲和仇恨,恢复善与真的崇高的道德律令,让欧洲现代文明起死回生。艾略特的诗和诗学是一个完整的同一体。它们共同形成了英美乃至西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的传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价值。20年代末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奥登诗派”就是新传统的受惠者。但是新一代的诗人基本上学习了艾略特的诗歌技法,而偏离甚至叛离了他的思想主张,日益走上激烈的变革社会的路子。
为了化解艾略特诗学与中国文化的隔膜,叶公超用对较互照的方法来阐发其诗学与中国古典诗论相通之处。他认为艾略特的诗学分别与中国古典诗论的“夺胎换骨”论和“文以载道”论相通。北宋僧人惠洪在笔记体诗话《冷斋夜话》卷一至卷五中多处引苏东坡、黄庭坚等宋代元祐年间的诗词家。他品鉴黄庭坚的诗论“夺胎换骨”法:“然不宜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惠洪,2012:14)这正好对应于艾略特的讲究用典故、旧句和史事,其目的是延续激活传统,弥补个人才能之不足,用旧材料熔铸新作。艾略特在《菲力普·马生格》中划分出“夺胎换骨”法的三种境界:低级的诗人模仿;一般的诗人剽窃;高明的诗人借用旧材料创造上品,“把他们所窃取的溶化于一种单独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叶公超,1998:125-126)。宋儒周敦颐在韩愈的“文以明道”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以载道”*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的原文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这里的道就是合乎四季更迭、仁义敬孝的天道和人道。在艾略特的诗学中就是“他在《奇异神明的追求》里所提出的‘tradition’和‘orthodoxy’两种观念”(叶公超,1998:126)。叶公超不仅吃透了艾略特的诗艺和诗学,而且在古今、中英诗学间打通。这是中西学问融通到极高明的境界,超越了极端排他的文化本位立场。
叶公超的《曹葆华译〈科学与诗〉序》尽管短小,实际上却是一篇视野开阔的瑞查兹研究专论。他不仅分析《科学与诗》,而且评论瑞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和《意义的意义》。与艾略特一样,瑞查兹提出了诗歌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据此他提出文学的价值论和传达论。文学的价值在于协调人的各种反应和情感,将心灵调和到平衡和谐的状态。这些理论观点可追溯到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在《文学的传记》中提出的批评观点。但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学术尚没有进步到产生现代心理学、生物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因此柯勒律治对文学的价值和传达这些问题探讨是“八分玄学和二分呓语”“直觉找不着明晰的文字”(叶公超,1998:147)。因此,文学理论的创新突破与学术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因果和影响关系。现代批评之产生自有其必然的学术土壤和历史条件,建立在现代新生的不同学科的基础之上。叶公超精准地指出了瑞查兹开创的现代批评的跨学科本质。这足以证明他作为中国现代批评先行者的洞见和修为。遗憾的是,能打通艾略特诗学与中国古典诗论的叶公超没有深入挖掘瑞查兹的价值论和传达论与中国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关系。
4叶公超的中国新诗学观
从1933年至1939年的七年中,叶公超发表了《文学的雅俗观》(1933)、《从印象到评价》(1934)、《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1934)、《谈读者的反应》(1936)、《论新诗》(1937)、《文艺与经验》(1939)六篇文章。从症候式阅读的角度来解读这七年中叶公超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嬗变,我们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他最早在1933年的《文学的雅俗观》中从观念辨析层面用哲学和语文学相结合的路数,围绕雅俗观来打通中西古典文论;其二,从叶公超诗学探究和建构主题发展深化的结构性模式来看,其诗学建构呈交替向前并深入的特点,即:诗学主题之间没有明显的断裂而是在交叉重叠的同时引向新的主题。例如,《从印象到评价》在继续关注中西文论打通的同时主要引入读者反应主题,而读者反应主题又贯穿了《从印象到评价》《谈读者的反应》和《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在《印象与批评》中更埋下了他诗学建构更新的主题——中国新文学和现代批评的文学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我们发现在1934年6月《学文》第2期上发表的《从印象到评价》中三个主题——中西文论比较与打通、读者反应理论、具有鲜明文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中国诗学——的交叉重叠。可以断言,1934年夏,叶公超的诗学建构基本上形成了内在的核心点。
叶公超的现代批评思想最闪光之处在于他在打通古今、沟通中英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具有鲜明文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中国新诗学。
他中国新诗学的成熟之作是《论新诗》和《文艺与经验》。他指出,中国新诗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旧诗与新诗之间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就是新诗人的出路、新诗的出路和新文学出路的问题;就是现代主义文学革命的前途和发展方向的问题;就是以新诗的发展为里程碑,以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为推手,以传达时代精神为己任的文学的民族主义指向。
新诗乃至新文学“把自己一个2000多年的文学传统看作一种背负,看作一副立意要解脱而事实上却似乎难于解脱的镣铐,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叶公超,1998:50)。他认为新诗人对旧诗和新诗应该兼收并蓄,而不应将旧诗视为镣铐。格律——无论是旧诗的格律还是新诗的格律——是诗的必需条件。“惟有在适合的格律里我们的情绪才能得到一种最有力量的传达形式;没有格律,我们的情绪只是散漫的、单调的、无组织的,所以格律根本不是束缚情绪的东西,而是根据诗人内在要求而形成的。”(叶公超,1998:51)但是他更辩证地指出,西方诗的格律外在于中国传统,中国传统格律的依据是古典文字,所以以白话文为媒介的新诗人真正的使命、最大的责任是开创中国新诗的格律的传统,也就是开创新诗的传统。
要在西方诗与中国传统诗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的诗的传统,新诗人应扩大意识的范围,融化传统文化和时代新知。以所有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为养料和原料,在综合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表现最具包容力的人类进步精神和理想。其次,新诗人应倾听时代的声音,表现时代的精神,使所有传统的文学与新时代的精神重新发酵融合。同时新诗人必须真切地聆听民族心灵的跳动。
假使文学里也要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诗人必须深刻感觉以往主要的潮流,必须明了他本国的心灵。如果他是有觉悟的人,他一定会感到这个心灵比他自己私人的更重要。它是会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就是一种发展。这种发展是精炼的、错综的。以往的伟大的作家的心灵都应当在新诗人的心灵中存留着、生活着。旧诗的情境、咏物寄托,甚至于唱和赠答,都可以变态地重现于新诗里。(叶公超,1998:63)
不难辨析,叶公超的新中国诗学渗透了艾略特的包容古今、包容传统的理念。
在《文艺与经验》中叶公超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这篇文章是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写的,因此无论是叶公超继续阐释的诗学观还是他所强调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回顾20多年的新文学历程,他发现其弊端或缺陷主要是表现题材的肤浅、脱离现实和文艺意识的狭隘。在表现题材上脱离了乡土中国尤其是传统社会分崩离析这一最迫切、逼人的现实。新小说充斥着个人的感伤和哀怨,套用恋爱—电影—失恋—革命这一时髦肤浅的公式。新诗表达的情调过于单调,多是偏向表达个人小悲哀的抒情诗。每一个时代有其独特的知觉和灵感,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文学尤其是伟大的作品自然地传达时代的知觉和灵感的声音,自然地流淌着时代的知觉和灵感。因此作家知觉的范围决定了他对生活和社会环境认识的程度,他灵感的深度决定了他对各种社会现象感悟的程度以及对其意义理解的程度。有了相当的知觉和灵感,能感悟生活和社会现象间深刻的关系,能深刻意识到时代的知觉和灵感。
叶公超的中国新诗学设定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国文学现代性。首先,中国文学现代性必然是文学的民族主义。这必然意味着中国新文学的道路、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必须坚持民族主义并追求民族更为光明的未来,也必然意味着中国现代批评在经历了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批评的相互碰撞和对话之后必须走向自我创新和发展之路。其次,中国文学现代性必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只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只有关切广阔的社会中波澜壮阔的事业和严肃的现实,新文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创造新的文学传统,才能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才能表现时代的问题并传达时代的声音。
中国文学现代性同时应具有文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性四个基本要素。当他的诗学探索最终设计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宏伟工程,当抗战的时代精神呼喊咆哮之际,他结束了在大学的教学实践和现代批评实践。1940年6月他离开西南联大,为自己14年来的探索画上了句号。
参考文献:
Baldick, Chris. 1987.TheSocialMissionofEnglishCriticism1848-1932[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liot, T. S. 1932.SelectedEssays1917-1932[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Kumar, Ashok. 2010. I. A.RichardsandNewCriticism[M]. New Delhi: Atlantic.
Richards, I. A. 1924.PrinciplesofLiteraryCriticism[M]. London: Routledge.
Shih, Shu-mei.2001.TheLureoftheModer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right, Iain. 1979. F. R. Leavis, the Scrutiny Movement and the Crisis[M]∥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 Jon Clark, Margot Heinemann etl. Ed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艾山.1985.文采风流、音容宛在:叶公超侧记[G]∥叶公超专辑资料(一).朱传誉主编.台北:台北天一出版社.
傅国涌.2004.叶公超传[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惠洪,费衮.2012.冷斋夜话·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孔子.2000.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
李欧梵.1981.西潮的彼岸[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李欧梵.1996.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M].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李欧梵.2005.未完成的现代性[G].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1991.清华大学史料选编[G].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学珍,郭建荣.2000.北京大学史料[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叶崇德.1993.回忆叶公超[M].上海:学林出版社.
叶公超.1998.叶公超批评文集[M].陈子善,编.珠海:珠海出版社.
责任编校:朱晓云
New Scape of Sino-English Comparative Poetics: On Ye Gongchao’s Exploration of the Dialogue and Renew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ics
TAOJiajun
Abstract: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studies new scape of the comparison, dialogue and renewal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ics explored by Ye Gongchao the pioneer of 20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y symptomatic reading. In his adolescent years and youth Ye Gongchao was merged in Anglo-American universities’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directly cultivated by such representatives of Anglo-American Modernism and modern criticism as robert Frost, T. S. Eliot and I. A. Richards. From 1926 to 1940, with universities such as 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as the stage and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such as The Crescent Moon and Xue Wen as the mouthpeice, he was bent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praxis of modern criticism. His thought of modern criticism comparatively interprets and harmonizes the poetics of T. S. Eliot and I. A. Richards and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constructs Chinese new poetics with literariness, nationality, temporality and sociality as the core elements.
Key words:Ye Gongchao; modern criticism; Sino-English poetic dialogue
作者简介:陶家俊,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后殖民研究、跨文化研究和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跨文化的文学场:20世纪中英现代主义的对话与认同”(11BWW009)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12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2-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