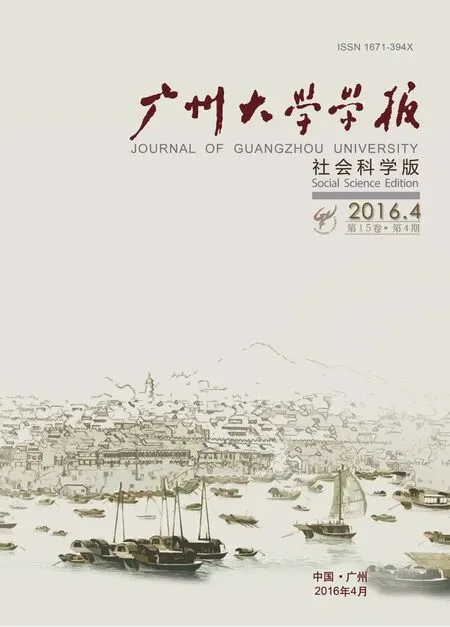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原则
2016-03-09钟明华邓欣欣
钟明华,邓欣欣,2
(1.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2.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原则
钟明华1,邓欣欣1,2
(1.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2.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摘 要:伴随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城市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地理标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盲目追求和对城市、城市空间认知的缺位,正在使城市空间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矛盾与冲突最集中的地方。空间与人的发展的失衡,空间的过度同质化,空间的“权力”特征和对自然空间的掠夺,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研究的突出问题。回归人的需要,尊重城市的本质,包容异质文化的多样性,回归城市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将成为我国城市空间正义追问中人们对空间发展的期待。
关键词:现代化进程;城市空间;空间危机;空间正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经济建设开启,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基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城市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前,城市正在成为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集中的地方,对于城市空间正义的追问日渐成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理论视角,空间正义如何实现成为人们期待解读当前社会关系的思考路径。
一、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危机
(一)空间与人的发展的失衡
我国空间发展和人的发展出现失衡,主要因为城市空间的稀缺性和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空间的稀缺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占地面积较广,城市发展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农业用地和农村空间为代价,空间的总量有限,城市空间更加有限。在大城市寸土寸金,土地的稀缺性增加了土地寻租的机会,成为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城乡关系的紧张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自空间的稀缺性。
第二,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城市大小的重要因素,很多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人口作为考察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截止2013年有大约13.6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而生活、工作在城市的农民工和农村户口人员大约有20%。
第三,城市人口素质亟待提高。在大量人口涌向城市的过程中,人口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人的城市化”主要是指进入到城市生活的人们和城市里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能保持一致或者能跟上城市文明发展的步伐,可以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和文明程度。由于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个体素质差异较大,并不是所有城市人口都能“城市化”,跟上城市文明发展的步伐。
(二)空间的过度同质化
城市的生命在于城市的个性,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连锁商业模式和品牌连锁机构已经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意义被过度同质化,不仅如此,很多极富特色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也在被逐渐弱化,忽视了不同城市空间发展的个性和特色。根据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扩张的理论分析,这是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扩张,占据空间、生产空间以减轻社会的内在矛盾,人为创造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以说,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同质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原因有二:其一,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对经济增长速度要求较高;其二,我国的城市发展之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我国长期处于农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进入城市化的时间较晚,对于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缺乏经验,进入城市化进程后,经济建设盲目地追究速度,忽视了城市的差异性建设,特别是城市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色等无形城市空间形态建设。
(三)空间的“权力”特征明显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1]我国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存在,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总体规划和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生产、资源的分配和产品的消费等社会行为几乎都来自指令性计划。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我们经济的迅速发展呈现出计划与实际脱节,产需分开,效率低下,动力不足等弊端,逐渐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但是计划体制的思想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进而影响城市空间的“设计”。我国的政治制度长期呈现出“行政化”“集权化”的“权力”特点,城市空间的权力过度化使空间变成某些人的“空间”,留下深刻的“政治”烙印过度的“权力”印记,会使城市空间失去城市的本来意义。
(四)对自然空间的掠夺
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中,人们似乎低估了自然的力量。山林、平原、湖泊、耕地、城市用地这些空间的自然形态被城市化膨胀的人口,硬化的土地和到处蔓延的大工业工厂慢慢吞噬,生态危机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在城市化的发展中,人口不断暴涨,增加了有限资源的负担,城市的扩张不断地侵蚀着土地资源,“据估计,2000年全国已有5 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在2001~2005年4年间,全国又净减少2 691万亩耕地,按劳均4亩耕地计算,相当于增加了67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0年又将有6 000万农民失业和失去土地。[2]城市空间不断对农村空间进行侵占,城市空间本身的拥挤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住房紧张,道路拥挤,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城市空间的发展。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它会对人类赖以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3]城市空间的发展如果是以生态环境的牺牲为代价,就必定要面对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的诘问
面对城市空间的危机,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空间?在借鉴和参考西方空间危机及其发展的基础上,我们试图回到城市空间,开启对城市空间正义的诘问。
(一)城市空间是谁的空间:人还是“物”化的人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物化”的意义在于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但是,“物化”也可能会使人异化,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物的关系。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对象化活动,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是资本不断增值的结果,资本的增值使人逐渐丧失了“主体性”,成为资本和商品的奴隶,商品交换本来应该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在资本和利益的驱动下,却颠倒成为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物对人的依赖性变成了人对物的依赖性。
城市空间是“属人”的空间,人作为手段和目的统一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出现的初衷是为了人们能更好的生活,对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的性追求应是城市空间存续的价值内涵。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在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随着对“物”的依赖,开始弱化或丧失。城市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机会,同时成为资本积累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目的性的实现离不开作为手段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手段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当手段是“物”时,它的价值在于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即是对人的有用性,一旦“物”成为人的目的性,城市空间就会变成对“物”的追求,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成赤裸裸的交易关系,人的手段价值会被扩大,甚至滥用,投射到城市空间上,就会倒置城市空间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二)城市空间的张力:同质还是多样
城市空间作为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整体反映,既有同质性又呈现出多样性。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由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层级组成,不同利益的差别使社会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社会需求,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收入水平、价值理念和组织方式;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城市空间有不同的城市个性,有不同的文化样态和价值理念;相同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城市空间也因历史、地域、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我国城市空间的现状正如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状况,因为不同物质利益群体的存在产生差异。马克思说:“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我国当前差异性社会的现状是:“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或趋于一致、而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则存在着各种差别、人民仍然分成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社会。”[6]因为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共同存在,在城市空间的发展上应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求同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共同目标一致,同样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应该机会均等,受到公平对待。承认差异,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长期会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发展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的产业结构之间还存在很多差异。应该对不同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业给予不同的差异政策。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包容差异、和谐共进,又要在统一的目标下完成空间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三)谁在影响城市空间:资本还是权力
城市空间中谁在影响或者主导着城市空间发展的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很长时间追求“价值”和“利润”的机器大工业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基本完成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机器工业大生产和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国家权力规定了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并且拥有暴力机构的制度框架,保证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时,有稳定的契约法则和法律保证,在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时,监管框架能够处理阶级冲突和调节不同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国家对于制度的制定和对暴力机构的拥有是权力的体现,从一开始,资本和权力就在城市空间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我国建国初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权力”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发展。比如我国的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区分了“非农业”和“农业”两类不同的户口之间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生活福利等社会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可以发现,当时户籍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和权力在城市空间分配中的象征,这种制度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空间的发展。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对“资本”的盲目崇拜,资本“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7]。物欲的膨胀和精神的匮乏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开始不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开始物化,资本和权力成为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城市空间的生态博弈:人与自然孰轻孰重
20世纪60年代之后,曾经一度,人们感受到城市空间的萎缩和倒退。随着城市经济的衰退、企业的破产、工人的失业、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开始对城市失去信心。例如战后的美国人口紧急下降,城市的郊区化发展,汽车工业的衰退,城市病的频出,贫富分化的加剧等。中国在近几年也出现了严重了城市问题:贫富分化,城市贫困,城市犯罪,城市发展的瓶颈制约等。最重要的是,城市的扩张是以工业化对城市生态和生态系统的侵蚀为代价的,而这种不计后果的发展带来的是更为可怕的生态危机。“城市性”不能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提到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城市的生态性”。
人与自然的生态竞争归根到底源于资本化利益驱动,而这种以敌对开始的不良关系,让双方的利益受损,生态资源日趋紧张,生态赤字日益严重,空间的分配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不公平、不正义的“空间分配结构”。城市空间中,资源是有限的,对有限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是造成环境和社会敌对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源还在于政治经济的原因。人们创造了城市,但是肆意地滥用城市资源,破坏城市自然环境,忽视对城市自然生态的关注,会使人类自身的利益受损。自然和生态也已经成为城市空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城市空间的演化,自然生态正在和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步伐保持一致。哈维就此提出了环境正义的概念,他指出要和环境合作,这样“才能获得先发制人的环境主动性,所以,环境正义问题就不得不与长期的可持续性探索结合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地适应了当代主要生态问题的国际性需要”[8]。人们对生态欠下的债务要偿还,但是这种偿还是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的。
三、城市空间正义实现的原则
城市空间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空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整体突现。哈维指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应当结合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从地理、空间的维度寻找解决的途径。不仅关注分配的结果,还强调公正的分配过程。在当下我国讨论空间正义的语境中,空间正义“更多是意味、指向或者说希望一种社会正义,希望在社会关系层面,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具有相对平等、公平的空间”[9]。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的实现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城市空间正义应体现“以人为本”
城市空间是人的空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城市空间建设的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会使空间的人性张力得到丰富和充实。近代工业化以来,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城市空间中出现了很多违背人本的现象,如:城市规划的失衡、城市空间结构设计的错位、城市功能定位不准确等,并引发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社会治安混乱、生活压力增大、人际交往的异化、理想信念的缺失、人们幸福指数偏低。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城市发展的本质相背离,不能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怎样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怎样的人。在以商品经济和经济利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金钱关系”,而人也变成了“物”。在我国当代城市空间的发展中,受西方“物欲”经济的影响,“消费主义”和“金钱关系”成为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品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需要体现了人们的本性,而本性又是人本质的表现。人对自己的需要是从“自己出发”去发现的,人的需要从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不断发展,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社会交往的满足和对自己的精神需求,是人的需求的更高需要。人对城市空间的建造、占有和发展,会因为各种不正义的状况发生而突显对正义的渴望。城市作为各种文明要素的系统构成,城市应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公正和平等,它的精神内在在于“以人为本”,体现人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空间的更大正义。
(二)城市空间正义的价值在于城市意义的回归
城市作为一个特定的空间有机体,它的公平正义是维持其继续繁荣、稳定发展的前提,城市性是“城市在历史发展中所生成与显现的城市的本质;在理念与实在的统一中,城市是人的社会性、创造性的现实化、经验化、空间化,城市是人的社会性、创造性在空间中的可经验性、可感受地具体生成、聚集与转换,也就是各类文明要素的空间聚集于系统转换”[10]。城市性和城市的发展相契合,空间正义的探讨是为了解决空间中的危机,重建空间正义的伦理价值。
列斐伏尔指出,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为城市权而斗争的过程,社会的城市化使社会的基本存在和运行方式都不能离开城市存在,过去在“工厂一个场所进行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已经转移到交通建设决策部门和那些受到这些决策影响的工薪穷人之间的斗争,转移到城市化过程中那些被动城市化的居民和那些主持城市化、甚至那些通过城市化大发不义之财的开发商之间的斗争”[11]。列斐伏尔认为控制了城市权就掌握了城市发展进程的权利,为资本家制造更多的“空间生产”的机会。城市化作为资本主义所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性中呈现出城市的异化。
哈维进一步指出,城市社会空间生产的民主管理权是城市权的重心,城市是政治、制度、文化在规划上的总体体现,城市空间问题的解决应该从内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调整,同时通过城市空间的设计从形式上消解城市空间内容的矛盾。也就是说,城市虽然是人工建成,但是城市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对城市空间正义的追求,应该充分体现城市的现代价值和文明理性,城市空间应该回归本来的规划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成为社会空间和人的关系的空间。
(三)城市空间正义应尊重异质文化的多样性
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在空间横向延伸和空间结构重组不断引发意识形态的困扰和价值观多元化的冲突时,人们不禁会进行城市空间正义的文化追问。
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冷战体系成为历史,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12]文化的流变和断裂,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时有发生,全球空间的开放已经打乱了人们认同的固有模式和固有格局。
在当代的城市空间中,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对话不断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反思,全球化带来的空间扩张开始产生均质化的趋势,但是异质文化并没有因为它的多样性而更快地被传统认可,反而激发了城市空间多元价值的碰撞和冲突。可以发现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伴随社会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碰撞,每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思潮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都希望占领到政治的制高点,而城市空间就成为激烈碰撞的空间载体。
在城市空间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哥特式建筑高耸入云的尖顶,美国新古典主义自由又不失传统的田园别墅,巴洛克建筑的自由动感和离经叛道,拜占庭式鲜明宗教色彩的高大穹顶,洛可可超越真实的梦幻空间结构等。这些外在的面貌都显示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在社会空间中曾经的利益权衡和权力彰显,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文化艺术的呈现。
列斐伏尔用“文化革命”一词来描述城市空间的文化体验,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在城市空间并通过都市社会的实现得以感受,对文化的诠释将成为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根源追问。城市空间因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审美、文化信仰和文化传统带来空间价值的不同判断标准,城市空间正义的实现,应回归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尊重异质文化的多样性。
(四)城市空间正义的实现应回归其生态性反思
过速的城市扩张常常以工业化对城市生态和生态系统的侵蚀为代价,城市病的频出使“城市的生态性”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为国人所熟知的“雾霾”已经成为城市空间环境恶化的代名词,雾霾的产生源自使每天84个自然村消失的城市化和获利远远小于危害的各种大工业的扩张、工业产品的产生和对GDP的盲目追求。一旦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失去本身应有的积极意义,变成“政绩的化妆品”,就会有“形象工程”“城市包装”和腐败滋生的温床。城市空间正义应该建立在城市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一味地追求经济的过速增长已经成为“单向度”的发展模式。
城市空间中对有限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是造成环境和社会敌对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生态竞争归根到底源于资本化利益驱动。城市空间正义危机之一,就是城市空间的发展是以对自然生态的无情掠夺为代价的,生态资源日趋紧张,生态赤字日益严重。工业化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空间的繁荣,但是城市化不代表工业化,城市空间的发展也并不是工业化或者资本化。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空间的发展正在回归生态理性,正义的环境不仅是环境问题,而是城市空间生态现代化的追求。环境的管理将成为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空间的分配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还包括在人与自然之间,城市空间正义回归生态理性,是空间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6.
[2] 陆大道,等.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5.
[3] 段进军,倪方钰.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思考——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J].苏州大学学报,2013(1):49-5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6] 任平.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J].江海学刊,2011 (2):24-31.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60.
[8] 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33-435.
[9] 陈忠.爱德华·索亚.空间与城市正义:理论张力和现实可能[J].苏州大学学报,2012(1):1-6.
[10]陈忠.城市意义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伦理建构[J].学习与探索,2011(2):1-6.
[11]吴细玲.城市社会空间与人的解放[J].哲学动态,2012(4):26-33.
[1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5.
[责任编辑 林雪漫]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Justice in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ZHONG Minghua1,DENG Xinxin1,2
(1.Marxist School,Sun Ye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275,China;2.Finance&Economics Law School,Guangdong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320,China)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 is accompanied by China's modernization.Urban space be-comes an importan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which indicates People's daily life,learning and development.The blind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ack of awareness about urban,make the urban space an area with most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of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The imbalance of space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excessive homogeneity of space,"power"feature of the space and plunder of natural space become prominent issues of urban space research.Return to people's needs,respect for the essence of city,tolerance of diversity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and ecological balance between city and nature will be people's expec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 in the inquiry of urban spatial justice.
Key words:modernization process;urban space;space crisis;spatial justice
作者简介:钟明华,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伦理学研究;邓欣欣,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广东财经大学副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的发展与现代化、高等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4CMK01)
收稿日期:2016-03-02
中图分类号:B82;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6)04-00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