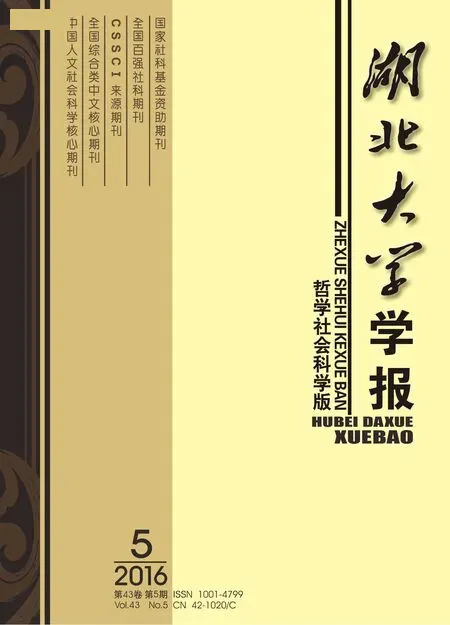论买卖合同的价格条款及其补价规则之完善
2016-03-09黎珞
黎 珞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论买卖合同的价格条款及其补价规则之完善
黎珞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价格是否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现行《合同法》提供的补价规则亦存在漏洞。价格待定买卖合同能否成立不应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合同的法律性质加以判断。在双方当事人已同意受合同约束的基础上,法律应允许部分不受自身内容与性质限制的缺价买卖合同的成立。为了填补现行补价规则的漏洞,应建立以合同的类型化作为逻辑展开的补价体系并辅之以“合理价格”为兜底条款的立法模式,尽可能覆盖全部缺价情形,促使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最终履行。
价格待定;买卖合同;必要条款;补价规则
买卖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明确的价格条款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价格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①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3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30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另外有学者则认为标的物价格“不再是订立买卖合同的必备条件”[1],承认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成立。那么,价格究竟是不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如果不是,价格在合同成立后如何确定,《合同法》中的补价规则该如何完善?这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履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拟就买卖合同的价格条款及其补价规则之完善进行研究。
一、对我国《合同法》中买卖合同价格条款规定的反思
(一)立法规范之解读
我国《合同法》对于买卖合同价格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在第12条、14条、61条、62条以及159条。其中第12条与第14条规定在《合同法》总则第二章合同的订立部分,第61条与第62条规定在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第159条规定在分则买卖合同部分;前面四个条文不仅适用于买卖合同,还适用于合同法分则中其他类型的有名合同,而第159条则专门适用于买卖合同。《合同法》第12条规定了各类合同成立通常具有的条款,从“一般包括”的字样中可以看出该条文属任意性规范,所涉事项无需强制性的订入合同之中;第14条是关于有效要约应符合的要件,由于要约发出后一经承诺合同立即成立,因此要约“内容具体确定”亦可理解为对合同内容的要求;第61条、62条第二项依次规定了补价方法,由于这两个条文规定在合同履行部分,且分别使用了“合同生效后”与“订立合同时”的字样,说明立法允许合同在价格确定前成立生效;依第159条的内容,“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买卖合同可以在缺少价款时成立。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标的与数量三个要素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只要合同具备这三个条款即可成立,这与《合同法》第61、62条没有对这三个要素制定补缺规则相符。
(二)买卖合同价格规范之反思
仔细分析以上有关买卖合同价格条款的规定,会发现其并非完美无缺。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疑问还有待理清,否则将会严重影响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及合同的履行。
1.价格是不是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如前所述根据《合同法》第61、62条以及159条的规定可知,包括买卖合同在内全部有名合同的成立均不需要价格条款,然而,《合同法》分则规定的一些特定类型的买卖合同则并非如此。某些特种买卖合同就必须明确价款才能成立,比如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8条之规定,因为“分期付款”中买受人应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因而只有在合同成立之时确定了总价款的数额,才能进一步明确分期付款的次数和每次的数额,分配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否则便不能成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合同法》第172条与173条分别规定了招投标买卖合同与拍卖合同,依照这两类合同的性质,只有价格条款确定之后合同才能成立。其次,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对于合同主要内容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因此价格条款亦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另外,依照我国《合同法》第61条、62条的规定,在价款不明确的情况下,买卖双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充。然而,当买卖标的物是某些不代替物时,如世间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假设双方当事人无法就价格达成协议、合同条款也未涉及价格、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交易习惯、履行地也没有该物品的市场价格,政府也没有定价或提供指导价,即适用所有补价方法仍不能定价的情况下,合同可能最终不能得到履行。总之,《合同法》在总则中一概规定合同可以在缺少价款时成立并不适用于分则中某些特殊的合同类型,价格对于这些合同的成立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有学者认为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是对待给付,价金同货物一样都是合同的标的物,因此价款必须是合同的必要条款[2],有学者认为“价格条款是买卖等有偿合同的必要条款”[3],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在特种物买卖合同等种类中,价格必须予以明确”[2]。那么,价款究竟是不是买卖合同的必要条款?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价款的规定是否有误?这些问题还有待研究。
2.价款补充规则存在缺陷。我国《合同法》第61条、62条为价格待定合同提供的价款补救方法适用于包括买卖合同在内的所有合同,但仔细考量,这些补救方法并不完整。
一方面,价款是买卖合同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方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于对方,另一方支付相应的价款,这样买卖合同最终才能得到履行;所以无论何时确定价款,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合同的标的物是特定物、最新面世的商品、履行地市场未曾出售的商品或是作为积压品、季节性产品等亟待处理的商品时,依次适用以上两条文所提供的补价方法依然无法确定价格时[4],法官应直接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还是行使自由裁量权为该合同提供一个价格?如果可以提供,法官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确定一个合理价格呢?《合同法》在此没有涉及,所以第61条、62条的价款补缺规则并不完整。
另一方面,由于第62条是在利用第61条仍不能确定有关内容的情况下才予以适用的,而第61条的适用是以“合同生效后”作为前提,所以《合同法》在此提供的补价规则仅仅适用于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即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不能适用第61条、62条的补缺规则,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合同法》第44条规定合同因尚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而不能生效,第45条、46条分别为附条件合同与附期限合同,第47条、48条、51条依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与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以上这些合同在成立时并不生效,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但依据第61条、62条设置的“合同生效后”之要件,买卖双方不能在上述合同生效前补充价款,这在法理上站不住脚,难道在此情况下不能补充合同漏洞吗?显然与合同自由原则相违背。因此,《合同法》第61条、62条中设置的“合同生效后”之条件不合理且缺乏实际意义[5]。
总之,价格待定买卖合同是否可以成立?该如何完善现有的价格补缺规则?这些实际问题都亟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二、价格条款与买卖合同成立的关系
对于买卖合同的成立是否应包括价款的争议,必须意识到合同成立最根本的标志是“当事人就主要的条款达成合意”[6]213,这包含“主要条款”与“合意”两个要件。
“主要条款”指合同内容需要具体明确,《合同法解释二》第1条虽然规定了合同成立的三个主要条款,但需要注意该条用语是合同“一般应当”而非“应当”成立,即在某些情况下,仅仅确立这三个条款还无法满足合同“主要条款”的要求。“合意”则反映双方当事人愿受合同之约束,是合同自由原则之体现,其重点是合同双方自由地确定合同的内容,只要“合意”的内容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第三人之利益,法律就不应禁止。判断“合意”已形成的方式有很多种,“主要条款”的达成是其中之一,这说明双方当事人有意在达成协议时约束自己,虽然价格等重要条款在未来才能确定,合同也不应无效[7]61。由于“主要条款”与各类合同的主要内容息息相关,因此,买卖合同的成立是否需要价格条款应结合合同的类型与具体内容综合加以判断,而不应在《合同法》总则中一刀切地认定所有种类买卖合同的成立均不需要价格条款。笔者认为,有两类特殊的买卖合同成立时必须明确价格条款:第一类源于标的物的特殊性,比如上文提到的商品房的买卖,由于行政法的干预致使价格成为该类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第二类则是因为某些买卖合同自身的性质,使得价款构成了该类合同成立不可或缺的要件,比如前文说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如果没有明确价格则无法实现其分期付款的合同内容,招投标买卖合同、拍卖合同等特种买卖亦是如此。
有研究表明,如果允许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可能会使双方陷入不愿承担的义务以及勉强接受非因约定所确定的价格导致不确定的交易风险[8]。那么法律是否应该承认其他不受自身法律性质限制的缺价买卖合同的成立呢?笔者认为,以上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首先,如前所述,合同之成立必以双方达成“合意”作为前提,如有证据证明双方愿受合同之约束,表明当事人已默示地接受未来确立价格的方法以及可能的合理数额,完全不存在真实意思之违背,与在合同成立之时约定价格并无差别。
该协议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筛选锚点,第二部分筛选出不被锚点支配的数据点,第三部分在筛选出的数据上计算skyline。
其次,法律承认缺价买卖合同之成立有助于维护买卖双方之间的合法权益、规避交易风险:法律一旦认可该类合同的成立,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4条之规定,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即发生效力、当事人负有确定价款的义务,如果事后一方反悔而不愿就价格继续协商,那么该方当事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假设缺价买卖合同不能成立,那么即使一方事后反悔而不愿继续协商价款,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是由缔约过失责任仅仅适用于“订立合同过程中”所决定的;相比较而言,无论从责任的构成要件还是责任的承担方式与范围来说,违约责任都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促使合同最终履行。
最后,价格待定买卖合同往往被运用于特定的交易情形之下:情况紧急来不及确定价格或者当事人为了规避商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急于确定价格的时候;对于前者,买方往往急需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以满足生产,同时卖方也不希望错失商业机会,因而双方会在价格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先行订立合同,以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后者,因为受市场因素影响,一些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在合同订立时与实际履行时会发生大幅变化,所以,为了规避订立合同时无法估量的商业风险、减少交易成本,买卖双方会选择在磋商阶段把握商机、促使合同成立。比如在“江苏刚正薄板科技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申请案”中,买卖双方在签订《产品供销合同》时没有明确价格,只在合同中规定“订货指导价,结算价格待定”,结算价格则由双方商定,而“商定价格”的内涵即是其自行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确定价格,遇涨则涨、遇跌则跌,这就是价格待定合同在实际交易中的具体运用。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价格是否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款不应一概而论,具有特殊法律性质或特殊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在成立时就必须具有明确的价格;由此,应调整我国现行《合同法》对合同成立条款的规定,在总则中仅需规定当事人、标的与数量三个要件,在分则中再规定价格等其他特殊类型买卖合同的成立要件,以消除总分则体例上存在的矛盾。至于一般的价格待定买卖合同,在双方当事人已同意受合同约束的基础上,法律应允许合同依当事人的约定而成立;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愿意受合同拘束之意思,可以通过双方是否就“主要条款”达成一致进行判断。另外,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7条之规定,“采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实际履行亦可以作为判断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方式。当然,合同之价格在履行时具备“可确定性”[9]76亦十分重要,而这取决于完整的补价规则。
三、价款补充规则之完善
虽然允许部分缺价买卖合同的成立有其合理性,但仍需制定相应的规则予以规避可能存在的交易风险。如上文所述,我国《合同法》第61条、62条提供的价格补缺规则并不完整,会出现部分标的物在适用既有补价方法之后仍然不能定价、合同最终不能履行的情况。所以,需要改进《合同法》中现有的补价规则,制定逻辑严密的补价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以至于“在私法的许多领域,法律的统一以及协调已经开始”[10]451;为了适应这种趋势,我国《合同法》立法也应“广泛地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使我们的合同法成为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11]。本节先对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立法与国际条约中有关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再对现行《合同法》补价规则加以完善。
(一)典型立法模式的比较研究
比较世界先进法制国家、地区的立法与国际条约中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补价规则,可以区分为三种立法模式:
1.限制型。此类立法模式以法国为代表,限制该类合同的成立。《法国民法典》第1591条规定“买卖的价金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确定并予指明”[12]1209;虽然第1592条规定“买卖的价金亦可由第三人进行仲裁(公断)”[12]1212,但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的态度却十分保守,他们认为只有当价格可由双方当事人指定的第三人确定,或依据官方指导价格、流行的市场价格确定时,合同才是有效的;如果再受到双方意愿或行为的影响,价格便不可确定,合同无效[7]62~63。
3.无条件承认型。采用此类立法模式的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欧洲合同法原则》也采纳了此类立法形式。在这类立法中只要双方达成愿受合同约束的合意便可以承认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并为之制定了详细的补价规则。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5条第1款不仅就买卖合同明确规定“当事方有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的,即使价格未定,仍可订立合同”[15]77,且提供了双方协商确定、第三方确定、单方确定、合理价格确定等多种定价方法;《意大利民法典》第1473条、1474条提供了依第三方定价、双方合意定价、市场价格定价等补价方法,显然承认缺价合同的成立,且未设置任何条件[16]357。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与《欧洲合同法原则》作为国际商事惯例,虽然不具有国际公约的性质、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没有强制性约束力,但作为国际商事领域的示范文本,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因而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较这两个条约,我们会发现,两者对于该类合同的规定大同小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1.14条就特意待定的条款进行了专门规定:“如果当事人各方意在订立一项合同,但却有意将一项条款留待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则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17]99《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04条亦规定:“如果合同未约定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式,则应视为当事人已同意了一合理价格。”[18]由此,两个国际条约均无条件的承认该类合同的成立。另外两国际条约同样提供了补价方法,前者认为可以将类似履行时的通常价格、一方确定的价格、第三人确定的价格、相似因素下的价格以及合理价格作为补充的价格;后者认为可以通过单方定价、第三人定价、相当因素定价以及以合理定价的方式来补充价款。
总之,除了法国限制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成立,大部分是采用有条件或者无条件承认的立法模式。这说明允许该类合同的成立已经成为国际主流,不同立法模式之间的主要区别仅存在于补价方法上。笔者认为,法国民法限制缺价买卖合同的成立与其民法典采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关:由于合同一经成立,所有权与风险负担即移转于买受人[19]96~97;为了降低交易风险,法国民法当然不能允许物权发生移转时,价格还未确定。我国《物权法》规定物权之移转需交付或者登记之后才能发生效力,因此并不存在法国民法遇到的问题,这就更说明了我国《合同法》具备承认部分缺价买卖合同成立的立法条件。
(二)补价体系之完善
通过对世界主流立法模式的考察,针对我国《合同法》补价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改良:第一,为了最大限度的涵盖全部价格待定的情形,应以价格待定买卖合同的具体类型作为规则展开的逻辑线索;第二,借鉴实用、灵活的立法经验,引入“合理价格”理论作为补价规则的兜底条款。
1.补价规则之逻辑展开。为了增强补价条款的适用性、覆盖全部可能产生的价格缺失情形,本文以买卖双方是否在合同中约定补价方法为标准,将价格待定买卖合同初步划分为已约定补价方法之合同与未约定补价方法之合同两大类:前者包括约定双方协议定价、一方定价、第三方定价的合同;后者为没有约定任何补价方法的空白价格合同,具体包括表面的空白合同与实质的空白合同两类[19]。
约定双方协议定价的买卖合同遵循合同自由原则,与一般合同的区别是推迟了定价时间;当双方最终无法协商定价时,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5条第1款(b)项①美国《统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评述》第2-305条第1款(b)项:“此种情况下,价格为交货时的合理价格,假如价格留待当事方约定,而当事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与《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04条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04条:“如果合同未约定价格或确定价格的方式,则视为当事人已同意了一合理价格。”规定最终价格为“合理价格”。笔者认为,此时“合理价格”已经不能由买卖双方而应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代为确定。约定一方定价的买卖合同,首先定价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确立一个价格,如果该方提出的价格明显不合理,相对方可以对该定价进行调整;如果定价方最后仍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另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定“合理价格”。对于第三方定价合同,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情形一,买卖双方未就委托之第三方达成一致,应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指定第三方定价;情形二,买卖双方已委托第三方,但该第三方不愿或不能定价,买卖双方可以另行指定第三方或者请求法院、仲裁机构重新指定第三方;情形三,委托的第三方定价明显不合理,当事人一方可以请求该第三方重新定价、更换第三方或请求法院、仲裁机构重新指定第三方。当然,第三方定价合同中出现以上三种情形后,买卖双方还可以选择直接协商确定“合理价格”或者请求法院、仲裁机构直接确定“合理价格”,这样操作起来更为简便。
订立未约定补价方法的买卖合同之后,买卖双方可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重新协商确定价格或定价方法,如果仍未达成协议,应交由法院或仲裁机构确定。对于表面的空白合同,其中暗含了买卖双方关于价格或定价方法的默示合意,需要法院或仲裁机构运用合同解释的方法予以揭示,结合买卖双方的交易习惯、行业惯例、合同条款或双方定立合同之后的行为加以判断:比如买卖双方存在长期的交易,某次忘记在合同中约定价格,在售价没有重大市场波动时可以沿用原来的交易价格进行本次交易;再比如买方向卖方发出订购单表示愿意购买卖方销售目录中的某种商品,且没有提出具体价格,但买方发出订购单的行为本身即表示其愿意支付卖方在销售目录上对应商品的报价,这也是默示确认价格。对于实质上的空白合同,法院、仲裁机构无法通过合同解释认定买卖双方之间默示地约定了价款或定价方法,可以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2-305条第1款(a)项③美国《统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评述》2-305条第1款(a)项:“此种情况下,价格为交货时的合理价格,当事方未提及价格。”、《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7条第(1)款④《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7条第(1)款:“如果合同未规定价格,也无如何确定价格的规定,在没有任何相反表示的情况下,应视为当事人各方引用在订立合同时可比较的相关贸易中进行此类履行时一般所应收取的价格,或者,若无此价格,应为一个合理的价格。”与《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04条之规定,此时法院或仲裁机构应提出一个合理数额作为买卖合同的价格。
2.补价兜底条款——“合理价格”的确定。根据上节分析,在最终无法定价时,依照该类合同的类型,或由双方当事人,或由法院、仲裁机构提出一个“合理价格”作为价款,这可以理解为定价的兜底条款,在国际立法中多有采用。不过笔者注意到,除了“合理价格”,在《意大利民法典》第1474条第1款①《意大利民法典》第1474条第1款:“如果契约以出卖人通常出售之物为标的物,且双方当事人未确定价格,亦既未就确定价格的形式达成合意,也未根据行政法规或行业规则进行确定,则推定双方当事人愿意接受出卖人通常采用的价格。”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7条第(1)款中分别使用了“通常价格”与“一般所应收取的价格”,均是指买卖双方在以往此类交易中履行的价款,主要针对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交易习惯的情形;构成“合理价格”的因素则不止交易习惯,“通常价格”作为“合理价格”之一种可以包含在“合理价格”之中。那么,该如何确定该“合理价格”呢?
笔者注意到,在美国《统一商法典》颁布之前,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曾经制定过一部《统一买卖法》(Uniform Sales Act,1906)在34个州适用,该法第九部分将“合理价格”定义为“是一个依赖于每个案件所处的特定情形这一事实的问题”②Daniel E.Murray.The“Open-Price”Sale of Goods Contract in a Worldwide Setting.89 Com.L.J.491,1984.;查阅美国联邦法院的相关判决,法官在不同的案件中判断“合理价格”时或是以“市场价格”代替,或是将“竞争价格”、“通告价格”、“发票价格”等等作为判断标准,都没有就“合理价格”达成统一适用的定义。如在Spartan Grain&Mill Co.v.Ayers案中卖家Spartan是一家饲料生产厂家,它卖给买受人Ayers的饲料的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卖家(市场价格);但法院并不认为该价格不合理,因为卖家答应以后购买所有买家生产的鸡蛋,这一揽子交易确保了买家将来鸡蛋的销售渠道③Spartan Grain,Mill Co.v.Ayers,517 F.2d 214,217,17UCC Rep.693,695(5th Cir.1975).。以上说明“合理价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确定“合理价格”的数额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衡量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有关因素。在我国必须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确认“合理价格”的规则,通过归纳影响判断的相关因素,本文认为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首先,应对合同条款加以解释看是否能得出价格,若不能,再依据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定价。若无交易经历,应根据合同履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定价。这样当然会出现标的物在履行地无市场价格的情况,笔者注意到我国《反倾销条例》提供了确定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这与确定价格待定标的物的售价相似。《反倾销条例》第四条④《反倾销条例》第4条:“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按照下列方法确定:(一)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有可比价格的,以该可比价格为正常价值;(二)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没有销售的,或者该同类产品的价格、数量不能据以进行公平比较的,以该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地区)的可比价格或者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为正常价值。进口产品不直接来自原产国(地区)的,按照前款第(一)项规定确定正常价值;但是,在产品仅通过出口国(地区)转运、产品在出口国(地区)无生产或者在出口国(地区)中不存在可比价格等情形下,可以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价格为正常价值。”首先将进口产品的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地区)市场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若无法确定在出口国(地区)的可比价格,则以该同类产品在适当第三国(地区)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或者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作为正常价值。由此,可以将类似产品价格、适当地区市场价格与产品构成价格相结合作为确定标的物售价的方法:当标的物在履行地无市场价格时,应以类似产品在履行地的市场价格作为“合理价格”;类似产品在履行地无市场价格时,可以类似产品在其他适当地区的售价为“合理价格”;以上方法均不能适用时,应以生产该产品的成本加上合理利润作为标的物的“合理价格”。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7条第(4)款⑤《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5.1.7条第(4)款:“如果确定价格需要参照的因素不存在,或已不再存在或已不可获得,则应取最近似的因素作为替代。”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07条⑥《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07条:“如果价格或合同的其他条款要参照某一因素加以确定,而该因素不曾存在或不再存在或不再能够找到,则应代之以最为相当的因素。”在确定价款时运用“最相似(相当)因素”的方法相似。
综上,以合同的类型化来构建补价规则、引入“合理价格”作为兜底条款的立法模式几乎可以涵盖全部情形,对于不替代物的买卖亦可通过“合理价格”的方法定价[20]。
四、结语
本文力图解决两个问题,我国《合同法》是否应该承认缺价买卖合同的成立以及如何完善现有买卖合同的价格补缺规则。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不应一概而论,那些具有特殊法律性质或标的物(如受行政法管制)的买卖合同在成立时必须具有明确的价格;在双方当事人已同意受合同约束的基础上,法律应允许其依当事人的约定而存在。由此,立法应调整《合同法》对合同成立条款的规定,在总则中仅需规定当事人、标的与数量三个要件,在分则中再规定价格等其他特殊类型买卖合同成立的要件,以消除总分则体例上存在的矛盾。对于第二个问题,在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模式、借鉴有关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以合同类型化为框架的补价规则并辅之以“合理价格”为兜底条款的立法模式,最大化的涵盖全部价格缺失的情形,促使买卖双方顺利履行合同。随着民商事交易的不断发展,契约自由、促进交易与提高效率的理念也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改进补价规则对降低交易风险、促进合同履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1]陈思.论我国《合同法》中买卖合同的价格问题[J].时代法学,2012,(1).
[2]张善斌,熊倪.比较法视野中买卖合同的价格条款[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3]刘婕妤.试析合同必要条款的范围[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2).
[4]喻志耀.价格不明合同合理价格的确定——新合同法第62条之不足与补救办法[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5]肖冰.论价格缺失对合同成立的影响——CISG与中国《合同法》的适用差异[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1).
[6]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Nellie Eunsoo Choi.Contracts With Open or Missing Term under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and the Common Law:A Proposal for Unification[J].Columbia Law Review,January 2003.
[9]伊曼纽尔.合同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10]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M].张新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1]梁慧星.合同法的成功与不足(上)[J].中外法学,1999,(6).
[12]法国民法典(下册)[M].罗结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3]德国民法典(第4版)[M].陈卫佐,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4]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5]ALI(美国法学会),NCCUSL(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美国统一商法典及其正式评述(第一卷)[M].孙新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意大利民法典[M].费安玲,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7]国际商事合同通则[M].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8]欧洲合同法原则[J].外国法译评,1999,(2).
[19]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20]吴思颖.货物买卖中的价格待定合同研究[J].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2006,(7).
[责任编辑:李严成、马建强]
D923.6
A
1001-4799(2016)05-0120-07
2015-11-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资助项目:14YJC820057
黎珞(1988-),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