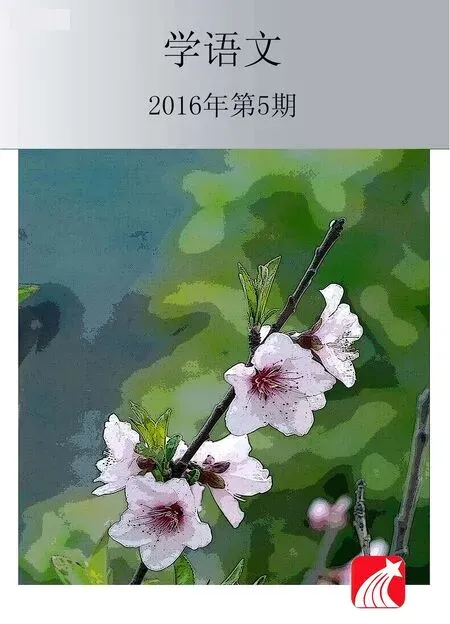男性身份的主体性重构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
2016-03-02章佩
□章佩
男性身份的主体性重构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
□章佩
《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激烈的中日民族冲突(外部冲突)代替了人性的内部冲突,电影对小说中出现的男性身份进行了主体性重构,删去了他们软弱、无能的特点,还原了他们本该具有的男性气质,刻画了中国男性在民族灾难面前的血性担当,弘扬了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品质。这样的改编出于民族主义及世俗英雄主义的考虑,也有商业目的。
男性;冲突;身份;主体性重构
2007年张艺谋买下严歌苓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版权,由严歌苓与刘恒合作改编成剧本,历时数年拍成同名电影《金陵十三钗》,并于2011年12月15日在全国公映。影片公映后掀起一片观影狂潮,观众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针对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学术界也纷纷刊文发表各种意见。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不同的角度探究这种改编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往的论述关注点大多是在综合分析两者的差异,或者关注在故事中做出巨大牺牲的一群风尘女子,而很少将关注点集中在故事中出现的男性身上。笔者发现小说着墨较多的是内部冲突,严歌苓将这些男性人物放在教堂这个封闭的空间,通过他们的言行心态来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揭示人性的弱点。而在电影中,故事以逃亡开始,以逃亡结束,激烈的中日民族冲突贯穿始终,影片削弱了对人性的剖析,着重突出的是在这种激烈的外部冲突中,在灾难面前男性所爆发出的人性的力量。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侯克明先生曾说过:“从小说到电影,故事在不同的文本形式中转换,必然产生畸变。一部分改变是出于适应不同艺术形式的需要,而另一部分改变则完全是出于叙述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1]在文本转换的过程中,随着冲突由内部到外部的转移,男性身份发生了巨大的主体性重构。基于观众期待、市场需求、电影审查等各方面因素,张艺谋对小说中的几位主要男性都做了身份的二度创作。这不仅适应了不同艺术形式的需要,也传达出张艺谋的主观意愿。
身份一词是指人的出生及社会地位。在中国,这个词附带了众多的感情色彩,几千年沉淀下来的身份观念及身份情结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身份一经确定,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被定位,如果有人做出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行为就会被人们所唾弃。《金陵十三钗》小说和电影中出现的主要男性有神父、士兵、陈乔治、书娟父亲,电影再创造了小说中的男性身份,还原了他们本该具有的男性气质。故事的展开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在这座发生战争的城市里,所有人的职业和身份可以简化为两类——有武器的士兵与无武器的平民,这样的划分方法便于我们定位男性的身份,便于探讨身份改编背后的原因及价值。
一、有武器的士兵
战争是由国家上层意志主导,以士兵行为来执行的,服从上级命令是士兵的天职。在战争状态下,士兵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武器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因此,我们可以此来区分这座发生战争的城市里的所有人。南京保卫战时,守卫南京的士兵大多是从淞沪会战中败退下来的残兵,本就军心不振,加之主帅唐生智及部分国军将领的临阵脱逃,更加重了撤退的无序与混乱,导致南京三天即告沦陷。战争中,侵略者往往通过屠杀士兵及践踏女性来宣告对这个民族或城市的占领,面对着日军的疯狂搜剿与残害,这群留在沦陷区的守城士兵的身份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在小说中,严歌苓将南京保卫战作为一个故事背景铺展开来,含蓄的表露出她对于放下武器成为战俘的中国士兵的同情兼讽刺。她笔下没有士兵携带武器与日军抗战到底的场景,而是让他们放下武器走进教堂以普通男性平民的身份与妓女们厮混。因此,小说集中展现的是士兵进教堂后与自己人之间发生的内部冲突,以及自我反思时的人性冲突,真正的外部冲突是在小说后半部分被日兵搜捕及刺杀时。在教堂的地窖里,士兵与妓女们相拥而舞,夜夜笙歌,当得知豆蔻的遭遇后,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被日军搜捕后,他们为了保护女学生和妓女,主动出面,忍辱被杀。但是,基于电影是纳入国家民族叙事层面这一因素的考虑,张艺谋削弱了国民性中不好的一面,减轻了国民之间的内部冲突,而加重了民族冲突。激烈的中日民族冲突贯穿影片始终,以逃亡开始,以逃亡结束,士兵全都被推至教堂外的战场上,与日军发生激烈的正面对抗,直至壮烈牺牲在战场上。
在小说中,放弃武器进入教堂避难的这群士兵,按照国际法就不算士兵而是平民身份,因此,揭去士兵这层身份外衣的他们在教堂里完全暴露出普通男性的情欲及软弱,战争留下的余悸被淡忘,灾难暂时远去的得过且过的心态,使得他们以平民的身份“今朝有酒今朝醉”,与妓女们夜夜狂欢,喝酒作乐。然而,当面对日军的搜捕时,他们士兵的身份再一次还原,突显出士兵在强大而残暴的敌人面前血性担当的一面。严歌苓用隐含着哀怨、讽刺又同情的笔触将这些男性形象移到纸上,记录了中国士兵软弱无能的一面,以求更好地烘托故事中做出牺牲的那群女性,让她们的形象更高大清晰,让她们的牺牲更加震撼人心。相反,张艺谋以一个男性导演的视角再创造了这些士兵形象,满足观众对于中国士兵高大完美形象的期待,另一方面,基于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造成的身体及精神的伤害,以及对于那些在抗战中壮烈牺牲的中国士兵的缅怀等因素,影片中出现的士兵形象都是英勇高大的。影片中的士兵始终拿着武器抗战到底,意味着他们一直以士兵的身份存在着。李教官带领的十几个教导队的士兵在影片开始时为了护送女学生而与日军激烈抗战,演绎了一段人与坦克(机器)的生死对决,仅剩的李教官一人,始终以士兵的身份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守护着这群女学生,最终与日军一个小分队同归于尽,充分突显出中国士兵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的铮铮铁骨。李教官进入教堂,安顿了奄奄一息的王浦生,归还了女学生遗失的鞋,便悄然离开了教堂,这些场景的刻画,让士兵的形象更丰满,让中国士兵的身份更深入人心,他们不仅有铮铮铁骨还有侠胆柔情。张艺谋加大战争戏码,花重金打造战争场景,并请威廉姆斯领衔的好莱坞特效团队来拍摄,使得影片的战争场面可与《拯救大兵瑞恩》相媲美。战争场景的精致刻画,还原了中国士兵的英勇气质,这一身份的主体性重构,着重证明了在灾难面前,直至最后一刻,士兵仍是保护我们国人的屏障,是民族的脊梁,是国家强大起来的支柱。
二、无武器的平民
相较于士兵,平民的身份就稍显复杂,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年长的老者,只要存在于这个人的社会里,他都具有身份,学生的身份、父亲的身份、医生的身份等等,身份一经确定,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被定位。小说中着重刻画的都是内部冲突,严歌苓将这些人物集中在教堂之中,通过短短几天的避难时间将这些人物的灵魂深处剖析给读者,让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严歌苓在《悲惨而绚烂的牺牲》中写道:“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这个故事是献给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中的女性牺牲者的。当故事中的牺牲铺展开来时,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而且绚烂。”[2]这篇小说是她以女性主义视角讲述的一个妓女救女学生的凄美故事,意在表达女性在灾难面前爆发的人性力量,因此,在小说中所有出现的中国男性都是以配角的身份展现的懦弱无能的形象,他们都做着与自身身份不符的事情。然而,电影与之正好相反,张艺谋以一个男性导演的视角来再创造这个故事时,着重考虑民族主义及世俗英雄主义叙事视角,还原了男性身份本该具有的气质,这样的改编也利于吸引更多的观众,达到商业目的,另一方面也利于弘扬民族气节。
小说中封闭的教堂环境让读者更集中的将关注点放在这里的内部冲突上,包括法比·阿多那多神父与妓女之间的冲突、书娟父亲(“双料博士”)与妻子及玉墨之间的家庭冲突、陈乔治的内心冲突。然而在电影中,外部冲突取代内部冲突,激烈的中日民族冲突贯穿始终,所有的人物此刻都是一致对外,团结并对抗日本侵略者,突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冲突的改变使得男性的身份也都发生了改变,没有了人物内心的剖析,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都是完美的男性形象。小说中的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是神父助理,他的身份使得他致力于保护女学生,同时,又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世使得他的身份很有意义,一方面,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来自省其劣根性,另一方面又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侧目审视中国的国民性。虽然小说中也刻画了他经不住诱惑的一面,但是他与英格曼神父是小说中唯一敢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的角色。电影中两位神父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电影原创的角色约翰,这个以入殓师的身份出场的小混混,在人性觉醒的过程中完成了由入殓师到神父的身份转换,从开始的只图利益到最终的舍身相护,由小混混蜕变为大英雄,完成了心灵的救赎,最后,他又以入殓师的身份为这群女性化妆,让女人们回到最年轻美丽的时刻。这个形象的虚构集中体现出张艺谋对于好莱坞电影的借鉴,通过世俗英雄主义叙事模式的运用,进军欧美主流电影市场,同时赢得更多的观众。
小说中的书娟父亲是从玉墨与书娟的回忆中呈现出的一个人物,作为丈夫他并不尽职,在没能保护妻女的情况下,与玉墨发生了一段婚外恋情,充分体现了一些中国男人软弱、轻浮、意志薄弱的劣根性。而在电影中,家庭内部冲突转变为与日军的冲突,他始终是以书娟父亲的身份存在着,为了帮助女儿逃离南京,他忍辱留在南京做日本人的翻译,游走在日军身边,他始终坚守着一个父亲所担当的责任,牢记着曾对书娟母亲许下的承诺“我答应过她母亲,要好好照顾她”。在电影的美化处理下,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国难当头,为了保护女儿,一个普通男人(父亲)所爆发出的男性力量,他是伟大、勇敢、有担当的。这一身份的主体性重构,更符合观众对于一个父亲身份的期待与认可。
小说中的陈乔治是教堂里一位二十四岁左右的橱子,在神父收养的十几年里在教堂干着杂活,始终坚信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信念。这种身份使得他在面对国难时,没有危机感与悲痛感,仅仅局限于眼前的享乐,与妓女偷情、把酒言欢。电影里因为神父的死导致教堂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失去了守护神的教堂显得格外混乱,陈乔治在这里只是一个跟女学生同龄的十四岁男孩,接受神父遗愿的他在此担任了监护人的身份,致力于保护这群女学生,以至于在最后主动充当第十三个女学生。陈乔治的角色是电影塑造得较成功的一个,他只是一个男孩,在一个同女学生一样需要被保护的年纪选择了誓死保护别人,电影删去了小说中那个懦弱无能的男性形象,经过美化处理后的他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最弱小的中国男人也可以恪守职责勇敢地保护身边的人。这一身份的主体性重构,加剧了故事的悲剧气息,增强了影片打动人心的震撼力量。
总之,从小说到电影,民族主义与世俗英雄主义叙事视角取代了女性主义视角,激烈的中日民族冲突(外部冲突)代替了人性的内部冲突,男性的身份经过主体性重构后更加深入人心。士兵、书娟父亲、陈乔治,他们不再像小说中刻画的那样好色、懦弱,不再与妓女们醉生梦死、把酒言欢,而是坚守各自身份所担负的职责,誓死保护女学生。基于观众期待、市场需求、电影审查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电影弱化了对于人性弱点的剖析,强化了民族性,刻画了中国男性在民族灾难面前的血性担当,弘扬了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品质。无论是英勇的李教官、隐忍的孟先生、还是弱小的陈乔治,在“妓女救国”的这个主题下,他们的牺牲都是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
[1]侯克明:《女性主义背景的英雄主义叙事——<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的文本转移》,《电影批评》2012年第1期。
[2]严歌苓:《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编 张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