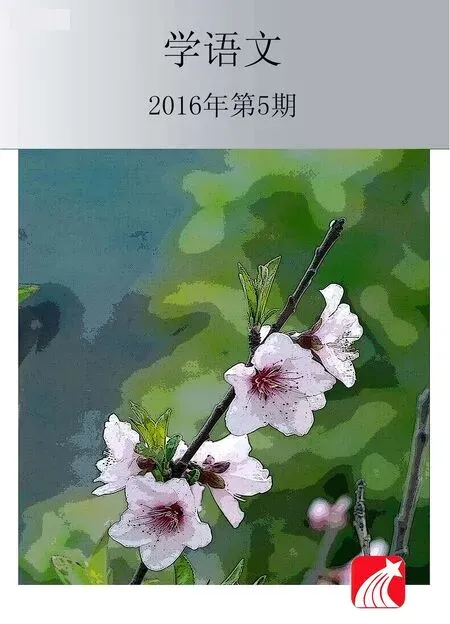《荷塘月色》的比较解读
——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2016-03-02刘彦青
□刘彦青
《荷塘月色》的比较解读
——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刘彦青
朱自清《荷塘月色》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两篇名作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均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愁绪,注重画面感的营造,凸显抒情主人公的身影,创设意境的空灵之美等。由两部作品的对读,可以更好地体悟《荷塘月色》这部现代散文包含着古典之美。
愁绪;画面感;抒情主人公;空灵
作为学者,朱自清在古典文化研究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中学教育对他的涉及只是简单局限在 《背影》、《荷塘月色》这样的现代散文局面,教学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选文教育容易使学生忽略作家人生经历、思想状态以及作品整体艺术特点的分析。朱自清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自然影响到散文创作。这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必须涉及的问题。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对《荷塘月色》的分析解读更多落在作品思想与艺术特点方面,而教材要求背诵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一大段落,又体现出对修辞手法学习的功利化。我们说有 “匠人”,有“大师”,忽视整体上对美感的把握,只强调具体的学习,固然是初步要求,但我们却要冒着培养“匠人”的危险。语文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代表,其特殊性在于把握具有美感的艺术形式,而直接的教育效果就是学生对美感的体悟,以及由此获得的心灵陶冶。
将朱自清《荷塘月色》与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进行比较,或以此为切入点对朱作的古典情愫进行整体把握,让学生在学习现代散文时享受古典之美,并由此展现一种文化的传承,很有必要。
我们先试看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中表现的思想,展现的艺术境界,与朱自清《荷塘月色》异曲同工。
一、挥之不去的愁绪
《荷塘月色》开篇便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种“不宁静”便是一种“愁绪”,首先点出内心的不宁静或者忧愁,交代了出行的原因,《荷塘月色》简单地讲就是“我”因心里不宁静而出行,欣赏荷塘月色的美景,由此联想古时采莲美景。但如果仅仅如此理解,文章也不会有那么大魅力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去体味作者欣赏美景的角度,联想事物的方式。
学者对“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分析很多。联系作品创作时间,即1927年7月“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朱自清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教书,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他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在稍后的《哪里走》一文中朱自清谈到他“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于是开始研究“国学”。《荷塘月色》有他“对白色恐怖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苦闷,也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乱世无奈的叹息。但造成他内心苦闷的并非单方面原因,文中两次出现妻子身影:“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作者口吻虽平淡,但可以看出“妻”对“我”是隔膜的。社会现实给他压力,身边又无倾诉的知己,可想此时的朱自清是何等孤独。
其实教师在授课时无需对愁绪原因作过多解读,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从愁绪入手,认识到笼罩在文中的情感基调是苦闷与忧愁。作者试图通过出行而排遣忧愁,但结果并不理想。
这也是苏轼《卜算子》的情感基调。据史料记载,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六年(1083)初,苏轼贬为黄州团练时。“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大量作品表现出乐观旷达的风貌,但深藏在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卜算子》中夜深人静的“幽人”独往来的原因当然也是苦闷忧愁,下阕直接点出“有恨无人省”,即无人懂我的忧愁,我为此更加苦闷。“幽人”也是因为忧愁而出行去排遣,恰如朱自清的夜行。这便是两者的共性,无处倾诉的苦闷情怀,知己难求的郁闷,这是古典文学常见的主题。
二、视觉上的画面感
《荷塘月色》的视觉效果由“月光”“荷塘”“荷叶”“荷花”“流水”“杨柳”等物象群组成,这些物象借助作者连喻、拟人、通感等巧妙高超的修辞手法,如一副水墨画一样,带给读者直观的视觉体悟。一部分是地上之景,一部分是天上之景,“月下荷塘”与“荷塘上的月色”两者所写的角度不同,直接着眼的物象也不一样,但两者互为背景,相互映衬,水乳交融。
《荷塘月色》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虚实相生,对荷塘的描写,作家采用了大量修辞手法,如将出水的荷叶比喻为“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荷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将光与影的交织比作“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树色“乍看像一团烟雾”,树缝里漏着一两点昏暗的灯光,被作者喻为没精打采的“渴睡人的眼”等等,这些巧妙生动的比喻以一种虚拟化的方式,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审美空间,展示出一幅清晰的画面。
再看《卜算子》,“缺月”“疏桐”“幽人”“孤鸿”“寒枝”“沙洲冷”这些物象群同样构建出来一种凄清孤冷的画面,限于字数,虽没有像《荷塘月色》那样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但是词人精心炼字使这首词的画面感凸显出来。“缺”字在描写月残缺的同时也写出了夜的昏暗,“疏”字以梧桐树枝头稀疏的叶子暗示了这是一个秋夜,“幽人”与“孤鸿”写出了人与鸟的形单影只,内心也定然是孤单寂寞的。“寒”与“冷”再次点明深秋,而寒冷的除了天气,还有无人理解的内心世界。词人选用的全都是冷色调词,展现的是冷色的画面,词人心境也得以呈现。
三、作者身影的凸显
两篇作品都出现了作者的形象。散文与词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自己。《荷塘月色》里的“我”便是朱自清,夜幕降临,他一个人出行,这种行走是为了排遣愁绪,文中清晰地描述了出行路线:“沿着荷塘”、“小煤屑路”、“荷塘的四面”,直至回归。此外,景物的描述方式,以及江南采莲的追忆,都展示了作者的心情。可以说《荷塘月色》中“我”的身影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中和、含蓄、内敛的特点,他的苦闷包括家国情怀、知己难求。作者对景物的观照视角在动与静之间,在细微之处,在宁静的夜里,也在对典籍的追忆中。再配合典雅的语言,娓娓道来的独白方式,使得作品散发出古典之美,体现着传统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诉求。
《卜算子》同样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同样有“幽人”独自在夜里出行,而与幽人相伴的便是那只“飘渺”的“孤鸿”。寒夜也因一只单飞的大雁而愈加幽静,幽人也因这只大雁而显得愈加孤单,因“孤鸿”的出现而使主人公形象更加凸显,乃至读到“拣尽寒枝不肯栖”时,我们甚至怀疑,这里具体指的究竟是谁?或者说本就没有“孤鸿”的存在,只是词人——幽人孤单内心的外化物,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也就理解了“飘渺”二字。虽然“有恨”但是“不伤”,全词充溢着古代文人“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韵味。
四、意境上的空灵之美
两首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境界是一种空灵之美。构成此种美的要素有二:黑夜的宁静和主人公的孤单。夜的宁静并不是死一般的寂寞,《荷塘月色》虽然是夜晚,“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脉脉的流水”、“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这些都以一种灵动的形式丰富着夜的宁静。换句话说,正是它们的存在,夜才愈加显得寂寞。同样《卜算子》中也是月与梧桐叶组成的光与影和谐的旋律,还有孤单大雁飘渺飞翔的身姿……正如唐人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除此之外,《荷塘月色》最后对江南的追忆,对《西洲曲》和《采莲赋》句子的征引,那“嬉游的光景”,给读者的是一种时空错位之感,以“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一句,将现实中的“荷塘月色”与古时采莲场景联系。现实中的美与诗歌中的美,此时的美与古时的美,两种时空场景的交融展示,强化了艺术上的空灵之感。
与环境的宁静相对照的是人物内心的 “颇不宁静”,这与夜色的宁静之间的强烈反差。两首作品的节奏都显得比较缓慢,我们称《荷塘月色》为一篇经典的“独语体”散文。它内敛的叙述方式,并不企图去与倾听者进行交流,只注重自己内心孤寂苦闷情怀的表达。孤独感与荒凉感并不妨碍作品的空灵之美。《卜算子》也就算是一首“独语体”词,“幽人”作为词人自称,他苦闷的内心并未在宁静的夜色里寻找到片刻安慰,结句“寂寞沙洲冷”将词人内心的孤独感与环境的荒凉感强化,展现出时空上的空灵之美。
[1]朱自清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1996年。
[2]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1991年。
[3]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编 潘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