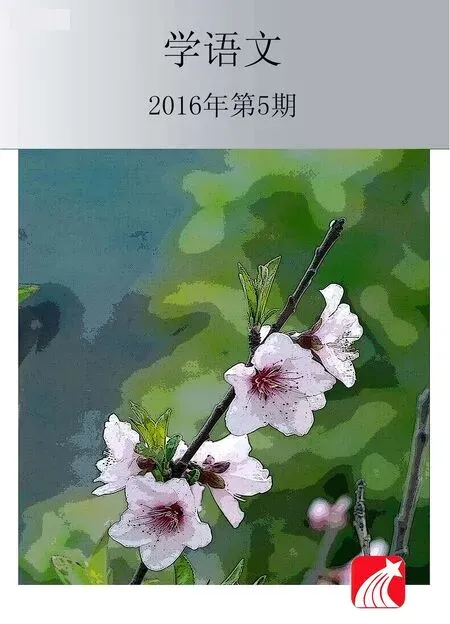一次灵魂的救赎
2016-03-02张光华
□张光华
一次灵魂的救赎
□张光华
文章从三个视角呈现了作者对拉三轮老王的认知过程:最初作者自恃条件优越,对老王给予的同情完全出于俯视下的关怀;后来老王抱病送来香油和鸡蛋,“直僵僵”的形体令作者震悚;几年后,作者渐渐明白了老王期盼亲情与温暖,却被自己忽略,进而产生愧怍,既是认识到老王朴素的道德自觉后的愧怍,更是面对老王自然守护朴素道德的愧怍。
同情;震悚;愧怍;救赎;悲天悯人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文章,记叙了作者自己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片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荒唐动乱的年代,作者夫妇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杨绛对老王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漫长过程,最终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自我救赎。
一、俯视下的同情
正如文章所言,起初作者和老王只是一般的顾客和车夫的关系,“他蹬,我坐”,所不同的是并非一路上互不交流——闷头坐车和埋头拉车,而是“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正是在“闲话”里,作者知晓了老王的穷——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老王的“失群落伍”——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他成了单干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杨绛很清楚“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指的是什么,北京解放后,在1956年全国倡导的“公私合营”大背景下,要求把各个行业的人都组织起来,反对私营,反对单干,后来因为要彻底地反对所谓的“阶级压迫”,不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三轮车就被取缔了,这对老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老王的眼睛瞎了一只——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居住条件差——一个荒僻的小胡同,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也是在“闲话”里,作者让我们感受到了老王生活的“苦”。在现代汉语中,最走投无路、最孤苦无依的一个汉字就是“只”字,作者在文中五处运用“只”字,具体准确地写出了老王孤苦伶仃、生活艰难的生存状况。“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老王只有一只眼。”“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他只说:“我不吃。”那是中国一段荒唐的历史,可是对生活在其中的老王或者是杨绛都是逃不脱的生存环境。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阻止老王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愿意给我们带送”冰块,车费减半,显出老王的老实厚道;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透露出老王的心地善良。老王的知恩图报还表现在,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
以善良去体察善良,作者杨绛无疑是用心的,也是真诚的:照顾老王的生意,坐他的车;老王再客气,也付给他应得的报酬;老王送来香油鸡蛋,不能让他白送,也给了钱。作者的善良还表现在关心老王生活,三轮改成平板三轮,生意不好做,作者关切地询问他是否能维持生活。作者的女儿也像她一样善良,知道老王有夜盲症,送给他大瓶鱼肝油。
联系一下背景,我们很清楚当时杨绛的处境状况:“文化大革命”爆发于1966年,当时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收到了残酷迫害,钱锺书、杨绛夫妇此时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挂木板,受批斗,剃成阴阳头,被驱赶到大街上游行,最后被发配去扫厕所……经受了漫长的苦痛折磨。作者曾在她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道:
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时,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戴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办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一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要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由此看来,当时老王在困顿中表现出善良不容易,作者在艰难时关心老王也实属不易。让我们感受到是两个不幸的人彼此间的关心。
但与老王的真诚相比,起初作者的关心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老王,是保持着一种距离和老王交往;她对老王的同情是不彻底的,她的善良是有保留的。在这种关心、同情里面,多多少少潜藏着自己幸运的意味:自己不那么穷,自己是健康的,自己不孤独,自己不倒霉。言语举止间表现着一种俯视老王的姿态。
二、平视中的震悚
情节发生转折的是老王抱病给我们送香油和鸡蛋的时候。作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老王的关系。文中五处“直”字的运用,具体准确地写出了老王病入膏肓时的生命状态。“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客观准确地写出老王重病状态下的没有活力和生气;“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作者的重复“直僵僵”是在“瘦”之后,程度更深。“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此处的“直”写出了老王无法弯曲迈步的样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和上一处一样,“直”写出了老王下楼时的艰难。“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直僵僵”身影预示着老王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为下文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
这五处“直”字详写了老王在去世前给“我”送香油、鸡蛋的过程,正是因为老王行动虽然如此困难,但还是坚持要来送东西,更能表现老王的善良和他知恩图报的品质。可“我”呢?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们完全可以揣度一下老王此时此刻真实的内心:杨先生啊,我的鸡蛋和香油真的不是来换钱的啊!你看,我都这样子了,还能活几天呢?我这样的一个人要钱还有什么用呢?我就是想把自己一点最值钱的东西留给我最亲的人啊!可我知道,我不配有这样的心思,你们都是有大学问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可我呢,一个一字不识的粗人,一个名声不好的拉三轮车的人。你们两位不嫌弃我,钱先生肯坐我的车,我知道就是看得起我,就是同情我,是高看我啊,是照顾我啊。可是,杨先生,钱先生,我还是要在心里叫你们一声亲人啊!
无独有偶,文章前面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细细体会:
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为何老王哑着嗓子悄悄一句“你还有钱吗”能让杨绛先生记忆多年?这是因为杨绛在现实里看到的如老王般的“老王们”多已狂暴,而老王却成了那个时代最稀缺的良善。老王对杨绛一家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心细如发的尊重,而这种关心和尊重,正是老王心灵深处最伟大的善良:一个不幸者对另一个不幸者人格的尊重、尊严的保护。老王说“我不是要钱”,但最后还收了钱是因为老王怕“我”真的托人给他送钱,平白给“我”添麻烦。所以多年之后,当愧怍感折磨杨绛时,当杨绛提笔准备记述老王时,就是这种原始般的朴素,让杨绛再看到的老王已经不仅是那个善良、富有同情心的老王了,杨绛透过好人老王看到了普通人群中悲天悯人品格、质朴道德情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杨绛先生通过老王还看到了这样质朴的存在对道德崩塌的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平视中,杨绛看到了眼前这个老王“直僵僵”的形体,藏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令她肃然起敬,以致多年以后依然记忆深刻。
三、仰视里的愧怍
作者多年以后,提笔写老王,她发现与老王相比,自己是自私的,自己的善良不如老王那么纯净。于是用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看老王,字里行间倾注着无限的情感。
别人的眼里,老王没有感受到怎样的温暖,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瞎掉了一只眼”是不幸的,本该赢得别人的同情、关心,可是这样“恶毒”的揣测——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关怀也没有,有的就是这样戳心窝子的冷言冷语。幸亏杨绛不是,才使得老王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作者连用了两个“也许”,来揣度老王瞎了一只眼的原因:“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无关乎品行,只剩下不幸;“得了恶病”而瞎了一眼,是“更深的不幸”。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感受到不幸,换位思考,这就是“同情”的逻辑。
“呀,他什么时候……”
这是老王的邻居老李提起老王死去的消息时作者的应答,后面的省略号,没有把“死”说出来,回避这个词,这可能是她愧怍的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杨绛害怕给老王增加负担,老王年老体弱,载钱锺书已很吃力,不忍心给老王带来更大负担。就去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林筱芳曾这样评价杨绛的文学语言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更值得玩味的是下面这句话: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明白”表达一种立体自觉,而“渐渐”则表明这一自觉的过程相当迟缓,相当漫长,相当深刻。以庸常的眼光看,杨绛完全没有必要“愧怍”。她在物质上没有亏待老王——“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钱”;在精神上也体现出对老王足够的平等和尊重——“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不因收入,地位上的差异而俯视老王,倒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另外杨绛明明也是不幸的,为何要说自己是幸运的人?她愧怍什么?
阅读杨绛的人都知道,杨先生对“文革”记忆的情感表述历来隐忍和节制,文中,她不写那时北京街头的疯狂,不写那时群体干出的最恶劣的极端勾当,她只写好人老王的朴素。那么这篇文章只是想告诉我们仅仅是一个好人老王和另一个好人杨绛吗?其实杨绛的思考是深刻的:与“老王”们比,作者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没在最困顿的物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与同时代的“杨绛”们比,她也是“幸运”的,因为运动过后她毕竟还活着。但“幸运”的定义在杨绛先生那里显然不是指一个人能够存在于世上,能够不像“老王”般为活命苦苦挣扎于这个世界。“一个幸运的人”实在是杨绛先生生存于对照下的安慰与感慨,这是先生对那个时代的反语。她为何“愧怍”?——老王想在最后的人世告别中获得家庭般的温暖和亲人般的关照,这种感恩与渴望亲情的复杂心理当时被杨绛忽略了,等到老王孤独甚至有些凄凉地离开人世后,杨绛才突然意识到这些而顿感“愧怍”。由此看,杨绛的“愧怍”就不仅仅是多年后明白了老王期盼亲情与温暖而不得的愧怍,而是认识到老王朴素的道德自觉后的愧怍,更是面对老王自然守护朴素道德的愧怍。杨绛先生的“愧怍”既是对道德担当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整个社会道德状态的忧虑和批判。
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下,在杨绛的生活视野中,在她的苦闷与忧虑中,老王就像一棵荒原上的树一般以最自然、最坚忍朴素的态度存在着。当杨绛有一天看到了这种存在的意义,这种来自草民阶层的朴素的道德自觉和对道德良知的坚守对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出于作家的使命,她要表现一个善良、正直、孤独、让人甚感其凄苦的老王,但她更要表现一个朴素的伟大的存在,她特别要传达自己从这样的一个“存在”中看到民族道德良知依然存在时的感动与灵魂受到的鼓舞。
在那个良知与道德普遍匮乏的时代,作者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底层依然有像老王这样的人在静静地坚守道德与良知。作者的“愧怍”就是对老王的敬仰,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灵魂的救赎,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待苦难人们的悲悯情怀,彰显了她敢于自责、深入思考社会的精神,是她人性光辉的所在,也是本文最富有内涵的意蕴所在。
[1]魏本亚、尹逊才:《十位名师教〈老王〉》,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
[2]《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上册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
[3]刘建春:《妙语引导学生探究》,《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1年第2期。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江淮学校)
[责编 潘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