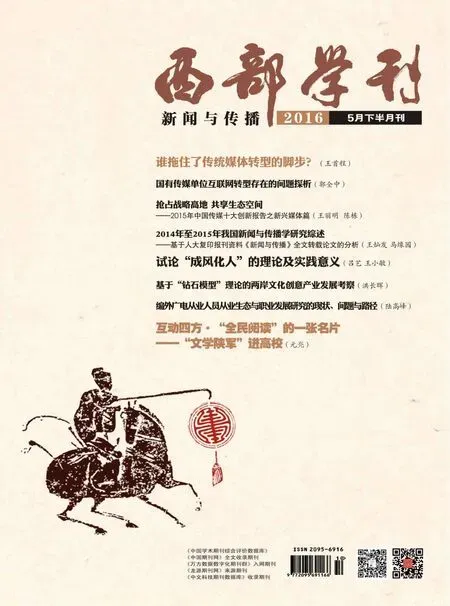从“想象”到“参与”:社交媒体与场景共同体
——以春节微信红包为例
2016-03-01王军峰
王军峰
从“想象”到“参与”:社交媒体与场景共同体
——以春节微信红包为例
王军峰
摘要:本文分析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社交媒体提供了何种技术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又是如何使得共同体建构的方式由“想象”到“参与”转变。同时,提出了“场景共同体”这一概念,以春节微信红包为个案来论证微信红包是如何以春节为“场景”,以社交媒体(微信)为平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用户)的参与和互动,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最终形成以“场景”为主的“场景共同体”的。
关键词:想象;参与;社交媒体;微信红包;场景共同体
引言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媒介又塑造着社会的形态。媒介技术及其使用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1]33对此,郭庆光教授指出,所谓媒介即讯息是说,任何一种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最重要的并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作为一种技术,其为社会发展开创的可能性。[2]118而正是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为社会成员通过媒介参与社会形态的塑造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
就媒介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媒介本身作为一种参与社会现实建构的力量,其为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当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3]一书中提到所谓民族只不过是一种通过印刷媒介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论述了“共同体”和传媒之间的关系:传媒是共同体得以产生的手段和路径,传媒通过自身的力量,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共同体”形象,而这种“共同体”建构的方式是通过“想象”。这种人为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无疑给人们提供了看待民族概念的全新视角。[4]73但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新的媒介造就的新社会形态,必然深刻影响着传统“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方式。[5]35本文分析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社交媒体提供了何种技术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又是如何使得共同体建构的方式由“想象”到“参与”转变。同时,提出了“场景共同体”这一概念,以春节微信红包为个案来论证微信红包是如何以春节为“场景”,以社交媒体(微信)为平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用户)的参与和互动,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最终形成以“场景”为主的“场景共同体”的。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提出
(一)关于“共同体”的文献综述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目前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主要从共同体建构方式和共同体类型两个维度进行:一方面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来看,以社会学家滕尼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共同体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6]15例如,滕尼斯将共同体称为“礼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我们”或者“我们的”意识,而成员之间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传统为纽带进行维系的。[7]340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建构论学者则认为,共同体是“人为建构”的,是想象的。他认为共同体就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4]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论述道: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以小说和报纸等印刷媒介为其形成的条件,而小说和报纸则为其形成提供了路径。[8]102而中国学者雷蔚真和丁步亭则认为,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共同体建构的方式将从“想象”到“行动”。而这一转变的出现是由于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造成的。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传媒会影响到传统的以印刷媒介为平台形成的建构共同体的方式,“在这种信息化资本主义以及电子媒介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依托于印刷科技的想象的共同体面临着瓦解与重建”最终导致网络媒介中的“共同体”进一步与传统的“想象的共同体”分道扬镳。[5]本文则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往的媒介构建共同体的路径和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介的发展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新的平台和新的方式。关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由最初的“自然而然”到“想象”再到“行动”“参与”和“互动”。
从类型来看,目前关于共同体的定义主要将其分为地域性类型(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和关系性类型(宗教团体、种族、社团等社会关系和共同情感),[9]20同时,功能性共同体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就地域性类型的共同体来说,最主要的学者当是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帕克对共同体和社区的英语词汇“community”的解释为: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三是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0]20这强调了共同体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以及成员对地域的依附性。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别从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共同体的类型。例如,涂尔干用“机械团结”表示共同体。韦伯在论述家族共同体的时候指出,家族共同体是在严格的个人尊卑关系基础上形成的。[10]706此外,功能性共同体也在近代诞生。功能性共同体主要强调它的功能性而不是结构性。[9]这种类型的共同体主要有科学共同体[11]60、法律职业共同体[12]76和知识共同体[13]123等。本文试图进一步提出“场景共同体”概念,主要用于阐释基于某种“场景”的具有一定社会参与和互动关系,以及具有共同情感、价值观念和信仰等因素的成员而形成的共同体。
(二)“场景共同体”概念的提出
“场景”是传播主体进行传播活动的空间和外部条件。传播主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都要受到场景的制约,因此,场景则构成了他们进行传播活动的“心理场”。[1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的意义大大增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15]20就场景本身来看,在新媒体时代,场景可以被分为实体场景和虚拟场景。前者主要的形式是事件(包括仪式、习俗、民俗、节日和具体的事件等),后者则主要是指网络虚拟空间中形成的场景,比如游戏中的场景。本文论述的场景主要是指“事件”场景,比如春节作为一种文化习俗(民俗)和节日的场景。因此,这些场景一方面为传播主体的活动提供了活动空间和“心理场”,另一方面,基于场景的服务和活动本质上都是对“用户”(社会成员)的服务。
基于场景在社交媒介时代的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场景共同体”这一概念,试图认为,它是指因场景的产生(出现)、发展、消失而产生(出现)、发展、消失的基于社会互动关系和共同情感、价值、立场、观点或者信仰等因素而产生的文化或行动共同体。
就场景共同体本身来讲,它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三点:场景本身、因场景而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以及共同情感、价值、立场观点等,它既可以出现在场景产生之前,也可能因场景产生及其共同体的形成而强化。具体来讲,就场景本身而言,场景是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它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也为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的产生以及共同情感、价值和立场观点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就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而言,它一定是因某种场景的存在而存在,因其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可以说,没有某种场景,那么这种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就难以产生。就共同情感、价值、立场和观点来看,一方面,既存的共同情感、价值等因素因某一场景的出现而被触发,为场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心理指向;另一方面,某一场景的出现以及在该场景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反过来又会强化这一既存的共同情感、价值和立场观点等。
同时,就场景共同体本身的特点来说,因为其依赖的前提条件是场景本身存在,而场景本身并不是一个持久的存在物,这一点对于事件类场景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它又具有临时性特征,它随着场景的消失有可能消失。但是,当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这种临时的“场景共同体”就可以被重新唤起。因此,场景共同体是一个能够召唤“集体记忆”的共同体。例如,因春节而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随着春节的结束而消失,在下一个春节又重新形成;因环境事件这一场景而形成的共同体,如PX项目引发的民众行动共同体随着危机的解除而消失,但是当下一场类似的危机出现时,这种共同体又会形成,并且因为上一次危机而产生的集体记忆又在下一次危机中被重新唤起。
值得注意的是,“场景共同体”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具体形态实际上本身并不是为移动互联网的产生而产生,最早的场景共同体是由原始社会巫术、祭祀等类似的仪式场景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情感和文化信仰的共同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则成为最具有组织性和规模性的场景共同体。而当代社会,除了仪式性的场景形成的场景共同体之外,还有诸如因环境事件而形成的特殊场景共同体。本文旨在论述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为这类“场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互动平台。在这样新的媒介环境下,社会成员是如何通过参与和互动而非想象的方式,在场景这一因素下促成共同体的形成的。
二、从想象到参与:社交媒体对共同体形成机制的影响
从媒介技术变迁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产生都将影响到媒介形态的变迁,也会影响到人对社会(共同体)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和参与的结果。就“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来看,其随着媒介技术本身的不断演变而呈现出从“想象”到“参与”的路径。
社交媒介对共同体形成机制的影响来看,也是如此,社交媒介的产生为共同体形成从“想象”到“参与和互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考量这一技术上的可能性,需要将社交媒体提供的可能放置在传媒与共同体形成机制演变的脉络中。就社会共同体本身的形成来说,大体上有三种方式:自然而然的生成、(通过媒介)“想象”、(通过媒介)参与和互动。这表明,媒介技术的变迁也会影响到人对社会(共同体)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和参与的结果。
就前媒介时期,共同体主要是依靠血缘、地缘或者伦理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大部分有面对面的交流,个体成员能够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而感知其他成员的存在、情感等。在这一阶段形成共同体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地缘等天然的产物,媒介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着社会本身规模的不断扩大,通过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已经难以形成更大的共同体,这时候,媒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通过印刷媒介提供的信息,社会成员通过“想象”的方式进行身份认同,他们想象着其他成员的存在方式,以自身的情感、信仰等体认其他成员,从而形成共同体。例如,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大量印刷出版的小说和报纸提供了这种阅读与再现。[8]此外,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在形成共同体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媒介成为形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而通过媒介的“想象”则是成为形成共同体的重要机制。
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移动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场景”这一资源具有了被开发的可能性,任何一种对场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际上都是基于场景的对社会成员的服务。而社会成员总是在一定的场景下活动,由此,场景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新纽带,在场景的连结下以新媒体为主要参与方式和平台的新行为产生。在新的媒介和场景中,传统的通过印刷媒介提供的“想象”建构共同体的方式已经面临着土崩瓦解,新的建构共同体的方式产生。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其技术基础是Web2.0的互动,其思想基础是使用者生产内容。[16]100这为成员(用户)之间的参与、互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就能够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网络虚拟关系的平台,具有突破时空的特性和双向性,它打破了传统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时空的限制,为社会成员通过虚拟网络关系进行互动交流提供了可能。这也意味着,基于以场景为纽带的以社交媒体为平台的,具有成员参与、互动特性的“场景共同体”产生具有新的路径和方式。但是,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只是为其影响人和社会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历史学家怀特所言:一种新的技术仅仅只是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门,但它并不强迫人们必须要进入。[17]141一种新的技术要对现实产生影响,并不仅仅依赖于技术的发明,它需要一系列有利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才能成为可能。[18]123社交媒介的产生只是为共同体建构从“想象”到“参与和互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还和现实的社会需求有着重要的关系。
就社会成员本身来说,这种需要首先表现为交流互动的需要。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这就决定了人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人需要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只有在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人才能够参与社会活动,成为社会成员。同时,这种需要也表现为身份认同的需要。个人只有在和“他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才能将自身放在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中,确定自身所处的位置,形成自身属于某一个群体的观念,这时候“自我的身份认同”才有可能形成。正是人的这种本质的社会性,使得其不断发明创造新的传播媒介,实现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交流互动需求决定了人的参与互动性。而社交媒体本身就提供了交流和互动的可能性。
三、参与、互动及场景共同体的形成:以微信红包为例
就本文论述的以春节(春晚)为主要场景的“场景共同体”的形成来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主要是微信)为其提供了新的参与路径、互动平台;微信红包则具体实现了成员之间参与、互动,这种参与互动主要目的在于以娱乐的方式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而春节(春晚)作为重要的场景,则成为激发社会成员共同情感,连接社会成员参与、互动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形成“场景共同体”的一种外部机制。
(一)以春节(春晚)为主要场景的纽带作用
任何一种媒介,其发挥作用一定是与现实条件相关联而产生的。社交媒介引导成员的参与、互动最终形成共同体也一定是和现实场景相关联的。而场景,一方面为社会成员的互动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场景又规定了在场景中的社会成员和行动者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认同、价值立场和观点信仰等深层次因素。春节(春晚)就是这样的场景。
从时间的维度上讲,春节本身是旧时间的结束和新时间的开启,它蕴含着人们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人们将自身的活动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内,形成一段时间内大范围的交流和互动。同时,从空间上看,春节作为一种习俗、一种节日和一种文化仪式,它起到的是在空间上对社会动员的作用。而这种社会动员的力量在于春节尤其是除夕意味着一年四季出门在外的人能够回家,意味着团圆。而分属不同地理空间的人们无论多远,回家团聚总是一种期盼。在这样的文化场景下,大规模的人口空间活动得以实现。
从春节场景本身所具有的规定社会成员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立场的角度看,春节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具有一种感召力量,它召唤所有的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的人(中华儿女)从天南地北回到家中,同时也回归、参与这一场民族共同的仪式。而作为个体,受到春节这一文化场景的召唤,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比如,远方的人回家、购买年货、送红包或者亲朋聚会。这些具体的行为都因为春节这一场景而成为可能。因此,一定程度上,作为场景的春节实际上作为一种纽带,调动了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同的中华儿女的参与和行动。而这也为社交媒体在这一场景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外部条件。
(二)微信红包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引导用户参与互动
在以春节为场景的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春节微信红包主要是以微信这种社交媒体为平台进行传播,从而引导社会成员参与互动,最终通过以娱乐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习俗)和共同情感的体认实现场景共同体的。
1.社会成员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人们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的特点上,而如果是研究者,就应该看到这一新事物与旧事物的联系及其环境的变化对人或事件如何发生影响。[19]3而微信红包就是这样一个新事物。但是,微信红包又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新事物,它是以新的传播技术为依托,以春节为场景对传统春节文化元素的开发,而这有利于激发用户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情感的延续。由此,用户即使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处于一个“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
例如,在传统的春节中,送红包是一种习俗。现今的“压岁钱”在古代传说中是镇妖祈福的压“祟”钱,到明清时候则成为用红色绳子串起来的铜钱,民国时候开始用红色的纸包裹,而现在,红包出现在除了春节之外的更多的场合,例如结婚、孩子满月、生日、乔迁新居等等。在送红包交往活动中常常蕴含着长辈对晚辈、朋友之间和同乡之间的美好祝愿。而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微信红包则是对传统红包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这样依据新的传播平台社会成员依旧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参与和体认。例如,依托微信平台,微信红包的派送突破了时空限制。无论是身在何地,只要有网络,只要微信账户有钱,就可以为你联系的任何人派送红包。由此,社会成员通过对微信红包的使用,使得其进入到传统的面对面送红包的春节场景中。
2.参与和互动:微信红包的技术设计以及平台的互动性。就微信本身在春节这一场景中的表现来看,其作为社交媒介进行的微信红包传播活动更多的是一种仪式,而非传递信息。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20]28,在这种“神圣典礼”中,社会成员被微信红包以“共享”“互动”“游戏”等方式纳入其中,形成基于文化场景的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微信红包的技术特性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就微信红包本身的技术特性来看,其产品简单易用,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用户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开微信红包,选择普通红包或者拼手气群红包,设置红包个数和总金额,然后将其推送到相应的个人或者微信群中就可以了。至于收红包,更简单,只要点开,然后拆开红包就可以完成。这种简单易用的产品特质使得任何有兴趣使用微信红包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其中。社会成员在参与的过程中,实际上是重复着以往的以面对面进行的红包派送和接收的体验。在这种重复体验中,社会成员获得的是共同的关于红包的记忆和情感。
其次,微信红包也具有社会特性。其中,最具有参与性、娱乐性和游戏性的是拼手气群红包。拼手气抢红包不仅仅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仪式。红包用户只需要设定总金额和红包个数,至于谁抢到多少是通过随机分配进行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却调动了用户的参与性。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同时也是一个“人品”和“手气”比较的过程,每一个参与的用户都会因为自己抢到红包的大小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变化。同时,用户也有可能将自己抢红包的结果分享出去,使得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样,微信红包的“抢”“发”以及“晒”实际上是对传统的面对面送红包和收红包这一春节行为和仪式在移动社交媒体中的延续。这在增加社会成员(微信用户)的活跃度、参与性和互动性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形式的认同,是对收发红包产生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的体认。因此,从这一场景来看,社会成员在发送微信红包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体认和共享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仪式、一种文化、一种与族群、社会、共同体的精神沟通”。[21]70
再次,微信红包与春晚相连接,形成了全面参与、互动的共同体。微信红包通过和春晚联合,实现了跨屏互动。这种互动方式,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成员对春晚这一场景新的参与途径和方式,而这种途径和方式又提高了成员的参与度。根据著名艾媒咨询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手机网民参与“春节红包”活动调查报告》显示,在这次春节红包大战中,受访手机网民76.4% 参了微信红包活动,61.3% 参与了手机QQ红包活动,57.2% 参与了支付宝红包活动。[22]这说明,大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微信这一社交媒体参与到春晚这一场景中。与此同时,微信的“摇一摇”功能为社会成员参与春晚实现互动提供了“入口”。只要用户通过微信“摇一摇”就能够参与到春晚中,根据统计,微信在央视春晚的直播活动中通过“摇一摇”功能总共发送高达5亿元的微信红包,尤其是在22: 30,“摇一摇”红包发送达到了最高峰——1.2亿个红包,这是2014年除夕夜峰值的4800倍!而总次数的峰值达到8.1亿次/分钟。[23]这都表明了社会成员通过微信而达到的对春晚的深度参与。在这种深度参与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强化了自身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通过跨屏互动参与到春晚的场景中,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相似性又强化了成员之间的身份、文化和情感认同。
总结
在社交媒体时代,场景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这使得场景作为形成共同体的纽带作用凸显。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关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开始从“想象”到“参与”和“互动”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交媒体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路径、方式和平台。社会成员正是通过社交媒体这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工具以参与、互动的方式,形成对共同体文化和共同体成员之间情感的体认,最终形成以场景为纽带的“场景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美)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高小岩.“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困境与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1).
[5]雷蔚真,丁步亭.从“想象”到“行动”:网络媒介对“共同体”的重构[J].当代传播,2012(5).
[6]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杜全生,韩智勇,周延泽,高瑞平.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0).
[7](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段宇晖.互联网时代“想象的共同体”的祛魅——兼论民族主义建构的困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9]李慧凤,蔡旭昶.“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J].学术月刊,2010(6).
[1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1]文学锋.试论科学共同体的非社会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3).
[12]张一鸣.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与反思[J].理论观察,2010(1).
[13]曹云华,周玉渊.知识共同体方法及其局限[J].河南社会科学,2009(2).
[14]冯炜.社会场景:传播主体的心理场[A].张国良,黄芝晓.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暨CAC/CCA中华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5]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新闻记者,2015(5).
[16]王贵斌,(美)斯蒂芬•麦克道威尔.媒介情境、社会传统与社交媒体集合行为[J].现代传播,2013(12).
[17]吴廷俊.韦路.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18]崔林.变革动因与背景范式——对互联网与印刷术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的比较[J].现代传播,2014(5).
[19]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0]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1]姜红.“仪式”“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的建构——另一种观念框架中的民生新闻[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
[22]艾媒咨询.指尖上的春节——2015年中国手机网民参与“春节红包”活动调查报告[EB/OL]. http:/ /www.iimedia.cn/38649.html,2015-02-25.
[23]许意强.16亿次微信和QQ红包,如何飞起来?[N].中国企业报,2015-03-03(18).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4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5-2-00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