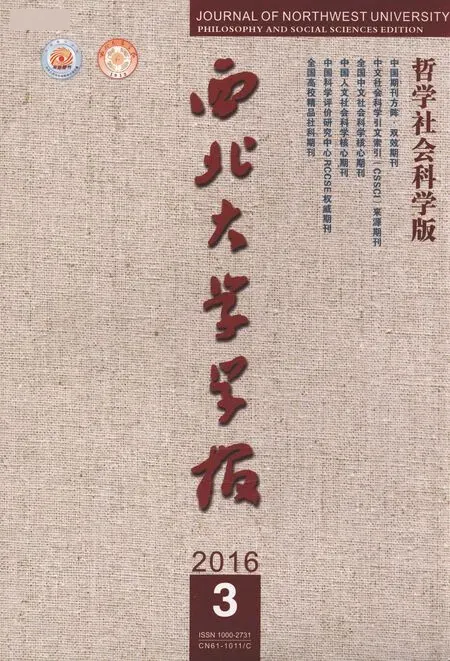历史文本的符号学阐释
——论德拉-沃尔佩对克罗齐美学观的批判与超越
2016-02-20张碧
张 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文学研究】
历史文本的符号学阐释
——论德拉-沃尔佩对克罗齐美学观的批判与超越
张碧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710127)
摘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德拉-沃尔佩在检审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观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结合符号学方法,从“历史”维度的文学观、隐喻观和文体论角度,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性阐释,从而使得20世纪意大利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超越。
关键词:德拉-沃尔佩;克罗齐;美学观;批判;超越
在西方近现代美学史上,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以其“直觉主义”等哲学表述而著称于世。大致在同一年代的略晚时期,意大利“科学马克思主义”代表、美学家伽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在其文学、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广泛借鉴了意大利文化传统中的一系列思想遗产,并由此逐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
在20世纪前半叶的相当长时间内,克罗齐都以其“直觉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主导着意大利哲学、美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同时,德拉-沃尔佩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对意大利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式改造,其中,消解意大利美学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便尤为重要。在此情况下,德拉-沃尔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及科学批评方法,直面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美学。德拉-沃尔佩多次直接批评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倾向,在事实上将克罗齐的相关观念作为理论反题,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式的批判。同时,对符号学的运用,也成为德拉-沃尔佩在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面所采取的重要方法维度。这样,德拉-沃尔佩对克罗齐美学观实现了唯物主义与科学式的超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意大利现代美学发展的旨趣与走向。
一、克罗齐与德拉-沃尔佩的“历史”维度文学观
众所周知,克罗齐继承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衣钵,将精神世界、情感因素视为理解历史及审美对象的基本维度,开创了其“直觉主义”的哲学-美学体系。在直觉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克罗齐形成了与20世纪诸多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的观点颇为接近的、带有浓郁唯心主义色彩的基本历史观。在克罗齐看来,“精神品质”是区别不同历史类型的唯一标准:那种对诸多史实材料进行科学、客观编纂工作的“编年史”方式,只能书写出学究式的历史书写;而真正的历史则由于灌注着生机勃勃的历史精神,因而能够产生出鲜活盎然的美学化历史叙述:“像那些一度含有一种历史思想、为了纪念它们所含有过的思想……一样,那些新生活的表现也仍然被视为先行的和确乎业已消失的生活的残余。”[1](P10)这种对“历史”类型的区分,恰体现出克罗齐对历史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历史的本质,体现为人类蓬勃而强健的精神品格。这种历史观,显然与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把握“历史”的方式截然不同,从而带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特征。
同时,克罗齐的语言观亦与这种观念一脉相承,认为语言决不仅是毫无生气的物质性实存,而是被赋予人类精神生活灵秀之气的产物:“语言……属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种种爱好中的一种,是人的欲望、意愿和行动、习惯、想象力的飞腾之一种。”[2](P52)由于文学以语言为基本表达媒介,因此克罗齐的语言观直接表现出他对文学和历史的逻辑关系的阐述。事实上,与近代以来多数历史主义文论家一样,克罗齐同样认识到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艺术类型与历史间的紧密关系:“不去考虑同说话有关的体制和习俗方面发生的情况,以及其他一切体制和习俗,那是不可能的。”[2](P53)值得注意的是,克罗齐尽管认识到文学与作为风俗、体制的“历史”息息相关,却由于将文学和历史一并视为精神生活的产物,从而忽视了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换言之,与被其称为“实证主义”者的传统历史主义思想家、文论家不同,克罗齐拒绝以科学理性的认知方式,从具体历史现实维度来审视文学、文化现象,而是由于将历史与语言、艺术等文化表征都不加区分地视为“精神生活”的产品,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融化到文化和文明历史中去的条件下,语言学才能变成为历史。”[2](P54)就艺术而言,“音乐作品、戏剧、诗歌,在它们被阐释之前什么都不是”[3](P166),作为符号的艺术品诚然具有浓厚的精神、情感因素,而克罗齐认识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诸多文化现象与历史间的联系,也自然无可非议;然而,由于将所有文化现象与历史不加分析地归结为抽象的“精神生活”,从而无法有效分辨出历史与诸多文化现象间转换关系的具体属性及实质,也未能对不同文化现象的个体属性及特征进行有效阐述。因此,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克罗齐的批评方法实际具有“反历史化”(de-historicize)倾向[4](P263)。
与克罗齐对“历史”概念的审美式理解相比,德拉-沃尔佩的认识大相径庭。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拉-沃尔佩认为,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对文学、文化现象的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客观地讲,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内部,对“历史”概念的界定彼此殊异,但德拉-沃尔佩明确将“历史”的本质界定为与特定时代经济基础相应的社会状况,并因此十分注重考察由经济基础所相应决定的特定意识形态。这样,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现象,作为与特定历史状况相应的意识形态产品,便必然是对经济基础的某种隐含的表达;换言之,经济基础所派生的意识形态,必然通过某种特殊机制转化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艺术话语。因此德拉-沃尔佩提出,只有将对特定时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考察作为基础,才可能通过对文化现象透视,来洞悉蕴于其中的历史特质。
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一道,德拉-沃尔佩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具有明显“科学主义”倾向的代表。在他看来,马克思从一开始便将知识的形成界定为反对神秘化(mystified)的科学性辩证法(scientific dialectic)的产物[5](P183-184)。较之同时代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德拉-沃尔佩更重视对由历史所派生的意识形态向文学、艺术形式的科学转化机制的描述与阐释,德拉-沃尔佩称这一机制为“语义的辩证法”,从而与克罗齐不加分辨地将“历史”与文化、文学等而视之的立场产生了本质区别。德拉-沃尔佩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克罗齐的历史观及主要以文学为主的艺术观进行了抨击。在他看来,“将‘逻辑性联合’(logical unity)从‘抒情性联合’(lyrical unity)里抽象、剥取出来,对于克罗齐一贯采取的审美批评而言,仍旧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实践,同时也堪称最拙劣的批评途径”[6](P26)。德拉-沃尔佩由此主张,必须将对文学及其他艺术符号形式的具体分析,与对蕴藏于其中的历史内涵的阐释结合起来。
由于符号学在语义分析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分析优势,因此德拉-沃尔佩将符号学方法作为重要方法途径,试图对美学批评的分析范式加以改善,恰如他本人所言:“我之所以运用语符学(glossematics),旨在勾勒一般审美符号学前为诗歌与文学夯实其语义学方面的基石。”[6](P12)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领域是由诸多不同支系构成,尽管不同符号学支系往往致力于一种对意义对象的理性、科学和技术化分析,但在符号学内部,这些支系之间往往不具有学理逻辑的统一性,换言之,由于不同符号学支系所关注的符号现象、对认识对象采取的批评方式皆有不同,因此,“符号学”处于一种流脉众多而庞杂的学科状态。同时,由于批评对象主要表现为对克罗齐“直觉主义”历史-美学观的含混性进行理性厘清,德拉-沃尔佩在运用符号学方法时,无暇对其所采取的符号学方法自身作流脉的梳理,而其所运用的“语符学”“语义学”“符号学”等一系列符号学术语间的关系亦略显含混。但总体而言,其所采取的符号学方法主要包括修辞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两种类型。正是在这两种符号学类型的方法基础上,德拉-沃尔佩借对克罗齐美学观的科学性批判,表达出对意大利近代美学观的改造意向。
二、作为“历史”的文学隐喻
在西方修辞学传统中,隐喻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修辞形式。由于隐喻的喻体/喻旨格局对应于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格局,因此隐喻是西方符号学的主要来源和重要支系[7](P24)。在西方文学史、尤其是中世纪意大利语言文学传统中,对隐喻、象征的等手法的运用,成为极其普遍的修辞手段。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的一系列诗作,便最能够体现这种以隐喻、象征为修辞手法的魅力,尤其是在他以意大利语写就的名作《神曲》中,种种隐含着诸多意识形态内涵的隐喻意象比比皆是。同时,但丁还从哲学的高度,指出隐喻在道德、宗教指涉方面的语义功能*详见但丁《论俗语》第二篇第一章,载吕同六编选《但丁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为隐喻在此后西方一系列文学创作、批评活动中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隐喻主要体现为以某种喻体形式,来逻辑性地表达深层次的引申意义,因此具有十分明显的智性特点。在西方修辞学传统中,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开始,隐喻便被与智性因素联系在一起*详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第二章,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同时,亦由于这种智性特征而影响着后世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详见刘宇、欧阳月思《隐喻、扩张意义及科学知识的符号建构》,载《符号与传媒》,总第7辑。。然而,克罗齐从其直觉主义观念出发,由于将语言的本质界定为“情感”的产物,并认为语言“情感”能够直接体现出智性因素,从而否定了语言的逻辑性、概念性作用,以及文学通过逻辑概念以表现智性因素的基本特质:“艺术是直觉,就它是知识的一种模型而言,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就其在概念地把握和澄清对象之前就直接理解对象而言,它必须被称为纯粹直觉”[8](P224),因此,克罗齐对作为修辞手法的语言隐喻所具有的智性因素很是不以为然:“寓意*“寓意”是隐喻的形式之一,克罗齐本人即对此加以界定:“我曾给寓意下过定义……把它说成是一种实践行为,一种写作形式(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东西),一种隐喻手法,从内在性质来说,与任何一种隐喻手法没有什么不同”。参见《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第22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一直是为人所不齿的:据我所知,转喻、称呼、形象描述等做法,总之,修辞学家的其他形象或比喻做法中没有一个不饱受这种反感待遇。”[2](P216)克罗齐显然认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本身就是直觉、情感的表现,如果以隐喻来表现对象,则会因为隐喻喻体的字面意义与喻旨间所产生的距离,而使隐喻技巧的智性因素妨碍读者心灵与文学所蕴含的直觉、情感世界的彼此通达。此外,克罗齐还援引了黑格尔(Georg Hegel)的观点:“黑格尔就把寓意称为冷酷的和苍白无力的(frostig and kahl),它产生于智力,而不是产生于对幻象的具体直觉和深切感受。”[2](P216)这种忽视文学隐喻及其智性的观点,使克罗齐无法认识到隐喻在再现历史意识形态方面所具有的媒介作用,也便使其文学观中的唯心主义特质再次彰显出来。
同时,德拉-沃尔佩深刻地意识到克罗齐忽视隐喻智性作用的错误认识,并主张将“历史”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意识形态关联起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把握文学的历史内涵。因此,德拉-沃尔佩不仅关注隐喻的基本表意功能,还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将隐喻运用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译解,再次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科学维度。
在德拉-沃尔佩看来,隐喻虽具有克罗齐所强调的直觉因素,但同时也能够以语言的逻辑、概念来加以表达,是通过语言形式对历史对象加以典型化的产物:“就隐喻而言,……体现为由类(genera)或属(type)为单位的经验式(审美的)抽象性合成物(abstractive synthesis),以及不具有抽象性、却具有实体性(concrete)的知性因素。”[6](P87)他以但丁《神曲》为例,指出作品中一系列作为隐喻的意象,无不渗透着中世纪特定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在《神曲》中,“‘森林’意味着此生此世的罪愆森林,也就是基督教阐释人生的教义层面的谬误与罪行”,“泪谷意谓人世”[6](P47),“但丁和阿奎那运用的中世纪宗教原型(type)是由隐喻式的(figurative)德性内涵构成的”[6](P50),也就是说,是对与中世纪自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宗教意识形态的隐喻式表达。
文学隐喻往往以“意象”形式来传达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智性因素,德拉-沃尔佩恰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意大利学者缪越陀里(Ludovico Muratori)曾提出,根据对想象与理智的关系的把握,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意象类型,其中,渗透着智性因素的意象类型最为重要[9](P317)。然而,克罗齐却以其直觉主义美学体系为据,提出“意象没有智性因素”以及“意象与逻辑概念间无法转换”的观点,原因在于,他将直觉品视为由情感引发的直觉的对象本身,同时“直觉也是知识,不杂概念”,“许多美学家都坚持艺术是‘形象’*“形象”“意象”及“图像”等不同译法均对应于西语“image”。……因为如果把概念除开,把只有历史事实身份的历史事实也除开,不让它们留在艺术范围之内,剩下来的内容就只有从最纯粹,最直接的方面(这就是从生机跳动方面,从感觉方面)所察知的那么一种实在”[10](P21),也就是说,作为图像符号的意象,仅需凭借读者的直觉感受,便可接受某种智性因素或知识,而无需逻辑概念的参与。克罗齐显然认为,作为图像符号的意象,仅仅通过感性认识即可传达“知识”,从而消解了逻辑概念在传达知识信息方面的功能。
必须指出的是,克罗齐对“意象”的理解,本指对象在心理投射的表象,而德拉-沃尔佩则将对克罗齐这一阐释的批评延展至文学批评中。德拉-沃尔佩显然意识到,克罗齐高估了作为图像符号的意象的符码传达能力,而在他看来,以逻辑概念为基础的语言符号,在符码传达能力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因此德拉-沃尔佩认为,作为心理表象的意象在被转化为文学意象时,只有将图像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其内在含义必须经由语言文字才能获得表达,也就是说,意象传达蕴含着智性因素的符码,必须经过逻辑概念途径。这样,“即便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涉及艺术知识时,如果单纯试图以‘意象’或‘直觉’的方式——而不同时有机地通过概念途径——来达成这种目的,则会被诱入玄秘论(mysticism)、甚至更为恶劣的教条论(dogmatism)的泥淖之中”[6](P20)。如以克罗齐本人的术语来表述德拉-沃尔佩的观点,则可陈述为:意象的空间形式只能提供关于个别对象的知性因素,而无法提供普遍性知识规律的概念,因此,逻辑概念的作用决不应被忽视。德拉-沃尔佩以诗句“耀眼的太阳光”为例来作阐释。在他看来,这一意象本是毫无意义的混乱事物的堆砌,唯有通过逻辑概念的作用,对这些混乱事物进行叙述化、整合化和符号体系化,使这一意象经由被“耀眼的”(great)、“太阳的”(of the sun)、“光线”(light)等词汇概念的体系化过程,才能使其脱离混乱状态,真正形成有机的符号语义体系,传达出应有的普遍性观念和审美效应:“意象唯有在与表现自身样态的词汇彼此充分对应时才能意趣盎然、灵韵生动”[6](P20),亦即传达诗歌的智性信息。
三、对艺术类型差异的阐释
德国美学家莱辛(Gotthold Lessing)在其《拉奥孔》中,从艺术形式角度界定了诗歌与绘画的差异性,从而从技术美学角度辨析出不同艺术形式的相对自律性。同时,他也对文化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采取的浪漫主义阐释方式进行了驳斥。莱辛与温克尔曼关于艺术形式所进行的这场潜在论争,质而言之,体现为艺术批评的技术性分析与浪漫式演绎这两种方法间的对立。及至20世纪,这种对立再次在克罗齐和德拉-沃尔佩两位意大利美学家之间展开。
不可否认,不同艺术类型间常常会发生诸如“通感”式的审美体验,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不同艺术类型一般都具有某种自律性审美特征。如果抹煞它们之间审美形式的差异性,那么不同艺术类型所引发的审美快感将会毫无区别,则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西方艺术精神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分野也将失去意义。但如前所述,由于克罗齐将历史、语言都理解为“精神活动”产物,并将艺术理解为与之等同的“直觉品”,因此,他取消了对历史、语言与艺术——尤其是艺术与艺术间的形式差异的分析,使得西方近代美学批评至少后退到18至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批评水平。
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左翼知识界曾普遍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界在这种影响下,在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时,往往倾向于采取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的方法维度。于是在文艺界、美学界,便产生了这样一种较为模式化的批评途径:无论分析何种类型的艺术品,都仅仅满足于将其作为上层建筑的产物,考察其在被生产时所处的历史及社会语境,而未能通过关注诸多艺术类型的不同符号形式,来分析其中渗透着怎样的特殊历史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与克罗齐从“精神生活”、直觉主义角度来不加区分地理解、度量不同艺术类型的做法十分相似:“我主张艺术的统一性”[2](P193),“对我来说,不论诗的理论和艺术的理论,还是美学的理论,我把语言理论看成同它们是一个东西。”[2](P47-48)
从德拉-沃尔佩的立场看, 无论是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观, 还是机械唯物主义批评观, 它们的共同缺陷都体现为忽视了不同艺术类型各自形式层面的审美特性, “每种艺术支系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表现和‘符号’体系, 唯有通过社会性分析, 才能洞察它们的结合过程。”[4](P236)于是, 德拉-沃尔佩试图通过委婉地批判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观的方式, 以表达对机械唯物主义相关论点的批评。 在他看来, 要实现美学、 艺术批评的科学化, 便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上, 结合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 来对诸多形式的艺术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形式分析。 在这种理解基础上,德拉-沃尔佩依据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拼贴”(bricolage)式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 分别从对语言文字、 色彩与线条、 音程等不同基本单位的考察入手, 对诗歌、 音乐、 电影等不同类型进行了极为精到的形式分析, 并由此展示出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品在由艺术质料组合成整体后, 形成其具体社会符号意义的过程*详见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符号语境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正是通过对符号学方法的借鉴,德拉-沃尔佩一方面批评了克罗齐美学观的唯心主义向度,另一方面,也借此对西方学界一度出现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分析模式进行了改进与纠正,从而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发展与改进,并由此逐步建立起其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同为20世纪意大利的重要美学家,德拉-沃尔佩从对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观的批评中,借由符号学方法,表达出其美学批评观的科学化、技术分析化倾向,并由此体现出对克罗齐美学观的超越:
首先,德拉-沃尔佩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纠正了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式历史唯心观对美学、文艺批评的影响,使20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美学由克罗齐的唯心主义范式一定程度地转向了唯物主义批评范式。
其次,对于克罗齐直觉主义观念所造成的忽视隐喻的做法,德拉-沃尔佩以符号学方法,阐明了作为符号的隐喻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
再次,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批评与当时的机械唯物主义批评具有明显的异质同构特征,这便使德拉-沃尔佩得以借对克罗齐相关论点的委婉批判,表达出改进机械唯物主义美学观的意愿,也由此引导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向艺术形式分析这一内在层面深入下去,从而使意大利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转向了批评范式的科学化。
由此可见,德拉-沃尔佩对当时以克罗齐为代表的意大利唯心主义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与超越,是对意大利近现代美学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他将符号学的科学批评思维引入美学批评范式之中,也为意大利美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掘进之途开辟了极为有益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贝内代托·克罗齐.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M].黄文捷,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3] 埃罗·塔拉斯蒂.表演艺术符号学:一个建议[J].段练,陆正兰,译.符号与传媒,2012,(5).
[4] FRASER J.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5] DELLA VOLPE G. Roussean and Marx[M].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79.
[6] DELLA VOLPE G. Critique of Taste[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7]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M].王国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 BENEDETTO C. Pure Intuition and The Lyrical Character of Arts[M]∥牛宏宝.现代西方美术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0]贝内德托·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赵琴]
The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On Della Volpe′s Critique and Exceeding on the Views of Aesthetics in Croce
ZHANG B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Abstract:The Italian Marxist aesthetician, Galvano Della Volpe criticized and interpreted Benedetto Croce′s views of aesthetics of intui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views of literature, views of metaphor and views of stylistics, on the posi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approaches of semiotics, and rendered the Italian aesthetics of 20 century completed the Marxism and historical improvement.
Key words:Della Volpe; Croce; views of aesthetics; critique; exceeding
收稿日期:2015-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X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碧,男,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北大学副教授,从事西方文论与西方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