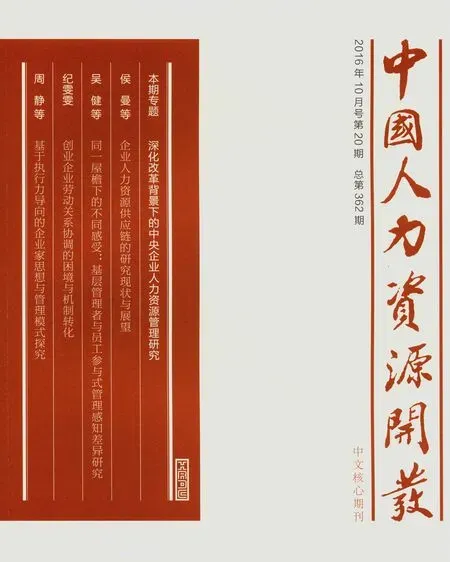超越规则的边界?
——比较视角下中国集体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2016-02-09孟泉
● 孟泉
超越规则的边界?
——比较视角下中国集体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
● 孟泉
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在出现罢工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具有化解与预防罢工功能的工具性博弈机制。本文通过对比D区与G省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集体谈判结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人罢工与地方政府政治空间开放双重因素的推动,但同时又受到地方政府管控与工人经济性诉求双重因素的局限。因此,其效果既实现工人工资的增长,也同时将罢工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嵌入并约束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而工会作为中间的调节组织推动了这种约束的形成。本文认为,谈判结构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暗示出在地方政府与工会对集体谈判间接或直接的介入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很难发展成为劳资自主形式的集体谈判。然而,工会作为调节组织其有效性将决定这类集体谈判机制再生产出工人的“同意”抑或“反抗”。
集体谈判 谈判结构 权力关系变化
一、中国情境下的集体谈判的变化
随着中国劳工问题逐步受到学界重视,近些年以劳工为重心的一系列研究逐渐涉及劳工运动与其制度化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如工人抗争模式、抗争过程中工人与政府的互动、集体谈判、工会在劳工运动中的角色与功能等(汪建华,2011,汪建华、孟泉,2013;Chen, 2010;吴清军,2012; Meng & Lu,2013;Chan & Hui,2012,2013)。在这些研究中,集体谈判机制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议题①。这一议题开始备受重视的原因首先源于学者对现实劳动关系变化的关注。特别是自2010年夏季沿海地区罢工潮之后,在制度层面,政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推广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设与实施(乔健,2012)。另外,某些地方制度的变化也成为一种对工人运动制度化的反应,如《广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除此之外,在罢工较为集中的一些地区,集体谈判或集体协商的机制逐步呈制度化和模式化的发展态势,如广东经验、大连经验等(孟泉,2013;路军,2013)。
从表面现象推断,相当一部分罢工都是依靠集体谈判(官方称作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有效实施才得以化解(常凯, 2013)。然而,很多学者之前对于中国集体协商的研究却暗示出党政推动的集体协商制度却是只是一种通过指标管理的方式实现的国家治理劳动关系的模式(吴清军,2012)。陈敬慈认为这种党政主导推行数字化管理的模式只能称之为形式化的集体协商制度(Chan & Hui, 2013)。因此,形式化的集体协商制度并不能导致劳资之间自主的谈判关系的形成,集体协商的本质成为党政与工会联合同资方的议价行为(吴清军,2012)。颇有兴味的是,在工人通过集体反抗行动的作用之下,集体谈判在企业层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虚转实,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资自主议价的结果,从而改善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面对这一新的变化,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变化的劳动关系情境之下,这种集体谈判机制的独特意涵到底是什么?其独特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如果这样的集体谈判机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真实的劳资博弈,那么,决定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有关集体谈判的西方经典理论入手,结合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在制度和执行层面的具体实践来分析。笔者首先通过对集体谈判相关理论的分析,从制度沿革与主体博弈行为两个角度梳理出中国集体谈判异于西方传统意义集体谈判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明确聚焦在中国特殊情境下本文的研究问题。其后,笔者选取了在2010年夏季发生罢工潮地区的两个典型案例,即D区和G省,集中对两个个案中有关集体谈判制度与集体谈判中各主体行为的变化进行阐述,旨在通过比较集体谈判机制实施的动力、集体谈判的结构变化与其功能发挥的局限性来挖掘决定集体谈判功能背后国家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最后,通过从这三个角度的比较分析,来讨论决定这一机制现实效果及影响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基于笔者在2010到2012年L省D市D区和G省两个出现罢工潮最为集中的地区进行的多次调研。在2010年两地皆发生了数十家企业连锁性的罢工潮,而两地的罢工问题也都是通过政府与工会的积极介入之下,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得以平息。同时,两地罢工企业中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也逐步成为了常规化的劳资议价机制。因此,对于考量罢工后集体谈判机制的运行十分具有典型性。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访谈对象涉及工人、工会工作者、政府官员及企业管理者。另外,笔者也参与到了个别案例具体的集体谈判过程中,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记录谈判的全过程。对于一些典型案例相关媒体报道的二手资料也是对本研究参考的有力佐证。
二、谈判结构与权力关系——中国集体谈判变化的独特性及其分析视角
对于集体谈判的理论性讨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即功能主义的视角与行为过程的视角。从集体谈判的功能角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主要强调集体谈判作为一种规则对产业关系的影响。
例如,韦伯夫妇早在1914年就提出集体谈判的经济功能,即工会依靠组织权力为其会员提高其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的机制,进而工人可以改善生活水平(Webb & Webb,1914∶150-276)。之后,英国学者弗兰德斯与克莱格又提出,集体谈判除了具有经济性的议价功能之外,还具有实现企业民主参与的管理功能(Flanders,1968;Clegg,1976)。而其他一些学者基于其对过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批评认为,通过有效的集体谈判制度安排还可以实现国家层面的产业民主与工会的合法性(Fox,1975;Ackers,2007)。这些观点暗示出了集体谈判的政治功能。
持有功能论的学者对集体谈判的研究基本止步于对集体谈判制度或机制影响效果的一种描述,而忽略了不同主体在集体谈判这一劳资博弈平台上的行为。于是,另一些有关集体谈判的研究从行为过程的视角指出,集体谈判作为一种产出规则的过程,其内在蕴含着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关系(Fox,1975;Kcohan,1980)。吴清军在引述布朗的比较研究后认为,这些集中讨论欧美集体谈判制度的理论并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集体谈判的制度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国家的特殊作用其解释力不足(吴清军,2012∶70)。然而,吴清军却并未继续讨论应该从哪些视角来分析中国的集体谈判的独特性。
本文认为仅仅将中国的集体谈判的制度安排按照西方的制度的标准进行对比,那么必然会忽略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多元化造成了产业关系多元化问题的存在(Hamann & Kelly,2009∶137-145)。仅仅参照西方集体谈判的功能来看中国的问题有欠客观,而应该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集体谈判制度构建与执行过程的独特路径。正如陈峰所提出的观点,工业公民权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大有不同之处,如英美是靠工人运动推动的工业公民权从政治权利到社会权利的转变;而在中国集体性工业公民权则在先入为主的工会体制以及个体权力的积极构建中被遏制了(陈峰,2011)。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就已经先入为主地在一系列的劳动法律法规中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并在2000年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4年颁布了新的《集体合同规定》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郑桥,2009∶402-428)。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以及执行层面的缺失,导致集体谈判呈现有程序性合同少实质性谈判的特点,工人也并未真正纳入这样的机制当中作为博弈的主体(Clarke et.al,2004;吴清军,2012)。在个体劳动权利的一系列法律出台后,工人的抗争又进一步被导入了“依法维权”的路径之下,而推动集体谈判的主要力量仍旧是国家和工会。无论如何,党政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路径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以后,例如2010年国家“三方会议”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工作方案》、全国总工会于2010年提出的“两个普遍”以及于2011 年下发的《中华全国总工会2011—2013 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等。然而,笔者从与2010年沿海地区罢工潮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工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集体谈判制度与执行的统一(路军,2013)。
另一方面,除了中国集体谈判的独特性除了体现在历史视角下制度演进的路径之上,参与谈判主体的互动博弈行为也会揭示其特殊性。一些针对近年来工人集体抗争的研究认为,集体谈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化解罢工的有效机制与手段,具有平息罢工的功能(李琪,2011;Chan & Hui,2012)。然而陈敬慈等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的工人罢工导致雇主最终接受以类似西方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的形式与工人在工资增长的诉求上达成妥协;但是随着工会在后续谈判中的介入,集体谈判的模式也有可能转变为“党政主导的集体谈判”模式(Chan & Hui,2013 )。在这个过程中,集体谈判的功能也由解决罢工过渡到了预防罢工。当然,还有另一些个案研究也透视出,在基层还是会出现一些制度与执行趋向统一的集体谈判“模式”,如工人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的结构性权力,推动雇主主动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化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温岭模式等(闻效仪,2011)。 由此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中国的集体协商机制并非是某些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劳资自主程度较高的集体谈判模式,而是一种国家与企业用以治理、管理劳动关系的工具性议价机制。
综上,就目前中国集体谈判的现实发展来看,其变化的特殊性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宏观制度层面,中国的集体谈判制度经历了从党政主导下先入为主的制度建设与执行的不统一,过渡到在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下,制度与执行一定程度上统一的过程。其二,在企业运行层面,中国的集体协商机制在被国家甚或雇主作为旨在发挥稳定劳动关系功能的工具化机制重新引入企业劳资关系调整之中。其突出表现就在于工人可以参与到集体谈判的过程中,进而影响了围绕集体谈判的党政、工会与工人等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基于这一判断,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聚焦为,在这种先入为主的制度安排条件下,为什么这种具有工具化色彩的集体谈判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解决和预防工人罢工的功能?这种中国劳动关系的“制度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的集体谈判功能变化体现在谈判结构的变化,而谈判结构的变化背后却是工人的力量卷入权力关系之中的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前者来说,中国的集体谈判机制变化,受到了集体谈判相关制度的变化的影响,这可以反映在集体谈判的结构②变化之上(Flanagan, 2008)。就法律而言,《劳动法》第33条和《劳动合同法》第51条,基本上已经将集体协商的双方当事人限制在了用人单位(企业)层级③。但是,地方集体协商的制度改变可以导致谈判的结构变化,如自2006年以来,为了解决集体协商在企业推进困难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始实施区域性或行业性集体协商的方式,但这样的方式虽然是谈判结果的表面变化,而实际上仍旧只能体现在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合同的数量上(吴清军,2012)。另一方面,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亦会受到参与集体协商行为主体互动的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博弈各方的权力(power)关系变化之上(Kelly,1998∶9-13)。然而,在中国的情境下,仅涉及劳资双方的权力关系解释力不足,必须考量国家与工会作为另外两个重要权力主体介入集体谈判后的对劳资权力关系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中,权力关系也必然是四方互动的结果(Chen, 2010)。这主要是因为国家与工会在介入解决2010年罢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企业与工人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进行议价,从而形成了“集体谈判的潜机制”(李琪,2011)。另外,最近对于珠三角和东北地区的罢工研究表明,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工会在党政的支持下,在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既从程序上代表了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又在工资集体协商的机制的完善与实施中扮演了重要的协调者和引导者的角色(Chan,2012;孟泉,2012)。综上,本文对个案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谈判结构与博弈主体的权力关系变化这两个影响集体谈判的主要面向,从而发掘导致集体谈判有效性的深层原因。后文将基于这一框架结合笔者的经验研究讨论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三、博弈传统的延伸——D区工资集体协商
D区是1984年由国务院认定的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在中国外资企业最早投资的开发区之一。到目前为止,该区有3500多家外资企业投资建立工厂或公司,其中跻身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达69家。笔者将通过梳理该地区罢工以及集体谈判机制建立、运行与变化的历史传统来说明双重动力的作用效果。
(一)集体协商机制变化的双重推动力
D区罢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在1994年3月全国第一家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W厂工人自发组织了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两天半,工人的诉求就是要增加工资的涨幅并减少工时。此事一出对日方雇主和全总都有所触动,并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最终迫使地方工会出面和日方经理就工人提出诉求展开协商,并增长工资。由于W厂工资的成功增长,带动了地方政府和工会为避免劳资冲突波及其他工厂而给整个工业园区的日资企业按统一标准普遍增长了工资。
自94年工资增长之后,随着《劳动法》的出台,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D区的日资企业逐步建立起了集体协商机制。但是,这一阶段的集体协商,并未完全反映出工人对工资增长的诉求,本质上只是企业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协商,对日方雇主的妥协④。但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工人工作压力的增大等因素,终于导致了2005年该地区连锁罢工的爆发。
2005年,该区16家日资企业与两家韩资企业中爆发了约2万名工人参加的连锁性罢工潮。此次罢工潮的起因是由于日本投资的T公司受到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要求缩短员工加班时间的整改意见。于是,公司决定缩短时间提高效率。但是,工人不仅难以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更由于加班时间的减少而导致工资降低。因此,T公司的工人们在无法忍受的条件下,终于将积怨转化为了五六百人参与的罢工行动。从2005年8月19日到9月14日,其他17家企业的工人陆续罢工。他们主要的诉求也基本集中在要求企业增长工资。
在介入平息罢工的工作中,D区区工会主席M先生,在通过与D市政府的沟通之后,得到了政府的授权和认可,并委托其作为政府的代表到企业中去与雇主通过集体协商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尽快化解罢工。应该说,区工会在劳资冲突之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通过政府赋予其介入罢工的权力,与企业工会配合,在雇主与工人之间促成了双方对工资增长幅度的妥协,从而既满足了工人工资增长的诉求,又化解了罢工问题(Chen,2010)。可见,集体协商又发挥了平息罢工的功能。
为了进一步避免更多的罢工出现,地方政府吸取这次“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开始强调工资指导线的作用,并经常和D区工会以及该区的企业工会沟通,试图以工资指导线作为支持企业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个有力的博弈策略。但是,对于企业工会主席来说,仍旧主要依靠自身在企业内部所能掌握的资源和长期摸索的谈判策略与雇主就工资增长和劳动条件等问题进行协商,企业工会仍旧处在“单打独斗”的阶段⑤。
然而,2010年更大规模的罢工潮再次爆发宣告了这一改革失败。2010年5月末到8月末,D区曝出自建立以来第二次“罢工潮”,波及企业达73家(其中46家日资企业),参与罢工的工人达七万多人。这次罢工潮从参与的工人人数到规模都超过了2005年。引发该区工人以罢工的形式进行抗争的直接原因仍旧是工资增长。对于D区的工人来说,工资增长的幅度要低于物价增长的幅度导致他们的月收入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的诉求,甚至出现了生活水平降低的状况。另外,在D区,大部分工人都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仅对自身的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提高,也更加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反抗精神(Pun &Lu,2010)。
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行为持续了一个月才得到全面平息。而罢工得以解决的关键就是企业工会迅速组织工人选举谈判代表,收集并迅速统一工人诉求,同时说服日方雇主与工会主席及工人代表,就工资的增幅问题进行反复谈判。而此时,区工会也与企业工会迅速沟通在工资增幅问题上的标准和限制,并介入部分企业劳资谈判的过程中,从而提供给企业工会政治上的支持,进而推动平息罢工。尽管官方话语中,对旨在平息罢工的谈判过程仍旧称之为“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然而,这一机制一方面是工人自发形成的团结力量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工人的参与与意见表达。因此,更加接近西方社会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Chan & Hui,2013)
实际上,2010年罢工潮的发生说明,D区工会在2005年之后改善的集体协商机制作用的局限性。很多参与过罢工工人承认企业工会每年确实帮助他们争取工资增长;却又认为工会与雇主展开的集体协商并没有解决他们的实际诉求。尽管企业工会也收集工人意见,但是这些意见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工会进行会总和修正,并且需要得到日方雇主同意的前提下实现有限的工资增长。而只有通过工人自组织的罢工才可以真正让工人的声音得到重视⑥。可见,企业工会通过“单打独斗”式的策略意在能够增强其在工人中的合法性,并由此预防罢工的出现。然而,工人的自发罢工再次对工会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而这种挑战也促使企业工会开始引入新的应对策略。
通过梳理D区工人罢工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工人通过罢工行动不断推动了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但是,D区政府与总工会一直以来在集体谈判制度的改革中,成为主导角色。故而,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实际上受到了双重动力的影响,即工人集体力量与政府、工会推动的制度改革。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之后D区区工会推进的集体谈判制度改革效果最为明显,表现在集体谈判的结构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集体谈判的行业化与集中化
2010年罢工潮事件平息之后,D区总工会开始改革集体协商制度,具体策略包括制定可预期的工资增长计划、与雇主组织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以及优化与整合外企联。这一系列改革直接影响了集体谈判结构的变化,其转变可以概括为集体谈判结构趋向集中化和行业化。
首先,D区区工会在工资增长标准方面制定了配套的制度,即由区工会推出的所谓“五年工资倍增计划”,承诺该区工人,五年工资增长实现翻一番。这一标准的制定即能够让工人的工资得到有序的增长,又是一种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预期。企业进而可以结合自身具体经营状况进行调整。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工人对工资增长有一个愿景,又可以让工人接受企业工会提出一些调整增长幅度的意见。
其次,由于日资企业是劳资冲突多发的企业类型,所以区总工会在企业工会与雇主展开集体谈判之前,会提前和该区日资企业商会展开非正式的讨论和协商。区工会尽量利用其代表政府的身份来让日资企业商会与其在工资增长问题上达成一致,并确定工资增长的上限与下限。其目的在于为了帮助企业工会缓解在集体协商中雇主一方的压力,这样就使企业工会在与雇主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就工资增长的底线与日方雇主达成默契。因此,在企业开展集体谈判之前,实际上,D区区工会已经和日资企业雇主确定了涉及谈判主要内容,即工资增长的范畴。总体来看,D区总工会在企业工会与雇主展开工资集体协商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区域层面与劳资双方的沟通。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谈判(工资集体协商)的结构趋向集中化。
最后,2010年罢工潮发生之前,区级工会也召集了部分在开展集体协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企业工会组成了以区域为单位的非正式工会信息沟通网络。然而,这一网络形成的主要基础是区工会主席与其他企业工会主席的私人关系,由于缺乏制度的强力支持,这一松散的网络作用比较有限。
新的工会主席上台后,发现了这一网络资源的重要价值,于是,以此网络为基础,根据不同行业与所有制的特点,发展改善了D区外企联(外资企业工会联合会),使外企联的组织结构更加规范。外企联将企业工会按行业及投资方划分为9个分站⑦。各区域分站建立党委,直接受外企联领导,形成长效沟通、联动工作机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通过上下级党委关系形成的工会网络,本质上,这个网络是借助了党委的名义实现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便更有效的开展工作。
总体来说,外企联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同行业内企业工会交流工资集体协商经验、互通信息的一个平台。行业化特点更为突出的外企联的发展,使企业工会组织在集体协商机制的执行中的行为、策略相似性增强,从而能够更好地保证工资增长并缓解了工会的压力。
(三)企业内部集体协商的效果
在D区总工会主导的集体谈判制度重塑背景下,直接导致了集体谈判结构由以往较为松散的企业层级的谈判向更为集中化的趋势过度。而这种制度安排在企业内部产生的效果则主要体现在企业工会的角色的转变,并同时增强了企业集体协商的有效性,进而提高了企业工会的合法性地位。2010年罢工平息之后,新上任的区工会T主席对D区企业工会开展集体协商机制的工作模式做出了重新的考量和总结。在他看来,D区工会以及企业工会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两点,即预防罢工和工资增长。
“作为工会组织,就是要想如何避免罢工现象。如何预防。需要工会做什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职工核心问题就是工资问题。维护职工工资就是最大的利益。另外,作为外资企业,作为职工的工资比较低的情况下,如何真正使工资正常工资增长正常机制。保证职工工资随着外界经济、物价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才是工会要做的事情。”⑧
但是,对企业工会来说实现这两个目的的过程中面临双重压力。这种压力一部分来自工人对工资增长的诉求,另一部分则来自雇主对区工会身份与行为的限制(Chen,2009)。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策略能够将企业工会从这两种压力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平衡、解决劳资之间因工资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区工会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下简称“职代会”制度)引入了D区的企业工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这一制度实际上已经为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作为一种制度资源,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加以再度开发和应用,这一企业工会的行为被视作发展民主参与改革的有效途径(冯同庆,2011:13-15)。
企业工会能够通过职代会制度与集体协商制度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有效地将企业工会从原有面对工人代表性不足的尴尬局面中解放出来。通过工会主导的工人直选,职代会成为了可以聚集工人意见的工会附属组织,但是这一组织对工资增长等问题所形成的最终意见就基本代表了所有员工统一的意见。另外,职代会还成为了工会工作宣传的一个阵地,在职代会上工会主席让所有参会的职工代表了解到企业工会为工人工资增长所付出的努力。因此,工会通过在职代会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工人的认可。由此将过往企业工会直接与雇主就工资增幅展开谈判的关系,转化为以工会作为中间人代表工人的意见与雇主谈判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工会实现了先与工人达成一致,再与雇主实现妥协的谈判机制。企业工会通过职代会机制的引入,在与资方的谈判策略上做出了有效的变化,将工人的权力真正引入了博弈的过程之中。
四、成功经验的复制——G省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
在2010年夏季发生在沿海地区的罢工潮中,另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G省十几家日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代工厂的罢工潮,其更具有行业性连锁罢工的突出特点。然而,集体谈判也成为了解决并预防罢工的有效手段。
(一)集体谈判的双向驱动力
2010年5月17日,G省F市的某汽车零部件厂(以下简称B厂),1500多名工人发起了持续了半月有余的罢工行动。参与行动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年龄在18岁到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人的抗争行为主要因为他们对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公正的工资体系以及中日员工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差距过大等问题产生了不满。由于商品市场物价的不断攀升,订单量过多等原因导致工人所需承担生产任务量的压力不断加大。这就造成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有失公正的报酬。于是,在两名积极分子牵头之下,持续半个月的罢工拉开了序幕。
不同于以往通常见诸媒体报端的工人抗争形式——在工厂以外的游行示威,B厂工人只是将活动的范围限制在厂内,并不时高唱爱国歌曲,高喊带有反日色彩的口号。在工人理性罢工的过程中,也受到了雇主的对抗,如采取威胁性和高压式的应对策略,如公司开除两名最初的罢工领袖;公司与实习学生工的校方共谋,以毕业证为要挟逼迫参与罢工的学生工尽快复工,逼迫参与罢工的学生工签订不再罢工的保证书等。S镇工会与罢工工人之间的冲突也进一步激怒了大部分工人,并导致已经复工的工人再次加入了罢工的队伍。
正值事态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G省政府高层开始重视该事件的发展,并将该事件定位为劳资之间的经济性纠纷,希望工会能够介入通过推动集体协商来平息罢工。其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策略主要决定于其需要平衡G省产业升级的经济发展需求与社会维稳的政治发展任务(Meng & Lu,2013)。之后,Z先生以省人大代表及与B集团在华合资的GB公司中方总经理的身份开始介入并极力促成劳资之间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此事。同时,N区政府劳动部门也努力协同Z先生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程序(集体谈判)的启动,以实现工人工资增长,尽快平息罢工。之后,在Z先生与劳动法专家C教授的斡旋之下,由原企业工会主席和四名罢工中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劳方首席代表与日方管理层五名首席代表展开了三轮有序的工资集体协商。最终,劳资双方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了一致。值得注意的是,B厂罢工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以至于G省汽配行业后续发生了十几起起罢工。而当B厂罢工通过集体谈判得以平息的策略也被政府认可,并通过G省总工会和各地方工会作为解决罢工的模式一一化解了后续的罢工。可以看出,汽车行业集体谈判得以促成在于工人罢工与政府包容双重动力发挥了作用(Meng & Lu,2013)。
(二)集体谈判模式的集中化复制
随着旨在平息罢工的B厂集体谈判模式逐步成型,G省工会在政府的支持下,以此模式迅速被推广到广东各地爆发罢工的汽车制造业的外资企业,进而这些企业的罢工也通过集体谈判得到了解决。
例如,在另一家日资零部件制造厂(以下简称D厂)出现的罢工事件解决也是因循B厂的成功经验。到D厂工人罢工的第三天,G市S区区政府由于担心会产生25家在其辖区内的汽配工厂的连锁罢工,于是开始介入此案并试图平息工人的罢工。同时,S区工会L副主席也被邀请协助介入处理此事。此后,S区工会副主席邀请在平息B厂罢工中的资方专家Z先生来和罢工工人谈判。然而,Z先生与工人的沟通并不顺畅,工人普遍不愿接受政府的协调,并表示对企业工会失去信心。所以,S区工会副主席随即开始转变策略,先对企业工会主席及11名工会委员做思想工作并共同商量应对策略。于此同时,S区工会副主席也在与该厂最高管理层达成一致意见后,公开劝说工人复工。在L副主席的劝导下,工人们本来计划一周的行动最终只坚持了3天,便答应重新复工。然而,此时日方管理人员对罢工工人轻蔑的态度激化了工人的反抗情绪。。L副工会主席遂再次与罢工工人沟通,希望罢工工人能够推举代表与企业和政府谈判。经过多次努力,工会终于使罢工工人接受选举谈判代表。然而,谈话当晚,罢工工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再次组织起来意图封堵工厂大门,拦截向厂外运送货物的火车以及日方管理者的班车。后来,在区领导与工会领导的介入之下再次平息。
最后,S区工会副主席动员11名指定的员工代表分组说服罢工员工选出了52名谈判代表。25日,由52名员工代表与资方开始展开集体谈判。企业工会K主席和4名员工代表作为劳方首席谈判代表。资方也吸取了过去因态度刻薄而导致恶果的教训,在谈判过程中保持友好的态度与气氛。经过谈判后,最终确定工人工资增长825元,全厂员工总体普调550元。另外,工人提出了623条谈判的意见被企业工会总结为220条,在后续的谈判中确定。雇主与工会承诺,集体谈判过程中只确定了工资问题,其他问题还要在两到三个月内谈完。总体看来,G省政府确定了劳资冲突的性质,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之后,G省地区级的工会(如G省总工会、GZ市总工会、N区总工会等)扮演了推进以集体谈判(工资集体协商)手段来化解罢工的重要角色。而这种地区工会推动的谈判模式的不断复制形成了一种更为集中化复制模式。
(三)由谈判到协商——缩水的政治空间
G省集体谈判模式集中化的复制暗示出工人自发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机制的实施起到了有效化解罢工的作用,这一阶段的集体谈判也更加趋近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盛行的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Meng & Lu,2013;Chan & Hui, 2013)。然而,其作用不止于此。以B厂这个典型案例来说,在G省总工会及时介入之下,辅助工人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及工会委员,但企业工会主席仍未有变动。与此同时,部分罢工积极分子也纷纷离开工厂,另谋职业。次年,在广东省总工会的辅助下, 3月11日劳资双方进行了2011年的工资集体协商,经过三轮博弈之后,工人的工资再次增长611元,基本满足了大多数工人的诉求。但是,参与正式协商的一线工人数量大幅减少,其对于工资增长等方面的意见,基本上都由班组长通过工会小组长逐级上报到企业工会,并由企业工会委员进行汇总后,作为主要的协商代表与资方进行协商。另外,资方也在认可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劳资之间沟通的渠道,旨在能够更深入了解工人的基本诉求及思想状态。总体来讲,B厂罢工工人在党政与工会约定明确的工资集体协商规则中,被动地参与到这种工会推动却可以实现增长工资目的劳资博弈过程中。
应该说,广东省工会在法律上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来介入这两个过程之中。从现象表面来看,广东省工会既在B厂组织工人进行工会重选工作,又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在第二次集体协商当中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⑨。因此,地方工会在实现工人在工会重组和通过协商程序增长工资两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代表性也得以彰显。
然而,正如陈峰指出地方工会作为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其目标、策略和行为都被限制在了政府既定的界限之内(Chen, 2009)。因此,在地方工会的积极干预之下,企业工会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民主选举则是需要从地方工会的干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中得出答案的。从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一方面,工会主席的人选并没有变动;另一方面,地方工会虽然也允许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或有参选积极性的工人参加选举,而最终成为工会委员选举的大部分都是管理层,一线员工所占比例甚少。相比之下,罢工后的第一次工资集体协商更加趋近于集体谈判。与罢工后的第一次协商相比,第二次协商中的普通员工参与度已经大幅降低,并且只有工资方面的诉求得以进入集体谈判的程序。
由此可见,地方工会介入的目的更加体现了工会选举和为了增长工人的工资而展开的集体协商在政治上必须是稳定并可控的。同时,工人的罢工行为得以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而避免;企业工会的重组也不会让一线员工的团结成为影响企业工会行为的决定性力量;广东省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工会维权的行为并未超越广东省经济、政治发展的原则,既可以让企业的生产继续稳定运行,也可以在政治层面实现对工会重组及集体谈判的稳定性与可控性。工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工会也成功的实现了对政府维稳功能的延伸。
由此可见,G省政府提供的包容性政治空间实际上只容纳了工资增长的实现,有关工人集体权利的诉求最多只能在工会控制的范围内接受,甚或未被考虑在内。所以,其集体谈判随着不断的被复制,背后的逻辑是针对工人自发形成的集体力量产生的转化或消弭的作用。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多数工人对于经济性诉求满足之后,也不再坚持为新的诉求而抗争。双重的动力在集体谈判机制的变化中被转化为劳资自主谈判的双重的阻力。
五、结论与讨论
(一)集体谈判背后的权力关系变化
通过对以上两个典型个案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导致地方政府与工会依靠推动劳资双方以“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罢工的直接动力正是工人的罢工行动。但是,不能忽略的另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地方政府政治空间的开放。因此,集体谈判得以实现的推动力包括工人自发形成的结社权力与政府的推动力(见表1)。
工人与政府双重动力的作用效果集中体现在两地的集体谈判的结构的变化之上。对于D区来说,在区工会制度化的改革中,集体谈判的结构由松散型的企业层面的谈判过渡到趋向集中化的谈判结构。具体来说,区域层面非正式的工会与雇主组织谈判确定了工资增长的区间,并作为企业工会谈判的参考标准。企业工会再根据自身企业的具体情况,代表工人与雇主在工资增长的幅度上进行议价,最终确定企业的工资增长幅度。企业工会进行的“组织裂变”的改革,有效的控制了工人参与谈判的程度。而对于G省来说,集体谈判结构也由过去的企业级的集体谈判转变为一种类似“模式复制”(pattern following)的非正式谈判结构(Katz et al. 2008)。然而,这种所谓模式复制结构的特殊性体现在政府通过区域工会介入集体谈判,从而实现政府控制权力的延伸,并有效的监督和引导了集体谈判中工人参与的整个程度。
尽管两地推进的集体谈判的结构模式不同,但实现的功能十分相似,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员工参与工资共决的谈判机制和工资增长的目的;却同时将工人的集体权力整合入可控的制度化路径,实现了平息与预防罢工的双重功能。集体谈判的这一效果,都决定于集体谈判机制运行背后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两地政府与工会通过引入制度化改革的权力有效的解决并避免了罢工。这使工人依靠团结形成的集体权力进入了制度化的束缚。这其中经历了两个具体阶段: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自发结社权力推动了为解决罢工的集体谈判,由于谈判代表的在议价过程中作用十分明显,这种谈判模式是比较趋近于劳资自主的谈判。而一旦集体谈判的模式形成之后,工人的集体权力被整合入了制度内运行,成为了党政与工会可控的权力。也就是政府与工会运用的制度性权力束缚了工人自发的结社权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自发形成的结社权力也并非毫无缺陷。其问题在于工人这种抗争的诉求仅止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即便在话语上对集体劳权(如工会改选、集体谈判权等)提出的诉求也是一种工具性的策略,而并非真正意味着劳工意识的提升与转变 (Meng & Lu, 2013)。这一点在汪建华对珠三角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佐证。他认为,工人的罢工行为背后充斥着一种“实用主义团结”文化。基于这种团结文化,工人们的抗争本质上就是市场博弈的手段,其经济性诉求是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制度性诉求也体现其对于议价机制常规化的期望(汪建华,2013)。但是,经济性的诉求使其自发形成的集体权力被嵌入制度路径,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具有潜在影响的权力。表现为一种可以被政府、工会与雇主识别的潜在能力,也只能发挥潜在的威慑功能。
正如塔罗所指出的“运动中的力量取决于外部机遇的动员,当机遇从最初的挑战者扩展到其他的集团,并转向高层精英和当权者时,运动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力量来源。在短期里,运动中的力量似乎不可抵抗,却很快消失,并无情的变成更为体制化的形式”(塔罗,2005)。限制D区劳资自主的集体谈判模式发展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基于谈判传统而形成的工人、工会与雇主之间的默契;而对于G省可以概括为旨在削弱并控制工人博弈权力的缩水的政治空间与工人经济性诉求的契合。但从本质上说,两者无甚差别。
因此,从表一的对比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实际上,两地的集体谈判结构的变化是决定于政府、工会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权力关系变化的原因是政府的控制策略调整与工人抗争的诉求恰巧形成了默契。也就是说,集体谈判的推动力与局限性都是劳、政双向作用的结果。其最终导致了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层面劳资自主的程度逐步降低,而趋向一种可控的集中化谈判结构,进而首先实现了解决罢工的功能,而后实现了预防罢工的功能。劳资相对自主的博弈关系在工人自发的结社力量逐步被吸纳进入制度化轨道后,在微观企业层面的谈判过程中随之转化为了一种劳资与工会共同参与的谈判机制。一方面,区域工会参与体现的政府意志是对于效率、稳定与国家合法性之间的平衡(Offe,1984);其背后支撑的权力来源是地方政府。另一方面,企业一级的工会参与发挥了既代表工人谈判,又要协调劳资关系的功能。因此,工会参与实际上是对员工参与的一种功能性组织化策略,意在控制工人的参与程度,协调劳资之间的矛盾。

表1 两地集体谈判比较
(二)制度化治理策略下再生产出的“同意”与“反抗”
总体来说,两地出现过罢工的企业中推行的集体谈判机制最终可以实现解决并预防罢工的功能主要决定于国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国家介入罢工的权力主要体现在政治空间的开放只容纳了工作场所中的利益博弈存在,而对于集体劳权的制度化趋势却并为出现。也就是说,集体谈判本质上是“国家搭台,劳资唱戏”的博弈形式,通过控制工人在集体谈判中的参与程度来避免工人再次形成自发的集体力量。
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其在一定空间内的流动性以及工会的协调作用这两个维度对于在集体谈判中的工人权力进一步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在D区由于工人的流动性相对较低,即使离开一家工厂还可以在该区的另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再加之大部分工人来自东北地区,现在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区域中可以有助于形成团结的资源。然而,区工会制度化改革强化了区工会和企业工会在工人与资方之间的调节功能。这种调节功能使劳资双方与工会在企业集体谈判的运行中与工会逐步形成了一种延续的默契,因此,只要保证工会在工资增长问题上协调得当,那么工人就更容易对目前的集体谈判机制产生认同,进而有效降低了罢工发生的可能性。相反,尽管G省工人流动性较高,构成了不稳定的工人群体结构,这必然会对团结的延续产生影响。然而,在G省曾经出现过罢工并以集体谈判方式成功化解的典范企业B厂工人在2013年3月再次以罢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工资增长的不满。工会主席的更替,使工人们认为集体谈判在新的工会主席推动下,使员工意见得不到重视,却逐步倾向于迎合日方雇主对工资增长的幅度的决定⑩。G省工会的撤出与B厂新工会主席轻视工人意见,实际上降低了工会利用集体谈判机制在劳资之间发挥的调节功能。这种迥异的现象暗示出国家通过引入制度化治理的策略来约束工人团结的形成,并不一定是长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在企业中的运行也许会再生产出工人新的“同意”或“反抗”。因此,这种“同意”与“反抗”都在集体谈判机制中被再生产出来的决定机制是什么,是未来笔者将会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注 释
① 在中国,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概念尚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并不能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集体谈判制度同日而语,笔者承认这一提法。但是,若将集体谈判与集体协商的定义对应实际的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行为来看,则很难界定哪一种行为就是谈判,哪一种行为就是协商。然而,从集体谈判的分类来看,分配型谈判意味着一种零和博弈;而整合性谈判则是一种“正和”的双赢谈判方式,而集体协商与后者更为相似,强调劳资双方就一个目标,通过交换意见和沟通,最终达成双赢的目的与合作的关系(Katz, et. al, 2004:185; 李琪,2008:185)。因此,为了避免概念使用的混乱,本文将沿用集体谈判这一概念,但是涉及官方已经确认的名称时,使用工资集体协商这一说法。
②集体谈判结构是指集体劳动合同影响或覆盖的劳资双方的范畴,也就是谈判单位(bargaining unit)的结构(Katz et al. 2008)。
③《劳动法》第33条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法》第51条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
④ 参见2010年4月6日W厂工会H主席访谈记录。
⑤参见2012年7月30日D区区工会S主席访谈记录。
⑥参见2011年8月17日W厂工会H主席访谈记录。
⑦ 9个工作站分别为:第一工作站(机械设备、通用设备、汽车零部件、微型马达)、第二工作站(机械设备、船舶机械、汽车零部件、空调配件)、第三工作站(电子电器1)、第四工作站(电子电器2)、第五工作站(服装企业)、第六工作站(制药、食品、服务业)、第七工作站(注塑、磨具、冲压)、第八工作站(建材、铸造、阀门、化工)、第九工作站(欧美企业)。
⑧ 引自2012年7月30日D区总工会T主席访谈记录。
⑨黄应来,“南海本田停工事件:日方最终接受增加工资方案”,《南方日报 》2011-03-02,http://gd.nfdaily.cn/content/2011-03/02/content_20591437.htm,2011/10/8最后一次引用。
⑩参见2012年7月22日B厂工人小F访谈记录。
1.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论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劳工政策的完善》,载《“劳资冲突与合作:集体劳动争议处理与规制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
2.陈峰:《罢工潮与工人集体权利的建构》,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1年,总第124卷。
3.冯同庆:《中国职代会制度,一个有希望的憧憬》,载《中国工人》,2011年第6期。
4.李琪:《产业关系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
5.李琪:《启动集体谈判的‘潜机制’》,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年第2期,第82-85页。
6.路军:《工会介入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载《中国工人》,2013年第3期。
7.孟泉、路军:《劳工三权实现的政治空间——地方政府与工人抗争的互动》,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2年第3期。
8.孟泉:《从劳资冲突到集体协商—通向制度化之路?》,载《中国工人》,2014年第3期。
9.乔健:《探索和谐劳动关系新政》,载《中国工人》,2012年第1期。
10.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11.汪建华:《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12.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13.闻效仪:《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为例》,载《社会》,2011年第1期。
14.吴清军:《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5.郑桥:《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与趋向》,常凯、乔健编著,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
16.Ackers, Peter. “Collective Bargaining as Industrial Democracy.”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7, 45( 1) .
17.Chan, Chris., and Elaine Hui.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Honda workers’ 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12. 54(5).
18.——“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 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China Quarterly, 2013.
19.Chen, Feng.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r: The Conf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ual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03. 176: 1006-1028.
20.—— “Union Power in China: Source, Operation and Constraints.” Modern China,2009. 35(6) : 662-689.
21.—— “Trade Union and the Quadripartite Interactions in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0. 201:104-124.
22.Clark, Simon., Lee Chang Hee., and Qi Li.“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4. 42( 2) :255-81.
23.Clark, Simon., and Tim Pringle.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 Trade Unions in Russia, China and Vietnam, Basingstro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4.Flanders,Alla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968, 6( 1) .
25.——“Natur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Flanders ( ed. ), Collective Bargaining.Harmondsworth: Penguin.1969.
26.Flangnan, Robert.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Blyton, Paul., Bacon, Niclolas., Fiorito, Jack. & Heery, Edmund.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8. pp 403-419.
27.Fox,Alan. “Industrial Relations: A Social Critique of Pluralist Ideology.”In J.Child ( ed.) , Man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28.—— “Collective Bargaining,Flanders,and the Webb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975, 13( 2) .
29.Hanann, Kerstin & John. Kelly,.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Blyton, Paul., Bacon, Niclolas., Fiorito, Jack. & Heery, Edmund.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8. pp129-186.
30.Katz, Harry., Thomas. Kochan, & Alexander. Colvin,. An Introduction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31.Kelly, John. Rethink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Mobilization, Collectivism and Long Waves, London: Routledge.1998.
32.——.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Kelly, John (eds) Industrial Relation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2002.
33.Kochan, Thomas, Harry. Katz, & R. B. McKersi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1986.
34.Meng, Quan., and Jun Lu. “Political Space in Achievement of Collective Labor Rights: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Workers’ Protest.”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2013.Vol12, No.3, p 465-488.
35.Offe, Claus.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1984.
36.Pun, Ngai., and Huilin Lu.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2010. 36(5): 493-519.
37.Webb, Sidney. & Beatrice.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New York: Longmans. 1914.
■ 责编/ 张新新 Tel: 010-88383907 E-mail: hrdxin@163.com
Beyond the Boundary of Regulations?——Power Relationship Behi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Meng Qu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o tackle strike issues, collective bargaining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strumental mechanism which serves to resolve and prevent the strike. By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typical cases, namely D District and G Province,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bargaining structure was impacted by dual elements, including both workers’ strike and the openness of political space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change was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workers’ economic pursuit. Therefore, the dual effects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clude wage increase and embedding workers’ collective power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route. Trade union, as the mediating organization, promoted the limitation. Arguably, th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hip behind the shift of bargaining structure implies that the wage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can hardly become automatic collective bargaining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workers with the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vention of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trade union.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de union as a mediating organization results in reproduction of consent or resistance via this sor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llective Bargaining; Bargaining Structure; Change of Power Relationship; Workers’ Strike
孟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劳动关系博士。电子邮箱:mengquan1982@gmail.com。
本文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别委托项目“工业园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演化与预防机制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