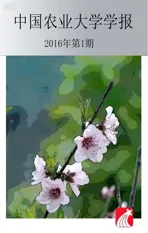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2016-01-25孙旭友芦信珠
孙旭友 芦信珠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
——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孙旭友芦信珠
[摘要]“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关键词]差序格局; 边界冲突; 场; 边际人格; 关系自觉
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提炼出“差序格局”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和亲属关系结构。这一概念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26。这一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经典概念,不仅唤起当代学者重新阐释、发展和验证“差序格局”的研究热潮,而且带来了很多学术性争论甚至研究分歧。大体而言,由“差序格局”引发的当代中国学者争论或者研究脉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重新阐释、批判和发展。这类研究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内涵与特征为主要着眼点,通过考证传统文化、乡土社会结构或宗法制度等,来修正、补充或辨明“差序格局”的合理性与解释局限。例如阎云翔的“差序格局等级论”[2]、翟学伟的“差序格局非等级论”[3]以及吴飞利用对丧服制度的研究纠正“差序格局”的解释局限[4]。二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生活遭遇的现实验证。这类研究主要以差序格局为对话对象,在转型中国社会现实变迁背景中来考察“差序格局”的现实遭遇,进而建构新的理论模型或经验性修正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如“圈层结构”[5]、“散射结构”[6]、“综合性差序格局”[7]等。第三是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预设为乡土中国甚至现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道德观念和资源配置方式,在社会转型语境下考察其对中国经济、法治、民主进程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例如肖瑛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序格局实现自身转化,形成基于理性意志的新差序格局,“理性意志与新差序格局的悖论性结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变得至为艰难和漫长”[8]。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差序格局的现代有效性和作用发挥[9]。学术界将“差序格局”作为一个问题域来进行学术对话,无论是理论修正、经验验证还是效用分析,都是在一种时间延伸、空间拓展和隔空对话等意义上的讨论。也就是说,这种集中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本身的研究,既相对忽视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原初背景、目的意图以及功能指向,也缺少对费孝通本人对“差序格局”想法的考察与参照。
晚年费孝通不仅对“差序格局”早年遭受的批评进行过“自我反思”[10],而且指出了“差序格局”的发展和修正路径。他在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边界问题的反思中提到:“我回想到早年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表达亲属关系的结构形态, 意义并不十分明白。经过这次对话中发生了文化有没有边界的问题, 我才进一步想到用‘场’的概念来补充‘差序格局’的意思”[11]158。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费以后的著述中,我们未能发现其关于如何利用“场”*“场”也是布迪厄学术的核心概念,但是布迪厄聚焦于“场域”的边界性、差异化和冲突,而费孝通却借助“场”的扩散性来弥合不同“场域”间的隔阂,强调场域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就此而言,费孝通的“场”是对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的突破和拓展。来发展和修正“差序格局”的进一步阐述,而且学界对费的这一重要反思和学术思想,也缺乏足够的敏感与重视。但是一个可喜的意外是,年轻学者萧楼较早注意到了费先生早年的“差序格局”和晚年思考的“场”,可以联结起来考虑的思想,并提出了“差序场”的分析性概念来延伸费孝通先生对“差序格局”的晚年思考。立足于转型社会的农村现实、人口流动和人际关系变迁,萧楼提出,“由于家庭经难以涵盖生产和生活,因此,面向更广阔社会的‘职业’也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水池’”[12]290。由 “家庭”和“职业”的链接和交织而成的立体化伦理关系,构成萧楼所言的当下农村社会关系“差序场”的基本图像。回到费孝通论述“场”“差序格局”以及二者关系的原始语境,笔者认为萧楼的研究即使不是对费老思想的曲解,也只是对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思考的误解或可能性之一。笔者发现,费孝通早年“差序格局”与晚年思考“场”的关联性是:“场”不仅是不同行动场域的融合或边界消解的产物,也构成中国文化甚至差序格局的内在构成因素;“场”不仅是当下人际关系交往的结构背景,也是弥合“差序格局”负面影响的有效方式。亦即是说,“场”不仅是嵌入“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要素,而利用“场”特征和作用来补充“差序格局”的内在缺陷,也是费孝通自我修正“差序格局”目的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遵从费孝通提出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研究路径和思考维度,倘若“场”既构成“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化内在的内在要素,又带有弥合“差序格局”的天然优势,那么,费老提议用“场”来补充“差序格局”什么问题?“场”与“差序格局”的内在关系及其机制是什么?“场”可以对差序格局带来什么样的补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回到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原始情景,也需要深度契合费孝通晚年思索用“场”修正“差序格局”的具体文本。
一、边界冲突:“差序格局”对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
费孝通写“差序格局”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讨论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自私”的时代议题。费孝通在“差序格局”一文的开篇就写到:“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1]23。差序格局是费孝通为了应对中国人“私”的生活现实和文化理念,而拓展出来的一个功能性概念。“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1]25。进而费孝通提出,“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1]29。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中国人“私”的直接关系及其意义,在后来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和分析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后来的学者大多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使用“差序格局”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如同吴飞所提醒的,“虽然文化批判时代已经过去,学者们对差序格局有了新的理解,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费孝通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原始语境,因为这一出发点贯穿了对差序格局的全部分析,以及《乡土中国》中很多相关的篇章,也潜在地影响了以后学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4]。这种丢弃“差序格局”原始语境和初始意图的做法,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无限度拓展了“差序格局”的解释范畴和内涵覆盖,进而掩饰了差序格局主要是费孝通针对亲属关系结构、人际关系结构的理论意图。二是消解了“差序格局”对“私”的功能解释力即对“私”的正功能与反功能的辨识以及对“差序格局”自身解决“私”的人际关系的内在机制及其局限分析。因此回到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原始语境、功能指向和社会情境实属必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愚、病、私、弱”被普遍当成中国人的几大痼疾。当时的很多学者都谈到过。例如梁启超就认为中国国民文化素质太低,具体表现在“一曰奴性,二曰愚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幼”,还表现为“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心之欠阀”[13]12。而晏阳初在乡村改造运动中明确提出,“中国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最基本的就是‘愚’‘穷’‘弱’‘私’,四大教育就是为解决农民这些基本问题而设计”[14]434。很显然,作为那个时代具有社会救亡使命感的费孝通也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并且认为:“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1]24。为此他还给出了一个“私”的公式,他说“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1]19。费孝通也跟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一样,从“家庭伦理”“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差序格局的道德维系和“忠孝悌、仁义礼”的道德要素出发,论证了中国人私人道德的泛滥和公共道德的缺少的文化构因和社会因素。“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是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30。虽然寻找私之为病的文化构因,是他写《差序格局》的出发点,但是笔者认为,费孝通作为一位“历史功能论者”[15],更在意的是“私”的现实影响和差序格局的文化功能。虽然“群疏远近”是费孝通批判“私”的主要维度和依据,但是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功能和社会秩序影响,也是费孝通力图揭示的社会功能面向。
另外,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也是为了应对和分析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群己关系。在《家族》一节,他做了如下说明“我曾在以上两章中,从群己关系上讨论到社会结构的格局”[1]37。在费孝通看来,私的实质,就是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的问题。中国“差序格局”文化和群己划分的“私”的理念与行动,既可能带来圈内互助、互惠与团结,也必然带有默顿意义上的“潜功能和反功能”,即圈层隔阂或者群己关系边界冲突[16]84。作为从微观描述乡土社会里个体的社会关系结构和行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不仅描述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亲疏远近的社会事实,也必然揭示了在道德理念和行动实践两个层面使人与人之间、圈与圈之间难以沟通,甚至产生阻隔和冲突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导致的人与人的斗争和利益纠纷。因为中国文化是“差序格局”样态的,群己的界限会随着差序的不同而不同;但不论在哪个层次上,中国人都是照顾里圈的利益,牺牲外圈的利益。而且行动者永远以自己为中心和根据亲疏远近来考虑问题,因而差序格局是自私的、个人化的和变动不居的。另一方面是以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社会圈子”导致的圈与圈之间的边界划分和关系冲突。圈子的对外封闭和对内亲密,会形成无数个不同层次、界限分明、亲疏有别的人际关系圈层。即使亲属关系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具有延伸和叠加性,但是“私人联系的网络”的有界限和群己关系仍然鲜明而可辨。
当然,这种“推己及人”的差序格局并非必然带来人际关系冲突和群体关系紧张的社会失序景象。中国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和无为政治等基层社会的有序性,即是对此最好的明证。这是因为在这种圈层分明、群己清晰的社会关系背后,是道德约束、伦理机制和社会制度安排合法化认同等结构性力量对“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调解和制衡。如梁漱溟“伦理本位”所阐释的“互为对方为重”的儒家强制性义务即“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17]74-81。中国人际关系是一个起始于“差序”,归属于“和”的具体相处过程和社会整体秩序逻辑。因此费老在谈论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特殊之处时才会提及,“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18]。这一例证的提出,显然揭示了“差序格局”内在具有一种弥合群己之别、你我之分和边界冲突的天然本能和道德本性。然而,“差序格局”内在弥合差异化人际关系的朴素能力,显然不能自觉平衡其带有的分化群体和关系分歧的破坏力。于是“私”的人性甚至民族性,既是“差序格局”显性的“反功能”形态,也是费孝通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之一。于是,晚年费孝通提出用“场”来补充“差序格局”的断言,就成为修正和发展“差序格局”以及弥合“私”的人际冲突和圈层隔阂,进而实现中国人际关系自觉的理论指向和实践路径。
二、关系自觉:“场”对差序格局的修正
费孝通所说的“场”对“差序格局”的补充意义,显然不完全等同于差序格局内在的“推己及人”的关系处理方式。费孝通是在何种情景下思考“场”以及阐述用“场”来补充差序格局呢?这需要再一次回到晚年费孝通论述“场”和“文化自觉”的两种原始语境。
第一个是启发式语境即费孝通基于田野调查和文化感知,对民族内部“文化有无边界”的自我反思。费孝通先生基于对人类学“文野之别”的前学科范式的警惕和自身的学术实践,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内在的民族独特性:民族无差别的道德态度。晚年费孝通常说,“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是怀有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种族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格局' 的中国!”[19]在反思和阐述“文化无界线”的学术历程中,费孝通提出文化接触中用“边际”替代“边界”,用“场”来描述不同文化扩散、碰撞和嫁接的事实。“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张出来的影响, 离中心越远, 受到的影响就越小, 成一种波浪形状。这相当于力学里“场”的概念, 适用于声、光、电、磁。场就是一种能量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构成的覆盖面。在这一片面积里, 所受不同强度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深浅、浓淡等等。但是划不出一条有和无的界线。”[20]在反思民族文化“中心—边际”效应和受不同文化影响的“边际人”过程中,费孝通反思了“差序格局”的意义,提出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意思。
反观费孝通反思“差序格局”的启发式语境,作者力图在“差序格局”中植入新的文化要素即中国文化的“中心—边际”效应。中国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或社会差序结构,内在性的具有兼容、重叠和凝聚的本性即“场”的扩散性和无边界性。这是中国文化中“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动指向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移情等在人际关系处理和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具体到“差序格局”,一层层的亲属关系圈或人际关系圈,不仅具有可明辨的圈层和亲疏远近的向心性,而且还具有文化“场”的扩散性和关系的交叉性。“场”内在性的构成中国人亲属关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和人际交往原则。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和民族内部文化交际立场,思考“场”对“差序格局”的补充,笔者可以大胆推测,费孝通先生肯定意识到,人际关系的“场”性,不仅内在于亲属关系的“差序格局”,而且“社会圈子”与“文化场”构成了中国人际关系结构和交往的二重性。另外,日常人际交往和亲属关系结构形态中深受“场”性塑造的中国人,不只是遵从亲疏远近交往关系的 “私人”,也不再是被无数个圈层规划而成的“边界人”或“圈内人”。不同的圈层内的个体,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是一个占据不同圈位、可以跨越不同圈层和穿透不同边界的“边际人”。因而中国人不仅具有阎云翔所言的弹性“差序人格”,还暗含一种“场”性所塑造的人格“边际性”或“边际人格”。从人际关系交往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具有区分你我和推己及人的行动二重性,也具有价值取向上的特殊化与普遍意识的道德态度二重性。这可以说既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旨趣之一,也是我们从中获得的第一点理论启示。
第二个是推延式语境指费孝通把“文化自觉”的认知,从民族内部文化间性推延至民族—国家间不同文化的全球化共存问题。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费孝通同样对“场”的功能性运作提出自己的想法。费孝通说:“由于提出文化是否有边界的问题, 促使我联想到我们当前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上, 若干主要文化正处在大规模的接触、冲突、嫁接, 一直到融合的过程中。我在考虑是否应当引进‘场’这个概念来认识这个过程”[20]。这是费孝通从传统中国文化的“关系和谐”到国际“民族共处”的文化超越和全球视野的拓展。引入“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纠正国家与文化的制度性联盟的强力趋势和自我划界,进而解决“文明冲突”的文化界线问题和秩序冲突问题。“‘场’就是由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 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 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可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那就是在人的感受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规范, 可以自主的选择。把冲突变成嫁接、互补, 导向融合”[20]。费孝通借助“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精神反思世界人类如何相处之道,同时利用“场”的无界性和扩散重叠性,把冲突变成互补,导向融合与共存。这是一种从理论阐释拓展至功能应用,从中国文化推延至国际层面的延伸过程,更是对如何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空间和文化交互作用空间的世界沉思。费孝通对“场”在空间范畴和功能应用的拓展,既是对“场”自身融合沟通与扩散覆盖的功能表述,也同时在映射“场”可以对“差序格局”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交往中“私”的功能纠错。
费孝通早年用“差序格局”体察中国人群己之别的关系结构和“私”的行动逻辑,聚焦于“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道德态度和交往原则给人际关系、社会秩序、道德制度和群体团结带来的负面影响。费孝通晚年力图用“场”的融合性功能来补充和纠正“差序格局”内在的破坏力和反功能。这种自我超越的学术反思和自我纠错,不仅指出差序格局内在的“场性”和中国人“边际人格”所具有的融合与兼顾的自我修复的功能机制,更是一种用“差序场”来纠正甚至替换差序格局的功能性负影响。这里所言的“差序场”对“差序格局”的替代,只是在人际关系处理、交往实践和文化接触中的功能替换,而非对差序格局的结构、实体和作用的取代。日常生活中动态的人际交往和关系处理,既要辨识“差序格局”的结构形态,还要导向“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谐。费孝通提出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意义,另一个意图就是要在功能意义上实现人际交往的“关系自觉”。费孝通是要把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化隐含的“场性”和朴素的道德“兼爱”,提升到一种关系自觉状态,进而构成人际交往的原则以及达成关系和谐的文化依据和社会路径。
三、结论与讨论
从费老的学习和师承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功能的。因而,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待费老如何提出、运用和发展“差序格局”,是推进“差序格局”研究的可行性分析视角。费先生对“差序格局”和中国人际关系(亲属关系)的认知,始终与社会现实的中国人“私”的私利主义和群己之别的群体关系相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理论旨趣是概括中国人亲属结构形态和交往结构,实践指向是对“推己及人”导致的“缺乏公德、差序有别、自利趋向”的社会事实的理论解释,是对群体间利益争夺与社会秩序整合的现实关怀。在着重提及“差序格局”固有的利益矛盾、关系分歧以及边界冲突等消极影响的同时,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论述,相对忽视差序格局导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结论,继而教导人们树立“修、齐、治、平”的积极价值。费孝通借助“差序格局”来分析中国人亲属关系结构和交往逻辑的“两面性”,不仅未能平衡“差序格局”的正反功能,也未及时指出如何弥合差序格局带来的“自私自利”和“边界冲突”等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和谐带有破坏力的路径。
晚年费孝通在反思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与文化“如何做到文化无边界式共处”的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用“场”来补充“差序格局”的研究议题。这既可以看作是费孝通对早年“差序格局”两个遗留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差序格局”理论和应用的路径拓展。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自我修正和发展路径指引,渗透着文化自觉的新思考和中国文化要素的重新嵌入。中国人际关系处理和交往方式不仅带有冲突性和群己关系分歧,还具有“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和兼容、凝聚的文化底色。这是中国文化内在“场”的扩散能力和无界限特征塑造的结果。无界限、重叠、融合等“场”特征,不仅内在于“差序格局”,而且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另一属性。中国人及其关系处理的“差序”和“场”的二重性,塑造了群己关系或亲属关系的“边际人”形象以及行动者“差序人格”和“边际人格”的双重道德价值观。而“场”所具有的融合、嫁接和无界线能力,不仅能对“差序格局”负面的“边界冲突”和关系紧张进行纠错,也可以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文明冲突”。立足差序格局而超越差序格局的“差序场”,不仅可以实现对差序格局的功能替代,也是费孝通力图实现“关系自觉”的路径选择,也可以看作是对差序格局的关系范畴与行为模式及其争论的超越。
遵从费孝通“文化自觉”和以“场”补充“差序格局”的思路,我们还需要讨论几个延伸性问题。第一,如何在国家—民族场域内实现多维度公民身份之可能,是对“场”与“边界”关系问题的探讨,更是对费孝通文化自觉中“多元”与“一体”关系问题[21]的理论深化。这一议题关系到民族、性别、种族、地域、环境等特殊的场所与身份、普遍性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看作是费孝通“差序格局”在公民身份理论的拓展应用。因为二者都在处理“我与非我”“我应该如何”以及“我是谁”等身份认同问题。
第二,如何达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双向连接。“差序格局”带有的“私”的观念和自我中心意识,始终与公共道德、公共意识、公共权利等公共领域相关或相对。因而,如何借助“场”的扩散性和无界限,实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嫁接,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议题。
第三,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多元一体”和“和而不同”等文化相处理念,成为国际学者思考全球文化交流和民族相处的理论之一。而如何借助中国文化特有的融合性、“差序格局”内嵌的“场”因素推动不同文明的融合,以及实现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差序性”和“边际性”与世界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的“有界性”和“冲突性”的链接等议题,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当然,由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等概念及其“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研究路径,可以推导和引申出很多的研究问题。笔者在此只是抛砖引玉,以便启发其他学者的思考和讨论。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4):201-213
[3]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3):152-158
[4]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在反思.开放时代,2011(1):112-122
[5]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9-121
[6]桂华等.散射结构: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青年研究,2011(1):44-54
[7]兰亚春.传统“差序格局”的现代诠释.社会科学战线,2013(5):180-182
[8]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探索与争鸣,2014(6):48-53
[9]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1):21-29
[10]刘忠魏.“己”的二重性:社会结构与主体关系.学术月刊,2014(1):80-88
[1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12]萧楼.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演进,晏阳初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5]乔建.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5-11
[16]Merton.SocialTheoryandSocial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1968
[1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3):15-16
[19]费孝通. 全球化” 新的挑战: 怎样为确立文化关系的“ 礼的秩序” 做出贡献?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2):54-55
[20]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21]奂平清.费孝通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兼论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学海,2014(4):24-32
From “Border Conflict” to “Relationship Conscious”——How Fei Xiaotong Used “Chang” Modified “Chaxugeju”
Sun XuyouLu Xinzhu
Abstract“Chaxugeju” is originally summarized theory tool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kinship by Fei and social structure, also the “private", moral function concept about analysis Chinese “In or Out”, “Circle consciousness”, and also contains negative impact on interpersonal tensions, hidden order and border conflicts. To supplement “Chaxugeju”, by diffusion, cross-border, non-fus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 is cultural reflective of the inherent “Reciprocity” and to reach “He” social order in Fei later year, but also eliminate barriers in real life relationships and to achieve caring practice of relationship conscious. “Cha Xu” and “Chang” duality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structure , actors “Cha Xu” and “Bian Ji” dual personality, constitute the practice logic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theory inspiration of Fei with the “Chang” supplement “Chaxugeju”.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study scope of “Chang” to supplement and amend “Chaxugeju” , need further digging.
Key wordsChaxuGeju; Border conflict; Chang; Marginal personality; Relationship conscious
(责任编辑:常英)
[作者简介]孙旭友,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讲师,邮编:250352;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KS08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3B23714)。
[收稿日期]2015-06-22
芦信珠,山东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