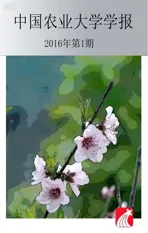“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2016-01-25聂家昕
聂家昕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
——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聂家昕
[摘要]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重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展现了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
[关键词]乡村天主教; 双向祛建制性; 家族团体秩序; 宗教团体秩序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视角
对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进而思考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的动因与特点是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个中心话题。其中,考察分析基督教的传播与地方社会血缘家族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是这一话题的重要构成部分。韦伯指出欧洲父系血缘组织在基督教和国家政权两种理性力量的冲击下,早在中世纪就已销声匿迹[1]。Jack Goody的研究进一步剖析呈现了基督教在地中海沿岸向欧洲内陆社会的传播过程中,教会通过嫁妆、女性财产继承、捐赠制度等方式,解构西欧内陆社会之前的父系血缘组织的漫长历史进程,并认为这形成了欧洲社会的个体主义传统,进而造就了欧洲近代社会的转型条件[2]。与欧洲社会的研究相比较,在中国汉人社会的研究中,虽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在根本上与中国社会的家族组织是不相容的[3],但立足田野的研究却表明,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①从基督教教派的分化进程来看,韦伯与Goody所指的基督教实际上是罗马正教,在中国被称为天主教。本文中笔者仅面对中国社会天主教的研究成果与相关议题,而不涉及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传播不仅没有产生发生于中世纪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4-6]。所以,这种差异缘何产生,就成为了一个需要追问的话题。
揆诸已有工作可以看到,学界的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下视角。其一,是在宗教文化结构的角度内进行的对比思考。总体来看,这一类工作的考察点多着落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体系与中国本土宗教信仰体系的结构类比层面。在这一维度之内,诸多学者认为天主教能在血缘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传播的原因在于,其本土化之后的教礼体系与中国本土大、小传统文化的结构类似性[7-9];其二,与前者有所关联,一些研究强调早期天主教差会、传教士的宣教策略,以及身为地方社会能人的早期皈信教徒的作用,认为这是天主教能否在华顺利传播的主要微观因素[10-12];其三,是在关注前两者的同时,将思考的重点进一步放置于外部宏观秩序的考察,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国家总体政治秩序更迭变迁对于天主教的影响,在这一线路中有学者直接否定了文化结构在宗教信仰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在19世纪后期的中华帝国中,天主教能够与本土宗族、家族相结合的动力在于教会能够为这些血缘群体提供经济、政治与法律维度的资源[13-14]。而这一切都与帝国政治、儒家技术谱系等能够提供声望、权利、财富的传统手段的衰退有关[15]。
对此,本文认为宗教文化结构角度内进行的对比思考,虽然一方面提供了相关的文化认同解释,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够对19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屡屡发生的天主教信仰与本土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情况作完满的解释。此外,这一判断还与伊利亚德[16]、卢曼[17]等学者认为基督宗教(包括所有基督教教派)线性时间观与一切传统宗教信仰的轮回式时间观念根本不同的观点相左。围绕传教士等宗教达人开展的宗教人物考察,呈现了宏观历史过程的微观细节。但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对个体行动者、微观细节等要素作深层次的类型归纳。因此,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与血缘家族组织相互融通的问题,在考察广度上不能仅被归结为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在内涵深度上也不能仅停留在行动策略的考察层面上。
由外部宏观秩序条件出发所作的进一步思考,在强调国家这一重要的体制性因素的同时,也将教会作为一种等量的制度性因素进行了考察,这凸显了宗教行动主体信仰选择的体制动力根源。但这些工作又多将宗族组织或者更广义上的血缘家族组织,设定在静止不动的供给接受状态。而实际的情况是,汉人社会的家族(宗族)组织是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传播过程的能动回应者,而且这一回应过程还因随国家形式的改变(在根源上是合法性来源的性格改变)而不断发生变迁的家族(宗族)组织的建制性而更加复杂。因此,天主教与中国本土社会血缘秩序关系模式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在关涉国家性格因素的前提下,将天主教与家族(宗族)组织均设定为能动行动者的条件下进行考察的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将在天主教教会组织与地方宗族(家族)“双向祛建制性”的维度内讨论乡村天主教皈信者的血缘家族一体化问题。本文中“建制性”概念的界定来源于卢曼宗教社会学理论对于传统宗教统合诸领域的制度潜能的阐述*建制性概念的主旨在于表明,中国本土家族组织与基督教教会的制度形成潜能。与学界经常使用的“制度性”有所不同,建制性更多强调组织形成制度的潜在能力,以及这一能力发挥作用的外在结构条件,而制度性强调的是组织现有的外在组织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可看做是建制性在不同外在条件下的制度实践后果。,相应的“祛建制性”指这种潜能的褪祛失魅状态。进一步地,“双向祛建制性”所关涉的是国家、天主教与本土家族(宗族)的三方结构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当下时段内这三方关系起源于明末清初。这一历史节点之后的传统帝国及其民族国家的转型历程,圈定了天主教与血缘家族(宗族)组织的基本关系。对于传统帝国社会而言,奠基于礼乐文明基础的国家与天主教的教会组织在根本的建制合法性上是互相冲突的。同时,由于分享礼法秩序的能力,决定了血缘家族组织基本建制能力的强弱,以及自身的规模大小。因此,当传统帝国可以有效履行终极建制功能来供给整体社会公共秩序时,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社会的地方血缘家族组织与天主教的教会组织是不能相容的*当然,本文并没有忽略这一时期少部分皈依天主教的家族组织。但就宗教选择的动机而言,这一部分家族组织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因为不满儒学体系的空洞说教和派系斗争而选择天主教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早期的皈信者是不满意当时帝国提供的社会公共性的。。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传统帝国担纲的整体社会公共性的式微,一方面削弱了礼法秩序对于地方家族(宗族)组织的示范指引作用,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天主教在建制性方面的终极竞争因素。这一变化的一个结果是,19世纪中后期大量皈信者因实际利益而非虔诚信仰加入天主教[18]。而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催生了其后的社会冲突运动。20世纪初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民族国家转型过程,因对传统合法性来源的否定,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建制能力的属性。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一方面中断了作为传统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族(宗族)的合法建制性,另一方面也在世俗主义的维度内于组织社会的功能层面消解了天主教教会的建制性,这即为本文所指的“双向祛建制性”过程。
在此研究理路中,本文将对居住于冀中赵村的乡村天主教皈信者群体(基本上都是骆姓村民)进行思考。其中笔者感兴趣的是身为整体骆姓家族之组成部分的骆姓教友,是怎样以及如何处理集于其一身的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身份关系的?对此,本文将通过展现村落生活中骆姓教友,对世俗生活中的“家族团体秩序”(这一团体包括奉教与没有奉教两部分的骆姓家族成员)与神圣宗教维度内的“宗教团体秩序”(这一团体仅包括奉教的骆姓家族成员)的一体化处理过程,勾画当下村落社会中天主教皈信者血缘一体化的社会事实。并进一步的在教会制度与本土家族制度的“双向祛建制性”维度内,讨论这种一体化的制度动力根源。
二、两种团体秩序
(一)家族团体秩序
位于冀中地区太行山东麓的赵村是笔者开展田野工作的地点*按照惯例,文章对村名以及田野工作的对象人群姓名进行了加工。。据县志记载,村落历史可追溯至明初,最初村内居民均为赵姓。其后,村落社会几经变迁,形成了现在分属于20个姓氏、22个家族约4 000村民的村落。作为村落社会的基本社群单位,“家族”在赵村的村落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与华南社会宗族研究[19-20]有所不同,在华北社会的研究中,学者普遍注意到这一地域的人群组织与华南区域研究所界定的经典宗族标准的差异,进而做一定标准的修正而继续运用宗族概念。于此,本文认为由于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宗族一直是与中华文明的政治体制相牵连的*相关研究表明,宗族是一种聚合政治、经济功能的社会制度。宗族的成立需要有严格的标准,其根源动力在于封建和帝国时期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礼法制度。,它是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过程中标示其组织内涵的。在强调宗法秩序的传统社会,宗族是在分享国家礼仪标准进而力图经由祭祀、科举等方式参与传统帝国社会政治过程的父系血缘团体,并因此具备族产、宗祠、族规等相应制度设施。与之比较,赵村的情况是至少上至清末村内绝大部分的血缘继嗣群体便无祠堂、无祖茔、无家族谱牒。在当下村落社会中同姓之族能够拥有的仅仅是模糊的祖源认同*这一方面的情况虽无正式史料记载,但可通过其他的田野工作间接证明。比如,通过村落亲属关系图的绘制可以发现许多1900年代左右出生的村民仅有如李和尚、张淘气、王物件之类的诨名,而无正式的称谓,以及村内人均不能追溯其所属家族的开基祖的现象,大体可以推见至少上至清末村内的许多家族没有文字能力,因而无法形成相关的宗族制度以及清晰的祖缘记忆。。所以本文用家族这一更加泛化的称谓来指称这些血缘继嗣组织。
对于赵村的家族组织而言,由其成员分享的“家族团体秩序”提供了家族整合的基本标准。总体而言,汉人社会传统的“家族团体秩序”具有传统儒家思想着重探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偏重于对“人”做社群关系的定位与思考的特点。通过对“五伦”以及亲、义、别、序、信的基本社会规范尺度的强调,这一秩序表现出鲜明的差序性[21-22],并由此维护生产了传统社会的差序性礼法秩序。但1949年之后的民族国家化过程,对传统家族那种具有政治潜能的“家庭化的社会组织模式”[23-24]的祛建制过程,使得家族组织的诸多公共职能(包括社会总体性公共秩序的生产功能)不复存在*虽然,近些年关于“宗族再造”现象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下的宗族(家族)组织仍然会对地方社会产生某些方面的影响。但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当下宗族的相关活动不再具有体制合法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赵村而言,虽无正式史料记载,但从亲属关系图谱所显示的姓名称谓,以及家族内没有谱牒的证据来推测,历史上村内的大部分家户中没有受过儒家教育的成员,因此没有能力形成正式的文字族谱,和形成清晰的祖源记忆,而这一切多少限制了这些家族参与分享礼法秩序的建制性能力。在当下的村落社会中,经历了1949年后的祛建制化过程,村内家族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家族秩序层面,对于由“家”“门”“户”的标准所表征的家族体系,人们更多的是依靠户内的日常家计生活来进行自我定位,而“门”与“户”的观念则仅仅在婚礼与葬礼的仪式过程才被表现出来。
首先,从“家”的标准层面来看,赵村的家族虽无谱牒,但村民基本可以通过“红白”事的仪式运作过程对“家族”进行清晰区分。一般来说,每有红白事,每个家族下面的每一门都会有一个“主事”的人到事主家去商议安排整个仪式。同时,由于现在村民的婚礼与葬礼均在家中操办,因此在仪式过程中每一门中也都会出人到事主家中帮忙。当然在仪式过程中,也有邻里朋友前来帮忙。虽然,这些人连同非本门的同宗成员都被称为“执事”,但“总管”(执事们的领导者)基本上都由同族成员担当。一般在婚礼或葬礼中会按照烧水、端菜、端馒头……的不同活计设置几个总管来组织协调众多执事。在村中这些帮忙的人的名单会被写在一张“执事单”上,并与“礼单”和“乡谊单”*“乡谊”是村民礼物交换行为中一类人的称呼,这类人一般拿很少的礼金,因此也不会参与仪式宴饮。当地人用乡谊的称谓将其与正式随礼并参与宴饮的人做区别。一同张贴于事主家的大门口处。这样,通过整个仪式过程,家族的整体界限得以呈现。
其次,就“门”的层次而言,村里人在强调其所属之“家”的范畴之后,如果遇有进一步需要详细说明的情境时,便会用“门”这一概念来进行下一步的划分。如村内许家分为“龙、凤、德、秀、仁”五门*许家在村内的情况较为特殊,据说其祖上曾有中举人的家族成员。这可能提供了其“龙、凤、德、秀、仁”的五门称谓的文化资源。,赵家分为“东、中、西”三门,但更多的时候村民只是知道这一家有几门,具体到哪一门如何命名就说不清楚了,因此他们经常会说“我们不是一门的,我家是什么门我也说不清”。而就“门”内的亲属关系而言,其强调的是五服之内的概念。所以“门”是一个有明显血缘关联的群体。此外,如前文已经介绍的,在每门之内均有一两位常任“主事人”。他们除了参与操办红白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调停家族内部纠纷之外,基本不见其他社会功能。
最后,就“户”的层次来看,赵村村民基本上是在“联邦家庭”的意义上来对其进行界定。一般来看,村内的这种家庭是由三代以内的核心家庭组成的,即祖父母家、父母家、子女(家)。在生计上,核心家庭每户有自己的收支,但是一般均会分担父辈或祖父辈的一些生活开支。在日常的生计劳动中,换工也基本上以这些核心家庭为主,在兄弟之间(宗亲方面),或姐妹之间(姻亲方面)来进行,其范围一般不会超过联邦家庭的范围。在对先人的祭祀上,祭祀成员的规模也不会超越宗亲中的三代以外家庭。
这样,由上述的三个层次来看,赵村村民的家族秩序就在“家”“门”“户”的概念层次中表现出明显的由远及近的差序性。但这同时也凸显出因建制功能萎缩而更多仪式象征意义的“家”“门”观念,与由日常私人生活所表达的“户”的观念在村民生活世界中的不同地位。
(二)宗教团体秩序
现在赵村有300多位天主教教友,他们中除了一位受洗两年的张姓教友和一对2009年春季受洗奉教的裴姓母女之外,其余的教友均为骆姓。因为,是骆姓家族五门中的三门,因此其他的村民称这些骆姓的教友为“奉教骆家”,以此区别同一家族之内不奉教的骆家成员。从祖上首辈皈信者到今天,奉教骆家的奉教历史已有百年。历史上骆姓教友归属于天主教遣史会正定教区,1949年后这一教区更名为石家庄教区,“文革”时期宗教活动被取缔,1980年代之后得以恢复。对于最初皈信天主教的原因,有骆姓教友介绍说其祖上有妇人曾具有领神的灵媒能力,后经常处于“着魔、中邪”的状态,家人对此毫无办法。但这种状态一到教堂中就可缓解,妇人遂开始奉教。其后这一门骆家人也逐渐都皈信天主教,并最终带动另外两门加入奉教行列。对此,由于无文献记载所以无法精确考证。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再次管窥的是骆家祖上应该是没有成员接受儒学科举教育的,因而也就无宗族式的族规家法。所以骆家才会有从事民间信仰的灵媒,所以才有可能较为顺畅的集体信奉天主教。这使得骆家人开始接受天主教教义,并拥有了相应的宗教团体秩序。
从教义看来,天主教的宗教团体秩序是导源于其“人观”理念的。天主教认为,人在本体上是由天主按照自身肖像创造并赋予灵魂彼此地位平等的产物。在社会层面上人由造物主获得权力,管理世间万物;在永生人的层面上依靠领洗、信有天主与天主一同生活而灵魂永存。为了实现永生人的目标,人需通过密契生活加入耶稣基督的神圣生命之中[25]。由于在基督宗教的现实宗教实践过程中,皈信者的密契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共同的弥撒或团契形式中,通过经年复始的具有明显时间节律性的宗教仪礼实践来进行的。因此,连同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教派的团体秩序的生产与运作,便都表现出明显的时间性。对于时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它与特定的文化体系的相应宇宙观,以及进一步的关联性政治权利有关。因此对时间的掌控为权力的掌控与分配提供了合法性来源[26]。在非西方社会,直线性天主教格里高利历法与传入地本土时间观之间的关系,直接关乎的是两套时间观背后的建制体系之间的权利关系。人类学民族志对南美与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研究表明,与殖民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天主教的传播,通过推行强调拯救秩序的仪式历法,瓦解了当地社会的旧有意识形态,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27-28]。在中国社会类似的过程有所不同。明末以来天主教的建制性一直都受到国家与地方的多重限制,这使得传教士采取了与中国本土历法体系进行磨合而非完全取代的策略[9]11。由此天主教的宗教团体性便只能在教礼仪式与本土世俗生活秩序相交织的时间节律中被间歇表达。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现代民族国家进程将这一特征进一步加强与固化。
这在赵村也有明显的表现。从教友个体的层面来看,赵村的教友也都要经历儿童洗礼、成人入教洗礼、坚振仪式、圣体敬礼、忏悔礼、圣秩授予礼、婚礼、傅油礼、葬礼,这一系列的人生礼仪。这些圣事使一个人得以成为天主教徒,或者进一步获得神品圣为神父,进而由此标示其宗教皈信者身份。在群体层面上,通过复活期、四旬期、圣诞期以及降临期的划分,以及相应周期内主日、庆节、纪念日的安排,天主教教友会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时间观念,并由此在群体上显露出独特的人群特征。在经年循环的圣事与仪礼的实践过程中,在对宗教教义的重复讲解与理解中,这种宗教性的团体秩序造就了一种与其他村民生活有别的社会事实。
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形态的人群组织秩序却并没有超越于宗教生活之外。如为了协助神父处理日常的宗教信仰事物,村内的教友会选出教会会长与副会长若干名。在已婚女性教友中设有亚娜会,并选有亚娜会会长及制定会规。“会长”(lay leader)即世俗领导,一般均由虔诚的有能力、有威望的教友担当,因此会长往往就是同一家户中各门的主事人。亚娜会是由已婚妇女组成的组织,其会长也需要具备前述会长的特质。在教友群体中,教会会长与亚娜会会长的角色,基本上都在特定的宗教活动中凸显,在日常生活中则没有特别之处。换言之,这种教友团体的群体秩序的表达是与宗教活动的时间性相关的。
此外,就宗教仪礼过程中人之位序的再安排过程来看,婴儿在出生后受洗的过程中,会选择年长的教友为“代父、代母”并获得圣名。代父、代母可能是婴儿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教友。而与此同时,婴儿的爷爷、奶奶又可能是其他教友的代父母,这样就可能会出现婴儿与其长辈有同一代父母的情况。因此在宗教活动期间被凸显的代父、代母关系就间歇性的对父系家庭的中的位序进行了重新的组织。在普通教友与神父的关系上来看,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神父由于获得了神品,因而与普同教友不同。在宗教生活中,即使是神父的长辈,也要跪拜于神父面前。这样,可以看出在宗教仪礼的实践过程中通过人之位序的重新排列,天主教教友们践行的是在天主面前均为子民的平等观念。但这一切仅限于宗教生活的过程之中,当宗教仪式结束,一切血缘伦理的序位关系就又一如既往*Jack Goody 的研究证明,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代父、代母与其宗教监护人之间具有超出宗教关系的财产继承关系,这种神亲体系对当时欧洲社会的社会组织的解构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村落天主教的血缘家族一体化:两套团体秩序的一体实践过程
(一)“家族团体秩序”的实践过程
赵村的天主教教友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家族体系之中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体现出家族团体秩序。按照村内人对家族成员“家”“门”“户”的划分标准,结合骆家的特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现奉教骆家对于家族团体秩序的实践过程。
如前文所介绍的,村里人是通过“红白”事的人生礼仪来表现他们为一个家族的事实的。对于教友与其所属的家族而言,这种方式也是适用的。具体而言,从红事(婚礼)方面来看,每对进行婚配的年轻教友,都要在教堂进行婚配弥撒,其后或者直接或者间隔三两天进行世俗的婚礼。在世俗婚礼的过程中,新婚夫妇首先祭拜的是耶稣像。具体过程是伴随着主婚人“一感谢主赐予生命、二感谢主赐予智慧、三感谢主赐予财富”的说词,新人要对耶稣圣像鞠躬三次,然后新人才开始敬拜父母。其后按照当地的民俗,人们开始戏弄公婆——这个过程中公婆的脸经常会被墨汁装扮得一塌糊涂。之后人们在欢笑中开始抛洒喜糖。在整个婚礼的世俗部分中,同家族成员各负其责。2009年5月,在一个骆姓教友的婚礼上,笔者亲见了这一分工过程。由于这个教友所在“门”的主事人是骆文德,所以他就自然地成为了总管或称为“执事头”,而其他四门的主事人中也有两位被选为了总管来协助骆文德。他们的责任是接待来客,酒席宴间敬酒表达谢意,照顾各桌客人。在其他具体事务上,骆家还分设了(记账)先生、厨师、看火、端盘子、烧水、打水、取馒头等执事,与其他村民家庭相同,这些执事均由骆家的成员来担当。在这次婚礼上,没有奉教的骆家中的一门的主事人骆校长的职务是记账先生,而村内本堂神父骆神父的二哥的职责是“取馒头”,按照他自己的介绍就是“负责给每桌端馒头”。
而就教友的葬礼而言,期间除了宗教部分的安排之外,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家族性的因素。一般来说,除了不烧纸的禁忌外,吊唁期间一般村民会到亡者家中随礼并凭吊亡者。在教堂内为亡者举行的仪式,对于普通村民也是开放的。对于教友所在家族而言,整个家族的每个分支都必须有代表人作为葬礼执事前来帮忙,他们的名字会用白色纸张书写,与白色的乡谊单、礼单一同张贴于村民家的大门口处*作为神职人员“神父”不会参加婚、葬礼的世俗部分。对此,教友们的解释是神父是脱俗了的人,因此不能参与此类世俗活动。。这样,无论从婚礼还是葬礼的过程来看,在“家”这一层面上,教友们在表现自身教友身份的同时,也表现出其归属于整个“骆姓”家族的事实。
其次,就“门”这一强调“五服”的标准来看,它在整个“家—门—户”的结构中处于一个中间过渡的状态,是村民们进一步结成“家族”的中间状态。在红白事的筹备过程中,门的范围与意义体现得尤为明显。按照赵村所在地区的通行做法,在红白事仪式正式进行之前,事主家要邀请其所在家族各门的“主事人”来家中商议具体事项。红事中内容大体包括,婚礼前与媒人约定一同前往女方家确定吉日、迎亲队伍的组成,以及确定婚礼中的客人名单等。在诸种事务商定之后,事主所在“门”的主事人会与另外一两位同族的他门的主事人一同到女方家中进行协商并下聘帖。如果是女孩子出嫁的话,主事人的任务就变成了在家中等对方人员登门进行协商,并作为重要的送亲人员,在婚礼当天护送女孩子出门。这些对于村里的骆姓教友而言也是适用的,在正式的婚礼仪式之前,骆家五门的主事人也会汇集于事主家中商议相关事项,在此过程中没有教友与非教友的区别。2009年10月,笔者在村内亲见了神父二哥的儿子的婚前会议。由神父二哥一家捎话,在当天晚饭之后,各门的主事人被请至家中。经过神父二哥与家族中主事人商议约定了与媒人一同前往女方家的具体日期、彩礼等相关事项的准备方案,以及给予媒人的酬劳等。其后由骆神父的大哥(神父所在门的主事人)书写了聘书。
在白事(葬礼)中,家中的主事人也要聚集在一起商议相关事宜。此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年轻的教友在其门中老年人去世之后也要披麻戴孝。虽然,披麻戴孝的年轻教友的人数范围可能会因亡者的辈分而有所伸缩,但不会超越于“门”的范围。在此意义上来说,就是超越“五服”的不用披麻戴孝。由此,可以看到除了一些具体因宗教因素造成的特殊不同之外,在具体的家族团体秩序的实践过程中,骆家的教友并没有脱离骆家而去。在“门”这一层面上,他们既因自己的宗教身份在一定的场景内表现出特定的族群性,但是在另一个更广义的范畴内依然与一种本土性的地方范畴保持一致。
再次,在“户”的层面上来看,村里骆姓教友的家庭组织模式与一般家庭的组织模式相差无几。在生计方面,教友家庭也是以核心家庭为主。在相关的生计活动与老年人的赡养行为中,教友家庭也会因应表现为“扩大家庭”与“联邦家庭”的形式。例如,在秋收活动之中,教友家庭的主要换工对象也与一般村民家庭相似,主要在同一家户的兄弟家庭间,或者姻亲中的连襟家庭间,或者好友、干亲*干亲是当地人通过给孩子认“干爸、干妈”而确定的拟亲关系。家庭之间完成。对于先人的祭祀,教友们称之为“追思以往”。一般来说,除了“圣”为神父的家族成员亡故后会被安葬在统一的神父墓地之外,村内骆姓教友在去世之后也会像普通村民一样被安葬于其自己耕地之内。于是在村边耕地中经常可以看到集中一处的同一门家族成员的墓穴。与其他村民的墓穴比较,教友的墓穴除了没有墓碑之外也无茔门,所以看不出阴宅的朝向。但适逢年节或者相关的宗教性节日,教友也会到田里墓穴边追思先人。只是在具体的细节上,教友们会咏颂相关的经文并洒播圣水。这虽与普通村民烧纸上供的祭祀行为有所不同,但是就祭祀的主体的结构来看又有相同之处,即教友也是以联邦家庭为单位到此门的墓地进行祭祀。这样在实际的田产权与阴宅的分布上,就形成了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由此,每一户教友家庭就又在祭祀这种象征行为中,表征了家族团体秩序。
(二)“宗教团体秩序”的实践过程
按照是否具有“神品”的标准,赵村教友的宗教团体秩序是由神父与普通教友两类人的宗教活动过程组成的。
首先,就神父的活动过程来看,在经历严格的神学教育完成修士的课程之后,一个普通教友经过晋铎仪式就可以获得七级神品成为神父。一般来说,在成为神父之后,神父本人要到异地的教堂去从事神职工作(牧灵)。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存在,如在神父身体不好等情况下,教区可以安排神父到距父母或兄弟姐妹家较近的地方工作。在工作内容方面,“服务圣道”、“服务圣事及圣体”、成为“天主子民的领袖”是神父牧灵的主要内容。骆神父是笔者在赵村中最为熟悉的人,他是两个教堂的本堂神父。每个周末早晨五点左右,骆神父就起床洗漱,开始准备第一个教堂的主日弥撒。六点左右,在教友基本上都已到教堂并进行过晨祷之后,伴着进堂曲身穿祭衣的神父会步入教堂,之后伴随洒圣水的圣歌神父会走下祭台,甩洒圣水。然后,在读经、讲经、互助平安之后,教友们会唱着圣歌排队前往祭台前领受圣体。之后,教友们会再做晨祷,这样在教友们的读经声中弥撒结束。在此之后,神父还要驱车赶往另外一个教堂主持弥撒仪式。由于领受圣体之前不能吃饭,所以神父吃早饭的时间一般会拖到九点之后。除了这些固定在周日的弥撒外,适逢其他的如复活节、圣诞节等主日,神父也要进行同样的活动。此外,遇有教友生病、病危,或婚礼,以及故去神父祭日,神父还要主持傅油圣事、婚庆弥撒,以及追思以往的宗教活动。每个月末,骆神父会与同一教区内的神父到教区的总堂内进行“避静”活动。通过这种灵修的方式,神父在互相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加深自己的信德。总的来说,神父每日的活动主要围绕宗教领域展开,而很少参与日常的其他非宗教活动。在这样的安排之下,神父在整个宗教秩序的实践过程中,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
另一方面,就普通教友群体而言,与每日的早晚课、晨晚祷交织的宗教活动是平日里的普通弥撒、周末主日弥撒,以及更为重要主日(如复活节、圣诞节)里的大瞻礼弥撒。
早晚课、晨晚祷是教友们每日必须进行的宗教活动。其进行的顺序为,每日早五六点钟教友在自己家中跪拜在圣母像前进行早课,之后八点左右到教堂内进行早祷。每日下午四点左右,教友们会到教堂做晚祷,之后接着进行的是每晚九点左右的晚课,与早课相似这个仪式一般也由教友独自在家中圣母像前跪拜完成。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也会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如年轻的教友每日需要早出晚归到外工作谋生或者外出求学,因而在时间上就难以保证,所以只有年纪较长的教友能完整地完成每日功课。与每日进行的日常功课相比较,弥撒仪式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天凡是在村内没有外出的教友,基本上都会到教堂内望弥撒。即使是临时有事错过此一堂口的弥撒,教友们也会到邻近堂口内参与仪式。到了复活节、圣诞节等大瞻礼时,那些平日忙碌的教友也要尽量空余出时间,参加相关的弥撒活动。
此外,在每年的特定时期之内,教友们会分批进行“避静”活动。在赵村一般是每年七月末亚娜会的女性教友会齐聚教堂进行避静活动。在此活动中,这些女性教友们会在亚娜会会长的带领下,反思自己在言与行上的过失。并讲述自己依靠信德度过这一年中最为艰难时刻的体验。当然其中会涉及到许多日常生活中妇女需要面对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一类的问题。村里男性教友的避静活动多安排在每年农历春节前后,因为这时教友们都在家中,因此人员齐整。在避静的过程中,除了相关教义的学习之外,对自己言行的反思,以及对信德的坚振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这样,与神父的宗教实践过程相比较,教友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宗教团体秩序就由于叠合了世俗生活的因素,而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从宗教仪式的程序来看,这种过渡特征虽发生于空间的转换、参与者规模的伸缩过程中,但其深层的动力节奏机制却根源于宗教仪轨的时间安排。其间,每个教友都会经历每天由家屋空间的每日功课到教堂祈祷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友会经历每日功课的个体到弥撒过程的教友团体的转变,以及普通弥撒到特定主日弥撒的升级过渡,这其中宗教团体秩序会被逐步的升级表达。但在这一切宗教性仪式生活之后,每日的世俗生活又将来临,人们又要复归家族团体秩序。
由此可以看到,赵村天主教教友的宗教团体秩序(除了神父之外)与其家族团体秩序之间是渐行渐远又渐行渐近的。通过上述的一套仪式过程,教友们在进行凡俗与神圣的转换过程中,也同时实现了自我身份由凡俗向神圣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性的团体秩序伴随着日常功课到弥撒仪式被渐强地表达出来,并最终在群体规模上实现了教友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划分。其后,在复归凡俗生活的过程中,俗世生活的团体秩序又重新浮现,于是二者便实现了有机地连接。
四、结论:“双向祛建制性”与两套团体秩序的连接
马克斯·韦伯认为基督教在根本上是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生共同体相对立的[29]。但是,赵村天主教教友对两套团体秩序的一体实践过程,却表明了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存有的天主教的宗教体系与本土地方血缘家族一体化的事实。对此,本文虽不排斥文化相似性角度内的相关理解,但更强调对外在体制性的说明。
赵村的田野经验显示,祖源、族谱等要件的缺乏使得村内的大部分血缘继嗣群体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组织,并同时表明这些血缘继嗣群体缺乏科举等进一步的参与整体政治过程的建制能力。这可能是当初骆家有妇人灵媒,以及天主教能够顺利传入骆家,并在传入后与其他同族非教友和平相处的重要条件。1949年之后,在新的国家政治化过程中家族被进一步消解,并在根本上失去参与整体政治过程的合法性。1980年代之后,家族虽有所恢复但仍然不具有政治参与的合法性,在赵村这一建制性的消解过程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家族公共职能的消失,村民对“家”“门”的象征化认识,以及更多集中于“户”这一层次的家庭伦理秩序定位。因此,祛建制化的家族,构成了天主教在赵村社会传承的一个非限制性原因。
另一方面,就天主教的宗教体系而言,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将对神圣性的理解归入历史中进行,这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宗教跳出历史寻找轮回的特性[30]。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基督教也受到古代宗教的影响,饱受轮回观念的困扰。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建制性教会的宗教精英阶层作为教义理解与阐释的担纲者,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这种困扰[31]。但当大而全的建制性宗教因社会演化而被消解时,凸显历史时间主题的宗教,即使不与各种传统宗教发生粘合,也只能是在一个有限范围内独善其身。在中国社会,1949年之后中国式民族国家化过程中的教会国家化,使得国家全面替代了以往教会承担的那部分社会功能与信仰负担,并进一步产生了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在建制上分裂、文化能力上限于停滞状态[32]的后果。伴随这一后果一同出现的是之前中国教会组织有限建制性的消解。于是,与西方宗教系统因整体社会演化而使基督教信仰通过凸显教义理论的历史时间主题来达成宗教意义的结果相仿[33],祛建制化的中国社会的基督教信仰所能担纲的也主要是线性时间概念中的宗教仪式实践,在赵村它表现于教友宗教团体秩序的运行过程中。这是天主教在当下的村落社会中能够与家族秩序相连接的内部原因。
实际上,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天主教与血缘家族组织的关系模式,在根本上是受整体宏观政治秩序影响的。诸多材料表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乡村社会的传播,多与当时社会动荡、整体政治秩序不稳,地方家族组织没有能力、没有途径或不热衷参与帝国政治相关*晚明时期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信奉天主教的事例均可为这一判断提供支持,学者的研究表明杨廷筠、徐光启、李之藻均失望于晚明时期儒家道德体系的崩解,虽参与过朋党之争但终感厌烦,进而以图通过信奉天主教重新理解进而重建道德秩序。,这为建制性的天主教提供了传播的空间。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整体性支配秩序的变迁,在完全消解传统社会的家族组织基础的同时,也完全祛除了包括政治功能在内的天主教的有限建制性。在这个角度看来,当下村落社会的家族组织与天主教之间的相容共处关系,可能较传统社会更为容易达成。更进一步地,在这一角度内对个体解放与现代性之崛起的经典社会学议题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创造,除了根源于基督教自身的宗教性格之外,更在于其形成于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宗教、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关系。与之比较,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基层的家族(宗族)组织还是制度性宗教组织,都只能是在由国家供给的整体性社会秩序的范围内定义自身,并圈定相应的行动内容,因而均不能成为形构社会的完全行为能力者。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应该仍将起决定作用。
[参考文献]
[1]Weber Max.TheReligionofChina,New York: free press,1951
[2]Jack Goody.ThedevelopmentofthefamilyandmarriageinEurop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Madsen Richard.China’sCatholics:TragedyandHopeinanEmergingCivilSocie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5]张先清.官方、宗族与天主教.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6]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7]秦家懿,孔汉斯.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8]张先清.清中叶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6(1):33-40
[9]梅欧金.“天主实义”在福建:在两个世界、两种时间之间//司徒琳,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0]Tsou Mingteh.Christian Mission as Confucian Intellectual:Gilbert Reid (1817—1927)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ChristianityinChina:FromtheEigh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1]Robert E Entenmann.Catholics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Sichuan∥ChristianityinChina:FromtheEigh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2]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1999(4):43-60
[13]Paul A cohen.ChinaandChristianity.Californ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14]Esherick,Joseph.TheOriginsoftheBoxer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5]John R Shepherd.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ChristianityinChina:FromtheEigh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6]Mircea Eliade.ThemythoftheEternalRetur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17]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刘峰,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8]狄德曼.华北的暴力和恐慌.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9]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潘小慧.迈向健全的人:儒家的人观.台湾:应用心理研究,2001(9):115-135
[2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德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4]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5]罗光.天主教的人论.台北:应用心理研究,2001(9):157-166
[26]Nancy D Munn.The culture anthropology of time:A critical essay.AnnualReviewAnthropology,1992(21)
[27]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8]Rickie Burman R.Time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on simbo,dolomon Islands.Man,New,1981(16):251-267
[29]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Ⅴ: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慧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0]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1]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慧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2]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刘小枫,著.圣灵降临的叙事.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3]卢克曼.无形的宗教.覃方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The Bidirectional Disconstitution and the Clan Integration of Rural Catholic——A Case Study on Rural Catholic in Zhao Village, Hebei Region
Nie Jiaxin
AbstractInstead of collapsing traditional clan happened in the Europe, the spread of Catholic in rural China specially merged with clan within a certain rang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fact that a group of rural catholic believers( in Zhao Village in Hebei Province), belong to the same lineage, handle their dual identity including blood kinship relations and Catholic faithful with an integration method. As for the bidirectional disconstitution process, the nation-state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for such integration. In this sense,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ountry driven by a strong executive power, inherited the same way from the late 19th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related issues.
Key wordsRural catholic; Bidirectional disconstitution; The order of clan; Religious order
(责任编辑:常英)
[作者简介]聂家昕,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邮编:110034。
[收稿日期]2015-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