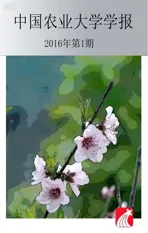生计与生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经济与农民日常生活——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①
2016-01-25马维强邓宏琴
马维强 邓宏琴
生计与生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经济与农民日常生活
——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①
马维强邓宏琴
[摘要]在集体化时代,为保障农业集体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并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国家通过经济制度安排的约束、政治意识形态的引导以及社会流动上的限制等手段使农民投身于农业生产,但劳动安排和工分管理的不足使集体生产产生困境。一些农民往往跨越国家政策规定的界限进行手工业劳作和倒买倒卖,这些手段被赋予了政治含义,受到约束限制,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戴上“帽子”,成为“阶级敌人”。不过,村民依然通过非农业劳动甚至偷盗来获得生存所需。农民的生存理性和村庄传统对于农民的生计观念和谋生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的现代性逻辑遭遇到农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抵抗,使看似无可辩驳、无法更改的人民公社体制机体受到村民虽然微弱但却是日积月累的侵蚀。
[关键词]集体化时代; 农民; 生计; 生存; 日常生活
集体化时代,国家农业集体经济制度的安排首先是基于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发展定位。国家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票证制度、口粮工分制等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村庄党政组织及生产队的组织管理,以及政治运动、政策宣传和阶级话语工具等的思想意识改造使农民投身于集体农业生产,劳动成为乡村农民的主要谋生手段。
农业生产对于1949年后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不言而喻。但从农业劳动的管理和组织运转来看,作为中枢的工分体制存在不足。由于对劳动数量和质量的信息收集和监督的成本高、难度大,难以将其与劳动报酬紧密对应,劳动者的动力不足;同时,国家直接领导和计划农业生产,并进行统一规定、管理、分配,这样就几乎完全控制了农业生产,包括剩余权支配。作为政策直接实施者的乡村干部尤其是生产(小)队干部升迁无望,也享受不到农业剩余收益,得到的对集体劳动监督和管理的激励同样不足[1]。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没有足够积极性进行集体农业生产,致使偷懒、欺哄、磨洋工、搭便车现象普遍发生。集体劳动陷入困境和恶性循环中,并形成了所谓的“柠檬市场”效应②柠檬市场效应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好的商品遭受淘汰,劣等商品取而代之,致使劣等品充斥市场。。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生产中集体收益下降并造成了过密化的倾向[2],但农民的劳动量却是饱满的,某一家户的劳动边际收益仍有可能增加,工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当有效地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3]。
尽管农民不能自由流动,却存在着一定的相对自主空间,如农民利用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谋生,被称为是对集体体制的“隐性退出”[4];作为管理者的村干部尽管不能享有剩余收益权,但能够利用“因控制着农村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初级分配而掌握的、以腐败形式存在的‘剩余控制权’来分享剩余”。而且,“乡村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冲破了国家对加工工业高利润的独占,由集体来组织并占有剩余”[1]。这些可以视为国家治理在乡村的积极调整和对于乡村社会的灵活适应,其结果是为农民构建了一定的自主空间。
与上述研究成果从制度性的、结构性的视角对农业生产效率和工分体制的运作困境进行探求不同,本文以村庄档案为资料基础,从日常生活即农民谋生的具体实践和过程的微观视角进行实证性的探讨,论述在国家严格控制管理下的农民群体是如何生存的,他们对于集体劳动有着怎样的体验和感受,除了农业劳动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生计方式,形成了怎样的生存策略,处于怎样的生存状况和境遇中,并揭示农民在点点滴滴的日常行为选择中如何形成了应对不同于国家意志的主体性建构,成为解构国家制度安排和形塑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因素。
一、“劳动最光荣”
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即约等于农业产出的逻辑推论和防止产生剥削、不劳而获的意识形态评判,国家认为农村的劳动力必须要占到农村人口的40%左右,这些劳动力中的95%左右要固定归生产队支配,这样能使农业有好的收成,就能缓和城市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就不会形成“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5]。人民公社内的每一个社员被要求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完成应该做的基本劳动日[6]。不仅是农村的农民,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机关工作人员、在校学生、知识分子几乎都被动员加入农业劳动的行列。许多的市镇非生产人员也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被认为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表现,符合人人劳动、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7]。
为了保障集体经济体制的运作,需要从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上形塑村民的劳动态度与劳动观念。为农业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贡献力量是国家对村民的劳动及劳动观念的要求。国家通过下发政令、发动各种运动,加强农业第一位、生产劳动第一位的思想意识宣传。是否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是否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是否跟着党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与贫下中农站在一起的标准,成为影响个人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的因素。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表述中,劳动是崇高的,劳动人民是伟大的,不劳动依赖别人生活是剥削、是可耻的。地主和富农正是由于自己不劳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劳动似乎成为衡量村民的政治立场、个人品质、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从而具有了政治意义。
农业劳动重要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并散播在村庄经济、行政组织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运作机制中,成为改造民众的思想观念、日常生活和谋生方式的重要因素。作为干部和党团员,首先要在劳动中起到领导带头作用,劳动成为评价党员干部的重要标准。作为一名普通社员,也应该在干部的指挥下好好劳动。许多因不安心于生产劳动而犯了“错误”的社员常用“好好劳动”的一套话语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因倒贩屠宰羊被逮住的吕广才在检查中写下了自己的保证:“我再不做与人民不利之事,在队里好好劳动,听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指挥,把自己投入到三大革命运动之中,为了今年农业的大丰收而大干特干加油干,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吕广才检查书.1971-1-25.双口村庄档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下同).XYJ-2-6-6。。
同时,农业生产劳动还是一个改造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大熔炉。四类分子作为“阶级敌人”的被专政和管制的过程,就是在人民监督下从劳动中“改造”自己的过程。刘清媛在个人检查中写道:“我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参加集体劳动,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的监督改造,使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大打农业翻身战,支援战备,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刘清媛的个人检查.1971-9-15.XYJ-3-1-2。。能否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是评判他们现实表现的重要依据。作为青年学生同样应该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杜松庄公社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个人总结——吴小涛.1972-1-31.XYJ-2-28-5。。
农业生产劳动在当时确乎成为了村庄一切事务的中心。对于农民而言,当时除了劳动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选择,而且在集体体制之下被组织起来,初期不仅会因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产生新奇感,同时其分散和不善于创新的特点也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乐于参与集体劳动并接受干部管理。农业劳动管理体制有利于劳力多的家庭,而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在生活上就会发生困难,但最基本的口粮能够得到保障。尽管农业劳动的边际效益相对低下,但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农民个体和家庭而言劳动力的投入仍然能带来收益的绝对增加。
在村庄的劳动管理中,工分是连接村民投入劳动与取得报酬的中介,是村庄的劳动管理以及公共生活得以运转的中枢,其高低直接关系着村民的收入,拿到高工分、获得高收益的经济理性而非政治觉悟是支配他们日常劳动的主要动力。柳春生在检讨班上交代自己挣工分的思想:“近几年来我愿意做大队工,原因是在大队做木活,每天能挣工分15分,在本队才12分。从去年开始,在大队劳动减少了工分,每天成了13分,我思想上就背了包袱,心想以前做的时候一天还给15分,现在做的时间也长了,技术也高了,工分反而给我减少了,以后我永不在大队做活,在我队做一天木活还给我记14分,以后大队叫我去做我就不去,如果再叫我去的时候我在劳动中等就是了。10天的工总要多做一两天”*柳春生的检查.1970-6-25.XYJ-2-63-3。。尽管柳对自己的此种行为做出批判,但获取更多工分始终是他的目标,这也是大多数村民不断投入劳动的目的。工分的高低虽不能与实际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但由于集体单位不能解雇过剩的劳动力,村民也没有更多的生存途径,所以只要边际产品大于零,劳动力的继续投入就合乎村民的经济逻辑[2]201。
工分体制对村民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但却存在着不足,既不能与劳动报酬直接挂钩,也难以与劳动质量相对应。村民为了多挣工分,常常不能保证农活质量,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存在偷懒、瞒哄现象。古秀堂检讨自己当共青团员,不能给没砍好地的社员们提出建议,自己反而也不能够按照队内所要求和规定的质量做到砍好,只想砍得快些,多砍一些,多挣些工分*古秀堂自我检查书.XYJ-2-19-1。。同时,工分记录也存在问题,工分登记不严格,多记、少记、漏记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记工员承认自己有时会给社员误记,也不能及时记、及时清,常出错误*吕荣磊的检查书.1965-10-21.XYJ-2-10-3;柳翠莲的自我检查书.1965-12-18.XYJ-2-57-1。。吴翠兰检讨自己有时正在记账或打工分时,孩子哭,心一急,就不可避免地要打错或记错工分*吴翠兰的检查书.XYJ-9-4-12。。而且,由于复杂的劳动安排,工分的记录有时并不局限于记工员,多人负责、随人而变容易造成工分错记,农民干部相沿成习的生活和思维方式难以与村庄公共管理对责任义务观念和工作素养的要求相适应。而且,究竟如何确定某一种农活的工分数量,村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规定,对于一些公共事务是否应记工分也会随人、随事而定*双口村干部座谈会记录.1976-1-1.XYJ-7-12-17。。
干部的工分登记问题相对较多,一些干部有时无论劳动与否都要登记工分,有的在城里、公社开会等也要记工分,在村庄里做社务和行政工作也记工分,记工员、保管的工分有时超过了普通全劳力的分数*杜松庄公社双口工作组工作汇报.1963-4-13. XYJ-8-6-12;各队队长自觉甩包袱开始.1964-12-10.XYJ-9-4-1;10队全体队员会议,干部甩包袱材料.1965-1-5.XYJ-9-4-4。。这样的记工实际已经模糊了干部正常补贴与非劳动所得之间的界限,使干部能以办理公共事务为借口赚高工分,并躲避劳动。团支书柳武斌就在支部揭盖子会议上说:“大部分干部不劳动,懒,有的连补助赚下成万分,但还是不劳动”*党员学习班会谈记录.1975-12-28.XYJ-7-12-11。。何魏质问刘岚温:“从今年劳动多少天数,工分挣了6 000多分,是地里一天天挣下的,还是游手好闲(得来的)?”*解决双口支部问题座谈会.1977-1-29.XYJ-7-12-3。事实上国家对于干部的补贴工分有明确规定,即不得超过全大队总工分的2%,但干部的补贴工分实际远远超出了这一比例。一些干部认为参加劳动会影响工作,只要把工作做好多补贴些工分算不了什么,只要增了产,哪还在乎几个干部的补贴工分呢?*工作组关于十二队的问题分析.1963-5-30.XYJ-8-6-10。这样的思想在村庄干部中普遍存在,使干部的补贴工分登记往往超出规定。此外,干部还庇护亲戚朋友得高工分,对于要好的就多记工分,不要好的就乱扣少记,甚至给干部私人干活也在生产队里记工分*对古建民的揭发材料.XYJ-1-1-3;对梁新发的揭发材料.时间不详.XYJ-2-76-7;杜松庄公社双口大队关于给与陈海亮撤职处分的决定.1962-2-20.XYJ-1-25-4;向工作队反映王铁林的问题.1965.XYJ-9-4-10。。
由于农业劳动难以分解为环环相扣的规范流程,难以形成职责明确的分工并进行较为客观的计时或计件取酬,管理、组织成本高昂。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所得工分与其劳动质量并不能直接挂钩,无论是干部的监督管理还是群众的相互监督,都无法与监督收益的公共性产生直接联系,欺哄难以避免,由此会挫伤村民劳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更何况村庄传统的经济理性、人情面子始终在公共管理体系和管理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干部的工作业务素质也尚需较大的提升。不过,不可忽视的是,农民可在集体劳动之外将自身的劳力投入到自留地中。双口村民时常将肥料、将自身的劳力更多地投入到自留地中,并且会私自扩大自留地,占用集体耕地。有学者将其称为隐性退出,而正是因为这种隐性退出部分地使僵化的公社体制有了一定的弹性,使人民公社体制得以维持下来[4]。
二、“自由职业者”
“集体化的效果并不优于以前的市场经济。尽管国家政权锐意进取,农业并未冲破过密化的老路。到1970年代末,农村劳动力的报酬仍只够维持生存,与解放前数百年一样”[2]317。农业集体经济使村民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空间有限,许多村民因此通过非农业劳动来谋取赖以生存的资源。他们或一边劳动、一边利用闲暇时间搞副业生产,或干脆放弃农业劳动通过其他手段谋生。生存的渴望使村民对于经济利益产生追逐,不仅在观念上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互矛盾,而且在日常的行为实践中也常常突破国家政策的界限。这会使安心于劳动的村民产生心理失衡,并威胁到村庄集体劳动的生产秩序,因此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
国家强化农业生产重要、劳动光荣的观念意识,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靠生产不靠商业,要求农民不热心于做生意,不弃农经商[21]662,但有的村民却认为劳动是“死受”,眼界狭窄且效益低下,是无能的表现,通过其他手段获得经济资源、不用“下苦”就能赚到钱的那些村民是“能人”[22]。柳春生就认为自己在大队做木活,工具拿上一大堆,说起来还是个有技术的,而不是只干农活的“受苦人”[11]。在柳看来,摆脱“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通过自身更具有技术含量的方式谋生,能够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这也是其他一些村民所具有的观念,他们认为能劳动而不劳动,进行倒买倒卖赚钱是脑袋活、能力强的体现。有的村庄干部甚至因为自身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本事”而自惭形秽。谢炳坤在生产队里当干部,但他认为自己没有说服社员特别是那些因投机倒把而发家的社员的资格。谢炳坤说:自己看到吕清文与葛大伟在队里劳动时歇单身,但在自留地里却挺尽心。常有人夸他们是能人,搞投机倒把,个人势力发达,人人羡慕个个称,而自己死钻在农业社,死劳动挺无能,哪有脸面能说服人。又认为吕清文的母亲更是个能人,本来能劳动而不劳动,还说多劳动仅够生活,活不成”[23]。经营副业与农业劳动不同,可以得到更多的现金,获取利益相对更为直接和迅速,数量也更大,这常常吸引着一些村民放弃劳动去赚现钱。朱玉凤对当时村民的“小动作”记忆犹新,她说:“那时社员有的请了假说去看病,实际是出去做买卖了,人们偷得卖油,去火柴厂拿火柴去太原卖。有的是因为孩子多,不够吃,不这样就活不了”*访谈对象:朱玉凤,女,65岁,平遥县双口村人。访谈时间:2009年5月2日。。争取生存资源“闹红尘”是村民生活的主要目标,经济理性支配着他们利用村庄集体经济体制和劳动管理的漏洞来谋取利益,缓解对于贫困的焦虑和在集体劳动中受束缚的压抑。
国家对于村民的家庭副业持鼓励发展的态度,认为其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队应该鼓励和领导社员积极发展各项副业生产。只要不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不影响集体生产和集体劳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破坏国家资源,就应当看作是正当的,就不应乱加干涉和限制[24]。对于半工半农的手工业劳动者,国家规定生产队要同他们协商,确定全年应做的劳动工分,以及交多少钱,记多少工分,对于他们所得的收入,除了经过全社群众协议,认为有必要交付少量公积金和公益金的以外,其余的全部归个人,由自己支配[25]。村民的家庭副业虽被明确定性为非资本主义,但实践中的个体副业常常处于尴尬境地。
村庄对于个体副业的管理处于模糊状态,没有明晰具体的办法,而且变动不居。以同一时段的村庄管理为例,大队在1961年11月—1962年1月规定平车在太原搞副业,拉大队平车的人每月交大队150元,拉个人车每月90元。在1962年3月下旬-4月上旬期间大队规定,拉大队车每月交大队125元,个人车80元*古云海交代材料.1965-11-15.XYJ-2-21-1。。但是刘洪富在1961年6月28号至1962年2月底在太原搞皮车运输时,却是每天交大队1元算作一个劳动日的10分即可*谈话记录.1965-5-24.XYJ-4-1-1。。梁步魁搞泥活,每月贴16元,杨福生剃头每年贴队80元,口粮钱不计在内,吃粮花钱买。韩全虎补牙及卖戒指等,每年贴小队200元钱。贾文宝、李治富(木匠)在大队里干,每月交45元,其中16元交给队作收入,29元记工分*柳绍军检查.1964-12-12.XYJ-9-4-2。。木匠白伟佳在太原拉木活,每月贴16元,给分口粮*各队队长自觉甩包袱开始——四队白平江检查.1964-12-10.XYJ-9-4-1。。由于各类副业的利润和收益不同,村民个体的劳动能力大小不同,村庄的管理亦理应随之体现出其间的差异,但这样的差异应该怎样管理,公积金、公益金和口粮钱应该如何交纳,国家并无具体的管理办法,村庄对此也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多因人因事而异。
无论是村干部还是从事副业的村民,在实践中都偏向于个人单干,即向大队交纳了基本的费用后自负盈亏。但一些村民由于工作习惯或者是利润的吸引,难以兼顾农业劳动,常常违反政策行事,加之阶级斗争被强化,副业单干受到更多约束,个人手工业往往被要求纳入集体经济的范围,个人谋取利益进行单干的空间有限。不过,谋求生计生存的愿望使村民有着各种因应策略,以集体的名义搞个人单干成为许多村民搞副业生产的隐蔽方式,如韩全虎补牙、卖戒指,许成在外修理裁缝机等,白伟佳在太原拉木活、吕荣闳当水泥工等,都是以生产队的集体名义做个人私活*柳绍军检查.1964-12-12.XYJ-9-4-2;何巍代表支部检查.1976-1-20.XYJ-7-12-13;相关问题的揭发.XYJ-8-5-13。。双口村的副业生产“成风”虽是因村民对利益的追逐引发,但与村庄干部不无关系。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干部在国家政策与村民利益、自身利益之间进行摇摆,在运动来临之际面对政治压力限制村民的谋利活动,在运动过后又会持迁就和宽容的态度。很多干部自身就被搞副业生产的利益所吸引,因而对个人的单干也放任自流,甚至与普通村民进行“合谋”,成为村民副业生产的庇护者和合作人。
对于没有技术的村民而言,倒买倒卖是他们在农业劳动以外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国家对于投机倒把的定义及对其处理规定了详细的标准,如倒贩统购物资、长途运输等,并明确提出将投机倒把与小商小贩区分开来, 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投机倒把者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小商贩则是除供销合作社和集市贸易之外的乡村商品计划与自由流通的重要补充[13]。但是,“国家对于投机倒把的界定含义笼统,内容损益不定,边界模糊,尺度盈缩无偿”[14]。这使村庄干部在管理中没有明确的执行标准,因而笼统地加以限制。村庄里村民的倒贩活动大多属于村民的日常经济交往,规模小,而且倒贩的商品有的并不属于统购物资,但都受到严格管理,尤其当运动来临时,只要与集体经济和农业劳动无关的谋生活动都有可能被定性为投机倒把。吕广才因屠杀牲畜、卖肉、贩卖羊和花椒树苗,但未交割头税和营业税而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他被迫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交代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在讯问中将自身贩卖和屠宰羊的时间、地点、数量、使用的交通工具、涉及的人、获利多少都一一交代清楚*柳绍军检查.1964-12-12.XYJ-9-4-2;何巍代表支部检查.1976-1-20.XYJ-7-12-13;相关问题的揭发.XYJ-8-5-13。。村民倒卖灯泡、肥田粉、锅盖、偷杀牲畜卖肉等涉及金额虽相对较少,但也都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被要求写检查交代错误,并且受到补税、退赔、罚款、没收工具等的处罚,如果是四类分子搞投机倒把,除了一般处罚外,个人管制也被延期*专政对象登记表——许满金.1966-4-12.XYJ-4-14-8。。有的甚至为此而遭到大会批斗,并定性为投机倒把罪*许瑞庭个人材料.XYJ-3-12-1至XYJ-3-12-7。。
副业经营由于利润相对较高并且脱离劳动管理而对农业集体生产构成威胁,因此受到较大限制。在“自谋职业”的村民看来,集体并不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反而是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制约,他们因此要挣脱这种牵制而获得自由,并努力利用“集体”的政治、经济资源来谋取个人利益,通过非农业劳动来谋取生存所需的资源。在吃饭是第一需要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无论是四类分子还是贫下中农,都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艰难挣扎,难以放弃对利益的追求和索取,也难以完全契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保证“规规矩矩”地站在政策规定的界限内。双口村灵活的手工业生产和倒买倒卖活动虽然受到约束限制,但却可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因而屡禁不止,“会过日子”的生活理性对“革命”的逻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
三、村庄里的“贼”
除了进行农业劳动和副业生产外,村民偷盗也是他们用以维持生存的手段,“这些或大或小的偷盗行为具有一种铭刻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模式”[15]。斯科特认为:乡下的偷窃行为很平常,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几乎都是农业生活的持久特点,并且国家及其代理人也无力控制。而当偷窃涉及有争议的财产权时,偷窃就并不仅仅是一种必须的生存选择,而且还被视作自然权利的实现。革命致力于改造乡村传统,不仅用集体经济体制取代分散的家户小农生产,而且对村民生产生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尤其在村庄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行为进行规范,如要求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应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积极主动地维护集体利益,不偷不盗等。但是,村民的偷盗,特别是对集体粮食和财产的偷盗现象却并不容易消逝。偷盗虽与革命现代性的逻辑相去甚远,却具有维持村民生存的功能,尤其在生存型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国家以政策规定和体制性约束要求村民将土地、财产入股到村庄集体经济继而造成财产权争议的背景下,村庄的偷盗行为更加难以避免。
1949年以后,农业集体经济制度使村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维持在较低水平,农村依然贫困,且仍有部分村民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双口生产大队关于访贫问寒的情况报告.1964-1-31.XYJ-8-6-6。。村庄流行着“不偷不挖,社会主义难爬”的俗语。对于部分村民而言,争取生存是本能,也是正当的,尽管有被捉、被罚的危险,但不偷就有可能无法生活下去,经济上的穷困成为偷盗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三年困难时期村庄的偷盗现象最为严重。当时村民偷的方法多样,许多人穿的衣服里外都是口袋,有的扎住裤管放粮食*访谈对象:陈中智,男,73岁,平遥县双口村人。访谈时间:2009年4月29日。。有的去地里吃玉米,就在杆子上吃,吃完再将外皮包好,乍眼一看看不出来。有的偷粮食,光偷中间不偷两边,以免让人看出来。“偷盗没仇,得便就偷”,人们碰上哪偷哪*访谈对象:朱玉凤,女,65岁,平遥县双口村人。访谈时间:2009年5月2日。。这样的偷盗在当时比较普遍。在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形下,能否填饱肚子的底线似乎已经超越了是否道德的社会舆论约束,更何况之前农民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引导和要求之下将自己的土地、财产作价入社,这种被剥夺感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缓释可能因偷盗而产生的道德负罪感。
村民偷盗的对象以集体财产为主,有的村民不仅在自身所在的生产队、其他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而且还到邻村进行偷盗,其中有个体行为也有集体行动。双口村的村民既偷过邻村的,也被邻村偷过,偷盗及互相偷盗似乎成为一股蔓延在双口及附近周围村庄的隐而不绝、禁而不绝的风潮。村庄中因偷盗而被判刑的村民属于个例,而且都是因偷盗村民的私人现金和财产*关于苏淑梅的个人材料. XYJ-3-16-1;梁岱盛的个人检查.XYJ-7-16-1,XYJ-3-20-1。。村庄中几乎没有因偷盗集体财产而被判刑的个案,偷窃集体的粮食在道义上与偷窃个人财产相比更容易为村庄的社会舆论和公共管理所宽容和接受。
捉贼要捉赃,偷盗者都抱有可以逃脱的侥幸心理,村庄里的一些偷盗现象常由于缺乏确凿证据而无法得到处理。偷盗虽能侥幸逃脱,但需要冒很大风险,有时会危及自身安全。王铁山在1963年夏收之际的一天趁黑夜宁静无人到九队场里偷小麦,当时场里有100瓦的一盏灯,他怕别人看见,便先去扭灯泡,孰料因手忙脚乱而触电,将手粘在灯泡口上。看守麦场的人看见后,急忙过去用木棍打下来,王铁山得以逃脱,看场者并未看清偷粮食的贼到底是谁。后来邱增宝到太原卖香瓜时在王的妻姐家找到了他,王对邱说:“那天晚上我在北庙后偷粮被电拉住,手上沾了一块肉,胳膊上也沾了一块,强强地(方言,非常费力地)爬回家,你回去以后可别告诉其他人。”可以想象王当时的疼痛及对于偷盗被逮的担忧,事后王的家人曾派人去问看场者是否看清楚被电打的人是谁*关于王铁山偷粮的证明材料.1970-4-3.XYJ-2-32-6。。面对与自己一样经常偷盗的邱增宝,王铁山几乎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的偷盗经历。在王看来,偷盗似乎并非难以启齿或罪无可恕,做贼心虚的心理压力可以承受,存在的安全隐患也可以掌控。受伤的经历并未让他放弃偷盗的念头,他甚至与人结伴行窃*王铁山的个人检查书.1965-11-21.XYJ-2-32-5。。
对于偷盗者而言,如果不被逮住就能获利;如果被逮住,需要退出偷盗的东西,有时可能再挨一顿揍,或者被加倍罚款,但常常不能兑现,因为已经很穷,干部有时无法追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偷盗现象的屡禁不止。针对村民的偷盗行为,尤其是收获季节的“捎带”粮食行为,村庄一般只稍作处理,如保卫、巡田员会在道口检查、搜身,如果搜到就会看拿了多少,在哪里拿得,把偷下的东西全部没收,再打上两棍子,或者把工分扣掉,不给记工分*访谈对象:王昌勇,男,65岁,平遥县双口村人。访谈时间:2009年5月2日。。
除了经济和精神被处罚外,有些偷窃者还会以挨打的形式受罚。1958年阴历8月,吕向成因家里没吃的,偷了20来穗将要成熟的玉茭,因牙口咬不动,便想驮到平遥城内卖了换现金再买别的吃,不料刚走到邻村就被那里的保卫抓住了,并被“押送”回双口村,正巧在村供销社门口碰上了支书王钢毅。王质问吕“又偷了玉茭穗到城内去?”在听到吕“活不了,偷了几穗”的回答后,王从供销社内拿了一条水车上用的铁绳拴在吕的脖子上,接着用一把铁锁锁住,并把吕拉到供销社南面的大队,将吕向成脖子上的铁绳的另一头栓在大队门口的明柱上,吕求饶无果。王钢毅在其他干部劝说后觉得公开惩罚不妥,便把吕拉到村北大桥上,用洋镐打了一顿,然后给吕解掉铁绳,放他回了家*关于干部殴打群众柳尚喜一事的证明材料. XYJ-1-6-2;关于支书惩罚吕向成的证明材料.XYJ-5-4-4;关于支书打人的检举材料.1965-12-11.XYJ-5-4-5。。村支书王刚毅在此将公共关系置于村庄私人关系之上,用“打”来治理村庄的偷盗行为,稳定村庄秩序。除了王之外,保卫股长和保卫组的成员也都曾用“打”来惩罚窃贼。在乡村社会中,“打”是处理邻里之间和乡村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冲突和纠纷的常见方式。由于乡村习性与文化的延续性,“打”的方式也往往被运用于乡村对于偷盗的治理中。
为了减少或消除偷盗行为,村庄干部有时也通过加倍(粮食或金钱)处罚来加大惩处力度,但这种不当的方式往往会引发村民的心理反弹,导致更多的偷盗行为。杜富强有一次因偷了17穗玉茭而被要求交罚款10元,最后他交了170穗玉茭。如此严重的惩罚让杜无法接受,他在检讨书中写道:“这样处理后,我自己更产生了一种恶劣的思想,认为自己为偷点菜食糊口,但反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我更得去偷。当时是初秋,社员开始上地劳动,我的思想就打下了底子,若偷不多少也得偷点,于是我经常在回家的路上捎带个一斤三斤,这是很多次的”*杜富强的检讨书.1964-1-15.XYJ-2-48-6。。耿睿智同样遭受到不公正的处罚。1974年9月下旬的一天夜间,耿与其他村民共五人在沙河以内偷割樤子被发现。当时按公定价是5分钱1斤,负责人尹杰和柳武金按私价1角钱1斤的十倍罚钱,耿共割了31斤,因而被罚31元整。由于耿当时没钱交这笔“巨”款,尹、柳二人便把耿的一辆自行车派人拿走,并且未等耿交款,也未征得其同意就将自行车以31元的价钱私自出卖,耿也未收到罚款收据。耿辩驳道:“我偷樤则不对,但不是惯偷,干部应该按党的政策加强教育,(让我)赔偿损失,以观后效,但干部们却是用一棒子把人打死的手段加倍罚款,把我全家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拿走出卖了”*耿睿智对自己被惩罚过重的问题的申述.1979-3-8.XYJ-5-5-31。。
公共治理方式的失当无益于对偷盗行为的治理,更何况有的村庄干部也会利用自身身份的便利而变相“行窃”。双口村的一些村干部利用职务、权力之便从生产队占取、占用粮食、蔬菜、布票、食油、现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日用品,白用、白拿集体的各种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具等。何魏就质问柳武金“社员拿紫树槐樤子和木业社木料就是偷,而你柳武金是有权明拿”*党员学习班上揭发问题记录.1975-12-25.XYJ-7-12-11。。有的干部还以管理偷盗为名义将罚款及赃物据为己有。如双口村有人偷了邻村的条则,被罚一斤一块钱,干部把罚下的钱买了烟然后分掉*揭公社党委盖子会议记录.1977-1-28.XYJ-7-12-2。。保卫扣下村民所偷的粮食后给所有保卫人员均分*柳尚云的个人检查.1965-11-16,XYJ-1-16-1。。保卫股长韩银富看到村民在田地里拿粮时不管,而是在道口设卡,再扣下私分*保卫韩银富第二次群众会检查.XYJ-1-21-1。。这实际也是一种变相的“偷盗行为”。干部的偷由于包裹了一层权力的保护膜而具有了安全性,而且彼此之间能进行合谋,与村民的偷盗相比更“安全”,更容易成功,而且很少被抓住*关于白平江偷窃甜菜的证明材料.1965-11-1.XYJ-1-26-3;梁新发的个人检查.1965-12-9.XYJ-2-76-15。。许多干部的偷盗行为是在四清、整风等运动中受到别人揭发和进行自我交代中才暴露出来并被予以处理。
在集体化时代,偷盗在乡村社会具有复杂的意涵。生活贫困是导致村民偷盗的重要原因,因此偷盗是他们不偷活不成的逼不得已,也是别人偷、自己不偷会吃亏的心理驱使,还是争取生存权利的一种努力挣扎。同时,由于存在财产权争议,村民以偷盗来平衡自身由加入集体经济体制而产生的被剥夺感,并借以实现利益弥补。干部自身的盗窃行为以及对于村民偷盗的失当治理招致他们对干部管理行为的合理、合法性的质疑,并引发更多的偷盗,以此来弥补自身对于干部利用职务谋利的利益缺失。因此,偷盗不是一种单纯的违背乡村道德规则的行为,或是因超越村庄公共管理规范而受到约束限制的行为,而是隐匿和内化在乡村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也是对村民糊口型经济和生存方式的重要补充。
四、结语
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经济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乡村农民,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在制度安排与个体行为选择之间形成平衡点,如何协调国家意志与个体意愿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冲突,都需要付诸努力。国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理念及对其实现途径的预设未能与小农的经济理性及村庄的公共管理体制实现有效融合,使国家的革命逻辑相对于复杂的乡村社会显得理想化和简单化,导致农民与国家进行的只是有限的合作和部分的接受,除此而外还有不合作和隐秘的反抗,他们对于国家管理的应对是“风声”来了紧一阵,“风声”过后仍照旧,“运动”式治理的效能有限。
生存型经济的威胁对于村民而言始终存在,他们谋求生计、生存的愿望更为凸显,而不是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其对于政治资源的争取更多地也是为了获得经济资源。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村民,都依然为了生计而奔波忙碌,只不过干部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受到更多行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生存的渴望使他们对于经济利益产生追逐,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也因此而形成庇护或共谋关系。这使农民通过其自身的文化和日常实践形成了不同于国家意志的意愿和行为选择,由此形成占据了一定的自主生存空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违背国家政策行为显然是一种“反行为”,与以革命的逻辑、公共关系和阶级关系超越代替生活逻辑和姻亲、血缘的村庄传统的制度安排和国家意识形态不相契合,但以“反行为”呈现出来的生活状貌正是集体化时代村民对生活需求的表达和他们真实生活的体现,是他们对自身的自由流动和多样谋生方式的权利争取。
可以说,革命逻辑虽然主导了村庄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但村民的生存理性和村庄传统仍坚韧地嵌入革命的枝蔓脉络中。国家全面覆盖而非嵌入式的覆盖并没有完全替代了以道义和人情来维系的乡村社会关系[16],农民的生活逻辑及由此而形成的村庄人际关系并未消失,农民并不完全听从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他们努力挣脱体制的束缚和意识形态规训,以自己擅长的方式经营自身的生活,于此求得生存和主体性的建构。村民的这些脱离制度轨道、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虽然是分散的,但威胁着集体经济和村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对集体经济体制构成威胁,也对国家向乡村传播的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具有排他性的政治文化形成解构,并成为经济体制创新和“创造性政治”的潜在因素[17],推动社会向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1995(4):178-189
[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5):1-19
[4]罗必良.限制退出、偷懒与劳动力柠檬市场——人民公社的制度特征及其低效率的根源.中国农业经济评论,2007(1):95-104
[5]中共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1961-4-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6∥《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7]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财粮贸办公室关于压缩市镇非生产人员回乡参加生产的报告.1958-1-16.山西政报.1958(4):30-33
[8]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61-11-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1997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1962-11-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1965-9-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971-2-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12]国务院关于统一管理农村副业生产的通知.1957-10-2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4]张学兵.当代中国史上“投机倒把罪”的兴废——以经济体制的变迁为视角.中共党史研究,2011(5):35-46
[15]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还,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6]董磊明.从覆盖到嵌入:国家与乡村1949-2011.战略与管理,2014(3/4)
[17]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经典模式的超越.学术月刊,2009(5): 5-14
Livelihoods and Survival: the Village Economy and the Daily Life of Farmer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A Case Study of ShuangkouVillage in Pingy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Ma WeiqiangDeng Hongqin
Abstract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the state had farmers being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guiding political ideology and restrictions on social mobility, which protected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system and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less labor arrangements and work-point management enabled collective production to be difficulties. Some farmers often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policies to be hand labor or profiteering, which had been given political meaning to be constrained. Some people even were put on the hat as the class enemies. However, the villagers still survived through non-agricultural labor or theft. The survival of farmers and villages tradi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odern revolutionary logic encountered peasant resistance logic of everyday life, which made the irrefutable and unchangeabl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e cumulative erosion by the villagers.
Key words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Farmers; Livelihoods; Survival; Daily life
(责任编辑:陈世栋)
[作者简介]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编:030006;
[基金项目]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9YJC770047)和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批准号:12&ZD147)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7-26
邓宏琴,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为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文中隐去了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