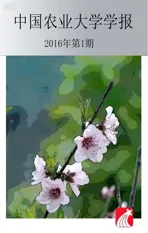地方感、民间信仰与村落整合——西汉水流域“犯丧”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2016-01-25台文泽
台文泽
地方感、民间信仰与村落整合
——西汉水流域“犯丧”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台文泽
[摘要]在西汉水流域的汉人社会中,“犯丧”信仰体现了人们关于死亡的一种独特认知与文化理解。生活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感觉结构,不仅是这一信仰本身在日常中得以再现的文化基础所在,还构成集体“烧犯丧”仪式实践的建构逻辑,从而显现了地方感在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性生成中的关键意义。
[关键词]地方感; 村落社会; 宗教整合; 犯丧; 西汉水流域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汉人“最重要的宗教传统”,就其社会整合性的讨论乃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议题。从研究现状看,相关研究有的试图在整体上给予理论阐释①代表性研究如林国平对闽台民间信仰的研究指出具有整合宗族、维系社区秩序的现实意义,参见文献[1];陈重成对大陆民间信仰仪式在将和人、家户、聚落、社区乃至区域贯穿起来的基础现实了高度的社会整合性,参见文献[2];高长江认为民间信仰具有的全民性特征使得其仪式实践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纽带,参见文献[3]。,有的则以具体个案进行实证分析②代表性成果如美国学者丁荷生(Dean Kenneth)对福建莆田地区600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指出村庙网络在地方治理中具有整合社会成员的作用,参见文献[4];甘满堂对福建民间信仰的研究指出,村庙构成了社区的公共生活空间所在,对社会产生着横向的整合作用,参见文献[5]。,然鲜有透过对信仰本身再现基础的考察来揭示其所具有的社会整合性。在甘肃东南部西汉水流域的汉人乡村社会中,至今传承一种特殊的习俗——“犯丧”(似于通常所谓的“僵尸”)信仰。据乡人口述的历史,1949年之前地方举行“烧犯丧”活动极为普遍,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因政府斥其“迷信”色彩浓厚受到严厉禁止。即便如此,习俗活动并未就此消绝,相反,在不同村落仍清晰保留着不时举行的历史记忆。从2012年7月到2013年9月,笔者在西汉水流域就这一传统信仰进行的调查发现: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感觉结构不仅是日常现实中这一信仰本身得以再现的文化基础所在,还构成集体“烧犯丧”仪式实践的内在逻辑,显现出它在民间信仰社会整合功能生成中的关键意义。
一、死尸恐惧:日常生活中的“犯丧”信仰呈现
在西汉水流域,“犯丧”作为一种信仰对象,往往令人谈之色变,却又被热衷谈及。按照人们的普遍说法,如果亡者入葬数年乃至数十年,肉身依然完整,或部分保存,尤其若面部依旧鲜艳,甚或比于生前,即为“犯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各种版本的传说、个人经历论说这一信仰存在:通常在夜晚会出现,披头散发,袭击活人,吸取人血,爱抓鸡,弄得坟头、棺材里散满鸡毛……这种充满神秘感的表述意味着犯丧构成了日常世界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就此而言,若家庭成员遭遇无法用医药治愈的疾病;地方上连续发生异常,诸如家畜死亡、庄稼歉收、死人等现实,都极可能被怀疑是家中去世的某位成员,或地方上已安葬的某位亡者犯丧引发的。由此观之,西汉水流域汉人信仰的犯丧折射出的是乡人的此种观念:相信死者尸骨的状态与活人的生活状态紧密关联。人类学家罗伯特·赫尔兹曾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民族的死亡观念和丧葬实践后指出:“尸骨的状态与灵魂的状态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灵魂必须等到他在现世的整个身躯完全消失才能再次回到世人中间”[6]。在西汉水流域汉人的丧葬实践中,此种观念明确显示,一些情况下,人们并不立即将亡者直接土葬,而是通过寄葬实践以求在风吹日晒的自然力作用下使尸骨彻底消解,然后再行土葬,从而保证死者灵魂可顺利获得超生。然而,倘若一旦与正常丧葬实践(不管是直接入土为安还是寄葬)预期相悖的情形发生,即出现肉身理应消化但却保存的现象,危机、恐惧便会侵袭人心。综上所述,犯丧信仰展现了人们对死亡的一种独特认知和文化理解。
乡人对犯丧的恐惧并非出于眼见为实,而是多基于想象的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有关传说的演绎、个人遭遇的夸张性描述营造、传播着人们的恐惧感,特别是在村落中享有神异权威身份的人士,是此类传说与经历的主要讲述者。相比之下,大多数乡民并无神异权威拥有的丰富故事和离奇经历,但这种不对称性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相信犯丧是真实存在的态度,而且在人们种种陈述中显现出,对它的认知与想象是完全基于日常生活中长期积累的关于人、事、物/空间的普遍感受。
其一,对亡者生前的个人特征、去世时的状态的感受,形塑了人们对犯丧是否发生的判断。一般而言,人们相信年轻、性格暴躁的亡者,尤其是非正常死亡(非疾病因素)的年轻人容易成为犯丧。例如,在西汉水流域的T村,20世纪90年代,一位南姓年轻人死后的两三年内,村落接连出现一些异常,村人怀疑是南氏成了犯丧,缘由中提到他死时是一个年轻人,也是个惯偷,爱打架,后来服毒自杀了。这些解释体现了将对亡者生前个人特征的感觉延续到了死后。另一个与个体特征相关的是亡者的性别,人们感觉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安葬后成为犯丧,特别是年轻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例如,在S镇境内,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个故事中,成为犯丧的便是一位因难产去世的女性亡者。在西汉水流域,人们普遍相信这种死于难产的“月婆子”最可能成为犯丧,而且煞气极重,对活人的危害也“最劲大”,是最难对付情况。
其二,亡者生前人际关系下的命运状态也构成了人们感知其是否变成犯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T村,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案例描述了MKZ被家人怀疑成为犯丧。MKZ生前没结婚,年老无力时便由侄子家养活,侄子家人却经常对其恶言相向,MKZ的遗产悉归侄子家所有。后来侄子家有人生病,便怀疑是MKZ成了犯丧,因想到MKZ死时对他们颇有怨气。侄子家便请人掏了MKZ的坟墓,并将其尸骨烧了*田野报告人:南芝林,男,90岁,C县小川镇天山村人,时间:2013年4月9日,地点:南氏家中。。实际上,在前述南姓年轻人的故事中,人际关系状态的因素也存在,他个人的行为使得村人将其视为一个危险人物,不为众人所接受,长期被村人所排斥、看不起,在他死后,人们则继续感受到他还会危害人,甚至要进行报复。
其三,犯丧出现与否也跟人们对亡者葬地风水空间的感觉紧密相关。例如在T村南姓年轻人的故事中,人们还解释说:他死后已经是“阴人”,又被村人葬在非常靠近两条大水沟汇合的地方,即把“阴人”葬在“阴”地,促其成为犯丧。又如在S镇那位“月婆子”的故事中,人们对其葬地风水状况的感觉甚为细腻:
她是一个月婆子,埋的地方在一个深沟里。这道沟你说有水淌哩却好像一个干沟,说是一个干沟却有点水淌哩,大多时候湿乎乎的。沟右侧是荒坡坡子,红沙土,月婆子埋在沟的另一边,是这家人的一块地。地的上边上一个大坎,你站高一点看,土坡与这家人地的上坎合起来就像一个杠头(耕犁),地上边的大坎是杠檐(犁檐),月婆子正好被埋在铧头上。风水上这就相当地不好,犹如犁头耕地一样,把埋下的死人给往出翻,是根本葬不稳死人的,加上是深沟地方,阴得很,埋的时候还接上地下沙层,沙吸水,埋下后棺材也把水也吸进去了,这些凑在一起,不该犯的都要犯了*田野报告人:曹喜娃,男,53岁,C县X镇人,时间:2013年4月10日,地点:X镇兴隆山祖师庙。。
这个故事表明,除了亡者个人特征之外,对葬地风水状况细腻之感知也构成解释她死后成为犯丧的另一重要因素。案例中,埋葬之地处在流水似有似无的山沟中,属于传统阴阳二元观念中的偏阴之地,更重要的是人们从葬地周遭地形感觉到亡者被安葬到了“犁穴”上,从而自然地想象会如犁地翻土一样安葬的亡者会被翻出来,根本不可能将她安葬得稳当。
在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美籍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曾以“弥散性宗教”的概念视之为一种与世俗的社会生活、制度混为一体的宗教样态[7],这启发了后来很多学者的思考,并深刻认识到,民间信仰研究并不能以某种固定类型框架获得完全理解,需一种源自民众生活经验的理解态度,特别是要体验到民众的信仰是由日常生活中长期积累的判断、体认周围事物及其存在的细腻感觉给予展现的。恰如杨念群所指出的,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大量信仰细节乃由地方独特“感觉结构”所形塑[8]。从西汉水流域汉人的犯丧信仰中可以看到,它形塑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疾病、现实遭遇的感觉性解释,这种解释方式完全不同于通常所谓的科学理性的方式,是一种人们在地方日常生活中长期积累的关于人、事、物/空间的经验性觉察能力。上述几个案例显示出,对亡者之年龄、性别、性格、死亡方式、坟地风水状态及人际关系状态与亡者尸骨状态之间关系的感知,清晰地呈现了多样化的基于生活积累形成的感觉结构:老/少、男/女、温和/暴烈、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阳/阴、关系和谐/关系冲突。由于这些感觉结构与人们生活的现实场景、历史背景密切关联,所以当相应感觉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再现时,人们生活中遭遇的异常便被敏锐地感觉为是出现了犯丧所致,从而使得犯丧信仰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被“再生产”出来:从一种观念存在成为生活中人们切实感受到的“现实”存在。
二、“烧犯丧”的集体实践:村落世界的剧场化
当村落连续遭遇的异常一旦被乡民感觉到是由犯丧所引起,恐惧随之袭来,并会迅速升格为集体感受的一场巨大危机。人类学家特纳指出,“为了控制危机蔓延,受到扰乱的社会体系的领袖人物或者代表秩序的成员会迅速采用特定的调整和矫正‘机制’……公共仪式的展演也属于矫正机制”[9]。在西汉水流域,汉人传统的集体“烧犯丧”活动便是此种意义上人们设计的一种公共仪式展演,作为危机的矫正机制,乡民意图通过将亡者未腐朽的尸体烧化为仅剩白骨或灰烬,以斩断灵魂与尸体依然保持着的联系,从而在宗教世界观的层面达到对危机的根本矫正和对恐惧的彻底消除。
在一场集体举行的烧犯丧仪式的开始,乡人先是请神显应,由设坛请神、降神、抛帖子等三个环节组成。按照惯例,坛场要求选择在村中海拔较高的地方,最好是能看得见全村的位置。设坛后即请神,由村落中的宗教权威“法官”负责,他们是道家居家派,归属正一道。在地方,人们依从自己的感觉,将神灵区分为“文神”和“武神”,前者为佛、菩萨等高级神灵,后者则是作为村落保护神的龙王老爷。相比而言,人们认为只有喜欢武力解决事情、敢打敢杀的后者镇压鬼魅、犯丧等恶邪力量最为灵验。所以,请神旨在请村落保护神龙王老爷临坛。请神后,法官代表众人向神灵禀明村落的最近遭遇,感觉到可能是发生了犯丧,求其佑助消除。神灵允否,由法官卜卦得知。不过人们认为,请神后还必须降神,因怀疑请神时可能有游走之神冒充,担心龙王老爷没有亲临。降神时,四个年轻人抬起龙王神轿,法官配合以咒语、茅山诀窍施法降神。一旦龙神轿疯狂旋转而难以停下,便被认为神已被降下来。反之,法官则会用瓦片、筛子击打神轿,它们分别象征着道教法术中的“五雷”“天罗”等酷刑,意乃强制神灵显应。“法比神大”,乃乡人对此举所作的解释。降神后,立马进行抛帖子仪式,一方面,是为了再验证降神是否可信,另一方面,是凭借神灵的力量对感觉村落已遭遇了犯丧的危机程度进行证实和判断。仪式中的帖子是写有判断吉凶文字的纸片,共三张,分别写“福”“灾”“祸”。其中,福帖的象征意义是地方和顺,灾帖的象征意义包括天灾、传染、犯丧,祸帖象征的的意义是人祸、犯丧,后两个都意味着村落遭遇了犯丧。制作好的帖子由法官交给一人秘密藏于村落三个不同地点。接着,在法官的主持下,人们紧随四人抬着的龙王老爷神轿而行,在全村境内寻被秘密藏起来的帖子。若能找到帖子,便再次确定神灵真的降临,更重要的是,人们还依据寻找到福帖、灾帖、祸帖的顺序来判断地方面临的吉凶程度:若最先找出福帖,意味着地方安宁,即使遭遇犯丧也不严重;若最先找出祸帖或灾贴,则不仅表明有犯丧,而且程度颇为严重。
继而进行的仪式活动是为出场的人和神确立行动规范,分别是先后举行的“立名单”“插界”两个环节。立名单时,每个家庭的“掌柜的”(男性户主)代表所在家庭将自己的名字签写于两张同样大小规格的纸上,或者按手印,以示同意并参与集体烧犯丧活动。一式二份的名单签好后,一份交给当方龙王会的头人保管,一份则交给当方龙王老爷保管——这份名单会被当众揣在神轿中龙王老爷像的怀里。头人是村落选出的民间权威,具有对仪式事务的指挥和裁决权,而龙王老爷是直接对应于地方的最高神界权威,在众人心中拥有至高的裁决权和公正权。人们解释说,此举旨在避免村落内发生可能的纠纷:众所周知,传统汉人观念中,逝去祖先的状态与活着的亲属的状态紧密关联,祖先坟地风水及其安葬状态对于祖先的状态至为关键,一般安葬好的祖坟是不能轻易动的,然而烧犯丧不仅要掘开亡者坟墓,还要烧掉未腐化或未腐化充分的亡尸。这样一来,祖荫观念与烧犯丧行动间的文化内在冲突便会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处理不好极可能会导致村落纠纷。在前述的抛帖子环节,虽以神的名义确定了犯丧存在,但并没有确定谁家安葬的亡者成了犯丧以及整个境内有多少,且与私人家庭举行的烧犯丧活动所不同的是,私人家庭举行的仪式一般会有明确感觉到的对象被怀疑,集体仪式则没有。由此,在正式烧犯丧之前通过这一方式既将村庄集体福祉平摊,使得每个家庭都有义务、责任为集体做出必要的牺牲,更避免因意外引发可能的内部纠纷。在紧接着进行插界仪式时,法官要制作五个界牌,分别写上东、南、西、北、中之相应五方五帝神名,或制作象征五方五帝之旗号的五色界旗,然后派四个人将东、西、南、北等四个界牌或界旗插于村落相应方向的边界处。这样的实践完全与人们的空间观念有关。在西汉水流域的汉人社会,人们不仅仅在物理意义上理解村落的空间结构,还从宗教宇宙观层次上想象与建构村落的的空间构造:想象自己居住的村落有一个中心,有东、南、西、北四向边界。这实质上体现的是以“四方—中央”为模型的传统“五方”空间观[10]。在神学的意义上,此环节旨在为仪式中神的活动确立一个社会性边界。人们解释说,如果邻村也有犯丧出现,一旦龙王老爷开始查犯丧,便可能会越界查到邻村人家的坟上,由此可能引发村际械斗。插界仪式通过把本村落与邻村的边界以神圣方式标画出来,虽是在神学上限制龙王老爷的活动范围,但实际上则是限制人的行动边界。比较这两个环节,前者透过“同意”机制消除村庄内部潜在的纠纷,后者则以神圣方式刻画边界达到避免与周边村落的可能冲突,分别塑造着村落的群体团结、边界意识。
接着顺序进行的“查犯丧”“烧犯丧”“扫煞”等环节构成了整个仪式的高潮。需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个体家庭举行的烧犯丧仪式因可直接怀疑到某位被安葬的亡者,故无须进行这一环节,但集体举行的仪式不管人们怀疑的对象多么明确,都需要通过这一环节以便在村落境内所有安葬的亡者中进行确定。实际进行前,还要先以特殊方式对龙王老爷进行保护。这种必要性常常透过西汉水流域普遍流传的一些烧犯丧故事所阐明,强调由于某些犯丧煞气太重,导致龙王老爷神力衰减,甚至丧失灵力。在进行保护时,人们用一块丈二长的白生布将龙王老爷的轿子紧紧裹住,白色为“阳”,鬼煞为“阴”,阳克阴,被认为具有保护作用。保护工作做好后,法官旋即施法驱使龙王老爷在境内查找犯丧。此时,抬神轿的人被认为不过是龙王老爷借用的脚力,并无自我意志。神轿走在最前面,人们紧随其后,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一旦走在最前的神轿冲向某个坟头,并迅速压在坟脊上,便意味着该坟埋葬的亡者成了犯丧。紧随的法官立马施法念咒,并用石灰将此坟圈住,石灰是白色的,属于“阳”,犯丧属“阴”,便可圈住犯丧,不能逃出。此外,这一环节选在中午进行,因正午前后至阳,犯丧不敢出坟墓。如此一个一个查找,直到查完全境所有的坟地。查出的被一一圈定后,待到晚上便集体出动火烧犯丧。这是一个紧张而激烈的时刻,人们谨慎地将坟墓挖开,掏出棺材,若是年轻亡者、煞气重、厉害的,便连棺材一起烧掉,若年老而亡、煞气轻的,便将尸体从棺材移出后烧掉,再将骨头装回棺材重新掩埋。烧完后,人们接着抬上神轿到村落各家进行扫煞,人们感觉还有流窜到居住区的煞气须要扫除。每到一家,神轿都要被抬到堂屋驱邪,同时法官使用“雷火”扫邪,还要施法将屋中的邪煞收伏,包在一张纸中,踩在自己脚底下带走。神轿出门后,法官会在该家屋门上方贴一道“飞符”,或于门扇上贴一道“坐符”,以护持家庭。仪式这般一家挨一家进行,每到一家众人都紧紧相随,绝不会漏过村落中任何一家。
最后,处理收伏的邪煞并隆重酬谢神灵佑助。扫煞后,人们便聚集神坛镇煞除邪。法官从鞋中拿出收服在纸包内的邪煞,装入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陶罐中,一边施法念咒,一边将事先准备的各种“禳物”装入罐中。禳物包括五色粮食、羊毛、菜籽、美子刺根、香灰、柿子蒂、高粱根须、芿子杆等。它们因为自身物性特征的差异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如柿子蒂的外形酷似印章,象征道教法器“翻天印”、 芿子杆分结的外形构造象征法器“三节鞭”、香火是万人虔诚焚香生成的隐喻“万人心”……都被认为具有镇压、消除煞气的作用。禳物装完,法官施法用纸将罐子封住,然后在神坛选一个地方,挖一个深三尺六寸的坑,置罐子于坑内,并将一个用椿木所制一尺二寸长的“五雷四镇”符插在坑中央,最后一边施法、念咒,一边将其掩埋。掩埋好后,还要在旁边立一个椿木符桩,长一丈二尺,上下两端画符头、符尾的纹样,中间抛光一侧上写:“敬请中央大梵张天王头戴黄铁帽身穿黄甲盔差我下凡镇鬼精止煞除邪。”桩顶悬挂一个筛子,筛口朝向桩身,一双绑成剪刀状的筷子系在筛底,隐喻道家法器“金刀剪”,筛底中央插一面用朱砂写有“佛”字的镜子,人们认为镜子能将佛法护佑照射到全境,这一意义也是坛场选在村落海拔较高处的原因。大桩立就,法官请龙王老爷守镇。镇期一百天,百天之后即进行揭镇、卸桩仪式,人们相信此时邪煞已被完全消除。为了感恩龙王老爷,人们集体出资购买牺牲,或聘请师公,隆重举行酬报活动。
纵观西汉水流域汉人的犯丧信仰实践,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犯丧危机开始,到集体举行“烧犯丧”仪式对危机进行化解,整个村落便逐步从日常的生活世界进入到凡俗与神圣融合的剧场世界,人、神、犯丧作为“演员”,彼此之间进行着不同性质的关系互动,最后人则借助神的力量将危机消除,将紊乱恢复为有序。但除上述神学层面的意义之外,犯丧信仰实践还对村落社会整合提供了多重意义。首先,从整个过程一开始,集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状态便发生了结构性转换,这一转换蕴含了明显的社会整合性,使得感受到同一恐惧、危机的人们凝聚起来并以共同的行动寻求对危机的矫正;其次,表现为仪式实践对于村落社会的整合:一方面,整个仪式过程实践所营造的集体欢腾场面,如涂尔干对澳洲土著宗教仪式分析一样,使得每一个人感受到村落集体实在的力量[11],另一方面,仪式中的特殊环节如“立名单”“插界”“扫煞”等分别在不同层面显现了独特的整合性;第三,仪式过程在不同的层面再生产了神圣符号的社会象征性。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作为地方保护神的信赖、认同进一步强化了它的集体象征性,一方面,剧场世界所演绎的地方保护神与犯丧、邪煞间的对立深刻地凸显了它在道德上的象征意义,这些对村落秩序维系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余论:地方感与村落社会的民间信仰整合
作为一个学术主题,“社会整合”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会受到社会构成力量的约束、规范与引导,其中宗教力便施予非常重要的影响,使得个体相互依赖形成一个稳定有序的群体*在涂尔干的论述中,“社会整合”含义体现为social solidarity一词,通常翻译为“社会团结”。晚年,他对宗教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展现他对宗教社会整合作用的精辟阐释。。在西汉水流域,犯丧信仰实践对村落社会的整合显现了多重意义,也充分表现在涂尔干所强调的集体意识、仪式营造的情感与气氛以及符号的象征意义等层面,但需要看到的是,这些多重意义产生的前提则是作为信仰再现基础的地方感,正是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感觉结构,人们彼此相似并达到对日常生活现象的相似理解,对疾病、遭遇做出同一性的解释,进而在共同的恐惧与危机感受中紧紧凝聚起来共同行动,因而也是仪式对村落发挥整合功能的前提。除此之外,地方感对于民间信仰社会整合性的生成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感觉结构显现的强烈道德色彩对于村落社会生活实践有明显控制和整合作用,例如作为构成人们感觉结构之一的人际关系方面,往往直接会引发人们进行反思,促使人们将人际关系中的行动与行动中的人际关系投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从而对村落社会秩序的良性运作产生积极意义;一方面,仪式实践对村落的整合也充满了感觉主义色彩,例如仪式实践中选择神坛位置的高度与保证村落全境清平的关联、“插界”建构的地方空间神圣感对群体边界的塑造、对神桩上系有“佛”字的镜子照射护佑功能的解释等,都无疑是透过感觉主义被赋予社会性指向,从而强化行动中村落集体与个体间的结构关系。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社会世界是处于不同生活方式之中的地位群体所形成的空间,人们在相似的类别身份中确立自己的地方感觉[12]。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相同,身份也基本相似,分享着相似的地方感。这种共同性对村落社会整体秩序的维系具有基础意义。一旦这种一致性被破坏或改变,必然会引发村落社会整合问题,这在各种内、外力作用下当代村落关系的变迁中最为明显,特别是作为维系村落的地方信仰体系不断被冲击时,寄寓其中的感觉结构便会最先发生变化,直至完全改变时,信仰体系的社会整合性便会不复生成。由此,研究启示我们如何在现实的情况下以新的动力、机制建构乡民一致的地方感,应是思考当代村落整合问题的一个重要层面。
[参考文献]
[1]林国平.论闽台民间信仰的社会历史作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2):111-117
[2]陈重成.中国大陆村落社会中的象征体系和权力架构.新世纪宗教研究(台湾),2003(3):105-141
[3]高长江.民间信仰: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本.世界宗教研究,2010(3):115-124
[4]Dean Kenneth. Local Communal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China.ChinaQuarterly, 2003(6):338-358
[5]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吴凤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0]潘朝阳.“中心—四方”空间形式及其宇宙论结构.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报告,1995(23):91-103
[11]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2]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SociallogicalTheory, 1989(1):14-25
Sense of Place, Folk Beliefs and Village Integratio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the Burn Zombie Custom in the West Han River Valley
Tai Wenze
AbstractThe faith for “zombie”, existed in the Han Chinese community in Western Han River Basin, reflects a unique knowled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n the death. The feeling structure formed by long-term life accumulation, not only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reproduction of this faith itself in their daily life, but also constitute a logic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burn guilty zombie” ceremony, which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nse of place in the folk beliefs of soc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Sense of place; Village society; Religious integration; Zombie; The West Han River Basin
(责任编辑:常英)
[作者简介]台文泽,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邮编:730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西汉水流域汉人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秩序建构”(项目编号15LZUJBWZY081)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