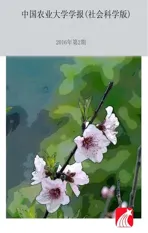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剥夺与异化
——对四川葛村资本农场的实地研究
2016-01-25潘璐周雪
潘 璐 周 雪
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剥夺与异化
——对四川葛村资本农场的实地研究
潘璐周雪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的推进,资本农场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活跃。文章以四川省葛村资本农场中的实地研究为例,通过对农场劳动组织与管理过程的分析,强调指出资本农场对农业雇工的劳动与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面对资本农场强制性的劳动分工、生产环节的拆分、生产知识的宰制等劳动组织方式,农业雇工被异化为企业生产律条下的附属品,逐渐丧失其生产生活中的自主性;同时,农民社会中的劳动伦理与道义掩盖了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夺,使其所遭遇的异化和剥夺进一步强化。通过对资本农场中农业雇工生产过程的剖析,文章对现代农业和以资本化、规模化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模式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资本农场; 农业雇工; 劳动组织; 生产关系; 异化
近年来,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最突出的发展趋势和转变方向[1]。土地流转被视为发展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的先决条件。相当数量的土地以不同形式发生了流转,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2]。大规模的土地流转背后往往伴随着资本下乡以及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的渗透,也引发了“三农”学者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势的讨论[3]。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都经历过农业资本主义的转型和资本农场的大规模发展,如英国18世纪末以暴力的圈地运动实现的“英格兰道路”和美国19世纪以土地平分运动等实现的“美国式道路”。变迁道路虽有不同,但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通常都表现为大规模资本经营取代小农经济、资本家对家庭农场主的替代、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化[4],它是以资本雇佣农业工人的农业生产,生产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并实现资本增值[5]。在中国,近年来资本向农业部门的不断渗透同样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由外部资本主导的资本农场逐渐活跃。资本农场是以资本雇佣劳动形式进行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领域中表现的载体[5]。从农场所有权来看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来看,资本农场与传统的家庭经营、集体经营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由成员作为所有权人,以劳动雇佣资本;而资本农场则是由资本为所有权人,以资本雇佣劳动[6]。一般来说,资本农场是由公司和企业经营,企业主和公司董事会决定农场经营的方向但并不参与农业生产,农场经营极具“统一性”: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耕作,统一管理,统一销售[7]。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大农场取代小农农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同时,政治经济学也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农业部门扩张所面临的障碍,如自然环境和生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劳动时间与工作时间之间的差异、劳动力和生产时间的无身份、作物的较长生长周期以及劳动力时常无法产生利润等问题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农业成为一个难以被资本主义收编的领域[8]。其中,对农业雇工的劳动监督是大规模资本农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业生产中作业场所开阔,即使雇佣农业劳动力,也不可能对其作业进行全面的监督。如果一定要进行监督,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9]。这是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存在的重要区别,也是大规模企业生产在农业部门遇到阻碍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农业中,农业工人的劳动价值远远低于农民自己的劳动价值[10]。一些中国学者也通过经验研究指出了资本农场的农业雇工与生产组织可能存在的问题。从雇工角度来看,在农场劳动力需求有限的情况下,更多农民在失地的同时被挤出雇工行业,沦为雇工的农民短时间内很难适应从生产资料所有者到雇工的身份转变[2]。尽管名义上,雇工是自由劳动者,然而缺乏生产性资源使其并无实质性的退出自由[6]。从资本农场角度来看,目前的农业雇工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与发展现代农业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11]。雇佣劳动存在一定道德风险,雇工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极高的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而抵消农场的生产效率[6,12],且资本农场使用雇工的粗放式经营很难有效应对自然风险[13]。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针对资本农场和农业雇工的学术讨论中,焦点大多集中在雇工经营的效率问题、雇工经营是否符合农业生产规律以及土地规模化集中后存在的社会公平问题,对于农业雇工的劳动过程和工作境遇则鲜有交待。
规模化的资本农场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对村庄侵略性强、管理成本高、监管风险大等问题。尽管如此,大批资本农场在村庄的兴起已成趋势,也由此引出了本文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在村庄,依靠大量雇工进行生产的资本农场如何进行劳动的组织与管理?作为雇工的农民其劳动过程与普通农户经营有何差别?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是否会如无产工人一般遭遇资本的剥夺与异化?2014年3月,笔者在四川省葛村*本文出现的所有地名和人名均为学术化名。进行了实地研究,以期在实践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笔者在村庄妇女主任的引荐下进入当地的一家资本农场,白天在农场和雇工一起工作聊天,以参与观察的方式了解农场的运转状况;晚上随雇工下班回家,了解他们的家庭和社区生活状况。在田野过程中,笔者对1名农场管理员、12名农场雇工、10名普通村民进行了深入访谈。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分析资本农场的劳动组织与管理情况,反思其对雇工劳动、生活与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
一、进入村庄的资本农场
葛村位于四川眉山市锦竹县临江镇,由9个村民小组构成。全村面积9.7平方公里,有1 200多户。村民主要种植水稻和油菜,水稻亩产1 200~1 300斤。葛村围绕岷江呈半圆形,主干公路将村庄分为两半,支公路较多,村民交通出行极为便利。村中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较为普遍,尤以男性劳动力外出居多,输出地包括广东、甘肃、青海、云南以及国外等多个地区。因此,农业生产主要由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承担。近年来,村民举家外出务工的情况越来越多,农地流转给村外人的现象也开始普遍。目前,葛村的外来农业经营者较多,但是规模较大且长年雇佣雇工的资本农场仅有一家,即本文的案例农场——丰业农场。
2010年,临江镇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在葛村引进一家农业公司——丰业公司。丰业公司通过并购和租赁等方式先后将葛村的一个大型养猪场和一、二队425亩耕地流转入公司,并分别成立“丰业牧业公司”和“丰业蔬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丰业农场),主要从事生猪养殖、蔬菜和苗木种植。流转了土地后的村民生计方式也有了变化:年轻有劳动能力者继续外出打工,年老者或有家庭负担的妇女则选择在周边寻找零活儿——大部分成为农场里的雇工。虽然名为“合作社”,但并无合作的实质,丰业蔬菜专业合作社完全是一个以雇佣劳动形式进行生产的资本农场,无论是村民还是地方官员均称呼公司经理梁丰业为“老板”。梁老板平时并不过问农场的具体经营情况,他聘用了葛村的妇女罗玲做农场管理员,聘请了乐山的一个师傅做技术指导,自己每个星期只来农场查看一次,对农场进行远程管理。
400多亩的农场除少数几亩地种了观光树之外,其余土地均种植蔬菜。农场蔬菜种植品种与当地农户不同,一些外地品种,如韩国莴苣、广西南瓜等在当地并不常见。农场蔬菜的生长周期与当地农户的生产季节历也有所不同,其蔬菜种植时间早于农户,收获时间也会提前。蔬菜成熟后并不在本地销售,而是卖到重庆、成都、宜宾、乐山等附近的大城市,由买家上门装货。在工业性生产要素(如农药、化肥、催长素等)和生产技术的调控下,农场的生产并没有当地农时所体现的四季分明的特点。因此,农场的劳动需求量非常大,需要招纳大批雇工。管理员罗玲这样介绍农场的工作情况:
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活儿干,没什么忙季和闲季的区分。比如3月开始种菜苗,中途需要照料,除草施肥浇水都是工作,4月又要开始摘菜,摘的过程中又要种菜苗,5、6月是最忙的,南瓜等几种蔬菜都成熟了,需要摘。蔬菜是按季种的,一般两三个月成熟了又要种下一季。来这里工作的雇工年龄在40多岁到70多岁,50岁以上的偏多,大家都住在附近。雇工按居住地分组,住得近的一团为一组,现在总共有4个组。忙的时候,一个组有40多个人,现在不是忙季,一个组有十多个人来,最多的时候农场里有160多个雇工。农场工作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工人一天至少要做满8个小时。工资每小时5元钱,一个雇工每天的工资是40元。
作为农场的管理人员,罗玲负责农场的所有事务,包括农场的雇工安排、工天计算、蔬菜客户联络、监工等工作。面对400多亩地的工作安排以及庞大的流动性雇工,管理员是如何组织、筛选和管理这些劳动力的呢?我们发现,内嵌于村庄中的人情和关系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除技术人员外,从管理者到普通雇工,农场人力资源均来自葛村。尽管他们进入农场后的身份角色发生了转变,但是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思维惯习仍旧在农场工作过程中占据重要作用。通过人情与关系,管理员在小组长和普通雇工的组织管理中自动形成了一套聘用与选拔方式。来农场干活的雇工大部分来自农场所处的二组或者距离二组最近的三组和五组,他们和管理员罗玲彼此认识。为了方便管理,罗玲按地域将大家分为4组,每组的成员住得比较近。每组选出了一个小组长,专门负责联络组员和通知消息。农场虽然每天都有活儿干,但每次的劳动力需求量不同,因此在选择每天由谁上班的时候,罗玲会按照人情关系的远近来做选择。小组长负责通知雇工上班,当农场需要的人员数量有限时,她们也会自己做出选择。下面是第一小组组长的选人方式:
活儿少的时候那边(农场)要人会有控制,比如一个村里要几个。大家都想去,但是也要不了这么多人,一般就会通知附近的,通知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一般通知那些比较熟的、聊得来的、关系好的。今天下雨就是突然接到通知要上班,我叫了几个平时常一起干的人。活儿少了,其他人想干也没有办法。
村民马洪生也是二组的人,土地流转给农场后就在梁老板的养猪场干活。养猪场的活儿更加辛苦,前一阵他干重活扭了腰,现在仍在家休养。当问及为什么不去梁老板的农场而选择在养猪场干活,他表示自己“没有那一层关系”:
农场不是谁都能去的,去农场干活儿也需要有人在那里。现在都不知道那些人提了多少只鸡给管理员了。我们没这层关系,那里有活儿也不叫我们。说的是报名就可以去,但是去了不熟的人,别人会给你脸色看,一直盯着你,做事儿不能让你慢了!
除了视人情远近来挑选雇工之外,作为村庄中间人的农场管理员也会在人情关系的影响下对雇工的管理适度宽松,偶有雇工上班迟到的现象,管理人员会看在往日情面上,让他们下班后把迟到的时间补上,而不是直接扣工资。有时雇工在上班时间因家里临时有急事、需要请假,管理员也会因为熟人关系适当宽容。作为外来人的农场主梁老板偶尔也会赠送雇工一些农场的资源作为一种工作奖励,以此为自己在村庄和村民中间获得一份面子,塑造自己“慈善资本家”的形象。比如,对于每天交货不合格的菜,梁老板会允许雇工将菜带回家。蔬菜地里长的青草,梁老板都默许雇工割回去喂猪和牛等。有时候养猪场流出的粪水较多,雇工也可以挑回家种地。当然,农民眼中的这些“资源”在农场看来则是一些剩余和废物,而农场主的“馈赠”也仅限于此。这些念及人情的做法虽然极其细微,但是在朴实的村民看来他们已经欠下了人情,只得通过努力工作或者赠送礼物等方式来加以回报。例如,村民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加班,以此表达对农场主和管理员的感激。
二、资本农场中的劳动安排与雇工管理
资本农场委身于市场,以盈利为目的。它在生产上主要采取工厂化管理模式,将农业耕种视为“田间操作”实现高效率大规模生产。在种植蔬菜经济作物的案例农场中,作物类型决定了机械化生产的不适用和大量雇工的必要性。在这种意义上,农民雇工就成了农场上可移动的“生产工具”。尽管雇工与管理者乡邻关系的特殊性使得农场管理中偶尔会有“温情”的一面,但是这种偶尔的温情无法掩盖资本农场中雇工成为商品化劳动力的现实,也无法掩盖资本农场的类工厂管理模式对雇工以土地和村庄为根基的生活造成的冲击与破坏。从自耕小农向雇工生产者的角色转变,使农民逐渐丧失了在农业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上的自主性,他们与自身的劳动和社区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与隔离。
(一)“螺丝钉”原则下的劳动分工
螺丝钉精神最初出现在雷锋的日记中,他认为螺丝钉虽然细小,但是缺少了它,整个机器将无法运转,如果一枚小螺丝钉没有拧紧,那么整个机器将出现故障。后来,螺丝钉精神被许多企业采用,用以鼓励员工以公司利益为重,在自己的岗位下完成自己被分配的任务。例如,一篇名为《富士康十连跳,员工不是螺丝钉》的网络文章中曾写道:“企业不能把自己当成一部印钞机,大把地出产着钞票,而视员工为印钞机上的一个个螺丝钉*“富士康十连跳,员工不是螺丝钉”,http:∥www.taoke.com/article/31637.htm,2010-05-24。。”而一篇著名的网络博文也曾描述工厂的生活:“工人变得和螺丝钉一样微不足道,而且是可以随时替换的螺丝钉*徐明天:“富士康螺丝钉,员工很不简单”,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eab9250100moct.html, 2010-11-10。。”在本文的丰业农场中,农场对雇工的定位和管理也秉持这一“螺丝钉”原则,注重雇工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一个部件的工具性,而作为人的个性被严重忽略。
在大批量的工作任务和人员调配下,为追求效益和方便管理,农场更多地强调任务的执行,忽略劳动者个性。因此,年龄、性别等劳动者的自身特征被忽略,雇工被贴上统一的标签,拥有相同的劳动价值,就如一颗螺丝钉,等待被随机安排到需要的岗位。
传统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性别分工,“男耕女织”是家庭的基本生产模式。在当下农村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老、少、妇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农场建立后,不少缺少生产资料或生计来源的留守老人和四、五十岁的留守妇女来到农场干活,目前农场雇工中超过80%为女性。然而,农场在工作分配中没有特别注重男女分工,仅通过人数来衡量工作劳动量需求。多数情况下,男女一起干活,不分轻重。女性雇工冯冬梅这样描述自己在农场的劳动分工:
我什么活都干过。打药、施肥、挖沟、摘菜、挑粪等,农场没有男女分工。管理员说某块地上需要几个人,组长就随便点几个人过去。平时在自己家里都是我一个人种地,这些活都干过,虽然累,也习惯了。再说,老板付的工资是一样的,你要领这点钱,就得会干活,还得把活干好。……种地的活儿都需要劳力,男的力气大做着要轻松些,但是女的也都能做,种的菜也还是一个样。
传统农业中,家庭会根据劳动力的强弱进行劳动分工,老人在分工中受到庇护。干农活时,挖、挑、抬、背等环节都不能缺少气力,但农场没有因年龄而形成分工差异。农场对劳动力需求较大,在招聘雇工时没有年龄的限定,只要村民有意愿,都可以到农场干活。这样的低要求吸引来了大批65岁以上的老年人,虽然年事已高,他们在农场仍旧不得不紧跟生产节奏,和大家完成相同的工作。
雇工许大妈70多岁了。在菜地里摘娃娃菜时,她的背篓已经装了很多,起身时又往背篓里放了两颗菜才开始向交货的地方走去。她说:“大家的背篓都满了,我也不能少,被管理员看到不好。”不管年龄有多高,来到农场就拥有了相同的身份,管理人员不会因年龄因素而有所偏袒。
在农作过程中同一化的劳动分工和劳动标准显然是从管理者角度作出的便利安排,这一做法既加剧了对劳动者的异化又降低了农场的工作效率。在相同工资回报下,身体强健的雇工容易产生消极行为(比如延长摘菜与背菜的时间),而体弱的老年雇工则为了获得工资报酬不得不隐忍负重,迫使自己付出更艰辛的劳动,承受更沉重的心理和道德压力。
(二)流水线式的生产环节拆分
效率是资本农场日常管理中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农场的农业生产工作就是“田间操作”,即像工厂车间操作一样对农业生产环节进行拆分。这种生产环节拆分类似于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在农场的耕作过程中,由于整体工作量较大,管理的人较多,因此被分配的任务需要尽可能的细化、简单、明确。管理员根据技术人员的需求,将雇工分配到某一个单一的程序上执行任务。比如:雇工上半天的任务可能是在白菜地里挖土,下半天又可能被调到菜地里锄草。原本随农时季节变动却又整体连续的农业生产过程现在被分割成一道道前后断裂的劳动工序,雇工只是依照管理员和技术员的指令完成被要求的某个动作和生产环节,他们在完成当前生产环节的时候,并不知道前后的工序是什么,有时候甚至不清楚自己某个劳动的作用和意义。这种生产环节的拆分使他们完全成为提供劳动力的工具。
这天下午,工人们如前几天一样,在地里摘白菜。突然,管理员罗玲走到地里告诉组长,今天摘完菜后到南边的地里挖沟。一组组长站着吼了一句:“不摘菜了,回家拿工具,在南边的地里挖沟!”大约10分钟左右,雇工陆续拿着工具赶到农场,20多个雇工集中在南边的地里。那块地明显是刚用松土机耕过的,从土的颜色看,不到半天时间。土面上稀松地撒上了白色圆颗粒肥料,雇工都表示不知道是什么肥,有人猜是磷肥或者碳铵。挖沟就是在耕过的土面上平均挖出浅浅的沟,使土地被一行行分成许多竖直的块。大家也不知道这块地是用来种什么的,管理员也没有告诉他们。后来据有人打听,这块地挖沟是用来种南瓜的。对于什么时候给菜地打农药、农药的用量等这些涉及生产过程的问题,雇工完全不清楚,都得听技术员的临时安排。打农药的时候是技术人员配好浓度之后告知雇工该怎么操作,雇工并不知道打的是什么药,对作物有什么作用和影响。
农业原本是一个完整连续性的生物过程,从作物种子落地、生根、发芽、成长都需要人的精心呵护和管理。农民对土地和作物种植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是土地的利用者也是照料者。在家庭生产经营中,农民会随时观察自己作物的生长情况,根据每棵植物的生长状况浇水、施肥、除草、打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十分细心:看到作物上的虫子,他们会顺手捉掉;锄草过程中挖坏了作物,他们会心疼;施肥打药都得小心,因为这影响着他们一年的收成。然而,农场耕作过程中生产环节的拆分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得僵硬。频繁地更换工作任务,使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弱化,没有稳定的管理对象,导致他们耕种的成就感降低。
农场生产环节的拆分,也使知识宰制现象凸显。农业种植原本是农民的老本行,在这里,他们却成了种植的“无知者”,对自己的技术操作充满了疑惑。工作过程中,技术人员成为农业种植的权威,他控制整个农场的生产进度,安排生产资料,指导耕种方式。他规划农场的生产布局,计划好每个步骤需要的劳动力,然后向管理人员提出劳动力需求,管理人员根据需求安排雇工。雇工在整个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完全听从技术人员安排:技术人员会将配好的农药交到雇工手中,雇工根据技术人员指定的量喷药;雇工在某块不知用途的土地上挖土,技术人员指定挖的深度;雇工根据要求的方式摘菜等。从本质上来说,雇工没有参与到种植技术与方法的制定过程中,也没有在看似更加专业先进的农场中真正学到任何新的种植知识和技术。在农场管理者看来,雇工不需要学习和了解技术,只需要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务即可。雇工大多认为在农场种地和家里没有区别,都是熟悉的农活。但是从他们的劳作行为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一些差异,比如:雇工已经适应了工人的身份,他们可以快速丢下手头的活转到下一个任务中,而不去考虑对于作物生产是否合理;他们更关心田块的土质是否容易挖沟和劳动强度的大小,而不是土壤本身是否有利于蔬菜生长。
那么,生产环节拆分后的细致分工与知识宰制下技术人员的统一操控真的可以提高大规模耕种的效益吗?在农场中,不同的雇工在南瓜地里挖出的沟深浅不一,娃娃菜收获时地里出现了大片不合格的畸形菜株,类似的现象都是以工业化的思维安排农业生产时所出现的问题。当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与时间和工资收入挂钩时,当农民从土地的照料者转变成土地上的“打工者”,农民在劳作时必然会由于注重效率而无法兼顾劳动质量。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且影响因素较多,雇工劳动对作物质量产生的影响无法直接检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断裂性的生产安排忽略了农业生产的精度和连续性,也弱化了雇工的生产责任。
(三)农场劳动与雇工生活的割裂
在农场管理制度的约束下,农民从原本的自足式家庭生产进入盈利性的农场生产,他们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发生了彻底转变,雇工的生活需求不再能直接从劳动中获取。在小农农业生产中,农民的生活需求与农业耕作紧密相连。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与需求安排农产品的生产和利用方式,也可以弹性调节生产与生活的时间。传统的农业既不存在劳动分工,也不存在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以及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分离[14]81。如祖田修所说,农活是一种人性的综合,它对于农业行为者具有经济之外更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9]。而在资本农场中,农场的所有生产资料和获得物的使用权和处置权均由农场主掌握,农场的生产活动也有统一的农时安排。因此,在向雇工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农民的生产劳动、劳动产品与生活需求之间出现了断裂。
以循环农业为特征的农户家庭经营极少产生“废物”。作物的根茎、秸秆和品相不好的蔬菜瓜果如果不能食用,也通常可以拿去喂猪或是积肥还田。农民会对土地上的产品物尽其用。而在农场,被蔬菜批发商挑剩的不合市场标准的蔬菜就成了“废物”,有时农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不合格的蔬菜送给雇工,但这样的赠送并不意味着雇工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哪怕是废品——具有实质上的支配权。农场里曾经发生的一起冲突就是因此而起,当雇工理所当然地想将农场里废弃的产品带回家再利用的时候,农民的生存理性遭遇了农场制度冰冷的回绝。
当天下午农场的任务比较重,要摘10吨大白菜。雇工们背着满满的白菜往返于菜地与大货车之间。菜地离装车的地方大约200米,中间是窄窄的田埂小路。雇工每一背篓菜都装得满满的,她们说今天任务重,装太少会被管理员责骂,不能耍滑。下午4点左右,客户需要的10吨白菜摘完了,组长回到地里说:“上面安排了,大家回家拿锄头,去最边上那块地里挖沟。”于是,雇工有的大步走路,有的骑自行车,都回家拿工具。这时,宋海兰将检验不合格的白菜捡了半背篓,准备回家。管理员看了她几眼,非常不满意,叫住了她。
管理员:“你在那里装菜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在上班,别人都回去拿工具了!任务还有这么多,就你还在这里悠闲。”
宋:“我看这菜扔了也没有用,反正要回家一趟,捡回家喂鸡。”
管理员:“这是在上班,也要有纪律。你当真把这儿当作自己家里了!这里的东西又不是你的,下班回家容许你们拿菜也是对得起你们!你不想好好干就不要来了!”
农田劳作与工厂劳动的时间安排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在工厂里,作息表支配着劳动时间的开始和结束;在田地里则相反,作息时间表受需要完成的劳动的支配,根据劳动的进程、天气的情况甚至可能是劳动者的疲劳状况,作息表始终是可以变动的。当农业劳动者是经营主时,他就是时间的主人:他自己确定他的作息表和劳动节奏[14]。然而,当农业劳动者是以雇工身份参与生产时,他的劳作时间便不再受自身掌控,也与农民和当地村庄的生活惯习发生了严重冲突。四川的春季雨水较多。由于农场经常出现临时约到客户上门收菜的情况,原本雨天不下地干活的农民也要常常冒雨去农场上班。我们在村庄的实地过程中就遇到了几次雇工雨天上班的情景。
下雨天1:“今天本来以为可以休息,下雨就不干活儿,结果上头临时通知去,我也得去。我通知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就收拾着去了。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下雨天干活儿,但是要交货也没办法。”(一组组长)
下雨天2:田里大部分人光着脑袋干活儿,没有任何遮雨的装备,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女性雇工说:“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还没下雨,不知道天气有变化,没有带遮雨工具,突然下雨了也没有办法。”尽管下雨,但是由于中午之前就要交货,雇工只能冒雨干活。
农民的劳作时间不同于工厂的刚性制度,在不太紧张或相对闲散的时候,农民有其安排自己时间的自由。“每天上午的劳动是雷同的,下午的劳动则有一些变化和有一定的选择。劳动极度紧张的‘硬时间’与可以自由、放松的‘软时间’交替出现,这无疑是农业劳动者所体验的时间节奏的特征之一”[14]54-55。而这些自由、放松的“软时间”通常是农民串门、聊天、赶集、打牌等等在社区中进行交往互动、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时刻。在进入农场工作、成为雇工之后,农民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被严重压缩,与社区生活出现了脱节。一位刘姓大爷这样诉说自己在农场工作之后生活上的变化:
我是村里老年协会的成员,以前经常参加老年协会组织的文艺活动,和老年朋友聊天打牌,生活挺安逸。但是来农场工作后,每个月要在农场工作二十五六天,基本上就没法参加那些活动了。村里有什么事儿都是老伴儿去参加。有时候吃酒(红白喜事)、赶集和庄稼活儿实在忙不过来,我就请一天假。以前没事儿的时候我会找几个人打牌聊天,现在只有下雨天不上班的时候偶尔打一下。
资本农场的雇工以农场利益为主,按农场的工作安排调整自己的时间。他们逐渐习惯了牺牲自己的生活需求,也逐渐脱离了家庭生产与村庄事务。与此同时,雇工的商品化劳动力身份被不断强化,更深地锁入了雇佣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之中。
三、雇工的劳动伦理与道义
农业政治经济学所忧虑的大规模企业农场生产中的劳动监督问题,在本研究的丰业农场中并未成为困扰农场的主要问题。即便是在农忙时节、组织上百个雇工进行生产的时候,农场的劳动管理也只是依靠一两个管理员。与此同时,农场的类工厂特征,使得农业雇工每天面对不公平的劳动分工、制度的压迫、断续的生产活动安排等。这种拆分式的、高强度的、与生活相割裂的农场劳动,为什么没有挫败雇工的劳动热情、产生消极怠工的情绪?为什么农场中的雇工鲜有对管理制度的抱怨,大多表现出顺从和任劳任怨呢?在农场的工作对于绝大多数雇工,特别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即便如此,相对于田间劳动的辛苦和劳动强度,每小时5元钱的工资并不足以成为让雇工如此认真工作的金钱激励。我们发现,雇工基于他们的乡土生活和小农道义形成了一种在农场中工作的劳动伦理,这才是使农场在低监督成本的情况下顺畅运转的关键。
与工厂工人不同,丰业农场中的雇工是葛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看重人情、面子,注重社会关系,他们也把这些村庄生活中遵从的惯习和道德原则带入了农场劳动实践中。因此,与工厂工人不同,这些雇工极少把自己的劳动表现与薪酬奖惩相挂钩,而是与地方社会中的道德准则相联系,由此形成了一些朴素的劳动伦理。例如,上班不能迟到,迟到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耽误农场的工作,那样显得有失诚信;只要农场有需要就要尽量“帮忙”,不能驳了老板和管理员的面子;工作要认真,如果种不好蔬菜就丢了庄户人的面子,等等。
在丰业农场,每天早上8点钟上班,每天工作必须做够8个小时,每小时5元钱。农场并没有设置类似工厂的刷卡机制,没有统一点名签到的流程,也没有关于考勤的奖惩制度,如果雇工上班迟到,只要下班时自觉把时间补上就好。管理员表示,农场几乎不存在迟到现象。雇工自己也很坚定地表明自己不可能迟到。在他们看来,“迟到”更多地意味着丢面子,而不是扣工钱。为了做到不迟到,不少雇工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作息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安排。雇工易大妈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女儿、女婿每天外出上班早起晚归,她这样描述自己在农场上班的时间计划:
如果要到农场上班,我早上6:30就要起床,吃完饭洗漱一番就7:30了,这时候孙子开始出发去镇上上学。然后,我开始去农场,这里走过去只要几分钟,过去后就等着管理员安排。知道自己要上班,每天早上都得把饭计划好,比如早上把中午的饭煮好,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热一下吃。有时候早上可以把菜也炒好,有时候简单好做的菜也可以中午回来再弄。中午的时候动作要快,不能迟到,回家如果没有剩饭就煮面或者煎鸡蛋,这样比较快。吃完饭马上下去,我们一般都不会迟到,都给了我们足够时间吃饭的(农场中午最多只有1个小时休息时间)。如果老是迟到,虽然不会扣钱处罚,但被管理人员说几句,面子上也过不去。
笔者曾经看到雇工中午下班后赶回家吃饭的情景。中午12点30分,雇工刚下班。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快速往家里赶,有的疾步走在路上。一位大约60多岁的大妈说,今天客户催货催得紧,中午1点半就要上班,要赶紧走,于是小跑着往家赶。如果管理者要求了时间,雇工就不允许自己迟到,他们认为迟到是“不好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对工作的一份热情,更多的是他们在熟人社会中承担的一种道德压力,在集体生活中破坏规则会显得难为情,也会在熟人面前丢了面子。同样,对面子的顾虑会促使雇工认真工作,期望自己种的菜长得好而获得好的“业绩”。好的“业绩”并不会给雇工带来额外的奖金收入,但是他们更看重作为一个好农民种得一块好田所获得的荣耀和认同。
农场里干活比较自由,干活儿时可以小声说话,但不能丢了手头的活儿。平时大家也都不会偷懒,都比较自觉,互相监督着。比如种菜时,虽然不是自己种的菜,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菜能种好,如果菜种得不好,死了,要负责任。哪个人种哪块菜大家心里都有数,如果种死了即使技术人员没发现,大家也会知道谁和谁种的菜死了。我们都是种惯了菜的,被批评了闹了笑话也不好看。如果种得好,大家也都看在眼里,技术人员也会高兴,大家也都觉得认可你这个人,很能干。农场收入好,老板心情好,才会大家都好。
农场中的雇工都没有劳动合同,如果他们不想在农场工作了,完全可以自由离开。但是据农场建立四年以来的情况看,雇工群体几乎没有太大变动。农场也没有出现缺少人手的情况,四年来都能正常运作。这些雇工每个月的工作时间大都在20天以上,更甚者,一个月会工作30天。这么高的出勤率几乎已经与工厂工人类似。在面临家庭生活繁杂事务以及农场生产与村庄生活严重割裂的情况下,这些雇工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一位在农场工作两年的66岁大妈做了这样的解释:
每个月我一般会工作二十七八天,家里老伴(丈夫)在种地,我就可以来农场干活。平时不会请假,实在有要紧事忙不过来的时候才会请个假,尽快把家里面的事儿忙完了又来。农忙的时候很多家里都需要收庄稼,但也不好意思请太长的假,你要是都请假回去了,农场这么多活儿怎么办?我们也不可能全都走了让农场空着吧,这样多不好。一般农忙的时候,如果需要收稻谷或者收玉米,我们(雇工之间)就自己商量着,比如今天你请假回去,明天我请假回去,总不会大家都请假,让管理人员不好办。
爱德华·大卫认为,大多数时候,农业工作的托付是基于信任关系的,为自己利益耕作的农民在这一点上比企业农场拥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10]134-135。而丰业农场的经营运转也恰恰得益于农场雇工基于小农道义所形成的工作伦理。农民社会中常有“人勤地不懒”之类的说法,将劳作能力和土地产出作为评价一个农民的重要标准,且常常与农民社会看重的美德——勤劳、能干、懂得技艺等相联系。虽然这些农民的角色已经从小农转变为农业雇工,耕作的土地也不再是自己的承包田,但他们依然遵从小农的行为标准,将农场工作的行为表现视为自己作为农民的道德品质的体现。村庄中的老人和妇女普遍缺少收入来源,即便是农场中每天40元的微薄收入在他们看来也是来之不易的“恩惠”,因此会努力维护农场的工作运转、完成农场的工作要求,以此作为一种回馈和信义。资本之所以能以低廉的价格和较低的管理成本在村庄组织起如此多的劳动力,正是由于对小农逻辑和道义理性的利用。然而,农民对道义的践行和自我诠释却极大地掩盖了他们向半无产化的商品化劳动力转变的本质,掩盖了农场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夺,也使得他们所遭遇的异化被进一步强化和合理化。
四、结语
以生产效率论,小农农场与大规模农场孰优孰劣一直是个充满争论的话题。小农式精耕细作、充分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劳动集约化生产与大规模农场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粗放式生产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多重价值是唯经济利润至上的资本农场难以企及的。对资本农场中劳动组织和雇工管理的观察分析又让我们得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思考两种农业模式的差异。如孟德拉斯所言,“不必服从雇主”或“不必受人监视”,这是农业劳动者的自豪[14]182。保持生产和生活上的自主性既是小农农业的特征之一,也是小农群体所奋斗追求的目标[15]。从小农农业中为家庭和生存而耕作,转变为在资本农场中为获取工资而耕作,农民在此过程中不仅丧失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被异化为企业生产律条下的附属品。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农场通过类工厂式的劳动管理为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制造了一系列冲突,这包括:农业生产与雇工生活世界的割裂,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与劳动者个体特征的矛盾,田间生产环节的拆分与作物生长连续性的背离,知识宰制与雇工劳动整体性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一方面违背了农业与自然交互协同式生产的规律、破坏了劳动者完整人性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因其对劳动者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制约而降低了农场的劳动生产效率。对于农场雇工而言,他们在土地被流转、生产和生活资料被商品化之后,自身又经历了劳动力商品化的新一轮冲击,成为土地上的“半无产化劳动者”[3]。虽然在土地流转后部分农业雇工还保有名义上的土地承包权,并未完全无产化,但资本农场中的生产实践已使他们如无产工人并无二致,其主体价值不再维系于他们的精神意志,而是转化成可估量计价的物品,丧失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
以村庄为背景、使用当地劳动力的资本农场在管理中借用了乡土社会看重的人情与面子,看似添了几分温情和人情味——缺少收入来源的留守老人对微薄的工资和老板偶尔施舍的废弃蔬菜感激不已,家中偶有琐事也可以向同是村中人的管理员请假,一些老年雇工甚至觉得大家共同劳动的场景排解了他们的孤独感、唤起了他们对集体公社时期的温馨回忆。于是,出于热爱土地、注重人情关系的朴素伦理,农场雇工努力克服着资本农场对他们生产生活造成的割裂与冲突,从生理和心理上加重着劳动过程中的自我剥夺。然而,温情的表象无法掩盖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夺与异化:同是村中人的管理员作为资本农场的代理人与雇工形成了鲜明的等级权力关系,严格控制着雇工的劳动过程;监管之下的雇工很少有时间聊天交谈,少有的交流也只是对工作的交代;雇工的商品化劳动力身份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与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割裂使他们的社会再生产变得更加艰难;进而,雇工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参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村社区发展都受到了严重阻碍。
在现实中,资本农场的劳动组织方式并不囿于本文案例农场的做法。例如,笔者曾经在河南农村看到,一些资本农场为摆脱地方文化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保护,大量从外地“搬运”更廉价的劳动力。由此,与生活世界和乡土文化完全割裂的农场雇工便只能更彻底地服务于资本农场追逐利润的经营目标。尽管资本农场中的劳动组织方式会因地而异,但是,正如巴纳吉提醒我们的,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和控制所呈现的这许多不同的具体形式,只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不同历程,农业资本主义其实质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和控制[16]。借用地方社会人情关系来组织雇工,也只不过是掩盖甚至变相强化了农民从中受到的剥夺。
从历史和当前的发展来看,资本农场的出现要么是以机械化生产排斥农民就业,要么是将农民转化为商品化劳动力和在地农民工。不论以何种方式组织和管理劳动力,资本农场的性质决定了其对农民和村庄剥夺的必然性。在国家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背景下,农民作为无谈判资本、无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必定会经历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严酷冲击。中国农业的未来依凭何种经营模式,经济学的主流话语显然无法对现实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本文的批判与反思意涵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党国英. 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 中国农村科技,2014(9):14
[2]张尊帅.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风险及其防范.现代经济探讨,2013(8):33-37
[3]Zhang, Q.F. and J.A. Donaldson. From Peasants to Farmers: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Labor Regimes, andLand-Rights Institutions in China’s Agrarian Transition.Politics&Society, 2010(4): 458-89
[4]张新光.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新疆大学学报,2008(4):5-9
[5]宁夏. 市场中求生:葛村小农的商品生产.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15
[6]伍开群,欧世平. 资本农场的制度逻辑. 华东经济管理,2013(5):159-163
[7]税尚楠. 农业经营模式的选择:资本农场或合作经营. 农业经济问题,2013(8):32-36
[8]Bernstein H. The Peasantry in Global Capitalism∥L. Panitch, C. Leys.SocialistRegister2001:WorkingClasses,GlobalRealiti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9]祖田修. 农学原论. 张玉林,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何增科,周凡,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1]严瑾. 工商资本投资现代农业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安徽农业科学,2014(4):1211-1212,1214
[12]袁赛男. 家庭农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基于家庭农场与传统小农户、雇工农场的比较.南方农村,2013(4):4-15
[13]贺雪峰. 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 中国乡村发现,2014(3):125-131
[14]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5]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 潘璐,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6]Banaji,J. The Metamorphoses of Agrarian Capitalism.JournalofAgrarianChange, 2002(1):96-119
(责任编辑:陈世栋)
Wage Labor in Capitalist Farm: Exploitation and Alienation——A field study on capitalist farm in Ge Village of Sichuan Province
Pan LuZhou Xue
AbstractSince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caled agriculture, capitalist farms are increasingly prospering as the rising entity in agriculture operation. Based on field study on one capitalist farm in Ge village of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d labor organizing and management in the capitalist farm and highlighted its control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of wage labors. Under the means of labor organizing in the farm, including mandatory labor division, split of production chains, domination of productive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etc, wage labor are alienated to subordinates to production discipline and have lost their autonomy in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Meanwhile, the traditional labor ethics and moralities in peasant society have to some extent covered the exploitation from capital,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alienation for wage labor.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labor process of wage labor in capitalist farm,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reflection on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cale and capital oriented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Capitalist farm; Wage labor; Labor organizing; Relation of Production; Alienation
[收稿日期]2015-10-27
[作者简介]潘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邮编:100083;周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