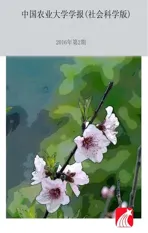论二十世纪前半叶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2016-01-25王宇雄
王宇雄
论二十世纪前半叶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王宇雄
[摘要]毛泽东和梁漱溟均把农民问题作为找寻国家出路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服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考量农民问题,梁漱溟基于中国社会基础的再造考量农民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张的方案取得了成功,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却没有什么成效。他们为解决农民问题而进行的努力,虽然结局不同,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中都内含了革命性和现代性两方面的因素。他们探索的思路和方案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中梁漱溟的探索尽管就确立建国基础而言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但就其解决农民问题本身而言还是有价值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从他们的思路中汲取营养,以求有助于解决农民问题。
[关键词]农民问题;全局问题; 政治问题; 革命性; 现代性
早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就开始了对毛泽东和梁漱溟求解农民问题的比较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对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学界已有成果基本上是围绕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观点,以及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和结果等展开分析,形成的共识主要有:他们二人均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但对农民问题产生的原因认识不同,毛泽东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导致的农民问题,而梁漱溟则认为是在西方侵略之下,“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崩溃导致了农民问题;他们都在找寻农民的出路,但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不同,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问题,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的方式解决农民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同,即毛泽东成功解决了农民问题,而梁漱溟的方案则以失败告束。就针对他们关于农民问题本身异同的比较而言,学界探讨业已颇为深入。笔者的研究汲取了学界的这些共识性成果。但笔者在研读学界已有成果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就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农民问题本身的认知和解决而展开的,对他们二人分析农民问题的前提和思考农民问题的宏观架构重视不够。
由于毛泽东和梁漱溟都不是抱着解决农民问题的目的去关注农民问题的,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进而关注农民问题的,因此,仅仅从他们对农民问题本身的认知和解决出发进行考量,难以对他们的农民问题有更加宏观和深入的把握。诸如农民是如何进入他们视野的,他们是如何在整个中国问题的架构下思考农民问题的,在他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中,近代中国的两大核心问题——革命化和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等,学界已有成果显然探讨不够。为了深化对毛泽东和梁漱溟农民问题的认识,笔者拟立足于在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大变迁中,他们宏观思考中国问题的角度,将20世纪前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作一回顾与比较,从他们本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与农民问题的关联中找寻二者关于农民问题认知的异同,从而突破仅就他们对农民问题本身认知的分析思路,从宏观上深化关于他们农民问题的比较研究。
一、全局问题引出农民问题
均出生于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毛泽东和梁漱溟,成长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各种救国思想相互涤荡的19和20世纪之交。找寻国家民族出路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他们二人作为自觉担当这一历史任务的杰出代表,都是在求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发现需要到农村和农民中去寻找力量,不约而同把着眼点放在农村,聚焦到农民身上,把农民问题作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进而去关注和解决农民问题,并非一开始就本着解决农民问题的旨意去关注和解决农民问题的。
(一)毛泽东: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关注农民问题
毛泽东早在其青少年时代,就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390他以天下为己任,一直在找寻国家民族的出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广泛接触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在对中国问题认知的基础上产生过“改造国民性”“实验新村主义”“建立湖南共和国”等不同的求解中国问题方案。他是在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2]379。自此,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思考中国问题,到工人中去找寻革命的力量。对此,于1936年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曾告诉斯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3]147。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依靠工人阶级,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工人运动上。毛泽东遵照中央局关于必须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指示,全力投身于组织、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4]110他是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组织和参与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以及亲自调查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于1926年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37。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进军长沙途中受挫的情况下,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主动放弃了攻打湖南省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转移到了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在农村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革命力量在山区的保存和发展,使他坚信中国问题必须进行农村革命才能得到解决。如果教条地理解的话,这样的做法显得十分吊诡,即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人所在地相互分离。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毛泽东领导的斗争却要在农村长期开展,而不是去攻打中心城市,这也是他和当时党中央分歧的症结所在。由此,毛泽东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把农村作为革命的基地,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后来于1945年,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表述,“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6]305。
(二)梁漱溟:解决中国问题需从农村找寻出路
梁漱溟和毛泽东一样,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执着于找寻国家民族的出路。他早年曾倾向立宪派,后来转向革命派,一度加入京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相信中国可以通过革命成功,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出现他期冀的局面,而是袁世凯专权,继之以北洋军阀混战,导致中国社会更加混乱无序,“辛亥以来,兵革迭兴,秩序破坏一次,社会纪纲经一度之堕毁,社会经济遭一度之斫丧”[7]524。后来北伐战争的成功,同样没有能够带来安定的局面,相反却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相互混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兴起。其通过革命而建国的心愿一次次落空,由此而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进而找寻其他建国路径。
梁漱溟带着对中国建国问题的困惑,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中国社会原本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问题在于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侵略和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老文化应付不了新环境,在为了应对西方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得不改变自己,但结果却是学西方没有成功,反而把自己原有的文化破坏了。原有文化遭到破坏,而新文化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伦理失范,“伦理本位”社会崩溃。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当为“改造文化,民族自救”,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伦理秩序,而不是进行武装斗争式的革命,“中国革命天然不是一个自下往上翻的革命;如果问题是社会内部自发,则可如此,但中国的革命问题不是内部自发,故不是自下往上翻的革命”[8]228。
既然中国社会的秩序重建问题无法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那又能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认为当走“乡村建设”之路,“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后答案或结论”[9]39。梁漱溟为什么要把眼光投向农村,将做农民工作进行乡村建设当成其求解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呢?他给出的理由和毛泽东颇为相似,“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不做农民运动是糊涂的”[8]104。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破坏从上层到基层,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到他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中国文化的根——乡村已遭到破坏,“中国文化已崩溃到根,已根本动摇;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已经崩溃,中国的老道理已经动摇了”[10]613。修复乡村的伦理秩序,把乡村建设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够造就乡村良好的秩序,形成建国的基础,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本意所在,也是他与其他仅仅因为农村自身的问题而关注农村者的区别所在。他于1929年2月从广州北上考察乡村建设,到达江苏昆山时,曾对黄炎培等人谈到,“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作些应作的事;而我则要以‘中国’这个大问题,在这里讨个究竟解决”[7]884。正是有了梁漱溟关注农民问题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这个前提,将梁漱溟同毛泽东的农民问题相比较才有价值。
毛泽东和梁漱溟两人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和国家出路的看法根本不同,但共同之处为均看重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和农民作为自己从事拯救国家民族事业奋斗的基点。不过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和民族工业的历史性缺席,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其实是一个现实中的虚体,毛泽东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去添补了这个主体位置。参见文献[15]。,梁漱溟则认为农民是道德教化的对象和社会建设的基本力量,这样的前提就注定他们对农民的认知和具体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互不相同。
二、政治问题统领农民问题
认清他们为什么关注于农民问题,就给我们理解他们分析农民问题的理路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做法提供了前提。即毛泽东和梁漱溟都是在求解中国问题的宏观架构下考量农民问题的,就他们解决农民问题各自的关注点来看,各自的方案和做法都是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
(一)毛泽东:服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思考和解决农民问题
如前所述,毛泽东是由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而关注农民问题的,因此,我们对其认识时,就不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孤立地去谈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问题。
毛泽东分析和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求得国家独立问题,中国共产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最大程度地争取到和发动起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主力军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而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要争取到农民,就要给他们以利益,满足农民的土地诉求是给他们以利益的最好方式。
基于这样的考量,毛泽东思考和解决农民问题主要是着眼于土地问题,通过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让农民摆脱封建阶级的压迫,获得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调动起他们的革命热情,吸引他们加入革命队伍中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由于“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11]1075。这样在满足他们土地要求、代表他们利益的基础上,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针对每个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掌握的调查研究资料,分析了农村阶级问题,形成了一条旨在消灭地主阶级满足农民土地诉求的土地革命路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抗日战争结束内战爆发后,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逐步过渡到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通过各个阶段不同的土地革命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者,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建国任务,当然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农民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目的就是发动阶级斗争。各个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心都是要调动起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因此,我们不能以建设的眼光来审视其做法。如出于革命的逻辑,依靠贫雇农当然是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带来了“左”的偏向问题,在整个土地改革中(包括土改与减租减息时期),“反复出现‘宁左勿右’,打击、排斥中农以及平均主义盛行的错误,出现中农怕当中农,‘恐富’、‘怕富’甚至乱打滥杀的现象以及‘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12]39。当然毛泽东也就某些问题做过多次的纠正工作,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经历了从“没收一切土地”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等的一系列转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强调要避免犯“左”的错误等。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进行认知时,要将其置于发动革命的角度来理智对待,否则的话,非但不可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如果按照梁漱溟“伦理本位”社会理路进行理解的话,甚至会陷入认为毛泽东的思路和做法破坏伦理亲情的对革命者进行抽象道德批判的“怪圈”。
(二)梁漱溟:基于中国社会基础的再造思考和解决农民问题
如前所述,在理解梁漱溟的农民问题时,同理解毛泽东的农民问题一样,也只能是基于其政治目的对其进行认知。
梁漱溟分析和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求得国权建立问题,而导致中国问题的原因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失调,伦理本位社会崩溃。通过革命的方式无法解决中国问题,需要通过建设的方式修复和重建中国的伦理秩序。由于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社会,因此,只能通过关注农民问题进行乡村建设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
梁漱溟于1934年8月13日对山东邹平乡学辅导员、乡理事作《村学乡学的由来》讲话时,曾指出,“我来邹平不为别的,就是探求如何改造中国的政治,如何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13]532。他的乡村建设活动目的很明确,解决农民问题是达到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手段。通过乡村建设,要培养起农民新政治习惯的能力,造就适应新政治生活的农民,“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可分两方面去说:一面是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一面是对于团体公共事务的活动力”[13]534。他就是抱着士大夫的“救世思想”和佛家的“普度众生”思想*梁漱溟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延续了中国传统“士”的济世救民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为中国乃至全人类找寻出路。另外,他年轻时曾一度倾心佛学有出家的愿望,后来虽未曾出家,但一直秉持佛家之“普度”思想行事。在其1933年的《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中,曾指出,“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参见文献[13]425。,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培养农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再造业已崩溃的社会结构。
梁漱溟认为农民最缺乏的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通过乡村建设要培养起农民的组织精神,使他们有能力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为了达此目的,首先需要启发农民的自觉意识,“所谓农民自觉,就是说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10]618。只有实现农民自觉,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解决。那么如何引发农民的自觉呢?梁漱溟认为要通过乡村组织的方式。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就是村学乡学,通过村学乡学使知识分子(乡村运动者)和农民联系起来*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上层动力,农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下层动力,只有二者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对农民进行启发和引导,农民问题进而中国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参见文献[13]206-220。,使农村居民觉悟和联系起来,打通乡村故有风俗和外部新知识的联系通道,使乡村充满生机和活力,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有组织的团体。同时,梁漱溟还设计了通过“流通金融、引入科学技术和促进合作组织”,把促兴农业置于整个乡村建设中的一套方案。他期冀通过实施其乡村建设方案,使乡村重建秩序,农民充满向上心,乡村充满生机和活力,农民和农业问题得到解决,乡村得以建设好,进而由农业引发工业和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中国建国的基础赖以奠定。可以说梁漱溟的设想和设计不可谓不周密。
1931—1937年,梁漱溟在军阀韩复渠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实验了他的乡村建设方案,后来由于日本的侵略被迫放弃。其实验确实给当时的邹平农村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14]45,但总体上却很不理想。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遇到了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8]573。事实上,在当时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政权而进行社会改造是不现实的。然而这和其初衷并不相符,“在梁漱溟看来,每一个政府都脱不了破坏乡村的干系,政权本身正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动力”[15]。这样其内在的深刻矛盾便为:正是由于现政权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才需要发动乡村建设运动,可乡村建设又要依附于现政权。至于说到没能使农民自觉和动起来,以此作为确立国权基础的目的就更只能是落空。在当时内外压迫的大社会环境中,梁漱溟这种充满传统士大夫文化情结和关怀情怀,以及佛家普度思想的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的行动,和抓住了农民的根本——土地诉求的毛泽东所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民响应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正如他1938年1月访问延安,谈到农民好静不好动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讲话所说的,“你错了!农民是要动的;他哪里要静?”[16]889也就是说,和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燃烧起了农民阶级斗争的烈火相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连最起码的让农民动起来都未能实现,遑论以此奠定建国基础。
在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术为指导,对农民进行了阶级和阶层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政治动员;梁漱溟以整体主义的观点看待农村居民,以外界知识分子带动抽象的农民群体进行乡村建设。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和共产党的区别,“他们的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功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我们则看乡村社会的内部,虽然不是全没有问题,然而乡村外面问题更严重;——就是整个乡村的破坏,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看乡村是一个整个的”[13]353。梁漱溟认为共产党是破坏乡村的力量,他的做法是在对乡村进行建设性建构。我们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相比梁漱溟的认知,显然毛泽东的分析切中了当时农民和农村的要害。梁漱溟的失败之处正在于他认为和共产党的不同之处,他“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17]。最后的结果为,毛泽东通过革命方式把农民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一并解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式,在解决不了农民问题的同时,政治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三、革命性和现代性相关联
实现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两大目标,革命性和现代性是近代中国变奏曲的双重音符。毛泽东和梁漱溟求解农民问题的过程中都交织着革命性和现代性这两大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基本问题。
(一)毛泽东:革命性中蕴含着现代性
毛泽东通过革命方式求解农民问题的思路和做法,是一个通过革命性的变化,奠定现代化建设基础的构想和过程,但在革命性变化的过程中,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的因子。
从革命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来看,可以用美国学者亨廷顿对革命的界定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理解,“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18]241。革命之后,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异于传统的现代性重建,为国家走向现代化打开了大门。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知时,当然其直接目的是要调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第一位的是革命性。通过发动和领导农民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为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和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奠定基础,也就是说,革命性为现代性提供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除去为农民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创造条之外,本身也体现出了现代性。如前所述,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做法就是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对封建生产和地主剥削基础的否定,是中国农村社会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没有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动摇,就不会有旧的社会结构的根本动摇。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就使中国农村社会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土地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18]273。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求解农民问题的方案,在革命性的同时,已有了现代性的成分,不过更多的是为农民走向现代化创造条件。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考量,具有现代性因子的除去根本土地制度的变革之外,还有就是他关于农民获得土地之后,如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思考。推动农民合作是毛泽东解决农民生产问题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克服小农分散状态生产的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1]931。虽然封建时代的小农生产是分散的,但我国农村自古就有互助性合作的传统,有些无法仅仅依靠家庭内部成员完成生产的传统农民,通过简单的合作克服生产中存在的种种困难,维系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毛泽东发现和提升了这种农民互助性合作组织的价值,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把它作为了农民摆脱分散个体生产,走向集体化生产的起始点,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反映。他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设计中国农民和农业现代化之路的。
(二)梁漱溟:现代性中蕴含着革命性
梁漱溟对农民问题的考量,是一个通过现代性的发展,达到革命性变革的构想和过程,但在现代性发展的设想中,本身就蕴含着革命性的因子。
在当时,梁漱溟认为他所从事的运动就是革命,“我们的运动,在外人看像是枝枝节节的改良运动,而实在不是。他是要完成‘革命’,实在是抱着远大的理想而作根本上改造”[13]947。当然就其做法本身来说毫无疑问是改良而非革命,但其确立国权的目标指向却是革命性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化潮流冲击的产物,他是在中西观照中发现了中国农民身上缺乏组织力和科学技术这两个现代性因子。他想通过乡村建设,培养农民的组织精神,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同时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且由农业引发工业的发展,是在找寻中国农民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旨在通过这种现代化的建设,重建中国社会结构,同时催生出新型的中国式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国权的建立奠定基础。
梁漱溟所强调的乡村建设首先要使农民自觉起来,指向的是人的现代化问题。从个人层次上来说,何谓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的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19]309。梁漱溟提出的通过农民自觉,学习和接受外面新的科学知识,自身组织起来,沟通乡村社会和外界的联系,就是农民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他指向的通过农民改变而使乡村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促成农民和农村现代化这一渐进改良的过程,同时也是引发农民和农村社会革命性变革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发展,将会催生出根本不同于传统农民的新农民,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新社会。不过这样良好的设想,在颠倒了建设和革命关系的前提下,只能是以落空而告终。
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还在找寻一条不同于欧美和日本的中国发展之路。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学西方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路没有走成,逼着我们根据中国为乡村社会的实际,走一条与它们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工业化,将必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是要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13]579。这是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设计。这种设计相对于西方工业化之路为人类唯一的现代化之路的观点,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虽然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无法进入实质性操作层面,但这种按照由农民问题的解决到全局问题的解决,由乡村的建设到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逻辑思路,所设计的中国发展不同于西方的路子,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规划。
他们二人的探索,尽管毛泽东的探索革命性成分占主,梁漱溟的探索现代性占主,但革命性和现代性都是交织着在一起的,目标指向是一致性的,均为建立独立的国权。不过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他们对革命性和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建构明显不同。目标指向一致的两套方案,由于前提预设和路径选择的不同,有了截然不同的实践过程和最终结果。
四、有结果但没有结束
土地改革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毛泽东通过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乃至全局问题的方案取得了成功,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既没有解决农民的现代性问题,更没有为国权的建立奠定基础。即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前者的成功和后者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成功是就农民的解放而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农民的现代化还远远谈不上,即在中国革命发展和农民解放互动中催生了新中国,但如何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仍然是新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前所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设计了一条合作化道路,引导他们走上了集体化之路,此后又进入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样由政府主导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强行变革的方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能够实现富裕农民的良好愿望,没有实现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顺应农民的呼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农民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日益暴露出如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和外部拥有强势主体的市场对接等问题,也就是说,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在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上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但对于农民的致富和现代化问题却是难以解决的。对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20]355。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飞跃”显然不是要回归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实践中进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创新。在新的世纪党中央找到了“第二个飞跃”的破解之法,那就是在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鼓励新型农民合作,通过提倡土地流转形成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等。在大力提倡农民新型合作的今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的个体农户生产的基础上,如何使农民组织和合作起来,在农民组织和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和农民的关系,如何使合作组织真正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如何实现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等,仍然是毛泽东和梁漱溟留给我们的难题。
在推动农民新型合作以及采取其他诸多举措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今天同样应当像毛泽东和梁漱溟那样,从宏观视野上进行考量。应当把农民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中国现代化实现的国家整体战略高度来考虑,而不能只就农民本身来考虑。农民问题只有在中国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不断解决,同时只有农民问题的不断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9]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温锐.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1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4]汪东林.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15]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辨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2):84-97
[1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7]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1-10
[18]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19]埃弗里特·罗吉斯,拉伯尔·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 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常英)
Study on Mao Zedong’s and Liang Shumin’s Awareness on Peasant Issu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ng Yuxiong
AbstractBoth Mao Zedong and Liang Shuming considered peasant issues as the basic problem helping the country finding a way out. Mao Zedong dealt with the peasant issue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while Liang Shuming did it based on the rebuilt of China’s social foundation. In terms of results, Mao wined while Liang’s experiment did not make any substantive progress. Although the end was different, their ideas and practices contained the relevance of both revolutionariness and modernit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lenty rationality involved in their methods and plans. For instance, Liang’s plan is idealized in terms of state foundation establishment, but has its due value in tackling the peasant issues. The author suggests even in nowadays, their ideas are valuable heritage to us in addressing the current farmer issues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Key wordsPeasant issues; Overall picture; Political problem; Revolutionariness; Modernity
[收稿日期]2015-08-27
[作者简介]王宇雄,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邮编:03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