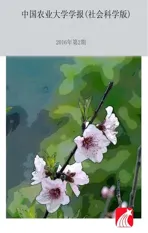小生产的经济学与政治学①
2016-01-25芭芭拉哈里斯怀特
芭芭拉·哈里斯- 怀特
小生产的经济学与政治学①
芭芭拉·哈里斯- 怀特
①本文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6讲的录音整理而来。讲座的英文主题为:“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Petty Production”。录音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汪淳玉副教授整理与翻译,翻译稿由博士生王维整理。
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英国牛津大学区域研究所与沃尔夫森学院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生于194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伦敦海外发展所、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她曾是牛津大学发展研究研究生项目创始人兼主任、伊丽莎白女皇机构(现为国际发展系)主任、当代印度研究研究生项目主任(创立者)以及区域研究所当代南亚研究项目创始人兼主任。其研究兴趣先后从农业市场经济学,转向印度社会规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公司资本;从市场导致的营养不良,逐渐转向贫困、性别偏见与性别关系、健康与残障、穷困与种姓歧视。她对南印度地区的农政变迁颇有研究,并自1972年来一直对该地区一个集镇的经济进行跟踪研究。目前主要致力于对政治生态学和能源消费与利用体制的探究。已经撰写、主编或合编出版了4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代表性作品包括《全球化与不安全感》《印度研究集》《面向21世纪的印度农村》《乡村商业资本:西孟加拉邦的农业市场》《发展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非洲与南亚》等。
“一种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相反,它可能意味着变化的力量与抵抗变化的力量达到了某种平衡。所以,某些看似静止不变、没有发展也没有转型的事物,其实可能包含了矛盾的力量。小生产正是如此,它具有一种内在的能力,能够抵抗多个市场的剥削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印度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小生产(petty production)的政治经济学。我所谓的“小生产”既简单又复杂,通常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意,但又千姿百态。小生产者可能是安装电视卫星天线的小公司、出售手机的店铺或小磨米厂的经营者,也可能是金匠、黄包车夫、清洁工人或种植水稻的农民。小生产的一端是受制于放贷人、貌似独立实为雇工的手工业者,另一端则无比接近于中等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然而,这些小生产者之间实现流动的可能性很小。为了研究印度小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我将采用我的同事加文·威廉姆斯(Gavin Williams)在1976年研究非洲农民的分析框架*参见Williams,Gavin. There is no theory of petit-bourgeois politic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976(6):84-89。。为此,我将首先总结加文关于非洲农民及其政治的观点,然后将他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今天的南亚地区。
一、加文的非洲农民分析框架
(一)非洲的农民及其政治
40年前,非洲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清一色的农民。农业经常被其他经济部门所压制,农民也经常被其他社会阶级所剥削,并被视为从事不发达生产的落后的人,因此几乎所有研究农民的人倾向于将农民视作一个即将烟消云散的阶级。加文·威廉姆斯是少数几个对此持异议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农民自身有其独特的生产逻辑,即他们的薪水和利润混在一起,并不完全融入市场经济,而且可以在境遇变差时随时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生产形式,所以农民虽臣属于国家或其他社会阶级,但他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幸存下来,并且就像蟑螂一样,几乎是杀不死的。加文还指出,小农经济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农民的劳动力可以低价出售,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更为廉价。当然,无论是财富还是雇佣劳动本身,都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二者都能与小农的生产形式相容。此外,加文认为,在小农社会,列宁主义所说的分化将会被诸如外出务工、再分配的义务等反向力量所抵消,农民可以通过辛勤劳作和自我剥削,通过追求生产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来战胜新技术、种植园和合作社。这种农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国家发展的困境和必须消除的障碍,于是20世纪70年代有大量文献指出,要控制农民的独立性,就必须控制交换关系;如果交换只能通过一种渠道进行,且这一渠道却紧紧掌握在国家手中时,农民自主性的丧失便指日可待。
接下来,加文转而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他认为非洲农民的政治十分独特,一方面,农民仍在为那些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制度效力;但另一方面,外部推行的发展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抗。如果非洲的殖民政府或后殖民政府和本地当权者沆瀣一气,例如试图强加沉重的税收和徭役,愚蠢地更改水浇地的用途,或是实行荒诞不经的农业规定时,农民也会运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谓的“弱者的武器”来对抗那些和政府勾结的上层阶级。在加文看来,尽管这些反抗并没有取得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对市场和政府的依赖。最后,加文认为,中国模式或者毛泽东的道路更适合非洲农民的政治。对20世纪70年代那些研究农民政治的西方学者而言,“毛主义”(Maoism)通常被解读为“农业优先政策”(agriculture-first policy),即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政府应着力发展满足消费需求的轻工业,而不是满足生产需求的重工业。加文认为这一政策让农民和现代国家的互动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农民政治,即农民不仅可以反抗,而且从长期来看农民政治还有融入国家政治的可能。
(二)对加文·威廉姆斯观点的评论
加文的观点招致了特里·拜尔斯(Terry Byres)和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等多方学者的批判。首先,加文坚称,“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能够保留下来”,拜尔斯和伯恩斯坦二人将这个观点指责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考察非洲农民更好的方式,是去了解代际再生产与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之间是如何实现连接的。其次,加文认为,“农民对资本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比资本雇佣的劳动力更为低廉”,拜尔斯和伯恩斯坦将其批评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认为我们更应该去考察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过程,并探究农民再生产的条件是如何被资本本身所形塑的。第三,加文将农民放在首位的做法,还被指责为“民粹主义”(populism),反对者认为,长期工业化政策的乘数效应将远远大于短期的农业优先政策的乘数效应,所以农民必须从属于工业,国家必须工业化,哪怕是血淋淋的农业工业化。
二、印度的小生产者
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发展将会偏向资本的一极,整个社会将会分化为资本和劳动力。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发问,发展中国家真的出现了这样极化的阶级吗?这是一场宏大的讨论,我希望自己的演讲能为这场讨论作点贡献。
印度的诸多社会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并不是向着资本的那一极发展,而是转型为小商品生产。西方的学术文献中有十多个不同的名词来描述这种生产形式,如自雇就业(self-employment)、自营企业(own-account enterprise)、小规模生产(small-scale production)、家户或家庭企业(household or family enterprise)、村办企业或小部门(cottage industry or the tiny sector)等,由此说明人们对如何看待这种生产形式尚无定论。我们所要谈论的小生产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家庭的生产,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从事生产或提供服务,它既代表资本,又代表劳动力,因此它是资本和劳动力这一彼此矛盾的阶级立场的结合。在印度,卷入市场流通和市场交换可能并不会形成极化的阶级,而是会形成无数这种形式的资本。
小商品生产在印度的农业和非农经济部门都相当盛行,且千姿百态,无所不及。小生产可能会嵌入其他生产过程之中,成为某一经济部门中的一个序列,例如,大多数的大米种植都是以极小的家庭企业作为生产单位,而大米一旦售出,就会进入中等或较大规模的资本体系中。小生产也可能自成一体,主导着某一个行业,例如,在印度部分地区,水果、蔬菜的生产和流通完全由小生产者掌控。此外,小生产还可能与其他生产形式共生共存,例如,在制衣业中雇佣劳动和小生产并行不悖。
有一次我在伦敦演讲时,亨利·伯恩斯坦曾提出一个反馈意见,“这种小生产形式难道没有地区上的差异吗?”今天,刚好伯恩斯坦也在讲座现场,我将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回应,尽管可能不完全贴切。实践经验表明,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地区自我雇佣的可能性确实有所不同。分布在印度西部的设籍种姓(scheduled castes),主要是由贱民和被剥夺了种姓的人构成,尽管他们往往是人数最少、最不打眼的群体,但却在商业领域中大展拳脚、游刃有余;而大部分生活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迪凡西斯(Adivasis)族人,却在当地的商业领域中表现平平,任凭为数不多的外来的马尔瓦尔人(Marwaris)把持商场。东北部的贸易对外来者来说是自由开放的,所以如果那些在印度大陆西部生活的、处于最底层的贱民能自由进入其市场,那么他们的成功将会指日可待。当然,印度不同社会群体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地理分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的。
小生产是印度最普遍的生产形式,是印度经济的脊梁,但也是阻碍印度全国市场形成的力量。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曾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家。”印度既有巨型的跨国公司,也有庞大的工人阶级,还有工会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但仍有53%~64%的工厂是小生产形式的、自营式的公司,它们甚至在国内市场上扮演着比大公司更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1990年印度改革以来,自由化政策使众多小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小生产形式的厂商翻了一倍。然而,印度大部分企业并没能通过积累而实现扩张,反而经历了微型化(miniaturization)的过程,即小企业通过增殖而变多,而非通过积累而变大。相关数据显示,现今95%以上的企业雇佣工人人数不足5人,平均雇佣工人的人数更从1990年的3人下降到了2005年的2.4人。此外,列宁主义所预期的农业领域的阶级分化也并没有出现任何迹象,印度有多达75%~85%的农民仅靠小规模土地为生,生活难以为继。据2005年国家无组织部门企业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nterprises in the Unorganized Sector,简称为NCEUS)报告,77%的印度人每天收入不超过20卢比,也就是不足人民币2块钱。在这个意义上,小商品生产者往往还是食不果腹的穷人,不仅要对抗生存的文化规范,还需要对抗生存的生物规范。
总之,小商品生产并不简单,所以在讨论中我不想将其本质化,也不想将它归结为同一的生产形式而使其成为一个统一体。它既可能与雇佣劳动相差无几,也可能十分接近中等程度的资本主义,还可以与其他生产形式共存。
三、小生产的经济学
(一)小生产的内在逻辑
接下来,我将运用加文·威廉姆斯关于非洲农民的研究框架来讨论印度的小生产。首先我要考察的是小生产的内在逻辑,学术界与此相关的文献众多,而且观点针锋相对。第一种观点将小生产描述为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即小生产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流逝,其生产组织、规模和消费结构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小生产者并不能独自存活,倘若没有市场交换,他们就不能实现再生产;他们产生的剩余价值也是不确定的,时有时无。亨利·伯恩斯坦还总结了小生产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受到的挤压,比如,小生产者经常遭遇农业投入的价格上涨、农产品的价格不变甚至下降的艰难处境,从而导致他们获得的利润下降。
第二种观点认为,小生产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而只是一种雇佣劳动,一种变相的计薪工作,因为其劳动力在形式上还是被资本所左右,尽管它可能实际上并未完全屈从。这一观点以印度的劳工统计数据、相关劳动法律和劳动经济学作为支撑,是对小生产最常见、最正统的解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简称SOAS)的延斯·莱尔歇(Jens Lerche)根据小生产面临的风险和资产规模对小生产进行了类型划分,他认为小生产的分化将势不可挡,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独立生产,一种戴着面具的雇佣劳动罢了。但若真是如此,小生产就意味着将雇佣劳动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直接用于再生产这种生产形式,只不过没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罢了。
第三种观点认为,小生产不是雇佣劳动,而是习惯于自我剥削的私营小公司。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简称为WFP)就曾在40年前将小生产者称为极为高效的企业家,而非雇佣工人。知名学者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诠释了“农民的生产为何高效”,即资本的逻辑是,当劳动的回报与工资相等时,若再追加任何劳动,将会使其产生的边际利润低于工资所产生的边际成本,于是资本将决定不再追加任何劳动投入;但小生产者的逻辑是追求生产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并不会就此停止工作,而是会工作到边际利润接近于零为止。当然,小生产的高效也可能意味着极度的自我剥削,而事实也正如此。对此,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资源从生产者流向了消费者,而不论消费者是谁,且小生产者的获利远远低于资本控制下的劳工。当然,这一论点也存在诸多争议。
第四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具有矛盾的阶级地位,尽管在小生产的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力并不存在对立。印度政治经济学家普勒姆·尚卡·贾(Prem Shankar Jha)表示,小生产者所获得的利润既不是对其劳动力的回报,也不是对他们自身作为资本家所承担风险的奖赏,而是二者的集合,也因此不会有特别的政治动力促成阶级的分化。所以,不同于延斯·莱尔歇对阶级分化势不可挡的乐观预期,普勒姆·尚卡·贾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动阶级分化。
第五种观点考察了小生产者所承受的多重剥削和压迫,以及这种生产形式下的非经济强制(non-economic coercion)。很显然,雇佣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剥削,但独立的小生产者为何也会处于被剥削的境地?这种剥削可能来自于租金,高利贷,还可能纯粹是因为他是被剥夺了种姓的人,比如,如果他们是被放逐者或不可接触的人,那么买进原材料时就要支付比普通人更高的价格,而在卖出产品时又不得不承受比其他商人更低的价格。据观察,小生产者至少在上述三种非劳动力的市场上受到交换关系的盘剥。
第六种观点认为,小生产是马克思所说的“传统、父族和政治的混合物”(archaic, patriarchal and political admixtures),这一观点可以见于女性主义者和性别研究者所著的大量文献。小生产是一种古老的交换和社会组织形式,很多人曾自信地认为它们必然会因现代性而消失,人们还普遍预言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起过重要作用的种姓、性别、宗教等因素必然会随现代性而烟消云散,例如,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人都对市场扩张的趋势抱有坚定而乐观的信念。但最终结果却并未如其所愿,因为这种混合物改头换面之后,迎合了资本的利益。所以,小生产者不仅仅是经济行动者,还是社会行动者,社会关系将影响到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机会、能做什么生意、能做多大生意、能在哪里做生意以及是否能够获得贷款等和生意有关的一切。
(二)小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其外部关系
这种生产形式貌似简单实则不然,它是如何生存下来并实现再生产的?在印度,为什么它会像蟑螂一样,生命顽强且无处不在?为了解释它的普遍性,我们需要考察小生产者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及其外部关系。尽管小生产者被收编进了资本的全部商品关系之中,但如果时势艰难,他们便可以全身而退,转而从事养家糊口的生计活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只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残留物呢?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瓦特(Elmar Altvater)就将非正式经济和不在政府调控范围内的家庭企业都视为后备军,认为它们是剩下的部分,起着规训雇佣劳工的作用。但实际上,小生产的经济形式要求的是较低的绝对收益和普遍不高的消费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利于增加其他经济部门的利润。
有些文献考察了小生产为什么不能实现积累。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本身是前资本主义的残留物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从而限制了其实现积累的可能性。我认为这一论断将小生产形式看作小农生产方式的表现,忽视了资本主义收编的多重逻辑,实际上这些小生产是为资本主义所收编,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衍生或残留。此外,生活中还存在继承、借贷、学徒制等多元的机制不断在为小生产提供启动资金。因此,“小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因为它在家庭层面上是简单再生产,但在社会层面上却创造出了足够的剩余,使其得以通过增殖而不是积累的方式实现再生产。
还有一些文献考察的是农业为什么不能实现积累。对此,西方产生了两大类文献和理论。第一类文献从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出发,认为互锁的合同让处于臣属地位的一方所能得到的利润远远不如他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水平,印度的“分成租合约”(sharecropping contract)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就死协议”(modeled to death)。为了理解和解释分成租合约的参与方为什么不能实现积累,学术界大概发明了15种不同的理论,但目前只有三种能被实践加以佐证,而其余的只是理论构想而已。“分成租合约”在经济学的语境下关注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要素,但在印度的农村还常常涉及到水、机器、种子、化肥、运输,甚至还有维修和保养等复杂的内容,甚至可能存在四方合同或五方合同。毫无疑问,这些合同最终导致农民处于臣属地位,而无法实现积累。此外,小生产者还处于一个不对等的支付体系中,他们在购买货物时需要马上付钱,而卖出后却要等两三个月才能拿到货款,从而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甚至不得不举借外债,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阻碍了其积累的进程。
第二类文献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制约农业实现积累的因素。这一类文献并没有过于关注合同,而是重点考察了小生产从属于其他社会阶级(尤其是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模式。有学者指出,印度农民在压迫性的商业化浪潮中别无选择,在最急迫的时候,他们经常被迫卖掉生产资料、甚至卖掉农场还贷;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们不得不又再次借款,高价购粮以度过难关,这种压迫性的交换关系让农民一再举债,难有盈余,阻碍了他们实现积累的进程。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制度可能是小生产者积累的障碍。以性别关系为例,印度妇女是经济发展的积极参与者,但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资产,因此不能获得任何抵押贷款。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所考察的那些印度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夺了种姓的群体与妇女的处境如出一辙。
最后,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小生产者内在的能力。一种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相反,它可能意味着变化的力量与抵抗变化的力量达到了某种平衡。所以,某些看似静止不变、没有发展也没有转型的事物,其实可能包含了矛盾的力量。小生产正是如此,它具有一种内在的能力,能够抵抗多个市场的剥削关系,例如,小企业之间的无息借贷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一种抵制剥削的能力。
(三)关于小商品生产的项目
关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学,我们还需要加以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是否有针对小生产的发展项目?印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对此持否定态度,一方面,过去20年来印度正式部门有记录的工作数量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就业的增长”(jobless growth);另一方面,经济之外的强制力量在印度无所不在,如社会制度的压力、赤裸裸的暴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等因素挤压了小生产生存的空间。安让·查克拉巴蒂(Anjan Chakrabarti)、阿吉特·乔杜里(Ajit Chaudhury)和斯蒂芬·卡伦伯格(Stephen Cullenberg)2009年发表在《剑桥经济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参见Chakrabarti,Anjan, AjitChaudhury and StephenCullenberg. Global order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India: the (post)colonial formation of the small-scale secto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6): 1169-1186。中也同样认为印度没有针对小生产者的项目,但他们分析的角度有别于帕特奈克。在他们看来,小生产者这一群体被学者、规划师、经济精英还有政治精英视而不见,仿佛不存在一样,从而成了“不可见的他者”,也因此没有出现为其服务的项目。然而,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和卡利安·桑亚尔(Kalyan Sanyal)认为存在类似的项目,他们将印度整个非企业部门视作以非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需求经济(needs economy),认为这些小生产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政府在剥夺式积累(如攫取土地和资源)的过程中,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其给予了政治性的补偿。
还有观点认为,项目是存在的,只不过其目标是异化小生产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关注食物流通体系,使得农业资本、农业企业以全新的规模入侵乡村经济,并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助长下扫荡了整个营销体系,从而使其触角延展到了零售业的终端。当庞大的资本占领市场、种植园农业不断扩张、街头兜售被不断取缔和摧毁时,印度的小生产遭遇了大规模的打击。根据经济普查,1990年,印度71%的企业是自营企业,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65%。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一场对小生产者的大规模围剿,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印度的发展项目不胜枚举,但却是对小生产发起进攻的战役。两天前,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看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图绘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如何抵制特易购(Tesco)和沃尔玛,这种抵制的言论在印度也相当盛行。
那么,印度到底有没有针对小规模生产的发展项目呢?我们不妨先列举一下印度开展过的多种名义的项目,例如,印度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设立了国家无组织部门企业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针对无组织部门的项目。该委员会为获得技术和资金而四处奔走,尝试整合各部门的需求,并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力量,试图推动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印度最近的五年规划中还有一些包容性发展的项目,但它想要包容的是穆斯林、设籍种姓等被发展遗漏的少数民族,是一种社会项目,而不是真正的经济项目,最终只招来了一片指责之声。以上政府以各种名义开展的项目往往都是杂乱无章、偶然和不连续的,因此我认为印度并没有针对小生产的项目。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甚至是摧毁小生产的项目,比如建立超市、美化城市、驱逐街头商贩等行动直接破坏了小生产的场所;政府在建立经济特区的过程中,通过管理磋商或是流血冲突直接摧毁了农业小生产者。还有一些原本为了保护和促进小生产的发展干预项目或合作社最终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例如小额信贷项目因腐败等现象的存在最终沦落为少数人追逐利润的工具。此外,有一些项目容忍了小生产的存在,但也只不过是既没有支持,亦没有反对而已,如印度绝大多数城镇都设有当地政府管理的市场,允许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穷人自由地做些买卖。
最后,小生产还因为法律条文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得以延续。例如,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规定了最低工资,其数额一般高于自由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这意味着,在最低工资的基准线之下,小生产者将不会面临来自雇佣工人的竞争。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或许印度真的像帕沙·查特吉和苏迪普塔·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多年前所总结的那样,经历过一场被动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我认为这场革命创造出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没有什么发展项目在为其服务。
四、小生产的政治学
接下来我将探讨的是小生产的政治学,即印度的小生产者参与政治的方式。第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是资本,而不是雇佣劳动力。然而,关于行会或协会以及农民运动的相关研究表明,小生产者确实被纳入了资本的阵营,但他们很快就被忽视了,“欢迎加入我们协会!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投票,可以和我们一起抗议。但对不起,我们不会顾及你的利益。”例如,对小生产者十分紧要,又让他们万分头疼的原料价格问题,就一直被印度这些组织视而不见。
第二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是雇佣劳动力。印度受过教育的人士认为,以雇佣劳动力的身份争取正当权利是小生产者表达政治意愿的主要形式,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尖锐的矛盾。例如,在印度的劳工统计数据和相关劳动法律中,不仅雇佣工人、小生产者被当作雇佣劳动力,而且雇工人数在5人以下的企业主和工厂主也被囊括在内。于是,在法律框架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被划归为一类,而这对小生产者来说,意味着他们被直接剥夺了公民权。因为印度的小生产者如果要以工人的身份立案,就必须指出谁是他的雇主,但很显然,相关的法律规定使得小生产者找不到雇主,除非他们有一个类似于雇主的、主要为他们提供资金的放贷人,方能就工作条件向法庭提起诉讼。如果我们从微观层面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伪装的雇佣工人被剥夺公民权的现象相当严重。此外,在小生产者被纳入工会,而不是自我雇佣联盟的地方,印度政府的政治倾向是反对任何针对生产条件的政治煽动,而现实也是如此,小生产者通常只会为了生产条件之外的权利与印度政府抗争。在大部分情况下,印度工人组织起来仅仅是为了食物、教育、社会保障权利等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但却放弃了为改善其工作条件而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可能性。
当然,小生产者会有一些自己的组织,如引人注目的自雇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简称SEWA)。它是印度目前唯一一个跨越了80个行业、成功组织了100万名自我雇佣的妇女的组织,其四重目标是工作安全、收入安全、粮食安全和社会保障,但它和工会一样,只和政府而不是雇主谈判。这个组织相当独特,既是工会又是银行,提供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它是一个合作社,可以提供培训;它是掮客,可以提供住所和商业便利;它有一个研发部门,一个生态旅游公司和卫生服务站;它还能提供照料儿童和法律方面的服务;在组织外部,它还与多个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组织保持联系。当然,这个组织之所以如此强大,还得益于国际网络的支持和捐助。而要获取海外资金的支持,又反过来要求它变得十分庞大,所以要复制它的模式极为困难。
毛主义者的运动是印度小生产者表达自身意愿的另一种政治途径。印度28个邦中有20个受到了毛主义的影响,但国内却几乎没有毛主义的经济项目。印度的毛主义将农业诊断为半封建主义,但若真是如此,那么毛主义者就卷入了一场消耗战,一场包围城镇的战争,而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阶级阵线;相反,如果将农业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统一的阶级阵线是有可能建立的,并将带来革命性的后果。所以我认为将印度农业诊断为半封建主义这一观点有误导性,是毛主义的一个重要咒语。
五、总结
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农民,南亚的小生产没有其独特的政治,不存在其必须采用的、独特的单一生产逻辑或交换关系,也从未形成过政党;小生产者不会竭其一生的商业生涯去实现更先进的积累方式,但他们的足迹遍布各个行业,还以转包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印度技术发达的部门里。我认为,小生产注定要继续,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小生产正处于向产业工人过渡的时期。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现代企业,哪怕它看上去并不像,这也正是我们要接受“小生产也是现代的”这一观点的为难之处。
正如中国的农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劳动力,使每年大约2 000万人离开土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一样,印度也有着大量受教育程度低下、自我雇佣的劳动力,这似乎意味着印度同样具备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但考虑到印度存在“无就业的增长”的现实,如果印度真像中国一样从农村释放出大量劳动力,那他们又将如何被城市部门所吸收呢?如何才能拆除那些制约资本积累的障碍呢?我认为,印度的设计师和规划者们应该对此做认真的思考。只要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只要小生产一直是印度经济的核心,印度就会一直只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不会崛起为像中国那样的大国。
问:印度存在一个强大的、处于上升态势的资产阶级,他们并不想与小生产者为伍,所以小生产者似乎是被剩下的一个群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想要的群体,而这或许就是小生产没能被主流经济形式收编或吸纳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从您的经验研究来看,印度的这些小生产者是否可能转型为真正的资本家?
答:小生产者并不是被“剩下”的阶级,而是社会经济中的大多数,只是像我们这样的学者把他们视为“剩下的”而已。我呼吁大家重新考察“小生产”这一概念,因为众多统计数据表明,它是印度最为常见的生产形式。所以,事实是印度的富人没有被吸纳,因为小生产者才是主流。其实,问题不在于如何成为主流,这些在传统上被命名、在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从来都是主流,只是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发展项目来看,他们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已。你提到小生产者是资产阶级不需要的群体,这点我在演讲中并未涉及。但如果你像韦伯那样根据消费和生活方式来定义“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他们无疑是需要小生产者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后,我们在考察印度南部的城市贫民窟时发现,中产阶级无时无刻不被小生产者包围,他们需要小生产者为其种植蔬菜、花卉,提供洗衣熨衣、贩卖小吃、补鞋等多种多样的服务,而这些需求则为低收入的小生产者带来了重要的乘数效应,所以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尽管如此,小生产者往往无法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而只能在数量上实现增殖,对此,我们必须将它视为一个发展问题认真对待。
你还问及印度的小生产如何向资本主义道路过渡的问题。其实印度的小生产早已被完全整合进资本的循环和流动过程中了。印度有些左翼人士认为,我所描绘的小生产者其实都是劳动者,保护并巩固劳工的权利才是印度政治的关键议题,但实际上印度只有3%的工人加入了有组织的联盟,这意味着劳工的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更不用说将小生产者面临的问题放到劳工运动中去解决了。如果要试图回答小生产者如何能够摆脱束缚并实现积累,我的答案是,小生产者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狭窄而稀少。尽管媒体上曾对那些出身于贫民窟的印度富豪大肆宣传,但那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的几个例外罢了。小生产者的转型需要技术、基础设施和信贷,这说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但这些东西早在50年前就被加以言说,而至今仍未带来任何改变。所以,到底要如何消除对这种生产形式的束缚,让小生产者能够实现积累和扩张而不是单纯地繁衍其数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问:您认为小生产者有能力应对很多限制条件,但这是一种能力,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却不能摆脱困境呢?
答:零利率的借贷以及在面临压力时家庭之间的各种互助和交换,是小生产者用以应对各种限制条件的策略,这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别无选择、绝处逢生。事实上,这种问题从没有被拷问,因为它并没有被重视,所以非常感谢你提出了这个很有趣的问题,而我本人对此并没有答案,而且我认为不止我一个人没有答案,因为学术界目前对小生产者的抵抗的研究接近于一片空白。最近,在印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发生了小型信贷公司之间的竞争悲剧,导致了多重无法偿还的债务,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自杀事件。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悲剧还与政府未能及时拯救这些家庭有关(小生产者在劳工运动中向政府请愿获得帮助,是一直以来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办法),导致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应对这场严重的危机。
问:小农逻辑通常与“小农能够生产供自己消费的粮食”这一事实有关,并且它还可以拓展为农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农耕生态学等更为重要的概念。我的问题是,小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一般小商品生产的逻辑,成为非农业的小生产者?
答:非农业经济,顾名思义,并非是以生存为目的。非农的生产者(可能除了回收处理废品等类似的小生产者之外),往往和大自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因此和农业的长期性、风险性、低回报等特征并无关联。那么,小农生产的特殊逻辑是否能够被带到非农业经济中呢?综合以前的文献来看,我认为,除了“追求生产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这一逻辑或许可以适用于非农业经济之外,其他逻辑似乎不太可能。
问:你在讲座快结束时所得出的结论让我陷入沉思,你是否是说如果印度大部分小商品生产者所受到的限制得以解除,那么印度在经济意义上就能成为一个强国?如果小生产者进行积累的限制被解除了,我们是否就能看到阶级分化的过程?
答:关于印度是否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或许需要在国际关系方面具备相当能力的人才能够回答。目前印度绝大多数人口还挣扎在温饱线上,所以印度的强大只不过是一个扭曲了的形象罢了。如果小生产扩张的种种限制条件被解除了,那么阶级分化就将是必然的。实际上,印度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然而,尽管不同形式的资本对印度持续地渗透,大规模私人部门也不断发育壮大,但印度的经济主要还是靠这种小生产形式而得以支撑。这意味着印度的左翼和右翼人士都需要缜密地思考,到底什么是阻碍了小生产进行分化的始作俑者。
问:小生产者没有形成任何政党,这是不是因为小生产类别太多或层级太多,使他们很难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据我所知,印度没有小生产者的政党,小生产者的政治被整合进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之中,比如小生产者作为资本涉足了商会和农民运动,作为劳动力加入了工会及其组织的斗争,或者自身形成了类似于自雇妇女协会的组织,甚至可能卷入了毛主义者的联盟。小生产者没有被整合进政党政治,是否是因为他们缺乏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我无法做出判断,但即便是在同一政党内部,针对同一议题也可能存在完全迥异的立场,例如,1980年,我在实地研究过程中访谈了某些政党的政治家,发现其党派内部就某些特定问题的立场的差异,甚至超过了不同政党之间的分歧。
问:小商品生产者能在跨国资本最先进的部门里扎根(如IT行业),成为发达资本内在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答:你的问题让大家注意到小生产者在全球供应链和IT行业的整合问题,我无法确切地知悉小生产在发达资本内所占的比例,但我立刻联想到不少以全球供应链为焦点的、涉及制衣业和金属制品的研究。这些研究指出,全球供应链要么被生产商控制,要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被需求的推动力所形塑,最终演变为以买方为动力,而非以卖方为中心。然而,我的博士生奥尔兰达·鲁思文(Orlanda Ruthven)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尽管供应链中的分包商和私人厂商已经完全被整合进了全球体系的生产过程,但他们仍将自己视为独立的生产者,而非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而工作的劳动力,并高度认同其自主性及自我存在的价值。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作为自主的生产者被整合到全球商品市场的供应链中,还有些生产者就只是薪金工人。此外,我们还应该考察性别和种姓如何制约了生产领域,如何让有些人获得了机遇,却让另一些人无门可入,这些中国听众很难想象和切身体会的“软制度”(soft institutions)正在成为印度巨大经济机遇面前冷酷无情的调节器。我曾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这个问题有所贡献,但一直未能如愿。
问:微观层面的性别关系会对小生产者造成何种影响?
答:我不确定能否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举例说明。小额信贷项目极大地赋予妇女以权力,但在某些地方小额信贷机构可能已经越界了,它们发现利润的诱惑无法抗拒,因此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它们开始将钱借给还不起的人,让那些负债而不清楚自己无力偿还的女性面临灾难,使得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深陷危机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女性被赋权了,但没有证据表明她们能够因此实现积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就此能够摆脱那些阻碍积累的交换关系,进而以小生产者的身份、以新的方式整合进既有的经济体系中。
问:小生产者往往是贱民或被剥夺了种姓的人,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在印度的种姓制度背景下来考察这个人群。我的问题是,小生产者如何在种姓制度的约束下实现向上流动呢?
答: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地位体系,对职业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限制。正如尼赫鲁、缪尔达尔等人所预言的那样,职业的种姓分层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了,但这种模糊化仅仅发生在边缘,而在经济的核心部分,种姓的分野仍然明晰可见。举个例子,在一个我研究了40年的小镇上,70%的磨坊主属于一个种姓,剩下的30%属于另一个种姓,但这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总体而言,职业的种姓分层仍然普遍存在于印度的绝大多数经济领域中,即便是在那些已经现代化了的、或正在现代化的部门也同样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分层复杂且明显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机会极少。尽管有些企业家一开始出身平凡,却最终富可敌国,例如阿兹姆·普雷姆吉(Azim Premji)最初以卖油起家,后来成为印度的IT大王,但这些飞黄腾达的案例恰恰只是极少数例外而已。通常的情况是,有些人可能最初没有什么产业,奋斗许久后终于拥有了一家店面或某个家族生意,但最终不得不将这笔资产分给他的儿子们,于是又沦落到之前那样捉襟见肘的境地。因此,小生产要实现向规模较大、有着相当数量雇佣工人(超过5人)的公司的过渡,在印度仍然举步维艰,处处受限。
(责任编辑:陈世栋)
主持人:非常感谢芭芭拉教授的演讲。她挑战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宏大理论,质疑了关于社会变迁和农民命运的宏大叙事,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对那些天真地想去寻找一些社会问题的线性解决方案,或是解释某些社会现象的宏大理论的人而言,芭芭拉的演讲可能让其大失所望了。因为她的演讲说明,我们难以找到某一种宏大的理论或解释。社会是真实的存在,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行动者的权力作用下总是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如印度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项目,对小生产或打压,或保护,或容忍。社会应当给不同的行动者以行使权力的空间——这是我从这次演讲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编者按:自2011年秋季学期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组织“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延请当代国内外著名学者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农政变迁”、“发展转型”两大主题阐发其卓越的研究与思考。这一系列讲座包容社会科学研究的多个学科、多种分析视角、多类主题,对于全面认识与理解乡土社会的历史传统、现实处境与未来前景,富有启迪。本刊将陆续刊登这一系列讲座的录音整理稿,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