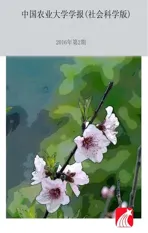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
——以陕南王村为例
2016-01-25李博左停
李 博 左 停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
——以陕南王村为例
李博左停
[摘要]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关键词]精准扶贫; 移民搬迁; 政策偏差; 扶贫治理
精准扶贫作为2014年中国扶贫系统提出的新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目标,具体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1]。精准扶贫的提出为当下中国的扶贫开发指明了新的道路。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扶贫移民搬迁近年来在中国部分省份逐步推广,并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效果。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以来,中国的扶贫移民政策经历了从针对个别问题、个别区域到在国家层面加以整体设计与全面推进的演变过程,其目标日益多元化[2]。扶贫移民是基于减贫而进行的贫困人口从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向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迁移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3]。中国最早的扶贫移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甘肃定西、河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被通称为“三西”移民。近年来扶贫移民已经拓展到了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陕西等省份。2011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异地扶贫搬迁作为专项扶贫的重要举措,提出“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扶贫对象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引导其他移民搬迁项目优先在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实施,加强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衔接,共同促进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4]。这一纲要的提出更加明确了今后扶贫移民搬迁的宗旨,为扶贫开发的实施奠定了相应的基础。但是从当前扶贫移民的效果来看,政策实施层面出现的偏差已成为困扰精准扶贫的最大障碍,主要表现为移民搬迁过程中精准识别的错位,扶贫治理的缺失,国家、地方、贫困户因各自利益差异而形成的制度性逻辑困境等。这些政策的偏差导致部分地区的扶贫开发逐步走向内卷化①扶贫的内卷化是指单位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同比例的减贫与脱贫效果,而使扶贫所惠及的目标群体偏离,目标范围减小。,甚至陷入了越扶越贫的怪圈。
目前,学术界针对扶贫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移民的政策演变、实施效果以及移民的权益保障、安置模式等方面。白南生和卢迈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移民的方法和经验进行了介绍,就移民开发政策的经济效果、扶贫效果、社会效果与生态效果进行了评估,并对扶贫移民规划与管理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5]。施国庆结合甘宁“三西”扶贫移民,粤北扶贫移民,广西及云南扶贫移民的实践,对扶贫移民的内涵、种类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指出扶贫移民应该从法律体系建设,资金管理,移民决策制定,移民群众工作,移民开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来推进[6]。郑瑞强从扶贫移民的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层面对移民实施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切实保障移民所享有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发展权益与和谐权益才能提高移民脱贫致富能力,其中政府对于扶贫移民保障负有服务提供、利益协调、整合资源与后续扶持等方面的责任[7]。从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是从扶贫移民的经验、思路、方法等方面来探讨扶贫移民的地方适应性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很多研究缺乏一定的调研分析与案例支撑,说服力较弱,从研究视角来看缺乏从精准扶贫层面来考虑扶贫移民的实施效果。为了使研究有更进一步的提升,本文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来透视扶贫移民搬迁的实践逻辑,并且从微观层面出发,选择陕西南部秦巴山区的一个扶贫移民开发村为研究对象,通过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来映射精准扶贫中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以及困扰精准扶贫的障碍。
一、王村扶贫移民搬迁的过程分析
王村*依照学术惯例,文章中的王村、张村均为化名。位于陕西省南部秦岭腹地的H县,距离县城21公里,现有10个村民小组,共380户,人口1 361人,村内山大沟深,属于典型的山地地貌类型,村民主要经济收入以传统农作物种植为主。另外,村内地势险要,生态脆弱,山洪、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为了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陕西省于2011年做出决定,在陕南28个县计划用10年时间实施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作。笔者所在团队分别于2014年8月,2015年4月至8月分四次在王村开展了为期60天的住村调研,主要就王村所实施的扶贫移民工程对村民进行了深入访谈。通过调研笔者发现,王村所实施的扶贫移民搬迁并没有带来地方政府所预期的效果,从政策执行过程、获益群体以及实施成效来看没有达到精准扶贫所期望的效果。为了对王村扶贫移民搬迁中政策执行偏差进行分析,笔者分别从搬迁前的搬迁户确认,搬迁中的政策执行逻辑,搬迁后的项目验收与生计选择四个方面对王村的扶贫搬迁过程进行了分析,从而探究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
(一)第一阶段:搬迁户的识别与动员
王村自2011年实行扶贫移民搬迁以来,截至到2015年6月共计185户完成了向移民搬迁点的搬迁。在搬迁安置中政府分批次对搬迁户进行补贴,其中最高补贴标准为每户3万元,搬迁户必须为村里确认的贫困户,那么对于贫困户的识别就是关乎能否实现搬迁的决定性因素。在贫困户的识别工作中,村委会成立了贫困户识别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为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村主任、副主任、村监委会主任、妇女主任6名成员。贫困户评选标准为农户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 666元,并且附带家里有土胚房,或者供养孩子上大学,以及村里的五保户、低保户、受灾户等。按照这个标准王村在2011年确立了220户贫困户,但在2011年第一批扶贫移民搬迁中只有20户进行了搬迁,这20户从地质条件差、交通、通讯闭塞的高山搬到了王村村委会所在地的移民搬迁点。令人困惑的是20户当中只有3户属于真正的贫困户,其它17户均为非贫困户,那么这17户非贫困户为什么也能实现搬迁呢?
通过访谈笔者得知,为了完成镇政府的搬迁任务,6名村干部挨家挨户去做贫困户的工作,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动员,很多贫困户表示同意搬迁,但是难以承担搬迁的费用。按照搬迁的成本计算,除国家补贴的3万元之外,每个农户还要负担17~18万元的搬迁费用,这笔费用对于贫困户来说根本无法承担。面对这种情况,村委会干部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只好动员村里经济状况较好,具有搬迁能力与搬迁意愿的非贫困户搬迁,最终确定了17户。另外确定搬迁的3户贫困户都是为了便于孩子在搬迁点附近的王村小学就近上学才做出了搬迁决定,其搬迁费用主要来自于亲戚朋友的赞助。到此,搬迁第一阶段搬迁户的识别和动员匆匆收场。
在第一阶段搬迁户也即贫困户的识别过程中,J镇镇政府、村干部与搬迁户三者陷入了复杂的涡旋之中,J镇镇政府为了完成上面的搬迁指标而不断向村干部施压,而村干部以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去动员贫困户搬迁,但是贫困户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放弃搬迁,致使搬迁指标流向了村里的非贫困户,所以在这一阶段搬迁户的精准识别上,完全背离了精准扶贫的宗旨,扶贫移民搬迁政策的实施偏离了所要达到的目标,扶贫的优惠政策没有惠及绝大多数的贫困户。
(二)第二阶段:搬迁中羸弱的地方财政
在移民搬迁房屋建设过程中,村里向确定的20户移民搬迁户每户征收了4 000元的管理费,令这20户搬迁户困惑的是,在搬迁之前村干部并没有说征收管理费,所以村民的意见都非常大。通过对村干部的访谈笔者得知,移民搬迁过程中收取的管理费主要是用于房屋建设过程中的协调费用,例如镇土管所人员的招待费用,村干部为张罗移民搬迁而花费的交通费、通讯费等开支,还有最后移民工程验收时的零碎开支。同样令村民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笔开支也要从搬迁的补贴里面扣取,村干部的回答是“上面只动员让搬迁,但搬迁过程中的一系列开支村委会根本无力承担,再加之村集体无收入,所以这笔钱只能由搬迁户来承担。”通过对J镇一名主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也即王村的包村干部访谈,笔者得知,王村所属的H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每年只有2亿多元,大部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而且H县贫困面较广,贫困人口较多,薄弱的地方财政难以承担所有移民搬迁的配套资金。
在第二阶段的搬迁过程中,虽然国家给予了贫困户一定的搬迁补贴,但是却忽略了搬迁过程的复杂性,王村所属的H县地方财政收入微薄,加之王村又无可观的村集体收入,羸弱的基层财政供血能力根本无法承担起搬迁过程中相关配套资金与运行成本的支出,所以倒逼村委会只能从搬迁户的补贴里面来支取这笔费用,对于搬迁户当中的17户非贫困户来说这笔费用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另外3户贫困户来说,无疑使得本来经济能力就较弱的贫困户雪上加霜,抬高了这些搬迁户的搬迁成本。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地方财政的供血功能的不足以及村级组织经济能力的欠缺更进一步加大了扶贫开发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羸弱的地方财政补贴能力无形中诱逼基层组织从国家财政中汲取营养,而汲取的这部分最终仍由搬迁户来承担。
(三)第三阶段:搬迁后工程验收中的治理缺失
在移民搬迁工程完毕之后,县扶贫办组织相关人员对移民搬迁工程进行了验收,在验收过程中,扶贫办认为王村搬迁点的新居布局散乱,规划参差不齐,有些出现伪造乱改的现象,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所以整个搬迁工程验收迟迟不得通过,影响了搬迁户的顺利搬迁。而据王村的村支书介绍,在移民工程建设过程中搬迁点的选址以及搬迁户的房屋构造、设计一直是由J镇的土管所负责实施,而工程完毕之后又由扶贫来组织验收,扶贫办表示不符合他们的设计思路,所以迟迟不能通过验收。最后,为了通过验收,村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人情关系来疏通扶贫办。最终扶贫办迫于上级政府大力推进扶贫移民搬迁的行动以及村民的压力最终通过了王村的扶贫移民工程验收,王村第一批20户搬迁户终于搬进了新的住所。
从第三阶段可以看出,在王村的移民搬迁过程中,房屋的规划与设计由J镇的土管所来实施,而搬迁之后的各项验收又由县扶贫办来完成,扶贫办主要从上级对于移民搬迁点的具体要求出发来进行新居的验收,而J镇土管所主要是从王村的地质、地形构造以及避灾等方面来考虑新居的规划,所以导致在搬迁完成之后项目验收上的问题。在此过程中,J镇土管所与县扶贫办在整个王村扶贫移民搬迁中基本处于脱嵌状态,缺乏有效的互动与交流,导致整个扶贫治理的细碎化与条块化,影响了扶贫开发的进程。
(四)第四阶段:搬迁后的可持续生计
经过2011—2013年三年的扶贫移民搬迁之后,截至2015年6月王村380户中完成移民搬迁的已有185户,这185户当中有135户集中在村里的移民搬迁安置点,50户移居到了镇政府所在地的张村移民搬迁点。因为张村位于J镇镇政府所在地,交通方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齐全,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为周边很多偏远山区村民首选的移民搬迁点。但是,搬到张村的村民耕地与户口仍然保留在王村,只是农闲时期到张村的新居去居住,现在张村很多房屋都属于无人居住的空房,有的房子虽然建设起来了,但是很多都是家徒四壁。村民表示,住在张村虽然交通、孩子上学方便,但是开支太大,再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之还要种地,部分村民反映,搬到张村以来开支翻了几番,所以很多村民还是选择大部分时间住在王村。
搬迁后,由于户籍、耕地、就业等后续配套工作的不完善限制了搬迁后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许多搬迁点的房屋成为摆设,而且很多房屋成为地方政府助推小城镇建设与城镇化的面子工程。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诸如张村这样的空村。所以从整个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来看,移民搬迁并未从根本上对农民的生计给予扶持,反而很多农民由于种地来回奔波于搬迁点与原住所,提高了生活的成本。另外从移民搬迁的实际效果来看,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带来农民生计的同步改善,搬迁后农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二、精准扶贫中扶贫移民搬迁的逻辑困境
(一)“背皮”搬迁:压力型体制下的精准识别
“背皮”搬迁是指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与基层利益不合理的诉求下而发生的一种典型的政策执行偏差现象,所谓的“背皮”就是冒名顶替的意思[8]。作为精准扶贫的基础性工作,精准识别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和人口识别出来,同时找准导致这些家庭或人口贫困的关键性因素[9]。在王村的移民搬迁中J镇镇政府为了顺利完成上级所下达的搬迁指标,迫于压力而安排村干部来动员村民搬迁,而村干部迫于镇政府的压力,为了完成指标动员了一批非贫困户来进行搬迁。识别瞄准的偏差一方面是由于J镇为省级示范镇,上级要求J镇必须在扶贫移民搬迁中发挥带头作用,所以镇政府为了能够保证自己的政绩把压力全转移到了王村。在压力型体制下,计划指标不仅仅存在信息不全、理性不及的问题,而且由于掺入了领导干部谋求政绩的机会主义因素而更具危害性[10]。另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搬迁的补贴太少,贫困户没有经济条件进行搬迁,致使搬迁的指标全部流入村里的非贫困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王村的精准扶贫识别层面,出现错位的主要原因一是当前基层体制的问题,扶贫政策在落地时部分地区为了表政绩出现了一定的指标化治理模式,如层层加压下指标、设任务,出现了拔苗助长、一蹴而就的现象。这种“压力型”的体制仅考虑所谓的硬指标,不仅忽略了基层政权组织执行目标的实际能力,而且忽略了那些被基层政府或民众认为至关重要的目标,同时当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11]。在王村扶贫搬迁中为了完任务,充指标,村一级与乡镇一级通过“共谋”完成了搬迁户的确定。二是国家在宏观政策制定方面还存在对地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的现象,王村所在的H县位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收入贫乏,主要靠国家的转移支付来完成各项经济建设,在扶贫移民搬迁过程中国家给予的补贴对于农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同时地方财政的乏力,资金配备有限。从整个扶贫政策制定方面来看,国家缺乏对地方经济水平与发展能力的充分考虑,在精准管理与精准预测方面仍然存在漏洞。
(二)制度与部门缺乏衔接:扶贫治理的碎片化
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性的任务,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各项制度的有效衔接、不同行政部门的密切配合是推进扶贫治理的重要举措。与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单一的农村扶贫治理模式相比较,目前农村扶贫治理呈现治理手段多元化以及多部门主导的状态[12]。在多部门所主导的扶贫治理中,制度的衔接与部门的配合是推动扶贫开发的有效办法。在精准扶贫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过程中更需要制度的有效衔接与部门的密切配合。而从目前整个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来看,扶贫治理的碎片化已经成为困扰精准扶贫有效实施的最大障碍。“碎片化”指向的是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13]。在王村的扶贫搬迁中,贫困户的识别仅靠几名村干部商议决定,而缺乏扶贫办、民政部门、社保部门以及乡镇有关职能部门的介入,所以在精准识别层面各个职能部门缺乏有效的配合、制度缺乏一定的衔接,导致在精准识别上缺乏科学性与村民的有效参与。另外在移民搬迁的房屋修建过程中,移民搬迁点的选址与移民房屋的建设由当地的土管所来进行规划与设计,但是最后的验收又由扶贫办负责,职能部门在移民搬迁过程中制度设计层面缺乏有效的衔接,如若在整个移民搬迁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配合,职能部门通过沟通与交流、共同进行搬迁的设计、规划与验收也不会导致后面扶贫移民搬迁验收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以职能为中心、功能分割、“鸽笼式”的部门设置或许能够实现局部效率的提高,但对于组织的整体效率却是一种妨碍[14]。
虽然国家在扶贫治理的整合层面也做了一定的努力,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开发式扶贫政策制度相联接的“两项制度衔接”政策。但是从扶贫治理的过程来看,整个扶贫体系的制度与政策衔接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在精准扶贫当中,地方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扶贫就是扶贫办的事,与其他行政部门没有关系。这种认识存在严重的不足,在当前的扶贫治理过程中,需要构建大的综合性扶贫治理体系,并且有效摒弃扶贫过程中部门之间的条块化、分散化,从而实现扶贫治理的碎片化向扶贫的整体性治理过渡。整体性治理能够“排除相互破坏、腐蚀的各种政策情境,更好地共享稀缺性资源,促使某一公共政策领域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间的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公共服务”[15]。扶贫不仅需要两项制度的衔接,更需要多项制度的融合与贯通,构建扶贫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最重要的是不同行政部门的有效衔接。通过构建大的综合性扶贫治理体系来实施扶贫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贯通、融合以及构建相关部门的联动扶贫机制。例如在王村的扶贫移民搬迁过程中涉及扶贫移民搬迁的扶贫办、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国土部门、环保部门、人事与社会保障部门、发改部门、城建部门等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和实际操作中需要有力的配合与相互的沟通、在制度层面构建有效的联动机制,避免扶贫治理体系的细碎化与条块化。
(三)利益的博弈:精准扶贫中多重制度逻辑的围困
从整个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扶贫移民搬迁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工程。但是为什么扶贫移民搬迁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导致一部分人陷于一定的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之中,出现二次贫困。在目前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国家从宏观战略层面出发,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与文件,对扶贫的阶段性任务及目标有了详细的规划,但是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来看很多地区由于财政、发展方式、地域性质的差异而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很难按照国家的制度设计进行实施。而且扶贫实践脱离了贫困户的现实需求,导致扶贫目标的脱靶。扶贫过程中的行动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部门与贫困户。正如周雪光、艾云所提出的“多种制度逻辑”,认为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推动和约束制度变迁,而不同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所以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因而不同行动主体的角色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获得认识, 需要在行动者群体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16]。在扶贫搬迁中,国家、地方政府部门、贫困户三者陷入了一定的制度性困境之中。国家所出台的扶贫规划纲要为扶贫开发制定了大的施政方略,意图通过扶贫移民搬迁来解决贫困问题。但是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尤其是类似于H县这样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扶贫开发难度大,地方财政收入微薄,按照国家制度设计,移民搬迁资金除国家的补贴之外,还需要地方财政的有效匹配。但是作为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大部分投入用在了地方经济建设之中,补贴力度有限,国家所推行的扶贫开发的重任与地方注重发展经济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是迫于压力型体制,地方政府只能逢以迎合。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其个人效用目标是政绩最大化或者说政治晋升机会最大化,也就是说它的背后遵循的是稳定存在的科层制逻辑[17]。对于贫困户来说依靠现在几亩耕地还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搬迁之后,耕种的不便、社会融入等都对贫困户的生计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且很多贫困户属于低保户、五保户,生计脆弱性较强,搬迁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农民的生计制度选择也为扶贫移民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多元行动主体与多重制度逻辑交织下的利益博弈使得扶贫开发陷入了制度性困境之中。
(四)生计的式微: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困境
关怀国际(CARE)认为农户的生计系统包括三个要素:拥有的能力(如教育、技能、健康、生理条件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的可及性以及经济活动[18]。扶贫移民搬迁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搬迁后村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从王村调研情况来看,搬迁后的农户除30%外出打工,其余70%的农户仍以务农为主。所以从生计的改善层面来看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移居到乡镇所在地的农户耕地仍然保留在原来的村子,而且原住房等也仍然保留着。很多农民虽然已经搬迁到了乡镇所在地,但是日常的种地、耕作等活动仍然在原来的村庄,对于靠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要来回往返于两个住所,加大了生活成本。现实中,连片特困地区常常是脆弱性交织体:高山峡谷土地稀少贫瘠,伴之以自然灾害频发;少数民族相对聚居或散居伴之以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人们行动能力较弱;经济欠发达,伴之以资本、人力资源匮乏;产业发展脆弱伴之以市场风险巨大等[19-20]。在王村虽然很多村民都实现了移民搬迁,但是却没有在职业的转型、产业的发展等方面有所改观,经济收入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很多农户表示移居到乡镇所在地以后,生活成本抬高,日常开支增多,对于没有技术和工作,靠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必然将增加生计的成本,从而使生计的脆弱性增强,造成生计的式微。所以,在精准扶贫中确保贫困户的可持续性生计仍面临较大的困难。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陕南地区王村扶贫移民搬迁为例,论述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扶贫移民搬迁的行动逻辑,并且对扶贫移民政策出现偏差的原因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诠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世化政策的诱导消解了精准识别的目标定位,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同时在扶贫搬迁过程中地方行政部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及制度衔接的缺失导致扶贫治理的条块化与细碎化,严重影响了扶贫开发的效率与进度,阻碍了大的综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形成,严重背离了精准扶贫中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要求。另外,在扶贫移民中,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由于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不同,而使扶贫移民陷入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国家定指标、注成效、推进度的制度设计背离了贫困地区薄弱的财政状况与发展路径,而逢以迎合和被笼罩在科层制与官僚化之下的地方政府在扶贫治理层面失去了一定的话语权,将追求政绩作为了自己的制度选择。从扶贫移民搬迁户来看,国家与地方政府制度设计背离了他们的实际需求,在生计的制度选择层面并没有实现大的改观,甚至造成了扶贫治理的内卷化。最后,从扶贫搬迁后村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来看,后续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导致了搬迁户的生计式微。
扶贫移民搬迁作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面对政策偏差的困境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纠正:首先,在政策制定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各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摈弃下指标、完任务的指标化治理,充分发挥地方在扶贫攻坚中的自主权;其次,继续加大对于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县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扶贫专项资金的拨付力度,在扶贫移民项目中提高国家匹配额度;再次,构建综合性扶贫治理体系,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形成多部门参与的扶贫联动机制,完善多项制度之间的衔接,使扶贫治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治理过渡。最后,不断强化扶贫搬迁后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如就业,社会保障等,进而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参考文献]
[1]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与现实挑战.贵州社会学,2015(8):156-162
[2]陆汉文,覃志敏.我国扶贫移民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趋势.贵州社会科学,2015(5):164-168
[3]郑瑞强,王英,张春美.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02-106
[4]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http:∥www.gov.cn/jrzg/ 2011-12/01/content200846_2.htm
[5]白南生,卢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移民:方法和经验.管理世界,2000(3):161-169
[6]施国庆,郑瑞强.扶贫移民:一种扶贫工作新思路.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4):68-75
[7]郑瑞强,施国庆.扶贫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42-47
[8]何得桂,党国英.西部山区避灾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及其影响研究——以陕南为例.青海社会科学,2015(5):65-74
[9]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10]唐海华.“压力型体制”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宁波党校学报,2006(1):22-28
[11]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116-122
[12]李小云.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3(7):101-106
[13]唐兴盛.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5):52-56
[14]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社会科学,2010(8):12-18
[15]曾凡军.政府组织功能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35-240
[16]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4):132-150
[17]汪玮,周育海.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案例的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13(9):97-104
[18]唐丽霞,李小云,左停.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性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贵州社会科学,2012(12):4-10
[19]陈艾,李雪萍.脆弱性——抗逆力: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5(2):92-99
[20]李雪萍,龙明阿真.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可行能力达致减贫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11(1):97-103
(责任编辑:陈世栋)
Encountering relocation:The discussion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tion relo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log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Take Wang village in southern Shaanxi for example
Li BoZuo Ting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logic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tion relocation in the four stages and finds that coercion of pressure system and the policy-induced of universality policy by executive-led, the two breeds masquerading. In addition, the lacks of system convergence and administrative joint in the process of relocation which led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 into Fragmented trouble and against the goals of precise support and precise management. Eventually. The differences in action logic, system selection and benefit demand of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verty family which led migration relocation into Institutional Logical Dilemmas.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become decay after relocation, it is a threat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Immigrant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in policy-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of Immigrants.
Key words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tion relocation; Policy devi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15-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西部地区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研究”(13XSH031)。
[作者简介]李博,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左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