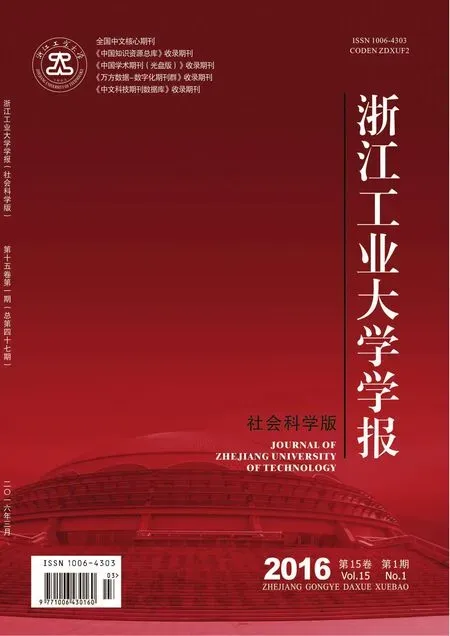“很是”辨析
2016-01-23孙力平
孙力平,王 萍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很是”辨析
孙力平,王萍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很+是”是一个同形异构形式,可以分为“很是1”、“很是2”和“很是3”,其性质和意义均有所不同。“很是1”是一种临时性的跨层结构;“很是2”是一个具有评注性语用功能的程度副词,能修饰形容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以及名词性成分;“很是3”是一个强调标记,其后多跟有界性成分。
关键词:跨层结构;程度副词;强调标记
在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语料中,“很+是”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组合。近代以来,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多,“很是”经历了词汇化并逐渐进入了汉语词汇系统。直至现代,“很是”的演变似乎仍在继续,并在原有用法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用法、新功能。
“很+是”性质、意义以及功能的变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文章主要是针对“很+是”的来源及其所能修饰的句法成分进行了讨论,对“很+是”形式的性质和意义也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张谊生(2003)在《“副+是”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变异》中对“副+是”的语法化历程结合“是”的性质作了相关论述,并指出现代汉语中的“很是”已经成为程度副词小类中的一员[1]。董秀芳(2004)在《“是”的进一步语法化:从虚词到词内成分》一文中也将“很是”列入了由“是”参与组成的双音节副词,并认为像“很是、越是、愣是”等一系列具有很多词汇特性的词应该收录到《现代汉语词典》中[2]。这两项研究成果都是将“很是”作为例证,但均未从微观上对“很是”作详细讨论。曾芳、宋艳旭(2006)的《“很是”考察》一文主要对“很+是”修饰体词性和谓词性成分的情况进行分类研究,认为应该根据不同句子对“很”和“是”的词性进行重新分析[3],但文章没有涉及对高度词汇化的“很是”的分析。陈丽丽、支庆玲(2011)在《说“很是”》中对“很是”的性质作了说明,认为“很是”修饰形容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时,属于附加结构,表示对后面成分的主观确认和强调;“很是”修饰名词性成分时,表示对后面成分的判断,是偏正结构[4]。
本文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很+是”作更加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主要是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用例*本文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语料库(CCL)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论证“很+是”实际上是一个同形异构形式,大致可以分解为性质和意义并不完全一样的“很是1”、“很是2”和“很是3”,并着重对“很是2” 和“很是3”的出现条件和语用功能进行阐释。
一、跨层的线性组合“很是1”
在汉语史上,“很+是”在同一类的“程度副词+是”(如“最是”“甚是”“更是”)中,出现时间较晚。例如“最+是”,仅以南朝至宋代著名文人诗句为例,我们就可以见到:
(1)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何逊《咏早梅诗》)
(2)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杜甫《咏怀古迹》之三)
(3)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4)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
(5)雨余花色倍鲜明,最是春深多晚晴。(黄庭坚《再和元礼春怀十首》之七)
而“很+是”用例的出现则要晚得多,这与“很”的程度副词用法产生较晚有密切关系。“很”的程度副词用法在元代初露端倪,于清代日渐兴盛,因此“很”与“是”连用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如在《红楼梦》中可以见到大量的“很是”,如:
(6)王夫人道:“很是,我们都要去瞧瞧他,倒怕他嫌闹的慌,说我们问他好罢。”(《红楼梦》第十一回)
(7)贾母听了,说:“这话很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8)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故听了这话,都说“很是”。(《红楼梦》第四十回)
然而,以上句中的“很+是”与本文所探讨的“很是”并不同形,其中“是”是形容词,表示“正确、对”的意思,“很是”即“很正确”、“很对”。这些“很是”是一个偏正结构,在句中充当谓语,后面并无其他成分。下例才是本文所论述的“很是”:
(9)你老人家只管卖人,不必说着一个扯着一个的。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么“拨出肉中刺,眼中钉”?(《红楼梦》第八十回)
此句中的“很是”即本文所说“很是”,其中“是”已经不是“正确、对”的意思,后面紧跟有其他成分。其他小说中的用例如:
(10)上了石台阶,到了屋中,蒋爷暗以为雷家哄了王爷些个银子,没见过世面,盖的房子不合样式,焉知晓到了屋中一看,很有大家的排场,糊裱得很干净,名人字画,古玩铜器,案桌几凳,幽雅沉静,很是庭房的式样,颇有大家风度。(石玉昆《三侠五义》)
(11)这个店的东家,原本是龙游县的三班总头杨国栋。在本地很是人物,无人不知。(郭小亭《济公全传》)
(12)寂笑道:“唐公!你为什么这般胆小?收纳一两个宫人,很是小事,就是那隋室江山,亦可唾手取得。”(蔡东藩《唐史演义》)
(13)彼此答应下合作,心中都安静了一些,象吃下一丸定神的药似的,虽然灵不灵很是问题,但总得有点信心。(老舍《文博士》)
诸如此类的“很是”我们称为“很是1”。显然,“很是1”只是一个临时的跨层组合,由程度副词“很”和判断动词“是”构成。“是”作为判断动词,其后一般接名词性成分构成标准的判断句。程度副词“很”出现在“是”之前,二者只是线性序列紧邻,在线性序列上共现,并不产生直接语法关系,因为“很”修饰的是其后的整个“是NP”,在认同判断“是+NP”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肯定,整体构成一个句法层面的状中结构。这一整体性偏正结构在句中主要作谓语,表示对所属NP的事件、情况作出评价,认为其符合判断标准的程度较高。如例(10)所述对象不仅“是庭房的式样”,而且在程度上予以进一步肯定,突出跟庭房样式的高度相似性。(11)中的“很是人物”不仅对“人物”给予判断还强调了“人物”的重要性。其余两例均有此用法,不再一一赘述。
处于前词汇化阶段的跨层线性组合“很是1”为其进一步演变提供了一个结构槽,为“很是2”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作为程度副词的“很是2”
随着“很是1”使用频率的增高,紧跟在“很是”后面的不仅仅是名词性的成分,也出现了谓词性的成分;尤其是随着其中“是”的进一步语法化及其语义的虚化,“很”和“是”在高频使用过程中逐步发生意义融合,并最终凝固成词,这就是“很是2”:
(1)而且那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他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象,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2)其实,道场的话使他颇觉宽慰,很是对他的意思,只是理智上觉得不应喜形于色就是了。(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3)到了延吉市,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很是痛苦。(《1994年报刊精选》)
“很是2”是个词汇化了的程度副词,这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肯定,如董秀芳将“是”定义为词内成分,认为这是“是”进一步语法化的表现[2]。
“很是2”和“很是1”不仅出现环境有别,更重要的是语法性质、意义不同。“很是1”中的“是”是判断动词,在“很+是”中居主导地位,因此,略去前面的“很”句子仍能成立;“很是2”中的“是”已经虚化为一个“词内成分”,在“很+是”中不占主导地位,删去后面的“是”句子仍能站得住。这是分辨“很是1”和“很是2”的一个简单标志。“很是2”的理性意义几乎等同于典型程度副词“很”,但“很是2”不只是表示事物性状程度的较高量,而且具有表意的主观性,具有评注性语用功能,这是“很是2”和 “很”在语法意义上的区别。
“很是2”在句中一般作状语,主要用来修饰形容词性成分。此外,一些动词性成分以及具有某些谓词性语义特征的名词性成分也可以受“很是2”修饰。前人对此虽有论及,但是将谓词性成分前的“很是”看作两个语气副词的连用,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下文主要对能够受“很是2”修饰的成分作一个全面的阐述,具体情况如下:
(一)“很是2”修饰形容词性成分
“很是2”最主要的语法功能是对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性状进行修饰,表现被修饰成分的高程度量,在语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主观表意性,突出了对事物性状程度的肯定,如:
(4)他养着一匹小毛驴,就像大个山羊那么高,但鞍镫铃铛齐全,打扮得很是漂亮。(孙犁《乡里旧闻(一)》)
(5)官场小说很是火热,究其原因不说大家也是很明白的。(源于微博)
例(4)中的“漂亮”是性质形容词,受“很是2”修饰后体现了说话人对“小毛驴”的“漂亮”程度的肯定。(5)中的状态形容词 “火热”也能受“很是2”修饰,这属于对形容词的二次记量,即通过主观赋量的方式使其在原来量点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量幅,表达了一定的主观化倾向。
(二)“很是2”修饰动词性成分
动词虽然是以表动作行为为主的一类词,但其内部小类的差异仍然较大。本文主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动词分为心理动词和非心理动词两大类进行分析研究。
1.心理动词。心理动词的认定,主要依据张谊生提出的广义心理动词说,即“将那些具有[+述人]特征并与心理、心态意义相关的动词都作为心理动词”[5]。“很”能够修饰心理动词,已经为学界公认。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大都也可以受“很是2”修饰,与其受“很”修饰相比,“很是2”更能强调说话者的主观感受。例如:
(6)唐校长,说实话,你提出学校创一流的想法我一直很是佩服,也真想跟着你大干一场。(《管理学案例分析》)
(7)李小龙平时在街头打斗太多,家里人很是担心他的成长教育问题。在这个思想“蜕变”阶段,家里人不失时机地安排李小龙离开香港,隔离旧日的生活环境和朋友圈子。于是,18岁的李小龙,漂洋过海,踏上了他的出生地,在全新的环境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张小蛇《李小龙的功夫人生》)
以上例句中的“佩服”“担心”都是表心理活动的动词,与受“很”修饰相比,“很是”不仅能体现客观程度量的增加,更能突出说话人主观认定的高程度量,这种“佩服”“担心”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主观判定标准的极大值。受到音节、韵律的制约,“很是2”通常不能修饰像“恨、爱、想、贪、顺”等一类的单音节心理动词。
2.非心理动词。非心理动词的范围十分广泛,但是能够受“很是2”修饰的非心理动词的数量较为有限,这类动词大都蕴含抽象性、可量度的[+性状义]语义特征。这些语义特征一方面是词语语素本身具有的,可以将这类词称为直接式性状义词语;另一方面是通过语素义融合(即词义)获得的,可以称这类词为间接式性状义词语,如:
(8)这典诗曾侍候过先帝,与她母后也很是亲近,时常进出官邸……(紫式部《源氏物语》)
(9)不过,近几年有钱的人修坟地的不少,除了立碑,还用水泥把坟包和地面都抹了,很是讲究。(何申《多彩的乡村》)
例(8)中的“亲近”一词属于直接式性状义词语,(9)中的“讲究”则是整个词义蕴含[+性状义]语义特征的间接式性状义词语,受“很是2”修饰后体现了叙述者对这种程度高量级性的主观评价。
3.动词性短语。“很是2”除了可以修饰一部分动词外,还可以修饰动词性短语。受“很是2”修饰的动词性短语纷繁复杂,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类:
①动宾短语。能够受“很是2”修饰的动宾短语大都结构较为紧凑,意义较为融合,并且具有可度量性和抽象的性状义特征,例如:
(10)虽然电视里的报道很是吓人,虽然也有几起倒墙垮房的意外事故,但作为市民的我们,却并未见有太多的紧张和恐惧。(《人民日报》)
上例中的动宾短语“吓人”与主语“报道”构成一个独立的事件。动宾短语“吓人”整体受“很是”修饰,体现了叙述者从主观感受出发对这一事件作出的评价。若抽掉“是”则其主观性的意味就大大减弱了。
②兼语短语。能够受“很是2”修饰的兼语短语主要是使令类短语(V1+N+V2),其中V1大都由“让”“叫”“令”等动词承担,V2主要表示N在V1的致使作用下产生的抽象结果,整个短语的动作性较弱,例如:
(11)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中国农民调查》)
句中的修饰语“很是”不仅能出现在使令类动词前,也可出现在使令类动词后,如“让人很是不得要领”。短语“不得要领”整体受“很是”修饰,体现了说话人对“这事”的主观评判,即在说话人看来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与只表程度的“很”相比,“很是”更能凸显高程度量。
③动补短语。动补短语中的V得/不C式,大都表示某种动作行为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程度等级性,可以受“很是2”修饰,例如:
(12)我们的这位继母,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对于我们兄弟也算很是说得过去了。(《作家文摘》)
(13)一名干警说:“委员会刚成立时,我很是想不通,觉得院里只管上班时间就够了,八小时以外是自己的时间,应该由我们自由支配。”(《人民日报》)
例(12)中“很是”修饰V得C结构“说得过去”,表明其实现的可能性较大,蕴含了叙述者根据自身感受作出的评价;例(13)“很是”修饰V不C结构“想不通”,体现了实现的可能性程度的极低量,是说话者从主观视角出发作出的评价。
与“很”相比,“很是2”修饰动词性成分的能力较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很是2”成词较晚,虽然使用频率在不断提高,但远不及“很”普遍;第二,受音节、韵律制约,“很是2”主要修饰限制双音节词语,这大大降低了它的使用范围;第三,“很是2”具有表意的主观性,因此不能自由出现在表强客观性词语前,若要修饰这类词语则往往要借助其他词语或者语境的辅助作用。
(三)“很是2”修饰名词性成分
程度副词可以修饰名词已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张谊生指出:“副词修饰名词这一语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是客观存在的”[6]。但并不是所有名词都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只有那些具有特殊语义内涵的名词才能受“很是2”修饰。能够受“很是2”修饰的名词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1.词义本身具有潜在的[+典型性]、[+量度义]、[+性状化]等语义特征,通过“很是2”修饰,可以将其潜在的语义特性激活并外显,这样名词就具有了某些谓词性特征,这类副名组合通常作句子的谓语。例如:
(14)西方人大概非常重视会,男士大多西装笔挺,女士多为长裙和职业装,三五成群边饮边谈,很是绅士。(源于科技文献)
(15)车过西乌旗(县)白音郭勒苏木(乡),我们随意走进一位牧民家中,屋里粉白的墙壁,瓷砖地面,各种家具很是“现代”,电视机正播映着《美丽的祖国》。(《人民日报》)
(16)吴沛说:“我瞧那位朋友,很是朋友,他和咱这里谁家有亲?为何常在这里住着呢?”(《施公案》)
例(14)、(15)中,名词“绅士”和“现代”词义本身就蕴含独特的、可量化的抽象性质,受“很是”修饰,这种意义更加外显,获得了表性状的特性。(16)中的“很是朋友”既可以分析为“很/是朋友”,指符合主观认定的朋友标准的程度评价义;也可以分析为“很是/朋友”,这是一个副名组合,副词“很是”将名词“朋友”谓词化、性状化,具有了充当谓语的功能。结合语境来看,将“很是朋友”分析为副名组合更恰当。
2.词义本身不具有[+典型性]、[+量度义]、[+性状化]等语义特性,但是通过语境赋予可以使这类名词获得临时的、外加的性状义,具备了受“很是2”修饰的语义基础。例如:
(17)我装腔作势,并带夸张的语气说:“很荣幸,我的朋友,你的推论是什么?”“你很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你完全正确!”(《沉默的证人》)
例(17)中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专有名词,结合语境,受“很是2”修饰后这一名词就获得了独特的“侦探能力强”“推理性强”的外显意义。
三、处于进一步演化中的“很是3”
在演化进程中,“很是2”之后除了可以接具有广义性状义的名词和谓词性成分外,还可以跟具有数量义特征的数量补语和宾语受数量短语修饰的动宾结构。如:
(1)记得当时北京第一家专门出售性药具的亚当夏娃商店开业时新闻界很是炒了一阵,性问题也一度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1994年报刊精选》)
(2)为了组织本届亚运会,广岛一共投入了150亿美元,这个数字很是吓唬住了一些亚奥理事会成员。(《1994年报刊精选》)
我们把处于这种句法环境中的“很+是”称为“很是3”。
“很是2”在修饰事物性状程度的同时也起到加强突出的作用,这是导致“很是3”用法产生的功能基础,进而促使“很是2”的用法发生分化,一部分仍保留原来的用法,一部分意义进一步虚化,成为一个具有强调标记作用的虚词。这一虚化进程是在隐喻机制的推动作用下产生的。“很是2”的典型用法是修饰谓词性成分,表示性状的高程度量,具有抽象的空间量度义。通过隐喻机制的作用,由空间域投射到时间域,分化出可以表时量“多量”性的“很是3”,进而类推扩展出表名量和动量的“多量”性用法。
“很是3”作为强调标记,主要表示对数量“多量性”的突出强调。方梅在《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1995)中指出“标记词的确认应遵循以下原则:(1)作为标记成分,它自身不负载实在的意义,因此,不可能带对比重音;(2)标记词的作用在于标示其后成分的焦点身份,所以焦点标记后的成分总是在语音上凸显的成分;(3)标记词不是句子线性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因此它被省略掉以后句子依然可以成立”[7]。“很是3”作为句子的附加成分,其存在与否对句子核心语义的表达以及句法成分的完整性并不产生影响,且对其后的数量短语起到焦点暗示功能,正符合焦点标记的判定三原则。但应指出,“很是3”与“很是2”的区别较为细微,或曰“很是3”仍处于“很是”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之所以将“很是3”定义为强调标记,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焦点标记词“是”;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突出“很是3”的强调性语用功能。
“很是3”与“很是2”在语义上也有所不同。“很是2”的词汇意义和“非常”“十分”等程度副词的意义非常接近,它们常常能够互换而句子基本语义不变,但“很是3”却不能替换为“非常”“十分”。试比较以下两例中的“很是”:
(3)说完很是灿烂地一笑。(《1994年报刊精选》)
(4)那时这个铁皮屋顶、砖墙结构的固定市场在全县很是风光了一番。(《1994年报刊精选》)
例(3)中的“很是”可以替换为“非常”“十分”等,句义基本不变;(4)中的“很是”则不然。前者为“很是2”,后者为“很是3”。
“很是3”强调标记语用功能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
1.被强调部分遵循句子自然重音所在的尾焦点,并且起到逆向语义增补作用。与“很是2”相比,“很是3”并未对紧邻其后的典型谓词性成分加以修饰,而是语义指向具有述谓性特征的数量短语并对其进行强调。受“很是3”修饰的“一+数量词+(名词)”数量短语大都具有 “无定性”“较少量”的语义特点。但整个短语被“很是3”强调后就具有了数量多、时量长的特殊含义,这就与“很是2”的顺向性状程度增强作用相区别,例如:
(5)这个发现,让我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中国艺人生存实录》)
(6)有关大学生就业,近期很是出了一些新鲜事儿,比如广州交管部门招聘交通协管员,应聘者云集,其中就有不少高学历者,而“大学生保姆”的话题,更是沸沸扬扬。(《北京晨报》)
例句(5)的“很是”并非修饰“得意”而重在强调“一段时间”,这就使得本来只具有“较少量”语义特征的“一段时间”的功能语义发生了变化,意在强调凸显“我”得意的时间之久,而非“得意”的程度之高。(6)同样强调“新鲜事”之多,这充分体现了“很是3”的焦点暗示性功能。
2.被强调部分大多具有[+离散性]的语义特征,离散性是有界性的突出表现。“有界—无界是客观事物在空间、时间和状态等方面的离散性和连续性的对立统一在认知上的体现,是人类认知和组织空间、时间概念的基本手段之一”[8]。沈家煊在《“有界”和“无界”》一文中指出名词的“有界和无界”体现为事物的可数与不可数的对立,动词的“有界和无界”体现为动作在时间轴上起迄点的有和无的对立[9]。“很是2”的被修饰成分具有[+性状义]的语义特征,表现出无界性,“很是3”的被强调成分具有[+离散性]的语义特征,体现了强有界性。且受“很是3”强调的数量短语大都倾向于和包含结果补语或者完成体标记“了”共现,这些成分的有界性和其后数量短语的[+离散性]语义特征有极强的匹配性。例如:
(7)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在首都市民中反响很大,赞扬者居多,似乎AA制的普遍实行已不太遥远。(《1994年报刊精选》)
(8)于是,他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领到的抽签表很是让德隆公司赚到了一笔钱。(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例(7)中“很是”强调存在隐性终结点的数量短语“一阵”以突出“热闹”的时间之长,这和分句中表完成体的“了”共现,增强了整体事件的有界性。例(8)“很是”指向具有上限的不定量短语“一笔钱”意在强调赚到钱数额之大的同时,也和结果补语的有界性相匹配。
综上所述,通过对“很+是”同形异构形式的性质和意义分别进行阐述,可以看出“很是”的演变过程是一个连续统。“很是1”是程度副词“很”和判断词“是”的线性连用,是一个临时性的组合;“很是2”在“很”和“是”频繁连用的基础上逐渐完成其词汇化过程,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评注性功能的程度副词。“很是2”在句中主要作状语,可以修饰具有[+性状义]语义特征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性成分,起加强程度的作用;“很是3”则是“很是2”进一步虚化的结果,是一个表“多量”的强调标记。“很是3”后通常出现含有[+离散性]语义特征的数量短语,并对此起突出强调的作用,具有焦点暗示功能。对“很+是”这一同形异构形式的深入辨析,既可以为进一步探究其词汇化历程提供线索,也可以丰富对“很是”意义、用法的认识,从而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 张谊生.“副+是”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变异[J].语言科学,2003(3):34-49.
[2] 董秀芳.“是”的进一步语法化:从虚词到词内成分[J].当代语言学,2004(1):35-44.
[3] 曾芳,宋艳旭.“很是”考察[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7):175-177.
[4] 陈丽丽,支庆玲. 说“很是”[J].语文学刊,2011(2):71-72.
[5]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53-154.
[6]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7.
[7] 方梅.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J].中国语文,1995(4):281.
[8] 陈忠.认知语言学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339-340.
[9] 沈家煊.“有界”和“无界”[J].中国语文,1995(5):367-380.
(责任编辑:薛蓉)
The discrimination of “Hen Shi”
SUN Liping, WANG 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
Abstract:In the present paper, we analyse the natures and meanings of “Hen Shi”, which is of the same form but different structur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bining the diachronic with the synchronic. Hen Shi1 is a cross-layer structure, which will chang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Shi”, Hen Shi2 is an expositive adverb of degree, which generally modify verbal part, adjective part and noun part. Hen Shi3 is multiply emphatic mark, which is followed by bounded element.
Keywords:cross-layer structure; expositive adverb of degree; emphatic mark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303(2016)01-0074-06
作者简介:孙力平(1951—),男,江西南昌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诗学和汉语语言学研究;王萍(1989—),女,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YY168)
收稿日期:201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