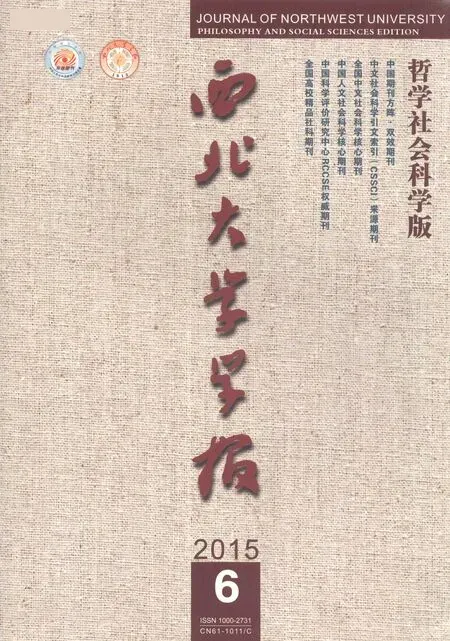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
2016-01-19郝旭东
郝旭东
(1.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46; 2.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
郝旭东1,2
(1.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210046; 2.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200241)
摘要:阅读《前分析篇》会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段论的格分为三种,而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却认为三段论的格有四种,这就导致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第四格问题。基于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格的划分依据、描述方式及其学科构想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亚里士多德将三段论界定为三个格的原因,肯定其三格划分的严格无误,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发掘出导致亚里士多德确定其划分依据的原因及其原因背后的动机,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由一个更为深远而新颖的视角,即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以及古典公理演绎系统的视角,对之作出更为恰当而合理的评价。
关键词:格;第四格;三段论;古典公理系统;科学观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我们的这种常用思维形式进行的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和探讨,其理论成果的核心内容我们沿用至今而没有问题。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誉为“西方逻辑之父”,从根本上说也正是由于其在三段论的研究过程中,首开先河地使用了“暂时脱离思维的具体内容,纯形式地专注于探讨思维形式结构”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评价说:“亚里士多德是深入考察并描述三段论各种形式的第一人,他做得那样严密和正确,以至于从来没有人在本质上对他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1](P364)到了近代,三段论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很多的发展和完善,以至于其面貌已与其诞生之初相去甚远,这也给我们阅读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其中第四格问题就是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问题,该问题可以细化为如下问题:亚里士多德到底有没有认识到第四格?导致亚里士多德格之三分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的背后有无更根本的推动因素?怎样评价亚里士多德的格之三分法才算真正公允?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比较合理的解答。
一、亚里士多德有没有认识到第四格
对于直言命题而言,量词有全称与特称之分;再加上肯定和否定,就可以形成四种不同的直言命题:全称肯定(A)、全称否定(E)、特称肯定(I)、特称否定(O)。三段论中的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分别就是这四种直言命题中的一种;而作为前提的两个直言命题具有一个共同的词项,该共同的词项即是中词,常用M来表示;其余的两个项分别被称为大项(P)和小项(S);其中,大项就是结论的谓项,小项就是结论的主项。包含大项的前提被称为大前提,包含小项的前提被称为小前提。如果按照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样的顺序来书写三段论,根据中词在前提中位置的不同,三段论就只会有下图所示的四种不同的框架结构,即四种不同的格。这就是如今传统形式逻辑关于对三段论的格之种类的论说,或者可以说这就是传统形式逻辑将三段论分为四个格的理由与过程。

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M-PP-MM-PP-M||/S-MS-MM-SM-SS-PS-PS-PS-P
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关于三段论的格之分类确确实实只给出了三个格(暂且不论是何意义上的三个格)。也许有人会将之解释为亚里士多德经常从实际应用出发来研究逻辑问题,同时又因为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的确几乎不使用第四格(传统形式逻辑所言的第四格),所以,亚里士多德才没有将之给出。然而,这样的解释太过牵强。因为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服务于论辩,而是要系统地去考察这种作为证明的推理形式,所以仅从是否有日常思维的使用需求来认定亚里士多德是否应该去区分和考察出第四格,就变得十分地缺乏说服力。试想,如果亚里士多德真的认识到了还可以区分出来一种不同的格的话,他会因为在日常思维中很少被使用而置之不理么?答案显然是:肯定不会。因为亚里士多德此处的工作,已经跳出了论辩术的局限,不会简单地以是否有论辩价值做取舍;而出于要系统考察这种重要推理形式的目的,如果可以更全面,他一定不会有遗漏,一定会想方设法将之区分并表述出来。
也许还有人会说,可能这种表达过于困难,所以尽管他认识到了,但却没能表达出来。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真的认识到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格,那么就意味着他已经知道、并且判断:三段论还存在着不同的形式结构;然而,想要作出形式结构的同与不同的判断,必须确实已经知道了其形式结构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因为思维的形式结构不同于某些晦涩的思想,你能感觉到不同却表达不出来;形式结构的同与不同,在逻辑上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和可判定性。也就是说,如果认识到了形式结构的不同,那就意味着一定知道了其不同之处在何处;如果你不能确切地指出其不同之处在何处,那就不能表明你认识到了形式结构的不同。这样,该说法其实就是在说,亚里士多德的确能指出(当然是用语言指出,而不是用手指指出)这种不同的形式结构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语言表达。于是,这种说法就变成了:亚里士多德既可以讲得出这种不同,又不可以讲得出这种不同。这显然是荒谬的。
更主要的证据在于,马玉珂先生[2](P63-66)和张家龙先生[3](P332-333)在其论著中都讲到,亚里士多德的直言三段论的第一格中包含着一种非标准式,亚里士多德列出来三个;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德奥夫拉斯特(De AF Last)又进行了明确补充,使其数目变成了五个。尽管这个补充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第四格的有效式,但德奥夫拉斯特仍然将这些有效式划归到第一格。这两个事实说明:首先,亚里士多德确实列举了第一格除四个正常有效式之外的另外三个有效式;而这三个有效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转换方式,确实也属于传统形式逻辑所讲的第四格的有效式。但由于亚里士多德仍然没有把它们划到第一格之外,这就恰恰说明了亚里士多德没有认识到可以进一步区分出来传统形式逻辑所讲的第四格,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作区分。其次,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理智地去相信,时间上距亚里士多德极近的德奥弗拉斯特的看法比我们的任何猜测都更值得让我们相信,即他们不仅理解而且也坚持了其老师的观点。所以,本文赞同王路先生[4](P121)“亚里士多德不仅没有考虑到第四格,也没有认识到第四格”的观点,或言,亚里士多德的确没有意识到三段论的格可以像现在的传统形式逻辑那样可以区分出四个格。
二、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三分法
然而,传统形式逻辑将三段论区分为四个格是如此的明晰、正确,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搞错了?是不是违反了划分的规则?否则,为何其划分会少了一个格?这些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因为简单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地位几乎可以说是以“三段论”而立,如果其三段论理论的缺陷过大,就将直接影响到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史上的评价。那么,事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亚里士多德对这三个格特征的描述——
第一格[5](25b34):(在一个前提中)中词包含于另一个词项,(在另一个前提中)中词包含另一个词项。第二格[5](26b36):(两个前提的)中词都是谓述两个主词(即中词在两个前提中都不是主词而是谓词)。第三格[5](p28a11):(两个前提的)中词都是被谓述的(即中词在两个前提中都是主词)。通过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各个格特征的描述可见,他对三段论的格的划分可以做如下概括:中词都是主词的为一类(即第三格);中词都是谓词的为一类(即第二格);在两个前提中,中词并非都是主词或并非都是谓词的为一类(即第一格)。于是,三段论就被划分成了三个格。相比较而言,其第二格和第三格与传统形式逻辑并无不同,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格:传统形式逻辑会进一步考察中词,若中词在大前提中为主词,在小前提中为谓词,则称之为第一格;若中词在大前提中为谓词,在小前提中为主词,则称之为第四格。
而导致这两种划分的方法不同的直接原因正如张家龙先生[3](P333-334)所言,“三分法完全是根据两个前提的中词位置,前提的次序没有什么关系,四分法却是根据结论的主谓词,从而确定前提的词项的排列,前提的次序一般已由结论的主谓词固定住了。由此可见,两种方法确定大词、小词的标准不同”。该观点与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Luca Sivits)的观点[6](P32)也是一致的。同时,张家龙先生又指出“按三分法,(传统形式逻辑的)第一格和第四格的两个前提都是“中项居中”,“中项在一个前提中做主词,在另一个前提中做谓词”,因此,两个格没有本质区别;按四分法,第一格和第四格有根本的不同。更概括地说,在传统形式逻辑的定义中,四个格所包含的两个前提在逻辑上是有区别;而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四个格所包含的两个前提在逻辑上是没有区别的,尽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称谓。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与传统形式逻辑的四分法在划分标准方面大体类似,但又有具体上的不同。大体类似是说,亚氏三分法的划分标准本质上仍然要考察中词在形式结构中的位置。具体上有不同是说,其对中词位置的考察表面来看具有一种概括性。而这种划分标准具体的不同,正是导致亚里士多德划分出来的格只有三个的直接原因:即,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格,实际上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第一格和第四格的并。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认识到第一格可以被进一步地区分出来传统形式逻辑所言的第一格和第四格,但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亚里士多德对格的考察少了一个格。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划分依据,全部的三段论的格的确只会有三种。数目上虽然确实少了一个数字,但他只是将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格加在一起分成了三类,在实质上并没有缺少什么。因此也就不能说亚里士多德的划分标准不严格。更为恰当地评价是:亚里士多德对格的划分的确是三个,即使现在来看它没有违反任何的划分规则,是一个正确的划分;但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划分标准不是足够精细,以至于未能将通常所说的第一格和第四格进一步区分开来而已。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究: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不是足够精细的划分标准?
三、亚里士多德采用如此划分标准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将三段论的格划分为三个格并没有错,只是由于其与我们现在通常所采用的划分标准稍有不同。我们想要进一步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亚里士多德采用了这种不能将第一格和第四格区分开来的划分标准?
三段论形式结构的描述方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形式结构是使用条件句[5](P25b37)来描述的,即:如果有前提之一,并且有前提之二,那么就有某结论。这种描述方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如果有前提之一,并且有前提之二”与“如果有前提之二,并且有前提之一”二者在逻辑上并无差别,即,“并且”所联结的两个前提可以交换位置,与次序无关;而如果前提可以是无序的,那么在结构上就不易进一步区分出第一格和第四格。更具体地说,观察表不难发现,第一格与第四格在形式结构上的区分十分明显。但如果把第一格和第四格都用条件句横写出来,由于两个前提的位置不固定、可以交换,这就导致我们难以方便地观察到两个前提次序性与结论主、谓项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也就难以发现可以经由结论的主、谓项,去定义大项和小项(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仅仅根据词项与中项在两个前提中的相对位置关系来定义大、小项);而只有这样去定义大项和小项,并且再由大小项对定义大小前提,才可以使得大、小前提与结论关联起来,才能够使得两个前提的次序性与三段论的形式结构自然地关联起来。否则,如果大、小前提与结论没有通过大、小项而联系起来的话,想把第四格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格中区分出来,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采用“竖写式”,即:在经由结论的主、谓项而定义了大项和小项之后,再将大前提定义为包含大项的前提,将小前提定义为包含小项的前提,然后再固定地按照“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方式来描述三段论的形式结构,就将意味着不仅考虑到了结论的主、谓项与两个前提之间的关联,而且也很自然地考虑到了两个前提的次序性。因而可以说竖写式天然就是为四分法而设计的,它可以在形式结构上清晰且轻易地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格中区分出第四格。所以说,由于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结构采用横写的条件句描述方式,直接导致了其三分法的划分依据不够精细,也最终导致了其三个格的划分结果。
那么这是否可以因此就说,竖写式好而横写的条件句描述方式就不好呢?也不能如此笼统地说。无可否认,在清晰描述三段论的形式结构方面,竖写式的确具有很强的直观表现力,当然也可以将之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在某个层面上的继续发展。因为通过竖写的方式,可以清晰地展示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格进一步区分出第四格。这种区分使得三段论学说在理论上有了更加精细的发展,因而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竖写式并不必然导致四分,它只是为格之四分及其结果表达提供了便利。只要我们是由结论的主谓项去定义大小项,然后再由大小项去定义大小前提,即使不竖写也可以轻易地对三段论的格做出四分。换言之,在这样的定义方式下,即使把第四格的竖写式交换大小前提的次序,得到的也不会是亚里士多德定义下的第一格,并且该格也不会与四分法的第一格相混淆。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有了标准的竖写式,那么对于三段论之格的区分工作就变得相对容易和方便了许多。
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亚里士多德横写的条件句描述方式不好,因为这种描述方式恰恰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适应了其构建学科的目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思想,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思想的源泉;为此,亚里士多德也经常以苏格拉底为例。经过统计,在《前分析篇》中“苏格拉底”一词出现了41次;而“几何学”一词却几乎以相类似频次地出现了35次。虽然这个统计数字不能必然地说明什么,但实际上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里士多德根深蒂固的科学观。他认为任何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问,都应当是像几何学那样演绎地构建起来:即从少数的几个概念和公理出发,可以推导出本学科的全部真命题,这也是古典公理系统的构建方法(也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要建立三段论的古典公理系统,所以其对三段论有效式的判定使用的是化归法,而不是传统形式逻辑所使用的规则法)。鉴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要演绎地构建该学科,是要建立一个古典的公理系统,所以竖写式并不比横写的条件句更具优势。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采取条件句的描述方式,其背后的动机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关于三段论的古典公理系统。他要建立的这种证明理论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要像几何学那样演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正是根源于这种学科构建的思想,才使得亚里士多德采取了古典演绎系统对公理和定理的典型描述方式:“如果………,那么……”
尽管亚里士多德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到现在所讲的第四格的有效式,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理论的价值和地位。因为亚里士多德构建的三段论体系,是要使之成为像几何学那样的古典公理演绎系统。在这个演绎系统中,公理性质的第一格AAA式和EAE式就是该系统的演绎出发点;而其他所有的有效式,包括最初亚里士多德没能给出的第四格的有效式,只不过是这个古典公理系统中的定理而已。但就一个古典公理系统而言,只要其作为出发点的公理确定了下来,那么这个系统可以推得出的定理就已经唯一地确定了下来,而无论该系统是否给出了该理论的全部定理。这就好似平面几何的五条公设一旦确定,其可以推得出的平面几何定理也就已经唯一地确定了下来;至于实际上欧几里德给出了多少可推出定理,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平面几何这个古典公理系统的大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由于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要给出的是三段论的古典公理系统,只要公理给得清楚,并且给出了一定数量的定理,那么作为古典公理系统的三段论体系在本质上就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起来,而不必给出本系统的所有定理。所以说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成功深刻地研究了三段论理论仍然是最公允、最恰当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小逻辑[M]. 贺麟,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2] 马玉珂. 西方逻辑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 张家龙. 逻辑学思想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4] 王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 BARNES J, PRIORA A.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6] 卢卡西维茨.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M]. 李真,李先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责任编辑陈萍]
【哲学研究】
On the Three Definitions of Aristotle’s Syllogisms
HAO Xu-dong1,2
(1.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4,China; 2.DepartmentofPhilosophy,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After reading the Analytica Priora, we find that Aristotle classified the figure of syllogism into three classes. Consequently, it causes the problem of the forth figure of syllogism. Based on checking the criteria for the figure’s classification, the way of describing figures and his idea of constructing a discipline, we disclose the reason that Aristotle considers there are three figures and conforms that his classification is correct. Moreover, it can als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Aristotle decides his criteria for the figure’s classification, and all of these will be conducive to evaluate Aristotle’s syllog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ical axiom system like Euclidean geometry.
Key words:figure; the forth figure; syllogism; classical axiom system; the view of science
作者简介:邬天启,男,河北涞源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从事信息哲学、中国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96);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ZX020)
收稿日期:2014-01-11
中图分类号:B81-09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