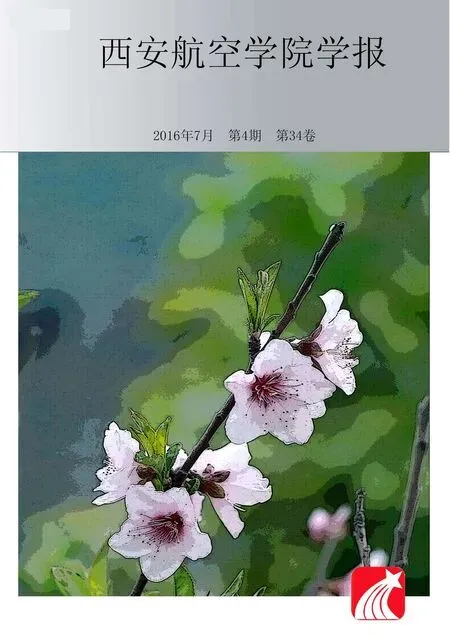父权视野下的母亲命运书写
——《百年孤独》与《丰乳肥臀》的母亲形象比较
2016-01-06张盛春
张盛春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四川 成都 611131)
父权视野下的母亲命运书写
——《百年孤独》与《丰乳肥臀》的母亲形象比较
张盛春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四川 成都 611131)
摘要:乌尔苏拉与上官鲁氏两位母亲,既表现出光辉与伟大的相同母性特征,又展示出悲剧命运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主要在于父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差异、作者对人物悲剧命运审视的不同视角及作者对女性不平等性别角色与地位的不同认识。
关键词:母亲;悲剧;命运;历史;父权制度
在《百年孤独》与《丰乳肥臀》中,马尔克斯与莫言分别向读者诠释了他们心目中的母亲形象。作为母亲,乌尔苏拉与上官鲁氏既表现出共同的生儿育女、坚韧顽强、支撑家族命运等光辉与伟大的母性特征,又显示了迥然不同的性格命运,展现了母亲形象的多样性。这种不同的审美范式,值得我们探究其背后的形成机制。
一、不同的性格命运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陶冶。”[1]乌尔苏拉与上官鲁氏辛酸与苦难的一生,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稍加分析,便可见她们二人的悲剧命运有着显然的不同。
首先,她们承受的苦难层次不同。上官鲁氏因三年未育遭受到婆家非人的虐待。她意识到一个畸形的真理,“人活一世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贞洁烈妇,就要挨打,受骂,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种,反倒成了正人君子。”[2]她被逼借种,甚至被败兵轮奸生子。在生下第七个女儿时,上官寿喜这个气疯的孱弱男人,抄起捶衣服的棒槌,打得她头破血流,还“恨恨地跑出去,从铁炉里夹出一块暗红的铁,烙在了妻子双腿之间”。可见她在精神与肉体上遭受到极端的摧残。在第八次生产时,她一个人在濒临死亡的边缘挣扎,全家人都伺候着难产的驴子生产。没有儿子,她的性命还不如一头驴。此外,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上发生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动荡不安的历史斗争中,上官鲁氏成为特定环境下不幸的一员,经历了失去数名亲人的痛苦,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承受着战争带来的死亡威胁。
与此相比,乌尔苏拉在家庭生活中,虽然精神上经历了丈夫、儿女先于她死去的痛苦,经历了子孙放荡不羁、一无所成的悲哀,经历了家族走向衰败的惨淡,但她与丈夫关系和睦、与孩子们关系融洽,未曾遭受到肉体上的暴力侵犯。而且始终乐观积极,依靠她的勤劳智慧,不断积攒财富,为家庭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财富来支撑家族的发展。“她将自己的甜食生意推上新的高峰,不仅在短短几年内挣回了儿子消耗在战争中的资财,还用纯金塞满了一个个葫芦埋在卧室里。‘只要上帝让我活着,’她时常这样说,‘这个净出疯子的家里就缺不了钱。’”[3]她受历史事件冲击的影响也较上官鲁氏为轻。在战争、罢工等动荡的历史下,尽管她内心充满不安与恐惧,担心儿子布恩迪亚上校的安危,但未曾遭受到肉体上的折磨。她基本能偏安家庭一隅,照常打理家庭事务,依旧经营着糖果小动物生意。在阿尔卡蒂奥横行马孔多时,她甚至曾一度管理过马孔多事务,让马孔多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使得当地百姓免受迫害。
其次,对待苦难她们态度不同。上官鲁氏面对封建父权制度和社会历史的冲击影响,表现出被动、消极的一面,其悲剧在于被动接受苦难命运。她如同一头沉默的老牛,以求生的本能艰辛地生存着。年幼,经历了缠足的剧痛;婚后,忍受婆家的虐待;成为家族的主导人物后,依然被动地承受着苦难,不能避免子女们走上党派之争带来的灾难,不能拒绝养育子女们扔给她的外孙,不忍断掉对儿子的哺乳,以致儿子患上恋乳症,直接导致她凭借儿子获得生存地位的希望破灭。
与此相比,乌尔苏拉的悲剧在于主动抗争苦难命运却无法摆脱失败的结局,犹如西西弗斯在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在困境面前,乌尔苏拉显示出积极的抗争精神和决不妥协的态度,她一生坚持与导致家族衰落的罪魁祸首“战争、斗鸡、放荡女人和疯狂举动”[4]作斗争,但最终都不能阻止男人们的昏聩迷狂,不能延续家族的发展。如对于丈夫沉醉科学实验,她由“劝阻不了”到“把观察仪摔在地上打得粉碎”,丈夫仍然陷入了永恒的谵妄状态发了疯;对子孙懒散放荡,她朝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求他们帮她重振家业,但无人响应;对于她一直担忧的乱伦,布恩迪亚家族成员间从未间断,并最终生育出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后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在考虑如何振兴家族,但家族最终被飓风抹去。
二、不同程度的圣母化形象
莫言将旺盛的生殖力和伟大的母爱赋予了饱经苦难的母亲上官鲁氏,但她不同于乌尔苏拉那种圣洁化的圣母形象,她既光辉,又卑劣,是善良与丑恶的结合体。
为了生育出男性继承人而乱伦借种、苟合,她沦为生育的工具。生育谈不上伟大与温情,只是她用来保住自己的家庭地位的手段,并以牺牲其他女性为代价。对于相同的骨肉,她对玉女叹息道:“儿呀,你多余了。”母亲对子女爱的本能被剥夺了,她丧失了母性的自主力量,沦为父权制度的同谋。她竭尽全力养育着这群孩子,促成她们生理上的长大,却无视精神、心理的成长,导致女儿们的自私,导致儿子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阳刚与魄力。对于痴呆的婆婆,上官鲁氏显露了她人性中卑劣、阴暗的心理,她仇恨地报复着婆婆: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面条,婆婆只能眼巴巴地瞧着,饿得受不了了,就自己爬进西厢房,以吞食驴粪蛋儿来充饥;后来又以婆婆啃玉女的耳朵为由残忍地将她打死。上官鲁氏丑陋、粗俗的一面,与传统圣洁化的圣母形象具有一定的距离。
相比之下,乌尔苏拉则是一个光辉的圣母形象,拥有善良、勤劳、坚韧、博大母爱的美好品格,体现出强烈的母性情怀,没有一点污浊性质,她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灵魂。在布恩迪亚这个疯狂的家庭里,她以坚定的意志、勤劳聪慧、善良豁达成为家庭的坚强支柱。她料理家庭事务,扩建家宅,经营动物糖果小生意,为家族成员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尽管她年逾百岁,患白内障几近失明,却仍然活力不减,始终满怀着重振家业的热情。对于孩子们,她理智地教养着,绝不放纵他们的错误,时刻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及时给予心灵的抚慰。在她眼里,次子布恩迪亚是个无力去爱的人,于是他被众人抛弃时及时给予精神安慰;她痛惜女儿们迷狂的爱情,却又能醒悟到阿玛兰坦是世上最温柔的女人,只有丽贝卡才拥有她希望自己的后代具备的品质。她年逾百岁,还时刻关注家人的一举一动,发现了梅梅自主恋爱的隐忧,劝说放荡的奥雷利亚诺第二回归家庭[5]等等。她以高度的责任感引导着布恩迪亚家族的成员成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要求的人。马尔克斯曾说:“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们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推倒历史。”[6]乌尔苏拉就是这样一位拯救世界的圣母形象,演绎了马尔克斯对女性的认识。
三、形成不同性格命运的原因
《百年孤独》和《丰乳肥臀》都以百年动荡历史为依托展现母亲们艰难困苦的一生,两位母亲在苦难悲剧命运、圣母化形象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以下主要探究人物性格命运不同的形成原因。
(一)父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制度差异
两位母亲在家庭生活中苦难命运程度不同,是因父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着制度差异。上官鲁氏苦难命运的形成在于封建中国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极端压制。在中国父权制度下,女性是丈夫的附庸,被剥夺了个人主体价值和存在权利,并在心理认知上形成了以男性为主体身份的客体认同。因此,她以“三从四德”中的“孝德”顺从婆婆的虐待,以“三从四德”中的“从夫”来忍受丈夫的凌辱,以“无后为大”中的“生儿育女”被逼接种来承受无尊严的生存。生活的残酷使她认识到一个女人的命运:“女人,不出嫁不行,出了嫁不生孩子不行,光生女孩也不行,要想在家庭中取得地位,必须生儿子。”[7]她以完成制度赋予的使命——孕育男性继承人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不惜割裂灵肉借种生子。作者以上官鲁氏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的命运,揭示了封建文化压抑下女性的悲剧,具有普遍性意义。
乌尔苏拉承受的苦难不如上官鲁氏深重,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西方社会具有与父权制度抗衡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教义规定了“男尊女卑”,同时又赋予了所有人平等的尊重和自由。基督教文化对父权制度存在一种强大的抗衡力量,使之呈现出不同于中国的特点。首先,西方并不强调子嗣的问题,“没有子嗣并不能导致夫妻离异,因为西方婚姻具有接受上帝看护的神圣性,生育子女在宗教教义上被视为上帝对女性原罪的惩罚,所以子嗣观念远不如中国文化中的那么根深蒂固。”[8]因此,乌尔苏拉在生育子女上没有遭受严重的肉体戕害。其次,在基督教的婚姻观中,婚姻是创造宇宙的主宰神所设立的,婚姻具有神圣性。同时视婚姻为盟约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因此,乌尔苏拉在婚姻生活中未曾遭受丈夫的欺凌,甚至她还成功阻止过丈夫的迁徙决定。第三,与中国女性卑从的多重对象不同,西方女性卑从的对象只有男性上帝和丈夫。因此,乌尔苏拉只要在家庭生活中顺从丈夫,便不会遭到更多对象如母亲、婆婆等人的压制。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女性经济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她们婚后对自己的嫁妆和财产享有所有权,而且在丈夫去世后,还能获得自己财产的支配权。这保证了女性不被完全财产化和剥夺作为人的权力。因此,乌尔苏拉凭借经营小生意,既保证了自己和家族几代人的物质生活,避免了物质匮乏带来的灾难,又能在家庭中具有一定的主导能力和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价值与才能,不至于被完全物化和失去人的尊严。
(二)作者对人物悲剧命运审视的不同视角
中国封建父权制度下,上官鲁氏的一生除了生殖和养育,没有任何主体价值及独立人格,因此她无力反抗任何苦难,既没法选择自己的人生,也无力掌握子女对各自命运的选择,仅以求生的顽强意志被动接受命运的桎梏。作者通过她被动顺从的悲剧命运意在揭露封建父权制度给妇女造成的不幸与灾难。她的一生都被男性继承人控制,并以此来获得生存的意义,显示其存在的价值。但儿子的窝囊无能使得她倾尽一生的希望破灭,这也寓示着她个人价值的消亡。上官鲁氏被动接受苦难的命运是作者对父权制度迫害女性的呼吁、控诉与同情。同时作者以上官鲁氏的悲剧命运反映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艰难历程及选择历程中国家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意在揭示社会历史变化对人产生的重大影响,影射那个年代古旧乡村里普通人的悲苦命运。
乌尔苏拉积极拯救家族失败的悲剧命运是作者对拉美民族孤独百年命运结局的影射,具有深厚的意蕴。十八世纪以来的拉丁美洲,经历了殖民入侵、独立革命、频繁内战、政权更迭、工人罢工等社会动荡。“布恩迪亚家族及马孔多很大程度上是哥伦比亚的缩影,它的生活现实反映了整个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生活现实,有着深远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9]布恩迪亚家族中只有乌尔苏拉理智清醒,她竭力阻止家族成员身上的偏执、纵欲、孤独,但布恩迪亚家族的人缺乏爱的能力,醉心孤独、缺乏团结、放纵行乐、固步自封、抗拒文明,作者意在说明单靠个人力量是无法与命运抗争的。通过她与布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命运的紧密连接,影射了拉丁美洲民族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困境,抨击充满战争、冷漠、孤独、因循守旧的拉美历史和现状,从而引起人们对拉美民族命运的关注。
(三)作者对女性不平等性别角色与地位的不同认识
在拉丁美洲文化中,女性“必须是纯洁的伴侣和神圣的母亲,她必须是属于家庭的、忘我的,永远将丈夫和孩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的,她必须是充满牺牲和奉献精神,逆来顺受的。”[10]乌尔苏拉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母亲,她具备一切美德,毫无瑕疵。她一生囿限于家庭事务中,并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掌控力,试图以拯救家族的没落来维护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平衡。马尔克斯说:“如果女人不留下来支撑家庭,男人就不知所措。男人之所以能离开家去做事,因为他知道回来的时候家里一切如故。”[11]乌尔苏拉是马尔克斯以父权制度为基础构建的一个圣母化形象,履行着传统文化赋予她的母亲职责,通过“圣母形象”使其生命形态呈现于世。马尔克斯说:“乌尔苏拉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我描绘的女人的楷模。”[12]这鲜明地表现了马尔克斯对女性不平等的性别角色与地位的认同,赞美和尊崇父权制度定义下的母亲形象,无意识地张扬了作者的男性中心文化意识。但这个被理想化、制度化的形象凌驾于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及母亲的自身体验,不可能全然体现她潜在的心灵感受。
非圣母形象的上官鲁氏,显示了作者对父权制度下女性不平等的性别角色与地位深刻的批判意识。他以上官鲁氏的卑劣、污浊等性格特点来批判封建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制、对人性和亲情的扭曲,这体现了莫言女性主义的一面。莫言说:“我的小说中的这个母亲形象,首先是被逼无奈,她要活下去,就必须走这条路,在家庭里面取得地位也必须走这样的路。”[13]正是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造就了这样一位具有道德瑕疵的母亲。莫言更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生活中母亲的生命状态,深入触及母亲人性中的复杂性。虽然上官鲁氏不是纯粹的大母神,但我们难以一味地指责,更多地报之以同情。“圣洁的母爱是美好的,畸变的母爱也与善恶、美丑无关,畸形、变态后的母亲,依然是人,依然是人世无数无痛无泪的并不崇高的悲剧中的一幕。”[14]
参考文献
[1] 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56.
[2] [7]莫言.莫言自选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433,427.
[3] [4][5]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131,168,169.
[6] [12]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10,21.
[8] 王影君.中西文化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J].武陵学刊,2011,36(2):122-127.
[9] 刘长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与“魔幻现实主义”[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6):74-79.
[10] 金灿.现代“圣母玛利亚”——中国女学者眼中的拉美女性[EB/OL].(2012-03-12)[2015-12-10].http://world.people.com.cn/GB/17361927.html.
[11] 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M].朱景东,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00.
[13] 莫言,刘琛.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莫言先生文学访谈录[J].东岳论丛,2012,33(10):5-10,2.
[14] 徐绍峰.颠覆与重写——新时期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变异原因与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2):63-70.
[责任编辑、校对:梁春燕]
收稿日期:2015-12-18
作者简介:张盛春(1979-),女,四川广安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33(2016)04-0067-04
Writing of Mother's F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rnity——Comparison of Mother Images inOneHundredYearsofSolitudeandWomenofChina
ZHANGSheng-chun
(Teach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Courses,Sichuan Vocation College of Art,Chengdu 611131,China)
Abstract:The two mothers Ursula and Shangguan Lu not only express the same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brilliance and greatness,but also embody the deep differences of tragic fate.The form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differences of patriarchy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the writer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viewing tragic fates of characters,and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women's unequal roles and positions.
Key words:mother;tragedy;fate;history;patri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