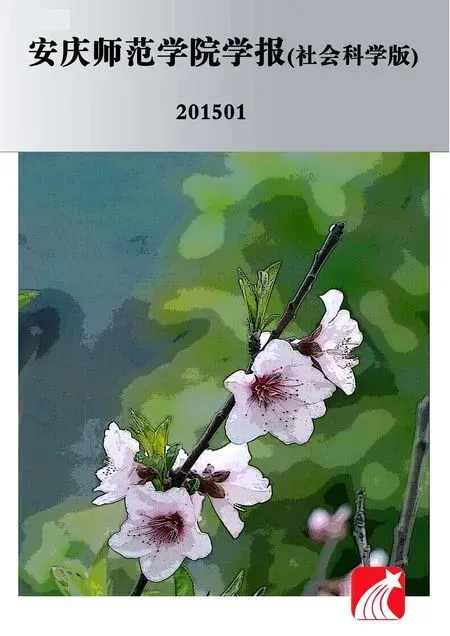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2015-12-17何承斌
何 承 斌
(安庆师范学院图书馆, 安徽 安庆 246133;安徽大学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何 承 斌
(安庆师范学院图书馆,安徽安庆246133;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遗嘱信托作为一种处理遗产的方式,在世界各国或地区广泛使用且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未能在我国得以实践及发展,其中立法滞后是其主要制约因素。遗嘱信托制度在我国有效运用的当务之急是完善立法,以明确信托成立要件、确定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限制财产存续期间等法律关系。
关键词:信托法;遗嘱信托;继承法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1.006
遗嘱信托是指身为委托人的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自己的财产权转移至受托人名下,由受托人依信托本旨,在委托人死亡后为遗嘱中所定受益人或其他特定目的管理及处分该财产[1]。遗嘱信托在世界各国或地区被长期而广泛地运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然而,遗嘱信托在国内无论是立法还是实务都裹足不前,已不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遗产规划需求。我们应当对遗嘱信托法律制度进行重新反思,让这一重要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其价值。本文将在梳理现实中的遗嘱信托立法层面的诸多问题以及借鉴世界发达国家遗嘱信托立法的基础上,尝试对遗嘱信托制度进行反思与重构。
一、 遗嘱信托立法评析与设计
遗嘱信托制度运用比较好的国家一般都有比较完备的立法,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尽管2001年我国相继颁布了《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法》以及2002年出台了《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结束了我国信托业务无章可循的局面。但对于遗嘱信托,可以说一直处于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状态,《继承法》没有涉及,而《信托法》仅有第 8 条和第13 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且与《民法》及《继承法》发生多处矛盾冲突,现有的立法无法构建遗嘱信托制度化的法律框架。
我国《信托法》开始实施至今已经十余年,规制的重点在于商事信托,制度设计上较多地体现商法特点,对遗嘱信托规定简单、零散,缺乏适用性、系统化的制度设计。虽然遗嘱信托兼具信托和遗嘱双重属性,但遗嘱属性更强于其信托属性,因为《信托法》是对信托制度中最为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规定,遗嘱信托是信托制度在家庭法领域的发展与体现,天然地与继承和《继承法》联系紧密,更多地体现出继承的规律和特点,可以说,遗嘱信托是公开化的继承。《继承法》作为全面规定继承制度的基本法,不可能对遗嘱信托这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继承方式视而不见,否则必然成为重大的法律空白。
我国《继承法》1985年颁布至今已近三十年的历史,实施时间长,适用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有些法律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果未来在《继承法》修改时,增加一章单独规定遗嘱信托制度,则不仅使《继承法》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而且较之《信托法》,在《继承法》中规定遗嘱信托制度更有针对性,也更有影响力,也更加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将会对我国民事信托事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遗嘱信托作为信托制度的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其设立、运行必须遵循《信托法》的规定,实现《继承法》和《信托法》关于遗嘱信托规定的协调和衔接,促进遗嘱信托制度的有效运用。
二、成立要件的缺陷与修正
我国《信托法》第8条规定,采用遗嘱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对于立法为何规定设立遗嘱信托须待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对信托达成合意才成立,有些学者认为,如果遗嘱信托的成立不需要受托人的承诺,可能出现委托人随意给受托人设立义务而损害受托人的权益,因而应当赋予受托人选择权利,否则有违公平原则。尽管这条规定从表面上看尊重了受托人的意志自由,但是这降低了遗嘱信托的工具性价值,存在着明显缺陷:(1)不符合遗嘱信托的性质。遗嘱信托须待委托人与受托人达成合意才能够成立,从性质上肯定遗嘱信托为双方法律行为,完全忽视了传统信托法上将信托设立行为视为单方法律行为的法理。英美衡平法有句格言:衡平法院不会使因受托人缺乏而失效[2]。多数国家的信托法都有类似规定。如韩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信托可根据委托者的遗嘱,或者委托者与受托者签订的契约而设立”[3]。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都规定并不以受托人承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为信托的成立要件。我国《继承法》也规定遗嘱成立仅凭立遗嘱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无须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或者承诺。(2)不利于实现委托人的真实意愿。遗嘱信托充分展示了委托人处置自己遗产的自由品格,更多体现了遗嘱信托设立的目的和价值。如果以受托人是否接受信托为成立条件,则意味着在没有受托人接受的情况下,遗嘱信托将不会成立,委托人的遗产将要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分配,致使其遗产仍为其他继承人所得,则其对遗产进行的处分或安排就会落空,甚而遗嘱继承的效力也被否定。仅因受托人不做出承诺而致使遗嘱信托不成立,显然违背了委托人的真实意愿。(3)导致《信托法》内部法条的逻辑悖论。《信托法》第 13条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受托人由受益人另行选任。根据第 8 条规定推知,因受托人拒绝或无能力接受信托而没有做出承诺致使遗嘱信托无法成立,信托受益人尚不存在,如此又何来受益人对受托人的另行选任呢?
我国《信托法》对于仅在受托人承诺时遗嘱信托才能够成立的规定,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无法衔接,不仅有违信托法理, 还会造成一系列的混乱及矛盾,也不利于委托人意志的实现及受益人利益的维护。鉴于此,我国信托法应该明确遗嘱信托的单方法律行为性质,使信托不需受托人的承诺即可成立。考虑到遗嘱信托的特殊情况,在其成立问题上应适用特殊的规则,即立遗嘱人死亡、遗嘱生效时,遗嘱信托成立,并不受被指定的受托人拒绝或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影响。如果被指定的受托人最终没有或者不能担任受托人,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受托人。
三、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的困境与定位
我国《信托法》第 2 条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自己的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管理及处分该财产的行为。其中“委托给”用语模糊不清,语焉不详,对于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说,“委托给”着重点在于委托而不说明财产权转移;还有人说,“委托给”既然有“给”,那说明财产权转移确是各取所需的。对信托财产所有权的权属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英国为代表的“双重所有权”模式,将信托财产所有权分割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前者为受托人所有,后者为受益人所有,受益人所享有的是最终性、实质上的所有权,这是为了减少受托人取得了受托财产却不履行受托义务以致损害受益人的利益。另一种以日本为代表的所有权转移模式,日本属于大陆法系,承受罗马法“一物一权”观念,强调财产的单一所有权,在移植信托制度过程中,一般规定受托人享有财产所有权。 如日本和韩国两个大陆法系国家均在其《信托法》中规定,信托是将财产权转移或为其它处理行为,并使他人依照一定目的进行财产管理或处理[4]。这里使用的“转移” 而非“委托”,意思清晰明确,信托关系成立后,受托人取得了财产所有权。反观我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容易产生歧义的在于“委托”二字,给信托财产的权属带来不明确性。为此,负责起草《信托法》的江平教授还做了专门解释,他指出《信托法》使用“委托”二字旨在使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能得到兼顾,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享有完全支配权,同时,受益人对于信托财产所获利益的享有能够得到保障,偏颇某一方都与信托本旨相违背[5]。但是在立法中这种模糊写法,是否能真正实现对受益人的保护呢?不管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是立法明确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以实现对受益人的保护,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的权属是信托关系的基石,应在立法中明确所有权归属。尽管“双重所有权”结构在英美法系适用得非常完善,但是大陆法系国家没有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二元分野,英美法系的“双重所有权”在大陆法系“单一所有权”体系中无法找到合适的定位,因而简单直接套用“双重所有权”来解决大陆法系国家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实不可行。我国也属于大陆法系国家,难以移植英美法系的“双重所有权”制度,因此在立法中应该借鉴日本等国的做法,可以在立法中将“委托”修改为“转移”,明确将信托财产所有权赋予受托人,充分调动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积极性,使得委托人的意愿得以有效实现。同时为受托人规定严密的义务体系来实现对受益人的保护,诸如规定受托人的忠实义务、谨慎义务和管理义务以及造成财产损失而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外,可以将债权人的撤销权扩充给受益人,增加受益人权利受到受托人侵害的救济权。
四、信托财产公示规定的不足与替代
我国《信托法》第10条规定,以应当办理信托登记的财产设立信托,应当办理信托登记,不登记该信托不产生效力。法律规定信托财产登记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财产的公示来保护善意第三人,从而实现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的功能。但是,制度设计达致良好愿望的前提是制度本身能够得以有效运行。我国《信托法》对于信托登记效力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使得遗嘱信托的生效处于尴尬的境地,致使遗嘱信托制度难以正常运转。首先,第10条仅规定了要登记,却没有规定申请登记者为何人。若为委托人,由于遗嘱信托是死因行为,委托人死亡后才生效,既然委托人已经死亡,又如何完成变更登记?委托人在生前进行信托财产登记,依据尚未生效的遗嘱去设立遗嘱信托当然就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若为委托人托付受托人待遗嘱生效时办理登记,那么根据《信托法》第10条的规定,该信托协议因未完成登记而没有生效,当受托人以尚未生效的信托协议申请办理信托财产登记,会陷入委托人生前办理登记时同样的困境。若为继承人,继承人能否履行登记仍是问题,继承人拒绝履行时,受益人的利益仍旧得不到保障。其次,即便登记生效,动产等不须登记的财产仍旧缺少公示性。
信托公示的目的在于使第三人对于信托财产存有受益负担的事实,有所知悉或者有知悉的可能,从而能客观考量交易的利益和风险,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害。虽然登记生效主义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当事人和信托财产的安全,但是它忽略了信托的自由和效率的法律价值。大陆法系的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对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设立的信托,非经登记或注册,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6]登记对抗主义只是影响信托的外部关系,即信托关系人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并不影响到信托的内部关系,对信托本身的成立与生效没有影响,对信托当事人仍然具有法律拘束力,这符合遗嘱信托的私法性质。比较而言,我国采取的登记生效主义实属过于严格,毕竟不同的信托公示的公示方式和价值目标都具有二重性,它不仅要考虑信托外部关系中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对信托内部关系中的当事人,尤其是受益人利益的保护问题。兼顾第三人与受益人两者之间利益,对信托公示的效力的规定,采取登记对抗的模式最为恰当。即将第 10 条改为: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五、财产存续期间限制的缺失与补全
我国《信托法》第51条规定信托终止的6种法定情形,如信托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信托当事人协商同意、信托被解除等,但都没有给予存续期间的限制。诚如有学者所说,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一国法律范围内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是信托制度具有的独特品性,“将个人处分财产的自由权扩展至最大”就是遗嘱信托制度的核心理念[7]。因而遗嘱信托制度在英国被形象地称为“从坟墓中伸出的手”,正是因为这项制度可以保证被继承人对其财产处分的个人意志在死后仍能被继续执行贯彻。但如果任凭遗嘱信托“这只手” 无期限控制财产流转,就会出现死人操控活人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从而对社会和谐与安定形成持久不利影响。
“信托法试图在个人原创力之张扬与国家公权力之贯彻两极间寻求冲突的平衡点,以降低信托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冲击。”[8]为此,英美判例法国家通过“禁止永续原则(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对委托人三大自由进行了合理的限制, 即禁止财产过分自由流通、强制财产持续累积、控制财产未来归属的自由,达到强行信托终止的结果,从而在财产处理方面实现了个人意志自由与社会整体意志之间的有效平衡。美国在其《信托法重述》(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Trusts)中也限定遗嘱信托持续的最高期限为受益人一生加上其死后 21 年,“权益价值确定的最后期限,必须限制在该权益设立人终其一生及其死后21 年内,超过此期限的权益没有价值拘束力”[9]。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遗嘱信托存续时间做具体规定,不利于促进财产的流转,也容易引发财产无限膨胀带来的财富两极分化。因此,建议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经验,遗嘱信托存续时间限定在信托设立时存活的受益人的一生加上21年。
结语
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名著《政府论》(下篇)中高呼道:“对人民自由地追求其正当利益应给予充分保护和有效帮助,而不是对人民的利益横加限制,这是政府建立法律制度真正意义之所在。”[10]审视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律制度,被继承人对遗产规划的自由需求因过多的强行性规定而受到抑制。遗嘱信托制度在遗产处理方面给予了被继承人更加多样化的选择,契合了时代需求。但遗嘱信托在我国仅被法律“提及”,却未被实际运用。因此,梳理我国现行遗嘱信托制度缺漏之处并加以具体构建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李礼仲.信托法规[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2006:49.
[2] 何宝玉.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72.
[3] 赖源河,王志诚.现代信托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7 .
[4] 丁雪娇.论信托财产的归属[J].法制博览,2013(1):89-91.
[5]于海涌.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3.
[6]日本信托法[EB/OL].(2010-11-20)[2014-3-25].http://wenku.baidu.com/view/c4ab95ce050876323112
1218.html.
[7] 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35 .
[8] 张天民.失去平衡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11.
[9] (美)约翰·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M].钟书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9.
[10]秦绪娜.洛克有限政理论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建设的启示[J].成人高教学刊,2009(3):21-26.
责任编校:汪沛
网络出版时间:2015-03-02 2:51:25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302.0952.006.html
Reflection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estamentary Trust in China
HE Cheng-bin
(School of Law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011, Anhui, China)
Abstract:Testamentary trust as a way of heritagetreatment iswidely used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a positive social effect, but it lacks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Delay of legislation is the main restricting factor.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for testamentary trust system for its effective use in China so that the established elements can be made explicitly, the trust property ownership can be determined, and the length of property duration can be limited.
Key words:trust law; testamentary trust; inheritance act
中图分类号:D922.282;D9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1-0024-04
收稿日期:2014-04-15
作者简介:何承斌,男,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安徽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