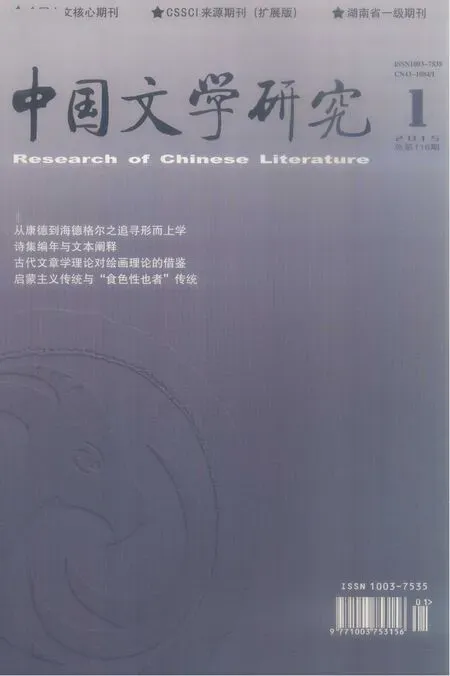生存困境与情感救赎——李泽厚“情本体论”探析
2015-11-14牟方磊
牟方磊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情本体论”是李泽厚近20 年来思想的重心所在。李泽厚虽然在著作中反复言及“情本体”,但他并未做系统集中的理论阐发,比较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亦嫌不足,这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所以梳理“情本体论”的线索、把握其体系、挖掘其内涵、阐发其意义便很有必要。本文不准备全面阐释“情本体论”的各个方面,而只关注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一是“情本体论”的现实针对性;二是“情本体论”的内涵;三是本体之情的类型与性质。
一、“情本体论”的现实针对性
李泽厚之所以提出“情本体论”,是出于对现代人生存意义匮乏问题的关注。
重视现代人生存意义匮乏问题,希望通过审美(情感)来解决,是上世纪70 年代末迄今李泽厚美学思想发展的主要走向。
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中,李泽厚在阐述“主体性”(包括“工艺—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层面)思想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意义匮乏的问题。李泽厚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基础上,人类改造世界的“工艺—社会结构”已极为突出,但社会、科技对个人的控制、奴役则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代语境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的地位、作用、意义和独特性、创造性、多样性、丰富性等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现代西方悲观主义哲学(主要指存在主义)“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体之间巨大矛盾和分裂”,要求从失去了个体存在意义的社会总体中挣脱出来,追求免除异化、寻求生命的真实价值亦即个体存在的丰富意义。这一问题与“文化—心理结构”密切相关,而其中的审美尤显重要,审美与“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认识和伦理不同:作为理性内化的“认识”和作为理性凝聚的“伦理”都是总体社会理性对于自然个体感性的支配,科技和道德最集中地体现了此种理性,它们极易造成个体的被压抑、被漠视以及个体的小我被淹没在总体的大我中。而在作为理性积淀的“审美”中,总体社会理性已经融化、渗透、落实在自然个体感性之中,这种“积淀了理性的感性”不仅是美的本质,同时也是人的本质,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紧密相联,审美问题成为解决总体、社会、理性与个体、自然和感性之间矛盾的关键。
《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1980)从人类主体性角度谈认识论,从个人主体性角度谈伦理学和美学。在此文第三部分,李泽厚认为康德在某些方面比黑格尔高明,康德看到了认识论不能穷尽哲学。存在主义不谈认识论,无害其为哲学,因为个人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也是哲学的重要主题。在第四部分,李泽厚对审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峰巅;从哲学上说,这是主体性的问题,从科学上说,这是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却愈来愈迫切而突出,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寂寞、孤独和无聊,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的严重课题。”
《批判》与《论纲》主要关注人类主体性,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心理结构”,但另一方面,李泽厚注意到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意义之匮乏,并且认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审美”(情感)是解决此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为“情本体论”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1983)中,李泽厚拓展了“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性”包括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
第一个“双重”是:它具有外在的即工艺一社会的结构面和内在的即文化一心理的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它具有人类群体(又可区分为不同社会、时代、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等)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
他对人类和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内部构成了辨析:
这种主体性的人性结构就是“理性的内化”(智力结构),“理性的凝聚”(意志结构)和“理性的积淀”(审美结构)。它们作为普遍形式是人类群体超生物族类的确证。它们落实在个体心理上,却是以创造性的心理功能而不断开拓和丰富自身而成为“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感受”(审美快乐)。普遍心理的结构形式和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便是人性主体性所要探究的基本课题。
在此,虽然李泽厚强调“普遍心理的结构形式和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是《论纲》和此文的主题,但其论述重点显然是后者。由人类主体性到个人主体性,由普遍心理的结构形式到个体心理的创造功能,由人性的历史积淀到人性的自由生成,可看作是从《批判》到《论纲》到此文的主要思想发展趋向。由此文对“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感受”(审美快乐)的阐述,对“审美”在个人心理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可以看出,心理美感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心理情感本体”已呼之欲出。
在《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1985 年)中,李泽厚明确提出“心理本体”和“情感本体”概念。他认为在现代社会语境下,要想消除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各种异化,提出文化—心理结构即人性建设的工作才是重要的。人性即是心理本体,其中又特别是情感本体。此本体是人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科学地探究此本体的历史起源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但这一切都不能解决现代人深切感受的个体自身的存在意义问题”。“个体自身的存在意义问题”只能由个体在实际生存中来解决,其中的关键即是个体自由地参与构建心理情感本体。
在《美学四讲》(1988)中,李泽厚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文化心理问题愈来愈显得重要,所以寻找、发现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如何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自觉塑造能与异常发达了的外在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人类心理本体,将教育学、美学推向前沿,这即是今日哲学和美学的任务,参与构建自己的心理情感本体可以成为个体生存意义的来源。
在《第四提纲》(1989)中,李泽厚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再次阐述了他的“双本体”观。在他看来,“如何活”关涉“工具本体“,“为什么活”关涉“心理本体”。在“如何活”大体已经或快要不成问题时,应该提出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的问题。“为什么活”不应该脱离“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情感本体”也只能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得以构建,即“‘为什么活’、活的意义诞生在‘如何活’的行程之中”。
《哲学探寻录》一文(1994)从“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出发,重点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1)如何活:人类主体性(2)为什么活:个人主体性(3)活得怎样: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第一个问题与“工具本体”相关,第二、三问题与“情本体”相关。人为什么活,需要自己去寻找、去发现、去选择、去决定,“活”或“不活”的意义都由人自己去建构。重建理性形而上学与纵情声色都不能成为经过后现代思想洗礼的当代人的生活意义来源,在没有人格神、没有本体现象两分的中国,只有提倡“情感本体论”,提倡“审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神学”,才能使个体人生寻找到某种皈依、归宿。
在《历史本体论》(2001)中,李泽厚认为只有“心理”才能成为人所诗意栖居的家园。“人活着”产生出它,它却日渐成为“人活着”的根本。“人活着”不仅是个生理事实,更是心理事实,在肉体存活之外,还有“我意识我活着”。而“我意识”不只是思想,而是包括全部感情、感觉等等在内的心理整体。从这一意义上说,“活”是非常具体的,人就是活在“情”中,活在对各式各样的“情感、情况、情境”的认同之中,这种“心理情感认同”成为“人活着”的依托、归宿所在。
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的下篇,李泽厚认为“情本体”是“乐感文化”的核心,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在中西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以道德理性为人生根本。李泽厚承认道德理性对于确证人性的意义,但他不认同“道德理性是人(人生、生活)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地”的观点,这种观点以宗教传统(两个世界)为立论背景,它在西方说得通,但在中国,“由于没有宗教传统和‘上帝’背景,中国的乐感文化和承续它的历史本体论便并不以道德—宗教作为人的最高目的和人生最高境地”,而是以理欲交融的“情”为根本,即“以普普通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际感情为‘本’为‘体’”。
在《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 年谈话录》(2012)中,李泽厚曾谈到“‘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情本体”内推为“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外推就是“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外推的关键是“两德论”(“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与“儒法互用”,内推则主要关注“现代人深切感受的个体自身的存在意义问题”。
可见,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出于对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意义匮乏问题的关注。在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人类主体已日益突出,但在科技工业大发展、物质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同时,个体生存却出现了异化状况:社会总体和科学技术对个体的控制、奴役,使得个体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与情感,而正面幸福的存在感却极度缺乏。这种异化状况亟需某种解决办法。针对现代人这种异化生存状况,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论”:不是“理”也不是“欲”,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情”能够为现代个体生存提供意义之源。“情本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情本体论”的内涵
出于对现代人生存意义匮乏问题的关注,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论”,希望从“情感”这一要素入手,为现代人构建某种生存意义之源。
从“人活着”(生存)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李泽厚将“个人主体性”(包括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思想组织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哲学探寻录》(1994)中,他提出著名的“三活”:“如何活”、“为什么活”与“活得怎样”。落实到个体生存层面,“如何活”关乎肉体、工具;“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则关乎心理、情感。“活着”不仅是肉体事实,更是心理事实。“情本体”从“人活着”这一心理事实角度立论,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之本体,即以“情感”作为“人活着”的归宿与最高境地。
“情感”之所以能够成为本体,首先在于“情”是生活(“人活着”)的主要内容。在强调人肉体存活(生理事实)的基础性的同时,李泽厚更重视人的“我意识我活着”(心理事实):
“我意识我活着”不能离开我肉体的存活,但“我意识我活着”确乎又不同于我肉体活着,而且也不能保证复制的我会像我现在如此这般去“我意识我活着”。
之所以被复制的“我”(他)不同于现在的“我”,是因为那个“我”(他)的具体的“活”——衣食住行、做爱睡觉的具体时、空、环境、条件、机遇与我现在具体的“活”并不相同。每个“我”的“活在世上”(being-in-the-world)并不相同。每个人的意识都是不同的,因为人的意识与人所身处的“具体时、空、环境、条件、机遇”密不可分,由“具体时、空、环境、条件、机遇”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即是人“心理存活”的具体内容,“意识”“不只是思想,而是包括全部感情、感觉等等在内的心理整体”,其中又尤以“感情”为最重要。在李泽厚看来,人与世界的各种“情感关系”构成了人之“活着”(心理存活)的主要内容:
人本来就生活在情感—欲望中,佛家希望“不住心”,甚或要消灭掉“七情六欲”,但喜怒哀惧爱恶欲,以及嫉妒、恼恨、骄贪、耻愤、同情、平静、感激……却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常实在且常在的情结、激情、心境。即使那无喜无悲、无怨无爱,不也是一种情境、心绪?它是生物—生理的,却历史地渗透了各各不同的具体人际内容。……它就是人的具体生存。
“情感”是在人心与外物的“感应”中形成的:“情感乃交感而生,是being-in-the-world(活在世上)的一种具体状况”。作为生活内容的“情”不仅包含内在性的“情感”也包含关系性的“情况”:
情者,情感,情况。情感与情况相交叉,就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并具有客观历史性的人与万事万物相处的状态。情况与情感两者交互作用,而成为“人道”。
“人活着”即是活在各种各样的情感、情况之中,情感生于情况,情况渗透着情感,两者“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人活着”的主要内容。
李泽厚将“人活着”区分为“肉体存活”和“我意识我活着”,“我意识我活着”不仅包括思想,也包括感情和感性等整体心理在内,那么,他为何认为“感情”比“思想”或“感性”更重要,更能成为“人活着”的主要内容?
在现代思想语境下,对于人的生活的完满性、充实性而言,“感情”比“思想”“感觉”要更加重要。在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思想之中,“思想”主要依赖人的“理性”,而“感觉”则更多依赖人的“感性”,“理性”与“感性”都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理性”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感性”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应”,主客二分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与世界的原初的、正常的关系,破坏了人的诗性生存状态,使人的生存状况不是沦落成机器式的刻板单调,就是动物式的欲望泛滥。为了反叛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客二分原则,现代西方哲学更多的将关注点转到“感情”,不管是胡塞尔的“直观”,还是柏格森的“直觉”,抑或海德格尔的“诗思”,都主要不是“理性”,也不是“感性”,而是“感情”:“感情”既非人与世界认知关系,也非人与世界的反应关系,而是人与世界的相互感应、共同存在,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本真原初关系。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李泽厚为何认为人与世界的各种“情感关系”构成了人之“活着”(心理存活)的主要内容。
“人活着”的主要内容是“情”(情感、情况),生活的意义与归宿只能在“情”中寻找,即人生的本体是现实生活之“情”而非某种超越现实的抽象本体,这是“情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李泽厚明确表示“情本体”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不同:
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是“情本体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可以做如下解读:“情本体”不是“现象—本体区分”意义上的“本体”。传统意义上的“本体”建立在“现象—本体”区分的基础上,现象是多元、流变、驳杂、虚幻的,本体是单一、凝固、纯净、真实的,现象要受本体的支配,现象虽然显现本体,但这种“显现”是不完全的(“理一万殊”),现象有时还会遮蔽甚至歪曲“本体”(如“假象”),所以有“透过现象见本质”的说法。康德更加极端,他将“现象”和“物自体”截然两分,人类能够认识的只是“现象”,“物自体”则根本不可知。而所谓“知性”提供“形式”,“感性”提供“材料”,更是将“现象”贬低为一堆杂乱无章的“质料”。“现象学”反对康德“认识形式整理认识材料从而决定认识最终结果”的观点,它提出“面向事情本身”口号,凸显“事情”(即“现象”)本身的重要性。依现象学,认识并非主观形式整理客观质料,而是认识者顺应“现象”,所谓“现象”,依海德格尔观点,即“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现象学反对区分、重视现象本身的观点,对后现代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有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反对“现象—本体”之区分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征。与西方文化强调“两个世界”相反(“现象—本体的二分”正是“两个世界”的立论基础),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一个世界”。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本体与现象浑然一体不可区分,落实到现实生存层面,中国人肯定和执着于生命、生活、人生、感性、世界,他们“不舍弃,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有生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本体、道、无限、超越即在此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这也即是说,“‘活’的(生命)意义即在‘活’(生命)本身,它来自此‘活’(生命)。也就是说,‘活的意义’就在这个人生世事中,要在这个人生世事中去寻求。”可见,中国的“一个世界”在根本意义上也是反形而上学的。
“‘情本体’即无本体”的观点,应该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上来考察。“情本体”不是“现象—本体”区分意义上的“本体”,它“是以现象为本”:不是以现象背后的东西为本,而是以现象本身为本。具体到生活上,不是以外在于生活的东西为本,而是以生活本身为本,所以李泽厚极为赞同“生活的意义就在生活本身,而不在他处”(梁漱溟语)的观念。对于个人而言,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情”,所以依李泽厚,生活的意义只能在“情”中:“情”既是人生的归宿(“为什么活”),也是人生的最高境地(“活得怎样”)。
“‘情本体’这一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也是“情本体论”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如何理解?
可以说,正是在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区分、反“狭义形而上学”等观点上,中国传统思想与后现代思想是相通的,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反对“广义形而上学”,这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后现代思想可以接头,这个对接点即是“情本体”。中国的“情本体”可以看作是对思辨理性哲学(“狭义形而上学”)与后现代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双重克服与超越。“人总是要寻求身心的安顿”是所有形而上学的内在心理动因,现代人也同样如此,但是现代人对形而上学的内在需求(寻求确定、整体、依靠)与后现代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彻底拒绝(崇尚不确定、碎片、流浪)之间却出现了矛盾。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洗礼”,现代人不可能再次回归传统形而上学的怀抱,但后现代思想又无法为现代人提供心灵的安居之所。新的生活哲学既要克服二者之失,又要吸收二者之长。现实生活中的“情”恰能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现实之“情”是多元、丰富、不确定、流变不息的,这些正是后现代思想之钟情所在;另一方面,现代人又可以在这种多元、丰富、不确定、流变不息的现实之“情”中安顿心灵,它可以代替传统形而上学发挥作用。“情本体论”已不是“狭义形而上学”,而是浸透了后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广义形而上学”,“‘情本体’这一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即此之谓也;这种“广义形而上学”“要求于有限中求无限,即实在处得超越,在人世间获道体””,所以说“它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李泽厚将这种“广义形而上学”称为“审美形而上学”:“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
三、本体之情的类型与性质
那么,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感”都能成为“本体”?这便涉及到“本体之情是何种情”即本体之情的类型与性质问题,这也是理解“情本体论”的一个关键点。
在《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1985)中,李泽厚最早谈到本体之“情”的类型:具有人生境界的人性感情;艺术创造与欣赏中的情感;“爱情、故园情、人际温暖、家的追求”等世俗情感。在《哲学探寻录》(1994)中,他认为本体之“情”既“可以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人际经验的肯定性的感受、体验、领悟、珍惜、回味和省视,也可以表现为一己身心与自然、宇宙相沟通、交流、融解、认同、合一的神秘经验。”前者是世俗情,后者则是宗教情。他还将这两类情感做了更细的划分:
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皈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
在《论语今读》(1998)、《历史本体论》(2002)等著作中,他将这两种情感总结为“七情正,天人乐”。所谓“七情正”,在中国古代就是指由“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所规制的人“弗学而能”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从而使“七情”成为“人情”。在现代语境下,李泽厚将它们改造为以下七种“人情”:亲情、友情、爱情、人际关系情、乡土家园情、集体奋进情、科学艺术情。所谓“天人乐”是指“天人交会的神秘经验”,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愉悦、宁静的审美感情、“天地境界”。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2004)中,他所论及的本体之“情”也不外世俗人间情与宗教神秘情两类。在《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2008)中,他主要谈的是“天人乐”,即“人与天(神)合一的平和、恬淡、宁静”,也即“悦志悦神”的最高审美情感。在“人与天道(神道)的沟通合一”这一点上,这种最高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是相通的,它在没有人格神传统的中国可以起到宗教的救赎作用,“美育代宗教”即此之谓。
可见,李泽厚所言的本体之情主要有世俗人间情与审美宗教情两种,即“七情正,天人乐”。由“正”“乐”可以看出,这两类情感具有两个共性:第一,它们都是肯定性情感;第二,它们都是中正之情。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李泽厚所认定的本体之情是正面、积极、平宁、愉悦之情而非负面、消极、激荡、痛苦之情。李泽厚之所以做如此认定,在我看来,其原因如下:
首先,从思想资源来看,李泽厚主要借重的是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依李泽厚,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中国是“乐感文化”。“罪感文化”以“两个世界”为立论根基,它轻此世此生重来世来生。“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为观念基础,它不去构想天国、来世,而是特别看重此世此生此情此境,“重生”“庆生”“乐生”正是“乐感文化”之特征。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孔颜乐处”等等,都是“乐感文化”的突出表现。但是这诸种“乐”并非放纵之“乐”,而是中和之“乐”,是某种“持续的情感、心境、mood,平宁淡远,无适无莫”。李泽厚承继“乐感文化”传统,认定本体之情是正面、积极、平宁、愉悦的,便不难理解。但同时,也应看到,李泽厚也注意到了“乐感文化”之不足,在《历史本体论》(2002)中,他说:
中国人更满足于天人合一式的肉体和心灵的大团圆,重视的是愉悦、宁静。……“天行健”“人性善”容易漠视人世苦难和心灵罪恶,沉沦在大团圆的世俗,从诗文到哲学,中国都缺乏那种对极端畏惧、极端神圣和罪恶感的深度探索。
李泽厚之所以要以“情本体”填充海德格尔的Being,一方面是他看到了Being 的空洞性与危险性,另一方面,他也是希望以Being 的深刻与力度矫正“乐感文化”本身之不足。
其次,从人生实况来看,只有肯定性的、中正的情感才有利于人正常健康、快乐充实地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说,对于人的生存质量而言,存在感比存在更重要,不过,说前者比后者重要并不意味着要为了前者舍弃后者,相反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情本体”提示人们在实际生存过程中,在重视物质生存基础性(工具本体)之同时,更应重视生存中的感觉、感受、体验、情感(心理本体)。但“存在感”的性质却有所不同,在现代社会,太多的人虽然存在着,却极度缺乏那种正面愉悦的存在感,支配、主宰现代人的心灵的,恰是人与自身、与他人、与外界环境的疏离、背反甚至对抗所引发的负面、痛苦的异化情感,虽然它们也是“存在感”,但对于人的正常健康、快乐充实的生存而言,它们却绝对不能够成为“本体”。人之生存的幸福感、充实感只能来自人对外界环境(包括自身状况)的情感认同,而这样的情感只能是肯定性的、中正的情感。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李泽厚既然提“情本体论”,并且认为人生的主要内容是“情”(情感、情况),这便包含着对于现实情感“全面认同”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定本体之情是正面、积极、平宁、愉悦之情而非负面、消极、激荡、痛苦之情,这“全面认同”和“部分认定”之间是否矛盾?
如上文所言,“情本体”是从“人活着”这一心理事实角度立论的。所谓“情本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情”(情感、情况)是生活之本,即“情”是生活(“人活着”)的主要内容;二是指“情”(情感、体验、心境)是人生之本,即“情”是人生的归宿与最高境地。李泽厚对于人生情感的“全面认同”主要体现于第一个层面,而对于情感的“部分认定”则主要体现于第二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着重点不同:第一个层面着重“情”的关系性,是对现实人生、感性生存的肯定,它所设置的潜在对话方是对此岸感性人生持否定态度的理式本体论或上帝本体论;第二个层面着重的是“情”的体验性,“某些”情感体验对于个体生存具有归宿意义,它所设置的潜在对话方有两个:一是具有片面性的理性本体论或欲望本体论,二是推重负面、消极、激荡、痛苦之情的某些宗教学说。不管是理性本体论、欲望本体论,还是某些宗教学说,其最大缺陷在于它们破坏了人之生存的完整性,李泽厚将“情”界定为理欲的融合,其根本旨归即在于保持人之生存的完整性。一些宗教徒通过自我折磨、肉体受虐来获得精神洗礼、灵魂超脱,李泽厚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提出“以审美代宗教”说,就是希望以更具日常性、更易接受的审美方式来代替宗教,个体可在审美情感体验中获得心灵的归宿与家园。如此看来,李泽厚的“全面认同”和“部分认定”之间并不矛盾,“全面认同”是意欲将个体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拉回现实人生,“部分认定”则是希望个体在现实人生中择取那些可以安顿心灵的人间情感。
与上个问题相关,另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情感并不都是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其产生具有极大的偶发性、随机性,那么,对于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突然涌现的负面情感、情绪,譬如痛苦、焦虑、烦忧、嫉妒、仇恨、怨愤等等,我们又应该如何对待、处理呢?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正面情感如何获得的问题,或者说,“情本体”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在个体生存过程之中?
对于生活在充满大量不确定因素的高风险社会中的人,如何克服负面情感、情绪,获得积极的、温暖的情感、情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对此,李泽厚并未直接谈及,但是联系他的整体思想,这个问题也可得到说明。在“情本体论”中存在着“原发情感”(当下出现的、生糙的经验情感、情绪)和“继发情感”(经过沉淀的心境体验)之分,本体之情并“不等于‘当下的’情感经验,而是那种具有相对恒定性绵延性的情感心境”。“原发情感”并不能担当人生本体的重任,能够成为人生本体归宿的是“继发情感”(经过沉淀的心境体验)。“心境体验”与“当下的”经验情感不同:“当下的”经验情感是流转不息的,心境体验则是相对恒定绵延的;“当下的”经验情感是生糙的、缺乏意蕴的,心境体验则是精致的、饱含意味的;“当下的”经验情感更偏重于感官反应,心境体验则更偏重于心灵体验。可以说,“心境体验”比“经验情感”处于更高层级,它是对“经验情感”的把握、体认、省视与回味。它在性质上介于“情感结构”与“经验情感”之间:既具有“情感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只有相对稳定才能承担起本体职责),又具有“经验情感”的多元性、在体性。在关系上它向内与“情感结构”、向外与“经验情感”相勾连,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为个体切实感受到的审美体验,它可以成为人的有限存在的最终“本体”。
“心境体验”之获得有赖于“时间”,在李泽厚看来,“心境体验”本质上即是一种“时间性情感”。李泽厚很早就注意到时间与情感的本质关联:
如果时间没有情感,那是机械的框架和恒等的苍白;如果情感没有时间,那是动物的本能和生命的虚无。只有期待(未来)、状态(现在)、记忆(过去)集于一身的情感的时间,才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命。
与现实生活、物质生产、概念语言不同,在情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完全溶为整体。
“时间”为“原发情感”向“心境体验”的转变创造了条件。时间创造了距离,距离产生了美,时间抹除“原发情感”与个体的那种原初的实际关联,使个体能够以超脱的心态重新体味、感受“原发情感”,经由时间的悬置、淘洗,“原发情感”(甚至包括痛苦、焦虑、烦忧、嫉妒、仇恨、怨愤等等负面情绪)生成为诗意的“心境体验”,正如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中所咏唱的:“……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时间性情感”是真正的本体之情,与经验情感的当下性不同,“时间性的情感体验”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打破客观的线性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使其失去控制力,通过情感体验,过去(历史)、未来得以进入当下。在情感体验中,过去、未来、现在交融汇聚成一点,凝聚成真正充实饱满的“此在”。
作为“时间性情感”的代表,李泽厚特别看重“珍惜”这种“心境体验”,他曾饱含深情地说:
“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一点也不寻常。即使“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它融化在情感中,也充实了此在。……品味、珍惜、回首这些偶然,凄怆地欢度生的荒谬,珍重自己的情感生存,人就可以“知命”。
在《实践美学短记》(2004、2006)中,他甚至将“珍惜”视为“情本体”的基本范畴:
“情本体”的基本范畴是“珍惜”。……如何通过这个有限人生亦即自己感性生存的偶然、渺小中去抓住无限和真实,“珍惜”便成为必要和充分条件。“情本体”之所以不去追求同质化的心、性、理、气,只确认此生偶在中的千千总总,也就是“珍惜”之故:珍惜此短暂偶在的生命、事件和与此相关的一切,这才有诗意地栖居或栖居的诗意。在李泽厚看来,“珍惜”不仅是回首过去,它是“让过去成为情感进入现在以开拓未来”,它也不仅是情感体验,它也包括实际行动,它是体验与生存的统一,是存在感与存在的统一。这种融过去、现在、未来于一体、融体验与行动于一体的“珍惜”就是人生本体,就是人生归宿:“人能在这里找到‘真实’,找到自由,找到永恒,找到家园,这即是人生本体所在”。正是“珍惜”,使原本是流变、生糙、缺乏意蕴的世俗经验情感借助时间的悬置、心灵的净化,而提升为持续、精致、饱含意味的诗性人生体验,同时,它也使高蹈、超越的宗教性情感充满现实感和人情味,在“珍惜”中,世俗情感获得超越性,宗教情感保有世间性,“七情正”与“天人乐”的内在矛盾在“珍惜”中获得解决,这是真正的“即实在处得超越,在人世间获道体”。
针对现代人生存意义匮乏这一状况,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论”。“情本体论”以肯定个体的现实感性生存为前提,认定某些“情感”(体验、心境)为人生的本体、归宿、家园。“情本体”在根本上说是“无本体”:“情本体”不是“现象—本体”意义上的“本体”,它是以“现实生活现象”为本;“情本体”不是以某种超越的实体为本,而是以多元、流变的现实“情感”为本。正因此,“情本体论”的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它不是“狭义形而上学”,而是“广义形而上学”,也即“审美形而上学”。“本体之情”包括世俗人间情(“七情正”)和宗教审美情(“天人乐”)两种,它们都具有正面、积极、平宁、愉悦的性质,它们不是当下的、原发的经验情感,而是经过沉淀的“心境体验”。“心境体验”之获得有赖“时间”,“心境体验”即是一种“时间性情感”,而作为“时间性情感”的代表,“珍惜”成了“情本体”的核心范畴。可见,由肯定现实感性生存到认定正面、积极、平宁、愉悦之情,再到揭示“心境体验”,直至归宿于“时间性珍惜”,“情本体论”的内在理路便清晰地展露出来。
〔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一版)〔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4〕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二版)〔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年10 月.
〔5〕〔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三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8〕牟方磊.情本体与此在存在——论《历史本体论》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与改造〔J〕. 中国文学研究,2013(1).
〔9〕张文初. 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J〕.文艺争鸣,2011(3).
〔10〕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1〕李泽厚、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年,第114页。
〔12〕牟方磊.李泽厚“情本体论”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3〕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