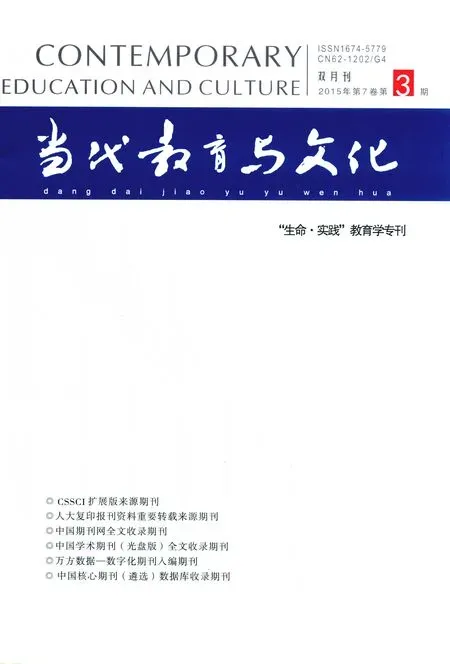“生命·实践”教育学思想的魅力:重新回到赫尔巴特
2015-06-01刘铁芳
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生命·实践”教育学思想的魅力:重新回到赫尔巴特
刘铁芳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新基础教育强调个体育德的整体性,凸显个体成德的文化性、自主性、教育性。新基础教育确实体现了作为学派的努力,在寻求当下教育实践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过程中,力求实现教育目的与方法的统一,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统一,现代视野与民族立场的统一。
新基础教育;“生命·实践”教育学;赫尔巴特;教育学
叶澜老师身上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这种自强不息的德性诉求反过来见证了叶澜老师强旺的生命力量。不仅保持了学术的青春,也保持了生命的青春状态。思考与言说的时候,眼睛发光。教育思考给人带来魅力。思想带来生命的魅力。
“生命·实践”教育学探究让人年轻,让人美。
教育学思想让人年轻,让人美。
贴近生命的思想让人年轻,让人美。
年轻代表着活力,是事实的描述;美是价值的评述。年轻指涉身体,美指涉心灵,文化自信与生命自信的洋溢,切实地认同自我从事的事业以及这种事业中的价值。
彰显金生鈜老师所言的生命成长之好。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意义首先显现为叶澜老师个人生命的美好,或者说叶澜老师个人的生命状态本身就是“生命·实践”教育学魅力的阐释。
一切教育学首先是人的自我教育之学。儿童生命的教育首先是成人生命自我教育的问题。
教育学要让他人生命美好,首先要让我们自己美好。
一、强调个体育德的整体性
所谓学派,中心就是独特的目标与路径的阐释与有机整合。
赫尔巴特以道德的目的统领心理学的方法,来实现教育的整合。以天地人事培育生命自觉,以教天地人事为路径,以生命自觉为目的,体现了目的与路径的充分整合,以生命自觉引领天地人事的教育,重建教育的整体性。实际上是重新回到赫尔巴特,以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
当代教育的难题正是教育的碎片化,我们教授了无数的课程,各种纷繁的知识,但整体上杂乱,缺少内在的整合。“新基础教育”正是试图应对并积极回答这一基本问题。
二、凸显个体成德的文化性
个体道德的形成作为文化习染的过程,其背后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化依据。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梳理出中国教育的基本主题,“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并赋予时代内涵,体现了教育的文化自觉。有人说,我们正在培养的是有知识而无文化的一代新人,技术化的教育留下的只有学了即忘的外在性知识,而缺少文化的印痕。
“新基础教育”针对教育的文化断裂,个体道德之内在文化资源的匮乏。茅于轼提出,个体道德的形成乃是利益的博弈。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但把个体道德归结为利益的博弈,勾销了个体道德的文化依据,降低了道德的文化品行,实际上是人的降格,生命沦为利益博弈的工具。
三、凸显个体成德的自主性
生命自觉融贯在日常生活之中,生命自觉的展开,一是朝向天地场域,提升自我置身天地之间的生命觉悟;一是面对公共生活,立足公共交往促成生命的自我反观。日常生活中的学生自主与民主个性的养成。
如果说传统的天地人事的教育更多地是强调个体体悟,以浩然之气养育自然生命,完成自然生命,是求证于个体内心的天地视域,立足公共生活的生命自觉则是养成公民人格与民主个性,是以公平正义教化社会生命,成全社会生命。“新基础教育”以生命自觉为中轴,融汇两者,现代社会的平等、民主理念,注重学生自主,凸显民主个性。
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天下-国家视域上的生命自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视域。
“新基础教育”回应了民主性格与公民教育的难题,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公民人格融合的问题。
四、凸显个体成德的学科性
重申赫尔巴特教学的教育性问题。早期的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中断言,既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也不存在“无教育的教学”,但后期的赫尔巴特这样说道:“但非一切教学都是教育性的,在这里有必要加以区别。例如,为了收益、为了生计或者出于业余爱好而学习,这时将不关心通过这种学习一个人会变好还是会变坏。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管他的目的是好是坏,或不好不坏,只要他有学习这些或学习那些的意图,对于他来说,那种能准确地、迅速地和吸引人地教给他需要的技巧的教书匠便是一个合适的教师。”赫尔巴特早年从哲学综合的视角提出教学的教育性,以求得教育的完整性。后期则是从现实出发,发现教学的教育性乃是一个问题。现代教育中存在一个基本难题,那就是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的断裂。
我们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正好印证了赫尔巴特后期的感怀,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两张皮,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脱节,在技术化的应试教育体系中勾销了教学之教育性的可能性。
“新基础教育”着力发掘学科育人价值,既是对当下现实教育难题的回应,也是对赫尔巴特教育主题的重新应答。“新基础教育”确实体现了作为学派的努力,在寻求当下教育实践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过程中,力求实现教育目的与方法的统一,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统一,现代视野与民族立场的统一。重新回到赫尔巴特。
五、思考与建议
我们今天的教育确实从整体上并不关心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尽管我们口头上十分关注,但在实际中往往一手软一手硬。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广义的方法)的脱节,教育目的的伦理性与教育方法的技术性,教育目的的品质追求与教育过程的效率追求始终是当下教育的根本性难题。
我们是否可能真正回应晚年赫尔巴特所遭遇的难题?或者说,我们如何可能深层地回应这个现代教育的基本难题,我们的“新基础教育”如何深层次回应这个难题?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从目标层面的归纳与阐释非常清晰,进一步延伸到路径层面的分析,在分析传统路径的合理性与今日教育的变迁的基础上,探索系统的今日教育路径体系。
建议一:话语体系的重建
从“新基础教育”中生长出系统的教育理论话语。期待新版的《教育概论》。整体思考中是否可以强化个体的公民实践: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成公民人格。
建议二:问题扩展的一点建议
学科教学与民主个性问题:研究儿童,特别是当代儿童的特点,他们的道德需求及其可能性。
建议三:期待对社会的教育责任的深度研究
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开放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教育的社会激励,开放的社会空间激励。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一心)
The Glamour of the Thoughts of“Life·Practice”Pedagogy:Returning to Herbart
LIU Tie-f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06,PRC)
New basic education lays emphasis on the integrity in cultivating individuals’ morality,and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cultural nature of,autonomy and scientificity in developing individuals’ morality.New basic educatio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endeavor of an academic school in its pursui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goals and methods,the unif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as well a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modern perspective and national stand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for the integr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new basic education;“Life·Practice”Pedagogy;Herbart;pedagogy
2015-04-28
G 40;G 52
A
1674-5779(2015)03-0066-04
刘铁芳(1969—),男,湖南桃江人。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教育学会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班主任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湖南省教师教育学会学校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