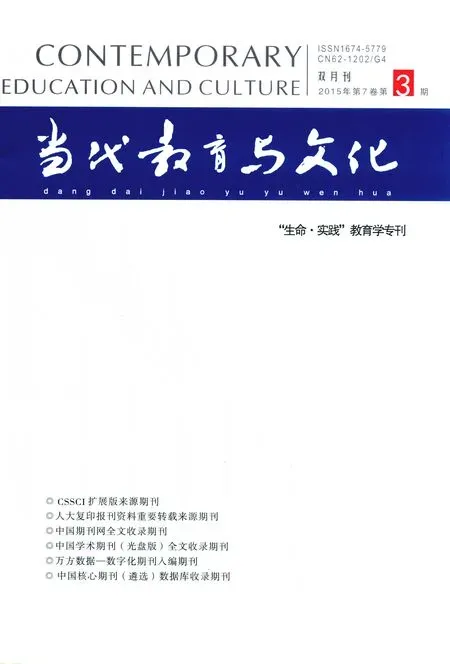论教育研究的“叶澜之路”
2015-06-01王鉴
王 鉴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70)

论教育研究的“叶澜之路”
王 鉴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70)
“生命·实践”教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理论思想,可称之为“生命·实践”教学论,其主要内容包括:课堂教学本质观、课堂教学价值观、课堂教学过程观、课堂教学评价观和课堂中的师生关系等。“生命·实践”教学论是当代中国教学论探索的第三个阶段,它呈现出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生成性与理论体系的归纳性。从方法论上为中国的教育研究探索出了一条独特而富有魅力的“叶澜之路”:探究学术源流、创建理论学派、行走天地人间、独爱冬春夏草。
“生命·实践”教育学;“生命·实践”教学论;叶澜之路
三月份,对我而言,是一个“疯狂的”阅读季节,伴随着西北早春的春暖花开,叶澜老师主编的沉甸甸的三套“生命·实践”教育学丛书摆上了我的书桌,虽然阅读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但对我而言,这么疯狂地阅读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每天早上醒来,想到丛书放在我的案头,心中有一种诱惑力,好像一份香味迷人的早餐摆在那里似的,能让我如此惦记着阅读并放弃睡懒觉的习惯的原因,不只是来自研讨会交给我的任务压力,更主要是来自“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的巨大吸引力。
我对于叶澜老师及其“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的关注历来已久,不仅我关注这一理论学派,而且我推荐给我的同事和我的博士生大量阅读叶澜老师及其同事们的著作与论文。因为我深深地知道,这是当代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成熟且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理论。叶澜老师是研究教育学原理的,但在我看来她也是研究课程与教学的专家,因为她的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学校的课堂教学;另一个是学校的班级管理。所以,教育理论要植根于学校教育的土壤,自然就要研究学校的教学与班组的管理,反过来,通过深入研究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才能洞察教育的最基本的理论。“生命·实践”教育学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研究道路,是在回归突破中不断超越自我的研究道路,我称之为“叶澜之路”,它对我们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人颇有启发意义。因为这是一条学术原创的研究道路,这是一条通过实践变革提升理论质量的学术道路,这也是一条学术研究者成长的道路。我是学教学论专业的,因此,作为学科“内立场”的研究者,我想选择一个相对与我而言熟悉且专业的视角,即教学论的学科视角,来理解叶澜老师所创立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我想从三个方面谈点个人的观点,以求教于大家。
一、教学论的主要内容
这一教学论思想有着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双重基础,教育理论基础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其根本的理论依据是“人学”理论,即“人不仅是发展的主体,而且是影响自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人决定自我的命运,教育应该使人意识到这一点,教人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第6页以下简称《论纲》。)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新基础教育”实验20余年扎根研究。叶澜老师的教学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她的一系列论著之中。其中重要的论文包括:1997年《教育研究》第9期的《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2002年第5期《重建课堂教学价值观》,第10期《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之二》,2003年第8期《改革课堂教学与课堂教学评价改革——“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之三》,2013年在《课程·教材·教法》上发表的《课堂教学过程再认识:功夫重在论外》等。重要的著作包括:“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丛书的“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之基本理论研究丛书”、“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变革丛书”、“合作学校变革丛书”等,尤其是叶澜老师的专著:《新基础教育论》《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报告集》等。叶澜老师的教学论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关于课堂教学的性质,她认为在于其教学目标任务的特殊性,即课堂教学的性质首先是由教育活动的宗旨规定的,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使包括教学在内的一切教育活动有别于人类其他的社会活动,否认这一点就背离了教学的性质。关于课堂教学的价值,她认为应该通过批判传统课堂教学价值而重建,传统的课堂教学价值在于知识的传递方面,重建课堂教学的价值观,即将课堂教学的价值定位于培养能在当代社会中主动健康发展的一代新人,用“主动”一词来形容“健康”,既体现了活动的状态,又内含了主体自觉,还指向了关系事物,且道出了追求期望,表达的是要求个体行为应有利于个体身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向上的指向。关于课堂教学过程观,叶澜老师提出了课堂教学过程必须关注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认识教学过程中不可取代的基本任务?如何认识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失的基本元素及其内在关系结构?如何认识教学过程展开、进行的独特内在逻辑?针对这三个基本问题,她提出了课堂教学的过程观重在对课堂教学基本要素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及其关系的理解与把握。关于课堂教学的评价观,她认为应该将评价改革贯穿于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全过程,形成一个层级递进、动态发展的评价系统。关于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她认为必须将其置于教学活动过程中,把握其内在不可分割性、相互规定性和交互生成性。
叶澜老师的教学论思想是她创立的“生命·实践”教育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内容,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正是立足于叶澜老师的理论构建、实践探索、学派创新的“叶澜之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路径决定了其学术的原创性、系统性、生成性与发展性,这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走出了一条示范之路。
二、“生命·实践”教学论的历史地位
我想把“生命·实践”育学中的“教学论”思想放在当代中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学科史中分析其历史地位。
正如叶澜老师所言,当代中国的学术风气的重新活跃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的。教学论学术领域也是一样。当代中国教学论的学科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教学认识论阶段。王策三先生从学习到工作接受过前苏联教育学系统的训练,他的教学认识论思想的源头正是凯洛夫教育学,他的代表作《教学论稿》是在他教授本科生的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内首本较为成熟的教学论专著,在高等院校教育学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中作为教材运用多年,到现在还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王策三先生认为,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以此为基本观点,分析了教学的本质及过程,并倡导教学的科学化发展。他认为教学论要从教学认识论上做文章,概括起来,有三个基本的命题:一是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是现代教学论的根本目标;二是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是教学的基本关系;三是教学模式多样综合是现代教学论的根本方式。这三个命题,解决了教学的目标、关系和方式等基础性的问题,是教学认识论的三个支柱,也是对教学改革和实践的理论思考。
第二个阶段,教学系统论阶段。随着教学论学科的发展,需要一个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学科存在的标志并作为人才培养的教材。李秉德先生和李定仁先生倡导的教学系统论应运而生,其学术观点主要集中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的《教学论》中,李先生用系统论的观点讲述了教学的七要素,即教师、学生、教学方法、课程、目的、反馈和环境,并论述了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就基本确立了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教学系统论或教学要素分析论成为一个较为完整且成熟的理论影响了教学论学科几十年,现在仍然是许多学者赞成的理论,也是许多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参考教材。
第三个阶段,“生命·实践”的教学论阶段。叶澜老师从一个更宏大的教育学的“世纪问题”的思考出发,即“教育学的双重依附性,与本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教育实践的断裂,存在着缺家园、缺内生长力、缺学术尊严的并不理想的生存状态。”(《论纲》第27)页来思考中国的教育学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形成的“生命·实践”教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论思想,形成“生命·实践”教学论,在叶澜老师的诸多著作中已经详细地表述了她的教学论思想。在理论方面,叶澜老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学的重建问题,这一学术重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有关理论、历史和方法论的批判反思的第一阶段、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新基础教育”实验探索的第二阶段、以“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创生为标志的第三阶段。在《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一书中,叶澜老师在学派生成历程的回溯性分析中进一步指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创建与形成先后近30年,历经五个阶段,开展多维多元的回归与突破,如‘冬虫夏草’般地展示出它的魅力。‘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回归与突破的最深的一个‘猛子’是扎入当代教育实践之涌动不息的大海,尤其是深度介入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学校改革的实践。”正是受到这种研究取向的影响,叶澜老师及其团队在中小学的课堂教学研究与变革中用力最多,成效最为显著,不仅为形成和完善教学论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合作校的课堂教学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从合作校变革丛书中表现得十分到位:既体现了实践第一线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又融合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的基本理念。“生命·实践”的教学论进而能够针对传统教学论的弊端而重建课堂教学的价值观、过程观与评价观。而且,在叶澜老师研究取向的影响下,国内众多的教育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学校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者,都开始关注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实践变革,形成了中国当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重返课堂教学实践的热潮。无疑将学校和课堂作为教育与教学研究的“田野”,深入其中,长期扎根,通过观察、访谈、与教师合作、听评课活动等,来研究学校教学活动。“生命·实践”教学论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为代表性的教学理论形成之道。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教学论学科发展是处在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阶段的话,它还是一种逻辑演绎的教学论,而“生命·实践”的教学论则是一种生成、归纳的教学论,它是叶澜老师近30年“新基础教育”实践探索的产物,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交互生成的产物,是要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的产物。所以,我总是期望着能从叶澜老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中读出“生命·实践”教学论的时代内涵,也常常盼望着她能再出版一本《“生命·实践”教育学》专著,其中包括体系较为完整的“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文化表达、学校课程、课堂教学、班级管理、教师发展、学生主体、学校变革等。虽然这样的表述有较为明显的学科痕迹,但它却能体现教育学的体系,所以,作为一本代表中国最高水平,又要与西方教育学对话的代表作,它既要相对保持学科原有的框架,又要有一定的创新突破,这才是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教育学,也能让教育学的研究者,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的研究者从中感受到一般教育学的普适性,更能让中国的教育研究者从中找到自信,进而增强其学术自觉。
三、“生命·实践”教学论的方法论思考
叶澜老师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有三个基本的支柱:一个是“上天工程”——能够进行抽象的理论构建与研究;一个是“入地工程”——进行实践研究能够“入地”,能够到中小学课堂中做研究;一个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尤其是学生的主动性与能动性,通过唤醒学生的主体性来激发真正的人性。30多年来,她确实做到了,并创建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不仅从教育理论上对中国的教育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从实践上走出了一条教育研究的“叶澜之路”,即扎根学校推动课堂变革与生命实践的交互式发展之路,正如叶澜老师所讲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生命·实践”教育学从20世纪90年代叶澜教师提出的“让课堂唤发生命的活力”到今天的“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中国式表达,历时近30年,五个阶段,大学理论工作团队与中小学实践工作团队交互生成,形成了有自己独特内涵,结构与外显存在形态,呈现出有学、有书、有行、有路、有人、有实体的全气候景象。这是一条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之路,也是一条教育研究的方法之路,值得当下的教育研究者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叶澜老师在《回望》和《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中,以她本人近30年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历程为主线,为我们勾勒了“生命·实践”教育学学派别生成史。不难看出,叶澜老师的学术思想是从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核心问题、教育科学现状的反思和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三个方面同步开始的,她以“人学”理论为基础,将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用系统动态变革的方法论,对教育基本理论体系作了重新阐释,对教育科学研究的自我意识进行反思,并以“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为路径进行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叶澜老师一方面进行着学术的理论重建,另一方面面向实践、深入实践、理解实践和实践工作者一起创新实践,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学校变革的实践之中,又通过学校变革的实践发展和完善“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理论。叶澜老师在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时指出,她的成长有一个从“知”到“慧”的过程,以“知”为基础,还要发展到“慧”。对教师而言,要有教育智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对学科的认识、思想方法、方法论和实践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大智慧,它体现为对事理、事态的一种洞察力,一种穿透力和透视力,以及善于融会贯通进而实现原创的能力。叶澜老师在分析她所创立的“生命·实践”育学派时也指出,把“生命·实践”作为基因式核心概念,是构建学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选择,它不仅是学派建设的基点,也是学派理论的理想,还是学派命脉的聚焦点。而这一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叶澜老师形象地比喻为“冬虫夏草”。叶澜老师关于“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她的退休而告一段落,相反,她在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的过渡时间段里提出的教育学的重建与中国教育学派的创建问题,将会成为抱有教育理想的众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追求的梦想。
我把“叶澜之路”概括为四句话:
1.探究学术源流。即以理论家的宽阔胸怀,关注中国教育学的“世纪问题”,考察百年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之路,思考中国教育学的生存状态,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理论研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学的双重依附性问题。
2.创建理论学派。呕心沥血,三十余载,既有青灯黄卷的孜孜以求,又有深入学校的串串脚印,更有对学生生命发展的慷慨激昂。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率领着一个团队的奋进,不是一个团队的战斗,是带领着中国主流的教育学研究者奋勇向前。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流派,不仅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而且可以自豪地与西方教育学交流对话,重新找回了中国教育学人的学术自信。
3.行走天地人间。“生命·实践”教育学,既有勇敢上天的理论气魄,又有扎根田野的踏实作风,更有以人为本的生命关怀。这样一群人,行走在天地人间,吟唱着生命赞歌,是何等意气风发、壮怀激烈!
4.独爱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何等神奇。冬虫蛰伏在地下,虽然要经历严冬的考验,但已经涌动着生命的潜能,夏天来临,“冬虫”向“夏草”的漫长演化过程中正在显露生命的绿意,正在展示着蓬勃向上的生命之美。冬虫夏草,主要在中国青藏高原,富有中国特色元素,以此隐喻中国特色的“生命·实践”教育学,真可谓匠心独具。
叶澜老师并不孤独,“叶澜之路”人来人往,“我们虽然渺小,却因深爱与执着而将一直行进在路上。”这条路,我们永远记住它,它叫“叶澜之路”,走的人多了,便会形成一条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一心)
On“Ye Lan’s Path”of Education Research
WANG Jia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Minoritie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70,PRC)
As teaching theories abound in“Life·Practice”Pedagogy,it can also be taken as“Life·Practice”teaching methodology,the main contents of which include views on the nature of classroom teaching,the value of classroom teaching,the proc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the structure of classroom teaching,and the evalu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Life·Practice”pedagogy is the third stage of the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edagogy.It represents the generative nature of the indigenous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nductive nature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Methodologically,it opens up a unique and glamorous“Path of Ye Lan”for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exploring the academic origin,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school,wandering in the world but favoring only green grass in winter,spring and summer.
“Life·Practice”Pedagogy;“Life·Practice”teaching methodology;Path of Ye Lan
2015-04-28
G 40;G 52
A
1674-5779(2015)03-0076-06
王鉴(1968—),男,甘肃通渭人,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代教育与文化》杂志主编。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课程论专业委员会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