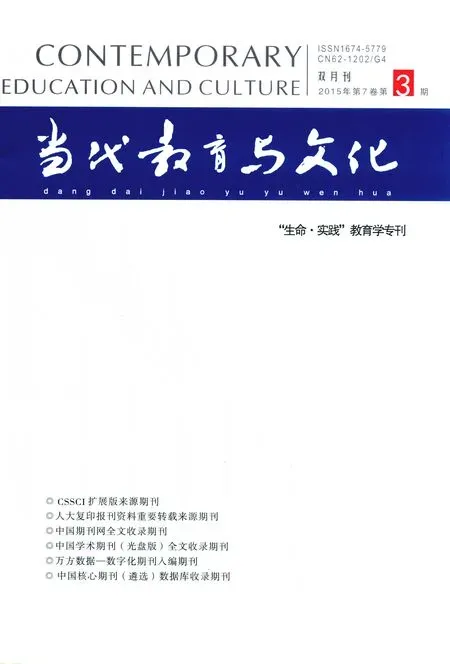“天、地、人”合一的“生命·实践”教学理论
2015-06-01和学新
和学新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天津 300070)

“天、地、人”合一的“生命·实践”教学理论
和学新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天津 300070)
“生命·实践”教育学形成了具有学派特色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在“天、地、人”合一中构建了“生命·实践”的教学理论。在教学理论方面就教学价值、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建,形成了自己的教学解释框架。
“生命·实践”教育学;教学理论;“天、地、人”合一
非常感谢叶澜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给我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三个系列30本大作,可以说是一套教育学大餐,非常美味,有待细细品味。
对于叶澜老师的研究、书和论文,一直在关注和学习,如读研究生时(我是李秉德先生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读到了叶澜老师的《教育研究及其方法》,受益很多,现在还不时在翻看和学习。现在我也让我的研究生阅读和学习,这本书对训练教育思维,提高教育研究意识很有帮助。从那之后,叶澜老师的《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等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叶澜老师也成为了我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他人”。我做博士论文《主体性教学研究》时(1995—1998跟随张敷荣先生)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叶澜老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也是我要求学生必读的书目,甚至是我们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招生考试的必读参考书,因为各个方向都要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内容,这是由我提议的。叶澜老师的《新基础教育论》《新基础教育研究史》《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等我都拜读过。可以说,新基础教育的研究与成果,我一直在学习和关注。
这次会议,三个系列30本书一起出版、发布,量很大,虽然已经提前拿到,但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深刻领会和把握,这里我主要是结合系列二的有关教学方面的著述谈谈学习心得和体会。
作为一个学派或者称得上一个学派的教育学理论,必然要关涉教学问题。教学问题是教育学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最核心问题,是反映教育学学科特色、教育学学科专业性质的内容。古今中外有影响的、可称得上学派的教育学理论无不有关于教学问题的论述或者最后都要落实到教学问题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教育思想,被称作传统教育理论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被称作现代教育理论的杜威教育思想,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凯洛夫教育学都是有关于教学问题的内容,而且教学问题也都是重点内容,他们在阐述教学问题前,都做了大量的基础理论铺垫。
“生命·实践”教育学在教学问题方面也是倾力探讨、研究和实践,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形成了具有学派特色的教学理论和实践。
我初步的总体感受是:在“天”“地”“人”合一中构建“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理论与实践。
首先说“天”“地”“人”合一。“天”“地”“人”合一体现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教学理论与实践构建的方法论。
所谓“天”是指顶天。“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基于深厚、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实际上,一个有影响或称得上学派的教育教学理论必然有自身对教育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的研究或追问,如对社会发展时代特征、学生培养规格或质量等的认识,要对教育教学的一些前提问题进行追问,形成学派所依赖的独特理论基础或认识。这是关系一个学派方向性的基础问题,也是决定一个学派理论高度和影响力的基础问题,更是决定一个学派能否站得住的基础问题。如赫尔巴特教育学建立在其伦理学和统觉心理学基础之上,形成了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的一套教学理论,通过凯洛夫教育学,至今还在影响着我国的教学实践。又如杜威教育理论,建立在其机能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有关儿童中心、教育与经验、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教育教学认识。“生命·实践”教育学在这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基础性理论工作。如提出了关于影响人发展的“二层次三因素说”,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巨大社会转型特征的体认及其这样一个时代特征下教育理想的构建,对学生发展特质的定位等都是这种前提性理论研究。
“二层次三因素说”认识到了活动与人的发展相互作用,使得教学关注到了学生活动与其发展、成长的关系,活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活动才是人所特有的,人的活动才是主动的,其他动物、植物的生命都是被动的本能的活动。教学培养人,就要关注到学生的这种积极主动的生命活动的价值。“二层次三因素说”实际上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学派的教学理论奠定了人性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融入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教育培养具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的具体个人主体,从而在教育教学质量规格、目标方面要突出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意义。这为学派的教学理论奠定了时代依据、价值依据和现实依据。
这种顶天的基础研究使得“生命·实践”教育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所谓“地”就是“立地”。“生命·实践”教育学在叶澜老师的主持下经历了20余年的实践探索(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到叶澜老师大学本科毕业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做过两年语文教师的经历),这20余年始终深深扎根于“教学领域”、“中小学一线”、“各科教学(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对教学的多方面的重建都是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在相关论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充满实践气息的丰富多彩的探索。“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理论充满了实践智慧。
所谓“人”是指叶澜老师及其带领下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研究者、中小学教师、中小学管理者(校长、主任等)、市区教育行政人员(局长、科长等),体现出的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和努力。一个学派的建立与发展靠个人很难,需要团队或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和不断的奋斗。“生命·实践”教育学这方面很突出。
所谓合一,就是以上三个方面的互动、沟通、交流,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沟通、交流,促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构建与不断改进和完善。
“天、地、人”合一体现出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深度互动与结合,实现着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身的理论提升与超越,这对我们从事教育研究的教育学人而言,是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气质、中国风格。
其次说“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理论。“生命·实践”教育学在教学理论方面就教学价值、教学过程、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建,形成了自己的教学解释框架。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教学价值取向定位于学生的主动健康发展,突出了教学的时代价值追求
在教学价值取向方面,在教学论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代重视道德培养、近代重视科学知识传授、现代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培养智力、陶冶个性品质和道德情操)等几个阶段。理论上或理想的教学应该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实际上,我国现实的教学实践中知识传授为主,教学论整体上或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起作用的主要还表现为知识教学论或认识论教学论。
20世纪末,新旧世纪交替之时,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人才质量规格的要求,既要考虑我国的现实,又要跟上世界的步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强调了“四个学会”(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发展(做人)),这是世界的共同认识。这要求我们在教学理论和实践层面要有所突破,要突破知识教学论或认识教学论的局限。
叶澜老师基于时代特征的把握和已有研究基础以及对现实课堂教学的体认,敏锐地提出了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对教学价值的时代追求进行了深入思考,突出了课堂教学的生命价值和学生的主动健康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也符合学生的发展可能性。
学生的主动健康发展是基于人的主体性。从人的主体性的特征结构来看,分为自主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三个方面,自主性的获得靠机制,给予自由的空间,人就可以获得自主性。创造性,在学理上,即人人具有创造性。但在人们的一般认识里,创造性不是普通人或所有人都能具有的,让人们接受起来有难度。甚至不少人认为,创造性是培养不出来的。这样在主体性的特征结构中,只有主动性这个特征,教育才具有较大的可作为性。所以说,“生命·实践”教育学教学价值取向定位于学生的主动发展是有现实可能性的,也容易被接受。
第二,强调教学过程的动态、互动、生成、开放等特性,丰富了对教学过程的认识
对教学过程的认识,我国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非常热烈的探讨,之后一直不断。除了特殊认识说外,实践说、审美说、价值增值说、交往说、多本质说等(我也提出了一个教学是师生通过交往方式在与课程内容之间的能动而现实的双重双向对象化过程中发挥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教育活动,简言之就是,师生能动而现实地发挥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教育活动),林林总总,很多观点。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教学过程的认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但仍是静态地看待教学过程,思维方式还是较为单一,流于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认识,没有看到教学过程的丰富多彩,没有看到教学活动的动态性和复杂多样性,总想用一个术语或简单的命题就能描述或表达出教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关键看这个术语或命题的概括度。
实际上,一般而言,活动是主体的活动,根据主体的“主体-主体”、“主体-客体”存在样态,主体活动可分为主体反映客体为主的认识活动,主体变革客体为主的改造或创造活动,主体占有客体满足主体的欣赏审美活动,主体检测客体为主的评价活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等几个基本活动形式。从活动的一般存在方式来看,教学过程应该有这些基本的表现方式。由此来看,教学过程不只是以上各种已有认识的一种,而是它们的集合,或者在不同的状态和时刻主要体现为某种或某些活动。比如在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不同的教学内容等情况下,教学过程就表现为不同的状态,有的表现为认识活动,有的表现为实践活动,有的可能既有认识活动,又有实践活动,甚至还有欣赏审美活动等。这表明了教学过程是复杂多样的。单从认识、实践、审美、交往等一个方面来刻画教学过程,显然是不行的。
“生命·实践”教育学超越了以往的不足,基于复杂性理论、基于对人的生命活动本性的认识,强调了教学过程的交往、动态、互动、生成、开放等特性,定位于学生的主动健康发展,使对教学过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综合的高度。
第三,超越了备课的经验局限,构建了系统化、复杂化、多样化的教学设计策略
我国教学论和教学实践层面在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方面十分重视备课,主要是“三备”,备教材、教法、学生,这是一种经验层面的做法。近些年来,开始关注系统化教学设计,在一些教学论教材中有相应章节出现。从教学设计来讲,对教学工作的准备不只是教材、教法和学生,涉及到教学的各个要素,除了这三个要素外,目标、课程、评价、手段(媒体)、管理、调控等,都是要考虑的,而且是一个系统化的准备过程。在教育技术学领域,系统化教学设计是作为一门课开设的(当然就教学设计的归属问题还曾经有一些争论)。
当把教学过程看成是一个具有复杂多样的生成、开放、交往性活动时,必然会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教学的准备工作。“生命·实践”教育学把教学视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在教学工作准备方面不再停留于“三备”,而是立足于课堂教学的复杂环境来设计教学。首先,在整体的主导思想上,设计参与型教学活动;其次,在教材分析方面,一方面是范例性、结构性、学科育人价值的基本视角分析,一方面是学段、单元、单元内、一节课内容以及具体教学内容特殊性及其育人价值的多层套嵌式分析;再次,在学情分析方面,采取积极的学生观,在学生现实基础和发展的可能性之间转换和提升,在内容价值与学生成长需求之间解读目标点,在学生个体差异中读出丰富性;最后,在教学实施层面,采取纵横两条设计线索。纵向采取“长程两段”设计教学,就是把教学分为两个时段,一个时段“教学结构”,用以解决教学内容的学习和把握,一个时段“运用结构”,用以解决教学内容的运用问题。横向设计为学生的主动学习留有空间。这种系统化的教学设计,解决了教学与学生发展、教学与学生生活、个体学习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沟通机制问题,使学生的主体参与活动能够落到实处。
第四,关注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探索了多样化的课型,使学科教学有了理论根基
对于学科育人价值,长期以来不被重视或者说是忽视的。一般重视的是学科知识本身的认识和把握,而学科知识怎么来的,在该学科知识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学生的生活、发展、成长有什么关系等,往往都是被忽视或轻视的。当然有的提出了学科德育用以解决育人问题,但学科德育与学科育人显然是不等价的,其内涵是狭窄的,涵盖不了育人内涵的丰富性。由于忽视或轻视学科的育人价值,造成的结果是各科教学后学生获得的往往是静态的学科知识,甚至是零散的、碎片化的知识,学生不会用该学科的知识、术语、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需,也不会系统表达,更不用说学生身心各方面素质的发展和提高了。
“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特别关注学科教学的价值,把学科的知识价值与育人价值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体现不同学科性质的多样化课型,如语文有10个系列课型,数学有8个系列课型,英语一级基础课型12个等。对于课型,一般是两种分类:一类是根据教学任务分为综合课和单一课(新授课、复习课、练习课、实习课、检查课);一类是根据教学方法分为讲授课、演示课、讨论课、阅读课等。这部分内容本身与学科教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是很重要的教学论内容,但一般的教学论教材探讨的不多。“生命·实践”教育学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这个方面并在这次出版的有关论著中体现了出来,这与其关注学科的育人价值的发挥是分不开的。这种认识对于深化教学论研究尤其是学科教学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建构了新型的教学主体交往关系,使教学的社会性实现具有了现实机制
人是活动的主宰。一般意义上,人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学活动中的人由教师和学生组成,因而人们一般把师生看成教学活动的主体。但在复杂的教学过程中,关涉其中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看待这种主体关系,尤其是其担负的社会意义是如何实现的,需要理论给以解释,教学实践需要以此理论给以引导。长期以来,教学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提出了多种解释,如主导主体论、单主体论、双主体论、复合主体论等,我也提出过层次分析论,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每一种解释都有质疑声音。
“生命·实践”教育学在这个问题上,超越了师生之间的主客关系认识模式,以“人”、“人”之间的主体间交往关系来认识,认为主体交往关系是教学过程中师生的第一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关键性论断。这种师生间的复杂交往关系,促成了教学系统活动的生成性、互动性、开放性、丰富性,从而对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社会合作等方面的发展产生影响,实现了教学的社会性价值。
当然,就“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主体关系来看,不局限于师生之间,实际上,除此之外,研究专家、中小学校长、家长、教育行政人员都参与了其中,“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主体关系更为复杂,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期待“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论的推出,也期待“生命·实践”教育学对课程问题的探讨。
以上是我学习“生命·实践”教育学系列论著之后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当之处,还请叶澜老师与“生命·实践”教育学团队批评。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一心)
Constructing the Teaching Theories of“Life·Practice”Pedagogy in“Heaven-Earth-and-Man”Oneness
HE Xue-x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300070,PRC)
“Life·Practice”pedagogy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teaching theories and teaching practice its special features of an academic school.It is in the“Heaven-Earth-and-Man”Oneness that the teaching theories of“Life·Practice”pedagogy come into being.It has reconstructed the teaching theories in such aspects as the value of teaching,the process of teaching,the teaching design,the teaching content,and teaching evaluation,and formed its own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eaching.
“Life·Practice”;pedagogy;teaching theory;“Heaven-Earth-and-Man”Oneness
2015-04-28
G 40;G 52
A
1674-5779(2015)03-0070-06
和学新(1966—),男,河南获嘉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天津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成员、天津市优秀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