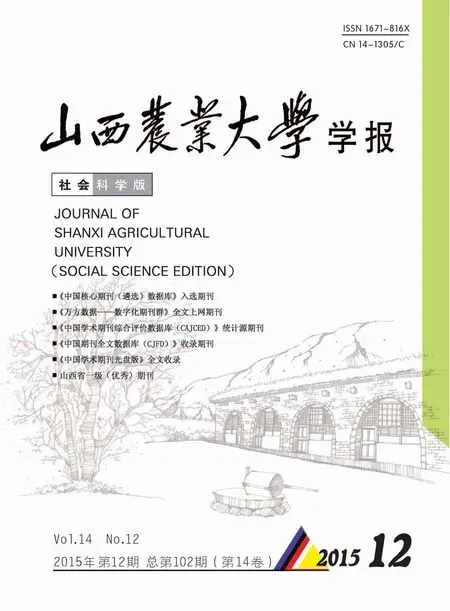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探析——以梅贻宝时期(1934~1936)为中心
2015-04-02荆玉杰李卫朝
荆玉杰,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探析
——以梅贻宝时期(1934~1936)为中心
荆玉杰,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1934~1936年,梅贻宝任铭贤学校校长,开启了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转型期。在“燕京模式”的基础上,铭贤学校吸收从事乡建工作的诸方之长,以自身农工专业为特色,走出了乡村建设的“铭贤道路”。在两年的乡村建设过程中铭贤学校实现了“自觉且自主”的转型,在乡村教育建设中注重教育的普及性和实践性,在乡村经济建设中注重农民的合作和科技的推广,为乡村实验区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梅贻宝
收稿日期:2015-06-30
作者简介:荆玉杰(1988-),男(汉),山西平陆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李卫朝,副教授。E-mail:sxauliweichao2013@163.com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5)12-1279-06
A study o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of 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On the Basis of the Y. P. Mei's Period (1934~1936)
JING Yu-jie,LI Wei-chao
(CollegeofMarxism,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Shanxi030801,China)
Abstract:Y. P. Mei's Period (1934~1936) was the transition time of 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Yenching mode and other useful experiences, 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 developed a characteristic road fitting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Oberlin-Shanxi Memorial School achieved a conscious and autonomous transformation, which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popularit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rural education process, and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of farmers and technology extension. 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experimental region by focusing on the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economy.
Key words:The 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 Rural construction; Y. P. Mei
在被迫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乡村出现了经济衰退、文化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救活乡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众多从事乡村建设的个人和团体。就其主体而言,有三种主要类型:“一是以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等构成的乡村建设主流派;二是教会组织、慈善机构、地方实力派人物开展的乡村建设;三是国民党中央部门和民国政府参与或主办的实验县(区)。”[1]近年来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多集中于乡建主流派的知识分子和地方实力派人物,而对院校的乡村建设少有涉及,对铭贤学校更是缺少关注。梅贻宝时期(1934~1936年)是铭贤学校的黄金发展期,学校的整体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乡村建设方面更是可圈可点,实现了由“自觉而不自主”到“自觉且自主”的转型。同时,围绕着乡村教育建设和乡村经济建设的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乡村地区和铭贤学校自身的发展。
一、从自觉到自主:困境中的乡建转型
近代乡村建设团体与国家及地方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力量可以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进场有利于乡村建设思想的制度化,但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乡村建设中扮演主导角色,又往往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即政府现代化目标凌驾于乡村建设目标之上,使乡村制度发展偏离了乡村建设的轨道”[2],或者造成乡村建设团体“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梁漱溟语)的尴尬。铭贤学校早期的乡村建设就陷入了这种尴尬之中。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活动肇始于孔祥熙对山西乡村问题的关注,归国不久的孔祥熙便发动全校师生在太谷乡村进行禁毒工作。由于阎锡山村制改革在山西的强势推进,铭贤早期的乡村建设不得不在村制改革的大框架下进行,其工作内容不外乎“六政三事”及“整理村范”等等,在具体实践中,还须服从太谷地方政府的安排。可以说,铭贤学校早期乡建工作是“自觉而不自主”的。
“自觉不自主”的困境严重制约着学校乡建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此时的“自觉”是感性“自觉”,对如何进行乡建尚且缺乏理性认知,其“自觉”性的发端更多是热情驱动而非理性驱使;另一方面,是时的“不自主”使学校无法摆脱地方政权的干扰,无法凸显出自身的优势,无法践行自身的乡村改造理念。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梅贻宝带领着铭贤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农工之路”奠定乡建转型的基石
近代高校成为乡村建设活动中异彩独放的一支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农科专业知识的掌握。农业技术改良和推广在乡建中的作用是直接和显著的,是时铭贤学校办学方向的转型奠定了其乡建转型的基石。1927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后,铭贤学校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在救亡的历史基调下,铭贤人认为:“吾国原系农业国家,为今后富强发展计,势非奠定农业基础,再借以从事工业建设则难与欧美各先进国家相争衡。”[3]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铭贤学校重点发展农工专业。1928年铭贤学校增设农科专业,延聘美国人穆懿尔担任农科主任,设立经济组、育种组、森林组、畜牧组及推广组等从事农业研究工作。1931年工科成立,在李海文的带领下从事设计、研制农具等工作。
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的内容“要可类归于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4]。与从事乡建的知识分子相比,学校的科技基础、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恰恰是其优势所在,而这一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校在乡建中往往侧重于经济与教育的一面,淡化政治的色彩。“学以事人”,组建农工专业的目的在于造福乡村,而乡村建设其时已成为铭贤学校进一步发展农工专业的内在需求。如何使知识更好地造福乡村,探索最贴合实际的乡建模式成为了铭贤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2.“燕京之风”带来乡建转型的机遇
燕京大学系1919年英美等国基督教新教差会在北京联合组建的教会大学,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大学中,燕京大学做出了乡村建设的最早尝试。其乡建活动肇始于1928年社会学系师生在北平清河镇的实践调查,之后在北平清河镇及山东汶上县设立农村实验区,进行乡村教育、经济建设、改进卫生等工作,由此形成了燕京大学以调查为先,集中全校力量独立在农村实验区进行整体性乡村改造的乡建模式。
1934年秋,梅贻宝迁任铭贤学校校长。梅贻宝在燕京大学时期素来重视乡村问题,他认为:“中国乃以农村立国,人口散布乡村,任何改进办法,必须深入乡村,方能收普及之效。”[5]曾与“梁漱溟先生畅论中国文化前瞻”[5],并先后考察了河北定县、山东邹平、江西黎川等乡村实验区,系统发掘各乡村实验区的特色与优势。担任铭贤学校校长之后,梅贻宝将自己的考察研究结果,尤其是燕京大学的乡建模式融入铭贤学校乡村建设之中,开始逐步打破村制改革框架的限制。对于“燕京模式”,铭贤学校选择了其调查优先与整体改造的特长,淡化了其宗教性。在乡村调查中,1935年3月,铭贤学校与燕京大学合作,聘请燕大教师在太谷从事乡村调查工作,“由刘志博君及选择具有代表太原平原一般农村之贯家堡等村举行调查……共完成太谷县20村概况调查、贯家堡村调查、东山底村调查三种”[6],作为乡村建设的基础资料。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铭贤学校进一步淡化“燕京模式”中的宗教化倾向,吸取其区域试验和整体改革的经验,最终选定贯家堡等二十余村为乡村实验区,准备进行教育、经济、卫生、文化等多方面的建设活动。
3.“他山之石”拓宽乡建转型的视野
虽有燕大模式作为范本,但乡建工作的推进仍需纳众家之长。1934年,甫任校长的梅贻宝携武寿铭参加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第二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汇集着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江问渔等多年从事乡建的知识分子以及诸多大学,梅贻宝以参会为契机,拓宽视野,继续为铭贤学校乡建工作的推进寻找借鉴。同从事乡建多年且取得丰富成果的组织相比,铭贤学校当时的工作确实略显单薄,但是,作为为数不多的从事乡建工作并参加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高级中学,铭贤学校为乡村建设做出的贡献是难能可贵的。会议中诸方对推进乡村教育和乡村经济的探讨,让铭贤人认识到乡村教育建设和乡村经济建设应是乡村建设的主题,而铭贤学校的农工专业恰恰是其特色所在,同时更认识到建设乡村实验区的紧迫性,因为这是其自主性的主要体现。由此,在自身农工专业的基础上,铭贤学校吸收燕京大学及梁漱溟、晏阳初等众家之长,围绕着乡村教育建设和乡村经济建设的主题,对乡村建设的感性自觉上升为理性自觉,真正开始了“自觉且自主”的乡村建设工作。
二、从普及到实践: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建设
由于传统精英教育体制的约束,中国的国民素质,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长期难以提升,这也成为制约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兴学校、开民智成为不少仁人志士的主张,“教育救国”一度成为时代的强音。但从“教育救国”思潮的发展脉络来看,其提倡者重视的是社会精英的力量,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同时,其教育的普及很难触及社会的基底,而这些生活在社会基底的大多数正是乡村教育的主要对象。
在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看来,教育实为“救活农村”的不二良方。梁漱溟先生讲:“乡村建设运动之做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7]晏阳初先生通过教育实践与社会调查,认为中国农村患有“愚、贫、弱、私”的顽疾,需经“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及“公民教育”来根治,而教育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方法,并非一切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贴膏药式的方法可比。”[8]铭贤学校乡村实验区的所在地贯家堡村文盲率高达77.6%,其中男子文盲65.5%,女子文盲98.3%。铭贤学校在梅贻宝的带领下针对贯家堡村的实际情况,在吸收定县经验的基础上,强调“以农民教育为一切建设之基础,初步工作集全力于教育之普及”[9],在“文字进乡”的过程中,注重乡村教育的群体面向与生活对象。
1.群体面向中的普及教育
晏阳初在定县实验区中强调:“平民教育的目的,即是全民的生活教育”[10],且“平民教育的第一步必须有文字教育”[8]。乡村中生活着多元群体,乡村教育应该针对多元群体实行不同的普及教育,由此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建立了“学校式”、“社会式”及“家庭式”教育结合的模式。铭贤学校乡村服务试验区以服务乡村为宗旨,在定县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根据贯家堡等地的特殊情况,采用“学校—社会—传递”式的模式,以学校教育普及基础教育,以社会教育培养乡建中坚,以传递教育提高妇女素质,从而促进农民素质的整体提升。
在学校教育方面,铭贤学校着力于兴办幼稚教育、改良小学教育。贯家堡等地缺乏幼稚教育,三到五岁的儿童“一向多在街上玩石耍土,骂人学乖,得不到正常教育”[3],铭贤学校遂于贯家堡设立乡村幼稚园,收容25个幼稚生,开贯家堡幼稚教育的先河。针对贯家堡小学设备、行政、编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铭贤学校对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使其校容、课程、学生习惯等等均有显著进步。另外,铭贤学校采用平教会出版的农民千字课为教材,以十五岁至二十六岁的青年为对象进行识字教育。
铭贤学校社会教育的对象与定县不同,定县社会教育的对象集中于接受过学校教育的群体,“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11],强调教育的延续性。铭贤学校的社会教育则以二十六至四十五岁的农民为对象,将闾邻长及三十岁上下的农民作为主体,强调教育的普及性,着重于培育乡建的中坚力量。
在定县家庭教育的基础上,铭贤学校更注重对妇女的传递教育。在乡村中妇女面对着庭院深深,“自幼即受旧道德观念的栽培,不能轻易走出庭院以外”[6],更难有接受教育的机会。阎锡山虽在山西全省提倡村治,但在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是相对有限的,村治“也只能影响到现在十余岁的女子;在村治运动达到高潮期间,已经‘完成’的女子不易受到若何深刻的刺激,所受到的也只是装饰与其他有形的改变;而脑海中所印的旧道德观念,一时不易洗刷净尽。”[6]铭贤学校以乡村小学中的学生为主力,利用课余时间回家教其父母姐妹,将教育传递至家庭之中,在识字教育的同时,将现代理念带回家庭,从而提高乡村妇女文化素质。
2.生活面向中的实践教育
晏阳初强调普通学校教育“只有书本知识和空洞理想,而未去民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从平民生活里找问题、找材料而去求解决方法。”[11]与普通学校教育相比,乡村教育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来解决农村问题,这就要求乡村教育必须贴合实际,贴近生活,注重教育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能够真正解决农村问题。
在乡村调查中,铭贤学校发现贯家堡等的农民在生活中地存在三大显性问题。其一,青年农夫的贫困问题。贯家堡等地的青年农夫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多是自耕农和佃农,少有人从事副业,谋生手段落后而且单一。其二,农村妇女的病弱问题。由于卫生知识的缺乏和基础医疗的缺失,贯家堡等地女性患病率远高于男性。其三,乡村精英的偏私问题。贯家堡村的政治结构是闭塞且内生的,虽经阎锡山政权的渗透,但并未触及其原生的精英生态,乡村精英的理念更是未得到现代洗礼的传统观念,这种陈旧且闭塞的观念严重阻碍乡村的现代变革。针对三大问题,铭贤学校在“文字进乡”的同时注重其生活面向,通过教育解决青年农民的贫困问题、乡村妇女的病弱问题以及基层官员的偏私问题。
针对青年农民的贫困问题,铭贤学校把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农夫单独编班,以学校农工科师生为主力,在课程设置上注重生计训练,教授合作思想、植物培育等等,将现代知识和技术带入乡村,培养青年农民的合作意识及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拓宽其谋生渠道。针对乡村妇女的病弱问题,铭贤学校设立单独的女子班,“每日午前上课,授以手工,唱歌,修身,千字课及卫生常识等课程”[9]。在普及基本卫生常识、宣传基本卫生理念的同时,铭贤学校致力于完善乡村卫生体系,在贯家堡等设立乡村诊疗所,方便乡村妇女寻医问药。针对基层官员的偏私问题,铭贤学校对以闾邻长为代表的精英进行公民教育,“课程以公民训练,珠算,新闻报告为内容,”[9]培养自律健全的公民意识,树立自觉团结的公民美德,拓宽其了解现代社会的渠道,促进乡村精英由“宗族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使其更为有效地参加乡村公共生活和乡村基层治理。
三、从合作生产到科技改良:转型中的乡村经济建设
经济衰退是近代农村的显性问题,民国时期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梁漱溟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的失败不外乎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12]。农业科学技术的落后自不待言,有宋以降,中国农民生活在乡村宗法共同体中,德业相劝、患难相恤的乡村宗法共同体虽为有联带负责、相互保障的伦理组织,但在被迫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宗法共同体在抵御经济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却显得苍白。中国乡村迫切需要在引进西方先进农业科技的同时建立超越宗族的新型经济组织,而这种组织“既异乎所谓个人本位,亦异乎所谓社会本位,恰能得其两相调和的分际……为能开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4]。梁氏更是断言:“要想农业进步,要想农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12]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立农业合作社与引进科学技术这两大措施来发展农村经济,而铭贤学校亦通过这两项措施来实现乡村实验区由家庭经验式生产向合作科技化生产的转型。
1.合作面向中的农业生产
合作主义思潮源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在英国“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式的供销合作社和德国雷发巽式的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五四运动前后,合作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以薛仙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将其视为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其政治温和性,合作社成为不同政治力量能够共同接受的改造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合作主义思潮虽然失去了以往的光彩,但其却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存土壤与实践平台——中国乡村,乡村建设者将合作社在中国乡村推展开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社多是生产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针对贯家堡等地农民借贷率、抵当率、负债额普遍较高等实际情况,铭贤学校一方面指导贯家堡等村指导建立信用合作社,促进农民之间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学校出资开办小额贷款,调节农村金融,促进学校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合作,通过两种合作方式来解决农民沉重的债务负担。
为了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铭贤学校在贯家堡、东咸阳、南咸阳、西咸阳、中咸阳、南张村六村联合会举办讲习会,“讲授合作原理,解释合作规章”[3]。各村农民在了解合作的意义之后,“深感合作之需要,纷纷自动组织”。1936年贯家堡信用合作社便“有社员20人,股金40元,举办信用放款一次,共贷出52元,到规定时间,本息如数还来”[3]。夏收之后粮价下跌,铭贤学校又指导该社建立小麦仓库,储备小麦28石,贷出款额140元。之后再购进煤油、煤炭等物资,由社员按需购买,因其便民效果,要求入社的农民日渐增多,而合作社也在东咸阳、南咸阳、西山底等地建立起来。
鉴于乡村实验区农业金融体系的缺失,铭贤学校出资调剂农村金融,在乡村服务试验区开办小本贷款业务,“遇有勤劳诚实之农友,需用小额款项,求生计之正当改进者,便可按章贷与款洋”[3]。这类贷款发放额虽然不高,但对饱受债务苦恼的农民确实有很大帮助。
2.科技面向中的农业改良
农业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而铭贤学校向实业学校的转型恰以发展农业技术为鹄,由此农工专业成为铭贤学校乡建的特色所在。为了凸显这一特色,提高农工专业的实力,梅贻宝先后两次呈请教育部补助经费,扩充农工专业,利用学校农工各科的试验及设备,“从事于农村经济、农村生计、作物改良、农具制造、毛织工业之各种事工”[3],通过现代农工科技促使农村复兴。在具体工作中,铭贤学校以开放心态积极学习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以笃实工作进行农业改良和推广。
在引进良种方面,铭贤学校针对山西乃至华北地区的特殊情况,在穆懿尔的带领下同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育成小麦新品种——“铭贤169号”,在对比试验中,“一六九号及二零四号两小麦品种,在省农务局霍县、长治等处产量平均高出农家品种百分之二十七与四十六。”[13]穆懿尔等人从美国引入“金皇后”等十余种优良品种,在15村26处的示范田中,“金皇后”的产量比农家品种高出20%—40%,1936年后“金皇后”在山西全省得到示范推广。
在畜牧推广方面,铭贤学校农科先后与太谷县及建设厅合作,创立推广中心,在山西省选择10县作为试点,推广“来航”鸡。在贯家堡实验区,铭贤学校组织成立羊种改进会,推广“软布来”羊。在病虫害防治方面,针对果树害虫,仅在1935年一年中铭贤学校便使用1137斤石灰硫磺合剂,喷射果树522株。同时,推广碳酸铜粉防治麦类黑穗病,因其效果显著,很快便有23处73家使用该项技术。
在学校农科进行农业改良的同时,铭贤学校的工科也为农具改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李海文的带领下,工科设立了肥皂厂、机械厂、木模厂等等,集中力量改良农具。先后制造了冰铁犁、除草机、玉米脱粒机等,其中使用工科新式犁的田地比使用旧式犁的产量竟高出18%。铭贤学校改良的农具受到了山西省建设厅及实业厅的肯定并被推广到全省。
四、结语
近代中国,众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不得不依靠农村,不得不从改变农村的面貌开始。他们当中既有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等从理论和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也有米迪刚等地方乡绅在自己家乡进行试验,还有地方军阀进行的乡村改良,更有一些高校的农学院在积极推进农业改良。但是像铭贤学校这样明确以农工专科为主打方向,集全校之力来进行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学校并不多见。
经过梅贻宝时期两年的探索与实践,铭贤学校实现了乡村建设活动的转型。在乡村建设的开展上,铭贤学校逐渐脱离了对政治力量的依附,凸显出其主体性作用;在乡村建设的模式上,铭贤学校改变了以学生乡村服务团、农村改进会为主的模式,吸收燕京大学经验,通过实地调查,组建乡村服务部,在太谷县贯家堡等地设立乡村实验区,实现了乡村建设的规模化发展;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铭贤学校以自身农工专业为依托,致力于农村经济的现代变革,走出了铭贤特色的乡建道路。
在两年的探索与实践中,铭贤学校在基础薄弱、环境闭塞的困境中取得了卓著成效。铭贤学人抱定“科技救国”的决心,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寻求国内外在农业领域有先进经验和技术的单位进行合作,他们诚恳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首先,铭贤学校在农业技术改良和推广方面的积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山西省农村的面貌,多次获得山西地方政府的肯定和赞扬;其次,铭贤学人的笃实精神和开放心态为铭贤学校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成为了山西省极少数拥有全国声望的学校之一;再次,经过前期的探索和实践,到了梅贻宝时期,铭贤学校探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乡村建设理念和模式,即凸显铭贤学校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以“科技救国”的精神来改造中国农村面貌,以“教育救国”的理念来开启民智,以开放心态来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以合作主义的模式来改善中国农村的经济。
铭贤学校在山西的乡村建设虽因日寇入侵而不得不中断,但仍然对近代山西特别是太谷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诚然,与其他团体和高校相比,铭贤学校显得默默无闻,其乡建活动也不那么引人关注,但对铭贤学校而言,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不只在于铭贤学校对乡村的贡献,更在于乡村建设对铭贤学校自身发展的影响。窥斑知豹,铭贤学校对乡建的探索是其探寻办学模式的一个缩影。在“学以事人”校训的引领下,铭贤学校转型为实业学校,乡村建设成为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乡建模式的过程中,铭贤学校并未被区位的劣势所限制,相反,她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不断找寻攻“玉”之“石”,这种开放的理念是铭贤学校取得发展的坚强基石,也是我们今日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景新,鲁可荣,刘重来.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
[2]宣朝庆.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2012(3):130.
[3]信德俭,温永峰,方亮,等编著.学以事人真知力行——铭贤学校办学评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207,257,258,251,252.
[4]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227-229,223-224.
[5]梅贻宝.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M].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60,61.
[6]武寿铭.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民国时期乡村调查丛编(二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254,275,275.
[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618.
[8]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5,123.
[9]太谷通讯.铭贤学校贯家堡乡建近况[J].民间,1935,2(16):30.
[10]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36.
[11]宋恩荣.晏阳初文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39.
[1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9,341.
[13]袁钰.制度变迁与华北农业近代化[J].文史月刊,2001(4):56.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