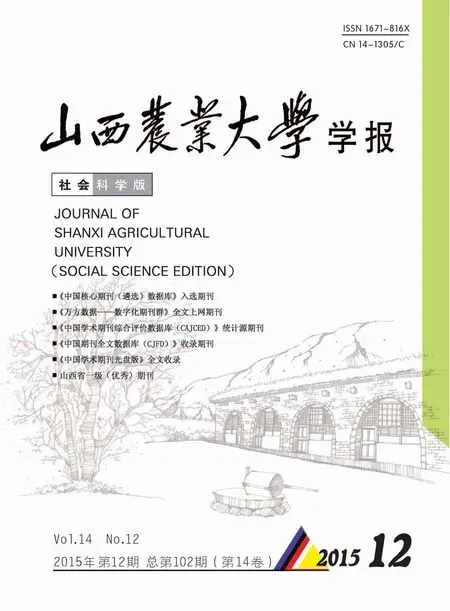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的历史考察
2015-04-02闫志敏李卫朝
闫志敏,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的历史考察
闫志敏,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以学校为阵地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也为其注入了活力。铭贤学校作为山西乡村建设活动的重镇,在此期间亦经历了肇起、发展、挫折、重建四个阶段。通过对其各个阶段乡建活动的梳理,总结其特点,希冀勾勒出铭贤学校一幅系统化、体系化的乡村建设活动图景。
关键词:铭贤学校;乡村建设活动;阶段
收稿日期:2015-09-07
作者简介:闫志敏(1981-),女(汉),山西长治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李卫朝,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历史与文化研究。E-mail:sxauliweichao2013@163.com
基金项目:2015年度山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ZXSK1502)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5)12-1285-05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of Rural Construction of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YAN Zhi-min, LI Wei-chao
(CollegeofMarxism,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Shanxi030801,China)
Abstract: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modern times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ft an important mark in history.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around the school also injected vigor into the movement. As the center of rur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Shanxi,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also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the origination, development, frust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each stage are summarized, which is expected to outline a system for rural construction activity.
Key words: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Rural construction; Stage
20世纪初,农村社会的失序以及“破产”衍生出了一场以“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为宗旨,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推广技术、提倡合作、流通金融、改善公共卫生等措施来复兴农村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栋、著述颇丰。近些年来对其研究更为深入,主要集中于乡建运动的重新审视、不同乡建派别和团体(乡村建设派、地方实力派、各高校及社会团体、国民政府等)思想理论及实践模式的比较、乡建运动性质的评价、乡建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等。山西太谷铭贤学校在这场运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它44年(1907-1951年)的办学历程中,乡村建设活动一直贯穿其办学的各个时期,不仅在当地农村开展了多项重塑乡村社会的活动,还为农村社会培养了大批实用性技术人才,但这方面的研究较欠缺。我们以20世纪上半叶乡村建设运动为背景,梳理铭贤学校不同阶段乡建活动的发展历程,呈现其在发展变迁过程中的特点,进而来管窥大变革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一、铭贤学校乡建活动的肇起
20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大力冲击和晚清有识之士“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曾一度受挫,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这场思想领域里的争论使得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跨入实践层面,直接导引了民国初年一些地方乡绅和地方主政官员利用其社会威望和地方行政资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最早始于晚清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1904年河北省定县地方乡绅米鉴三、米迪刚父子以翟城村为示范,发动了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以及发展村庄经济等为内容的乡村自治。辛亥革命后,他们的“村治”思想随着定县县长孙发绪赴任山西省继续发酵,而后被1917年执掌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吸纳,在山西省开始了以村为基层政治组织的乡村治理,其主导的“村治”运动(即普及教育,振兴实业)对山西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使山西变成了乡村实验的“模范省”,铭贤学校早期的乡建活动即受此影响而次第展开。
铭贤学校创立之初,正值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这项活动因与铭贤中学时期“培养博爱济公、服务社会的人”的办学宗旨相契合而得到了孔祥熙大力支持。他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六政”,要求师生在寒暑假深入农村,向家乡父老宣传、讲解“六政”,并办理识字运动及公民训练。为增进效能,还指导学生组织乡村服务团每逢周六周日前往附近农村帮助学校教员办理民众教育等,这对引领农村文化、促进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1922年到1924年铭贤学校又配合阎锡山“村治”改革在太谷开展了以“整理村范协进团”为核心的乡村禁毒运动,对整顿当地不良社会风气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基于当时政局动荡、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的惨淡状况,校园内的师生对校外的现实世界极为关注,他们希望从现实的观察中寻求结论,然后用所得的结论去实验实用的技术。铭贤学子参与社会事业的热情非常高,学校层面也非常鼓励师生参与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服务。1924年铭贤学校校刊社创办的《铭贤校刊》开辟了多个专栏,经常刊登学生关于社会调查的文章。如1924年1卷1期“调查”一栏中刊登了配合阎锡山“村治”改革的《整理村范之报告》《太谷社会生活的状况》两篇调研报告,1924年1卷2期 “批评”一栏中学生王思仪的《我对杨家庄之观察和感想》,1926年3卷1期 “调查”中学生常启源的《我乡婚俗述略(一)(二)》,1927年4卷1期“记述”中学生苗向荣的《我自己改良村制的一个报告》等,反映了铭贤学校对农村社会事业的重视以及铭贤学子改造农村社会的热忱。
这一时期铭贤学校的乡建活动尚处于萌芽阶段,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其乡建活动的内容较为零散,形式较为单一,尚未形成体系;二是其乡建活动过程主要受地方政府影响推进,重在配合阎锡山“村治”改革开展一些乡建工作,尚处在“自觉而不自主”的层面。但即便如此,铭贤学校早期的这些乡建活动还是为当时封闭落后的山西农村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为之后进行全方位的乡村建设实验奠定了基础。
二、铭贤学校乡建活动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高潮。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全国从事乡村工作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1]各类乡建团体纷纷涌现,就其模式而言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等构成的乡村建设主流派;二是教会组织、慈善机构、地方实力派人物开展的乡村建设;三是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国民政府参与或主办的实验县(区)。[2]这一时期,乡村建设者们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对乡村社会做了全方位的设计和改造。他们的乡建模式及实验区各具特色,但就其对中国农村问题实质的把握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来看有两类,一类是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从教育入手,通过“文化教育——乡村社会改造”的模式来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另一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代表人物是卢作孚在四川重庆北碚所实施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的乡建模式,取得了较大实践成就。铭贤学校的乡建活动主要受第一类乡建模式的影响。此外,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掀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也间接加快了铭贤乡建活动的进程,其时有基督教背景的学校普遍进行了调整,社会服务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社会服务作为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社会服务的优先领域逐渐成为教会学校社会服务工作中的亮点,有教会背景的铭贤学校亦在此之内。
在上述背景下,20年代末30年代初铭贤学校教育方向逐渐明朗化,开始朝农业专门学校发展,注重实科教育。1928年开始筹办农科,聘美国欧柏林学院的志愿者穆懿尔(R.T.Moyer)为农科主任。1930年代逐步由农科发展至工科、勤工俭学制及乡村服务科。这一时期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活动有了全面快速的发展,侧重于两方面:
1.开展农工科教学和研究。铭贤学校为发展农科,设立了育种组、经济组、牧畜组、森林组、推广组等,聘用了一批农科大学生及农专毕业生,开始从事作物育种、畜种改良、家畜疾病防治、果树品种引进等初步的科研工作,另外还设有农场、畜牧场、园艺场以开展试验使用。在穆懿尔的带领下,铭贤学校在推广作物优良品种、改进农业耕作方式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铭贤学校在农业及教学科研取得一定成绩后,成立了农业推广组,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同年,铭贤学校筹办工科,聘请李廷魁任主任。学校设有小型木模厂、铁工厂、纺织厂、翻砂厂、印刷厂、肥皂厂等,主要是设计制造和改良农机具,为农业服务。此外,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铭贤学校农科还与太谷县政府合作定期召开太谷县农产展览会,重在展示农业改良产品,推广良种优畜,对推广农业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
2.设立农村服务实验区。1934年至1936年,梅贻宝先生代理铭贤校长,他在任期内积极扩充农工两科,先后两次呈请教育部补助经费共7万元,使得铭贤学校的办学经费大为宽裕,为开展乡村实验提供了经济基础。1934年秋,铭贤学校乡村服务部正式成立。1936年选定太谷县以南、贯家堡附近20个村为实验区,设办事处于贯家堡村,武寿铭任干事,开展了以农民为对象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设总务、经济、教育、娱乐、卫生等股。各股包括很多具体事项,如经济股是成立农业信用合作社,实施小额信贷,举办讲习会,宣讲合作原理、合作经营、合作法规等;教育股是与贯家堡村政人员组成普及教育委员会,设立农民教育馆在全村开展学校式、社会式、传递式教育,制备巡回书箱,按期巡回,以便阅览;娱乐股是在村里设立民众俱乐部、儿童游艺室,请话剧团、晋乐团入村巡演;卫生股是对农民讲授卫生常识,设立乡村诊疗所,与太谷公理会仁术医院合作,定期到村里出诊等。此外还开展了各类社会工作,一是与村公所成立拒毒会、附设戒毒所,规定凡沾染毒品嗜好者,不论男女一律强迫戒毒;二是与金陵大学农科合作,聘请专员分赴各地调查农村社会概况,并联合邻近各县开设农村展览会,提倡作物改良,助益农民;三是邀请燕京大学社会服务系刘志博主持乡村调查,在与武寿铭的合作下完成4.3万余字的《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涉及贯家堡社会、经济、家庭、生活等各方面。
这一时期铭贤学校的乡建活动处于定型发展阶段,亦是其黄金时期,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特色:一是从其农村服务实验区的机构设置和各股分工开展的工作内容来看,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实验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已意识到从全局来改进乡村,解决当时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二是其乡建工作已经走上正轨,并形成了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二者相互辅助、相互促进的较为体系化的格局;三是其乡建活动进入“自觉且自主”层面,形成了有目的、有规划、独立的乡建模式。
三、铭贤学校乡建活动的挫折
1937年5月,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国民党政府国防委员会要求在农工科方面做出成就的铭贤学校筹办农工专科学校。随即铭贤学校成立了农工专科学校董事会,拨出20万美元作为筹建基金,扩建校舍,购置设备。正当筹备工作就绪,决定于1938年春季开始招生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曾一度被国人寄予厚望的乡村建设运动遭受重挫,一系列地域性的乡村建设实验遂告停顿。这其中包括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以及当时各高校、各社会团体的农村实验区,如燕京大学“清河社会实验区”、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惠北民众教育实验区”、黄炎培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苏昆山徐公桥模式”、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的“晓庄模式”等均被迫中止,铭贤学校的太谷贯家堡实验区也未能幸免。
1937年10月山西局势亦危在旦夕,铭贤学校难以立足被迫南迁,至此铭贤师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长途跋涉,之后的18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先后辗转晋豫陕川四省,迁址运城、陕县、西安、沔县、金堂五地。在抗日救国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下,铭贤学子义不容辞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大潮中,积极组织抗日宣传,教民众唱抗日歌曲,在街头公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 《铁蹄下的吼声》《最后一计》《顺民》),举办募集寒衣等的小型讲演会,均收到很好的抗日宣传效果;还在课余时间前往后方医院为伤兵服务,替他们写家信,与他们谈心,在校内轮流为医院裁制绷带,有时还去火车站直接用担架接送伤兵,有的甚至投笔从戎,直接参军。
这一时期铭贤师生历经种种磨难,异常艰辛,但他们从未丧失对中国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心和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心。所以铭贤学校具体的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虽不得不暂停,但是其乡村建设的步伐并未中止:一是通过乡村建设改造农村社会的理念从未断绝,铭贤学人仍然秉持改造中国乡村面貌的信念,积极为储备乡村建设人才而努力。即使是在南迁的颠簸之中,铭贤学校也弦歌不辍,教学工作从未间断。每到一地,铭贤学子或借宿文庙、武庙,或租用当地学校部分校舍,或借用新生活俱乐部等,保证了各年级课堂教学、实验实习、课外作业、考试考查的正常进行,为将来的乡村建设活动积累了人力资源;二是在南迁的过程中,铭贤师生探访了众多农村地区,更为直观的感知了中国乡村实情,对中国乡村实际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些为铭贤学校随后续行的乡村建设活动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三是铭贤学校的南迁之旅同样也是铭贤学校的思想之旅、文化之旅。在迁移过程中,铭贤一直是教职员工、家属、学生一路同行,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一路相随,“文化的种子”一路撒播,乡村建设理念也随之播散。
四、铭贤学校乡建活动的重建
整个抗战时期,除卢作孚主持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坚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外,30年代涌现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各派的乡建运动因频繁的战事以及资金、人力、物力的匮乏或停止或削减或合并,仅剩部分高校因有办学资源为依托,其乡建活动得以延续,如金陵大学农学院迁到华西校园后继续展开农业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齐鲁大学在乡村卫生调查、家政和作物改良方面的工作也仍有推进。
铭贤学校1939年5月在选定四川省金堂县曾家寨为新的校址后,其办学历程进入了又一个辉煌期,1940年秋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开始招生。成立之初就强调“专科之成立,重在造就工农两方面之实用人才,故于实习方面特别重视,对各实验室的设备与实验工厂及农牧场之筹办,更不惜巨资,力求完善”。[3]1943年8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复,铭贤学校又由专科升为本科,成立私立铭贤学院,学制由3年改为4年。学校的两度升级为乡建工作的再度重启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着重展开以下乡建工作:
1.深入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铭贤农工专科和铭贤学院相继成立后,伴随着的是师资力量的壮大、科研设备和厂房的扩充,有助于铭贤师生开展更广更深的学术研究。这一时期沿承以往传统,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融入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中,先后开展了金堂烟叶改良工作、金堂棉业改良工作、玉蜀黎高粱示范实验工作等,对当地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的改良发挥了积极效用。另外,铭贤学校这一时期更注重开展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交流。铭贤学校与国民政府农林部、财政部、中央农业试验场、农业推广委员会、四川省等部门合作进行了多项研究。譬如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兴办肥料试验;与农产促进委员会合作办理陕甘农业推广工作;与财政部四川烟叶示范场合作示范烟园;与农林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合作举办小麦良种示范;受中央庚款董事会委托研究中国草业防治牲畜体外寄生虫;与农产促进委员会举办畜牧兽医讲习班等。[4]
2.重启乡村服务工作。到达金堂后,铭贤学校因抗战爆发而终止的乡村服务工作重新起航。1939年10月在金堂县南七华里的姚家渡乡恢复了社会服务部的工作,并专设经费成立乡村服务团,设立办事处,派人专门负责办理,分总务、抗建、经济、卫生、教育、调查六项。除“抗建”外,基本延续了太谷县贯家堡实验区时的乡建活动内容。“抗建”工作主要是服务出征家属,如代写书信、代洽政府优待款粮、探寻前方征人消息、请求合法免纳各种摊款、征募慰劳品服务抗战军人家属等事宜。
3.实现产学研的三重结合。铭贤学校实用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抗战时期大后方物资匮乏的农村现实迫使学校投资兴建的作物及畜牧实验场、化学工程实验场、机械实习工厂、纺织实习工厂、翻砂实习厂、锻工实习厂等担负了多重功能,除供学生实验实习、培养基本技能外,还生产各种产品以供社会消费,为学校增加收入。据统计,1941年年产稻谷100担、蔬菜上万斤、烟草100担、树苗5万多株,牧场有奶牛、软布来羊、美国纯种猪、来航鸡等优良畜禽,年产牛奶6000磅、羊奶3000磅、特种羊毛100磅。[5]铭贤学校教学实习工厂的实验成果推入市场产生了良好效益。《金堂县志》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铭贤农工专科学校生产的纺织产品有绿色斜纹布、条纹麻纱布、方格布、羊毛制服呢;机械产品有车床、织布机和当时市场上难以买到的风筒、天平;化工产品有硫酸、硝酸、冰醋酸等;酿造实习工厂制出的精酿酱油日产100~600公斤,市场上供不应求。”[6]这些产品为抗战时期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的乡村地区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一线生机。
这一时期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活动处在重建阶段,亦有其特点。其一在农业研究和技术推广方面更为深入,并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农业人才;其二是乡村服务工作具有承继性,虽然工作的基本内容没有大的改变,但其“服务民众”的思想及实践一直贯穿始终,秉承了铭贤学校“学以事人”的校训。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乡村社会建设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铭贤学校近半个世纪的乡建活动贯穿了其办学各个时期(铭贤中学时期、铭贤农工专科时期、铭贤学院时期),亦经历了肇起、发展、挫折、重建四个阶段。它每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点部分折射了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历程,其“服务民众、服务社会”的办学精神在乡村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对改善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重整社会风气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305.
[2] 王景新,鲁可荣,刘重来.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
[3] 民国三十年铭贤学校校务报告[Z].山西农业大学档案馆,铭贤学校档案(86).
[4] 信德俭,温永峰,方亮,等.学以事人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5.
[5] 山西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山西农业大学校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18.
[6]四川省金堂县志编纂委员会.金堂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438.
(编辑:程俐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