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解构与“主体”重建:《百年孤独》互文性分析
2015-03-24李翠蓉
李翠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影响”解构与“主体”重建:《百年孤独》互文性分析
李翠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后现代语境中诞生的理论术语“互文性”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解构术语。既然文本只是一个符号空间,“作者”这个文本的主体就自动“消亡”。然而,如果给予互文性概念一个特殊的参照点,它将成为建构术语。传统的“影响”研究就可以作为互文性的参照点,因为“影响”是从一个作家到另一个作家的、单向的、不可逆的过程,属于时间范式。注重空间范式的互文性能够解构“影响”,寻找作品的原创性,由此重新建构创作主体——“作者”。
主体重构;影响;互文性;泛文本
互文性将文本看作是没有主体的符号,将文学创作消解于能指游戏的空间。互文性处理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非个人化领域,因此带来“作者”这个创作主体的解构:“零度写作”与“作者死亡”。但互文性内在的空间范式及动态性特征,能够对单向的、线性的“影响”研究进行解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主体的重建。而克里斯特瓦的“泛文本”概念使得这种分析能够由理论走向实践。本文将采用上述理论从互文性与“影响”的比较、目标文本的互文性与泛文本互文性3个方面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进行主体重构。
一、“影响”与互文性
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的《西班牙语词典》中“influencia”(影响)的词根为“inflǔens”,是由古典拉丁文的动词“influěre”(流向、流出)演变而成;“互文性”的法语为“intertextualité”(概念首次是用法语提出),同义的西班牙语单词为 “intertextualidad”, 二者均源于拉丁文的“intertextus”一词,前缀“inter”的意思为互相的、彼此之间的,后缀“textus”本意为织物、编织品,因此,整个词语的拉丁文原意即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
从以上的词源学分析不难看出:“影响”由于它的“流向……”本义就决定了“影响”有一个落差,即由先到后、由高到低、由一个作家到另一个作家、由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内在秩序。“影响”研究以作者为研究主体,以事实考据与科学推理为研究方法,对文本进行确定性、自律性、客体化、科学化和中心化的诉求,这是现代语境中对语言象征功能的一种阐释,而在后现代语境中,对文本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互动性、非线性、非中心化的追求则体现在对语言符号化的演绎上,“互文性”这一概念更加适合运用于此种趋势的研究。
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于上个世纪中叶提出“互文性”概念:任何文本均处于一个文本空间,是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的“文本马赛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互文性更加看重空间范式,反对“影响”研究的时间范式,它试图对线性的历史做空间处理,因为线性模式意味着一个不可逆反的过程,意味着权威、因果、源流,互文性研究则“使得源流、传统、继承、影响等一切基于时间秩序的概念彻底失效”[1]。互文性也突破了“影响”研究的瓶颈:“并不能截然将个人才能与本时期作家共用的意象、技法和观念等公共智慧清晰地区分开来”[2]。
互文性概念为文学批评研究提供新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作者”这个创作主体的消解。既然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那么“作者”这个完整主体将不复存在。巴尔特(Roland Barthes)就演绎出“作者死亡论”与“零度写作”等概念,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也声称:“一切诗歌的主题和技巧已被千百年来的诗人们用尽”[3]。与布鲁姆这种“逆反”式诗评一样,互文性这个更加属于现象学范畴的理论,虽然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变动不拘的、开放的拓扑空间,但确实有将文本的意义消解于无限的能指游戏中的趋势。
因为互文性概念蕴涵空间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运用互文性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但若利用互文性对某一种或几种具体“影响”进行解构,则能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作者”(此处指“从一位作家到另一位作家”这个“影响”研究秩序中的后者)这个创作主体。互文性将不再宣告“作者死亡”,而是能够帮助其重生,“泛文本”则是能使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的关键。“泛文本”概念突破“文字”的束缚,不再停留在狭义的“文本”自身,如同德里达对“文本”概念外延的界定,即“包含一定意义的微型符号形式,如一个仪式、一种表情、一段音乐、一个词语等,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非文字的”[4]。
克里斯特瓦是从巴赫金 (Mijaíl Bajtín) 的“对话主义”理论出发,提出“互文性”这个理论,前者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她的理论建构在其泛文本主义之上:“‘文本’、‘另一个文本’或‘引文’等词语在她那里都具有极为宽泛的含义。她所说的‘文本’可以确指一部文学作品,但首先是指一种意义生产过程;她所说的‘另一个文本’可以确指另一部文学作品,但首先是指一切社会实践;各种社会历史文本不一定属于自然语言,但都‘像语言那样来结构’,所以任何符号系统或文化现象(社会实践)都可以看作是‘文本’”[5]。
在目标文本《百年孤独》的“影响”研究中,批评家给加西亚·马尔克斯 “贴上”了卡夫卡、福克纳及海明威等欧美作家的“标签”。《百年孤独》同福克纳作品的互文性更多地体现在故事背景的相似性:“尘土飞扬的道路,炎热而贫穷的村庄,绝望的居民”[6]。故事中所涉及的历史——美国果品公司在拉美建立大量香蕉公司——无异也是使这两位作家作品体现互文性的原因之一。海明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则是“柏拉图式的”[7]:“是一种抽象的叙事艺术的影响:一是语言文字的浓缩,二是生活素材的浓缩”[8]。因为当时刚踏入报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寻求一种简洁、紧凑、明朗的文体,海明威的叙事风格正好符合他的追求。
卡夫卡的影响,更多地是一种鼓励。《变形记》让加西亚明白了外祖母讲的故事其实是“可信”的,是可以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如果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那我也能写出来”[9]。《变形记》的传奇魔幻让加西亚将自己的直接、间接经验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读完作品的第二天,他就写出了自己文学创作生涯的第一个故事《第三次无可奈何》。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影响客观存在,但应该注意的是不应该以“贴标签”这种方式来过度标榜。否则,作品的动态互文性则会被简化为静态的、单向的、不可逆的、线性的“影响”。
《百年孤独》批评过程中的“标签现象”严重到让作者试图完全摒弃“影响”,“批评家们那么顽强地强调福克纳对我作品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竟差点被他们说服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我纯粹出于偶然开始阅读福克纳的小说时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10]。上述事实显然只是加西亚愤怒的情绪表达,真假尚待甄别。因为《枯枝败叶》于1955年发表,而作者1950年2月陪母亲回乡下卖房子时,在轮船上阅读的小说正是福克纳的《八月之光》。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激烈反应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埃尔内斯托·博肯宁(Ernesto Volkening)所论述的“文化殖民”:“这种贴标签的方式表面上为了增加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认可度,建立让人尊敬的文学家谱。但更深层次却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似乎只有像这些有名的欧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才能获得自己的文学成就”[11]。此处的“文化殖民”正是“影响”研究的必然结果之一,因为它的内在秩序为一位作家对另一位作家的“影响”,是后者“原创性”的解构过程。如果想突破这种单一的、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范式影响,则应该采用动态空间范式的互文性解析作品《百年孤独》的创作过程,重建“作者”这个创作主体。
二 、《百年孤独》中的文本动态交织
《百年孤独》(1967)出版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过3部小说与一本故事集:《枯枝败叶》(1955)、《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58)、《恶时辰》(1962)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1962),其中《恶时辰》获得了哥伦比亚当年的埃索文学奖。这些作品与《百年孤独》共同构成了马孔多世界的大拼图,而后者“就是这个拼图游戏中最重要的拼板”[12]。分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预想《百年孤独》与同时期其他作品之间可能存在互文性。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其他作品及《百年孤独》的特殊写作过程。
12岁,加西亚懂得了什么是故事,那就是“一夜之间,外祖父母死了,白蚁把房子毁了,镇子陷入了贫困。仿佛一场破坏性的大风从那里席卷而过似的”[13]。17岁时他萌生将故事写下来的想法,意识到自己能力不够就选择了放弃。5年后,他开始写作《大屋》,草稿一共三百多页,但当时并未结书出版,不过后来的《枯枝败叶》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的大部分故事都源自于此。1967年5月出版的《百年孤独》已经是加西亚对“马孔多”故事的第三次尝试。
尽管《枯枝败叶》就文学成就而言,确实不算优秀,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曾经评论,这部作品作者创作的痕迹过于明显,跟现实的刻意距离让作品中的人物死气沉沉[14],但它第一个孕育了马孔多。后来加西亚直接用它作为短篇故事《伊莎贝拉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的题目。《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与其他书中的马孔多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他书中的马孔多在地上行走,而《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却在梦里飞行”[15]。马孔多的地理位置总是孤立的,气候均为炎热多雨。《蒙蒂尔寡妇》中描写天气的句子是“好像这雨永远也停不下来了”[16]。《百年孤独》中的雨也足足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
除了虚构世界的背景相似,生活在马孔多的人们好像亦能无“纸”界交流。《蒙蒂尔寡妇》中的寡妇在死前见到了格兰德大妈,并向她询问自己的死期;奥雷利亚诺上校也从《枯枝败叶》中介绍信的作者摇身一变成了《百年孤独》里的主角;《星期六后的一天》中出现的寡妇雷贝卡·布恩蒂亚也“有幸”成为《百年孤独》中的“寡妇”,她的死亡是两部作品的描写重点之一,甚至连她的仆人阿尔赫尼达在两部作品中名字都未曾改变。
正是因为加西亚文学创作的这种连续性,使得《百年孤独》与其他作品的互文痕迹随处可见。在这3次的尝试中,我们总能看到相似的人物或相近的人物性格,《百年孤独》中不断武力收敛民众土地的阿尔卡蒂奥·布恩蒂亚,能让我们依稀回忆起《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唐·萨巴斯与《巴尔塔萨尔一个幸运的下午》中的何塞·蒙蒂尔;而坚毅执着甚至可爱可怜的上校则在《百年孤独》和《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出现。就如同哈瑞斯(Luis Haras)评价的一样,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里,“年迈的上校,细心但苦闷的医生,安静强悍的女性形象从未缺少过”[17]。如果说《百年孤独》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期作品互文更多是因为创作经历的同源性,实属作者“无意”为之:因为同时创作《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与《恶时辰》,加西亚就曾无意识地“把一部作品的东西加到另外一部作品中”[18];那么,马孔多与其他作家的虚构世界“相通”则多少是作者“有意”而为。这种互文本身的目的不在于突出“影响”,建立文学系谱,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宽广的互文空间。
《百年孤独》中出现了维克多·休格斯(Víctor Huges)、阿尔特米奥·克罗斯(Artemio Cruz)及罗卡玛多乌尔(Rocamadour)[19],这3个人物分别是阿莱赫·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的《启蒙世纪》、卡洛斯·富恩德斯(Carlos Fuentes) 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及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跳房子》中的人物。借用和重提其他作品中的人物关键不在于转述的过程,而在于转述所产生的效果。让《百年孤独》中的人物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让马孔多和其他虚构世界相通,建立一个跨越书本的、开放的文本交织空间,增加小说的逼真性。如果你相信其他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马孔多里的故事对你来说应该也是“历历在目”;反之,当你怀疑其他作品中的情节时,你会在《百年孤独》中得到“印证”。
加西亚·马尔克斯时而模仿自己喜欢的作家。书中无章节只留空白的写法,相信细心的读者在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惊世之作《佩德罗·帕拉莫》中早已领略;被无数作家模仿过的《百年孤独》的经典开篇,显示作者对时间结构的操控游刃有余,笔者认为,这也应该部分归功于《佩德罗·帕拉莫》,后者的开篇点出了3个时间: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前者的开篇同样给出了3个时间:将来、现在和过去。也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是把《佩德罗·帕拉莫》中的3个时间向前移动了一格。这样才成就了《百年孤独》中的经典环形叙事结构。
三、《百年孤独》与现实互“文”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过一个名为《淹死在电里的小孩》的短篇故事。据加西亚自述,在一个有客人拜访的晚上,灯突然熄了。他们叫来了电工,在维修时,加西亚问道,什么是电?电工回答道,电就如同水,打开水龙头,电就出来了。据此作者创作了《淹死在电里的小孩》。这段创作经历说明作品更多的互文本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泛文本”——一定意义的微型符号形式。
《百年孤独》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是一段不停折磨着他的记忆,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一种感觉的书面陈述。加西亚8岁前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充满孤寂忧愤与鬼魂幽灵的家庭里住着一个故事大王——外祖母,任何鬼怪神奇的故事一经她娓娓道来, 便轻松平凡, 仿佛聊家常似的, 让人“确信无疑”。这段奇特的童年时光成为加西亚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如西班牙作家安娜·玛丽亚·马图特所述,人的成长并不是一个“变大”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尤其是在失去童真之后,人就会开始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有选择性地记忆,不像童年时候,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难以忘怀,所以童年的记忆总是最丰富的,最真切的。这些记忆留在脑海中,不断发酵。而作家如能成功地利用这种内心创作,则有可能写出不朽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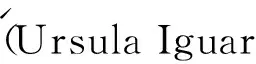
借用身边人的名字是因为作者对他们的性格印象深刻,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家人的名字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因为我觉得他们独一无二,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坚定地认为,我小说中的人物只有在拥有自己独特的、能够与他们的性格匹配的名字之后,才能鲜活起来”[24]。除了人物名字直接取自现实,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也采取“拿来主义”:“奥雷利亚诺继续每天下午和四个讨论者碰头,他们分别叫阿尔巴罗、赫尔曼、阿尔方索和加夫列尔”[25]。除了加夫列尔指作者自己,其他三位都是他现实生活中的文学挚友。同四位年轻文人一同出现在书中的加泰罗尼亚智者,是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位人物。这位于西班牙内战之际来到哥伦比亚的“百科全书式的文人”[26],是巴兰基利亚小组两位老师之一(另一位是何塞·菲尼克斯·富恩马约尔)。
马孔多世界的建立者为名誉而杀人后,一直被此事缠绕,甚至被死者“跟踪”;加西亚的外祖父在千日战争中杀死了战友帕切克(Medardo Pacheco),为此他心里从未得到安宁;瞎眼的乌苏拉在黑暗之中依然能够辨清方向,靠其他感官摸到自己想拿的东西,让家人一度不知道她已经瞎眼;加西亚的姑姥姥佩德拉(外祖父的姐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前提下,能够在黑暗中行动自如”[27]。此外,学钢琴,藏情书在饼干盒中,牡丹花下绣花,制作动物糖和铸造小金鱼均有现实根据。
作品接受现实这个“泛文本”的影响,这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单向,很多时候都能体现其双向性。在《百年孤独》中,作者描写1928年的香蕉工人大罢工时,并不清楚死者的数目,尽管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也未得出正确的数据:“唯一的分歧在于死者的数目”[28]。最后作者“决定”死伤人数为“三千”。有趣的是,2005年,哥伦比亚当局政府举行纪念活动,会议活动的主持者请求到会人员默哀一分钟,以纪念三千死者。很多“魔幻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对《百年孤独》的现实根据很容易认识不充分,因为对拉丁美洲的现实了解不足,更容易把很多“活生生的现实”归结于作者的虚构或夸张。如同加西亚在诺贝尔获奖词中所述的那样,因为他们很难想象比波罗的海海面还宽的亚马逊河河面;难以想象在欧洲只意味着电闪雷鸣的“暴风雨”在拉美的含义:它可以持续5个月,整整几个钟点急促的闪电接连不断,犹如血色的飞瀑,大气在连续雷鸣的震荡中颤抖,雷的炸裂声在无垠的山间激荡;难以想象能在5分钟内煮熟鸡蛋的沸腾溪水;隔空医治病牛的奇象;会跳舞的赤豆;吸引胡里奥·科塔萨尔驻足几小时的美西螈。在如此“富于想象力”的现实面前,加西亚坚持做它的搬运工,因为“我从未想到也未曾能做到任何比现实更为惊人的事,我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借助于诗把现实改变一下位置”[29]。
《百年孤独》开篇父子俩去看冰,那是一桩“盛事”,马孔多人均为之着迷,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并指望用这“凉得烫手的冰砖”建造房子,使马孔多成为永远凉爽的城市,那是因为现实中的巴兰基里亚总是酷暑难挡。生长在孤独落后的马孔多人“少见多怪”的事情还不只这件。吉普赛人的磁铁使他们大为震惊,他们被它“非凡的魔力”所慑服,幻想用它吸出地下的金子;吉普赛人的照相机让他们望而生畏;他们为意大利人的自动钢琴倾倒;美国的火车在马孔多被誉为旷世奇物。但最让他们恼火的还是据此改编而成的电影,因为他们为之痛哭流涕的人物,在一部影片里本已死亡并被埋葬了,却在另一部影片里活得挺好而且变成了阿拉伯人。花了钱来跟人物共命运的观众,受不了这闻所未闻的欺骗,于是把电影院砸了个稀巴烂。
马孔多人看外面世界就如同他乡人看拉美现实一样,“孤陋寡闻”: “高三米而没有屋顶的浴室”、“吃泥土和石灰浆的女孩”、“缝制裹尸布的女人”[30]看似少见,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生活的拉美现实中都能找到依据。哈瑞斯曾经说马孔多既奇怪又熟悉,既特殊又普遍,这是分别从他乡人和故乡人的眼光来看待马孔多的。
结语:
《百年孤独》的互文性解析并未走向非个人化,而是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创作主体”的重建: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寻找依据。因为动态的、空间范式的互文性在没有任何“支点”,或者说是“参照点”时,容易走向“一切皆互文”的无限泛化趋势,甚至导致相对主义或者不可知论。但当我们通过对目标文本的“影响”研究——福克纳、海明威及卡夫卡——的解构,以此作为“支点”,则能运用互文性理论建构“作者”这个本已随着互文性理论“消解”的文本主体。
[1] 秦海鹰.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J]. 法国研究,2006-12-30:20.
[2] 李玉平. “影响”研究与“互文性”之比较[J] . 外国文学研究,2004(2):4.
[3] 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2.
[4] 段慧敏. 作为创作技法和阅读手法的互文性[J]. 国外理论动态,2010-03-04:90.
[5] 秦海鹰.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J]. 法国研究,2006-12-30:17.
[6] 朱景冬,选编.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0.
[7] Haras, Luis. Los nuestros[M]. Buenos Aires: Ed. Sudamericana, 1977:398.
[8] 陈众议.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47.
[9] Gustavo, Juan. Entrevista con García Márquez[Z]. 1981-04-28:6.
[10] 朱景冬,选编.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3.
[11] Volkening, Ernesto.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o el trópico desembrujado[J]. Rev. de la Cultura de Occidente, N° 40, 1964:273.
[12] Haras, Luis. Los nuestros[M]. Buenos Aires: Ed. Sudamericana, 1977:418.
[13] 朱景冬,选编.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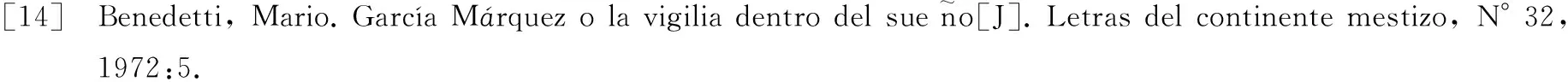

[16]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Los funerales de la Mаmá Grande[M]. Buenos Aires: Ed. Sudamericana, 1962:9.
[17] Haras, Luis. Los nuestros[M]. Buenos Aires: Ed. Sudamericana, 1977:397.
[18] Guibert, Rita. Entrevista con García Márquez[Z]. Edi. Novaro, 1974:14.
[20] 陈众议.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12.
[21] 陈众议.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08.
[22]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Vivir para contarla[M]. Barcelona: Debolsillo, 2005:38.
[24]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Vivir para contarla[M]. Barcelona: Debolsillo, 2005:51.
[26]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Vivir para contarla[M]. Barcelona:Debolsillo, 2005:111.
[27]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Vivir para contarla[M]. Barcelona: Debolsillo, 2005:72.
[28]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Vivir para contarla[M]. Barcelona: Debolsillo, 2005:61.
[29] 朱景冬,选编.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6.
[30]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Vivir para contarla[M]. Barcelona: Debolsillo, 2005: 37, 79, 70.
Deconstruction of “Influ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ntertextuality inOneHundredYearsofSolitude
LI Cui-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e intertextuality, emerged in postmodern times,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a deconstruction term, considering that every text is in a sign space, the “author”, the subject of the text disappears. Nevertheless, if the intertextuality possesses one special point of reference, it could be a construction term, and the traditional criticism concept “influence” plays the role. Its interior order: from one writer to another transforms the “influence” into an irreversible one-way temporal concept. The spatial concept intertextuality deconstructs the “influence”, pursuit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work and finally reconstructs the subject of the text——the “author”.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 Influence; Intertextuality; “Text”
2014-11-06
李翠蓉(1985~),女,汉,四川绵阳人,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拉丁美洲文学。
I106.4
A
1672-4860(2015)02-002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