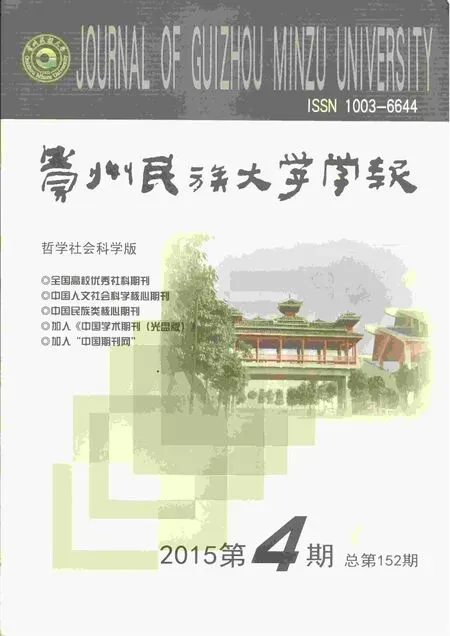论我国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法律限制①
2015-03-20银洁
银 洁
(贵州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领域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代位求偿权亦进行了规定,其经历多次修订,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与保障,但是其规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带来了实践困境与理论争议。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其在适用中的诸项法律限制,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权利行使的名义限制
代位求偿权的取得是依照法律的规定,那么在实践中便首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保险人以谁的名义进行权利的行使。在该制度出现的早期,各国在实践中往往采用的是以被保险人之名义进行求偿,但是后来伴随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各国基本上都在立法与实践中采用双重模式,即保险人既能够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进行索赔,也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索赔。[1]P332-333
我国《保险法》伴随着实践发展而多次进行修订和完善,但是在此问题上始终未能给予明确的规定。唯有我国《海上保险特别诉讼规则》在此问题上予以明确,其以条文形式明确要求保险人以自己之名义行使请求权,但是这种规定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在立法未能明确解疑的情况下,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主张在法理上应以保险人自己之名义来进行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立法的模糊造成了实践的混乱,各地采取的标准和做法不统一,有的以保险人名义,有的则以被保险人的名义。
本文认为应当在立法中明确以保险人自己名义行使该权,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该权实质是一种债权的转让。对于该权的性质,学界观点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 债权拟制转移说;2. 赔偿请求权说;3.债权请求权转移说。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具体而言,是指第三人因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造成被保险人损失而产生的债权关系,保险人在支付完保险赔偿金之后取得对第三人的请求赔偿权,这种请求赔偿权自支付完保险赔偿金之时起,求偿权就由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于是,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以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原债权为基础的债权请求权。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债权,保险代位求偿权只是一种相对权,保险人只是获得一种向第三人请求一定给付的权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确定的利益,并且这种权利对第三人的财产不具有优先性,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其他债权人一样,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故而,由于保险人的理赔而在其理赔范围内取得了向第三人进行请求损害赔偿的代位求偿权,实际上是被保险人享有的在理赔金额范围内的债权发生了转让,由保险人取得该债权,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唯有债权人发生了变更,由被保险人变为保险人,所以保险人是该债权的权利人,而不是代理人,当然应以其自己的名义进行主张。
第二,我国相关立法已经做出了此种规定。例如我国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其第94条、95 条中便以明文形式对此予以了规定和明确。
最后,从权利行使的结果和程序上分析,也应当对此予以明确。因为在实践中保险人行使该权之后,获得的赔偿由其自己享有,如果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那么赔偿归属又属于保险人,在逻辑上说不通。此外,在被保险人的损害较大,而且保险人所支付的理赔金额不足以弥补全部损失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在剩余部分的范围内依然享有针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此同时,保险人则在理赔金额的限度内享有该权利。如果其行使该权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那么便会出现在法庭审判中同一名义下两个请求权的问题,法院在裁决中的表述便会出现问题。
二、权利行使的对象限制
代位求偿权是发生在特定的相对人之间的,在确定了权利人以何种名义行使权利之后,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就是厘定该权利的对象。该问题在表面上似乎十分清晰和明确,然而其界定中却存在着棘手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对于该权利的行使对象,各国在立法中都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我国在立法中也做出了相似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如果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是故意造成《保险法》第60 条第1 款之情形,那么保险人可以对其主张该权,但是如果其不是故意,那么就不能对其主张该权。这表明,我国对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也进行了限制。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一种观点认为,“组成人员”前面的“其”字,应理解为前面的“家庭”的代称,所以也就是家庭成员或者家庭的组成人员,这种理解是将“组成人员”作为对家庭成员的扩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采更广义的理解,“家庭成员”不只限于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并相互负有扶养义务的人,例如配偶和父母、子女等,还应当包括具有姻亲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以及民事法律上的近亲属,例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2]“组成人员”前面的“其”应认定为“被保险人”的代称,意即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主要是指被保险人是法人的情况下,与被保险人具有劳动关系、委托关系等密切相关的人,例如雇员或者代理人等。本文认同第二种观点,主要的理由如下。
第一,在理解“家庭成员”时应注意两点。首先,法律作此限制规定在于防止从被保险人的共同利益人被追偿,导致责任重叠。所以,为了避免被保险人一边获得保险人的理赔,一边又要对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进行赔偿,法律应当将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来扩张“家庭成员”。其次,“家庭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虽然民法对于近亲属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但是这不足以解释“家庭成员”。而且社会实践是复杂多变的,不应从形式上进行简单的限定,而应根据法理和立法目的,作出符合被保险人利益的解释。
第二,在理解“组成人员”时应把握两点。首先,这一表述是针对被保险人是法人的情况,应将其理解为与被保险人关于保险利益具有某种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成员,例如从事法人事务的雇员、代理人等。因为这些人从事法人的事务,履行自己的职务,与被保险人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如果代位求偿得以进行,那么就会造成被保险人一边得到保险理赔,另一边又要被求偿,那么保险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损害也得不到填补。其次,这种“组成人员”还应当进行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受到保险人求偿的限制,因为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数量大,事务多,存在很多与被保险人并无共同利害关系的人,对此不应当限制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总之,在认定和把握这一法律表述的时候,应以财产保险基本理念,即“损失填补”为基础,把握维护被保险人利益这一目的,维持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利益平衡。
三、权利行使的时效限制
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请求权的行使涉及相对人的利益,从法律定分止争、诉讼证据收集、债务人利益保护等多个角度的考量,创设了时效制度,我国也在民法中规定了请求权的时效制度。在一定的期限内,权利人能够对相对人予以请求,但超出时效期限之后,相对人便获得了时效上的抗辩,能够有力的阻碍请求权的实现。代位求偿权的实质也是请求权,那么根据理论与逻辑上的分析,其也应当适用时效制度。可以说保险人在按照法律取得该代位求偿权之后,就需要按照时效制度,在一定的期限内向第三人求偿,当超出该法定期限后就可能会遭到第三人的时效抗辩,而无法实现求偿。但是我国目前仅仅规定了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理赔的诉讼时效,却并没有规定代位求偿权的时效,对此本文作出如下分析。
时效制度的适用存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时效的长短,其二是起算点。由于该权利与被保险人对致损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对该权利时效的期间与起算点具有关键意义,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保险代位求偿权是由法律规定而取得的,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在界定时效长短上,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当根据具体的保险标的,标的不同则适用不同的时效期限。我国《民法通则》中也规定了多种时效期限,例如1年、2年,还有20年等。对于起算点则应当界定为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之时,只有在此情形下,保险人才具有行使权利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就无法行使。[3]P138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对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的适用,应完全依照被保险人对直接致损的第三人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这种观点主张,该权利实际上是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债权转让,两者是同质的,只是权利人进行更换,所以时效的期限和起算点都应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致。也就是说,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起算点是从被保险人知道损害赔偿义务人之时,而期限也与其相同。
对于这两种观点,本文赞同后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该权利的实质是一种债权的转让,既然是转让,那么保险人所承接的权利必然与原来的权利是一样的,唯独是权利主体的变更,所以在时效上也应当是承接原来权利所有的时效,并无差别。另外,在权利的转让中,任何人都只能转让自己享有的权利,而不能超出该限度之外,所以时效也必然不能超出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期限。故而起算点和期限都是与被保险人对致损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这种时效的界定能够促使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尽快理赔,更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利益。因为代位求偿权是在保险人理赔之后获得,而时效则往往在损害之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如果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怠于理赔,那么将会使自己处于代位求偿的不利状况之中。所以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实践中保险人理赔缓慢的问题,更好的保障被保险人的权益。
第三,这种时效的界定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致损第三人。第三人由于某种原因而负担损害赔偿责任,从其角度出发,时效的适用当然应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并没有特殊之处,不能因为有保险人的存在而对其时效利益予以变更,更不能因为保险人的存在而损害其时效利益。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合同关系,是内部关系,并不能影响第三人的责任负担,也不能加重其时效的负担。
四、权利行使的范围限制
依据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来源不同,主要分为法定说和约定说两种,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都采取“代位法定主义”的立法模式,将保险代位求偿权性质定义为法定权利,因而,即便在合同中并没有进行约定,也不会影响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在我国,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权的权利是基于保险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而并非需要保险人被保险人事先的约定,因此,即便保险合同中并未对此做出相关的约定,只要法定的条件得到满足和实现,保险人便能够对第三人提出相关的赔偿请求。
那么,保险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既然为法定债权移转,二者是否完全相同呢?本文认为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前者主要是基于被保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其仅限于财产权,并且其权利范围应该受到保险给付数额的限制;如果是基于人格权、身份权而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人身权利的专属性质,是不适用代位求偿权的。本文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责任的方式不同,其二是赔偿的范围不同。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对此有所规定,根据不同的侵权客体和程度可以分为多种责任形式,例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而且能够返还财产的就应当予以返还,能够恢复原状的就应当予以恢复,两者都不可能的时候就要进行赔偿,此外,因为损害而导致被保险人产生其他损失的,依照法律也要进行相应的赔偿。如果是因为违约而产生的保险标的遭受损害,那么第三人还可能要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但是前者权利则仅限于赔偿损失,并不包括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等。[4]P321
对于第二个问题,二者也不完全一致。首先,前者的范围是限制在保险责任之内的,如果是保险责任之内的损失,那么保险人在理赔之后能够在此范围内行使代位求偿权,如果造成损失的原因并不在保险责任之内,那么保险人不负担理赔责任,那么也就不存在代位求偿权。其次,在金额上,两者也存在差异。第一,如果第三人对被保险人进行了全部损失的赔偿,那么被保险人的损害就得到了填补,此时保险人就不用再对被保险人进行理赔,也就不会产生代位求偿权。第二,如果在损害发生后,由于法律的规定或者第三人具有的赔偿能力有限,第三人仅对被保险人进行了部分损失的赔偿,那么被保险人的损害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填补,此时应当发挥保险的利益弥补和风险分散的功能,由保险人对剩余部分的损失予以理赔,其操作方法是将被保险人已获得的部分补偿先予扣除,然后再将保险金额的差额予以补足。在这种情况下,该权利便存在于这差额之中。第三,如果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重大,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或者损失超出了保险金额的上限,那么保险人所能够支付的赔偿并不能填补被保险人的全部损失,此时该权利的范围限于理赔金额,超出部分则属于损害赔偿之救济。[5]P352
结论
保险代位求偿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其实质是债权请求权移转,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应当以保险人自己的名义,应正确把握法律对于其行使对象所作出的缩限,在时效制度上,应当认定其与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相同的。在责任的范围限制上,代位求偿权只有损害赔偿一种形式,数额范围亦有所限制。相信随着我国实践与理论的不断发展,我国保险法的相关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
[1]邓成明.中外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
[2]王林清,杨心忠. 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限制理论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1,(5).
[3]梁宇贤. 保险法新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覃有土. 保险法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詹昊. 保险市场规制的经济法分析[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