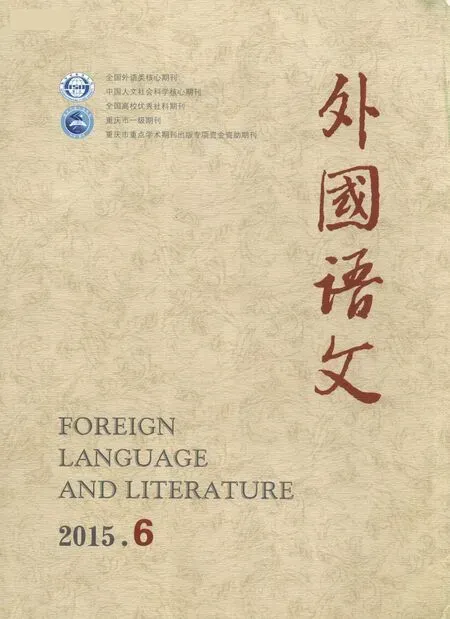共生固恋的母女情怀——论林芙美子《放浪记》中的母女书写
2015-03-20杨本明董春燕
杨本明 董春燕
(1.上海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3 2.四川外国语大学 应用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
林芙美子(1903-1951)是日本昭和时期的著名女性作家,其代表作“《放浪记》(放浪記,1930)被认为是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在母女关系的书写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水田宗子、野田敦子,2014:58)。在《放浪记》这部小说当中,林芙美子对共生固恋的母女关系进行了补写,填补了文学叙事中母女关系书写的空白,解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日本女性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学者伊里加蕾指出:“女性必须重视与母亲的关系,因为一旦我们身为女人,我们总是母亲。”(邱小轻,2010:116)女性主义学者一直重视母女关系书写的重大意义,认为女性书写是女性群体确证自我身份的重要范式,女性要通过自我书写“言说女性的语言,言说女性的愉悦”(冯海青,2013:81)。在昭和文学史上,对母女关系的书写和探讨也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小说这一文学领域里,女性要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和进行性别确证,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以林芙美子《放浪记》中的母女书写为切入口,检视林芙美子文学中共生固恋的母女关系图景,探讨林芙美子文本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1.从“母子书写”到“母女书写”
母女关系是家庭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家庭伦理结构中最亲密的血缘亲情之一。母女关系书写本应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之一,但是当我们用审视的目光来检阅经典文本时,我们不难发现文学文本中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成为文学叙事中被忽略的空白之页,而与之相反的是母子关系书写成为文学叙事的滥觞。这是因为宗法父权社会的伦理文化赋予了母亲父权制代言人的身份,“父严母慈、夫义妇顺”是儒家人伦秩序的核心(徐亚玲,2014:103)。尤其是在父亲缺席的家庭当中,母亲既是一家之主,又是宗法秩序的替身。她作为具有最高权力的封建家长,承担着维护和代言父权秩序的职责。由于长期以来父权秩序的规训和对封建宗法伦理观念的不断内化,母亲“必须按照男权社会的规范条律来处理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血缘父亲缺席和父亲无作为的家庭,母亲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强势的父权文化,顺从‘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以此来治理统治家庭结构,确立家长权威”(刘传霞,2007:106)。这种母亲的角色往往肩负着双重使命,其一是作为“父亲”的替身把儿子形塑成父权性别秩序接班人,以此达到“母以子为贵”的目的,确保自己在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结构中的地位:其二是要把女儿培养成知书达理、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借以确保父权秩序在另外一个家庭权力结构中得以持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家庭中,母亲已经不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主体,而是一个被父权秩序和封建宗法伦理观念所同化和扭曲的母亲,她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相夫教子、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责任,成为父权秩序的代言人,异化为“菲勒斯母亲”的文化角色。在文学叙事领域,“慈母孝子”的文学叙事长期占据着文学书写的舞台,文学创作者也毫不吝啬地挥洒了大量的笔墨,母子关系叙事成为文学叙事之滥觞。
另一方面,母女关系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之一被驱逐出文学叙事的谱系,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他者。这主要有两种原因使然:其一,千百年来,日本社会的权力延续主要奉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在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家庭伦理结构中,女性从一开始便被排斥在权力序列之外。女儿在家庭当中只是短暂客居的一员,在等级森严的家庭权力序列当中,她们要从父、从兄,女性没有自我言说的机会和权力。而一旦嫁为人妻,她们便成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原先家庭的权力序列当中被隔离,继而被迫开始另外一种从夫而居的生活方式,这时“父权”和“夫权”顺利实现了权力的交接。这种母女关系在家庭权力序列当中是无足轻重的,她们对家庭秩序的影响非常少。其二,母女关系的书写被强大的男权文化所遮蔽,男性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力,学习汉文典籍、舞文弄墨成为公卿大夫炫耀学问、陶冶情操的特权,女性被驱逐出这一领域之外,她们只能把玩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平假名”,借以打发深宫内院当中寂寞的光阴。
进入近代以来,男性作家也在不经意间浮光掠影般地涉及到母女关系的叙述。比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有岛武郎的《某个女人》。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中,母亲阿政替代了丈夫成为选择女儿夫婿的决策者,内海文三的职位变更直接决定着他在阿政心目中的地位,而在强势的母亲的干预之下,阿势没有进行自我选择的权力,她只好随母亲的意志而移情于本田升。同阿势不同的是有岛武郎的《某个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叶子对母亲进行了彻底的背叛。母亲信奉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叶子对此嗤之以鼻,并给予了殊死的反抗,叶子企图通过叛逆父权代言人——母亲的决定来实现对父权的颠覆。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位男性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母女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一个延伸,母亲代替了宗法家族中父亲这个发号施令者的角色,母亲承载的仍旧是父亲的意志。所以进入近代以来,女性的自我解放往往都伴随着对母亲说教的反叛和抗争,她们通过揭露婚姻家庭生活中母亲生存境遇的悲苦和不幸来展现母亲被遮蔽的女性欲望,并借以控诉被父权秩序所摧残的母亲的凄苦人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男权规范的母亲角色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母女关系的否定,而是通过对被男权化和现实功利所腐蚀伤害的母女关系的审视,来重建被父权制所放逐和割裂的母女关系。”(刘传霞,2007:107)女作家不厌其烦地对母女关系进行书写,正是要重建一种更为和谐、更为亲密的母女关系,通过对母亲主体性地位的确认来获取对女性自我主体性的追认。当然,女性作家对母女关系的书写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父权协助者——母亲这一角色的反叛方面,如果母亲这一角色本身就具备反抗男权,勇于冲破性别秩序藩篱的个性,那么对母亲的叙述就会呈现出高度的自我认同和共鸣。《放浪记》中的母女关系书写无疑属于后者,林芙美子通过对和谐的母女情深的书写,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共生固恋的母女关系图景。
2.对父权的缺位审判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里加蕾指出:“母女关系作为社会伦理关系当中的重要一环经常被忽视,成为文学叙事中的黑暗大陆,父权秩序摧毁了母女关系这一最能体现关爱和丰饶的感情纽带,母女关系成为父权文化中缺失的支柱。”(邱小轻,2010:116)伊里加蕾认为“母女关系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互惠关系,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而显然这种和谐关系的建立其前提是必须对强大的父权话语体系进行颠覆”(邱小轻,2010:117)。为此,斩伐父权、颠覆父权秩序的话语体系成为女性书写首先需要面对的课题。
林芙美子在《放浪记》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母女间共生固恋的和谐世界。在这部作品中母亲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自立意识的女强人,她拒绝父权秩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对陈腐的封建秩序和清规戒律不屑一顾。她为了追求自己的恋爱和婚姻自由,勇敢地冲出家庭的重重阻挠,同父亲私奔并辗转于九州各地。婚后不久,父亲经商发财,他开始讨厌母亲,两个人开始不断争吵。由于感情的不和,父亲娶了二房。母亲并没有忍气吞声、低三下四地维持这段伤痕累累的婚姻,她带着“我”像娜拉一样离开家庭,依靠四处行商来养活自己,自觉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作为行动上的传教者和精神上的引路人,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给予“我”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启迪,为“我”树立了女性自主自立的精神楷模。作为女儿“我”毅然斩断了与父亲之间的精神纽带,拒绝同他见面,而与母亲却始终固守着和谐的、共生固恋的母女情怀。“我”和母亲之间结成共同反抗父权秩序和性别压迫的攻守同盟,这种建立在相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性别体验基础之上的母女关系,对于颠覆父权性别秩序、建立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放浪记》中对父亲的缺位审判成为女性确立主体地位的重要方式。虽然在三部《放浪记》中都有“我”和继父的对白,但是父亲这一代表封建等级秩序的强大力量被刻意地加以淡化,而“我”和母亲则成为言说的主体走向前台。家里的一切事情都由母亲做主,在第一章中继父一登场就成了无足轻重,甚至是软弱无能的人。他“小心翼翼,过分的忠厚老实,同时异常粗野,像个山里人,他的人生多半掩埋在辛劳之中。母亲带着我嫁给了养父,打那之后,我仿佛过上了无家的生活。无论走到何处,皆有置身于小小客栈的感觉”(林芙美子,2011:3);父亲小肚鸡肠,经常和母亲吵架,我甚至盼望着“只要继父和母亲分手,我就和母亲一起过。母女两人拼命工作养活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都让“我”看不惯,“我真的讨厌继父。他是个懦弱的人,总是在母亲的点拨下生活。这种没出息的男人,真让人上火”(林芙美子,2011:357)。
我们不难发现在林芙美子的笔下传统文学叙事中高大、勇敢、威猛、无所不能的父亲形象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父亲角色总是很“小心翼翼”“忠厚老实”,并且有一点“性格粗野”,有时甚至要依靠“我”和母亲的接济才能生活。传统文学文本中所向披靡的父亲突然间变得畏畏缩缩,一无是处,懦弱、没出息、难以自立,甚至连养家糊口都勉为其难。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知道父亲的角色经常被赋予过多的想象和社会期待。作为丈夫或父亲,男性这个角色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角色,他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家庭当中发号施令的主导者。价值二元论无疑是维护男性“硬汉”形象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要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必须颠覆这种价值观念上的二元制。林芙美子在《放浪记》中对母亲的书写不惜笔墨,而对父亲的书写大都一笔带过,这种“父亲缺位”的叙事模式具有“审父书写”的性质。“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却经常成为缺席者,他只存在于“我”的创伤性记忆当中或偶尔在他陷入经济困境之时有所提及。这种张扬女性自身,淡化“父亲”的书写模式不仅使女性有了自我言说和自我表达的机会,也使“父亲”(父权)在女性的言说中成为被言说、被叙述的客体,一个非主体性存在的“他者”。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对“父亲”进行缺席审判,消解了父权的强大话语体系,也兼具了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色彩。
3.共生固恋的母女情怀
另一方面,林芙美子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上面,对母亲的书写,对母爱的讴歌,对母女间浓浓情义的描写也是《放浪记》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放浪记》中,林芙美子将都市女工对母亲的思念、爱恋和依赖毫不隐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将长期以来一直被遮蔽的母女关系图景重新还原到文学叙事的场域。林芙美子和母亲都经历了不幸的婚姻,被丈夫和父亲抛弃的共同生命体验让她们结成了精神上的同盟。“母女这种同质的生存处境,使她们之间有一种依恋,更重要的是,有一种女性本质的同情和支持。母亲的生存意义是为了孩子们的成长而捐弃一切,包括属于自己的任何幸福和权益。她同情女儿在本质上是同情女性,希望女儿不要成为‘绣花枕头’,而要‘书读得好,有学问’。母亲把自我的压抑和焦虑化成对女儿的爱护和同情,使女儿的命运不成为母亲命运的复制。母亲的生命与女儿息息相关,汇入女儿的人生河道,女儿的生命中也充满对母亲的爱恋和同情。”(王芳,1994:9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浪记》描写的不是女儿对母亲的反叛,更多的文本被用来叙述母女之间共生固恋的和谐关系,一种哀伤而不失温馨的母女情怀,母女间的书信往来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东京打拼,但是并没有忘记远在他乡的“母亲”,通过书信的交往时刻保持着和她在感情上的沟通。每当“我”收到“母亲”的来信,“我的心中涌出一股爱怜之情,真想马上靠在母亲怀中”。虽然“我”收入微薄,每天“从早干到晚。也只能拿到六角的报酬”(林芙美子,2011:31),但是每当母亲经济拮据的时候,“我”都会给她寄钱,尽管“我”自己经常食不果腹,居无定所。
在《放浪记》中,“母亲”和“我”互相给予对方经济上和感情上的支持,母女俩通过信封里夹钱的方式给对方经济援助的次数多达11次。如上文所述,“我”作为女工在工厂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每天只能拿到六角钱,除去每月5元的房租,工资所剩无几,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但是即便如此,一收到母亲的求助信,“我”立即把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积蓄全部寄给母亲。这种母女之间的通信其实早已超出了经济援助的范畴,她们通过来往的信件建立起母女之间坚不可摧的精神纽带,表达了母女间共生固恋的母女情怀。作为离开故土,前往异乡寻梦的年轻女性,母爱成为她们倾诉内心苦闷,抚平情感创伤的最佳良药。当她们在陌生的都市撞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的时刻,母爱依旧是供她们随时停靠的港湾,因此对母亲的眷恋和找寻让女性作家能够浓墨重彩地去描写母女间的浓浓亲情。
4.母女间共同的性别体验
笔者认为林芙美子的成长和创作都源自母亲对她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她本人也意识到母亲的性格和人品对自身的影响,在《放浪记》中才能流露出对母亲高度的感恩和认同。严格来说《放浪记》不单单是一部小说,还兼具了自传的性质。林芙美子坎坷的生命体验和复杂的情感经历为《放浪记》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综观林芙美子的人生历程和她母亲的人生轨迹,我们不难发现这对母女人生经历的高度重合,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婚恋生活方面,两者都经历了多次感情的波折。林芙美子的母亲林菊是鹿儿岛樱岛人士,家里经营一家温泉旅馆,在当地虽然算不上是名门望族,但是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而其生父宫田麻太郎则是来自异乡四国的卖货郎,一穷二白,所以他们的婚姻受到林家父母的强烈反对。而林菊则具备了萨摩藩女子敢爱敢恨的性格,偷偷跟宫田麻太郎私奔,两人一直辗转到山口县下关市才安顿下来。后来宫田麻太郎的经济状况好转,开始拈花惹草,娶了一名叫作阿浜的小妾,不久林菊和阿浜之间产生了矛盾,在风雪交加的大年夜,林菊和女儿被逐出家门。林菊的第一段婚姻可以说同林芙美子的第一段感情生活极为相似,《放浪记》中登场的“岛上的男人”其原型就是林芙美子的初恋情人冈野军一,冈野军一家族是因岛地区的富庶人家,所以他同林芙美子的交往一开始就受到冈野家人的反对,虽然林芙美子多次亲赴冈野家求情,最后都是无果而终。这段感情经历给林芙美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但是也让她认识到在婚姻生活中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所以想要成为暴发户的梦想一直伴随着她。同田边若男的第二段婚姻和野村吉哉的第三段婚姻也没能持续多久,最终都因为男性的移情别恋而告终。从这三段不幸的婚姻和父亲纳妾这件事当中,林芙美子意识到女性在婚恋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男性的不可靠,同时也意识到只有母亲才是不离不弃、相依为命的人,所以她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在她的笔下才能够得以自然地流露,特别是在婚姻上接二连三的不幸让这对母女同病相怜,《放浪记》文本中叙述的母女情深不得不说源自女性本能的相互同情。
其次,在经济生活方面,两者都表现出高度的自立意识和超然的态度。即使是在食不果腹的困难时刻,林芙美子和母亲都不曾向男性低头和乞讨,而是依靠自我的努力和母女间的相互扶持度过难关。在第一部《放浪记》的开始部分,父亲纳妾之事,母亲并没有委曲求全,向父亲乞讨,继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是在大年夜携同女儿出走。在那个年代,离开封建家长制的家庭庇护就意味着放弃被男性抚养的权利,女性很容易面临残酷的生死困境,但是母亲并没有妥协,而是选择了自食其力。这种不依靠男性,自食其力的基因遗传给了林芙美子。在东京最初的那几年,她每天都面临着饥饿、失业和孤独的折磨,但是林芙美子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没有因生存问题而堕落为“艺妓”或“娼妇”,而是依靠摆地摊、借债、下工厂等最辛苦的工作养活自己。林芙美子母女俩在这一方面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她们同样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但又同样没有迷失自我,依靠自身的努力挣扎在城市的边缘。
由此可见母亲作为林芙美子精神上的楷模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引路人,她无疑成为林芙美子性别成长之路上的航标,她的婚姻观、经济观、人生观给林芙美子以巨大的影响。母亲以激烈对抗的方式反对父权秩序对婚姻的干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母亲独立的性格和不屈的抗争为林芙美子搭建了一条通向女性独立自主彼岸的涉渡之舟。同样在林芙美子的文学书写当中,“我”冲出了性别秩序的樊篱,放弃了对男性依附的幻想。“我”从农村来到现代都市东京,施展了女性长期被压抑、被遮蔽的人性潜能,在自我与社会的不断冲突和融合中确立了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认同,实现了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证。
5.结语
郭春林认为:“私人写作是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关怀,是私人拥有地远离了政治和社会中心的生存空间,是对个体的生存体验的沉静反观和谛听,是独自站在镜子前,将我视为他者的审视,是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喃喃叙述’,是心灵在无人观赏时的独舞和独白。”(郭春林,1999:59)那么,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母亲不存在主体性的男权社会”(王俊英,2014:102),林芙美子的同时代女性的言说是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人生命体验的自我检视,“抹去了父权制度给予母女关系的虚假光辉”(李芳,2014:77),她以前所未有的表现方式发掘了昭和时期普通女性被淹没的历史,再现了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女性欲望,彰显了日本近代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开辟了女性写作的私语空间。
在都市当中遭遇人生的不如意之时,与母亲之间建立的共生固恋的精神纽带帮“我”抚平精神上的创伤,母亲独立自主的坚强个性鼓励着“我”不断克服人性的软弱。林芙美子在《放浪记》当中建构的和谐的母女关系补写了传统文学叙事中对母女关系叙事的空白之页,解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为女性群体挣脱性别秩序羁绊提供了现实的方策。
[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冯海青.论卡特对萨德的戏仿与颠覆[J].当代外国文学,2013(4):81.
[3]郭春林.从“私语”到“私人写作”[J].文学评论,1999(5):59.
[4]李芳.渐行渐远的悲歌[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4(2):77.
[5]林芙美子.放浪记[M].魏大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刘传霞.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的政治叙述[J].晋阳学刊,2007(6):106.
[7]邱小轻.主体间性与母女关系的社会伦理解构[J].求索,2010(8):116.
[8]水田宗子,野田敦子.制度の外部を志向する新しい女性像[J].現代詩手帖,2014(4):54.
[9]王芳.论现代女性文本中的母女情节[J].求索,1999(4):99.
[10]王俊英.女性主义主题下对《春风秋雨》的解读[J].电影文学,2014(17):102.
[11]徐亚玲.《红楼梦》中的母子关系与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J].时代文学,2014(6):103.
[12]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