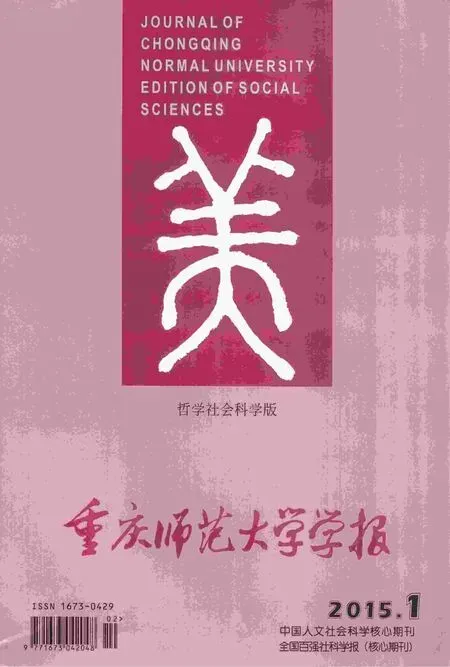由蛮夷到华夏:试析周秦之际巴人族群身份的变化
2015-03-20刘力郗海芸
刘 力 郗 海 芸
(1.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族群(Ethnic group或ethnicity)是指人类历史以来区分我族及“他者”的分类方式之一。就民族学上言之,主要是指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体,也称族团。人类学者则更为强调“族群”作为“人群主观认同之结群”。[1]13诸如“华夏”,“并非由共同血缘、语言与文化播衍所形成的人群,而是由人们之‘主观认同’所构成的群体”,这个主观认同概念,也就是“华夏认同”。[2]31“华夏”作为一个想象的血缘共同体,其的出现与演变实与早期政治国家同步,即随着地域国家治域的扩展,华夏族群的边缘(或华夏成员)亦处于不断变迁中,显现了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华夏族群的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撑的。本文拟以周秦之际巴人族群身份的前后变化观之华夏族群与政治国家的同步性。
一、由“南土”到“蛮夷”
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巴人活动的是商代甲骨文,其中记录了商王武丁及其夫人妇好征伐巴方的事情。[3]199周初,巴亦曾作为“友邦冢君”随同周武王参加牧野之战,充当先锋,“歌舞以凌殷人”。战后巴被周王赐爵位以“子”,“武王既客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4]2因之成为西周之“南土”,“武王克商……巴、濮、楚、邓 ,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
作为“南土”“远国”的巴与西周王室似保持了较为友好的政治联盟关系。《逸周书·王会篇》就曾记载周成王在洛阳召开诸侯大会,巴人进贡比翼鸟的事情。其时的盟会,不仅是西周王室威权的彰显,“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昭公三年)。同时也是与会邦国与周王室关系亲密的显现。此后,巴人以巴子国身份向周王室缴纳贡物。“巴国向周王室缴纳的贡物就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等物”[5]5。其时对于西周王室而言,巴为“远国”更多的是一种较之于中原邦国在地理位置上遥远的如实描述而不含夷狄蛮荒之鄙弃寓意。
之所以如此,在于其时为周所克的殷商与西周自身还皆是一种政治联盟体,商王与周天子只是其势力范围内各邦国的共主。此时,由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之诸侯贵族各成族落,各祀其祖、其神,尚未形成一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群体。[2]38换言之,其时的华夏意识尚不强烈,而所谓的夷狄也尚未包括鄙弃成分,亦即是说早期的夷狄观并不含有文化歧视与种族歧视的成分。所谓华夏、东夷之名概就地理方位而言,并无褒贬之意,华夏不过亦是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族称而已。[6]120如“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为东夷之人却任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且杀掉治水无功的夏族首领鲧,这一切并未招致民怨:“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亟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史记》卷二《夏本纪》)其后,舜推举治水有功的禹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人,同时任命辅佐禹治水的商族首领契为司徒,掌整个部落联盟的教化,也并未招致四牧十二岳的质疑。而禹年老之后,部落联盟首领的继承人选也并未局限于华夏族,而是选定东夷族的首领益,亦未见华夏族以华夷之论予以否定。
然而,随着西周王室的衰微,乃至最终为犬戎所灭,“这个事件,成为东方诸国的一个重要历史记忆。‘戎狄’从此完全成为‘异族’的代名词”[2]42。东迁后的周王一方面失去了对于所封邦国诸侯们的实际管控权,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其所封诸侯国在与周边蛮夷戎狄争夺生态资源以及领导权的战争中的旗帜,亦即所谓的“尊王攘夷”。在这一征战过程中,“早期周所封诸侯开始自称‘夏’、‘华’或‘华夏’,以别于他们心目中的蛮夷戎狄”[1]183。同时,东方诸侯因共同的忧患意识而团结起来抵抗戎狄的入侵,以期维护、争夺其资源领域边缘,于是作为“人类资源竞争与分配的工具”[1]5的族群认同——华夏认同亦开始出现。
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作为族群的身份确认,是指成员对于自己所属族群认知和情感依附。有学者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而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而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又来自“共同族源记忆”造成的血缘性共同体想象。[1]4华夏作为集族群、政治、空间与文化于一体的族群,其认同的形成不只依赖共同的“边缘”,更依赖共同的“起源”、共同的“族源记忆”。这“起源”便是可以让所有华夏产生同胞手足之情的“根基历史”。春秋战国时,随着诸侯邦国之间以及诸侯与蛮夷戎狄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在此过程中,“黄帝”作为“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产物,逐渐成为华夏之祖先。[2]43
随着“华夏认同形成后,所有自称华夏的人群都以‘族源’来证明自己是华夏”[1]129。即是说,如果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或拟图跻身华夏之列,就得让自己的族群有家族之“姓”且家族祖源能与黄帝、炎帝后裔血脉相联接,而不享有此血缘性“祖源”的族群则被鄙弃为蛮夷戎狄。在此过程中,巴因着地处偏远,一方面开始从政治序列上脱离周王室,“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且“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4]3进而加入了诸侯争地以战的行列。同时,较之于其时中原诸侯邦国日渐强化的华夏认同——黄帝祖源谱系,巴族却流传着廪君传说的记忆。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此传说最早见于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世本》。清人对古《世本》的辑佚现存八种,其中的七种都引录了“巴人廪君五姓”的传说与历史。如此详细的记述,一方面反映了巴人早期的社会状况,是巴人重要的集体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则显现了其时的巴人有着别于中原华夏认同谱系的古老的祖源记忆。由此,政治序列上与中原邦国的疏远甚至相互为敌以及族源传说上与黄帝(或炎帝)后裔缺乏血缘相连,伴随春秋战国日渐强化的华夏认同意识,巴亦开始由周之“南土”而被鄙弃为西南蛮夷。这在《世本》中都还可见一斑。《世本》著者收录整理系于巴郡、南郡之下,并缀之以“蛮”。而巴郡设置于秦灭巴蜀后的第三年,即周赧王元年(前314),南郡设于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显然,其时的巴虽然在行政序列上进入了秦之郡县,但还是被视之为华夏之外的“蛮”。
二、开土列郡:秦对巴的更化
战国末期,七国争雄。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携“横扫六合”的统一态势在争霸中胜出,由此秦不仅由西戎之国华丽跻身为华夏,还随着其政治上的一统而逐渐成为华夏在政治上的象征。为了加强对巴的管控,从公元前316年始到公元前221年的近百年中,秦不仅屡修栈道,穿越秦巴山地,通过汉中,到达巴蜀,从而加强与该地域间的联系。还在巴推行开发与更化,从而在加速巴从行政序列上隶属于中央集权的同时,更是推动其与中原文化习俗的交融,最终使得巴“染秦化”而“安之”。
首先,借助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更元九年),巴、蜀两国发生矛盾,巴国统治者向秦国请兵伐蜀之机,秦先是出兵灭蜀,“十月取之,遂定蜀”(《战国策·秦策》)。随后又趁势“执(巴)王以归”。作为独立方国的巴国在历史上宣告结束,成为秦国的附庸。为加强对巴属地的控制,秦将本国施行的郡县制移植于巴,开始在该地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惠王后元(或称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秦在原巴国之地设置巴郡,“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置巴郡”,后“(周赧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4]29在巴郡下面,秦又分置一些县。虽然具体数目不详,但可考者有六:一是江州,“巴县附郭,古巴子国都也。秦置江州,以巴郡治焉”[7]2980;一是垫江,垫江曾为巴国重镇,有“别都”之称,秦灭巴后,置垫江县属巴郡;[8]103一为鱼腹,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载:“奉节县附郭,秦置鱼腹县,属巴郡”[7]2959;一为朐忍,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七载:“开州,秦汉之代为巴郡朐忍县地。”[8]104一为阆中,阆中是巴国最后的都城,秦置为巴郡属县,《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八载:“阆中县,附郭,秦县,汉属巴郡。”[7]2919又据《蜀中名胜记》卷二十四载:“阆中本秦旧县,张仪伐蜀所置。”一为枳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涪)州城,本秦枳县城也。”[8]10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秦所置巴郡还包括“宕渠”一县。[9]609较之于之前西周邦国分封的世袭,秦所施行的郡守、县令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郡县制的施行,不仅使得君主在这些行政区域内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边远地区族群对于中央政权的归顺与认同。
不仅如此,秦还在巴地仿照咸阳修筑城池,构筑营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巴郡,张仪筑有“江州”,“其中心在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上至小什字之间”[10]。同时还筑有阆中城,《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五载:“《(元丰)九域志》云:阆中古城本张仪城也。《图经》云:秦司马错执巴王以归阆中,遂筑此城。今仪庙存焉,谓之张丞相庙。”[8]105这些“与咸阳同制”城池的修筑,使之既是统治者居住、统治的中心,又是工商业荟萃的繁华闹市,更是控制巴广大地域的军事重镇,且使得巴地与中原地区在行政规制上更趋一致。体制上的更化,使得巴由春秋战国的一个诸侯国转而被纳入到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之中,且较早的被纳入了未来秦帝国的治域之内。
其次,在巴地实行较为优厚的政治经济政策,藉此推动巴人对于秦政权的认同。“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此处虽然还是以“蛮夷”视巴,但却对于“君长”的巴贵族保留了其对本族的相当支配权,且给予其“世尚秦女”的恩宠。此外,规定巴民统一享有“爵比不更”,且可以以之抵罪,较之于其他族群无疑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除却“世尚秦女”“爵比不更”此类政治上的优待,秦对巴还施予经济赋税方面的优厚政策。对于巴人头目,每年平均出赋二千六百一十六个“半两”钱,而巴民户则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幏,《说文解字》释为:“幏,南郡蛮夷賨布。”依照云梦秦简《金布律》可知,八尺为一“布”,八丈二尺为十又四分之一布,而“钱十一当一布”,共折合钱一百一十三个。[8]109而关中居民则是“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史记·货殖列传》)比较之下,巴人每岁要少缴纳八十七个钱。而巴人每岁交三十镞鸡羽,也就是缴纳三十支夹于箭杆尾端的野鸡翎,这对于以渔猎为主的巴人并非难事。
此外,在秦人与巴人关系纠纷的处理上,更是明显的给予巴人以偏袒,“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4]4这是秦在巴地推行的羁縻政策,旨在保持蛮夷地区的稳定。秦的这些羁縻之策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在实施上述政策之后,史书载“夷人安之”。“安之”既是巴地社会秩序安定的写照,更是巴人对于秦政权的归顺与认同。
再次,通过移民徙徒加速对巴文化习俗上的更化。向巴蜀大规模移民是在秦惠文王时。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军先后灭蜀、巴,后以巴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统一六国后,始皇除了将地方豪强、六国贵族及其后裔迁居关中外,还将一大批富商大贾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迁到南阳、巴蜀等边远之地。“(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4]35。
这些关中地区的大量移民迁入巴蜀,不仅极大的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巴蜀社会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加速了巴蜀被纳入中原华夏圈的步伐。随着关中的秦汉王朝为巩固后方或安置流民相继大规模移民巴蜀,以秦汉为政治象征的的华夏语言、文字系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逐渐对巴蜀产生极大的影响,巴蜀民众开始日渐“染秦化”:“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家有铜盐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豚牺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4]32-33这种较之于政治上的认同更为深层次的习俗认同、心里认同不仅增进了巴人与中原华夏族群在心里上的亲密度,而且也加剧了彼此间的趋同乃至认同。
三、祖源变更:跻身华夏之域
公元前221年,秦专制中央集权帝国建立,其也成为华夏族群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1]125。一方面,与“大一统”帝国相呼应,作为中原族群指称的“华夏”也开始由春秋战国时的多元结盟向一体化过渡。另一方面,“当一个新国家成立时,为政者总是希望各族群放下根基性的族群感情联系,而团结在造成国家群体的公民联系之中。”[1]18对于新生的秦帝国而言,以政治治域版图为限尽可能扩大华夏认同的边界,将更多族群纳入华夏之列,从而以共同的华夏认同实现对于帝国政权一统的认同,这无疑是一有效途径与手段。要获得一个族群的认同,最为核心的在于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共同的祖先,“人群以共同族源来凝聚认同,而认同变迁又由改变族源来完成。因此,强调、休整或虚构一个族源历史,对于任何人群都非常重要。”[1]54
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到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巴国故地的民众由于秦对其长期的政治经济改造和文化变革而逐渐“染秦化”,在文化模式方面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11]从性质上来看,这是由一种作为独立王国形态和民族性质的文化,向作为秦汉统一帝国内的一种地域形态和以秦汉文化为符号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的转化。[12]笔者以为,这种“染秦化”亦或是“以秦汉文化为符号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均说明了其时经过近百年更化的巴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乃至心里认同诸方面与中原华夏的渐趋接近。
在此视域下,无论是基于巴自身拟图位列华夏之域的期盼亦或是秦帝国为政权一统所需而将其视为华夏,对于其时的巴而言,要实现由蛮夷到华夏的族群身份转变,就必然涉及到对于自身族源记忆即祖源传说的改变,即要将有关巴族群的族源传说与华夏的黄帝(炎帝)血脉支系进行沟通。
关于巴人祖先开始与华夏始祖相关联见诸于《山海经·海内经》,其载:“西南有巴国。太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亦有:“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对于这些记载,有学者认为,其时帝启都安邑,南距巫山一二千里以上。其统治尚未达到长江流域。启派孟涂之说难以令人置信。很大可能是后来史家受华夏正统思想的影响,对非华夏集团的首领常常冠以华夏统治集团中某种官职的称号,借以显示“一统”局面。孟涂这位巴人的首领被称为“夏后启之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8]6-7
随着大一统秦帝国的建立,关于“巴”祖源传说亦有了新的历史记忆版本: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
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於涂山,辛壬癸甲
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
铭存焉……巴国远世则黄、炎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
卫也。[4]2
在这一新的族源记忆中,巴不仅在“人皇始出”即为“九州”(九囿)之一,而且也是黄帝、高阳之支脉,改变了的记忆族群从血统上打通了巴与华夏之间的内在相连。对于这一改变,顾颉刚先生曾明确提出是“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因为原本巴蜀“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13]而承认这一改变的意义则在于承认巴的华夏身份,“承认巴蜀统治家族的血缘与政治权威皆来自以黄帝为隐喻的中原华夏,如此也便是宣称巴蜀为华夏之域,域中之人为华夏之人。”[2]70故有学者以为,由巴的族属嬗变开始,其已是“内诸夏”范畴,不属于“外夷狄”的对象了。[14]
如果说郡县制的施行,使得巴由一方邦国开始变而为巴郡,藉此进入秦帝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序列,并渐趋实现对于帝国的政权认同;而巴祖源传说的这一改变,显现的则是巴人在文化心理乃至于情感上的认同变迁。祖源记忆作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能起到凝聚族群的重要作用,人们也据此进行族群认同或排斥。黄帝作为中国古史传说中最重要的英雄人物,在战国至西汉初已被确立为华夏的始祖。[2]43-45而巴族通过找寻一个新的华夏祖先,不仅实现自身族群由蛮夷向华夏的合理化转变,同时也表明了其的华夏认同。
秦末战乱,原东方六国旧地烽烟四起,社会秩序大乱,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遭到破坏。唯有原秦国腹地关中、汉中和巴蜀一直安定如初,既没有爆发反秦的农民起义,更没有出现将军和郡守的反叛。有学者指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则在于百姓在心理上形成的对于故国的认同。[15]正是基于这种对于帝国政权的认同以及对于华夏族群的认同,使得其后的巴(蜀)成为秦汉帝国牢固的后方基地。
要之,春秋战国以降,随着大“九州”、大一统观念不断出现,“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夏意识也渐趋形成且强化。随着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使远在中原外缘的西部、南方边陲,在传统上被华夏人视为戎、蛮的秦、楚等国,也通过政治统一战争,进入了华夏族群与政治国家的行列。这种以统一天下为使命的争霸战,虽然是以军事的血腥手段,但是,通过由诸侯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直接推动了华夏族群一体化的进程。其结果是除了建立了华夏政治大一统国家外,也空前加快了华夏族群一体化的融合进程,华夷民族的界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族群的界限向四周大大推移。[16]随着秦大一统帝国的开创,华夏的族群界限与范围则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进一步扩展。
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血缘想象共同体的族群——华夏,其的族群边界依托于中原政权治域边界的扩展而扩展。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华夏也开始由春秋战国时的多元走向帝国视域下的一体化。巴由“蛮夷”至“华夏”族群身份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央集权帝国政治一统视域下华夏渐趋一统的产物与反映,由此也彰显了传统中国与华夏族群的同构性,亦即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华夏的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4][晋]常璩.华阳国志[O].济南:齐鲁书社,2012.
[5]贾大全,陈一石.四川茶叶史[M].成都:巴蜀书社,1989.
[6]陈志刚.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本属性:中原王朝陆基性国土防御体系——以封贡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内部组成、运作规律为中心[C]//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7.
[8]管维良.巴族史[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6.
[9]马白非.郡县制·上[C]//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琦看.古代的重庆[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1).
[11]段渝.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J].中国史研究,1999,(1).
[12]段渝.论战国末秦汉之际巴蜀文化转型的机制[J].中华文化论坛,2005,(3).
[13]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M]//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4]黎小龙.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J].民族研究,2004,(3).
[15]孟祥才.论巴蜀在秦汉统一大业中的作用[J].三峡学刊(四川三峡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4,(2、3)
[16]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J].历史研究,2011,(3).